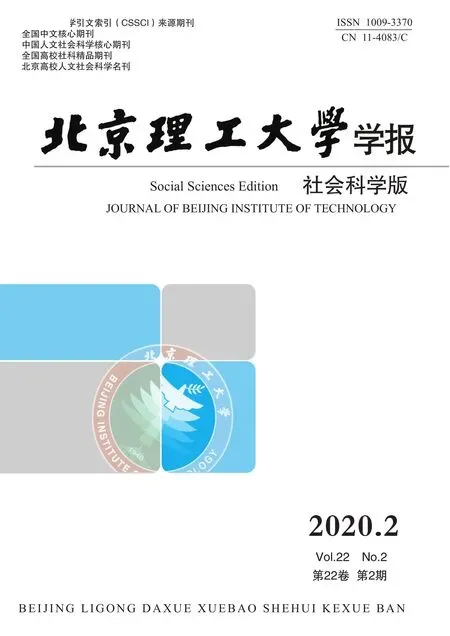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王晓红,胡士磊,张 奔
(1.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哈尔滨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的[1],典型表现之一是中国许多城市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为改善环境质量,中国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如为改善空气质量,政府先后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安排大量专项资金用以重点支持黄标车淘汰、散煤替代和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等工作。为改善水质量,政府出台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推行“河长制”。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环境信息公开和对地方官员污染防治工作的考核问责。然而,许多居民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成效并不满意,如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两成的受访者认为空气质量并无改善甚至仍在恶化[2]97。公众对政府污染防治不力的担忧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是否可以被信赖”的讨论[3]88。加之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传统社会所具有的“差序格局”的“熟人信任”正逐渐演变为“陌生人信任”,而由于新旧信任观之间缺乏较好的衔接机制,导致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4],在此背景下,政府信任首当其冲,广大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事件层出不穷[5]。在此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已超越环境问题本身并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生活议题,从而可能深刻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2]98。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是任何政治系统稳固和有效运行的根本保障[6],低的政府信任度不仅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引发社会动荡,也会增加社会运行成本。而政治参与能够增强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形式,它能够起到“政治安全阀”的作用,有助于加强社会稳定[7]。因此,政府信任和民众的政治参与问题始终为学界和政界所关注。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危害已经得到诸多研究的证实[8]2[9],然而,由于有关环境污染与民众对政府信任和民众政治参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很少,环境污染是否危害政府的公信力和抑制民众的政治参与行为目前尚不明晰。
基于此,本文实证研究了环境污染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力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环境污染是否危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二是不同环境污染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三是环境污染是否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较之以往的相关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考察了居民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而非聚焦离大多数居民日常生活较远的环境污染灾害[8]1-28或全国层面一般性环境污染严重度[10]34-43[11]1-52[12]78-95的影响,由于居住地环境状况与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针对性更强。第二,不同于已有研究笼统考察环境污染状况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本文通过将环境污染细分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洞悉了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信任影响的差异,从而得到已有研究未能揭示的新发现。第三,除了聚焦环境污染对居民政治态度(即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本文还分析了环境污染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视角更全面,有利于更加深入地揭示环境污染对居民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政府信任和居民政治参与有关研究成果,为政府加强和改进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污染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政府信任是公民对政府即便在没有连续的检查和监督下也将“做正确的事”,运作产生出与公民的期待相一致结果的判断或信念[13-14]。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例如,王学义和何兴邦[2]97-108考察空气污染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感知的空气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Gong等[8]1-28实证研究环境污染灾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环境污染灾害负向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孙伟力[10]34-43、刘朝林[11]1-52、邓明和仇勇[12]78-95分别考察了全国层面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与政府信任间的关系,均发现公众的环境污染感知抑制了他们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以上研究认为,环境污染能够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不同于其他事物如转基因食品等的影响,环境污染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且被广泛证实的,它会强化居民对自身患病和死亡风险的感知,激发人们对责任归属的识别和讨论[2]98[3]90。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公民和政府间的关系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政府在获取公权力后理应履行代理人的职责[15]。环境权是基本和重要的人权[16],保护居民的环境权、保障人们在健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居民对环境污染状况的感知直接影响其对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价,进而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此外,居民环境污染状况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还会因民众的社会互动过程而得以强化,即居民对当地环境污染状况的感知越严重,其与家人、朋友、同事或网友讨论环境污染问题就越频繁,而社会互动过程往往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蔓延[2]98,从而强化人们对政府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不得力的认知,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得到进一步削弱。其次,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会提升居民对环保问题的敏感度和关注度,进而提升居民的环境意识,而居民环境意识的提升会提高其对更优质环境质量的期望,从而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提出更高要求[2]99,“高环境治理水平要求”和“低环境治理能力现实”的差异会越发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居民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假设2.居民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
假设3.居民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假设4.居民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尽管居民居住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都会弱化居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然而,不同环境污染类型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差异。相较于水污染,空气污染治理对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配合程度的要求更高,这是因为造成空气污染的污染物流动性更强,能够很容易地随风传播到其他地区。例如,有学者研究发现,2006年4月北京强降尘事件的降尘饱和烃主要来自中蒙边境和毛乌素沙地,而北京周边贡献的份额很小[17]。因此,一个地区的水污染(如湖泊污染、水库污染、沟渠污染,大江大河污染除外)可能只需要当地政府或周边地区政府的努力,而空气质量的改善往往需要全国各地区甚至他国的共同努力,这就凸显出中央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的顶层设计能力和进行统一调度、指挥和督导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纯净的空气这样的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而纯净的水这样的地区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应由地方政府负责[18]。正因为如此,居民可能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环境治理责任产生不同的判断和定位,即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而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居民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
假设6.居民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
(二)环境污染与居民政治参与行为
居民居住地环境污染越严重,居民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评价越差,而且环境污染还会增强人们对政府腐败行为的感知[19],强化人们对政府施政能力和服务水平的质疑。例如,一些居民会认为,某些环保官员在环境治理方面慢作为、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将环保资金中饱私囊;也有一些居民认为,环保部门行政人员能力不足、履职不当。事实上,中央政府下拨的环保专项资金被贪污、挪用和侵吞挥霍,环保官员因履职不力被问责和查处等现象屡屡见诸报端[20]。而当人们感知政府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时,他们对政府政策的认同度可能会降低,表现出更低的政策遵从行为,参与政治活动(如参与基层民主选举)的意愿和热情也可能会减弱。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居民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假设8.居民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二、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模型构建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典型的离散型排序数据,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不适用,考虑到因变量的数据特点,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Airpollutioni表示居民i感知的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Waterpollutioni表示居民i感知的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Xi表示控制变量向量;ε1i为随机扰动项;α0、α1和α2为待估参数;γ1为待估系数向量。
Trust*i表示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潜变量,是不可观测变量,它与可观测的政府信任度Trusti的关系如下
其中,μ1<μ2<…<μ4称为切点,均为待估参数。
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参与与否)是典型的二分类数据,因此,本文采用Probit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Airpollutioni、Waterpollutioni、Xi的含义同上;ε2i为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β0、β1和 β2为待估参数;γ2为待估系数向量。
Participation*i表示不可观测的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潜变量,它与可观测的居民政治参与行为Participationi的关系如下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微观数据来自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始于2003年,此后每1~2年进行一期,但由于只有CGSS2010同时调查了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和其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随机选答模块,仅出生于1月、4月、6月和8月的调查对象回答),所以本文选用CGSS2010作为数据来源。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覆盖了全国31个省 (市、区),获得11 785个样本量,应答率71.32%[21]。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后,获得有效样本3 284个。
本文使用的宏观数据(各城市人均GDP水平)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个别地市(湖北恩施、云南大理、新疆喀什)的数据缺失,通过查阅相关省份统计年鉴、地市统计年鉴或统计公报获得。
(三)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第一个因变量为居民对政府信的任度,分别包括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参考已有研究[10]37[22]652,通过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您对于中央政府、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来测度,居民的政府信任度被具体设定为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和完全可信五个类别,分别赋值1~5,值越大表示居民对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
本文第二个因变量为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参考已有研究[23],通过问卷中对应的问题“近三年,您是否在居(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来测度,选项为“投过票”(赋值为1)和“没有投过票”(赋值为0)。
自变量为环境污染状况,包括空气污染状况和水污染状况。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在您居住的地方,空气污染(或水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选项包括“一点也不严重”“不太严重”“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分别赋值1、2、3、4。与此同时,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纳入总体环境问题严重度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在问卷中对应的问题为“根据您自己的判断,整体上看,您觉得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否严重?”选项包括“根本不严重”“不太严重”“既严重也不严重”“比较严重”和“非常严重”,分别赋值1、2、3、4、5。
遵循已有研究[2]101[8]7[10]37,结合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本文纳入若干控制变量,其中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访者实际年龄的自然对数值)、性别(男性=1;女性=0)、受教育程度(没有受过任何教育=0;私塾=1;小学=2;初中=3;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技校=4; 大学本科或专科=5;研究生及以上=6)、婚姻状况(已婚/分居未离婚=1;未婚/同居/离婚/丧偶=0)、宗教信仰(信仰宗教=1;不信仰宗教=0)、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1;其他=0)、个人收入(受访者个人年收入加1的对数值)、主观幸福感(很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3;比较幸福=4;完全幸福=5)、互联网使用强度(从不=1;很少=2;有时=3;经常=4;总是=5)、居住地类型(居住在城市=1;居住在农村=0)、所在区域(包括“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受访者居住在该区域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区域划分按照国家统计局最新标准,即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和琼 11 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晋、吉、黑、皖、赣、豫、鄂和湘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渝、川、黔、滇、藏、陕、甘、青、宁、新、桂和蒙 12 个省(市、区),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元)的对数值。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为防止异常值的干扰,回归分析时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缩尾处理。
图1和图2分别展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和城、乡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平均信任度。由图1可知,就中央政府信任度而言,东部地区值低于中部地区值,而中部地区值低于西部地区值;就地方政府信任度而言,西部地区值最高,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由图2可知,农村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城市居民。此外,无论是分区域来看还是分城乡来看,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均高于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验证了一些学者所发现的当前中国所存在的“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12]85[22]652[24]。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分析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O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M1~M3、M5~M7汇报了模型的回归系数,M4、M8汇报了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考察对居民完全信任政府的影响)。由表2模型结果可知,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单独考察空气污染或水污染的效应时,无论是空气污染(M1、M5),还是水污染(M2、M6),都对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当统一考察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效应时,研究发现,空气污染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却不显著(M3、M7);水污染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均产生负向影响,但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更显著(M3、M4、M7、M8),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从而假设1~假设6均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也揭示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一是居民年龄、政治面貌和主观幸福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年龄越大、主观幸福感越强及党员身份的居民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越高,与已有研究[12]87的发现相一致,即居民年龄越大,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越高,党员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也高于非党员。二是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现有研究[2]103[12]87[25]结论相一致。三是男性居民、已婚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分别比女性居民、未婚居民、无宗教信仰的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低,但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无显著影响。四是互联网使用强度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的影响不显著,与现有研究[10]39结果一致。不同于传统媒体,互联网受政府管制相对较少[26]。而且,根据负性偏向理论(Negativity Bias Theory),负性信息比正向和中性信息对大脑的情绪处理有更大影响[27],因此,为博眼球和增加点击率,互联网媒体偏向于报道一些容易引发轰动的新闻,如官员的腐败新闻等[28]。因此,居民使用互联网越频繁,其接触各类政治相关负面消息的可能性越大,加之居民与中央政府距离较远,获取的信息相对有限,互联网场域中各种负面信息的传播和交汇很容易使居民对中央政府的工作产生强烈的负反馈[10]41,从而降低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五是人均GDP水平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不显著。人均GDP越高的地区居民对中央政府可能有更高的期望,对政府工作的要求也越高,而现实中政府政务工作可能未能有效满足居民的期望,从而降低了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此外,相较于东部地区居民,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较高,这与描述性统计部分的研究发现一致。
接下来考察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模型结果可知,就总体样本而言,无论是单独考察空气污染或水污染的效应还是统一考察二者的效应,空气污染、水污染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绝大多数居民已经建立起较好的权利意识,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行使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环境居住地的环境污染现象还能激发广大居民的环境抗争和维权意识[29],期望通过行使基层民主选举权利更好地保障自己的环境权[30]。特别是,由于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农村居民可以通过行使基层选举权选出自己满意的村委班子成员,左右乡村工业项目选址和去留,以更好地保护乡村环境和防治环境污染。
控制变量方面,结果显示,居民年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互联网使用强度对其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居民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政治参与,已婚居民、有宗教信仰的居民比未婚居民、无宗教信仰的居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倾向性大,而互联网使用强度越大,居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倾向性越低。人均GDP水平对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济越发达,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就越高,与已有研究[31]的观点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东部,但西部地区居民比东部地区居民具有更高的政治参与度,这与一些研究[32]的发现一致,可能的解释为西部地区居民的政策遵从意识较强,大多数居民会按照政策要求行使自己的投票权,而东部地区居民思想意识更加开放、多元,政策遵从意识相对较弱,从而更可能因工作等事项选择放弃自己的投票权。此外,东、西部地区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可能并非是线性的。出于相类似的原因,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表现出更高的政治参与度。

表2 环境污染状况对政府信任影响的有序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表3 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影响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二)分区域和分城乡的回归结果
前文考察了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包括空气污染状况和水污染状况)对政府信任(包括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和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并得出了一系列研究结论。然而,上述研究结论针对的是全体样本,对于不同居民群体研究结论是否依然适用有待考察,为探究由全体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在不同群体层面是否有细微差异,接下来分别基于不同地理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和不同居住区(城市、农村)来深入考察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4、表5和表6所示。

表4 环境污染状况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分区域的回归结果)

表5 环境污染状况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分城乡的回归结果)

表6 环境污染状况对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分区域和分城乡的回归结果)
由表4和表5可知,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主要表现在东部区域、城市区域,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经过长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和城市区域居民对中央政府工作的要求和期待更高。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及城市和农村均有表现,表明中国各地区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此外,表4和表5的结果再次验证了 “居民会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环境治理责任产生不同判断与定位”的结论。
表6表明空气污染状况对绝大多数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对小部分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M2、M5)。相比之下,无论是分区域还是分城乡来看,居民感知的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居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更换变量和更换样本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CGSS2010问卷还询问了居民对全国层面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看法(随机选答模块,仅出生于2月、9月、11月和12月的调查对象回答),本文选取此变量作为居民感知的环境污染状况的替代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感知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度产生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产生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状况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但研究也发现,其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从而基本支持了前文的结论①此处未列出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相比较可知,选取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程度比作为自变量比选取。全国层面的环境问题严重程度作为自然变量能够更加深入地考察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勾勒出更加全面、细致的图景。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及其政治参与问题始终是学界和政界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环境污染状况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目前存在“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格局,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其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2.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其中,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这表明居民会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不同环境治理责任产生不同的判断和定位。
3.空气污染损害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城市区域,而水污染损害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在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均有表现。
4.居民感知的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促进居民进行政治参与。
5.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而互联网使用强度的增大会降低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也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但不会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产生显著影响。
上述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即环境污染问题早已超越环境问题本身,而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社会生活议题,环境污染治理关系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社会稳定。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要下大力气进行环境污染治理,确保工作做到实处,重塑居民对政府治污的信心,使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得到稳固与提升。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尤其要重视中国东部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工作及各大城市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治理工作,为此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行之有效的环境污染治理规划,充分发挥整体指挥、综合协调的作用,并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督导,有效化解地方政府间环境污染“碎片化”治理困境;地方政府要尤其重视本地区的水污染治理工作,有效承担起环境污染治理责任人和执行者应尽的责任,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各级政府要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增进民生福祉,增强民众的主观幸福感,进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政府要强化对民众感受的调查研究,及时了解民众对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感知评价和他们的环境诉求,以更好地改进自身工作。远离民众感受的政府工作安排是没有意义的,政府环境治理效果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33]。建议未来让民众参与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评价中,开展“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价。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政府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既能丰富政府环境治理的智力资本,也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环境决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34],既能增进民众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的认知,也利于强化政府部门环境治理工作的动力。
第三,政府要建立公正透明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加强与民众的沟通交流,使民众更好地知悉政府各项环境政策和政府为治理环境污染所付出的诸多努力,降低民众对居住地环境污染的焦虑感,强化互联网场域中政府环境治理信息与居民感知环境改善状况主观评价间的共振,进而增强民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正反馈。
本文研究发现,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损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证实了已有相近研究的结论[2]97[8]1[10]34[11]31[12]78。与此同时,本文发现居民感知的居住地不同环境污染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而居民感知的居住地水污染严重程度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比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此外,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不会抑制居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这是本文的创新发现和特色之处。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质量的指标具有多元性,本文仅引入了主观指标(居民感知的居住地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程度),以后的研究需要引入客观指标(如PM 2.5年均浓度、工业废水排放量等)。二是本文没有分析环境污染对居民的政府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机制,未来会在参照相关研究[2]97-108[12]78-95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