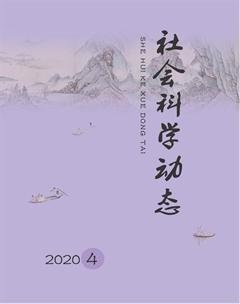晓苏小说的悲悯叙事
摘要:在中短篇小说集《为一个光棍说话》中,晓苏坚持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不论是高校题材中对知识分子寒冷刺骨庸碌日常的刻画,还是乡村题材小说中对油菜坡人情冷暖的描摹,始终尊重平民生命形态的复杂性,保持其小说的人情温度。作家通过对叙事人的精心选择,以及对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工匠般的雕琢,展示小说人物复杂幽深的内心,最大程度地唤起读者同情乃至共鸣,使其作品保持极高可读性的同时,蕴含着一种古典的人道关怀的温暖。
关键词:晓苏;人文关怀;内视点;叙事节奏
一
自“零度写作”概念被罗兰·巴特提出之后,“为……说话”似乎成了一个禁忌的句式,现代形态的文学拒绝如此鲜明的作家立场,这在靠近所谓客观性的同时也丧失了古典文学所具有的人情关怀,在直观的阅读效果上,它将文学推入冷酷的境地,尽管其本意是想揭露冷漠而非依附。与很多耽溺于“零度写作”效果的小说家相比,晓苏的创作显得不那么“摩登”,他的小说从来不缺少也不回避温度,其最新小说集《为一个光棍说话》或可带我们感知这种久违的“为……说话”的人情温暖。
《为一个光棍说话》主要收录了晓苏1990年至今在《山花》杂志上先后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作为“锐眼撷花”文丛之一,2020年1月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这本集子中,不论是高校题材《春寒》《平衡》《黑箱》中对知识分子寒冷刺骨庸碌日常的刻画,还是乡村题材《为一个光棍说话》《镇长的弟弟》《松油灯》等小说中对油菜坡人情冷暖的描摹,晓苏总是以悲悯的情怀观照着笔下人物的世俗生活和生死悲喜,或金刚怒目,或菩萨低眉,使人触目便觉厚重的悲悯之意,小说的人情温暖也由此生发而来。
在晓苏早期创作中,金刚怒目式的批判更加显而易见,他笔下的故事大多是直接乃至粗粝的,情感上也基本是“但凡世间无仁义,人人心中有梁山”① 的畅快侠义。《无灯的元宵》发表于1990年第10期的《山花》,是晓苏相当早期的创作。小说从孩子龙儿的视角来写他的父亲龙大蛟——油菜坡的村长。龙大蛟不管做什么,都要当油菜坡最领头的那一个,过年鞭炮要买响儿最多的,正月初一要当第一个放鞭炮的,一定要龙儿考第一这样元宵节家里才好挂上油菜坡最多的灯笼。在龙儿眼里,屁股总是要高高撅着的龙大蛟“是个怪东西”。因此他故意没有考第一,这把龙大蛟气得一个灯笼都没挂,孩子心中却很是快活。尽管作者在叙事中恪守了儿童视角的认知界限,没有直接点出龙大蛟的“怪”到底是什么,却还是让说不清原因的龙儿完成了对龙大蛟的惩罚,故事中存在着明确的正邪两方。发表于1992年的《黑箱》同样如此,张西村有着偷女生内裤的癖好,他在一次行窃时恰好撞见同学陈可与恋人亲密的场景,便以此要挟两人交代亲密的细节,更在毕业工作分配时逼迫陈可到湘西,而自己黑箱操作后留在了城市。但在事情都要了结之时,书记突然带着揭发信来到了张西村的寝室,打开了张西村存放偷来内裤的黑箱。不难猜测,作为小说中的反面角色张西村受到该有的惩罚,完全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
可以看出,晓苏前期的小说往往是非分明,有着较为清晰的正、反面人物,小说的內在逻辑也是简洁明快的惩恶扬善,损有余而补不足。但随着晓苏创作的发展,这种是非分明的故事越来越少见,而像《寡妇年》《镇长的弟弟》《姓孔的老头》《拯救豌豆》等暧昧、含混、复杂、缠绕的故事越来越多,小说中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自然也不存在惩恶扬善的发展逻辑,这无疑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本来面貌,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所谓的生活的广阔,就在它是不能用任何模式、标准、范式去描述的,它总是要突破那些明晰的边界,就好像漫过堤坝的河流。”② 这种创作上的前后变化,固然有作家在思想深度、艺术风格和美学价值上的考量,但究其根本,恐怕还是与作家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有关。悲悯情怀使得作家持续关注民间,挖掘民间的缺失与充盈,尊重平民生命形态的复杂性,从而打破了前期创作中单一的道德界限,从金刚怒目易变为菩萨低眉,给予笔下一个个灰色人物深切的人文关怀,保持了小说的人情温度。那么,这份难能可贵的悲悯是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小说家的叙事,而他又是如何在叙事中将这份悲悯处理得隐而不露、沉潜低徊的呢?
二
既然要叙事,那么谁来讲故事?叙事人的选择至关重要。熟谙叙事艺术的晓苏总是巧妙地设计讲故事的人,或在第三人称叙事中运用“内视点”,透过主人公去思考、聚焦事件,让主人公在读者不经意间悄悄“说话”;或选择与故事主人公具有一定距离,又有着特定联系的旁观者,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中的说话人向读者讲述故事。
第三人称叙事中“内视点”的运用,往往从情感上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马克·柯里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用非常通俗的语言介绍了这种心理机制,“当我们对他人的内心生活、动机、恐惧等有很多了解时,就更能同情他们”③。晓苏在小说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写作技巧,让主人公自己成为“讲故事的人”,《生日歌》就是这样一部小说。“邱金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一个犯过罪的主人公成为读者进入故事的“内视点”。邱金出了监狱最记挂的是父亲七十岁的生日,遂马不停蹄地往油菜坡赶,路上他几乎花光身上所有的钱买了猪头和猪蹄作为父亲的生日礼物,而在这份礼物曲折送回的途中,邱金已经觉察到弟弟妹妹亲情的淡漠。在父亲生日宴上,邱金发现猪蹄不见了,弟弟妹妹互相猜疑,他只能回到镇上找卖肉人要说法。故事的结尾处邱金又拔刀刺向明显无辜的卖肉人,但其动因却是不忍直面亲情破灭的现实,这使得读者无法将邱金视为极恶之人,反而对其境遇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同情。
除却主人公自己,晓苏也经常设置旁观者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说话人,这些说话人或是久住油菜坡的乡亲,或是来到油菜坡工作的人,他们与主人公没有身份上的绝对差异,这使得说话人可以平视的视角体察主人公的人生境遇。小说中,叙事人带着读者进入故事,读者的阅读视角会向叙事人的内视角无限靠近,加之这种平视叙事人的选择,产生的一个重要阅读效果便是“共情”。如在小说《书虹医生》中,一位十五岁的少年讲述了在油菜坡工作的妇产科医生书虹生活巨变的故事。怀有仰慕之情的少年看书虹医生的前后变化,必定不会是高高在上的批判与审视态度,随着叙事的展开,读者不断向叙事人靠近,在最后目送书虹医生离开时获得与叙事人共同的感受。
有意味的是,晓苏在小说中大量选用少年和书虹医生这样性别对立的叙事人,如《镇长的弟弟》中一行三人,两男一女,偏偏选择唯一的女性唐糖来讲这个假镇长弟弟的故事;《寡妇年》中故事主角是油菜坡三个“守活寡”的女性,而叙事人是一心想调离油菜坡小学的男老师;《伤心老家》的故事主角是退休回老家建砖厂乃至殒命的尤龙,而叙事人是他年轻时相恋的老乡西凤。男主人公的故事由女性诉说,女主人公的故事由男性诉说,两性情感的复杂纠缠往往使叙事人的诉说更有细腻幽微之处,读者看到的是经过叙事人感知折光后的现实困境,恐怕也心有戚戚然。
通过叙事人的精心选择,小说家得以在叙事中隐藏自己,但这并不意味著晓苏作为一个小说家没有立场和态度,他运用“内视点”展示人物复杂幽深的内心,使其得以立体化,或巧选旁观者作为叙事人,利用叙事人的感知带有温度地诉说事件,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唤起读者同情乃至共情的感受,这使得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与作者潜在的悲悯之意产生共鸣。
三
除了谁来讲故事,如何讲故事即对叙事节奏的把控,也是作家传达自己意图的重要方式。悲悯虽不是请命,但也并非嚎哭,晓苏笔下几乎所有的乡土小说都与油菜坡这个封闭甚至落后的空间环境有关,生活在这片黄灿灿原野上的油菜坡人成为作家诉说的媒介。但与很多底层文学不同,晓苏从来不会无节制地进行苦难叙事,虽然油菜坡人同样面临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匮乏,但他们不会在苦难中退化到只有所谓人性,而没有人情的地步。这种恰如其分的“为底层说话”,得益于小说家经由叙事节奏传达出的叙事关怀。
缓于所当缓,是晓苏调节叙事节奏的一种方式。《镇长的弟弟》起笔是叙事人唐糖一行三人从东莞到了湖北襄阳,准备去给冯知三拜年。冯知三住在油菜坡,“经过襄阳市,我们还要到康山县,再从康山县到老垭镇,然后才能去油菜坡。不过,一到老垭镇就好了,因为冯知三的哥哥是那个镇的镇长”④。然而,故事并没有像唐糖设想得如此简单流畅,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延宕他们到油菜坡的旅程。终于到了老垭镇,事先约好的冯知三并没有出现在车站,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三人只好找到镇政府,却得知冯知三并不是镇长的弟弟,他的哥哥是油菜坡一位四十多岁的光棍。至此,三人这条从襄阳到油菜坡的拜年之路,经由小说家的安排,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地放缓乃至停顿,因为只有放缓叙事节奏,假冒镇长弟弟的冯知三才有时间展现他复杂的人情与人性。与唐糖三人不停等待的一天相比,其中隐含的冯知三的一天是如此的忙碌,这种悲切的忙碌固然展现了他社会底层的处境,但也表现出了他人性的光芒,即是没有镇长弟弟这个“光环”,他似乎依然足够“体面”,可以说这是小说家赋予人物的叙事关怀。
类似的方式还有小说叙事中的止于所当止。小说《松油灯》中,瞎子冯丙出门时总带盏松油灯,这让油菜坡人好生惊讶。一盏瞎子手中的松油灯成为第一个“谜”,但作家很快就解开这个谜题,原来这是因为在冯丙三十六岁生日那天一个女人进入他家,让他第一次体验了欢爱,冯丙不知道她是谁,只找到了这个女人悄悄离开后留下的这盏松油灯。于是,女人是谁便成为新的“谜”。冯丙有三个怀疑的对象,当他找她们对证时,她们却全都否认了。冯丙没有放弃,他想“要是在邻村这两个地方还是找不到那个女人,那他将会提上松油灯到更远一点儿的地方去推磨,比如妹妹冯珍所在的黄坪”⑤。行文至此,拥有全知视角的读者不难捕捉到作者的暗示,那个女人应该是瞎子冯丙的亲妹妹,这个谜底在小说中已经多有暗示,比如她从不出声,比如她对冯丙家的熟悉,这种不伦的关系在叙事中变得可以被读者所接受。但作者在这里停住了叙事,并不将所谓的真相残忍地揭示出来。《生日歌》《镇长的弟弟》的结尾同样如此,邱金没有明确锁定是谁拿走了那个猪蹄,唐糖也没有看到喝农药自杀那个人的面孔,虽然事实可能不难揣测,但晓苏隐而不露,选择将最终真相雾化处理,在叙事中为笔下人物保持住他们生命中应有的尊严。
综上所述,正因晓苏一以贯之的悲悯情怀,以及小说家对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工匠般的雕琢,才使其作品保持极高可读性的同时,蕴含着一种古典的人道关怀的温暖。这不是 “零度写作”理性分析层面上的关怀,而是读者在感性层面上可以感知到乃至产生共情的关怀,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注释:
① 张大春:《序曲:但凡世间无仁义人人心中有梁山》,收录于周华健2013年《江湖》专辑。
② 金立群、晓苏:《一个孤独的写作者——晓苏访谈录》,《小说评论》2012年第6期。
③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④ 晓苏:《镇长的弟弟》,《为一个光棍说话》,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第178页。
⑤ 晓苏:《松油灯》,《为一个光棍说话》,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版,第242页。
作者简介:孙秋月,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