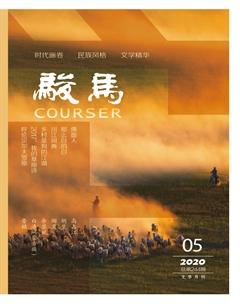那么白的白
胡斐
大雪是来咬人的。但人还得出门,遇它细密的牙齿。起初不疼,咬得人心里酥麻,疼要到了冻瓷实的傍晚。
市场里快被脚踩成烂泥塘了。来来回回,早晨有一波人,中午就寂寞了。简易棚子下是菜和水果,都捂着棉被,摊主都跑了,去周围一圈铁皮的房子里烤火。逢有顾客,才一个撵一个回去售卖。铁皮房子里的日用百货应有尽有。
“调料王”系着围裙,脸上有一块胭脂红,波浪一样的卷发过年才烫的。她吐着瓜子壳,扑扑地像吐一串口水,眼睛却看着那间修鞋铺。
修鞋铺里是李菊,起初看雪,后来看偶然走过玻璃拉门前的人,再后来就看对面那栋镶了淡淡白边的楼。五楼的阳台上,四十多岁的男主人穿一件两股筋的背心,在给绿植浇水。那块被晾衣架、绿色盆植和撂起来的纸箱子攻占的狭小空间里,他裸露的皮肤显著地跳出来,喧软、细嫩同时油腻地白着。李菊下意识去摸自己的手,为了干活方便,她戴着剪去五个指尖的毛线手套,断茬处拿补鞋的线缝缀好了,每天和各种各样的鞋纠缠不清,手套早已经分不清本来面目。就像李菊的手,也早已经看不出是李菊的手了。她觉得那不是一个男人该有的雪白,该是她的,该是她那双手的。
被男人的雪白拉远了思绪的时候,李菊也就忘了自己的冷。她的冷和走在街上的人不一样,他们瑟缩着脖子看上去很冷,但那冷肯定只是一时的,他们总会回到只穿背心的家里。李菊的冷是连续不断的,像棉花糖,绕一圈再绕一圈,要拉多长就有多长。
其实四平方米的小铁皮房子里,烧着煤球炉。但除了需要烧开水的时候,那个煤球炉的火都是压着的,温吞吞,李菊不让它死也不让它活。整个市场的修鞋摊位里,就数李菊的生意差,客人少,毕竟她手艺一般。就为了这个,李菊自觉地克扣着自己。当然,有客人要坐进铁皮房子里等着拿鞋的时候,李菊会自觉地让火旺一点。还有一种情形,是李森林过来说话的时候。
于是李森林就过来了,开了自己修鞋铺的门,走不过三步,就进了李菊的门。他捎来一块蜂窝煤,也不多说,自顾自替李菊捅开了火,炉子上的烧水壶轻轻地唱起来,不久就欢快地嘶嘶鸣叫着,冒出热腾腾的水汽。
“调料王”扑扑的瓜子壳就是奔这幅画面去的,热腾腾的小房子,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偶尔说话,偶尔眼神碰一下再闪开,女人低头哧哧地笑,男人身子前仰几乎就要摸到女人的膝盖,却将将就停在那里,摆一个烤火的姿势。几乎能听得见自己吐出的那声“呸”了,“调料王”拿出笤帚去欺负那些瓜子壳,哗哗地拢到一处再哗哗地堆出门。
早前“调料王”才是那个画面里的女人,被八角、茴香、干姜、肉蔻、辣椒面的浓烈环拥着,她摇摇摆摆的笑追着李森林,总想要打湿他的衣角。他扭捏一下,不就范,也不草草离场,总要陪着她演一演。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偶尔都要跳脱一下。她也没那么当真过,偏偏他不陪她演了,她从跷跷板上跌了下去,就感觉到了疼。疼了,眼睛里就进了沙子,有時候揉出的是酸,有时候是刺,有时候是一把白刃的刀。譬如卖鱼的刘三刮鱼鳞的那把,要多么快多么熟练,眨眼间就修出一条圆润的鱼身来。
水开的时候,李菊去拎水壶,李森林手快,先够着了。把水挪一挪,还是让壶微滚着,问她刚才在看啥?李菊抬头,阳台上那个雪白的只穿背心的男人还在,愣了一下。李森林也抬头看,说你看,白不白?李菊不搭腔,李森林打趣,说我要是有那么白,就能做小白脸了。这句被李菊呸了一下,李森林又说,你要是有这么白,就美得不得了了。李菊顺嘴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没那么白?我要不是修鞋的,比他白。李森林又说,你白不白都好看。
雪下那么白,有人觉得凄凉,也有人觉得可爱。就是这样。
这座城几年以前是另一番样子,比如中心公园那时候还没盖起来,西郊那时候也还没有层层叠叠的楼房,总之现在的时间比过去的时间快了,眨眼间就能发生很多事情。
至于李菊,短暂的修鞋生涯已经让她的一双手糙成了老树皮,虽然她干活的时候,姿态麻利清爽,拔下旧鞋跟,打磨,切割胶皮,涂抹胶水,粘合,修整,为顾客换双鞋跟一气呵成,没有多余的累赘。但如果她忽然抬头看一眼,或者讨好地笑一次,就立刻暴露了她身上的疏离感。她到底和这座城市还没有骨血相连,好像来一点什么事情,就很容易把她和它分开。不像李森林,他操着一口总会让人误解那是咬到了舌头的外地语言,却流露出他和这个城市密不可分的坦然。
当然,这坦然和不可分源于他在城里有一套房子,两室一厅,阳台还可以让李森林像个城里人一样,穿着背心招摇地晾一晾他的几件好衣服。没什么不同啊,他跟李菊说,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有时候我比他们还会享受呢。
李菊不说话,淡淡笑两下,她长得还算好看,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虽然是坐在铁皮房子里,戴着脏污的手套,干着修鞋的活儿,但她长得清秀可人,除了笑的时候会露出几颗稍稍泛着黄的牙齿。她在顾客面前不避讳那些牙齿,该露就露了,在李森林面前她就忍不住要藏着。
李森林修鞋手艺好,爱陪客人聊天,能唱家乡小调,还喜欢去舞场里跳跳舞,市场里的人喜欢他,顾客也都喜欢他。第一次见李菊,他逗她,喊哥呗,都姓李,也不分姓。李菊彷徨,看了看领她来见李森林的老乡,老乡笑得很舒展,她就叫了声李哥。李森林咧着嘴呵呵笑,很受用的样子。
那时候李菊刚和自己的男人离婚,一个人跑到城里来。李菊的男人其实是老实男人,在家乡的砖厂上班,拼苦力,一个月挣个两三千,李菊在家里种几亩地,伺候老人,都风平浪静。男人对她也算体贴,夜里冷了知道把她的脚捂在怀里,炒个肉菜会当着婆婆面往她碗里夹大块瘦肉。后来是被砖厂的出纳给搅黄了。那个大屁股的桂花,胸前像装着两座白花花晃荡的池塘,一走一摇,水就要溢出来的汹涌。李菊替男人去砖厂取过几次工资,回来还跟男人说桂花的胖,笑话她那一身肥厚的肉。结果那堆肉躺到他男人怀里了,还是别的长舌妇说给李菊听的。男人常年干活,胳膊粗壮有力,搂住李菊的时候,像老虎抱着一只小白兔,李菊想着他抱着那丰腴女人的样子,呕出一地酸水。男人回家,李菊就逼问,男人平时不跟人争,也没有坏心眼,就低低地说,你别嚷嚷,我就是一时糊涂,没忍住。男人给李菊认错,说小菊,你知道我的,二柱他们进城还去个理发店按摩,我连门也不敢进。要不是,要不是她逗引,还自个儿往我怀里钻,我哪敢啊?李菊冷哼一声,你一个搬砖干粗活的,她凭什么?男人说这我咋知道,反正我去领工资,她把我留到晚了,拿她那胸就蹭我胳膊,我躲了,真的,可她就抱住我脖子不放,菊,小菊,真是她自己来的!李菊说你恶心!男人说是,我是恶心,我以后再不恶心你了,我今天就跟她断了。李菊说断了,看样子你们俩时间久了,什么时候开始的?男人沁了一头的汗,统共,也就那么两三次。李菊觉得一百只老鼠的爪子在抠自己的心口。李菊说你是喜欢她了吗?咱俩离了吧。男人急了,小菊,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桂花就是一时,那么一会儿,上床下床的事情,我心里就你,没别人,打死我也不会离的。李菊说还桂花,叫那么亲热,你还不是喜欢她吗?她自己呜呜地又哭了,男人赶紧澄清,说那个骚娘们儿,她就是个骚娘们儿。李菊更气了,她骚,你不是更骚?她一个女人,你不碰她会有什么事?男人还是一迭声地认错,说就是鬼迷心窍,迷迷糊糊就那样了。
没人觉得大惊小怪,邻居、亲戚甚至娘家人都用相同的话劝她,也不当真的,他总归心里有你。本来李菊想忍,她劝自己也把这样的事情当吃饭吃出粒沙子,硌了下牙,吐出去就好了。到了别人都吐出去了,她不行,她就是拗不过自己的心和眼睛,男人忽然有了重影,经常变成两个人,她看他一眼,她碰他一下,就总看到他怀里腻着那个肉乎乎的桂花。她知道这样的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咬着牙离开了男人,没要孩子,也没要钱,跑到城里碰到修鞋的老乡就学了修鞋。
李森林一直对李菊不错,但也就是这样而已了。离“调料王”意图打湿他衣角替他更衣的距离还远。不过是门挨着门,李菊手艺不熟练,隔三差五需要一个老师傅指点一下。他就是热情,想帮她。也许帮着帮着走得太近了,挨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闲闲说话的场景太频繁了,两个人自己没觉察到吧。市场里传了很久,“调料王”像画小人书,编了一本又一本,满市场都当电视连续剧看,就瞒着他们俩人。
雪下出一层白又一层白,天地都白了。李森林和李菊在小铁皮屋子里暖暖地过了一下午,没客人来。顾客修鞋都不是要紧的事情,不会往又冷又滑的街上来。再等一会儿,天就快黑了。李森林说等下要回去吃火锅,问李菊要不要一起?李菊当然说不要,她知道李森林是有老婆的,所以中午会回去,晚上又要早早回。满市场只有他中午回家,而且是回一个半小时。这么算下来,他比别人忙的时间少很多,生意都靠好人缘撑着。每每他这么问,都只是寒暄,也就像聊聊天气一样平常吧。他也知道她不会当真,却还是细细给她讲要烫什么菜,一定要有羊肉吧,还要有粉条,他说还有年里剩下的肉丸子,冰箱里冻着豆腐,差不多了吧,对了,再加点自己腌的酸菜,来一把韭菜。李菊垂了眼睛,被他讲得舌底里生津,也悄悄在心里想,要不要回了出租屋里,也用炉子烫一点热乎乎的肉菜吃。
这饮食烟火的日子,无非也就是这样吧。
门被推开的时候,两个人都还沉浸在滚烫鲜活的想象里。冷不防一股子凶狠的风扑进来,炉火被吹到东扭西扭定不下来。一群人涌进来,还没反应过来,已经推开了李森林,揪住了李菊。声音鞭炮一样响脆的,那是巴掌扇在了她脸上,或者沉闷像哑炮,那估计是脚板踢到了她棉衣裹着的身上。总之各种响,各种揍,各种哀嚎。
李森林冲过去,被推开了,再冲过去,又被推开了。是他家的亲戚吧,他一连声喊着四叔的,满嘴的白灰胡须,还看得出在咬牙喊使劲。李森林扯开了嗓子,四叔,你们这是造什么孽?她跟你们有什么冤什么仇?
叫他四叔,他才肯斜着看李森林一眼,破鞋!让你再跟她好!家里的老婆你当她死了么!
李森林说胡扯些啥?我们啥也没干。一边喊着冲过去救李菊,更是添了一桶油,火烧得更旺。一群人撕扯开了李菊的衣服,像剥葱。李菊哀哀地求,不要,一面喊着救命,一面护紧了周身。哪里也顾不过来,一双手敌不过十几双手。还嫌地方小,十几双手把她拎出了铁皮屋,扔到了外面的雪里。
李菊不到两百块钱的棉衣被扯开了,梗粗的鸭毛到处飞,到处飘,看起来比雪下得还认真,再落一地,粘到四处的人身上。李菊哪里也不护了,没力气了,木头人一个,任他们捏任他们摆。
李森林要打110,被抢去了手机,转身朝鸡鱼肉、日用百货店主还有“调料王”那里高喊,快报警啊!不知道有没有人打电话,却都涌过来看热闹,正月十五看社火一样的表情。像围出了一个戏台,看着李菊被剥成白萝卜样,原来她真是很白的,别看那双手粗成老树皮,身子却是白的。她不哭,也没有眼泪,头发挡住了脸,转眼“白萝卜”被市场的烂泥塘染成了黑一块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
羊肉铺的刀被李森林抢过来了,他扑过来,一群人自动撒了手,以四叔为轴心,围成了半徑,看他要怎么冲杀。
李森林有拿刀的胆,却没有刺到别人肉里的心。但保不齐逼急了眼会不会有,而且四叔那群人并不打算逼急了他,他们只想吓退离他近的女人罢了。管是李菊,还是别人,靠李森林太近就都要吓一吓的。也没人过去斗狠,看李森林挥舞着刀,风车一样,跟李菊喊,进门去,快进门去。
修鞋铺的门还是完好的,李菊于是披散着头发,在烂泥塘里匍匐。好不容易摔进了门里,才敢哭,才想到眼泪早该流出来了。她开始恨,恨桂花,恨男人,恨李森林,恨这个下雪的天,恨自己那个被染成肮脏的身子。等她从嗓子里尖厉地嚎出来时,像谁拿着刀刮玻璃,刺拉拉地噪,让人心里吞不下吐不出去的噪。
李森林拿着刀,把着门,眼睛血红。慢慢就没人了,四叔那群人打也打了,气也出了,吆喝着早走了。看热闹的都是市场里的人,往日那么熟的脸都认不出来了,一个一个,青的脸,乌的嘴,钩子一样的眼睛。顾客三三两两来,就势也就散了。
李菊浑身的肉像要掉下来,动一下掉一块,但又不掉,再动一下再哆嗦一下。疼也折磨她,不让她好受。她喊李森林,滚远。李森林要送她去医院,被她再骂一遍滚远。她只有嘴里有力气,手和脚的力气都散尽了。
医院还是去了,她那个样子再窝在铁皮房子里,指不定就僵掉了。李森林替她裹了自己的大袄,叫了一辆出租车,颤颤巍巍扶着李菊,她疼一声,他心尖就跳一下。自己是作了什么孽吗?真的没有,天雷打下来他也敢说没有,那是凭什么呢?是他欠谁的吗?算下来,也算不清楚。
李菊好歹昏睡在医院的床上了,发着高烧,浑身都是火炉。李森林寸步不离,电话被丢在哪里了,他出来的时候忘了去捡,忙的间隙想到家里的老婆还没有吃饭,再一转念,却想饿死她算了。四叔是老婆娘家人,那一群也都是,他们不给他活,那让她一起不活算了。
他干脆一夜不回。守在李菊床头,她醒了,喂她水,喂她粥。她睡了,他也趴在她脚底迷糊着。亮的时候拉开病房的窗帘。雪把街冻住了,把城冻住了。虫子一样的车和人,在马路上蠕蠕地挪。活就是这么不容易,哪里都得小心不是么?
李菊也来了一段时间了,还不知道李森林的事情。满市场知道的人也没几个,都只隐约听说过李森林的风流债。他总去公园里跳舞,腰身扭得比女人还好看,那块场地三元一张票的时候就跳,换了夜场迪厅的时候仍跳,成了旱冰场的时候还跳,没谁比他长情。跳舞时间一长,别人都有固定舞伴,他定不下来。起初是交谊舞,舞场外面的人都喊交谊舞交谊舞,他搂别人的腰,女人搂他的肩背,贴得近了,女人的粉饼香腻腻的沾上身。必须要手握在一起的,他早早就回去洗干净,总要把手搓洗个十几二十遍的。舞曲一响起来,他就什么也不想了,鼓点敲在脚上,一点不错地跟着,前进,前进,后退,插花。行云流水的夜,搂肩搂腰的夜。
是从跳舞开始,李森林挨了打。还是四叔那一群人,起初是打他。后来不奏效,打完了,伤好了,李森林还是手洗个半干净,指甲缝里藏着鞋油皮屑,脸上抹了大宝去舞场里前进后退转圈,不到十二点想不到回家。四叔他们就换了方式,不揍他,揍和他跳舞的女人。一个,两个,三个,和李森林跳舞的女人越来越少,偶尔有不知情的孤单单去了,被李森林邀下场,以为他是舞蹈老师,被带得花团锦簇,再一夜奔着他来了舞场,李森林却冷了脸,装不认识,也就讪讪躲远了。
就这么跳了几年,大家改跳广场舞了,才省下心来。谁也不搂谁了,谁也不挨谁了,自己抖自己的肩,自己转自己的腰吧。李森林还是领舞,带着上至六十下至几岁的孩子旋转跳跃不停歇,外场围一圈看的人,目光都在他身上,他像大功率的聚光灯,被众人的追光熨得心里舒服。
“调料王”当然知道有关那些挨打的事情,但哪里危险哪里才有趣味,她就是那种要往生活里丢石头看浪花的人。她招惹李森林,也不过就是招惹,知道分寸,知道闪躲。李菊自己懵懂,飞蛾一样撞进蜘蛛网了,只能怨她自己。
十几年前,李森林是农村的,老婆是城郊的,遇着了,也没多想就凑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也是大雪的天,天上玻璃,地上也明镜,从上到下的瓷实。傍晚的时候他们过马路,齐齐被撞了。他滑出了马路牙子,老婆瘫在了床上。在医院里耗了一年多,老婆说不出话,娘家人主动要求回家养吧,别把钱都送给医院了。剩的赔偿款够在城郊买套房子,就买了。几年以后城郊拆迁,又换了大的,还有了余钱。他是一肩挑着房子,一肩担着老婆,就那么一路走过来的。四叔他们无非怕他还挑着房子,却扔了老婆。
可是没有跳舞的那点乐,他觉得也撑不下来。那些粗的腰细的腰,肉的手骨感的手,笨拙的脚轻盈的脚,都给了他念想。不过就是碰一碰热的,动的。不然一夜一夜怎么熬,要从年轻熬到中年,再熬到老,再熬到死。
李菊听他说跳舞的事情,听他说挨打的事情,听他说摸手搂腰的事情,没听到他说跟谁真的好过,好到脱了衣服的那种。他说做不出,也就是想想。不知道怎么的,她信他。不知道怎么了,她就把手放到了他手里。两只手有些像,粗粗的,爬满伤痕的,怎么也洗不干净指甲缝的。他起初不敢动,再来轻轻摩擦了一下手背,抚了抚指肚。那两只手像两只蝴蝶,停在一朵花上,阳光照着,偶尔扇动一下翅膀。
出了医院,李森林送李菊回她的出租屋。就在菜市场附近,三百块钱一居室的老楼房,楼道黑漆漆,墙面被各种文字和颜色覆盖了,楼梯间有风的时候纸片塑料袋呼啦啦地飞。房子里倒是通了暖气,暖气费李菊自己交,也有旧热水器可以洗热水澡。
浑身青紫的李菊把自己泡进温水里,细细地搓,但不敢站太久。她回想那天大雪的白,自己的白,被满市场的人看进眼里的白,手颤了一下。放下一头湿淋淋的头发,照一下镜子,她觉得自己蜕了一层皮。
白蛇蜕皮,青蛇蜕皮,蜕无数次皮修成了人。她躺在床上,水水的眼睛看李森林。他躲了一阵,也没处躲。李菊的男人去年末的时候来过一次,告诉她娃儿也得要人管,他也得要人管,桂花做饭家里人都爱吃,桂花的好性格哄得一屋子人都开心。那么,他就打算和桂花一起过了。他没问她要不要回去,他就说要和桂花一起过了。她出来了,拗着一股性子,并没咬定再不回去,还存着回心转意的小心思,不说出来罢了,以为当她男人那么久了,终归会懂的。但这人间,最是个懂字没法测量,可深可浅,可到身体可到思想。最后的结局,别人打她都是用手用脚用棍子,那个男人打她就用一句话。一句话也就够了,她也半死不活了。
那么好了,她的男人没了,李森林的女人相当于没了。她蜕了皮,白白的肉身,人的肉身。也没什么好想的,都是清白的。清白了以后的清白,雪被踩脏了以后,再铺一层雪的白。李森林为那白哭了一鼻子,他的眼泪怕是攒了太多年,怎么也揩不净,她的手替他抹去一层,又涌出来了,再抹,还有,是有泉水住在他身子里吧。
回到市场是半个月以后了,李菊换了新袄,李森林买的,将将好掐着腰。李菊脸养白了,一朵白梨花样,从市场的东头走到西头,南角拐到北角,脸上是盈盈的笑,笑里其实是绵密的雪。鸡鱼肉、日杂铺子的主人以及“调料王”迎着那雪,拿不出合适的表情,冷了不好,热了也不对,笑都干巴巴。
日子如常,两家修鞋铺的生意卻混杂到了一起,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忙的时候一起忙,闲的时候一起闲。但一起闲的时候,李森林剥了桔子喂李菊,嗑一堆瓜子攒许多瓜子仁儿喂李菊。李菊喂他是用眼睛,是用嘴,是用白。“调料王”砸烂几个罐子,骂婊子,那有什么意思?太多的事情要两个人才有趣味,连生气也是。比如李菊偶尔撇嘴,李森林就知道她哪里不痛快了,就去挠她,就去哄她,搂着她的腰跳快三慢四,探戈他也跳得来的,总归在舞场里那么多年了。有的是时间,一点一点教李菊,有的是黑夜,一步一步摇啊摇。
四叔那群人被关了几个,是李森林干的。李菊蜕了皮,蛇一样,他蜕一层皮,老虎一样。报了警,看守所里让他们住几晚,总会学乖的。以前他都忍着让着,到了发现会把人惯坏,惯到不讲理,也就豁出去了,豁出去了反而没啥了,出来的几个都蔫了,没进去的还要跳着找李森林,冤冤相报何时了,算了吧!也就算了,李森林都做好冲锋陷阵败逃反攻N条方案了,最后敌方武器入库了。也好,和平解放。
转眼就没雪了,杏花白了桃花红。李森林请四叔他们来家里吃饭,李菊掌勺,她从老家带来的手艺,红焖羊肉,黄焖小排,辣子鸡,水煮鱼,大炒小炒十八盘,光为菜单她就琢磨了一个星期。
菜先在桌上摆着,没筷子,众人一起看李森林怎么喂睡在床上的女人吃饭。女人的下巴挤出波浪状来,那没力量的一身肉轻软绵密,碰一下就晕出一圈浪,白而喧腾的浪花。李森林盛了鸡汤,一勺一勺吹凉了很有节奏地往女人嘴里喂,白胖的女人一副娇嗔的表情,喝一口咂巴下嘴,很享受的样子。看得出来,李森林习惯了这样的喂,女人也安于这样的喂。时间是最好的镜子,好不好都能看得出来,亲戚们看得也明白。喝完了汤,李森林又喂女人吃了几块炖到要化的肉,女人吃饱了,他帮她开了墙上挂着的电视,热热闹闹,花红柳绿。还要翻身,把波浪一样的身子翻一下,揉捏几把。至于吃喝拉撒,每一样拆开了去,都是要耗力气的,耗时间的,耗耐心的。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多少年了,也没个记帐本,没法拿给四叔他们看。
李菊说大家上桌吃饭吧,筷子一一摆好,四叔带头,恭恭敬敬坐好。酒喝到嘴里,是辣的,是催眼泪的。李森林到底忍住了,碰杯碰得山响。四叔也回敬他,他端起来喝光了,拿起鸡腿,撕了一条肉,却往李菊嘴里送。她躲了一下,又凑过去接住了。满桌静了一下,又融化了,酒还是酒,接着喝。
李森林请四叔的时候就说了,房子是老婆的,谁要是养她,就把他那个担子接过去两头挑,四叔也行,别人也行。四叔不养,别人也不养,那他就一直养着。他挑惯了,肩上有力气,也还担得动。
喝醉了,吃好了,都摇摇晃晃出门去,一排站在街上。接着看李森林和李菊两个人把那团白胖的浪花抱到了躺椅上,阳光也是白的,白的光,白的热。椅子上的女人难得见到阳光,以前李森林一个人弄不动她,有李菊就好了。她竟然笑了,嘴角流下线一样亮的水花。李菊帮她轻轻地擦一下,拿起梳子替她梳剪得短短的头发。梳一下,浪花欢腾一次。
人都慢慢走了,散到四处去。李森林说着再来噢,像在空空的天里敲了一面小鼓,叮叮咚咚的。他凑过去嗅李菊身上的香,手揽着一个女人温热的腰,把一条街都当了舞场。街上的花白的白,粉的粉,都看着。长日苦短,长日漫长。
责任编辑 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