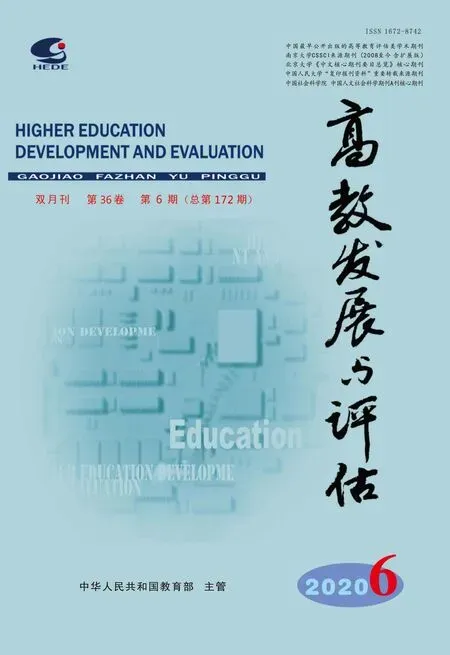大学治理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张庆晓,周石其,刘素兰
(1.江西理工大学,江西 赣州 341001;2.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来源
本文以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文献来源,运用高级检索,检索条件为“标题与主题=大学治理”(TI=universitygovernance and TS= universitygovernance),文献类型锁定为论文(Article),检索领域限定为教育学(Educational Research)领域,时间跨度为2010年-2018年(截止到2018年12月3日),共获得411篇文献数据。
(二)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HistCite引文分析软件、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和Excel软件。HistCite可以快速的帮助研究者显示大学治理这一领域不同文献之间的关系,绘制出发展历史。CiteSpace可以帮助研究者绘制知识图谱,分析该领域的动态演进。本文主要是通过CiteSpace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结合HistCite软件得出的引文分析结果,分析大学治理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二、研究结果分析
从全球范围来看,学者围绕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比较多。本文通过研究相关成果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高影响力作者分布和载文期刊分布展示大学治理的外在表现,并通过仔细分析相关经典文献,结合关键词聚类来透视大学治理内在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一)时间分布
从时间维度分析大学治理研究的动向,侧重于通过观察不同时间段内的发文量、绘制指数趋势线判断其发展态势。如图1所示,在2010年-2018年间,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6篇增长到2018年的73篇,增幅明显。具体分析来看,从2010年-2014年期间,大学治理文献年载文量均超过16篇,基本保持平稳态势;但随着大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复杂,各国学者对大学治理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和思考,国外有关大学治理的研究成果数量在2015年出现小高峰,之后稳步增长,说明大学治理是各国高等教育关注的热点问题。借助Excel软件绘制指数趋势线,再借助公式计算指数R的平方值与趋势线共识y的值。从计算结果来看,R的平方值为0.861 6,趋势线y=12.325e0.224 8x,R的平方值越接近1说明趋势线拟合程度越高,趋势线越可靠[1]。由此可以判断: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情依然不减,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

图1 2010年-2018年大学治理研究文献的数量变化趋势图
(二)空间分布
从横向维度分析大学治理研究的现状,主要是围绕发文的国家、作者所在机构进行分析。发文分布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一国家在该研究领域话语权的象征,从深层次来讲,则与国家的研究水平、科技竞争力密切相关。本文采用HistCite软件的两个指标:TLCS和TGCS。TLCS ( Total Local Citation Score)代表本地引用次数,即某篇文献在当前数据库中被引用的次数;TGCS (Total Global Citation Score)代表总被引次数,即某篇文章被整个WOS数据库中的文献所引用的次数[2]。文献的TLCS数值越高,表示文献的影响力越大。从表1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德国、加拿大、挪威、意大利、葡萄牙和荷兰。其中,德国的发文总量虽然排名第五,但是其TLCS却排名第一,说明德国在大学治理研究领域的影响力比较大;澳大利亚的发文量排第三,TLCS数值和德国相比差距很小,位列第二,TGCS排第三,其整体的研究实力比较强;英国的发文总量排第二,TGCS排名第二,TLCS排名第三,与其传统的高等教育强国地位是密不可分的;挪威的发文量只有18篇,但是文献的TLCS数值超越了美国,说明挪威的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和重视;美国的发文量和TGCS均位居第一位,TGCS高达344,说明美国是大学治理研究的高产出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大学治理方面的研究虽然总被引频次排名第四,发文量也比较多,但被引频次排名靠后,位列8位,学术影响力有待提高。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结论: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挪威、美国是研究大学治理问题的第一梯队,而这些国家基本都是传统的高等教育强国。

表1 大学治理研究文献的国家(地区)分布统计TOP10
(三)研究机构分析
从研究机构分析来看,按TLCS大小排序,如表2所示,德国的康斯坦斯大学虽然发文量仅有2篇,但TLCS高达12次,TGCS也排名第3,说明康斯坦茨大学的研究文献得到了学者的认可和关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发文量排名第1,TGCS排名第1,TLCS排名第2,说明其整体研究实力较强。在排名前十位的研究机构中,澳大利亚有3所,德国有2所,其余为1所。

表2 大学治理研究文献的研究机构分布统计TOP10
(三)高影响力作者分析
本文采用H指数分析高影响力作者。H 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乔治·赫希 (Jorge Hirsch)于2005年提出来的,主要用来评价学者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水平,并将其定义为“某学者发表文献中共有h篇的被引频次达到至少h次”[3]。H指数的高低与学者的论文数量及论文被引次数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当学者的H指数较高时,他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就较大。H指数有效避免了自引、高被引单篇论文的影响,对学者的评价较为客观,并可以预测学者未来的学术成就。本文根据H指数的计算方法,利用HistCite软件分析411条记录,以作者为关键字段按照TLCS大小排序,最终选取TLCS 值和 H 值都较高的前十位学者,如表3所示。

表3 大学治理研究高影响力学者统计TOP10
从表3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Jones GA教授和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Rowlands J教授,H指数和发文量均为5。通过追踪两位学者的研究方向可知,Jones GA教授是多伦多大学的公共政策分析和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围绕大学自治、府学关系及大学国际化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Rowlands J教授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他主要的学术成果集中在组织变革、大学治理、学术治理及质量保障方面。
(四)载文期刊分布
在 2010年-2018年间,大学治理的相关研究分散在132中期刊上,发文量前十位的期刊如表4所示。前十种刊物合计发文量为169篇,占发文总量的41.1%。其中, “Higher Education”载文量最多,为 51 篇,TLCS 最高的期刊依然为“Higher Education”,数值为 49篇,说明在大学治理研究领域中该刊物最受认可,被学者引用和关注的最多。

表4 大学治理研究文献的发表期刊分布统计 TOP10
(五)载文期刊分布与核心文献分析
某文献的LCS (Local Citation Score) 数值越大,说明某篇文献受学者的认可程度越高,文献就越经典。一般认为,在本地数据库中,LCS数值为3及以上即为核心文献,因此在 HistCite软件中,将搜集的411篇文献按 LCS大小进行排序,可得到10篇高影响力核心文献,如表5所示。对比表5与表3发现,高影响力学者与核心文献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在这10篇高影响力文献中,刊物“HigherEducationStudiesinHigherEducation”均发表3篇文献,“Minerva”发表了2篇文献。核心文献对某一研究领的贡献较大,后期的研究者多是在继承核心文献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或有所突破。

表5 大学治理研究核心文献统计TOP10
综合分析表5及表3发现,Dobbins M、Knill C和Vogtle EM三者在合作的《高等教育治理的跨国比较分析框架》一文中提供了一个分析高等教育治理的综合框架,能够更系统地跟踪欧洲高等教育正在经历的变化。三者在研究了历史上三种根深蒂固的欧洲高等教育模式——学术自治模式、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后,对高等教育治理的实证指标进行系统的分类。在基于反映国家、市场和学术界之间关系的模式中,总结出权力机构平衡、财务治理、人员自主和实质性事项的经验指标[4]。Christensen T在《大学治理改革:更多自治的潜在问题?》中认为大学治理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以提高公共组织效率为重点的更广泛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论述了大学改革的一般性思想,强调大学应该像其他公共组织一样对待改革。同时他认为,大学通过改革获得的自主权会减少,而不是像企业家们经常承诺的那样,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文中的分析以组织理论中的一种变革方法为基础,将结构、文化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解释改革进程及其影响[5]。Vidovich L和Currie J在《高等教育中的自治和信任》中指出采用更多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当代高等教育的一种趋势。两者通过“信任”的视角来分析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治理政策的变化。分析表明,尽管“信任-不信任”关系的动态很复杂,但国家治理协议助长了整个教育系统的不信任文化,甚至包括特定利益群体之间达成的信任“解决方案”。这一分析为对高等教育治理的初步调查提供了一个步骤[6]。Teelken C在《遵从主义还是实用主义:学术界如何处理高等教育中的管理主义——三个国家的比较研究》中采用访谈法,通过对荷兰、瑞典和联合王国10所大学的工作人员进行48次访谈,调查了欧洲各地的大学采用的私营部门的组织战略、结构、技术、管理手段和价值观是否对高校的主要任务产生有害的影响,对这些结果在制度和专业理论框架内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将其与三个中心主题联系起来:“象征性遵从”、“专业实用主义”和“正式工具”[7]271。RowlandsJ在《学术委员会:高等教育管理中知识含量较低而学术资本较多?》中通过对比分析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学术委员会发现:大学开始以服务全球知识经济的发展为主要任务,通过研究当代大学治理结构与20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治理结构的异同发现当前董事会的权力和地位显著下降,但更加注重发挥保障学术质量的功能,而学术委员会已经成为跨国企业大学和学术工作角色和职能争夺的关键场所[8]。此外,表5中的其他核心文献分别基于不同国家研究了大学治理中的董事会角色的变化、评价与制度问题以及竞争、领导力对大学改革的促进作用等,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六)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的前沿与热点分析
1.研究前沿分析
陈超美教授认为,使用突现主题术语比使用出现频次最高的主题词更适合探测学科发展的新兴趋势和突然变化[9]。通过CiteSpace软件中的突现词探测(Burstness)功能,研究词频的时间分布,将频次变化率高的主题词从中挖掘出来,描述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表6列举了2010年到2018年间大学治理研究的5个突现词。2010年出现了两个突现词: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和大学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这可能是因为大学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越来越关注投入与效益的产出比,而管理主义符合产业组织理论的“利润最大化模式”。2011年出现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突现词;2012年、2014年的突现词是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和问责(accountability),这是与大学的外部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反映了民众对大学的呼声,要求大学承担公共责任,提高组织效率,回应社会需求。

表6 大学治理研究的突现词统计
2.研究热点分析
大学治理研究的热点可以通过该研究领域中学者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和学者们共同使用的高频关键词反映出来。本文采用 CiteSpace 5.3 R4 (64-bit),以关键词为节点,时间分区为1 年,阀值为 Top 50per slice,连线强度为Cosine,采用网络裁剪选择寻径法(pathfinder),绘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即大学治理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共得到节点170 个,连线440 条,如图2所示。

图2 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热点知识图谱
在CiteSpace中,中心性(centrality)指标可以用来观测某一节点对其他节点的联系控制作用,数值越大,控制作用越强,越需要引起重视。从表7可以看出大学治理研究的关键词主要包括:改革(reform)、全球化(globalization)、治理(governance)、政策(policy)、影响(impact)、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教育(education)、权力(power)、澳大利亚(Australia)、视角(perspective)、大学(university)、管理(management)、大学治理(university governance)、知识(knowledge)、市场(market)、问责(accountability)、中国(China)、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领导力(leadership)及政治(politics)等。分析表7可以看出,关键词的中心性排序与频次排序是不同的。从频次排序来看,高等教育位列第一;但从中心性来看,改革中心性最高,占据核心位置。这表明,在大学治理研究领域有关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较为普遍,而研究的核心集中在大学改革的研究上。此外,大学治理还与全球化、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中围绕澳大利亚大学治理的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

表7 大学治理研究高频关键词中心性和频次排序统计
结合图2、表4和表7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学治理主要围绕以下四大主题开展研究:一是大学治理的全球化视野研究,二是基于不同理论的大学外部治理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的评估与问责研究,四是基于不同视角的大学治理研究。
主题一:大学治理的全球化视野研究。全球化是当今大学治理的重要内涵,也是大学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Richard Whitley分析了经合组织不同国家的国情对大学转型的影响,分析认为,尽管大学治理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其目的显然是要将大学转变为具有权威性的一体化集体,且如果国家结构和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不太可能实现大学较高的组织行为水平,并认为目前有四种理想的大学类型可以从其战略和运作自主权、能力上加以区分:空心型、国家承包型、国家特许型和私人投资组合型[10]。Marc Tadaki和Christopher Tremewan认为国际化与全球化高度相关,大学越来越多的寻求制定国际化的战略和方案,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与国际财团接触和通过国际财团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基于此,应尝试建立国际联盟以重塑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主张用建立全球化大学中介机构的理论框架来勾画和审视国际联盟的变革潜力,并用亚太地区国际知名研究型大学联盟探索一个实证案例[11]。William Yat Wai Lo将研究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国家比较关注的“高等教育霸权”问题上,分析了全球高等教育霸权主义的本质,并运用软实力的概念,探讨全球霸权主义是如何在高等教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解释了为什么非西方国家原意遵循英美模式来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他认为新兴的大学排名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具有重塑全球高等教育格局的治理工具的潜力[12]。
主题二:高等教育的评估与问责研究。评估与问责是国外高等教育改革最流行的口号,它们作为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规制着国外大学的治理体系。Giliberto Capano调查了意大利高等教育评价与机构问责制度,包括如何在意大利高等教育系统中实施评价,大学如何承担问责责任以及问责后会产生何种影响等。分析结果显示:虽然意大利每一所高校都接受了评估,但对其自身的业绩没有任何影响;机构问责制效力低下,而大学在财务和管理的角度继续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13]。Tero Erkkil和Ossi Piironen将竞争、排名和问责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欧洲高等教育的跨国治理带来一定程度的一致性,避免分散化、碎片化的阐释。根据文本证据,问责制是以竞争逻辑为依据的,而竞争逻辑又通过比较排名的做法得到了加强[14]。Megan Kimber 和Lisa C. Ehrich用“民主赤字”的理论分析澳大利亚的大学管理,这一理论被应用于威斯敏斯特式国家的公共部门,文中分析了大学民主文化被削弱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管理人员权力的增加、审计文化的盛行和合同雇用的广泛使用,更多的是因为以问责作为反应能力的评价取代了作为责任的问责制[15]。
主题三:基于不同理论的大学外部治理研究。国外学者通过不同理论围绕大学外部治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该主题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他主题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深刻。通过阅读文献,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运用的理论为:新公共管理、制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管理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大学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组织治理理论等。Tom Christensen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大学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公共组织的效率,大学应该像其他公共组织一样对待改革,进而在财务、管理和决策事物上有更大的自主权,但实际上大学通过改革更容易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以及从政府以外的其他来源获取资源的压力[16]。Christine Teelken则从制度理论框架内分析欧洲各地大学普遍采用的私营部门的管理措施,如组织战略、结构、技术、管理手段和价值观等,同时采用实地访谈的方法,调查这些措施的有效性,以便高校提升管理效率[7]290。Richard Whitley认为,过去40多年来,许多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公共科学管理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治理机制日益趋于外向型、正规化,改变了不同团体和组织对研究优先事项和评估的相对权威,并产生了一些新的权威[17]。Jose Joaquin Brunner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分析了大学治理的类型、动态和趋势,认为成功的大学组织是能够改变其治理的,换言之,即它们的指挥机构和控制结构能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在文中,作者分析了大学治理的三种基本类型:官僚制、合议制和企业家制,无论大学治理主体如何发生变化,均是大学的密切相关者,并确定了其产生变化的力量和演变趋势[18]。Davide Donina, Michele Meoli和Stefano Paleari则从公共管理改革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国家角色,并将其与治理均衡器模型联系起来,以评价当前改革进程对意大利高等教育系统权力分享安排与协调机制的影响[19]。Ka Ho Mok批判性地考察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通过公司化战略改造国立大学的举措,得出即使这两国均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学治理的理念和做法,两国政府也不愿放弃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权[20]。MarekKwiek研究了大学治理理论模型是否适合波兰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是为了检验学院模式在波兰案例中的应用[21]。
主题四:基于不同视角的大学治理研究。国外学者对大学治理研究的视角比较多,通过比较视角、文化视角、政策视角及组织视角等审视大学治理的不同侧面。主题四与主题三的部分内容存有重叠。Ivar Bleiklie,Stefan Lange对比分析了德国和挪威在大学改革中采取不同策略的原因,得出国家文化传统对改革有着重要影响的论断[22]。Rómulo Pinheiro, David Charles和Glen A. Jones从跨国比较的角度出发,分析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三国在公平、制度多样性及区域发展问题上的挑战及方法[23]。Gilberto Capano对意大利高等教育的评价与制度问责中,分析了问责对意大利高等教育的影响,得出机构问责制的作用较低的论断[24]。Peter M. Kretek,Žarko Dragšiĉ和Barbara M. Kehm则围绕董事会成员角色的变化分析了大学治理的变化,并进一步拓展至治理行为者角色及治理行为空间等领域[25]。
三、展 望
本文通过借助HistCite引文分析软件、CiteSpace和Excel软件对国外大学治理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展示了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的具体信息。从研究内容看,大学治理依然是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成果数量基本保持上升态势,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四大主题展开,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治理的研究框架。从研究特点看,国外学者一般从全球视野讨论大学治理问题,进而与大学国际化、大学排行榜、企业化的问题产生联系。从研究方法看,以逻辑和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研究范式、以问卷调查和面板数据为基础的量化研究和以访谈、观察、案例研究为基础的质性研究均有所体现,研究方法多元化趋势明显。从研究国别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学者发文总量位居前列,说明这些国家的学者对大学治理的关注度较高,而德国的学术影响力排在第一位。从研究作者来看,对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较多,但大多数研究者是独立发文,合作发文的研究者较少,说明在该领域作者没形成研究共同体,体系化的科研网络没有形成。
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治理保持较高的关注度,成果也很丰富,其中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但总体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二元论分野的研究,难以突破二元思维的制约;在关于大学外部治理方面,则着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国家政策、政府对大学的影响,而鲜有全球视野的思维。另外,由于大学治理的复杂性,国内学者多采用“理想模型”的方法进行宏观理论阐述,但理论研究范式无法解读大学治理的微观领域,而西方学者基于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对微观领域的探讨则比较深入[26]。
总之,大学治理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不同群体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嫁接到大学身上,冲突和博弈成为大学发展的常态。大学治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主题,这就要求国内研究者既要有全球视野,又要有本土思维,要努力寻求两者的平衡。同时,良好的大学治理也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应然之意,对大学治理的研究已经从“不可为之到主动为之”,这也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