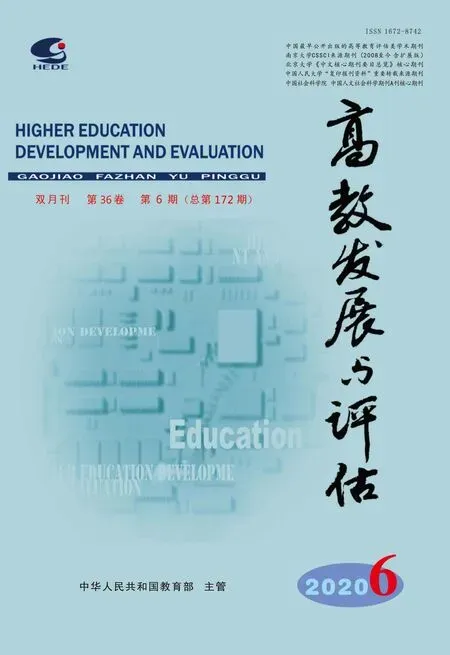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历史、结构与功能
李明忠,杨丽娜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中国院校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介性研究,目前虽已进入规范发展阶段[1],但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和组织化仍是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作为中国院校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开展的最重要专业组织,肩负着引领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化、组织化发展的重任。纵观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历程,美国院校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在积极推动美国乃至全世界院校研究的组织化、专业化及规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组织领导和专业引领作用。因此,本文通过探究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发展演变、组织结构和功能,以期为中国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与相关专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有效借鉴。
一、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历史演变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于1965年正式成立,是美国院校研究组织化、专业化的重要标志,正如卡罗琳·博伊尔斯(Carolyn V. Boyles)所言,标志着“作为高等教育一部分的整体性院校研究框架已经建立。”[2](1)1964年院校研究年会上提出成立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提议,并于1965年年会通过该提议,随之协会正式成立。美国院校研究协会官网显示的成立时间为1966年,这是指协会作为非盈利学术组织得到密歇根州政府承认的时间。很多学者倾向于将1965年作为协会正式成立时间,本文对此表示赞同。目前,协会拥有4 700余名会员(包括240余名国际会员),遍布全世界1 800多所机构,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院校研究专业组织[3]。协会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酝酿期、稳定与初步发展期、繁荣发展期、成熟期。
(一)1955年-1965年:酝酿期
美国院校研究大致分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前院校研究协会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院校研究协会时期”。美国学者泰特罗(W. L. Tetlow)认为,从17、18世纪殖民地学院的“建校研究”直到20世纪初的“院校调查运动”,均为早期院校研究活动[4]。虽然“院校调查运动”直接推动美国很多高校广泛开展自我调查研究,但却是“被动”地进行院校研究实践,并未出现大规模、有组织的院校研究活动。有数据显示,1955年,美国只有10所高校设立院校研究办公室,专门从事院校研究的人员只有几十人[5]。
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真正”的“院校研究”开始于“二战”以后。“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高校内部组织和管理日益复杂,高校开始自觉、主动地开展高校内部科学管理的相关调查和研究,直接推动了大量的院校研究办公室的成立和院校研究实践活动的开展。从1956年起,美国联邦和州教育组织、区域协调机构以及美国教育理事会等组织,通过支持、赞助或举办一系列院校研究研讨会和讲习班,积极推动高校开展院校研究[6]。例如,美国教育理事会于1957年召开大学校长会议呼吁大学尽快任命专职院校研究人员;美国教育理事会和各区域协调机构于1959年赞助并召开关于衡量教师工作量的研讨会;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斯坦福大学于1959年共同举办院校研究专题讲习班,共有113所高校的150人参加;南方区域教育委员会于1960年针对负责注册、招生、预算等工作的行政人员开设研习班;美国教育理事会于1960年委托布伦博(A. J. Brumbaugh)编写《开展研究以改进高等学校工作》(ResearchDesignedtoImproveInstitutionsofHigherLearning),以便指导高校有效开展院校研究工作,等等。这些研讨会和讲习班不但使高校充分认识到院校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推动他们设立众多院校研究办公室,而且培训大量院校研究人员,提升其院校研究能力,极大地推动了院校研究的普及推广和组织化进程。截至1965年,美国共有115所高校建立了院校研究办公室[7]46。
此外,早期成立的院校研究办公室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对院校研究的组织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芝加哥大学和“十大联盟”(Big Ten Universities)等十一所高校的院校研究人员于1960年成立了院校研究委员会(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Eleven),定期举行专题研讨,交流院校研究资讯,开展大量跨院校研究,为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建立做了有益探索。他们举办的“院校研究研讨会”(seminar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把分散的院校研究力量聚集起来,使参会者认识到举办一个常规化会议的重要性和价值,这一共识使本次研讨会成为院校研究年会的雏形。1961年3月,第一届“院校研究年会”(The National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orum)(2)1961年举办第一届院校研究年会,1965年成立院校研究协会,自1966年起,协会将院校研究年会这一活动作为协会年会延续下来,至2020年已连续举办60届。正式在芝加哥举行。前两届参会资格仅限“邀请-出席”方式,只有部分区域协调机构和高校院校研究办公室的50余名人员参会。考虑到这种参会方式的局限性,同时为了更好地凝聚与壮大院校研究力量,第三届年会放宽参会资格,参加人员激增至200人,故而年会在规范性管理方面作出较大改善,要求参会人员积极提交论文,增加专题报告和主席演讲环节,其规范性、开放性与影响力得到持续扩大。随着年会的连续召开,分散的院校研究力量逐渐汇集,联系更加密切,互动更加频繁,建立一种组织制度以有效凝聚、管理及服务院校研究人员的需求日益迫切。在1965年的第五届年会上,美国院校研究协会正式成立,最初共有会员382名[8]125。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成立是美国院校研究发展中的里程碑,标志着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院校研究的正式开始。
(二)1965年-1975年:稳定与初步发展期
1965年-1975年是协会谋求稳定并取得初步发展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定义IR”和完善组织结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院校研究在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中已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正如弗朗西斯·鲁尔克(Francis E. Rourke)和格伦·布鲁克斯(Glenn E. Brooks)所言,“在高等教育中使用现代管理技术趋势的核心是院校研究。”[7]41但院校研究在内涵、性质与功能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论,“学术抑或管理”之争首当其冲,因此,“定义IR”成为协会在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1970年,乔·索普(Joe L. Saupe)和詹姆斯·蒙哥马利(James R. Montgomery)发表的《院校研究的性质与作用:给高校的备忘录》(TheNatureandRoleofInstitutionalResearch——MemotoaCollegeorUniversity)认为,院校研究主要是通过数据收集与分析、提供咨询建议等工作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决策和有效运作[9]。对院校研究的这一新阐释得到院校研究领域各方人士和相关机构的高度认可。另外,西德尼·素斯洛(Sidney Suslow)在这场争论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不断明晰IR的概念边界、积极争取埃索教育基金会(ESSO Education Fundation)的赞助而组织召开院校研究未来发展的专题研讨等一系列工作,有力地推动院校研究定位“管理而非学术”的发展方向。
随着协会对院校研究的定义与阐释为其专业化发展和实践活动开展指明方向,完善内部组织结构成为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任务。比如,协会为了加强管理、保障自身有序运行,于1965年出台《AIR章程》(AIR Constitution),从制度和规范上不断完善内部结构。再如,为了支持、管理和规范一系列院校研究主题的专著和其他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协会于1972年设立出版物委员会(Publications Board),从1973年开始发行《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74年开始发行《院校研究新方向》(NewDirectionsforInstitutionalResearch)系列丛书,进一步加快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进程。1974年AIR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AIR)的设立是协会组织结构和治理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协会早期的工作场地和经费均依赖于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志愿人员所属机构的支持,具有志愿组织与志愿人员的鲜明特点,难以大规模地推动院校研究的开展。为了大规模、高质量、更加规范地推进院校研究工作,协会专门设立AIR办公室并聘请行政主席(Administrative Director)(3)协会主席每年换届,至今共53届主席。执行主席无任期限制,至今共4届,简·丘拉克为第一任行政主席,第二任则由行政主席改为执行主席,先后由特里·罗素、兰迪·斯温、克里斯汀·凯勒担任。——简·丘拉克(Jean Chulak),开始拥有固定办公场所、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执行财务、会员资格、年会、出版物等方面的行政职能,从本质上实现了从志愿组织到专业组织的转变。随着这一时期协会的稳定发展和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会员人数直线递增,从1965年的382名增加到1975年的1 060名[8]125。协会还不断调整会员资格的标准及分类,1976年修订的《AIR章程》取消了正式会员和准会员这两种带有等级色彩的类别,重新规定定期会员、研究生会员、退休会员和杰出会员四种类别。
(三)1975年-1990年:繁荣发展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方面,由于美国高等教育持续遭受经济困扰,致使高等教育入学率下降,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信任降低,院校研究对高校改革发展的咨询决策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存在价值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来源渠道和分析技术更加多样、分散,导致一些非院校研究人员也开展院校研究工作,各高校院校研究办公室的职责和院校研究人员的工作范畴日益模糊。为了解决院校研究的生存问题,提升其研究质量,协会于20世纪80年代围绕“信息与技术”“院校研究角色”“提升质量”等主题召开学术年会和专题研讨,正视信息技术对院校研究的挑战与冲击,增强信息技术与院校研究之间的契合性,提升院校研究的质量。其中,伯纳德·希恩(Bernard Sheehan)提出了著名的“三帽理论”(Three Hat Theory),其核心观念是院校研究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应戴着决策者、分析师和技术人员的帽子,系多重角色于一身[10]。这一思想对理性认识院校研究的生存价值,明晰院校研究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院校研究者的作用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
随着生存危机得以解决,协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规模持续扩大,组织结构日益完善,积极制定未来发展规划。第一,协会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第一个国际性附属机构——欧洲院校研究协会(European AIR)成立;仅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本土14个州的区域组织加入协会;会员人数和参加年会人数均创历史新高,国际会员更是从1973年的51个增至1981年的259个[8]65。第二,协会组织结构日益完善。协会为适应内外部需求与变化,增设多个委员会,如设立附属机构委员会(Affiliated Groups Committee)和国际发展委员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具体管理附属机构和协调国际交流合作事务。第三,制定协会发展规划。面对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协会逐渐将焦点转移到未来发展规划和会员专业发展方面。1982年,AIR办公室任命一个由12人组成的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ssion),历时18个月,制定了第一个重要规划——《重新评估协会的宗旨与目标》(ReassessthePurposesandObjectivesoftheAssociation),建议协会向非会员开放专门知识资源,发展更多类型会员,提升会员专业能力[8]67。协会积极采纳此建议,比如,在会员专业发展方面,协会积极拓展服务领域,针对会员的不同类型制定不同目标的专业培训计划,设立“杰出服务奖”“荣誉奖”“论坛最佳论文奖”等来表彰为协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会员,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会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四)1990年至今:成熟期
1990年代协会的重点是调整组织治理结构和提升院校研究专业化水平。第一,在协会治理结构调整方面,表现为两点:其一,聘用专业人员作为执行主席。随着简·丘拉克的退休,协会迎来重要变革时期。过渡委员会对协会性质、办公室结构与工作业务等方面进行调查后得出重要结论,办公室工作需要增强院校研究专业声音。因此,协会于1991年9月第一次聘用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特里·罗素(Terry Russell)为执行主席(Executive Director)。从行政主席到执行主席的转变体现协会治理方式走向专业化管理道路。其二,董事会成为协会的理事机构。为了使领导政策与治理方式相适应,协会于1993年重新审查并修订《AIR章程》,成立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替代执行委员会,并任命董事会成员为各委员会主任。执行主席作为联结董事会和各委员会的重要纽带,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各委员会的活动中,不但使其行动力得到有效增强,而且也使各委员会从相对孤立走向协作,极大改善了内部组织文化,艾伦·查菲(Ellen Chaffee)称这一系列变化为:“从一种非常特别的'家庭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行政化、合法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8]83第二,在院校研究专业化水平提升方面,得益于特里的专业领导、人脉关系及其不懈的努力,协会获得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的大量资助,制定新的培训计划——AIR研究机构系列(AIR Institute Series)、增加出版物和奖学金等。协会还于1992年正式通过《院校研究职业实践与道德条例》(TheCodeofEthicsandProfessionalPracticeoftheAssociationforInstitutionalResearch),并成立职业道德工作专责小组,推进职业道德教育的培训与宣传,提升院校研究人员的专业认同和身份认同。协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职业道德标准的制定以及会员专业培训活动的开展,逐渐推动院校研究从一个职业领域发展为一个成熟专业。
21世纪初是过渡期,协会面临各级政府拨款减少、特里退休、缺少专职工作人员等诸多挑战,过渡委员会较好地解决了这些困难并取得进一步发展。2007年,AIR办公室迁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购置了永久性办公大楼;执行主席兰迪·斯温(Randy Swing)在2007年-2016年任职期间,争取来源多元的捐赠,开展更加多样化的会员服务与专业发展机会,提供院校研究认证服务,极大地促进了协会的发展。其中,会员数量从3 810名增加到4 105名,增长近8%;协会总资产从210万美元增长到470万美元、净资产从85万美元增长到390万美元[11];AIR办公室专职人员从11人增至22人,专职人员的增加不但使协会减少了对志愿人员的依赖,而且极大提升了专业管理水平。随着斯温即将卸任,董事会于2016年5月成立执行主席遴选委员会(Executive Director Search Committee),委托AGB招聘公司(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earch)寻找具有良好协作与精湛领导能力、丰富专业知识的新任执行主席。2017年,克里斯汀·凯勒(Christine M. Keller)就任执行主席,在其领导下,协会更加注重与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组织开展合作、举办研讨、出版专著,致力于通过数据和研究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改革和发展。
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协会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规范化、成熟化的专业组织,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院校研究活动开展和专业化发展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正如比尔·拉舍尔(Bill Lasher)所言,协会已经并将继续对院校研究的开展产生深远影响[8]133。
二、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经过近六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董事会为领导核心,由AIR办公室、各委员会和国内外附属机构等多元结构共同组成的专业组织,如图1所示,引领和推动着美国乃至全世界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
It is thus clear that the Phu ri collection includes manuscripts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at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m belonged to a very early period such as the 10th century, whereas the latest ones go back to the 14th century.

图1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组织结构
董事会是协会的理事机构,由副主席、主席、前任主席3名领导和9名一般成员构成,他们代表全体会员利益,制定符合协会自身的组织愿景与行为期望,征求会员意见并运用于决策制定,定期评估组织绩效[12]。在3名领导中,仅副主席一职由会员代表选举产生,共任期3年,第一年担任副主席,在主席无法履行职责时代表其行使权力,并担任治理指导与培训委员会(Governance Orientation Training Committee)主任;第二年接任主席一职,负责组织和协调协会及董事会各项工作;第三年则成为前任主席并兼任提名与选举委员会(Nominations & Elections Committee,NEC)主任,以其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管理经验,协助、支持主席和副主席开展协会工作。9名一般成员由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任期3年,可担任董事会秘书、协会的财务主管或各委员会成员等职位,除此之外,还需要参与董事会自我评估,协助董事会新成员完成任职培训,协助协会组织活动,与会员及各委员会保持有效联系等工作。
AIR办公室是协会的执行部门,接受执行主席的领导,目前共有28名工作人员,包括4名执行团队成员和24名工作人员。4名执行团队成员为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Executive Director & CEO)、执行副主席兼首席财务官(Deputy Director & CFO)、战略技术主任(Strategy Director of Technology)和高级研究与创新主任(Senior Director for Research & Initiatives);24名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会员参与、会议服务、教育和研究、传播与营销、财务与运营等事宜[13]。自1974年成立以来,AIR办公室一直负责组织院校研究年会,管理与出版院校研究刊物,处理协会国际性事务等职能,尤其是2007年以来,随着协会购置永久性办公大楼,AIR办公室人员规模增大,职能更加多元,积极满足协会各方面工作的需要,为其组织化、专业化、国际化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协会不断调整完善组织结构,董事会会根据具体情况设立或解散各个委员会。实际上,AIR办公室承担的很多职能最初是由各个委员会负责执行的。比如,专业发展委员会(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的宗旨是为协会会员专业发展和继续教育提供指导和监督,国际发展委员会负责国际会员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交流和合作。目前,委员会分为常设和特设两种类型。常设委员会包括三个,一是提名与选举委员会,基于公平、公正、科学原则组织提名与选举工作,为董事会和各委员会精心选举资质优异、经验丰富、领导力强的领导者;二是治理指导与培训委员会,每年为董事会和NEC的新老成员提供组织治理的指导和培训计划;三是IR未来委员会(IR Future Committee),主要帮助董事会成员及会员了解院校研究和协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提供相关咨询建议。特设委员会则是基于某项任务而暂时设立,随着任务完成则予以解散,例如会员类别委员会(Membership Categories Committee)、最佳论文奖委员会(Best Paper Award Committee)等,前者负责会员资格与类型的制定和调整,后者负责年会学术论文的评审。
拥有附属机构是协会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协会拥有43个本土附属机构,包括6个非地域性附属机构(Non-Geographic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11个区域性附属机构(U.S. Regiona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26个州或地方附属机构(U.S. State/Loca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协会还拥有8个国际附属机构(International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涉及欧洲、北非、南非、东南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台湾等地区的院校研究专业组织[14]。附属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专业团体,他们和协会之间遵循相互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正如里奇·霍华德(Rich Howard)所言:“他们更独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互惠协议的联盟,而不是把他们当做美国的区域性组织。”[8]87
(二)治理方式
协会实行“志愿领导+专业治理”的独特模式,采用以约翰·卡费(John Carver)首创的政策治理模型(The Carver Policy Governance Model)为主的治理体系[15]。这一治理体系赋予董事会领导协会的权力,代表会员制定协会的组织目标,规范协会的运行方式,评估协会的工作成效。协会的具体管理由执行主席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致力于通过精准战略和有效行动来实施。
《AIR章程和法规》(AIRConstitutionandBylaws)和《治理政策》(GovernancePolicies)作为协会治理的两个重要文件,明确规定了协会的性质、宗旨、管理机制和治理政策。《治理政策》赋予执行主席治理权力,明确了董事会与执行主席的权力范围与问责制度,执行主席在董事会制定的政策基础上,享有绝对的执行力,不受董事会及其成员的干预,以完成协会愿景为最终目标[16]。因此,董事会是一个志愿性领导团队,不直接参与协会的日常运行,而是制定凸显AIR价值观的治理政策,并将所有权力授权于协会的执行主席。执行主席作为协会的首席执行官,应对董事会制定的协会业绩和目标期望负责并接受问责,通过领导和管理AIR办公室,以其富有远见的战略眼光和高度的专业能力实现协会的各项目标。同时,会员自我管理和志愿服务也是协会治理体系的优良传统。协会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和专职人员,志愿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奉献对协会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密歇根大学一位员工曾为1973年年会顺利召开志愿工作1 500小时(4)因1 500小时换算每日10个工时,则需工作150天,从其工作时间与工作量来说,不符合志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笔者对此产生质疑,因无其他参考文献进行核实,故作出解释。详见:RICE G,COUGHLIN M A,HOWARD R.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The First 50 Years. Tallahassee: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2011:56.,时至今日协会年会论文的评审工作仍由会员志愿参与完成。
三、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主要功能
美国院校研究协会自成立以来,在推动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利用数据资源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决策、提升会员专业素质与专业能力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院校研究有效开展的权威领导者和首要践行者。
(一)推动院校研究专业化发展
第一,明确界定院校研究内涵。院校研究的性质、作用和价值的争论一直伴随着院校研究的发展[17]。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抑或管理”之争,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生存危机,甚至是21世纪面对学校效能运动冲击所带来内涵模糊、功能缺失、工作范畴不明等问题,都需要协会在科学界定院校研究内涵、明晰工作职能等方面做出积极应对。一方面,自1961年第一届年会召开以来,60届年会中共有37届年会主题与“院校研究”自身有关,如“定义IR”、“院校研究的概念框架”、“院校研究的当务之急”、“院校研究角色”等。另一方面,协会多次开展院校研究全国性调查活动,以便更好地了解院校研究工作范畴和工作重点。例如,在21世纪面对学校效能运动中“IE”(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对“IR”的功能冲击,协会于2012年开展了一项高级IR和高级IE领导者工作范畴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协会的一系列努力中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人物和理论,伯纳德·希恩的“三帽理论”、詹姆斯·弗里德里克斯·沃克文(James Fredericks Volkwein)的“黄金三角”(Golden Triangle)理论均是其中的典型,他们在科学界定院校研究的内涵与价值、重新审视院校研究的职能与范畴、明确院校研究人员的角色定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推动院校研究专业知识的生产、出版与传播。协会拥有学术期刊、专著、电子刊物、研究报告等众多出版物,为院校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奠定了重要知识基础。1973年创刊的《高等教育研究》是协会会刊,被赞誉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风向标”;1974年开始出版的《院校研究新方向》,是协会为探讨院校研究相关问题而专门设立的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180余本,呈现院校研究的最新前沿、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被沃克文评价为协会最有特色的出版物[18];协会主办多种电子刊物,例如每月通讯eAIR关注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最新信息和院校研究最新实践动态,《专业档案》(ProfessionalFile)主要转载与院校研究实践和院校研究模型有关的热点文章,《院校研究应用》(IRApplication)则专注于院校研究的方法、技术和工具;研究报告是协会围绕院校研究相关主题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和评估活动的成果。这些出版物作为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前沿与实践指导思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院校研究领域的核心知识,而且成为推动院校研究专业化的重要驱动力。
第三,制定院校研究领域的职业道德条例。为了更好地推动院校研究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协会于1992年秋制定出台了《院校研究职业实践与道德条例》,随后于2001年、2013年进行修订。这一条例在院校研究的能力、实践、保密问题及职业规范等方面,为院校研究专业人员提供了一整套职业道德标准,旨在帮助会员加强院校研究职业岗位认知,提高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明确院校研究人员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实现协会对美国高等教育改革以及高校发展的专业服务作用[19]。由此可知,该条例作为指导院校研究职业实践的重要道德原则与标准,体现了院校研究作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领域应具有的专业性和规范性。
(二)为高等教育提供数据支持和科学决策
提供基于数据分析的科学决策是院校研究的核心功能。院校研究人员只有将收集到的数据转化成推动高校改革发展的有效决策,才能发挥其作用。协会官网的阐述“高等教育发展的数据和决策”(Data and Decis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便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注重数据的收集与共享、加强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提供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是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第一,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同类高校因为可能会面临相似的管理问题,所以在数据需求方面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数据的收集与交流共享是协会的重要工作。一方面,协会不但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大规模数据调查活动,而且支持会员自主开展调查研究,为高等教育界及会员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另一方面,协会与美国大学数据交流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Data Exchange,AAUDE)、高等教育数据共享协会(Higher Education Data Sharing Consortium,HEDS)等组织和数据库共享数据,以便对高校管理决策制定提供支持。
第二,加强院校研究人员数据分析能力的培训。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数据类型和新的分析工具为院校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分析方式。因此,协会十分注重院校研究人员数据分析能力的培训,会不定期对会员开展新工具新技术使用情况的大型调查,比如对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系统、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分析工具和谷歌学术搜索等数据类型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对策和开展专业培训,帮助院校研究人员尽快学会使用新工具新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协会在每年年会上均为有关组织和厂商提供最新院校研究软件展示的平台,包括各种数据库、统计分析软件、数据测量工具和技术等,为广大会员提供了解和购买的便捷渠道。更重要的是,协会为不同层次的院校研究人员提供不同的数据分析课程训练,如为新入职人员提供提升研究技能的“数据与决策培训课程”(The Data and Decisions Academy),包括“院校研究的工作性质及工作内容”、“数据管理”、“实用调查设计”以及“将数据转化为支持性决策”等主题[20]。
第三,通过数据分析促进高等教育科学决策与规划。协会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接受捐赠或委托等形式,大力开展院校研究实践活动,在提供大量数据和信息的基础上,为联邦政府、高校领导、政策制定者等提供科学决策和有效建议。例如,协会根据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捐赠要求,开展了《关于全国院校研究办公室的调查》(NationalSurveyofIROffices)、《制定院校研究的理想实践声明》(StatementofAspirationalPracticeforInstitutionalResearch)等项目,不但提出了一种综合的院校研究方法,而且开发了一种院校层面的自我评估工具,有助于实现高质量院校研究实践的发展愿景[21]。协会还与全美学生事务管理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Personnel Administrators,NASPA)联合开展全国性调查,并基于数据分析提出多项改进建议,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成功[22]。由此可知,协会在数据导向的决策模式中,活跃在院校研究、政策评估及发展规划等各个领域,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发展提供科学决策和规划建议。
(三)促进会员的专业发展
协会是一个庞大的会员制组织,致力于为广大会员提供专业资源、学习平台和实践机会,大力提高其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能力,推动其专业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为会员提供专业服务是协会的首要宗旨。
第一,提供专业资源。专业资源是最基本的会员福利,可满足会员专业发展的基本需求。会员可从协会出版物、电子刊物及各种院校研究项目中获取专业资源,如,会员可通过会员专属福利——AIR电子图书馆(AIR E-Library)——订阅协会的学术期刊、专著以及《专业档案》等,及时跟踪学术前沿,开阔研究视野,提高专业素养。
第二,提供交流与学习平台。协会通过组织学术年会、专题研讨及专题培训等活动为院校研究人员(包括会员和非会员)搭建交流与学习的平台。例如,2018年协会年会持续五天,参会者高达2 000余名,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300余次,除年度会议外,还设有一系列专题研讨、提高院校研究人员新技能的研习班、晚餐小组交流活动、相关专业资源(包括出版物、研究报告、最新数据库和分析工具等)的展览等,对加强会员学术交流、开阔视野有积极作用。再如,协会针对不同层次的院校研究工作人员制定不同发展目标的职业培训课程,涉及院校研究的知识、技能、方法与素养等方面的培训。有为新入职院校研究人员提供的训练课程,一般由经验丰富的研究专家开设课堂,在线学习,为期6周;还有为院校研究资深专家提供综合性课程,包括领导力课程、科技与分析技能课、项目管理类课程,确保这些资深专家晋升为管理者后,能更好地管理团队,胜任更具挑战性的工作。由此可见,专业培训的内容针对性强,学习方式灵活,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深受欢迎,效果极佳。
第三,支持会员参与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协会为了提升会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开辟了形式多样的有效途径,包括提供院校研究工作最新最全的职位空缺信息,提名本人或同事担任协会领导,设立表彰奖项,提供研究资助等。例如,协会专门设立“杰出贡献奖”表彰为协会及院校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会员;协会与NCES、NSF等联合设立项目资金,每年资助3-10项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和3-10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23]。
四、结 语
1965年成立的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不但是美国院校研究专业化、组织化、制度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是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一步重视,亟需高等教育研究和院校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和智力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作为目前中国院校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专业组织,应积极借鉴美国院校研究协会的先进经验,深入推动中国院校研究的专业化、组织化发展,提升院校研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和高校改革发展的服务能力。
第一,完善院校研究分会自身组织结构。美国院校研究协会不但有固定办公场所、较充足的经费支持和较大规模的专职工作人员,而且具有结构完整、分工明确、运行良好等特点。与之相比,中国院校研究分会及秘书处先后挂靠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理工大学等单位,属于挂靠性学术组织,虽设有理事会、秘书处和学会章程等,但在组织结构、治理方式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如办公场所、办公资金主要由挂靠单位提供,各项事务工作大多由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兼任,导致无法大规模、高度专业化地开展各项活动,不利于院校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院校研究分会在保留专业人员志愿工作和服务之外,应进一步完善内部结构,加大秘书处办公室的建制和投入力度,聘请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加强分会的功能拓展。
第二,推动中国院校研究的组织化建设。院校研究分会应充分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指导和帮助各省份和各高校加强院校研究。一是鼓励和指导各省成立省级院校研究机构,可纳入院校研究分会的附属机构,从省级层面推动各省院校研究活动的深入开展。四川省院校研究会作为中国首个省级院校研究会,通过积极举办年会与学术研讨会,凝聚四川省院校研究力量,鼓励与支持院校研究实践活动,有效推进了四川院校研究工作。随后,陕西省院校研究会于2013年成立,河北省院校研究会也于2018年开始筹备,省级院校研究会在推动本省院校研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是提升本省院校研究水平、增强高等教育实力的重要平台。二是促进各高校或新设院校研究办公室,或推动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向院校研究机构转型,从组织机制和制度保障方面推进院校研究。刘献君教授极力倡导高校设立院校研究机构,并建议大部分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实际承担的主要是管理研究与管理咨询等院校研究工作,应转型为院校研究机构,从而组织化、制度化、科学化地开展院校研究工作[24]。
第三,促进中国院校研究的专业化发展。院校研究分会及部分高校虽举办过一些专题培训班,但由于时间过短、规模不大、实践性不强等原因,致使成效不明显[25]。随着院校研究组织化制度化建设对院校研究专业化和院校研究人员专业化的诉求日益迫切,院校研究分会应在继续开展专题培训班的同时,需要在以下两方面积极努力:其一,进一步加强教材、专著、学术期刊等专业知识的生产和出版,构建院校研究专业化的核心知识体系。可喜的是,院校研究分会于2018年12月15日举办“院校研究课程与教材建设学术研讨会”,针对院校研究课程建设、中国院校研究丛书编写等主题进行了研讨和部署。其二,加强院校研究专业人员的培养和培训。一方面,考虑到目前中国部分高校已在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等学科下设置院校研究方向的现实状况,建议院校研究分会积极制定院校研究的相关课程和知识要求,通过构建核心课程模块、注重研究方法学习等,加强院校研究方向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院校研究分会领衔并组织相关专家积极论证院校研究专业设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可考虑在教育学(或管理学)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抑或考虑设置兼具教育学、管理学、大数据等的跨学科专业,并做好院校研究专业学位质量标准、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等方面的科学规划和调研论证,推动院校研究成为一个专业并提供相应学位,大力培养院校研究后备人才。
第四,提升院校研究分会的专业服务水平。其一,充分利用分会这一平台及其影响,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专业引领及交流沟通等作用,在办好年会的同时,积极构建院校研究共同体,通过不定期召开专题研讨和学术活动,为广大会员和院校研究人员提供学习、交流的机会,进一步增强学术服务水平。“中国院校研究优秀青年学者”评选活动就是院校研究分会在会员服务方面的有效举措。其二,领衔并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开展专题研究,通过设计研究选题、组织相关力量、提供课题资助等形式,进一步促进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合作,努力提高中国院校研究的整体水平。其三,明确“学术立会”导向,加强分会的智库服务功能,在引领思想、服务决策及推动实践等方面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和高校改革发展提供高水平专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