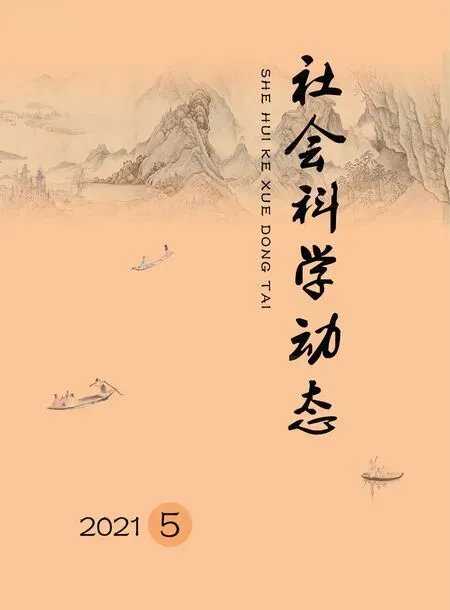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观念探析
——兼与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多”观念比较
严存生
“政治”乃管理 “众人之事”。“政治”是个复合词,既可以作名词用,即“政”——公共的社会事务;又可以作动词用,即“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或治理。“政治文化”即一个社会对 “政治”事务及其管理所形成的观念和技术 (体制、制度、方法)。世界上各地区、国家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因而其传统的 “政治文化”和体制也有所不相同。我国的 “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强调集中统一 ,它与西方的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力分散明显有别。本文探析了我国的这一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真谛,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了简要地比较。
一、 “一” 与 “道”
“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用于表达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个概念。“道”是存在于事物内部决定其存在和发展道路的东西。“道”无处不在,无事不有。但它隐含于事物之中,无影无形,不能为人的感官所认知,人只能通过心的静思(理性思考)来领会它。因而“道”给人的感觉是“虚”。被人认识和诉说的“道”就是“理”。我国古代人认为,世界是统一的,因而有统一的“道”,它是各种事物的总根源,又是有差别的,世界上有天、地和人三类大事物,各有其“道”和“理”。人过社会生活之“道”和“理”就是“义”。“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它是人际交往的原则和观念。“礼”者,即礼节仪式,它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仪表、准绳,是制度化了的道义,用以规制人的言行,使之和谐统一。
“道”的观念揭示了事物的共同性、同一性,即同一类事物有共同的本质、根源、运动规律和共同的归宿。因而“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统一,故“道”也别名为“一”。《黄帝四经·道原经》曰:道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刑(形)。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则(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刑(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 《黄帝四经·十大经·成法》 曰:“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以守一名。上拴之天,下施之四海。吾闻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复一,民无乱纪。……一者,道之本也,胡为而无长。□□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於天地,一之理,施於四海。”老子的《道德经》 也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应该指出的是,“道”之“一”,不是“唯一”“单一”,而是“统一”“同一”“一体”或“普遍性”。因为“唯一”“单一”说的是存在的绝对“独立性”,此物与它物不相容,即没有任何交往和联系。“统一”“同一”“一体”否认这种观念,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虽然存在着千千万万种事物,且事物与事物是有差别的,每种、每个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但由于它们都存在于世界中,因而会与其他事物有交往,彼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彼此交融在一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能联系起来,结成一个统一体。此叫“普遍性”“同一性”。这就是说,是“和而不同”或“合而不同”。用当代流行的一个观念来说叫“一体多元” (One diversity),它的含义是任何复杂的事物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多种渊源,或者说其内部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是一个“多”和“一”不断变化的过程。因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的和简单的,或者说都是“一分为二”的,甚至是“一分为三、四……”的。不仅客观存在的事物如此,而且人对这些事物的认识所产生的概念、观念也是如此。一句话,事物之间存在差别和矛盾,但也存在共同性,因而事物只能在与其他事物保持的总体统一中追求“独立性”,不能破坏总体的统一,否则就破坏了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我国文化把“一”与“道”联系起来。
二、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 “政” 与 “一”
(一)“政” 的概念
“政”即“政治”,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作为名词,指社会的公共事务,作为动词,又简称“治”“牧”,广义上指执掌国家权力,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包括防御外敌、治灾、治恶、治邪,治奸,惩罚不轨者,维护社会秩序,使之符合人生和社会之道。故称执政者为“执道者”。管子在《君臣上》中曰:“道者,诚人之姓(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此)是无以理人,非兹(此)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在《兵法》中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形势解》中曰:“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又曰:“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荀子·王霸》 曰:“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由此看来,执政者的任务就是通过选贤任能和立法定制等各种办法宣传和维护道义,并躬身示范之。周文王曾问太公:“何如而可以为天下?”对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可以求天下;恩盖天下,然后王天下;权盖天下,然后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后天下恃。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东汉末思想家荀悦在谈到“政”时说:“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民作基,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业,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贤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业惟敦,是谓政体也。致治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无由行矣。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行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谓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正因如此,执政者执政时应树立起“道行天下”“公天下”“民为本”等一系列观念。如夏禹时《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已明确地提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周初的《六韬》中已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吕氏春秋·孟春纪·贵公》中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顺民》 曰:“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管子·权修篇》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 《管子·权修》亦有言:“君人者,以民为天,民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亡”。①《孟子·离娄上》 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荀子在《王霸》中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要视“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汉之贾谊对“民为本”的思想做了更全面的论述。他说:“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呜呼,戒之哉,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
(二)“政” 的真谛是 “正”
《管子·法法》曰:“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正”其含义丰富,包括几个方面:
首先,是执政者要“名正”,即其名位有正当性、合法性。因为“名正”才能“言顺”,发布的政令才有权威性。《论语·子路》 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以措手足。”“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次,其执政的目的是使人们的行为符合“道” (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种人各随其性,各尽其宜,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并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管子·君臣上》曰:“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此)是无以理人,非兹(此)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管子·兵法》曰:“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再次,是执政者品行端正,方法公平,即执政者站在公而不是私的立场上,发布和执行政令。因为只有如此,其政令才可能是正确的,也才可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和遵守。《论语·子路》 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颜渊》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管子·牧民》曰:“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管子·法法》曰:“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
复次,执政者必须用手中的权力,并依法用赏罚两种办法,鼓励符合道的行为,惩罚有悖道义的行为。这样一来,社会才有统一的秩序。《管子·法法》曰:”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管子·正》 曰:“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
(三)“政” 所追求的形式价值是 “一”,方法是 “致中和”
在我国,强调“统一”特别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甚至把“一”与“政”统一起来,说“政”或社会治理就是“一”,故称之为“一政”“一众“一民”。这意味着,“一”是政治追求的价值目标值之一。《礼记·乐记》曰: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管子·立政》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 《管子·明法解》曰:“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得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境)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
如何在方法上实现“一”,“合”呢?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回答是“致中和”。“中”者“中庸”。其“中”者“适当”;“庸” 者,“用”也。不同的物,适当地用,事适当地处理,其结果就是“和谐”“统一”,既各得其宜,又能合而为一体。故“中庸”也称“中和”。②其核心是“过犹不及”,有度,正当,政事中坚持“中庸”原则,才会取得理想的结果。《论语·学而》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荀子·儒效》曰:“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正当”应有三义:
其一,是名正,名当实,实事求是,对社会事物性质的认识和概括正确。包括其所获取得名位的公正。即执政者其地位名分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管子·心术上》 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 《管子·白心》曰:“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名自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九守》中又说:“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于实,实生于德,德生于理,理生于智,智生于当。”
其二,更重要的是治理中所出台的政令合于事物的本性,使其物各随其性,各得其用;人各展其才,各随其愿;事各得其宜。《管子·版法》 曰:“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其三,是令当其时,即政令的发布的时机恰当,合于时势,能与时俱进。故《管子·立政》曰:“出令时当曰政”。
(四)“政” 实现 “一” 和衡量 “中和” 的标准和方式是 “法”
“政”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中和”,那么,衡量“一”“中和”的标准是什呢?古人的回答是礼法。《荀子·王制》曰:“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荀子·儒效》曰:“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因为,“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管子·法法》 曰:“政者,正也……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尹文子也说:“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 《韩非子·有度》 曰;“一民之轨,莫如法。”《鹖冠子·度一》曰; “守一而制万物者,法也。”
为什么是礼法呢?因为礼法是道之用③,是表现于现实生活中的道,从而也是衡量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它以社会权力为后盾,因而也是实现道的最有效的手段。对此许多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均有论述。
如《黄帝四经》 指出,法渊源于道,是道之用,是显现出来的道。法是根据对道的认识而制定出来的,用以衡量事物的准则。二者的区别只在于一个隐,一个显;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一个神秘,一个明白。《十大经·观》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经法·道法》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 正因如此,用法来统一人们的行为,治理国家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客观的依据。法是公正无私的,用法来治国理政就能取得好的效果,但“以法度治”者不得背离道。《经法·君正》曰:“法度者,正(政)之至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经法·道法》曰:“称以权衡,参以天当。天下有事,必有巧验。事如直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也就是说,有了“法”这个辨别是非和区分真伪的标准,我们就能识别繁杂的事物,也就能以正确的方法安排我们的行动和治理好国家,使之符合“道”的要求。这也意味着不能背离道“以法度治”。《经法·道法》曰:“故执道者④,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是治国理政要 “以法度治”,而“以法度治”要严格遵循道,不能随意制定法,否则就会召来灾祸。《经法·君正》曰:“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又曰:“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
又如管子在《君臣上》中曰:“道者,诚人之姓(生)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试)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此)是无以理人,非兹(此)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国,其道临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诸民,其所恶者能除诸民。所欲者能得诸民,故贤材遂;所恶者能除诸民,故奸伪省。如冶之于金,陶之于埴,制在工也。”在《兵法》中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形势解》中曰:“民之从有道也,如饥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阴也。故有道则民归之,无道则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又曰:“道者,所以变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则言自顺,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
再如荀子在《王霸》中曰:“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愍、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埶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由此看来,我国政治上强调“统一”,实际上是统一于“道”之用的“法”。也就是说,包含着“法治”的意蕴。
三、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 “一” 观念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一)对 “政治” 中 “一” 的人性思考
我们知道,人是地球上一种特殊的物种,即具有理性思辨能力(自由意志)因而会追求自由(独立自主性),并过着群居或社会生活的动物。而自由意味着独立,社会意味着统一。二者似乎是对立的,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依赖和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只有在社会中才会产生和增长,自由也主要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的不受制于他人,能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活动时。而且,由于人们的交往会使他们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需要社会组织制定相应的规则作为标准,以划清其合理性的界线,协调解决已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存在离开社会的所谓个人自由。离开社会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当然也不会有自由可言。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进行,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人的自由的实现,也不例外。所以,不能从单个人的意义上去谈人的自由问题。个人的自由只有在集体中和在社会里才可能实现,也才有意义。正如马克思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有可能有个人的自由。”⑤这意味着在人性中存在一个矛盾——追求自由、获得独立与必须统一过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因而必须接受所在社会组织的约束,从而是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故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⑥。因为,政治正是基于并消解、统一人的这种二重性的一种机制。它把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协调统一起来,使它们不相冲突,并能融合于社会组织的整体的价值追求中。很显然,在人类历史的很长时期里,国家正是这样的社会组织,而法律则是其划分各种自由合理与否的权威性尺度。因而国家的执政者就是社会分工中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员。
由此看来,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是政治动物,也决定了应把“一”作为政治活动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因为社会组织越大、团结越紧密,才会越强大,人们才能从中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精神文化财富。所以,自由是社会的,个人自由应以社会自由为前提和基础。
“一”的政治文化观念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作用是很大的。它不仅使我国保有广泛的疆土和深厚的文化,而且在世界上长期处于繁荣强大领先的地位,也使我国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统和很高的组织纪律性。而这些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战胜重大的社会和自然灾害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短短几个月中,在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发动的种种围攻战(贸易战、科技战、边境的军事挑衅战、疫情甩锅战)的不利环境下,我国却迅速地控制住疫情和恢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其动作之迅速,组织之严密有效,令世界各国无不佩服和称奇。
不过,理想和现实并不是完全同一的。由于在历史上人们对“一”的正确全面地理解有个过程,加上其他观念的干扰⑦,和历史环境的特殊⑧,因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了君主制的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但不能因此否认政治上的“一”的观念的合理之处。
(二)我国政治文化中的 “一” 与西方政治文化的 “多” 相比较
世界是复杂的,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文化上会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我国政治文化中的强调统一有别,西方政治文化中则强调了“自由”“多”和“分”。这特别表现在其“政治自由主义”⑨理论,尤其是其中的“个人自由至上”观念和“分权制衡”理论。
“个人自由至上”观念主要表现于国家权力起源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权观念中。社会契约论是近代西方流行的关于国家权力起源的一种假设。它认为人类的历史可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两个阶段。“自然状态”是人类的无政府状态。那时,人们各自独立地生活着,因而享有一种自然的自由或权利。但由于个人势单力薄,加上彼此间难免发生冲突,因而很难以战胜猛兽,生活很不安定,充满着危险和痛苦。人是有理性的,实践使大家逐渐地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签订一个彼此不相伤害的契约,即制定出能表达着正义的法律,并把其一部分自然权利让渡和集中起来成为一种能维护这一种契约,从而能更好地保护其自由的社会权力,即国家组织,才能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说,国家权力来自人们的自然权利,并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权)。而且,由于人们在签订社会契约时,并没有交出所有的自然权利,只是交出了自卫权⑩,因而国家权力的使用是有限的,不能侵犯未交出来的那部分自然权利。这意味着,自然权利(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渊源,保护自然权利(人权)是其存在的目的,因而自然权利(人权)是至上的,“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权力来源于和服务于它,并以之为限。所以,在他们心目中,个人永远置身于国家之上,个人是“原子”式分散地存在的,个人和个人之间永远不可能融为一体。包括家庭中夫妇之间,各有其私——隐私和私产。社会中的各种组织也是一样,如各种经济组织(企业、商业、金融业)、文化教育体育组织、政治社团(政党)等,包括国家内部各部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是分离的,并享有绝对的“独立性”。中央和地方也是如此,多实行联邦制,地方享有部分独立的权力。这样一来,在西方的社会观念里,社会是分散存在的一个个的个体和群体,是不可能真正地把人们统合为一体的,国家只是他们名义上的政治领导,并不享有控制其行为的绝对权力。因而,在西方的政治文化里,强调的是“自由”“分散”“多”,而不是“一”。
显然,西方的这种社会观念是有其合理之处的,即它看到人性中追求自由的价值,以及自由存在和发展中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因为人类社会的精神物质财富是有赖于人的高度自由的,政治上的压制自由会桎栖人精神上的创造性。但离开社会的统一而过分地强调自由和分散,显然是不科学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会使一个社会的人们难以凝聚为一体,从事巨大的社会事务,如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次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就是例子。西方大部分的发达国家,有优越的医疗条件,之所以制止不了疫情,而且使之泛滥起来,越来越严重,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西方占主流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不敢采取有力的措施,阻止人们群聚,从而错过了防治的有利时机。而受自由主义政治观念影响下的这些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自觉地接受这些阻止行动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如公共场所戴口罩、居家自禁、禁止举行群众性聚会,停工、停课、封城),甚至还出现以游行示威的办法公开对抗这些措施实施。
应该指出的是,西方的“政治文化”在观念上强调“多”“分”“斗” (博弈),除了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占主流的人性观念上的“性恶论”。这一“性恶论”认为人生而“自私”,是个“功利”的动物,政治精英们也不例外。如他们说,人内心不具有道德动机,其行为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进行的。如商人只是为了获取有利润才与其他人交往,在交往中把别人不是当目的,只是当工具对待的。⑪正因如此,他们为了获得所理想的利益,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欺骗、厄诈、暴力等非道德手段。政治精英们也是如此,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争权夺利,在政治斗争中使用的手段是公开的欺骗和阴谋鬼计,所以都应被视为一伙“无赖”⑫。西方的其他思想家还认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必要的恶,即为了制止更大恶——无政府状态而使用的暴力。正因如此,西方的政治文化是不主张真正的统一的,也不认为在政治活动中使用不道德手段是不“正当”的。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政治活动,包括“民主”制国家的政治都非常混乱,充满着欺诈和恶斗,很难达到真正和长期的统一,处于实际上的分裂状态。其在国际的政治活动中更是如此,推行从林法则,肆意地破坏自然环境和掠夺别国的资源,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高喊“X 国第一”的口号,随意地制裁不听话者,甚至用战争、暗杀等恐怖手段实现其罪恶的目的。但是,显然,这样的行为是难以长期地维护其强大、统一和霸权地位的。这也就是西方历史上长期达不到统一的原因所在。
概言之,“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用以表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范畴,“一”是其别名。“义”为人的社会生活之道,而“政”则是实现社会生活的“一”的机制,作为“道”之用的“法”是用于衡量“义”的标准。这是因为,人是地球上的一个特殊物种,具有理性思辨能力,因而向往着自由(独立),是主张“分”的,但由于个人势单力薄,难以独立地生活,因而又被迫与他人联合起来,过一种群居或社会的生活。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生存下来,并称霸于全世界。这意味着人性中包含有两种对立的因素或价值取向:“分”或“多”与“合”或“一”。分为了追求自由(独立性),而合(组织起来)才能获得根本的和更大的利益。这两种价值追求,表面上看似是对立的,实际上却是可以融合的。因为“一”与“多”是与 “合”与“分”相对而言的,“合”或“一”是以“分”或“多”为前提和基础的。“分”的越“多”,个体的独立性越大,其创造性才会越大,因而“合”起来“一”才会越大,越有意义。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的“合”往往是以某些突出的个体为核心形成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是可以融合统一的。而“政治”就是把二者融合统一起来的社会机制。它通过建立各种社会组织及其相应的社会规则,特别是公共权威性的政治国家组织和法律规则的办法来实现这一任务。而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具有公共权威性的国家组织和法律规则正是实现这一政治使命的最好方式。因为国家组织的法律规则是站在“公”的立场,依据人之“道”(本性、规律)为全社会确立了统一的行为标准,并凭借其社会权力保障它被普遍地遵守。显然,这个“统一”是允许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由的,只要这些自由是“合理的”,即不侵害别人的同样自由和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法律洽洽是衡量这一合理性的准则。由此看来,“政治”所追求的价值是“一”,而这种“一”是允许某种程度的个体自由的,所以其本质是“和”,即和谐。只有以它为前提和基础,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所以“一”包含着“多”。显然,我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符合这种“政治”观念的。而正因如此,这种观念的合理性保障了我国传统文化持续了五千年,并且长期繁荣强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虽然清末一百年来,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下有所衰落,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迅速地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科技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获得了两弹一星的巨大成果;上个世纪下半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用了不到半个世纪,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显然,这与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强调“一”的观念有某种密切的关系。而这次能奇迹般地战胜新冠肺炎和在世界霸权主义的多重围攻之下立于不败之地,更清楚地显示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因而,我们应客观地、正确地评价这个传统的政治文化,批判西方一些政治家对它片面地歪曲和攻击,克服其局限性,挖掘其合理的价值,使其在百年难有的大变动中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继续发挥指路明灯的作用
注释:
① 据说,齐桓公曾问管子“王者何贵?”管子回答曰“贵天”。齐桓公于是台头望天。管子接着说:“所谓天者,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背)之则亡。”语出汉代韩婴《韩诗外传》卷四。《曹刿论战》中亦有言:“君人者,以百姓为天。”
② 《说文》“庸,用也”,《广雅·解释诂》 “庸,和也。”
③《易传·系辞上·第十一章》曰: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管子·任法》曰:“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④ 执道者又称“义者”。《十六经》曰:“吾畏天,爱地,亲民”“所谓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宵。”“义者,众之所(愿)死也。”《经法》曰:执道者,“俗者顺民心,德者爱勉之”,施政时“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4 页。
⑥ 他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 ‘出族、法外、失去坛火 (无家无邦的人)’,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第6—7 页。
⑦ 如君主至上观念。
⑧ 由于人类社会初期,家族、部落、部族的很分散,中央政权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地方的控制不可能十分有力,因而出现了部落联盟制、家族国家等政治体制。其统一的过程也难免充满着军事暴力。这与政治文化上的“一”观念,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能视为对其理解和实施的一种片面性,或者也可以说是其实现中历史中所走的一段弯路。
⑨“政治自由主义”是近现代西方流行的一种政治观念,这种观念极力主张“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认为人生而自由,而市场是展现和实现这一自由的最好场所。政府在其中所起的只是“守夜人”的作用。即只是个人自由的保护者和调结者,无权侵犯“个人自由”和干涉“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
⑩ 霍布斯认为交出了全部自然权利,洛克认为只交了出自卫权。
⑪ 如亚当·斯密说:“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3—14 页。
⑫ 休谟说:“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第 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