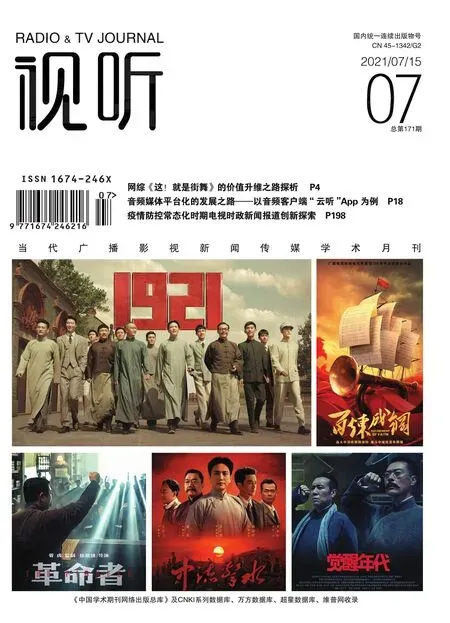电视人文主义下边缘话语呈现的伦理透视
——以《和陌生人说话》为研究对象
洪 图
《和陌生人说话》是由陈晓楠主持、腾讯新闻出品的一档网络访谈节目。节目摒弃了传统名人大腕分享人生的套路,更多选取被社会忽视或极少被关注的群体的故事。例如22岁国内知名的“杀马特教父”、为死囚犯写遗书的前服刑人员,该节目创新性地对话这些特殊群体。本文以该栏目为研究对象,梳理媒体对于边缘话语的深刻影响,并从融合传播角度积极构建合乎伦理的访谈策略。
一、边缘话语媒体呈现的正当性
在市场利益的引导下,情感能够成为一种消费的产品。不少访谈节目消费当事人的生活遭遇,有声音质疑边缘群体在访谈节目中的曝光。实质上,媒体传播边缘话语,对边缘群体本身和社会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媒体传播赋权
美国学者巴隆曾提出媒介接近权的概念,其核心要点是社会中的成员有权通过大众传媒获得观点的自由表达。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大众传媒时代媒介传播平台和渠道较为稀少的状态得到改变。然而由于权力资本的背后操控,边缘群体的传播力微弱,不能像强势集团那样占有主流媒介进行发声。因此数字媒介时代下,网络媒体成为这种小众力量得以展示的平台,访谈节目有利于对各群体公平传播,协助边缘群体增加其权利和能力。
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指出,赋权是一种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来自小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当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对话”时,赋权的效果更为显著。首先,访谈节目为边缘群体增加社会动员。如第七期《我不是神女》中,节目对话校园精神暴力受害者,引起了同样有被霸陵遭遇的群体在微博发声。栏目给这些边缘群体提供了组织的媒介。其次,访谈节目打破边缘群体社会交往的屏障。媒体传播的过程本身也是对边缘群体的赋权过程。原先不被人熟知或理解的“人体冷冻”“重金整容”等边缘行为,通过节目的呈现,在社会中拓宽了相关群体生存的基本依靠。
(二)重塑社会认同
曼纽尔·卡斯特在探讨集体认同问题时提到,“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人们获得社会认同是基本的生存需要。但由于地理、经济的隔阂,我们无法以第一视角直接和各类群体接触,因此主流大众常依据自身刻板印象对边缘话语赋予消极意味。访谈节目的深入对话,正在改变这场认同危机。
首先,谈话栏目减少阶级隔阂。对曾经被视为异类的“杀马特教父”而言,怪异形象是他和世界交流的方式,在这背后正是四五线城市年轻人和社会之间的隔阂,体现着留守儿童抱团取暖的辛酸。在媒体的对话过程中,受众逐渐淡化了对这类群体的负面标签,重新给予被挡在主流话语规则之外的社会下层群体理解和认同。
其次,谈话栏目弥合社会偏见。节目中涉及到丁克一族对家庭和自我的新风尚、爱美女性对整容的推崇和自我认同等边缘话语的记录,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世俗观念的偏见,将他们与所谓的“道德缺陷者”划清界限,在倾听、包容之下最终导向多元的社会话语。
(三)受众自我审视
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认为,人能够与自身进行互动,“自我互动”是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内在化。通过自我传播,人能够在与社会他人的联系中认识自己,并不断实现自我的发展和完善。《和陌生人说话》节目中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不断转变,给人们日益不变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观赏视角。
《和陌生人说话》与边缘群体的对话过程,也是受众自我传播的过程。在《我给死囚犯写遗书》一期中,观众看到死囚身上被忽视的人性一面,然而犯罪后的醒悟已无用。因此受众在倾听对话的同时,遵守规则和敬畏生命的观念也在自我传播,正如节目口号“我们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随着媒体的深入对话,人重新审视自己,并采取积极、正向的行动。
二、访谈类节目存在的伦理问题
媒体呈现边缘话语的作用不可小觑,与此同时,节目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症结也不可忽视。访谈节目在呈现边缘话语过程中表现出的选题不当、采访越界、逼问细节等都会加剧边缘群体的痛苦。
(一)选题庸俗,背离健康风气
正如尼尔·波兹曼描述的媒介时代:“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某些调解访谈类节目看似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实质上在贩卖普通人的生活悲剧,用庸俗吸睛的选题来换取收视率。此类访谈节目选择离奇个案,过度展示畸形与丑恶,严重影响了大众传媒的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访谈节目为获得社会关注度,往往会和有一定成就和名声的偶像或明星产生关联。例如某期访谈《我找明星女儿要5000万》,当事人的诉求在普通的法律咨询中已经被否决,但节目组在知悉该“影星”的真实身份后,仍然选择将此类选题搬上荧屏,违反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二)呈现不当,构成二次伤害
二次伤害是指当事人已经受到伤害后,由于媒体工作者不规范的采访方式,给当事人及其亲属带来了第二次的伤害。部分访谈类节目为达到节目效果,采用“揭疤式”访谈策略,深度挖掘当事人的隐私,又无力支持后续的康复和安抚,使被访者承受外界和内心的双重伤害。
发生此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主持人采用不恰当的采访方式。边缘群体所经历的事实,主要来源于被访者的自我叙述。但部分主持人对于事件前因后果过分关注,在采访中忽视被访人的情绪,将访谈凌驾于基本的人性之上。其次,电视影像画面过分放大隐私。相比于言语,图片和视频的视觉冲击力更强,受众对视觉信息的信任程度远高于文字。电视栏目中常见对当事人经历的影像再现,影像中被夸大的事实、过度追求的细节,可能导致被访者受到外界的二次解读,因负面的评论引发二次伤害。
三、合乎伦理的媒体呈现策略
在边缘话语被“标签化”解读的当下,媒体把握好对边缘群体报道的责任伦理十分迫切。只有从采访方式到影像制作再到现场布景和选题等节目生产的各个流程中都贯穿着责任伦理思想,才能弥合社会偏见,弘扬公平正义。
(一)主持人不越界:不定义、不评论
边缘群体由于自身的特殊经历,“贴标签”“剑走偏锋”“单枪直入”的访谈方式对于话题度的他们可能会造成影响。因此在访谈中主持人更需注重人文关怀,不应立足于主流文化的道德规范对被访者进行单向抓取。在《和陌生人说话》节目中,主持人陈晓楠运用“自画像”式的访谈风格,充分给予受访者说话的空间,努力将访谈营造成真实的聊天状态,使被访者的自我叙述始终是交流的主线。
主持人作为倾听者,其不越界的采访行为对传播品质和效果有益。采访不越界能够体现媒体人素养,维护节目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在必要时刻的留白艺术,也将对边缘群体的评价和思考留给观众,唤起观众意涵丰富的情感共鸣。
(二)优化影像制作方式:保留隐私之地
视觉影像的传播伦理,含有传播者对用何种方式手段传播视觉作品的思考。首先,节目简洁明快的剪辑手法,删除了一些叙事情节,只保留被访者的语气和形态,为当事人保留隐私之地。在《猎艳者》一期中,关于“五步陷阱法”只做了点到为止的呈现。“最大限度传达信息,最小限度造成伤害”,应成为传播者在节目制作中需要遵循的指导思路。
其次,节目采用后现代主义制作风格,以温和的方式折射出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和陌生人说话》栏目时长较短,给予观众轻松自由的观看状态,使节目成为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探讨平台。节目融入“素人”采访,由于人们的理解方式存在差异,因此读者获得的认知也各不相同,这就在制作上规避了栏目对边缘话语的议程设置。节目认可了不同个体的多元化思想,让更多人对社会现实问题产生进一步的思考。
(三)创新布景,构建私人心理场
心理学家勒温在1936年提出了心理场的概念。他把人和环境视为一个格式塔整体。心理场并不完全等同于物理场,个人言行思想受诸多内外、远近的因素复合引发。《和陌生人说话》节目既是电视节目,也是对有特殊经历的当事人的情感介入,因此媒体呈现形式需注重拉近受众与被访者的距离。
首先,《和陌生人说话》节目在采访环境布置上相对简单,以白色靠椅和灰色背景墙为主要陪衬,被访者不会受到外界声音的干扰,观众也更能将注意力集中于主持人和被访者的话语中。此外,近景和特写镜头的多次使用,进一步缩短了观众与被访者的心理距离。对私人心理场的创新布景,更加真实地还原了受访者的经历,更营造了观众的心理在场,从而产生对边缘话语的情感认同。
(四)审慎选题,坚持媒体责任伦理
媒体处于市场竞争中,节目内容的生产纷纷以受众趣味为导向,忽视了媒体从业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媒体作为社会的探测器,对于边缘群体的关怀不能缺席。
首先,访谈节目所关注的议题应当下沉,将报道视角拓展到社会的边缘群体,传递未被关注的声音诉求。其次,媒体的责任伦理所包含的范畴,更包括长远的未来,对边缘话语的关注不应伴随着节目热度的下降而散去。再次,在信息繁杂的时代,媒体对于边缘群体的形象建构常常有失公允,难以用中立客观的标准扩展议题。因此媒体应减少自身的主观价值判断,将涉及到价值取向的问题放到特定的情景中讨论,全面地呈现事件的本真。
四、结语
在福柯的观点中,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中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通过一系列的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边缘群体的牢固控制。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媒体对于边缘话语的呈现能够改善边缘群体的“失语”现象。边缘话语的媒体呈现,能够督促媒体承担责任伦理,在传递边缘群体声音的同时,形成温情、理性的社会风尚,构建融合传播时代下多元开放的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