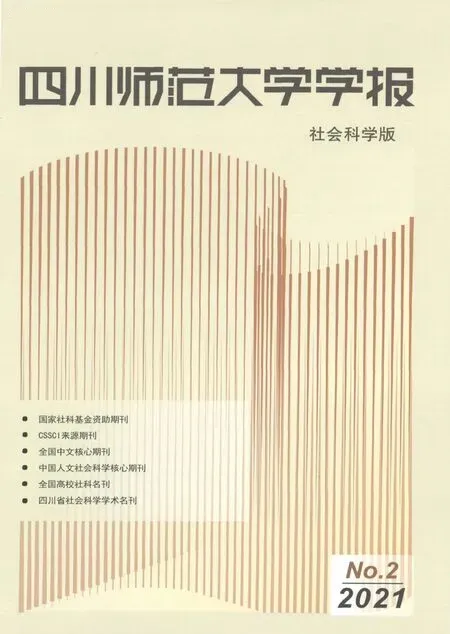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二卡”的世界:卡夫卡与卡尔维诺寓言小说之比较
罗文彦 曾艳兵
奥匈帝国作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和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是西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两位伟大作家。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二卡”创作的寓言小说却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个异彩纷呈的世界。
一直以来,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卡夫卡的大部分重要作品都准确描绘了现代人或其异化物身处荒谬世界中的孤独感和被排斥感,而且他“将现实转换成一种寓言,并循着神话追溯人类生存的痛苦”(1)Pawel Ernst, 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 (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4), 255.。因此卡夫卡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可以当作揭示生命痛楚的寓言来解读,这些作品的“深度和形式深深吸引了世界各国的读者,卡夫卡笔下生活在绝望世界里的人物,其实是在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的生动写照”(2)〔捷〕拉德克·马利《寻找卡夫卡》,卢盈江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而卡尔维诺恰是这些深受影响的读者之一,他在40余年的文坛生涯中一直尝试用各种手法表现当代人孤寂而惶恐的生活和心灵。卡尔维诺曾表示:“对一名作家来讲,真正的挑战是利用一种看似缥缈,可以产生一种幻觉的语言,来解释我们所处环境的错综复杂,就像卡夫卡那样。”(3)〔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王建全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于是他呈现给我们一个个明亮、奇诡而又富于童话诗意的寓言世界,其本人也被认为是一位明显带有后现代风格的寓言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卡尔维诺对卡夫卡这位前辈极其推崇。他在《为什么读经典》(Perchéleggereiclassici)一书中明确把卡夫卡纳入经典作家之列——“我爱卡夫卡,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4)〔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他还在一些访谈和论著中多次提及卡夫卡的作品,甚至准备为他最喜爱的卡夫卡作品《美国》(DerVerschollene)推荐作序,后因突然离世未能成文。由此可见,卡尔维诺熟谙卡夫卡的作品,而且在他的寓言小说中也能感受到卡夫卡非凡的想象力、震撼的异化主题及简练精确的表现手法等对他的深刻影响。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曾对“二卡”作品中的关联发表评述:“《看不见的城市》(it:Lecittàinvisibili)就像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一样,能够在欣赏者理解的模式中继续流传,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传奇的纯粹形式、奇妙的体裁和思考的境界。这篇小说和卡夫卡的《中国长城》(BeimBauderChinesischenMauer)一起,为我们需要而又已不配得到的,或争取不到的文学赋予了新的活力。”(5)〔美〕哈罗德·布鲁姆《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童燕萍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然而卡夫卡与卡尔维诺都属于无法轻易界定的独创性作家,“二卡”在原创思想和个人风格等方面都具有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卡夫卡认为“理解的开始即是对死亡的渴望”(6)〔英〕约翰·萨瑟兰《耶鲁文学小历史》,王君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因而人类在荒谬窘境中的悲伤和沮丧也就无处可避,但卡尔维诺在此中却看到了生活的意义与希望。此外,卡夫卡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自己颠覆传统又一以贯之的风格,而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则似一台不断磨合、调试的文学机器。这些关联与疏离使得对“二卡”寓言小说的比较研究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显现出他们作品跨越时代的经典性。
一 相连的世界
卡夫卡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作品(3篇未竟的长篇小说和近80多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以变形、荒诞的意象寓示现代人的异化、孤独、迷惘等窘境。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以“业余作家”的身份孤独地献身于自我书写,直到逝世后他的价值才逐渐为人所知,不但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还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英国时下畅销书作家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新作《蟑螂》(TheCockroach)就在向卡夫卡致敬。书中的主人公吉姆先前在生活中受尽白眼,一觉醒来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蟑螂,同时成为了英国最有权势的人。如此离奇的情节不难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变形记》(DieVerwandlung)中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卡夫卡虽然带有“现代主义作家”的标签,但实际上在西方小说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但突破了传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还启发了后世,推进了后现代主义的发展。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四五十年代的荒诞派以及六十年代的美国“黑色幽默”都能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找到影子。同样,被认为是典型后现代作家的卡尔维诺也不能简单地以后现代主义来界定其所有作品,在他看来,“在文学形态上面,很难区分出之前和之后,或者在‘传统’和‘先锋派’中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7)〔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学机器》,魏怡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因此,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卡尔维诺之间不可能是泾渭分明、毫无交集的。现实中卡尔维诺就曾多次表达对卡夫卡的肯定和赞赏。在其编著的《怪诞故事集》(RaccontiFantasticiDell’Ottocento)中卡尔维诺点明了卡夫卡的寓言小说在表现内心悲情时的巨大力量,认为此种表现可与美国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最成功的道德寓言作品相媲美。此外,卡尔维诺还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具有强有力的讽刺力量,直指他是一个爱幻想的人,把卡夫卡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共同视作两位大师,“虽然方式有所不同,但表现手法同样精确、简练,而且像钉子一样干脆”(8)〔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学机器》,第140页。。
卡尔维诺还在其小说诗学著作《美国讲稿》(Lezioniamericane:Seiproposteperilprossimomillennio)第一章“轻逸”中特意提及了卡夫卡的一则小故事《煤桶骑士》(DerKübelreiter)。该故事篇幅短小但意义隽永,后来还被收录到我国中学语文课本中。卡尔维诺对此的评论是:“卡夫卡的许多短篇故事都很神秘,这篇尤胜。……这个空桶是贫苦、愿望与追求的象征,它使你离开了互助与自私的地面,把你提升到你那谦卑的请求再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程度。作者的这种构思能使我们产生永无止境的联想。”(9)〔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很明显,卡尔维诺从中获取的最直接的联想就是首章题名——“轻逸”。没有煤就落不到地的“煤桶骑士”只能悬浮在空中,是那么的“轻”,而他背后的生活却是那么的“重”。这种反差深深地吸引了卡尔维诺,以轻示重,以文学的“轻逸”克服现世的“沉重”,成为了卡尔维诺一贯倡导和追求的重要文学标准。为此他还特地引述了“柏尔修斯杀死美杜莎”这则希腊神话,认为“柏尔修斯的力量在于始终拒绝正面观察,而不是拒绝与妖魔共处”(10)〔意〕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第226页。。这里“不拒绝与妖魔共处”可视作不避讳现实的沉重与黑暗,而“始终拒绝正面观察”则是不欲自身石化,最终柏尔修斯依靠最轻的物质(风和云)和间接的形象斩杀了妖女。卡尔维诺在此以柏尔修斯的事迹表明他并非忽视或否认“重”的存在,只是不喜欢因生活的“重”导出文学作品的“重”,反而用“轻”直面这个世界,以此将“重”克服,而不是与其一同沉沦。之后,卡尔维诺进一步表明“轻”是与精确、果断相连而与含混、疏忽无关,它建立在深思之上,不是空洞的轻浮之“轻”。为此他还点明了“轻”的三种含义:“一、减轻词语的重量。从而使意义附着在没有重量的词语上时,变得像词语那样轻微。……二、叙述这样一种思维或心理过程,其中包含着细微的不可感知的因素,或者其中的描写高度抽象。……三、具有象征意义的‘轻’的形象。”(11)〔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第5页。总之,在文学“轻逸”的表面承载的实是另外一种更大的重量。将此投射在卡尔维诺的寓言小说中很少有让人感到沉重的东西和压抑的气氛,即使所述与现实相关也似真似幻,就连战争场景描写也没有直白、血腥的画面,反而像是一出人间的恶作剧。由此可见卡夫卡的“以轻示重”对卡尔维诺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然而卡夫卡的寓言小说不仅是卡尔维诺“轻逸”思想的溯源地,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异化表现也被卡尔维诺汲取吸纳入自己的寓言小说中。卡尔维诺曾表示:“卡夫卡以为自己是在写形而上学的寓言,却以从未被超越的方式道出了当代人的异化。”(12)〔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美国讲稿》,第17-18页。由此可见,异化是卡夫卡寓言小说的一个重要标签并引起了卡尔维诺的注意。卡夫卡早期作品《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甲虫之变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异化形象,给文学界带来极大启示和震撼。之后卡夫卡常常在其寓言小说中将人异化为弱小的动物,如鼹鼠、猴子、耗子、狗等,以表现被现实社会摧毁和迫害的凡人。如此,“人的异化”就成为卡夫卡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作为对自我和世界的深层次思考引发出人与社会之间早已割裂的状态。而为卡尔维诺带来国际声誉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中(Ilviscontedimezzato,Ilbaronerampante,Ilcavaliereinesistente)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异化形象——“分成两半的子爵”。所幸的是子爵最后复归为一,成为了一个善恶交错的“正常人”,而格里高尔却未能恢复人形,只能在被社会和家庭抛弃后郁郁而终。此外,三部曲中另一个经典形象“树上的男爵”和卡夫卡的“煤桶骑士”也都表现了类似的身体异化,而且结局都是乘风而去不知所踪。但仔细对比仍有差异,男爵树上栖居的异化行为是主动的,是为了更好地和现实相处。他最后的离去方式也实现了自己永不下树的承诺,因而见证了他一生的墓志铭:“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这说明男爵的一生是有意义而且完整的。而“煤桶骑士”则是位底层人士,骑行空桶只为求煤维生,被驱赶后无奈飞到冰山那头。他的行为是被迫的,结局不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悲剧故事。除了异化为具形的生物,卡夫卡还在《家长的忧虑》(SorgenderEltern)中杜撰了一个谜一样的生物——“奥德拉德克”。与它对应的是卡尔维诺《宇宙奇趣集》(TutteLecosmicomiche)中的“qfwfq”——一个不断变化的精灵。区别在一个是追寻该谜团,一个是借其观察世界,讲述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透过这些形似的异化形象可知,卡夫卡和卡尔维诺寓言小说中的异化表现有所关联但又大相径庭。虽然他们都借助异化这一方式为我们描绘了有关现代人的诸种困境,但卡尔维诺明显展现了他对人类自身发展和社会前景抱有的希望,而卡夫卡则表现出他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不安。
卡夫卡寓言小说中流露出的这种情绪无疑也使读者感受到了时代的痛苦与荒诞。同时这些寓言小说又具有晦涩曲折、情节支离和思路跳跃的特性,很多故事无源无终没有明确的方向。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甚至在其书《悠游小说林》(SixWalksintheFictionalWoods)中提及一段轶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借了一本卡夫卡的小说给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后者奉还时却说:“我读不下去,人脑没有那么复杂。”(13)〔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黄寤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爱因斯坦作出如此感慨是因为卡夫卡的大多数作品都把一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化为了夹缠不清的“迷宫”。而卡夫卡也自愿困于“迷宫”中,尽量不透露出谜底,给读者留下无限阐释的空间,让人难以理解却又引人求解,得不到解答的读者们只能徜徉在“迷宫”中往复求证。这些把卡夫卡和读者们都困于其中的“迷宫”,实则反映的即是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现实。
作为卡夫卡的书迷,卡尔维诺自然也从其作品中领略到了现实社会迷宫般的纷乱与荒谬。但卡尔维诺已不满足于再现如此迷宫,他向迷宫提出了挑战:“外在世界不啻一座座迷宫,作家不可沉浸于客观地记叙外在世界,从而淹没在迷宫之中。艺术家应该寻求出路,尽管需要突破一座又一座迷宫,应该向迷宫宣战。”(14)何太宰选编《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为此,卡尔维诺寓言小说的写作对象囊括了整个宇宙,从古至今、从人类到非生物、从地球到外太空,力求从多维度展现迷宫的多样性。此外,卡尔维诺还大胆创新,利用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原理,通过戏仿、互文、元叙事等多种表现手法重构自己熟悉的现实元素,以丰富的表现形式剖析迷宫的复杂性以展现其意义。《命运交叉的城堡》(Ilcastellodeidestiniincrociati)、《看不见的城市》(Lecittàinvisibili)、《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Seunanotted'invernounviaggiatore)等都是卡尔维诺挑战迷宫的优秀代表作品。卡尔维诺不仅提出问题,还努力寻找答案并追索意义,体现了与卡夫卡截然不同的认知差异。
诚然,卡夫卡和卡尔维诺是分属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伟大作家,但他们的寓言小说世界却有着深切的关联,“后辈”卡尔维诺无论是在文学思想还是在创作手法方面都深受“前辈”卡夫卡的启发。但这又并非是两个沿袭重合的世界,它们闪现出两位作家各自鲜明的个人特征。
二 “法的门前”与“圣约翰之路”
虽然书写于不同时代,卡夫卡和卡尔维诺的寓言小说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映了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威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必然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和思考,并在各自的寓言小说中有不同的展现。
从卡夫卡的寓言小说中,我们能直接感受到权力机构带来的压抑氛围,它能摧毁任何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普通人。这种影响通常以各种表象出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其中最具代表性且给人深刻印象的即是强大的“法”的形象。在卡夫卡的寓言小说中,“法”、“法律”所代表的威权实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意象,这并非单纯地出于卡夫卡的专业和职业角度,还有原生家庭带来的深刻影响。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早年生活艰辛,创业成功后逐渐形成了强势、严厉的性格,即使对家人也非常专制。而卡夫卡本身又是一个优柔寡断、精神敏感且脆弱的人,在父亲的强力压迫下主修了法律专业,毕业后郁郁寡欢地从事一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因此在无法抗拒的父权和工作双重压力下,文学成为卡夫卡纾解情绪的唯一出口,他在这个自我世界里肆意地表达着个人感受。从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判决》(DasUrteil)就能直观感受到这种对强大父权的无条件服从:书中的父亲叫儿子去死的时候,那个“我”的身体便先于意识行动,条件反射般地从桥上跳入河里。这种自然而然的服从来自卡夫卡自小的父权阴影,儿时他曾因半夜找水喝不断哭闹而被父亲从床上拎起来,关在门外。卡夫卡曾在《致父亲》(AufVater)一书中描述此事对他的影响:“以我的天性,我根本无法把我认为很自然的那次荒唐的要水的哭闹同极其可怕的被抱出去这件事联系在一起。许多年后我还经常惊恐地想象这么个场面:那个巨大的人,我的父亲,审判我的最后法庭,会几乎毫无理由地向我走来,在夜里把我从床上抱到阳台上去,而我在他眼里就是这样无足轻重。”(15)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插图本):第7卷》,叶廷芳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第342页。或许就是这件令卡夫卡终身难忘之事触发了《审判》(DerProzess)的诞生,他把压制性的父权进一步提升为强大的权力机构即“法”所代表的威权实体,后者对普通人具有无可辩驳的压倒性威势。
《审判》讲述了一个荒谬离奇的故事,银行襄理K在30岁生日当天无端被捕,他为了摆脱“被告”身份上下奔走,但最后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一年后终被带走被私刑处死。书中逮捕K的理由未知,执法机构也非常神秘,看似威严公正的部门实则沆瀣一气。K在奔走呼号无果后终于明白他能做的唯一有意义的事就是在“被告”席上等待审判,个人与“法”的悬殊对比映衬出“法”的霸权与威势,人在其面前极其渺小无能,只能被动地接受与服从。书中一个重要片段是神父在训导K时给他讲述了一个“法的门前”的故事,这则小寓言可视作整篇小说的注解,也让K幡然领悟到自己与法的真实关系。故事中乡下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在法的门前徘徊、不得而入,弥留之际法的守门人为他点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在这里取得进入的许可,因为这个入口是专为你而设的。现在我要走过去把它关上”(16)〔奥〕弗兰兹·卡夫卡《审判》,姬健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4页。。这里专为其设置的法门即是专为其做的判决,被判决者不能主动靠近,只能被动等待,继而神父说出了点睛之语:“判决不会突然下达,审判程序会逐渐变成判决。”(17)〔奥〕弗兰兹·卡夫卡《审判》,第250页。于是K明白了自逮捕命令发布之时起对他的判决就已经启动,于是他工作开始魂不守舍,活动于各色人等却又处处碰壁,这种等待和煎熬也是给予他的判决内容。所以最后被黑衣人带到行刑地时K束手配合、毫无反抗之意,只有死亡才能让他彻底摆脱作为“被告”等待判决的命运。卡夫卡在《审判》中准确描述了普通个体面对威权的绝望,以平淡而冷静的语气揭示了在荒谬的“法”的门前一般人如同蝼蚁般渺小而徒劳的命运。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城堡》(DasSchloss)中,威权又幻化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堡”。书中土地测量员K想尽各种办法,无论如何都靠近不了“城堡”,最后无奈而亡。两部作品的主人公有着相同的名字和类似的命运,无论威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距离普通个体无限遥远,它强大的压制性力量让人无法主动靠近,只能被动地徘徊和忍耐。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18)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与此相对应,卡尔维诺在其寓言小说中对有关威权的描述与处理却与卡夫卡大相径庭,这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有着一定关系。卡尔维诺出生于一个科学家家庭,从小在多元、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孩童时母亲就给卡尔维诺订阅了儿童画报,引发了他无尽的想象力并逐渐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战胜利后他入读都灵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出版社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和卡夫卡相比,卡尔维诺的成长过程更加轻松、顺意,他从事的职业正是他自小的兴趣所在,虽然父亲也曾希望子承父业,但对他的选择并未多加干预。卡尔维诺曾撰文《圣约翰之路》(LastradadiSanGiovanni)追忆父亲,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勤恳而令人尊敬的人,父子关系也较为平和。他曾坦言:“我的童年波澜不惊,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又平静的世界里,我对于世界充满多姿多彩和层出不穷的想象,却对激烈的冲突毫无概念。”(19)〔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论童话》,黄丽媛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由于他和卡夫卡有完全不同的个人感受和经历,即使面对相同主题,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样态。
出现类似父子关系紧张情节的卡尔维诺寓言小说《树上的男爵》就让我们看到了和《判决》完全不同的走向及结局。书中柯西莫和弟弟由于放走了作为食材的蜗牛被父亲鞭打一顿后关进小屋,结束惩罚后柯西莫仍然拒绝吃蜗牛膳食。父亲让他从饭桌上滚开,柯西莫愤而攀上了庭院中的圣栎树,父亲威胁他“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我绝不下树!’他说到做到”(20)〔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吴正仪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即使受到父亲的肉体惩罚和言语斥责柯西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与《判决》中就算是荒谬的命令也不敢丝毫违逆父亲的儿子形成鲜明对比。但柯西莫并没有完全割舍亲情,他仍然关心父亲的健康并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家族的佩剑,“我将尽一切努力以配得上‘人’这个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21)〔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第128页。。柯西莫的誓言与行动表明了他既是家庭的一员、父亲的儿子,也是独立的个体,这是柯西莫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卡尔维诺理想的家庭关系。既然柯西莫能够坦然面对与父亲的关系,他在之后遭遇其他威权势力时自然也不会被动等待或者无条件服从。于是我们继而看到了柯西莫领导村民击退海盗的袭击、在封建王朝复辟后带领民众保卫财产、抵抗反动军队的疯狂抢劫……所有这一切正是卡尔维诺所认为的应对威权的最好方式。因此,柯西莫的树上栖居生活不是逃避,而是以一种特殊形式实现他在各种威权下保持自己所认可的“人”这个称号。
在另一篇寓言小说《砍头》中,卡尔维诺更加明确地表现了他对威权的警惕和态度。小说中他幻想出一个特殊国度,那里对威权的遏制是通过定期处死被选举出来的头头们来实现的,因为“不可能想成为头头,却又不想被斧头砍割,只有感受到这种召唤的人才可以成为头领”(22)〔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你说“喂”之前》,刘月樵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页。。这一准则在那个国度成为抵御威权的方式,“只有当权威被已经声明放弃享受权力的各种特权的人施行时,才是可以接受的,而这个人实际已经不再被算做活着的人了”(23)〔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你说“喂”之前》,第140-141页。。事实证明效果极佳,“通过对身体施加相对不太起眼的损害,它获得了道德上的显著效果”(24)〔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你说“喂”之前》,第145页。。小说中的这种设想显然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但这个荒诞的故事却表现出卡尔维诺对威权问题的积极思考。
由上可见,卡夫卡和卡尔维诺在他们的寓言小说中对威权主题有着程度不同但深刻而细致的描绘。很明显,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与他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融,表达了他对外部世界及其统治力量的无力感。尽管在卡夫卡的寓言小说中呈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徘徊在比现实更残酷的威权实体前的失败者,但我们却能够透过他们更加清晰地理解现实生活。就像英国作家约翰·萨瑟兰(John Suntherland)所说:“文学梦境之地中描述的虚构世界往往充满温情,给你以舒适的感觉,能够让人逃离日常生活中冰冷的现实。而《城堡》中所描绘的世界却比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世界更加冰冷。正如法国哲学家萨特一针见血指出来的那样,这个世界才真实。”(25)〔美〕 劳拉·米勒主编《伟大的虚构》,张超斌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143页。卡尔维诺当然也意识到这一残酷的现实,为此他开出两种免遭痛苦的药方:“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26)〔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页。显然,卡尔维诺发现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之道,从而坚定地行进在通往希望的“圣约翰之路”上。通过比照卡夫卡和卡尔维诺对这一相同主题的不同表述,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二者和而不同的独特思想。
三 “未完成的完成”与“完成的未完成”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思想和审美的结晶,反映了个人对时代的思考。伟大的作家通过作品体现其风格,这当然也包括卡夫卡和卡尔维诺在内。然而同为独创性作家,他们的风格自然不可能井然一致,但却各具精彩。
作为一名特殊的“业余作家”,卡夫卡生前只出版了少数作品。弥留之际他嘱托好友马克思·布罗德(Max Brod)把其未出版作品的手稿全部销毁,幸而布罗德没有遵照他的意愿,反而把这些手稿编辑出版,也把卡夫卡推向了世界文学的殿堂。然而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包括一些公认的杰作如《审判》、《城堡》、《美国》都是没有最终完成的,但与此相反,他的作品风格却在创作伊始就被确立并贯穿于其寓言小说始终。黑色幽默般的反讽笔调、刻意推延的不确定性、悖谬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卡夫卡独一无二的写作风格。
从卡夫卡最早的短篇小说《判决》中乖顺的儿子遵从父亲的“判决”,一边高呼表达对父母的爱意,一边义无反顾投河自尽,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反讽笔调。之后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死后反倒让家人解脱、行刑者与自己设计的行刑机器同归于尽、饥饿表演者的表演最终却演变成绝食……这些看似轻松的反讽笔调却书写着恐怖的事件。犹太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说:“卡夫卡有一种罕见的才能,能够自己创造寓言,而且他寓言的意义从来不会被清晰的阐释所穷尽:相反,他会想尽办法防止阐释。”(27)〔美〕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陈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而防止阐释的方法就是在不确定中推延,卡夫卡特别擅长制造一些和主线关系似有似无的情节来延缓事件的进程。《审判》中K与多个女人的关系和他的官司缠绕在一起,却又分散了他对官司的注意力。K对这些女人的欲望既与他通向法的途径有关,也造成迂回和延迟,阻碍了他对法的寻求。由是“K常常沉迷于周围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这种习惯既让这些细节成为通向目标的中介,也让它们成为阻碍,阻挠目标的实现”(28)〔美〕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112页。。同样地,《城堡》中土地测量员K也遇到了障碍,伯爵派驻村庄的克拉姆就是其最大的障碍。克拉姆从不谈及正事,一有人提到公事,他就会跑出房间。吊诡的是K拒绝和克拉姆沟通,反而勾引了克拉姆的情人,于是又旁生出其他的故事枝节,导致小说的后半部分变成一场混乱的对话,故事的初衷反而被逐渐湮灭。卡夫卡似乎在刻意抵制故事的结束,无意给出读者最后的答案,他不打算也不在乎让读者读懂。但这种不完整性恰是它存在的意义,不表明观点本身就是表明观点,这正是卡夫卡独特的风格所在。因为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就毫无意义,所以不欲在其作品中多做解释,“对他而言阐释上的不确定性维持着世界的运行,使其保持平衡”(29)〔美〕 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166页。。但这也给予我们机会任意地赋予这些作品意义而获得与己的通感,由此“卡夫卡文字的卓越之处就在——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在许多方面,卡夫卡的文字超越了自己的时代”(30)〔捷〕 拉德克·马利《寻找卡夫卡》,卢盈江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88页。。
卡夫卡作品另外一个显著的风格特征——“悖谬”在其寓言小说中也非常瞩目,小说人物常常被置于不同的“悖谬”环境之中。这个奇怪的过程可以通过弗洛伊德的“铜壶逻辑”来展现:“A从B那里借了一把铜壶,但当A还回去之后却被B起诉,因为现在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没法再用了。A辩称:‘第一,我从没有向B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壶上就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还给他时,壶是好好的。’”(31)〔美〕 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第109页。这三条理由每一条单独看都有道理,但同时使用就互相排斥。卡夫卡把这种逻辑“悖谬”熟练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审判》中的法院画家蒂托雷利为K分析了三种避免被定罪的方法:第一种是“无罪开释”,但无法核实,因为法院的最终判决从不发布;第二种是“诡称无罪开释”,表面宣布无罪但仍存在重新被逮捕的可能;第三种是“延期审理”,让诉讼永远停留在进程中。这三种方式的前提都是有罪推定,而且清白也无从证明。显然K不可能同时追求这三种策略,但任选一种都会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灾难中。这种典型的悖谬在卡夫卡的寓言小说中俯拾皆是,他甚至把读者也引入其中。小说《美国》和真正的美国相距甚远,如果读者去过真实的 “美国”,受现实影响理解小说可能会有偏差;如果没去过,又如何能理解卡夫卡的“美国”?可见这种无解的悖谬是理解卡夫卡的必要一环,因此也衍生出“卡夫卡式写作”、“卡夫卡式审判”、“卡夫卡式世界”等一系列“卡夫卡式”悖谬,指代各种违背个人意志又无法摆脱的荒诞境遇。由此可知,卡夫卡的作品虽未完成,但风格早已确立,这也是他区别于其他经典作家的鲜明而独特之处。
而作品风格和卡夫卡大相径庭的卡尔维诺,则可以从他对最喜爱的卡夫卡作品《美国》的评述中探知其风格倾向。“我一直认为它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或许不限于此——的杰出小说。至于其共通性,可以这么说:迷失在无垠世界中的某个人的冒险与孤独,寻找启发和内心自我建设。”(32)〔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巴黎隐士》,倪安宇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这里的“冒险”和“自我建设”正好与卡尔维诺的文学思想契合,因为“我(卡尔维诺)希望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新鲜的,我希望每一次我的名字都会被当做一个新人作者……一旦发现某种文学体裁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我一定会拼命在这个方向上尝试,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此路不通,否则我是片刻不得安宁的。又因为我不喜欢半途而废,所以一定会继续走下去,直到努力结出结果——一本新书”(33)〔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第141页。。卡尔维诺每一部完结的作品都是他奋力挑战的成果,而且他总是把对各种新事物的敏锐感知汇入自己的创作风格中,丰富自我、无有止境。
卡尔维诺的文坛处女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Ilsentierodeinididiragno)就是借用了一个男孩的视角呈现一段特殊的历史。这部初具寓言色彩的小说避开了当时流行的新现实主义写实风格,转而用一种新生的眼光探寻世界,卡尔维诺由此蜚声文坛。但他并未继续这一风格,转而创作了魔幻寓言小说《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因为对他来说“唯独利用成功,不花任何力气不断迎合大众期待,才令人不齿”(34)〔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巴黎隐士》,第212页。,所以他不会写别人期望他写的小说,要写他自己喜欢的小说。这套被卡尔维诺喜爱的三部曲也被世人所喜爱,不仅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还奠定了他的寓言大师的地位。但卡尔维诺并不满足于此,他的观察视野反而愈加广阔,从现代工业社会下的人文关怀到对新兴前沿科技的大胆畅想,不仅把人类、动物,而且把非生命、半抽象的物体也作为小说叙述的对象,创作了《马可瓦多》(Marcovaldoovverolestagioniincittà)、《阿根廷蚂蚁》(Linepithemahumile)、《烟云》(Lanuvoladismog)、《宇宙奇趣集》等佳作。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卡尔维诺全家搬到巴黎定居直至80年代初,卡尔维诺受到法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哲学、文学理论和科学中汲取了惊人的灵感,把对组合式游戏的兴趣融入实验主义和古典文学技巧,创作了一批风格异趣的奇作。受有关塔罗牌叙事功能的符号学和结构学论文启发所创作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就是把塔罗牌作为组合叙事机器,借助它把诸多故事片段构建成彼此交叉重叠的“迷宫”,从而达到故事增殖的目的。而看似仿写《马克·波罗游记》(IlMilione)的城市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则是利用晶体模式把11个主题下的55个城市按照一套不同规律组成的固定格式编串在一起。如此构造除了体现多面性、稳定性和晶体的折射能力,还凸显了文本的精确表现和丰富内涵。最具轰动效应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则是一部典型的“元小说”,读者跟随小说中多米诺骨牌式的寻书之旅看到了各具风格、五光十色的小说世界。卡尔维诺在百科全书模式下,把文本作为囊括各种变幻多端形式的集合,各种关系交织一炉以实现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企图。这些令人眼花缭乱、风格各异的寓言小说反映了卡尔维诺的兴趣所在,“教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的实验配方满足不了我,要是翻不出新花样我就觉得不好玩”(35)〔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巴黎隐士》,第213页。。出于对世界复杂性和多重性的感知,卡尔维诺乐于采纳不断出现的新元素构筑奇特的叙事技艺,在丰富作品表现的同时也带来技性乐趣。正如他本人所说:“在每次写作之前,都必须做出选择:……总之,选择一种风格。”(36)〔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论童话》,第13-14页。由此可见,卡尔维诺的行文风格是没有固定的,虽然他的作品(除了遗作)都有始有终,但风格莫测,并未完成。
相较卡尔维诺,卡夫卡过世后才在文坛赢得声名,虽然他的作品大都是未竟之作,但风格早已确立并贯穿始终。而卡尔维诺二十余岁即扬名文坛,每一部作品都超乎想象,风格却在不断变幻,若非猝然离世不知还会带给我们多少风格奇绝的作品。“未完成的完成”和“完成的未完成”恰恰展现了“二卡”的经典性和他们作品的特殊价值。
四 结语
卡夫卡和卡尔维诺都是文坛留名的一代大师,他们的寓言小说作品也是公认的杰作,这些作品都突破了传统的写实和典型化手法,从其构筑的虚幻甚至荒诞世界中展现了现实社会的真实。但卡夫卡的写作是出世的,他主动与时代保持着距离,只是将文学视为情绪的纾解,在这个自我世界中主要关心内在和个人感受。幸而卡夫卡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他的作品总是有直抵人心灵的力量。而卡尔维诺则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个世界越是毫无意义和凶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越是不可能置身历史之外,越是不能拒绝竭尽我们所能,为世界留下一个理智和人性化的痕迹”(37)〔意〕 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学机器》,第56-57页。。虽然入笔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的寓言小说却有着深切的关联,卡尔维诺无论在文学思想还是创作手法方面都深受前辈卡夫卡的影响。然而同为独创性作家,他们的寓言小说又予人不同的感受。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在荒诞世界的迷宫中踌躇无途的失败者,从他笔下冷静的嘲讽中体味到世界本真的残酷。与此相反,卡尔维诺却是千方百计突破自我的局限,从多角度去反映生活的真实,引领我们在科学和艺术精神下窥思这万花筒般的世界并对未来报以积极的希望。卡夫卡的寓言世界小而沉重,反讽、悖谬、不确定性的风格一以贯之;卡尔维诺的寓言世界则广而轻盈,永远在探索莫测风格的征途上。但他们的作品都如同时代的先知,指引着一代代读者去理解和思考所处的社会和世界,具有毋庸置疑的跨越时代的经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