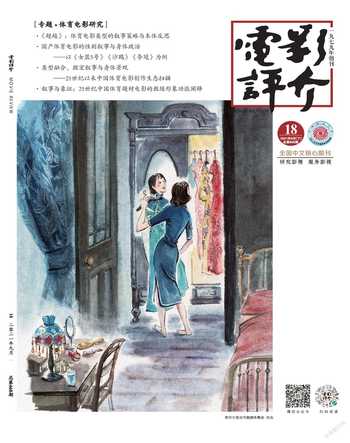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浴血誓言》的生命叙事、人伦本位与影像逻辑
凌燕

近年,中国主旋律战争影片佳作频出,《八佰》《金刚川》《长津湖》等为中国电影产业技术升级树立了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屡次掀起消费热潮的同时,也使高概念模式越来越受到当下战争题材影片创作者的青睐。与此同时,对于一个成熟的产业来说,产业结构的完善还需要大量中小成本影片,后者对于丰富电影的创意性表达、提升电影工业的活力起着重要作用。影片《浴血誓言》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结合类型化叙事,对西路军不畏牺牲、浴血奋战的精神进行了本土化阐释和表达,拓展了中小成本战争影片的表意空间。
一、东方价值理念下的生命与牺牲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奉命成立西路军,渡黄河、抗顽敌,肩负起创建甘北革命根据地和打通苏联红军支援西北通道的重任,因兵力悬殊、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影片以此为背景,讲述红军西渡黄河时,在河西地区与以马步芳为首的匪徒顽强血战。老虎团营长牛大勇和几名红军战士为掩护革命新生儿不畏牺牲,坚守使命,在藏族百姓、地方医生、安帐活佛等各方协助下,最终走出祁连雪山的故事。
无论是中国战争影片,还是在世界范围来看,对战争下的人性进行哲学思考,对个体生命表达尊重,继而表现反战思想及人类共通的情感与价值,是当代战争片的重要发展趋势,《浴血誓言》核心冲突在于,在敌强我弱,不断被追击、围堵的状态下,保护一个新生儿,将大大增加突围的难度,可能使更多战士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为什么要保护这个新生儿、该不该为保护他牺牲其他战士的生命,就成为影片首先要解决的人物行动的基本逻辑。
毋庸讳言,在中国战争影片对其叙事进行现代化更新的過程中,西方战争影片是重要的参照(更新的目的,一来是为了赢得当代观众的认可,同时也是为了未来能被世界市场所接纳),一些影片在学习借鉴后者的叙事手法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战争观、人性观、生命观全盘复制,但这并非我们真正需要的中国故事。
在西方的生命哲学中,生命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人生就是实现个人幸福的过程,且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则更看重生命的社会价值,主张为了他人、为了社会、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我,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影片开始初遇女兵营长方兰时,牛大勇并不知道她怀孕即将生产,只是交待战士们带着那个女同志走,方兰担心自己拖后腿执意拒绝同行,他只好把大衣和马留下,此时是出于对方兰意见的尊重和对战士们安全的考虑。得知方兰即将生产,钱贵说“大勇,咱不能走,人家女同志要生娃”,牛大勇让其他战士先走,自己和钱贵留下照顾,努力做到两全,不给其他战士带来更多的危险。至此,对方兰的照顾,主要是出于人道和同为红军战士的战友情。当方兰生下一个男婴,所有战士都很激动,因为“咱们部队有后了”,在战事处于极端不利、与主力部队失散,几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时,这个新生命给了大家巨大的鼓舞。接下来,直至突围成功,牛大勇从未向战士们下达一定要保护好新生命的命令,但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完成这份没有说出的诺言和这项没有下达的使命。即使在孩子因饥饿啼哭引来敌人,也没有一个人提出放弃。尊重生命,在这里,不再是空洞的理念,而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大家的共识。面对着这样一个代表着希望的生命,每个人都有了保护他的责任,这种超功利的价值理念,是不问得失和成败的。
当然,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如果只沿袭传统文化理念而不进行发展,很难与当代观众对话。传统生命哲学中,生命是属于集体的,只有在对集体的奉献中才能体现个体生命的价值,这常常导致对生命的不珍惜,这在当代社会中是不能接受的。影片中,顺子、钱贵、小川子先后牺牲,每一个生命消逝,影片都用了专门的段落去表现牛大勇对他们的追悼。当受伤的红军战士将刀举向自己时,高医生一把夺下并告诉他:“要活着”。舍生取义固然重要,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使命更要保全自己、尊重生命更为重要,这是对生命至上、以民为本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诠释。
在一些战争题材影片中,为了进行作者化表达,战争被推至后景,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战争的意义。事实上,战争一方面是反人性的,另一方面,一些战争又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社会更替的台阶,本片没有全景呈现西路军历史和重大战役,但在其生命意义表达中,却使西路军及其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在逆境中对信仰的坚守深深留在观众心中。
新生婴儿虎子,表层所指推动情节发展,深层所指引出作者表达。在电影的一幅主题海报中,并没有剧中人出现,而是以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为背景,在这面红旗下,有一双饱经战争洗礼,却依然结实有力的双手,这双大手托起了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婴儿,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在这束生命之光下,睡得很安逸。这个孩子是红军的后代,也是革命的火种,更是祖国的希望。创作者希望观众通过电影不仅能够了解西路军历史,更能感受信仰的坚守与担当,生命的延续与传承。片中未提信仰二字,却内在地体现信仰的力量,并且将信仰与人性表现结合。奥拉母亲明知收留红军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仍然劝责儿子,因为她认为见死不救和杀生一样,也是因为看到婴儿是她的个人的情感渴求。匪首马团长对着被俘的英子说:“好好的娃娃,跟上红匪去受罪”,这既是对敌人去脸谱化的表现,更是从敌人的视角表现红军战士们信仰的力量。影片将传统文化理念、人道主义和弘扬红军坚持信仰不畏牺牲的精神有机缝合在一起。战争中渺小的个体,在看似不可抗拒的外部压力面前,仍以顽强的生命力拼死一搏,有利于使人们获得超出日常的精神力量,并且向当代观众发出感召:在正确和坚定的价值信念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二、人伦本位的英雄形象塑造
在战争题材电影中,英雄形象塑造既是决定影片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更是发挥其社会价值的重要载体。早期英雄是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如《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等既具有超凡的能力、坚定的信仰、强大的感召力,富有传奇性,也往往遮蔽其作为个体的自由情感,这种符码化的人物借助共同的时代和历史体验可以产生激励作用,但对于不同时代、完全不具有相似体验的观众而言,很难产生情感勾连,如何创造既符合历史本质,又能回应当代观众的审美期待、被当代观众接受的英雄形象,使英雄人物与现代观众产生情感勾连,从而使主流价值观得到有效传播,一直是当下战争题材电影创作者们所面临和正在努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和高大全式的英雄都已经不再适应用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故事讲述,将英雄还原为人,既顺应了世俗化的审美需求,也符合当下的人文精神追求。有的影片通过强化英雄鲜明的个性甚至性格弱点来增强英雄的人性化,有的则直接将普通人建构或指认为英雄,《浴血誓言》选择后者。影片中,除了牛大勇,都是普通战士,而牛大勇也不过是个营长,在几场遭遇和突围战中,并没有突出牛大勇的个人力量。主人公的感染力并非来自于他基于身体的过人能力,而是自于他的意志、品质,或者说人格魅力与精神感染力。他有个性,因性格直爽急躁被多福吐槽“还营长呢?算什么营长!”同時,他也能根据形势作出变通,在需要时命令川子“违规”烧火烤土豆;作为部队基层领导,他事事冲在前,在钱贵牺牲的那场战斗中,他与钱贵争抢突围,最终以营长身份命令钱贵服从,但钱贵擅自突围,既表现钱贵作为普通士兵英勇无畏的精神,也体现牛大勇身体力行以个人魅力影响着身边战士(钱贵说,以前每次都是我听你的,你冲在前)。同时,他也有着作为领导的冷静、谋虑和理性:面对熊熊大火燃起,奥拉母亲即将被烧死,他阻止激动不已要闯进去拼命的奥拉和英子,以便从全局考虑,不作无谓的牺牲。
影片并没有将牛大勇塑造为以一当十,一个人拯救所有人的个人主义英雄,其角色内核是中国传统的仁义和情谊。中国文化主张伦理本位,儒家思想认为每一个人应该按照伦理关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担当好自己在社会和家庭应承担的责任。牛大勇是营长,对部下有领导和保护的责任,对战友有生死的情谊,对方兰、英子、婴儿的保护,更像是一个家庭中的长者对幼弱者的保护。当得知钱贵在突围中牺牲,方兰心痛愧疚,说“都是我害的”,牛大勇说:“不怪你,也不怪孩子,这本来就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此时,他面对的是母亲和孩子,而非战士。在奥拉母亲被马匪烧死后,他对奥拉说“我牛大勇欠你们一条命,想要的话,把我的命拿去”,正是这种重义守信感染了奥拉,使其加入到与马匪的战斗中。
中国文化将“义”而非成败作为衡量英雄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义”的实现需要以巨大的付出为代价时,能够舍生取义者方显出英雄本色,出场时间并不多的士兵钱贵大叔,无疑也是一个英雄。如梁漱溟所说,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
在这支队伍里,充满着亲人般的情谊和信赖,牛营长管钱贵叫哥,川子管钱贵叫大叔,英子称呼方兰为姐。在牛大勇命令小川子等人先走时,小川子说“营长,你在四川收我入伍时,说好以后我就跟着你,我知道跟你没错,你对我那么好。”这种质朴的表达喻指的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人民的选择。当钱贵与牛大勇争着冲向险境时,钱贵说“你还认不认我这大哥?”牛大勇说“你还认不认我这营长?”作为战士,钱贵不得不听命,但很快,他便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大哥”的样子。
方兰并非牛大勇的手下,牛大勇率领众人保护方兰及其新生儿与其说是在遵守军队纪律或完成军队任务,不如说是来自文化深层的信念和坚守,对生命的尊重和不惜一切代价的保护更是出于义和情。所谓“浴血誓言”甚至并没有一个仪式化的场面,无论是牛大勇还是战士们,都没有把“我们一定要把方营长和孩子保护好”挂在嘴边,就像革命战争时期许多战士并没有过言语宣誓,却用生命践行了自己心中的诺言。这样的书写呼应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写英雄的文化浪潮,同时又拒绝了其后的创作中英雄的江湖气、霸气取向。英雄牛大勇有鲜明的男性气质、有些许个性,有谋略、担当,甚至宽容、隐忍,接近当代理性男人的典范。影片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承续了勇于牺牲和奉献,利他主义的英雄定义,另一方面,坚守伦理本位的英雄使得和平年代和市场经济浪潮中英雄和信仰不再是空洞而浮泛的能指,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现革命英雄形象的现代转型。
三、电影化逻辑的遵循与缺失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社会效益就意味着经济效益,那么到了今天,主旋律作品也必须直面市场挑战,想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首先要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才具备宣发能力,从而引起文化消费热潮。想要获得经济效益,首先要考虑如何增强主旋律战争影片的观赏性,按照市场规律和电影的艺术生产逻辑去进行创作,塑造人物、情节设计符合电影创作逻辑,并且提供当代的价值理念,才能够达成与当代观众的对话,引起观众的认同,进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传达。
总体来看,近年来的国产战争片创作越来越注重在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方面遵循电影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有些战争片追求全景式记录还原特定历史事件,注重视觉奇观营造,线索庞杂,主线不清;或是注重哲学反思、过于追求艺术化,叙事的复杂化,这些都造成了观众的接受障碍。正如学者贾磊磊所指出,我们许多战争片“主要是根据战争、战役的进程来设计情节,不是根据人物的性格逻辑设计情节”[1],遵循电影化逻辑而不仅仅是历史逻辑、政治逻辑,是当前战争影片创作者应当强化的创作理念。
《浴血誓言》故事是虚构的,并没有真实原型,表明创作者的目的不是机械复原历史,而是选择在忠实历史本质的基础上进行讲述和重构,虚构故事可获得充分的想象空间,创作者放弃了更为保险的表现真实的历史事件的途径,也是以鲜明的姿态表明对电影化逻辑的追求。影片情节采取护送(营救)任务模式,克服一个障碍,新的障碍又产生,不断出现敌人和新的困境,不断突围和解决,孩子生下来旋即遭到马匪围攻,解围后妈妈没奶孩子没有食物,遇到藏民伸出援手,但继而又迎来更大困境(奥拉母亲被烧死,方兰及孩子被俘),主人公克服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
影片按照线性叙事,使得故事较为聚焦,每一段落又采取双线平行交织,使得主线(护送母子)清晰,副线(红军与马匪的对抗)作为外在的压力一直强化着牛营长一行人的行动压力,既保证了情节的紧凑、集中,双方冲突激烈,也使观众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感受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情感变化、价值抉择,在获得视觉体验的同时,情感、心灵、价值理念等也得到冲击和洗礼。
从观影的接受规律来说,认同心理机制起着重要作用。观众必须通过建立对人物的理解、同情,才能对他的命运产生关切。如前所述,护送革命新生儿,并非上级下达的任务,影片通过合理而流畅的剧情设置,在牛大勇们逐渐认识自己使命的过程中,观众也随之理解了战士们不畏牺牲保护这个孩子的选择。
影片故事发生的空间在甘南地区,西北特有的自然风貌、骑马作战使影片某种程度上具有中国西部片的风格,给观众带来陌生化体验。影片甚至还融合了一些公路片的元素,随着突围和行军地点的转换,地理空间也不断变化,丹霞地貌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颇具奇观化效果,在不同地点,新的人物出现,推进了叙事进程。藏地文化、宗教不仅参与了叙事,也使影片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视听语言方面,影片以非饱和色为主要色调,给人阴冷凝重感,烘托战争局势的严酷和故事的悲壮,镜头运动有力地推进叙事和渲染气氛、大量近景和特写镜头突出了细节,剪辑流畅、音乐也有一定冲击力,电影总体上呈现了较好的战争片质感。
在总体遵循类型电影逻辑的基础上,影片还采用了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影片对西路军将士所身处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战争形势无疑是遵循现实主义的,但对西路军坚韧不屈、大无畏的精神和坚定的信仰的表现则是浪漫主义、写意的。
影片开头和结尾用了相同的画面:悲壮的音乐声中,在一面铺展开的写着夜老虎团的旗帜中间,摆放着一只军号、一卷白布、一张家庭照片、一串铜元。铜元是顺子一路上捡的,牺牲前他把它交给牛营长,希望能给兵工厂多造几颗子弹;军号是小战士川子牺牲前最渴望吹响的;白布是钱贵牺牲前嘱咐牛大勇给自己蒙上双眼用的,因为他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世道。这个写意画面以简洁而富有象征寓意的画面,喻指这些不畏牺牲的普通平凡的战士是夜老虎团乃至红军和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历史正是由这些鲜活的无名的个体组成的。一方面避免了过度直白的思想表达,另一方面也便于叙事的充分展开。大量战斗场面采用逆光摄影,象征革命处于逆境中,通过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来积极拓展“主旋律”的艺术表现力,使观众从中体验革命的崇高感、唤起对革命历史及其当代成果的认同。写意手法的运用也使得影片总体基调悲壮而不压抑。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影片在表現战争残酷的同时,需要给人以力量,毕竟,在表现战争残酷的基础上,没有超越的精神做引领,就难以给观众希望和力量。
历史本身就是有感染力的,西路军精神更是给当代人带来了震撼,这使得创作者们在创作过程中饱含激情,并体现在文本中,但这种主观情感有时会影响对历史的还原。西路军处于明显弱势,人员少、缺弹药、多日饥寒交迫,并且进入的是马匪势力范围,后者更为熟悉地势,擅长马战,但影片中战士们屡次被围攻均能顺利脱险,枪法、战斗力等明显压倒敌人,革命浪漫主义只有在与现实主义充分结合才能发挥其艺术感染力,过于乐观地处理削弱了西路军战斗的残酷性,淡化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艰巨性。
另一方面,过于理想化的呈现,不但影响观众对历史真实的认识,也会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前提下,战士们虽然有精神力量的支撑,但难免会有人畏惧,历经战火的过程应当同时也是人物成长的过程。但影片中主要人物始终情绪饱满、缺乏起伏变化。比如,女主人公方兰在战乱中和大家的保护下生下孩子,但是生产似乎并没有给其身心带来明显影响,新增的“母亲”身份也未能丰富这一人物的层次,造成人物成长弧度不够。在对英雄的塑造上,首先应将英雄还原为人,但另一方面,英雄不能仅仅是普通人。
作为缺少明星、缺少话题性的中小制作,或许《浴血誓言》自身就像影片中所致敬的无数无名英雄一样,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更多充当着基石。影片在思想价值的呈现上,没有一味地迎合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而是体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念;在创作手法上,在继承经典战争片传统的基础上,也在积极探索和建构与当代战争片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美学风格,其创作得失既是中小成本战争题材影片活力的体现,也提示我们,如何面向新的社会语境讲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塑造既能感召当代本土观众,甚至感染国外观众的英雄形象,是创作者们所要思考的持久命题。
【作者简介】 凌 燕,女,广西来宾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影视文化、传媒研究。
参考文献:
[1]贾磊磊.战争电影:国家形象的颠覆与建构[ J ].电影创作,2002(03):50-58.
——献给第一线的交警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