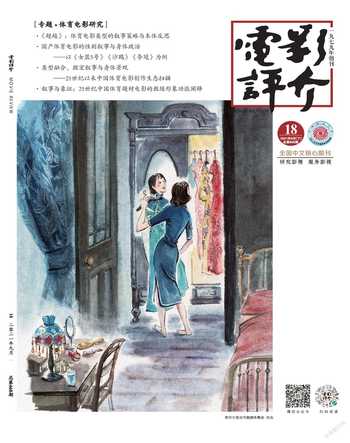国产体育电影的性别叙事与身体政治
李宁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断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1]身体并非传统身心二元论中作为灵魂附属的肉体,身体即主体,它是种种权力或意识形态塑造的结果。而作为以身体为核心意象的电影样式,体育电影的魅力在于展现速度、力量等种种身体景观,以艰难重重的身心成长故事来激荡人心,并通过身体的观看与塑造等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由于身体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勾连,身体往往“既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对象,也是民族国家自身的隐喻。”[2]正因如此,体育/体育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常常和国家形象、民族认同等联系在一起。而由于我国近现代以来国难深重的历史遭际,以及长期奉行的特殊体育体制,这种联系就显得更加紧密。
在我国电影史脉络中,体育电影始终不算一种主流样式,也缺乏较为深厚的类型经验。近年来,随着《激战》(2013)、《破风》(2015)、《超越》(2020)等电影的出现,体育电影创作正以种种美学新变引起人们的关注。有趣的是,据统计,与国外体育电影大多以男性为主要角色不同,国产体育电影则以女性和青少年为主要角色,存在一种“女性优先”[3]现象。因此,本文选取了中国电影史中富有代表性的三部女性体育电影:《女篮5号》(1957)、《沙鸥》(1981)与《夺冠》(2020)。这三部影片出自三个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时期:《女篮5号》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步稳固之际,《沙鸥》问世于改革开放初期,《夺冠》诞生在改革开放逾40载的新时代。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上述三部影片中女性形象与性别叙事的流变,尝试探寻不同时期国产体育电影的身体政治表达,进一步总结国产体育电影的文化内涵与美学风格的嬗变。
一、无父女性:从摩登到革命
《女篮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彩色故事片,也是谢晋独立执导的第二部长片。如谢晋本人所言,影片的主旨在于“通过一个女子篮球队的指导田振华一生的经历和他在爱情上悲欢离合的遭遇,反映出体育事业在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体育事业的各种不同的看法。”[4]在既有的电影史书写中,这部影片普遍被视为“十七年”电影美学的代表作之一。的确,《女篮5号》采取了与同时代许多电影相同的美学策略或模式——“批旧颂新”[5],即将万马齐喑的旧社会与生气蓬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比,由此展现后者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法性。不过,与《白毛女》(1950)、《柳堡的故事》(1958)等那些以工农兵为主要人物的同时代影片相比,《女篮5号》在人物形象、视觉图谱等方面都表现出某种异质性。
这种异质性在于,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有较为显著的女性气质与性别意识。或许是由于发生在上海这一摩登都市的原因,片中的女性角色被塑造得更加时尚靓丽。林小洁等女篮队员留着各种时髦发型,身着各式鲜艳衣裙,尽显青春活力;林小洁的母亲林洁则体现出旧上海都市女性的优雅知性气质。有研究者甚至称影片为一部既保留海派时装片风格又兼具中华人民共和国风貌的“新时装电影”[6]。片中有这样有趣的一幕:刚刚到达训练基地的田振华正在与搭档老孟交谈,很快引来女篮队员们好奇地围观,此时伴随着老孟的提醒——“这些女孩子不好带啊,没有一个不调皮捣蛋的。”在这个男性被凝视的场景中,从未执导过女篮队员的田振华面对一众少女流露出与年龄不符的羞涩感与无措感。而面对陌生的教练,女队员们则毫无顾忌地交头接耳、上下打量,甚至流露出一种观看的愉悦感。从队员们就训练强度问题与教练产生摩擦、林小洁坚持报考大学而非体育学院等其他细节也可以看出,影片塑造的是一群有个性的、有主见的摩登女性。
《女篮5号》的这种异质性在当时并非未被察觉。据说,由于有人质疑该片对党的领导反映不够且有“锦标主义”①趋向,使得影片差点胎死腹中,幸亏周恩来总理以及彼时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等人的肯定才得以顺利问世。[7]而对于影片艺术手法上的质疑,最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在《从<女篮5號>想起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夏衍指出了该片“一个可能不很被人注意、可是性质上却是相当重要的缺点”[8],即片中的林洁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其居住环境的布景设计得过于华丽精致了,不符合其人物设定,有过于脱离现实、美化生活之嫌。在他看来,“由于这堂布景的设计不当,而使这部影片的主题、故事结构、甚至人物性格,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害。”[9]
夏衍对于影片布景的质疑并非吹毛求疵,而是相当有识见地看出了《女篮5号》与彼时“勤俭建国”②背景下所倡导的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美学之间的不同。或者说,“‘女篮5号’的房间让夏衍看到上海电影的美学危险”。[10]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代表着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其后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是延安文艺传统。而从谢晋的封建大家族的出身以及他的艺术成长背景来看,他典型地代表了上海电影传统。当谢晋带着自身的创作传统去适应新的社会文化语境时,难免会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固有的美学趣味。《女篮5号》中的上海都市空间、反复出镜的象征爱情的兰花、充满生活趣味的木偶不倒翁、较为女性化的女性角色以及夏衍所指出的华丽布景,都可谓上海市民电影传统的一种体现。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部电影“相当巧妙地把某些上海电影传统‘嫁接’到了延安电影传统上,使得影片主旨的传达和表达具有丰富的含义乃至‘寓言性’。”[11]谢晋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影片拍摄的时间恰好位于1956年“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③的提出。而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美学策略,《女篮5号》与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文艺实践之间构成了一种既共谋又略带抵牾的张力关系。
看到了《女篮5号》的这种美学异质性,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这部影片在性别叙事上的特异之处:它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充满女性气质与女性意识的差异化个体是如何在政治下被引导与改造为一种超性别的“人民”,并最终融入到集体洪流中的。
影片塑造了两位无父的女性形象——林小洁与林洁母女俩,她们也是新旧两个时代的代表。从相差无几的姓名到身披5号球衣等,都可以看出二人构成了一种互看的镜像结构,“一种重合与互置的关系”[12]。林洁生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嫁入资本家之门。父亲作为球队老板,为了赚取而拼命压榨和剥削球员,甚至命令他们在跟外国球队比赛时打假球,置体育精神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丈夫作为纨绔子弟,则整日寻花问柳、不问家事。由于不堪丈夫的身心虐待,林洁选择携女儿逃离魔爪,含辛茹苦地将女儿抚养成人。她如同一位出走的娜拉,断绝了与旧社会的关联,但又始终孑然一身、精神无依。从小生长在单身家庭的女儿林小洁虽然成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她看重个人的前途和利益,对体育事业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理想主义与献身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也较为淡薄。例如,在面对田振华为什么不报考体育学院的疑问时,她回答道:“打球我是喜欢的,但让我进体育学院,一辈子搞体育,我不干,我又不是考不上大学。”这种论调,显然不足以称得上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革命者。
林洁与林小洁在现实生活中父亲角色的缺席,是二人精神层面亟需引导的一种隐喻,而男主人公田振华恰恰充当了象征意义上的父亲/导师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源远流长的代父传统,所谓“代父”便是代替父亲行使养育职责。“大家庭是中国社会一大特征,而另一特征不妨暂称之为代父(surrogate fathers)。代父包括生父不在时,取其位而代之的养父、伯叔、邻里等等。”[13]《女篮5号》的叙事策略便体现出了这种“代父”传统。整部影片表面上讲述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家庭伦理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两个无父女性是如何被田振华这一男性所代表的革命者引导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政治轨道中的。
田振华出场时的着装和道具十分耐人寻味:他怀抱一盆郁郁葱葱的兰花,在集体开会时身穿印有“西南军区”字样的上衣。“军区”加“兰花”的搭配,恰恰是“革命”与“爱情”的叠合。而一开始面对女队员们还颇有些拘谨局促的他,很快便娴熟地扮演起了精神导师的角色。为了让林小洁提升集体主义意识,他宁愿比赛失利也要将其打入冷宫,尽管林小洁的迟到是无心之举;而当林小洁长期积累的委屈和不满最终爆发,并叫嚣着“我不干了,我走好了”时,田振华则结合自己在旧社会为资本家打球的悲惨经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挽回了前者,并最终说服她改报体育学院。田振华的种种规训与引导带给林洁母女的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当受伤的林小洁面临到底要不要做手术的艰难抉择时,林洁信任地对田振华说:“你来决定吧。”而创作者则给林小洁安排了一个再直白不过的“认父”场景:病床上的她拿出报考体育学院的志愿书,并向田振华坦白自己的心声:“我从小就没有父亲,这些日子来很自然的有一种感觉,我想要是有你这样一位父亲,那该多好!”
影片末尾,田振华带领女篮队员一路北上,到北京参加欢送出国运动员大会。同时,林洁收到田振华的来信,在对方希望出国前见到她一面的请求下动身前往北京。从上海到北京,这一空间位移的政治隐喻再明显不过。接下来则是影片最具仪式色彩的场景:在国歌中,田振华与林小洁等一众女篮运动员排列成整饬有序的队伍,面目坚毅地接受检阅,而准时赶到会场的林洁则无比欣慰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一场景既是一个革命动员仪式,也是一个家庭重聚仪式。在田振华的引导下,林洁/林小洁终于从摩登女性蜕变为一种超性别的或去性别化的社会主义新女性,也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家庭关系。
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当林洁/林小洁们被询唤为弱化女性气质的“人民”并鼓励她们广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时,她们仍然被要求担当起家庭妇女的传统角色。片子有这样看似不经意的一幕:女队员们发现田振华自己洗衣服,感到十分讶异。田振华问她们:“你们不自己洗啊?”队员们答道:“你是男人呀!”对于这样的回答,田振华的第一反应是解释自己是单身太久所以习惯了自己洗,同时默认了男性不应洗衣服的传统规范。这似乎是当代中国女性的一种独特又无奈的历史境遇:既要扮演起能顶半边天的社会角色,也要不放弃根深蒂固的家庭角色。
二、创伤女性:现代化焦虑与非典型新人
与《女篮5号》中的林小洁相比,电影《沙鸥》中“沙鸥”这一女性形象的设置颇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是父亲缺失,同样遭遇身体创伤。十分有趣的是,在相对应的男性人物形象上,《沙鸥》并没有塑造一个类似田振华一样的“代父”角色,而是设置了“沈大威”这一不幸罹难的恋人角色。这种性别叙事上的差异是颇有意味的:如果说《女篮5号》强调的是无父女性如何在精神之父的帮助下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女性的话,那么《沙鸥》强调的则是创伤女性如何在没有男性引导的情况下走出人生困境并成長为社会主义新人。
作为女排运动员的她急切地想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从她的“我要的是金牌,不是银牌”“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人没有目标,就没有生活”等言论可以看出,她有着明晰的个人奋斗目标。但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她遭遇了多重打击:先是身体的伤病与比赛的失败让她心生退意并决定成为家庭妇女,紧接着爱人的突然离世让她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正如戴锦华所言,这部影片“将第四代的共同主题:关于历史的剥夺、关于丧失、关于‘一切都离我而去’,译写为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人。而在这部影片中,女主人公沙鸥甚至没有得到机会来实现对主流文化中关于女性的二项对立、或曰二难处境——事业/家庭、‘女强人’/贤内助的选择或背负这一女性的困境。历史和灾难永远地夺去了一切。”[14]
影片中的高潮段落也是最富有象征意味的段落,是沙鸥在爱人离世后漫无目的地漫步在圆明园。同时,影片以旁白的方式反复强调着一句台词:“能烧的都烧了,只剩下大石头了”。如同有论者所言,“作为一个基本政治符号,圆明园的意义又超出了任何特殊历史时段的限制,而是在中国现代史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上被不断唤起。”[15]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伤痕文学”“伤痕美术”等为代表的艺术创作中,圆明园这一充满历史意味的废墟空间频频出现在各种作品中。这一空间承载的沉重而深刻的历史记忆,契合了经历浩劫之后人们的情感状态与生存体验。而当沙鸥置身在一片狼藉、断壁残垣的废墟中时,其象征意义不可谓不明显:一个狂热的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崩塌。那么,废墟之上,如何重生?
新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着一种现代化焦虑的情绪。人们在各个领域急切地寻找着现代化的标准,想要在废墟之上重建新的现代化中国。例如,《沙鸥》导演张暖忻与编剧李陀在1979年合写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便是艺术领域追求现代化的显著体现,而《沙鸥》本片也可视为这篇宣言的一次生动实践。与此同时,《沙鸥》尝试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如何成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新人?
在1978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明确提出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方案:“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16]邓小平在1980年就这一问题作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的明确指示①。与此同时,面对彼时年轻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迷惘、虚无的精神状况,《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5月以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全民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这便是喧嚣一时的“潘晓讨论”②。
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才能够更为清晰地把握“沙鸥”这一人物形象的独特性及其引发的争议。在导演阐述中,张暖忻明确指出要塑造一位经历重重挫折但不放弃人生崇高信念与奋斗精神的人物。面对当时火热的“潘晓讨论”,她表示“要用这部影片来参加这场讨论,对人生的意义问题,作出我们的回答。”[17]不过,沙鸥这一人物在被视为“一代新人的形象”[18]而饱受赞扬的同时也引发了激烈争议。就连编剧李陀本人也明确察觉到,“人们对影片主题的认识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19]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沙鸥这一人物所坚持的理想主义到底是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例如,有人就认为“沙鸥精神”跟当时的“女排精神”是迥异的,前者过于看重个人的荣誉,后者则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以青春的血肉之躯,为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去争取世界性的最高荣誉。”[20]有人认为沙鸥之所以不是一个好的典型人物的原因,在于影片“并未呈现出主人公从为个人拼搏到为祖国争光的飞跃”[21]。有人甚至举出影片中沙鸥丢掉银牌的场景,认为她“无权把象征祖国和民族荣誉的银牌抛进大海之中”。[22]
上述对于沙鸥这一人物的质疑有其合理性,这是因为影片的确更着重表现个人激情与自我奋斗。与《女篮5号》所展现的个体融入集体不同,《沙鸥》体现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某种疏离。例如,尽管沙鸥为了代表国家参赛宁愿冒瘫痪之险,但这一行为更多出于对自我荣誉的渴望。这种若有似无的疏离,来自创作者有意在主题表达上的模糊处理。追根究底,这是创作者在一个巨大的转折时代所采取的一种迂回或含混的美学策略:一方面试图以高扬个人主义的方式与疮痍满目的集体主义时代挥手作别,另一方面又要以书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汇入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洪流中。由此,影片也呈现出一种昂扬与感伤并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混杂的面目,沙鸥也最终被建构为一位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沙鸥》上映后不久,中国女排在日本第一次夺得世界杯桂冠,影片以这种预言的方式与现实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而“沙鸥精神”与“女排精神”之间的貌合神离,根本上可以说是彼时游移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的生动体现,这是转折年代无法逃避的断裂与冲撞。
三、独立女性:在集体记忆与自我实现之间
《女篮5号》和《沙鸥》中处理的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电影《夺冠》中同样被反复讨论。或者可以说,这是中国体育电影中无法绕过的核心议题。与前两部电影不同,《夺冠》的时空跨度更大,它以国家女子排球队一波三折的发展来勾勒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流出某种史诗叙述的雄心。正如编剧张冀本人所言,“用两个人物、三场比赛来展现改革开放的时代、展现一支三代人球队的结构是很早就定下来的。”[23]而这种叙事结构,使得影片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体育观念的变化及其背后文化精神的迁移。
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历史文本的本质乃是一种虚构的诗性语言,其制造意义的机制主要依赖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四种修辞方式。其中,提喻是用综合性的方式来看待对象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体本质上不同于部分之和,各部分只是作为整体之微观复制品。”[24]《夺冠》便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即从女排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是三场重要比赛)这一切口入手去展开对整体改革开放历史的想象。不过,由于故事与人物的原型在现实中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太为人熟知,导致影片的创作空间大为受限。创作者无法过度偏离历史,来讲述一个充满未知的、打破观众期待视野的故事。正如有论者所言,“‘夺冠’的影片标题更像是对一段已发生的历史的再度确认,而不是对预期中有待实现的目标的想象。”[25]甚至有人称其为一部充满了各种符合和形容词的“过气的报告文学”[26]。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导致影片在故事层面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创作者还是通过“郎平”这一独立女性形象的塑造传递出体育观念与女性意识的变化。影片看似塑造了郎平与陈忠和两位主人公,实际上把叙事重心几乎都偏移到了前者。也因此,很多人质疑影片为郎平的个人传记,连陈忠和本人也因影片对自己的不实塑造而表示抗议。有趣的是,与《女篮5号》中林小洁与田振华的“父女”组合、《沙鸥》中沙鸥与沈大威的恋人组合不同,《夺冠》中塑造了郎平与陈忠和这一对亦“敌”亦友的朋友组合。林小洁需要精神之父田振华的引导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女性,沙鸥在恋人去世后陷入彷徨无依的境地,但《夺冠》中的郎平是一位独立自强的、无需男性引导甚至敢于挑战男权秩序的女性形象。影片中有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在上任女排主教练后召开的“女排发展”专家研讨会上,郎平只身面对前主教练、顾问、教授等组成的清一色的男性专家团队以及他们偏于保守的发展立场,响亮地提出女排只有“改革”这一条路可走的决断。在改革遇到挫折之际,面对专家们提出的令国家青年队参加国际女排的提议,她颇有魄力甚至有些专断地现场予以反击。在独立的郎平面前,陈忠和这一人物便显得更加隐忍和谦让。
如果将影片中1981年与2016年的两场比赛放在一起,会有一种强烈的嬗变意味。在第一场对阵日本的比赛中,面对严峻的局势,老教练袁伟民说出了这样一番激励队员的话语:“如果你们在这场比赛输了,你们会后悔一辈子,因为你们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来到这场比赛的。”而几十年后,现场聆听过这番话语的郎平在面对自己的队员们时却说“我希望我的队员不只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优秀的人”,并鼓励她们打出自己的比赛,“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从代表民族比赛到代表自己比赛,这并非一种二元对立式的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迁移,而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后国家崛起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影片中的郎平经历了这一变化,深刻体验过体育运动过分被国族荣誉所裹挟的感受,体验过国家落后的现代化焦虑,才由衷地认识到享受比赛、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郎平/陈忠和这对人物形象被塑造为全球化/本土化两股力量的象征。后者不会说英文,没有留洋经验,始终秉承着本土传统的训练方法。前者则游学并执教美国,汲取了国外的体育理念,并将其运用到自身发展中。更有趣的是,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竞争与博弈的关系,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姿态。尽管影片中的陈忠和不具备前沿的全球视野,但他并没有一味泥古不化,而是坦然地让贤举能,接受并配合郎平的上任。郎平在追求國际先进发展理念的同时,又并非以洋为尊,而是内心秉持着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这种对中国/西方、本土化/全球化关系的探讨,与其说是对过去40余年改革开放历史的简单复写,不如说是立足当下的一种重新叙述和想象。在影片的书写中,不再是男性凝视/引导女性,而是女性引导/挑战男性。而“郎平”这一独立自觉的“大女主”形象,又十分显著地与当下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潮流下女性意识的崛起形成了有趣的呼应。
结语
从无父女性、创伤女性到独立女性,《女篮5号》《沙鸥》与《夺冠》三部影片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叙事经历了有趣而显著的转变。《女篮5号》中,无父女性林小洁需要经过田振华这一精神之父的引导才能汇入革命的集体;《沙鸥》中,创伤女性沙鸥试图摆脱集体主义与男权秩序的废墟,以此寻求个人奋斗与自我发展;《夺冠》中,独立女性郎平经历女排艰难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终于在集体记忆与自我实现之间找到了平衡的可能。从计划体制下集体主义的规训、到历史断裂处个体主义的高扬,再到大国崛起时代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交融,上述三部电影在不期然间以独特的身体政治勾连起了波折重重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这也是国产体育电影更深层的文化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 李 宁,男,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艺术理论、影视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主旋律’的概念史研究”(编号:2020NTSS4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谢有顺.文学身体学[ J ].花城,2001(06):192-205.
[2]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33.
[3]李金宝.体育影像传播——百年中国体育电影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62-63.
[4]谢晋.创作《女篮5号》的一些体会[C]//谢晋编.谢晋电影选集 体育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24.
[5]王一川.革命式改革:改革开放时代的电影文化修辞[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263.
[6]曾焱.青年谢晋和他的电影哲学[ J ].三联生活周刊,2004(40).
[7]《南方人物周刊》编著.前辈[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338.
[8][9]程季华主编.夏衍电影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756,756.
[10]毛尖.性别政治和社会主义美学的危机——从《女篮5号》的房间说起[ 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03):29-37.
[11]饶曙光.不同反响的《女篮5号》[C]//谢晋编.谢晋电影选集 体育卷.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117.
[12]刘宏球.体育:民族、家国与爱情——论谢晋的体育电影[ J ].当代电影,2008(03):113-117.
[13]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08.
[14]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 J ].当代电影,1994(06):37-45.
[15][美]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M].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51.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81-182.
[17]张暖忻.《沙鸥》导演阐述[C]//中国电影出版社编.沙鸥——从剧本到影片.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85.
[18]向梅.一代新人的形象——赞影片《沙鸥》[C]//中国电影出版社编.沙鸥——从剧本到影片.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386.
[19]李陀.电影剧作中的电影美感——《沙鸥》剧本創作体会[C]//中国电影出版社编.沙鸥——从剧本到影片.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170.
[20]成无功.典型应该是特定的——影片《沙鸥》异议[ J ].电影艺术,1982(08):14-18.
[21]黄式宪.不应当忽略电影创新中一些值得警觉的问题[ J ].电影艺术,1982(03):33-35.
[22]杭志忠等.“沙鸥扔银牌”合适吗?[ J ].电影评介,1982(03):19.
[23]张冀,赵卫防,孟琪.中国体育题材电影及编剧创作——从《夺冠》谈起[ J ].当代电影,2020(11):45-55.
[24][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6.
[25]孙柏.《夺冠》:中国女排精神的时代变迁[ J ].电影艺术,2020(02):75-77.
[26]杨时旸.《夺冠》这部聒噪的电影没能让你记住任何一个角色[ J ].南方人物周刊,20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