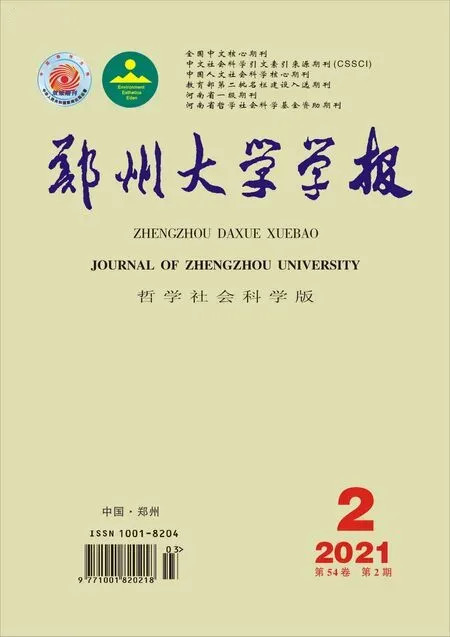演戏助赈:晚清时期慈善演艺活动的萌生
岳 鹏 星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演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一般包含戏剧、歌舞、杂技等表演艺术,其“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祭祀活动,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以及流传至今的传说、仪式都可以看到人类早期的演艺活动痕迹”[1](P14)。慈善演艺是一种慈善与演艺相互结合的社会活动。将“慈善演艺”作为整体词汇,史料所见最早在清末。例如,1906年2月11日,为了赈济台湾当地的灾荒,台湾当地便举办过“慈善演艺会,将其获益之金”,加入募集款之中[2](P4)。目前,学界针对慈善事业、演艺情况、慈善义演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只是对于慈善演艺的专题研究,还尚属少见。本文以早期报纸报道为史料,对晚清时期慈善演艺活动萌生的源头进行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一、冲击与反应:西式慈善演艺范例的刺激
慈善事业多与日常生活的变故相关联,尤以灾荒时期为多见。大灾之年,往往需要政府与社会齐心协力,才能帮助普通民众渡过难关。在中国近代史上,“丁戊奇荒”对于清政府荒政制度的影响至深,促进了近代义赈的诞生,而上海地区特有的氛围逐渐促成了慈善演艺的萌生。
“丁戊奇荒”是发生于1876-1879年的特大灾荒,持续时间长,波及晋、豫、冀、鲁、陕等北方五省,影响深远[3]。正是在此次灾情发生的过程中,江南富庶之地的一些绅商最早发起了义赈活动。义赈是由民间自由劝赈、募集费用并自行发放物资或赈款的“民捐民办赈灾活动”[4](P496)。针对“丁戊奇荒”的赈灾而诞生的“近代义赈”成为该时期慈善事业中民间力量的基本面相[5]。
在义赈陆续开展的同时,上海地区的《申报》对于救灾进行了积极呼吁和鼓吹。其中,1877年2月8日刊载的一篇头版头条文章即《论演戏救灾事》,颇为令人关注。该文章开篇便记述了一段文字,讲述报人自己翻阅香港报刊《近事编录》,发现上面一篇文字如此记述:“日前有英国战船猝遭沉溺,兵丁水手死于是役者,殊堪悲怜,复有家属零丁孤寡,无所倚靠,更觉可怜。有心者即于十九晚相集演剧,于赴观者皆税其赀,即以是夕所税之赀,尽为周济沉渔家属之用。此其立心不减于仁人施济,且使来观者既得娱目,亦足以写其好行。其德之心,不待签捐,无烦代贷,一举两得,诚为甚便。使世之演戏皆如此用心,则谓之有益亦无不可。”[6]根据《近事编录》上面的记载,香港地区有西方人士因为英国水手死去,家属生活困难,便“相集演剧”,并将演出所得用于救济这些水手的家属。对于此种慈善与演艺相结合的方式,《近事编录》表示,此举既为“娱目”,又“写其好行”,表达了善意,可谓一举两得。文章并感慨演戏为善代表着一种有益的活动。
《申报》报人还谈到了自己曾经看到的类似之举动:“因思去冬上海租界寄居之法人,缘法国有一地方饥荒,法人之在沪者欲集赀以赈之,亦用此法。演戏两日所得之赀,尽行寄往,以助赈务。”[6]在该报人的视野里,不仅英国人曾经演剧为善,寄居在上海的法国人士也曾经因为法国本土饥荒,举行演戏活动,戏资赈饥。文章认为此种方法“亦可谓良矣”[6]。
通过以上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行善手法,该报人果断呼吁华人也效仿此法。他说:“出赀者不费大力而集腋成裘,众擎易举,既得多赀,有益正事。使华人亦能效其所为,遇事照此办理,势必易于成就。”[6]在该报人看来,对于慈善演艺之事情,组织者可以很容易达到集腋成裘的效果,十分有益于“正事”即开展慈善救济。为此,该报人恳切呼吁“演戏之优伶”,率先行动起来,认为果能如此,慈善演艺事业则因为“优伶以成”,优伶自身的社会地位也会提升,以至于民众将不会将优伶视为“贱业”。该报人一定程度上也在吸引和刺激演艺界人士能够发挥先锋作用。
该报人甚至还从上海地区演戏的习俗中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人提议,各戏馆演戏筹款之举,自然可以成功。他说:“余初闻之,亦谓事尚可行,何也?因租界各戏馆,一至残冬,所有寄居租界之各处客民,均求各戏馆代演一宵,所得余赀,尽归求演各人分用,名之曰打野鸡,向来如此,今冬尤甚。余因有此习俗,故以为事在可成,盖谓戏馆肯帮数人之用度,岂有不肯帮赈大众之饥饿乎?不料竟无人肯言也。”[6]租界的各戏馆,因为商业性演出的缘由,为了延续日常的生计、招揽顾客,因此根据传统习俗,每年年关之时候,都会有“打野鸡”的习俗。关于“打野鸡”,《清稗类钞》曾有记载:“上海各戏园之至腊月也,四方过客皆纷纷言归,家居者料量度岁,方日不暇给,戏园之生涯自必锐减。至是而案目商于园主,有请客之举。请客者,以戏券售之于向识之看客,恒较常日为昂,俗谚谓之打野鸡。”[7]也就是说,打野鸡相当于熟客的包戏,此对于戏馆的熟客而言是有利益的,对于戏馆而言则意味着增加一场或者几场演出。因此,该报人认为,既然戏馆能够为一部分人演出,为何就不能够为广大的饥民而演出呢?只是当时尚无人向各戏馆言明。
最后,他发表了自己的感言:
盖欲使各戏馆知西人有此办法,或能触目动心,有此一举,亦未可知。虽然,西人之为此者,实非平日演戏之优伶,赖戏以猎食谋生者也。而各戏馆之优伶,固借此以事蓄养赡,苟少一夕之赀,即少一日之用,似不可以一概而言。但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古人已有明言。况仅一宵所得尽行助赈,似于各馆尚无大损,何不以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令受之者感激,闻之者羡慕,或能因此感动而勃然兴起,乐输重赀往助赈务,以为彼演戏者尚能如此,何况我辈席丰履厚者哉!果能如此,则其有功于赈务实属不少,岂得犹谓演戏为无益之行为,非有益之举动乎?吾是以不惜谆谆相劝而不肯止也。又况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从此沪上各戏馆之美名,亦可以与西人演戏行善之美名同见称于一时也,岂不美乎![6]
该报人的言辞之中,包含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作者的目的很明确,即希望各戏馆能够知道西人的办法,仿照办理。第二,表达中西之间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以戏为生之人,还是可以表达自身的善意,况且临时性的演出对于各戏馆而言,并不会影响多少,但是对于助赈之事,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三,劝诫以戏为生计之人,能够“以小人之业而为君子之事”,并呼吁“席丰履厚”之人也积极参与进来,不可人后。第四,畅想演戏行善之事情取得成功,即可将戏“无益”转而为“有益之举动”,进而营造上海戏馆的行善“美名”,与西方慈善演艺行为并驾齐驱。
几乎在《申报》发文呼吁的同一时期,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已经展开了慈善演艺活动用于助赈。1877年2月18日,西人已“在外国戏院串作音乐会,所收银则以供济中国饥民”[8]。此次演出中,上海的地方官“亦到会倾听,西人亦咸集以观,或一男一女独唱或男女十余人互唱,丝竹杂陈不一其式。观者皆闻之忘倦”[9]。此次西人的慈善演艺活动“所收之银约及一千元”,用于赈灾[10]。
《申报》的呼吁以及西人慈善演艺的行动,刺激着上海的戏馆和华人。而西人通过慈善演艺的善举手法提供给华人一种在慈善与演艺之间的全新思考。在这种氛围之中,华人自主兴办慈善演艺事业开始慢慢起步,并饱含了自身的文化特质。
二、戏资助赈:华人慈善演艺活动的原初起步
缘于“丁戊奇荒”的影响,上海地区的演艺领域出现了另一番景象,即上海地区戏资助赈活动的出现,使得具备现代性意涵的慈善与演艺的结合成为现实,华人慈善演艺活动开始逐渐萌生。
正如前述,西方慈善演艺的影响与刺激,以及《申报》的呼吁营造出一种氛围,希望华人能够采纳演戏助赈这一手法。结果不出月余,《申报》上便登载了一则《戏资助赈》的报道,该文的署名人为“鹤鸣园领班”[11]。该文论在《申报》上刊登了一个星期,主要讲述了三层意思:第一,山东和苏北地区发生灾荒(此即“丁戊奇荒”),官绅竭力捐助,在华的外国人也积极参与救灾,可谓善与人同、不分畛域。第二,鹤鸣戏园针对灾荒,愿意拿出“歌舞之余资襄赈”。所有演艺人员,从该月“十五日为始,端阳节止,以半月一给”,除房租和伙食等开销外,将余下的款项用于购买粮食,进行助赈。第三,该戏园演艺人士表示此举乃各尽心力,希望绅商士庶能够积极参与。
鹤鸣戏园领班发表告白,愿意演戏助赈,此举对于《申报》报人而言是惊喜之行为,1877年4月26日,《申报》上专门发表一篇《戏资赈饥》的文章来提醒阅报之人的关注。文中称:“兹见本报后幅鹤鸣戏园所列之告白,知从本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每日所得戏赀除去房租火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赈款,何优孟中亦知自好如是哉!按本埠外国戏园日前亦有此举,则知天良其在,为善最乐之语非虚也。”[11]
从这则文论来看,似乎笔法和情感出于与《论演戏救灾事》一文同样的报人之手。文中除了特别提醒读者关注鹤鸣戏园的告白之外,尤其称赞鹤鸣戏园的演艺人士“优孟中亦知自好如是”,此与外国戏园演戏助赈之举一样,可谓“天良其在,为善最乐”。
此次慈善演艺活动之中,鹤鸣戏园承诺从是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即西历4月28日到6月15日,总计50天。鹤鸣戏园的演出消息鼓舞了该报人的信心和热情。为了进一步论述演戏助赈的重要价值,并进一步以鹤鸣戏园为例进行呼吁,隔了三天之后,该报人专门在4月30日的《申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文章开篇便说:“去岁山东旱灾,其地土著之人,死亡载道,真有见之不忍见,闻之不忍闻者。故各处中外绅商以及富户,或有出赀以倡捐者,或有出力以劝捐者,集成巨款,送山东以助赈项之不逮,深有合乎孟子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之意也。”[12]此即“丁戊奇荒”背景下,中外绅商以及富户开展义赈的情形,并以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高度赞扬了慈善救济的行为。同时,该报人还表示自己一直关注戏曲演艺界中参与慈善救济的情况:“耳后阅香港各报均言,当东华医院开局劝助山东赈项之时,有开高升戏园主人罗某捐银一千两。余深喜中国戏园亦有如此一人,真不愧为勇于为义之人。”[12]与香港的罗某相比,“上海所设之戏馆,闻亦曾经英国教士慕先生亲身往劝,每戏馆仅肯捐洋两元”。该报人在做了一番回顾后,对鹤鸣戏园领班发布的告白感到惊喜:“鹤鸣戏园之领班竟有此举,余又为之喜而不寐。盖喜余言之未尽付诸东风也。”[12]但对于鹤鸣戏园以半月为一期将赈款邮寄的方法,作者也表示担忧:“但余昨闻有人言及山东燕台之教士英人李佳来催上海所得之捐银,务望于西历六月初五日以前赶紧寄到。若过此期,麦已登场,彼亦不愿再往散赈,致滋物议云云。而鹤鸣戏园领班之告白,则以半月一寄为期,若能提前赶寄,则尤为山东灾民之幸也。”[12]言外之意,即希望鹤鸣戏园能够尽快行动起来,筹集善款,提前寄送。
此外,该报人还对于鹤鸣戏园以及领班进行了核查,表示:“闻此领班向在上海经演戏为业,后因犯案拟军旋蒙两次,恩赦援例免罪释放。今岁新正在园演戏,每日书夜可得三百余洋,除用度外,每日可剩二百洋内外。今愿以五十日所剩之洋尽为山东救灾之项,可以至万洋光景。若据李佳来信所言,现在山东情形每人有洋三元,即能延活以至麦秋,今得此款可以救活三千余人,其功亦不浅矣。”如此之贡献,使得该报人内心中升起了景仰之心,认为“领班以获罪幸免之身,想而为此义举,在国法则可谓为赎罪,在儒教则可谓为改过,在佛门则可谓为忏悔,在道家则可谓为禳解然,犹谓为有所为而为之也”。文章在称赞该领班之余,还赞扬全体演艺人士“所难得者阖班之人均愿捐出辛工,襄成此义举耳”[12]。鹤鸣戏园领班以及全体伶人自身进行演艺助善的行为,在报人看来百益而无一害。
《书本报戏资助赈告白后》一文洋洋洒洒,以较大的篇幅和笔墨在跟踪报道了鹤鸣戏园举办演戏助赈的同时,也积极呼吁其他戏园以及演艺人士也积极投入到这种行为中去。言辞切切,使人身临其境,不禁感慨报人的良苦用心,也不禁感慨《申报》馆的努力。从另外一方面论之,新兴的传播媒体《申报》积极开展舆论宣传,并试图引领话语,鼓吹慈善演艺事业的优长之处,展示了近代传播媒介的力量。
极有可能是因为鹤鸣戏园的示范性影响以及《申报》馆呼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7年5月11日,久乐园顺天乐班发布告白,表示愿意加入慈善演艺事业。在启文中,开篇便简述了灾荒的影响以及时人针对灾荒的赈济情况。“窃闻灾以奇称,贵捐金而纾难财,为义用当,破格以济公。慨自上天降灾,下民遭劫,东省之登、莱、青,江苏之淮、徐、海诸郡县均缘水旱频仍凶荒,迭告饥寒交迫,饿莩盈途,易子析骸,伤心惨目。幸蒙各省大宪先后奏赈,官绅、商客踊跃书捐,即西国官商之来华者亦复集赀凑寄,可谓无分畛域,善与人同。”在如此背景之下,久乐园顺天乐班表示:“本园不揣薄绵,拟分所得戏金寄襄赈务。”考虑到顺天乐班“甫经到沪,深恐力不从心,因定四月初二日起试办一月”,并“酌减位票价目,彚送绅商士庶”,“即以所得票金支发园租工食外,其余全数禀缴广肇公所,代交招商局总宪,酌量分寄山东江北各属助赈”。该班还表示:“现已将一切费用格外节省,以期多存余资。一月后,办有成效,再行照章续办。”对于此举可能起到的效果,该班认为:“明知杯水车薪无补于事,但泰山不拘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伏求俯鉴愚诚玉成善举,万间广厦原非寸木可成,九仞为山要由一篑所始。”[13]
为了进一步向未来的宾客解说具体的“酌减位票价目”的情况,顺天乐班还专门在启文后面发布了具体的办法。针对减少票价,“本园桌票原价六毫,椅票原价四毫,板票原价二毫,今减桌票为四毫,椅票为二毫”。至于“汇送绅商士庶”办法:“凡宝行、宝号、公馆每桌送票十二条,领银五元。椅票十二条,领银二元五毫。送票后七日照收,以期集腋成裘。”对于“本园所送桌椅票不填日子,分用、合用悉听尊便,或持桌票坐椅位请以一票作两票用,或持椅票坐桌位请以两票作一票用”,对于“坐位茶食格外周备”,为了满足营业性收入的需要,或者可能是考虑到休整的因素,表示“惟礼拜一、五日日夜停演”。针对戏资的问题,该戏班明确表示:“本园除园租不能减外,所有在事人等,工食均减发六成,以资节省,冀多存余赀,以襄赈款也。”该戏班为了顾客着想,而且考虑到夜戏可能带来的不安全性,表示:“本园在火马路西首。贵客夜深来往恐嫌僻静,现已添雇巡捕四人、巡丁十余人分守栅门路口,以免人多生事,并护送贵客深夜来往也。”[13]
顺天乐班发布的启文中,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戏班已经灵活地开始寻找营业性的营销渠道,如采用“酌减位票价目,汇送绅商士庶”的办法。二是戏班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通过提供安全性服务来减少顾客雏形顾虑,并在戏园中提供相应茶食服务招徕生意。三是顺天乐班并不是完全的在不讲究自身生计的前提下进行慈善演艺,而是不能让久乐园即戏园受到日常影响,所以园租不减,同时,所有参与的演艺人士即伶人工食减少六成,勉强维持生存之下,用于集资筹赈。四是为了戏班自身的生计,演出时间中周一和周五两天是不参与慈善演出的,可能用于日常的营业性演出。
比较久乐园与鹤鸣戏园,容易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也还是有所不同。相似的地方在于二者均是戏班自身进行慈善演艺,演出所得用于筹赈。二者的不同在于久乐园已经开始关注到营业性与慈善演艺的不同,思考演出方式的不同该如何取舍的问题。
就在鹤鸣戏园与久乐园顺天乐班进行慈善演艺的时候,5月21日,《申报》发布了一篇评论性文字,专门讨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宜,并将鹤鸣戏园和久乐园作为例子,进行论述。《申报》发布的头版头条评论性文章《论戏园节钱助赈事因述所见》中,与此前呼吁戏园参与慈善演艺不同,此次视角已经转移而为呼吁“入酒馆、妓馆、戏馆诸公”能够转变消费观念,节钱助赈。文章指出:“凡善举之事,随时随地可以量力倡助集而成之,不必尽富商大贾动辄解赠巨万而后可以济事也。”实际上提出慈善是日常民众点滴的财富累积与分配,并且是量力而行的集腋成裘之行为,完全靠“富商大贾”并不是最好的方式。接着,文章就日常民众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讨,认为“通都大邑之中,五方杂处人间,应酬之费必十倍于乡僻小地。若上海一海边埠头耳,人之到此者,勿论妓馆、酒馆、戏馆必入之。或每日招邀,迭为东道主;或间日一往,以叙友朋,恣游宴;即极知省俭之人,亦必旬日一至、一月一至”。也就是说单就在上海这个地方,缘于民众日常生活的习性,兼具娱乐性质与日常交际需求的妓馆、酒馆、戏馆成为大众常常涉足之地。而这些涉足期间的人“又不必尽富商大贾与夫显宦客官之暂时至止者,即橐笔寒儒、经纪小伙,亦尝呼朋引类,游宴其中”。因此消费习惯而带动的酒店、茶店、烟店等生意异常兴盛,“费不必洋钱者,较之别处所用,亦多至十倍”。针对这样的现象,文章呼吁:“于此十倍之中,大者省费一月十元,小者省费每月一元,尚不至于杜门谢交,无可赏心悦目。盖通计一月之中,在殷富者十元之洋,不过太仓之一粟。即平常之人,每月一元办差,如钱绳之串底。月省此十元、一元,止须于阔绰之中,少存减省即已留此有余。”文中以为此节省之费用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这些款项用于慈善救济事业,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苟有如山东青、莱之饥荒者,一赴上海而愬之,有何捐赈之不可办哉!”
为了进一步论述节费助赈的重要意义,文章还说:“前山东之灾西教士倡为启文,而捐者络绎不绝。香港之西人、日本之西人,均各解囊相助,交教士散赈。旅居上海者更无论已。本馆方谓西人肯如此急公好义,而中士之人反不能拯中土之灾,未免甘心让美于西人。厥后中人亦均乐输助赈源源而来。”[14]如此看来,中国民众应该试图超越西人,积极献身慈善救济事业。此语境之中,透露出中国人进行慈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途要走,至少慈善意识领域内需要提升。
文章接着提到鹤鸣戏园和久乐戏园助赈的情况,认为鹤鸣戏园和久乐戏园开展了演戏助赈活动,是率先开启了演艺助赈的先河,运用“折扣其一切开销以其余资赈饥之用”的“歙钱之法”是中国人天良之发的体现。针对有些人认为“戏园藉此招生意,以看客之钱资,其博取美名”的说法,文章认为:“不然。人情惟无所激动于中,即有是心亦不感发,彼赴园看戏者,岂非即余所谓月可省十元至一元之人哉?有此可省之费而不知省,藉戏园之倡,定此章多住数次,既得恣游嬉之乐,又遂戏园敛助之意,明则耗看戏之省,而暗已襄助善举,一事而三善备焉。是亦何乐而不为哉!彼戏园故不以招生意为嫌,而居然登之告白示之众人,亦可谓好善有诚矣!然诸观剧者必待戏园之倡行此法,始以多出资者匀其半以充赈,何如以平日之少出资者,留其余以待赈,不尤为实惠哉!”[14]针对戏园开展演戏助赈的异样看法,文章进行了辩驳,并指出人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慈善,而其中个人在戏园日常消费转而为进行慈善活动,并不会影响到自身娱乐,反而能够博取善士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同时,《申报》中对于鹤鸣戏园和久乐园进行戏资助赈行为的支持态度,也在散播一种全新的慈善理念,即寓善于乐。
鹤鸣戏园是1877年4月28日开始慈善演艺到6月15日止,持续50天。久乐园班是1877年5月14日开始慈善演艺持续一个月,截止到6月14日。鹤鸣戏园和久乐园开展的慈善演艺活动成为将慈善与演艺进行融合的起始,可以认为是中国包含现代性意涵的慈善演艺活动的开端与起步。从此,中国的演艺助善逐渐增多,并成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转型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助赈专场:华人慈善演艺活动的进一步拓展
在“丁戊奇荒”的背景之下,营业性质的上海鹤鸣戏园率先发起了慈善演艺活动,久乐戏园紧随其后,奠定了运用“折扣其一切开销以其余资赈饥之用”的中国戏园慈善演艺筹款之模式。因此,1877年可以认为是中国慈善演艺的兴起之年。
继鹤鸣戏园和久乐园之后,中国慈善演艺活动在演出规模的拓展方面有了进一步发展。
可能是受到《申报》的一再呼吁,1878年5月,上海著名的天仙园、丹桂园、大观园分别表示开始专场式的分期助赈演出活动。《申报》刊文如下:
直陕晋豫四省死亡遍野,本报已详载言之矣。沪上一隅,人咸向善,筹捐筹赈,书 不胜书。兹闻经募司董向各戏园熟商助赈,丹桂园许于本月二十六日即礼拜一起,每逢礼拜一、四日演,共一月,计八期。大观园于本月二十六日夜即礼拜一,又本月三十日夜即礼拜五,又五月初三夜即礼拜一,又五月初七夜即礼拜五,共四期。天仙园于本月二十九夜起即礼拜四,共一月,计四期。三园每逢是期,邀集名优,排演新戏,所集戏赀,除茶点开销之外,余洋尽数送交果育堂助赈。凡诸君欲及时行乐者,皆宜届期往观,既畅游兴,藉助赈资,真一举而两得也。呜呼,诸伶之好义如此,方诸古人抑何多让哉!惟老三雅、禧春两园尚未闻定议,想善与人同,当无不闻风兴起也。[15]
该文实际上包含着几层意思:第一,面对“丁戊奇荒”,上海地区开展了义赈活动,此次大观、丹桂和天仙戏园准备“分期助赈”,实际上是办理义赈的“经募司董”向各戏园商量的结果,背后反映了义赈同人的主动作为。第二,大观、丹桂和天仙戏园各自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分期助赈行动。第三,三个戏园为了吸引顾客,通过“邀集名优,排演新戏”来进行,此可以认为是戏园自身的举措,也体现出营业性质的戏园自身的娱乐特性。第四,三个戏园在善款筹措上,依然采用了“除茶点开销”之外的方案,将戏资上缴慈善机构即果育堂。第五,三戏园的演戏助赈之举,是伶人投身慈善救济事业的见证,体现了伶人的担当。而演戏助赈对于顾客而言,则“畅游兴”又“助赈资”,一举两得。并希望其他戏园如老三雅、禧春能够加入到分期助赈中来,发挥善与人同的效应。
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慈善救济在物质层面,主要针对的是物质资源如何分配的问题。营业性戏园维持自身的收入对于戏园自身而言是第一位的,举办慈善演艺活动,自身的临时性收入会减少,但长远看,可能因为慈善演艺塑造的良好形象又会成为自身的价值,进而带来经济收入。因此,在临时性质或者短期持续性质的慈善演艺活动中,能够合理规避因为经济收入降低而过于影响自身的生计和成本的情况之下,是最起码的商业经济准则。
因此,这三个戏园实行的“分期助赈”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鹤鸣戏园和久乐园戏园在营业策略上的延伸和提高。三个戏园从单个讲,丹桂戏园的慈善演艺场次最多。而从演出时间来看,基本上都选择了礼拜一、四、五这三个时间。而且,演出的场次以夜戏居多。通过演出日期,可以知道当时上海租界的戏园已经明显受到西历时间观念的影响。时人记载当时上海民众的日常生活:“第一开心逢礼拜,家家车马候临门。娘姨寻客司空惯,不向书场向戏园。”[16]从西人“礼拜”观念的渗入到普通市民奔“向戏园”的变化,可见上海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趋向。而丹桂、大观和天仙之所以选择礼拜一、四、五的夜场,是因为这三个时间往往顾客没有周六、周日多。如此一来,选择可能顾客最少的时间,进行慈善演艺活动,从经济上讲对于戏园的收入影响最小。从这个角度而言,大观、天仙和丹桂戏园为代表的上海租界戏园已经包含了比较多的现代性时间管理概念,其中也折射出慈善演艺活动中已经隐含较多的现代性因素。
三个戏园分期助赈期满之后,《申报》上登载了善款的具体情况:
前登贵报告白,有沪上大观、丹桂、天仙三戏园分期助赈一节,兹已期满,计大观园共缴洋二百零四元九角三分半,丹桂园共缴洋六十六员(元)七角四分,天仙园共缴洋四十九元七角四分,三共计洋三百廿一元四角一分半。此款本由本账房经募,今仍由本账房统收汇交果育堂汇解灾区作赈矣。此布。高易账房启。[17]
此则史料表明,一方面通过《申报》发布善款征信,体现了慈善救济活动的近代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民众更加明晰和跟进慈善演艺活动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使得民众发掘慈善演艺活动的善举一方面表现在表演过程中,另一方面则是常规的善款。分析善款的额度,还可以看到大观戏园、天仙戏园和丹桂戏园的经济效益状况。
慈善演艺的拓展除了“分期助赈”的情况之外,还体现为一种新的思考,此即“抽戏资助赈说”。1878年,为了赈灾,针对演艺领域,有人倡议另外一种参与慈善救济之法,即“抽戏资助赈说”。此种说法是有苏州“云水散人”提出的。他认为“迩来中州之灾,振古罕有,各行各业筹款往赈,既已无微不至,无力不竭奏,上而陶朱富室不惜破产以周,下而里巷蒙童亦知解铃而赠,甚至佛门老衲典衣钵以布施,妓院名姬积缠头以为购,而不知赈款究属有限,赈务尚无边际”[18]。戏馆可以承担筹款助赈的功能:“转辗思维,窃以戏馆一行或可酌行劝募,按每一戏馆日可延客百五六十人,少亦有二三十人,每日每人照加一十文作为赈款,每日作百客算,可捐钱二千文,每月可捐钱六十千文……在彼惠而不费,在我取不伤廉,而又可随赈务以行止,如能令上海、镇江均能允行,赈款亦不无小补也。愿筹赈诸君其图之。”[18]
此种新颖的助赈方法具有较明显的特点:第一,此筹款办法是针对“戏馆一行或可酌行劝募”,将戏馆每天“每人照加一十文作为赈款”。实际上是一种增加票价,将票价中的部分戏资进行助赈的方式。第二,此种筹款方法的优势在于“在彼惠而不费,在我取不伤廉,而又可随赈务以行止”,即稍稍增加了戏馆顾客的票价,戏馆拿出增加部分助赈,可以随着赈灾的进行而进行,赈灾结束则停止增加票价。第三,提出此种方法的人实际上身在苏州,并希望此种方法在镇江和上海两地都可以实行。
显然,此种“抽戏资助赈”的方法具有“寓征于价”之意味。对于戏馆而言,似乎并不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还能够满足顾客向善之心,并根据赈灾的进程而调整。与戏馆自身作为主体进行慈善演艺而言,此种助赈的方法似乎与演艺人士并无多少关联,但是毕竟属于演艺领域内的筹赈手段,因此与戏馆还是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质。
四、结 语
晚清时期,慈善演艺活动逐渐萌生。其间,受到了西方人士的刺激,通过《论演戏救灾事》便可以窥见其间西方慈善演艺的影响,体现为中西文化之间的碰撞。同时,《申报》作为现代性传播媒介载体的影响与促动也非常重要。《申报》的持续呼吁和跟踪性质的报道,使得慈善演艺行为开始在上海的戏馆中诞生。鹤鸣戏园于1877年4月28日率先发起的演出持续50天。紧跟其后的久乐园于是年5月14日持续演出一个月之久。1878年,天仙、大观和丹桂戏园作为上海著名的营业性戏园,开展了一个月的“分期助赈”,使得戏园为主体开展的慈善演艺规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在演艺领域内,时人提出的“抽戏资助赈”的方法,也增加了慈善演艺的内涵。
就文化视角言之,众多不同景象的慈善演艺情况,甚至不同戏园的不同演艺,其背后体现的是“寓善于乐”的理念内核。娱乐与慈善相互结合,有娱乐对于慈善的利用,也有慈善对于娱乐的需求,二者之间在慈善救济领域与演艺领域的相互作用,造就了饱含现代性意味的近代慈善演艺文化事象。慈善演艺中针对伶人的所谓“以下等之人而为上等之事”[12],折射出传统中国自身的文化特质。在慈善演艺领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使得中国慈善演艺事业呈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一面,进而展示了中西方之间在慈善领域内的一致与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