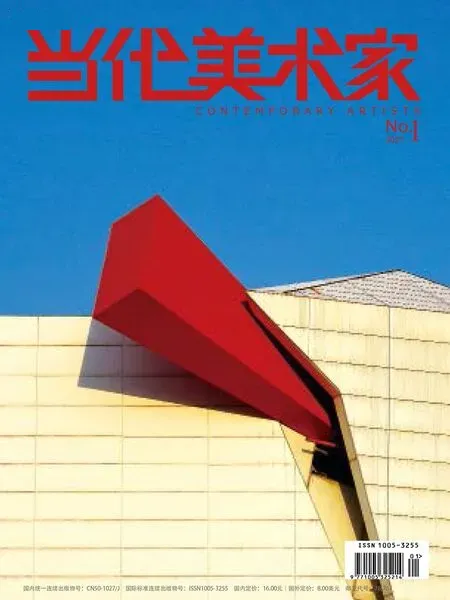礼物
——2021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学生提名奖
韦嘉 曹根 邓坤 洪文学 黄杰 候逸杰 焦兴涛 刘毓灵 刘诗琪 雷韵冰 马俊 申子叶 何桂彦 唐金凤 王钰婷 吴清鹤 姚德科 邹丹(排名不分先后,按发言顺序排列)

1邓坤看·见木雕尺寸可变2018-20202021“礼物”造型艺术学院学生作品提名奖展览现场
韦嘉:今天我特别感慨。一年前我们在这里举办了第一届“礼物”学生作品提名奖的展览和研讨会,从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畅想第二届。没有想到过去一年是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年份,我们都怀疑今年“礼物”提名奖是否能如期举行。最后仍然有150位同学投递作品,我很欣喜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尤其2020年上半年,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学习和创作,大家在家仍然在坚持创作,利用下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作品。布展期间每一位同学利用展厅的场域,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作品充分呈现,这对本科生而言是有难度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他们的焦虑、困惑,更多的是他们的坚持、理想,我觉得这非常可贵。
展览还是有遗憾的地方,希望疫情快点结束,明年有更多的同学们和专家加入“礼物”提名奖。
2021“礼物”造型艺术学院学生提名奖
2021年1月6日—1月20日
主办: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
独家赞助:easyart艺直购
展览地点: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2侯逸杰无题石版56cm×76cm2020

3侯逸杰虎虎虎石版56cm×38cm2019
曹根:从2016年开始,我的关注点在于建立内在秩序感、构成感的空间,创作焦点不仅是眼下的题材,还包括自身的性格特质,以及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我从生活中汲取感受,经由自己的观看方式进行体验,后期不断演变自己的图像,从而形成作品。创作中我利用手绘与版画结合的方式,画面被重构与整合。 通过调试手绘与丝网印刷的比重,突破以前的预期,以建立某种平衡关系。
我用柔性的材片进行版画实验,通过版画的复制性在画面中进行推演,这种复制性刺激了我的工作方式,让图像变得更简化,这也让我转变了自身的绘画方式。
2020年我创作了一些奇怪的风景。因为疫情原因我只能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进行写生,我想在熟悉的环境中增加陌生感,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风景,局部的排列也影响了我的审美观察方式。
我最近的创作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来到虚拟世界的体验。虚拟世界的体验同样真实,甚至比现实生活更加强烈。在画面中我以点状的形式在虚拟游戏规则中建立一种秩序。
邓坤:我以木雕的形式雕刻自己的内心独白、对周遭世界的感悟、对人和世界的理解,这是一个由外而内自见、自省、自觉的过程。
我的小木雕系列,关注自己内心世界、内心的独白,题材来自记忆或者想象,雕刻的手法是虚拟的推敲、局部的推敲,使用的工具比较多,从电锯到各种平刀、斧头、镰刀等。《倒影》有触摸感;《红秋裤》经历了我的两次否定;《午觉》是我第三个阶段的作品。开始创作小木雕的时候我特别拘谨,后来尝试用斧头雕刻,找大块的感觉,并产生了一些创作的偶然性。
我疫情期间的思考,更多的是祈愿和希望。在这期间,我创作了《财神》和《佛眼》。《佛眼》有一点游离和不确定,我可能舍不得对细节的刻划,中间又加入了很深入的东西。
“大学城即景”系列,我从内部世界转向对现实的关注,用速写的方式记录对时代的所想所感。从《广场舞大妈》开始,我确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用斧劈的方式进行创作,很畅快。
我的创作采用直接雕刻技法,没有底稿、小稿、草稿,主要是偶然性和过程性的体现,呈现了手工制作感。从对局部的迷恋到对大关系的把控和书写,从幻想走向现实,内观而作,由心而出,释放又克制,回到雕与刻,回归到原始,回归本质,让双眼、双手进行思考。
洪文学:我的创作关于记忆碎片化,图像模糊重现、片段式的方式进行绘画语言独特性的探索。短时记忆通过复述传递,形成长时间的记忆。我的作品以瞬间性、碎片感、模糊化为主,内容以日常元素为主,伴随有一些场景、空间。
我以北漂住在地下室的记忆和真实的生活场景空间进行了创作。我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尝试这样的创作方式,来源是比较具体的体验。然后逐渐带着相对来说晦涩、压抑的情绪寻找像仓库、废墟这样的空间,以及很少被关注的杂物。后来我发现创作比较乏力,就继续北漂,用一个暑假去学习,形成了这一幅作品。这是一个转折点,我在追问真实的自己是什么,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因为我的生活经历,选择了很通俗,比较模糊的、去除了人物脸部、繁杂场景的方式。
第二个系列的作品“记忆系列”,是我本科毕业创作的一部分,采用了图像组合的形式。我选择了关于春节记忆的小片段。我没有安全感,或者说孤独、疏离,创作也带着这样的感觉。比如床边的光,作品中温暖里会带有小小的孤寂。“物语系列”我用多种组合的角度呈现日常生活的瞬间,呈现了插画式的不同视角。
“光系列”是我当下的创作,压抑的情绪有了一些改变。作品类似小资生活的瞬间,但我想表达自己理解的都市的温度。
黄杰:我把自己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法称之为“个体工厂”。以我去年的作品为例,我收集了一些传统农具,把它们重新拆解、打磨,然后再设计卡板、缝纫,为了达到更精细的程度,我边设计边缝纫,然后包裹,最后组装。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个人的身份好像转变成了一个工人,不停地计时、计件。
2015年我就开始以“杀马特”群体与渐渐被遗忘的农具相结合。我对“杀马特”的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对他们最强烈的印象也许是发型。2015年我感受到了城乡差异,我感觉城市发展特别快,农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一条路可以走一辈子。当时我看了一部电影《心花怒放》,因为电影里的“杀马特”,我开始关注他们。
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农具开始被遗忘、弃用,我想通过另一种方式让物体异化、失控化,重新回到美术馆展示它们,让不同年龄层重新认识过去和这些农具。
每一次展览我都希望以不同的方式呈现,这一次我以荧光橙作为背景,以一种杀马特的审美方式,营造一种失控感,表达今天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我把“杀马特”群体放大为一个整体,以农村的审美视角与消费文化碰撞,产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我在思考:创作以个人方法、个人经验出发与社会发生关系在当下是否是可行的?
候逸杰:我的创作有两次转变。本科我学习的是木刻语言方向,进入研究生阶段我延续了这个方向。但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创作进入了惯性,顺手的感觉让我很警惕。木刻的特性让我的思考进入了既有的模式,我希望作出一些新的尝试,拓宽自己。所以,我转向了石版画。
石版画有更直接的表达,也有更丰富的表现,给我带来了一些刺激,创作面貌发生了第一次变化。但版画的特质决定了特殊的工作方式,这要求我要有长期规划、全面掌控、预见性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不久之后我遇到了困境,很难将瞬时的感受和长时间理性的工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阶段我无法进行个人语言的持续推动。这其实是一个对自己推倒和重建的过程,也是自我怀疑和否定的过程。
我基于之前不成立的画面进行覆盖、破坏和重新修改,创作了一幅作品,为我提供了另外的可能性。通过自我否定,在某种程度上放下了心理的负担和枷锁。从这之后我的创作走向更为直接的方式。
那之后,我慢慢找到了石版画的肌理和语言、特质、温度感,找到了自己诉说的方式。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每一次的变化都基于对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在反复与自己对抗的过程中慢慢推进作品。在与自己反复拉扯的过程中,我也在不停追问自己创作的源头,反问自己,理清创作来源和思路。
焦兴涛:这5位同学可以分为3个类型。曹根和洪文学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习过程,不断探索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内心和外部世界,他们的语言、主题变化、探索比较多,这是非常自然的学习过程。探寻自己和外部世界、语言之间的联系,必须要通过很多的实验;邓坤和黄杰专注于具体的材料、技法、方式,围绕材料、形式和背后的文化含义、暗示进行工作;候逸杰最具有语言和表达的自觉意识。
艺术是语言无法到达的,所以我们才用艺术去呈现。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要用语言去讲?因为除了作品,我们还希望感受创作作品的人,他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能更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讲述”就像房间里的墙和柱头,它们不是空间,但是因为它们,我们能感受和理解、触摸这样的空间,这就是讲述的意义。
从学校人才培养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基于艺术创作实践对自己工作方法的归纳、建立和艺术史的关系,个人的创作往往到后期会失去方向,这也是研究生培养非常重要的一点。“礼物”提名奖通过入选艺术家的讲演,从作品出发,告诉自己、告诉大家他们的创作逻辑、方法和自己的艺术史。
刘毓灵:从我学习雕塑开始,就有一种无力感,在基础课程上我觉得我不太会做雕塑。后来我开始接触木雕,也还是处于一种无力的状态,作品没有独特性,但我还是坚持下去了。5年过去,到了毕业创作。我觉得毕业创作是我和之前不同的阶段,那件作品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些情绪,当时处在疫情期间,觉得自己技术上也不过关,整体上有一种负面情绪。亮丽的颜色从第一视觉上会吸引到别人,也会消解自身的负面情绪,给人感觉更清新。
我现在还是处于兜圈子的状态,还在探索。《再见了,玛丽亚》是我开学以来做的一批作品,布展的方式上我想打破常规。我自身也处在很混沌的状态,就制造了一个比较混乱的场域,它没有第一视觉点、中心点,观众要在其中发现一些独特的东西——不是靠第一视觉把大家吸引过来,而是走进这其中观察到一些东西。这件作品也是我对木材的尝试,创作的成品和预想有一些偏差。我想我应该训练一下自己对雕塑的观察方法,我把头部和下半部分做成立方体,通过视觉的训练,不用尺子、水平仪,只靠眼睛和雕刻刀做立方体的形。做出了一个立方面,但是其他面没有做到,我就保留没有做出来的部分。
刘诗琪:我本次展览的作品《接触系列》延续了之前的想法,这组作品创作时间并不长,是2020年下半年陆续完成的。
我喜欢用拍照的方式记录自己身体的变化。有一次我拍下了这样的照片:皮肤形状因外部压力改变,又恢复原状,我开始对皮肤的可塑性和因压力造成的皮肤痕迹产生、消失的过程感兴趣。现实生活中的伤害也有私人化、难以被察觉的特质。我想作为记录者,把印痕当做伤害的见证,开始了第一组作品。2019年,我选择有代表性的图片转化成绘画。这之后我开始关注外界物对可塑性个体的挤压和伤害的现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想往材料方向做一些延伸,第二组作品的关键词是儿童。儿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塑物,会因不同的文化输入往不同的方向成长。材料方面我选择了可塑性强的黏土、彩砂这些儿童玩具,完成了作品《保持距离》。但我还是想回到完全的架上绘画。
接下来的延伸,就是作品《接触系列》。某些意义上,气球的特质和人很像,有弹性、可塑性,可以承受一定范围的压力,但超出范围就会爆炸。我用肉色气球作为对象,让自己成为施暴者,将气球模拟成身体,构建出各种场景,记录我和气球紧张的挤压关系,结合高饱和、热烈的背景,同时对一些物品进行虚化、锯齿化的处理,把画面氛围中和,形成了这组作品。这组作品还算不上成熟,但也是朝着我的理想效果做的一次尝试。
雷韵冰:我本科在雕塑系第四工作室器物工作室学习,对物的迷恋对我创作的影响非常重大。
我觉得艺术家有两种身份,第一种是导演,要处理各种关系,预设所有可能性,记录过程,然后按逻辑顺势推导。另一种身份是海盗,一旦他靠岸跟公众会面,会亮出手中的宝物——他的创作。 我本科时更像海盗,研究生期间我想往导演的身份前进,尝试处理一些综合性的关系。
《如何把一个苹果分给563个人》,我用了苹果、砂纸、卷纸。我把苹果在砂纸上磨一下,然后印在纸上,563次后苹果被消磨掉了。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一卷苹果,这个过程有点像健身,是我自己的劳动或健身方式。“印”类似版画,卷纸可以被分割、分发,形成了传递功能。我决定把这一卷苹果以分发的方式带给大家。
疫情期间我每天待在家里,不能接触外界,只能通过手机了解信息,但是信息非常复杂、具有欺骗性,感觉世界被折叠了。《人间共盒》我做了这样的结构——盒子打开后拥有巨大的空间,但是折叠起来,又只是一个盒子,像我们当下身处的世界。
《王氏花架》是2020年5—8月在地创作的作品,属于“艺术门诊、艺术治疗”计划,以门诊的方式发现家庭的问题,以艺术的形式解决。我遇到的是一个姓王的家庭,他们想要一个花架。实地考察后我利用他们的姓氏融入作品,作品更加流畅,更符合他们对生活的期待。

4黄杰作品展览现场
马俊: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我和何春怡两个人合作的。
《童时发生》是以黑色方盒子的空间形式(3m×3m)搭建出的作品。作品中的小孩源于我堂哥的孩子。他从小生病,不长头发,在学校经常受到歧视、被欺负;小学还没毕业父母就离异了,刚上中学因下河游泳淹死了。这件事成了我的心结,之后我一直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2019年11月,我找到堂哥的孩子淹死的水坝,自由落体坠入河中,想体验在水中窒息、在空中失控的感觉。因为习俗,小孩去世后不会有葬礼,我想以某一种方式怀念、纪念他。
2018年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去了西藏,把自己头发剃光了,想感受一下没有头发的感觉,2019年做这件作品之前又剃了一次。我们最开始设计的作品有三个进出口,现场空间很乱,最后留了两个进出口。空间里有很多儿童的衣物、鞋子、玩具,都是收集的儿童使用过的东西,形成这样一个场域。
申子叶:我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以材料还原物,以材料自身语言创作组成作品,让材料跟我自己发生关系。
这次的参展作品《长江》,一部分灵感源于我大三木雕课的作品,沿用了当时的线性语言。玉的打磨过程离不开水,我把每一块玉做成了河流的形态,组成长江。上游的水比较清澈,中下游被污染之后呈现出黄色。
《关系系列1》我用石膏给自己翻模,作品的内部形体是我自己,外部打磨形成抽象的形体,有对比关系,还有虚与实、内与外的关系。《关系系列2》是《关系系列1》的延续。石膏是一种中间媒介,不能被永久保存。我通过之前的模具进行翻模,烧成了陶瓷。陶瓷很脆弱、易碎,中途断裂了很多,我用金线把裂缝补好了,还挺好看。
《天使印记》是对疫情的思考和创作。我们经常会看到医生和护士长期佩戴口罩,脸上有很多印记。棉签的形态很像病毒,我用棉签和医用材料组合在一起,做出了一些可以佩戴的作品,加入了一些当代首饰的观念。
其实我现在处在比较迷茫的阶段,马上就要开始毕业创作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出很好的作品,希望找到自己的艺术方向。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艺术家,能不能成为艺术家,也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能走多远,但是我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何桂彦:申子叶、刘毓灵都谈到迷茫,我能感受到你们在语言方式寻求中的探索。
我个人觉得在研究生期间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语言媒介和材料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解决现实、时代以及个人内心之间的关系。此前5个同学的发言中,雷韵冰、马俊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从一个个体的点出发,在工作方式上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作品不是学校和工作室的产物,涉及到社会调查,涉及到对一个阶层或者深层次的探索。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的艺术文化的内涵、所积淀的思考,才会让作品变得更加有力量,这在这两位同学的创作中体现得比较好。
第三是跟既有的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特别重要。很多年轻艺术家会很迷茫:我们学美术史干什么?我认为,学美术史更重要的是形成美术史的思维方式,这对大家的成长特别重要。今后的创作,会跟既有的知识系统对话。比如雕塑,材料会涉及到古典主义雕塑、现代主义雕塑、1960年以来的雕塑。材料本身是物理的、过程的,同时也跟场域发生了关系。作品可能会源自于偶然、生活体验、不断试错,这都没有问题。但一旦以更高层面要求自己,以及在上下文当中判断自己作品的时候,它一定会跟既有的知识系统对话。这个知识系统可能来自于既有的东西,也可能来自自身的经验,它会为艺术创作找到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
唐金凤:我的作品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数码绘画和纸本。我的创作方式跟个人的性格、习惯、兴趣有关,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猎奇的玩具、搞怪和趣味性的东西,还喜欢写脚本,设想一些故事情节。我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不断画小短线是一个疗愈的过程,鲜艳的颜色充斥在画面中,也让人很有安全感。
作品中有我自己设定故事情节和趣味性的人物形象,我和朋友相处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很搞笑的行为,我就会记录下来,在作品中演变成更浮夸搞怪的形象。
我平时收集了很多各种人物形象小稿,就把它们全部放在一个画面里了。
考研期间我压力很大,又很想画画,就创作了这一组作品。当时我在记单词,这件作品是用马克笔、记号笔画的。因为我英语很烂,所以就不断地写,然后用酒精破坏它、消解它,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记下来很多,但是完成了作品。
王钰婷:2018—2020年我个人的创作脉络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在创作内容和学习的目的上会有一些变化。
2018年,我进行了两个方向的训练,一是对去概念化图像的转换,二是材料熟悉。这期间有很多画面图像来源于文本,通过文本到图像的转换,对自己进行图像训练。
2019年上半年,我们集中学习制作版画。当时我对版画的控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采取了版画和绘画结合的方式。
2020年上半年,因为疫情待在家里,感觉被网络信息,以及对未来的恐惧裹挟着,我需要寻找一个出口。这一组作品我下意识地采取了冷色调和红色调组合,展现出红色很微妙又有点危险的感觉。
2020年6月,我回到重庆,生日那天室友送给我她自己养的玫瑰和百合。我当时非常想以花作为主题进行创作,而且想对自己的观察进行训练,看着花写生。但是我画得非常慢,最后定格在花枯萎的样子。这两张画,不光有和生活、他人的连接,也有在绘画中突破的训练,对现实观察的训练。
第五个阶段我进入了全新的学习,想在创作中有一些新的启发,尝试了很多材料和绘画的方式。研究生期间,我的时间变得很碎片,所以有很多时间推翻上一次的构思,再进入下一个阶段,像走螺旋楼梯一样。
吴清鹤:我演讲的主题是“公共艺术如何塑造我”。
我去了很多公共艺术现场,看过这么多的现场后有一个反思:现场不是艺术家的画布,尤其对公共艺术来说。那我如何在现场创作?
研究生刚入学的时候我在杭州莫干山,和当地的竹编艺人共同完成了一组作品。2019年我参加七塘雕塑实验基地,通过调研跟当地百姓交流,他们说竹子会发声。我以竹子为媒介,寻找创作的灵感,每一根竹子加上不同的铃铛,观众可以参与互动。
我在海南跟父亲一起完成了《行走的厨房》。我们家是做焊工的,父亲长期在外工作的时候我母亲会跟在后面。我给每个厨具加了腿,妈妈觉得很奇怪,我说父亲的付出也有你一半的辛劳。
经历了这么多现场,我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假问题就不会有真创造,这一点仅对公共艺术而言。公共艺术中,有公共性、互动性、在地性、艺术性,把我原来绘画的方式转回了现场。这一次参展的作品是《微观·铁路岁月》,它是2019年完成的。黄桷坪社区里有一些老物件、以前的记忆,我采用了线上线下相互结合的方式。这个作品能成立,放在铁路山村,现场有很多灰暗的空间,我只是通过很小的动作把它激活了。
公共艺术让我有问题意识、现场意识。问题意识是真问题意识,现场会告诉我该如何做,如何放低艺术家的姿态。三年下来由本科绘画状态,慢慢走到室外,有一种小我到大我的过程。

6吴清鹤协助:王婧、刘佳、鲁炳辉微观·铁路岁月综合材料尺寸可变2019
姚德科:我在大三时对之前的幼稚行为完全否定,停止了绘画,开始写文字梳理自己。写到现在,我慢慢从一个感性的人变成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版画制作中最有趣的是过程性、特殊性。过去很多版画都以最终印刷结果为展示,关注更多的是版画图像的结果,没有过程。我觉得这削弱了版画的特殊性,因为从制版开始,版画已经开始制作了,过程性的思考贯穿了我近年来的实验。
人们用各种方法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冲突。《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我通过木版的破坏来制造矛盾,再通过转印、印刷,之后我用颜料把原来的伤痕、矛盾掩盖掉,最终形成一个人的形状。好像我们都会用各种方式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冲突,让大家看起来像个正常人,表现一种表里不一的情绪。
在《微笑》中我故意把版画的结果削弱了,6个相同的笑脸,让观众去观察每个图像木刻的过程。通常木刻的状态、背后的情绪是隐藏起来的,我故意情绪化放大、拉大,最终形成这样的画面,也恰好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
艺术让我了解自己,面对矛盾的同时,也是在和自己和解的过程。我经常会怀疑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属于艺术圈这个环境,可能因为快要毕业了,现实和理想的问题逐渐被放大,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
我的作品就像我的内心一样充满矛盾,我想表达社会的种种矛盾和现象。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更像看一面镜子,可以看到我内心的转变。以前的作品就像自画像,对我来说,这些作品更像是自我疗愈的一颗糖。
邹丹:我本科读的是工业设计系,所以我是一个跨专业的学生,创作周期还比较短。
一开始我和很多喜欢绘画的同学一样,画一些照相写实和具象表达的风格。之后我延续了这种创作逻辑和脉络,了解到图像学的一些知识,创作上进行了图像的结合,比如戴脚铐的猴子、资本家的形象、奢侈品牌的图像符号和荒漠图像结合的冲突,表达画面上的错位感。
后来我开始被线条的美感和植物之间层层叠叠的感觉吸引,随着深入的学习、对其他艺术家的研究,以及自身的感受,我的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平常会收集一些手抄本、小人书、漫画作为素材,这些作品的形象不存在特定的解码,我希望通过图像重新组合和拼贴、堆叠,让它们有一种新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图像经历了变形之后的另一种解码。劳森伯格的创作对我影响很大。
研二到研三期间,在材料上我放弃了传统的亚麻布,选择了半透明的纱,并且发现了可以转印的材料。我之前总舍弃不掉点线面的创作习惯,可能是学院派的通病,后来我在创作中有意舍掉这种惯性。
针对这次展览,我还想做一些空间上的尝试,比如利用墙角展示纱面的作品。这件作品中有一些图像是爱迪尔马雷,他是一个科学家,在医疗、心脏、航空方面很有建树。他在研究时不经意创造的图像,在我看来有一种审美艺术的图像感,但是这种身份的错位感让我很感兴趣。
我还在同一个画框上放置了双面纱,上面的图像一些是我收集的,一些是我创造的。从正面看过去,和从背面看会一种错位感,两层图像会堆叠在一起。
韦嘉:这一组差异性特别大,他们都面临各自的创作状态。唐金凤敏锐、敏感、直接,她的作品就是一种情绪。王钰婷在本科阶段就显示出非常强的自觉性,选择了今天这种绘画方式,特别异样、冷峻,不符合她的年龄段。如今她最新的作品反而变成了非常具有结构形态、简化的画面,这是在创作中非常难得的过程。吴清鹤是在地创作的典型性艺术家,这一次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可贵的尝试,把他的田野观察、在地的沟通和观察得来的切入点,通过结合空间、话语的创作移植到美术馆。姚德科的作品体现出很强的思辨,这在版画本科阶段比较难得。他很早就提出问题的介入,反思版画过程性和结果之间互动的联系。我之前不知道邹丹的研究生学习是跨专业的,在我看来她的图像已经比较成熟了,碎片化的图像通过她的整合,形成有个人印记的偏向风景形态的图像转换,显示出她缜密的思考和具有成效的实验。
作为一场活动来讲,“礼物”提名展今天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创作者、执行者来讲,今天又是一个开始,我们梳理了自己的过程,对未来的判断、自己艺术道路的路径,包括如何在未来更好地跟同学们沟通和呈现作品,这是一个新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