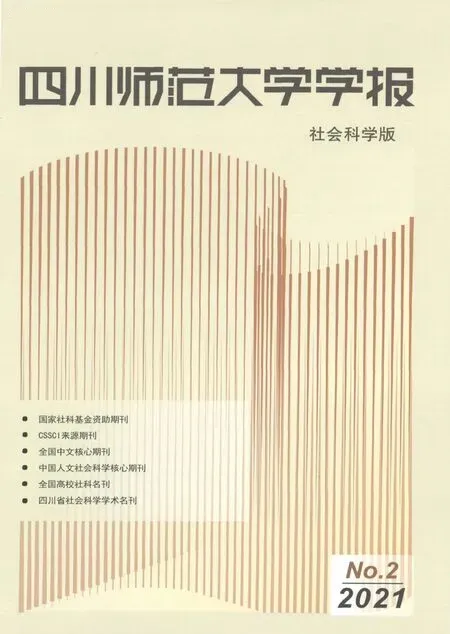实践作为人的自由与本质
——从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马克思的发展变革
李科政
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门类,实践哲学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节点上、在众多独具风格的哲学家笔下,常常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历史性的纵向比较常常给人一种误导性的印象:那些伟大历史人物的实践哲学在内容上仿佛是毫不相干的。除了共享“实践哲学”这一相同的名称,以及把“实践”当作共同的研究对象之外,他们的观点与论证似乎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由于缺乏足够深入的反思,单从历史文本的表面叙述出发,那些伟人们甚至连“实践”为何物都远没有达成共识。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深入的考察告诉我们,那些真正富有洞见的实践哲学,无论它们在细节上表现出何种难以调和的差异,“实践”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始终都与人的自由和本质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根本就是一回事。在几乎所有成体系的实践哲学中,“实践”“自由”与“本质”都构成了一个相互叙述、相互证成的概念体系,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论证框架,并且在该学科的发展史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贯彻。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这一论证框架就已基本成型,并且在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学者那里发展得更加成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代表了该学科的一次重大变革,但他的学说依旧遵循了这一古老的论证框架。
一 亚里士多德的奠基
西文中的“实践(practice)”和“实践的(practical)”都直接来自拉丁文,但它们的根源是古希腊文中的Praxis(πρãξι)和praktikos(πρāκτικ)。Praxis(πρãξι)是动词的名词形式,praktikos(πρāκτικ)是它的形容词形式。的意思是“去做”或“行动”,因此,Praxis(πρãξι)无非就是“做”或“行动”,praktikos(πρāκτικó)也无非就是“关乎行动的”。因此,古希腊语中的“实践”和“实践的”,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差别不大。然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所讨论的“实践”,却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它排除了同样“关乎行动”的“创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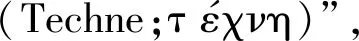
实践与道德行动的关系。就本文的意图而言,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似乎把实践等同于道德能力,把创制本身——而不是在同一个善的或恶的目的的关系中的创制——看作道德上中立的。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并且把“明智”与“技术”都算作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他也强调说:“伦理德性既然是种选择性的品质,而选择是一种经过思考的欲望。”(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21页(1139a)。因此,伦理德性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更具体地说,是要接受理性中“推理的”部分(推理能力)的指导(6)实践的理性并非“知道某物是什么”的能力,后者在近代学者那里被称为知性。一般而言的实践理性是这样一种能力,它在已知的多个知性命题之间做出推理,并最终得出一个“我应当如何行动”的结论命题。近期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对《尼格马科伦理学》中的实践推理形式的细节性讨论,可参见:朱清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再思考》,《道德与文明》2018年第3期。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多加论述。——节制、勇敢、公正等伦理德性,若不是在实践和创制的指导之下,若无明智和技术的德性,就无法得到培养(7)对于这个问题,廖申白教授曾指出,有德之人的感情与理智具有良好的关系,即感情“听从”理智,并合力使行为的欲望受到实践理智的调整。因此,他强调,(伦理的)德性是需要通过“实践的努力”才能获得的。参见:廖申白《德性的“主体性”与“普遍性”——基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一种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11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实践的还是创制的理智德性,都适于指导道德行动。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实践直接地与道德行动有关,创制则仅仅间接地、作为手段与道德目的有关,并且也可以如此与非道德的、不道德的目的有关。因此,真正说来,唯有实践才是理性中的道德推理能力,也唯有道德理性才是真正实践的理性。(8)更为深入的研究与论证,可参见:聂敏里《亚里士多德论理智德性》,《世界哲学》2015第1期,第85-100页。当然,必须承认,这种从道德相关性的角度对实践与创制的区分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并不是十分明显,但它将在后世的实践哲学中,尤其是康德的伦理学中,得到更丰富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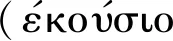
实践与人的本质相关。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对人的本质的确切定义,但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一个说法,即人有别于植物、动物的特殊性在于其“有理性(逻各斯)部分的活动”(13)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14页(1098a)。,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依据这一说法,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说法——例如,“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14)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980a)。,以及“对每一事物是本的东西,自然就是最强大、最使其快乐的东西。对人来说这就是合于理智的生命”(1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8页(1178a)。——人们通常都推定,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实践就必须是人的本质性活动。正如前文所言,伦理德性必须接受理性的指导:“明智原则本乎伦理德性,而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1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9页(1178a)。。这意味着,明智的行动,亦即有德的行动实践地体现出人的理性本质。当然,亚里士多德似乎没有把实践看作理性本质的最高体现。事实上,他推崇理论思辨甚于实践,思辨的生活是他心目中最高的幸福:“只有这种活动(思辨活动)才可以说由于自身被热爱……从这种活动中什么也不生成。而从实践活动中,我们或多或少总要得到另外的东西。”(1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第227页(1177b)。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毕竟把实践与人的本质关联起来了。而且,这种关联有助于为实践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实践与人的自由的关系提供证成。
总结起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提供了一个“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在其中,“实践”“自由”与“本质”有一种相互叙述、相互证成的系统联系。简单来说:实践(狭义的实践)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关乎人的道德行动;道德行动是出自自由的行动,唯有自由的行动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从而是实践的;实践是出自理性的活动,理性是人的本性,理性本性在自由的实践中得到现实体现。正如前文所言,这一框架在后世的实践哲学中得到了贯彻,并且发展得更加成熟。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下康德的实践哲学。
二 康德的发展
康德主要在广义上使用“实践”一词,但狭义的实践观念在他那里发展得更为彻底。实践与创制的区分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实践理性批判》中表现为“定言命令式与假言命令式”,以及“纯粹实践理性与经验实践理性”。而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才更为明确地区分了“道德实践”与“技术实践”。在他看来,前者是“按照自由概念的实践”,从而完全独立地构成了实践哲学;后者则是“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从而“必须只被作算理论哲学的补充”(18)康德《判断力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6:171-172)。本文在引用康德著作时,除了标明中译本页码外,还依据学界惯例标明普鲁士王家科学院版的卷号与页码。。因此,对于康德来说,道德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一回事。而且,这一点唯有在他对人的自由与本质的讨论中,才能获得充分的理解。
自由的两个层次。谈及康德的自由观,很难不与奥古斯丁联系起来,后者在其著作中引入了一种古希腊人不曾明确意识到的、更高层次的自由观念。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他区分了两种状态下人的自由。(1)原罪中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自由表现为人对种种低等善(善的事物)的意欲和选择,但他无法超越这些低级善,从而不可避免将遭受永死的惩罚。(2)元祖犯罪前的自由。在这种状态下,人并不必然屈从于低等善,而是有能力自由地意愿高等善(作为至善的上帝),从而有能力自由地赢得永生的奖赏(19)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成官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依照康德的术语,这两种自由大致上就相当于“实践的自由”与“先验的自由”。其中,实践的自由是任性(Willkür)的自由(20)康德著作中的“意志(Wille)”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意志是指仅仅为理性自身所规定的意志,也就是道德意志,它是一个相对于“任性(Willkür)”的概念,后者是为感性的动机所规定的意志;广义的意志则同时包括狭义的意志与任性。在奥古斯丁那里,原罪中的人的意志就对应于康德的任性,因为前者是指那种必然地为感性动机所规定的意志。同样,元祖犯罪前的意志,如果是一个追求低级善的意志,也相当于康德的任性;但如果它是一个追求高级善的意志,则相当于康德的狭义的意志。,是自由任性(arbitrium liberum)的属性,具体表现为“不被感性冲动强制、能在不同可能性间作出选择的能力”(21)吕超《人类自由作为自我建构、自我实现的存在论结构——对康德自由概念的存在论解读》,《哲学研究》2019年第4期,第90页。,并且因此有别于动物性的任性(arbitrium brutum)(22)动物也有任性,但与人的任性殊为不同。康德指出:“任性就它以生理变异的方式(由于感性的动因)受到刺激而言,是感性的;如果它能够以生理变异的方式被必然化,它就叫做动物性的(arbitrium brutum [动物性的任性])。人的任性虽然是一种arbitrium sensitivum [感性的任性],但却不是brutum[动物性的],而是liberum[自由的],因为感性并不使其行为成为必然的,相反,人固有一种独立于感性冲动的强迫而自行决定自己的能力。”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3页(B562)。。相应地,先验的自由是意志(Wille)的自由,它消极地表现为意志“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积极地表现为“意志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法则”(2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4:446)。,亦即意志的自律(自治;Autonomie)。换句话说,这种自由就是意志完全独立于自然的必然性。
实践与先验的自由。先验自由的观念意义重大。首先,正如康德所言,实践的自由可以从经验中得到证实,但倘若没有一种先验的自由,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实践的自由,它是实践的自由得以可能的条件(2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第384页(B562)。。实践的自由之为“实践的”,是因为理性在任性中并非无所作为。但如果一切行动都仅仅是由任性所规定的,加之任性本身的规定根据总归是一个自然概念(偏好的一个对象),那么,它们在根本上就仍然只是依据自然法则发生的,同自然中的其他运动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正如前文所言,实践的自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自愿”)不足以解释行动的道德性。如果一切行动都只是自然运动的结果,那它们就毫无道德性可言。这意味着,规定道德行动的意志(作为行动的原因)必须自身就是一个独立于自然的原因。因此,道德现象本身就昭示了先验自由的客观实在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把道德法则说成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根据),把自由说成是道德法则ratio essendi(存在根据)(25)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脚注①。。因此,在康德看来,唯有在道德行动中才能发现一种彻底的自发性,使之作为真正实践的东西同自然的运动区别开来。
实践与人的理性本质。在康德那里,实践不仅同人的本质相关,并且实际上等同于人的本质。同以往的哲学家一样,康德把人看作理性的存在者,并且频频使用“理性本性(vernünftige Natur)”这一术语。而且,他在考察人的理性本性时,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视角,把“理性”看作一种活动着的、活生生的本性,看作人现实存在的方式。例如,在与自然事物的比较中,康德把理性存在者的独有特征描述为,“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亦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26)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30页(4:412)。。然后,通过对两种自由的澄清,明确了唯有以理性自身为根据(目的)的意志、亦即自我立法的意志才是真正实践的意志。他又进一步指出,“有理性的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2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49页(4:429)。,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是一个普遍立法的意志”(2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52页(4:431)。。因此,在康德那里,实践与人的理性本质上是一回事:实践无非就是理性特有的活动,也是其特有的存在方式,若非通过实践来展示自身,理性就还不是现实的——它要么被设想为依旧停留在一种假定的潜能之中,要么就根本不存在。
道德实践的困境。对于康德来说,道德实践就是理性本性的自我实现。但他承认,人同时是感性的存在者,受制于种种自然偏好,从而不仅有可能、而且时常把偏好的动机置于道德的动机之上(29)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2页(6:36-37)。康德用“动机次序的颠倒”和“根本恶”的观念来解释道德归责问题(即人自身何以是道德上恶的行动的原因,并且要为之负有罪责)。对康德伦理学最为常见的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康德把人的自然欲求或偏好看作恶行的原因,这也是他遭遇最多最狠的批评的地方,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康德即便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也至少是一个不通人情的家伙。导致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对《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粗暴解读,以及学界长期以来对《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忽视。事实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目标是要追寻道德行动的道德性来源,并且最终锁定了实践理性的自我立法,否定了偏好或偏好的对象具有充当这一来源的资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偏好或偏好的对象就是不道德行动的恶性来源。正如帕通(Paton)所指出的:“这两种动机是否能够出现在同一个道德行动之中,以及其中一种动机是否能够支持另一种动机……根本没有在《奠基》中得到讨论。”参见:H. J. Paton,The Moral Law or Kant’s 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NY: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1948),19。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也从没有反对人可以出自偏好而行动,他只是要求我们必须同时出自义务而行动。直到《纯然理性界限的宗教》中,康德才正面处理了恶性的来源与道德规则问题,并且提出了“动机次序的颠倒”与“根本恶”的观念。在康德看来,人对自然事物的感性偏好本身非但不是恶,反而还出自一种善的禀赋。事实上,惟有当偏好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相冲突时,人蓄意地选择把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依据偏好行事,而不是依据道德行事,才导致了道德上恶的行动。。在康德看来,这种“动机的颠倒”并非源自人类存在者的一种“生而俱有的”禀赋(Anlage),而是源自一种“自己招致的”倾向(Hang),“因为这种倾向存在于任意性意志的违背法则的准则中,而准则都是出自自由意志的”(30)刘凤娟《康德论人性中的善恶共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30页。。这大致就是康德的“根本恶”思想。根据他的解释,人只要同时是理性的和感性的,“动机的颠倒”在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根本恶是“不能借助于人力铲除的”(31)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第23页(6:37)。,人根本无法一劳永逸地战胜恶的倾向,达到道德上的完善。也就是说,人(至少就作为个体的人而言)在今生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道德上的完善,更遑论要求“德福一致”的至善。这是一个令人尴尬和悲哀的困境,康德把它叫作“实践理性的二论背反”(3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第106-107(5:113-114)、114-123页(5:122-132)。。而且,他没能为此找到别的出路,只能请上帝施以援手,把“更高的救赎”交托给神恩(33)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注释本)》,第106页(6:118)。。正因为如此,艾伦·伍德深信,“神恩”必须被看作康德伦理学中除了“自由”“不朽”与“上帝”之外的第四个公设(34)Allen Wood,Kant’s Moral Religio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248.。
如此,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在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下,康德以一套严密体系克服了亚里士多德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并且把以道德实践为核心的实践哲学发展到了更为成熟的形态。然而,以道德实践为核心的观念似乎也把实践哲学带上了绝路,并且最终因为上帝的出场,即便不至于使作为自发性活动的实践观念遭到彻底的否定,也不可避免地会为之带来难以回应的质疑。接下来,我们将考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他如何突破这一发展瓶颈,并因此实现了实践哲学的一次重大变革。
三 马克思的变革
谈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必须要考虑他的道德批判思想,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与传统实践哲学,尤其是康德道德哲学之间的思想联系——所幸,这种联系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赵敦华、俞吾金、王南湜等学者都十分重视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35)赵敦华《马克思哲学要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19-221页;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68页;王南湜《重提一桩学术公案:“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5期,第12页。。有学者甚至提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实践概念”,“正是借助对康德道德思想的分析这一重要环节,马克思才为道德找到真正的存在论基础,也正是借助这一新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视野,马克思才进一步推进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现象及其背后机制的观察、剖析和批判”(36)吴辉《论马克思和涂尔干对康德道德思想批判性阐释的范式差异》,《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1页。。判断这一评价是否恰当并非本文的主旨,但它足以表明,马克思以“劳动”为中心的实践哲学与传统以“道德”为中心的实践哲学或许并不像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不甚相干,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马克思的道德批判。马克思没有把道德现象当作一个专门的(更不是最重要的)主题来加以研究,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现象根植于现实的社会历史之中,对这一根源的揭示与批判远比对道德批判本身来得重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关心道德问题,相反,他的道德批判思想十分深刻。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把道德意识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把它看作是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的反映,在根本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例如,他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无产者)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再如,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批判孔德派说:“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15页。而且,在许多地方,马克思都把道德意识看作社会进步的阻力,有学者甚至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即使在道德意识成为革命性的地方,它的内容仍然由它所认可的阶级利益决定”(39)艾伦·W.伍德《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马克思关于道德的思想》,张娜、林进平译,《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5期,第11页。。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道德意识终究只是特定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意识形态,那就根本没有什么理性独立于自然的先验立法。因此,即便道德意识无需遭到彻底的否定,实践哲学的触角也必须延伸至更为基础的领域,“道德批判作为一种价值不能被由反映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历史批判所替代”(40)吴家华、施钰《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悖论”及其消解》,《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9页。,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再是“道德中心的”。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于康德来说,真正的实践是道德实践、纯粹理性的实践;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则应当是劳动实践、感性的实践。这一分歧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极易使人忽略它们在本质上的同一性,甚至可能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纯然技术实践的哲学。然而,正如前文所言,亚里士多德-康德式的实践哲学之所以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严格说来,并不是因为道德实践是“道德的”,而是因为它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这才是“实践”概念的本质内涵。因此,当马克思把道德现象解构为历史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道德意识也就不再表现为无条件的命令式,道德活动也就不再表现为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既然生产关系本身就是生产性的劳动实践的产物,那么,道德现象的根源也就只能到后者中去寻找。但是,马克思指出,劳动活动不止是“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更是人的“类生活”本身,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者,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把它“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对此,有学者解释说:“人的生产活动是人遵循其自由意志而进行的自主的、多样的和普遍的活动。”(42)汪信、柳丹飞《马克思的类概念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46页。作者还具体指出:“虽然人的生产活动最初也是为了肉体生存,但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并没有完全受制于这种自然需要,而是能够将这种需要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由此自由地控制这种需要。”“不同于动物千篇一律的生产,人的生产是充满个性的多样化生产,每个生产者的个性都将在其自由选择的活动对象、活动方式和活动领域等方面得到体现。”“人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质就在于人能够有意识地突破这一自然局限,实现由被物种属性所决定到自我决定的飞跃。”根据这些描述,人在把自然需求当作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时,在自由地为自己的生产活动设定对象或目的时,这些对象和目的对于人的意志和意识来说依旧是外在的。换句话说,在这些解释中,生产活动并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是以自身以外的别的东西为目的的活动,从而是技术实践的,而非纯粹实践的。这个解释固然是正确的,也确实表达出了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一个本质性区别,但没有完全脱离“手段-目的”的解释,并且似乎忽视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活动(作为人类存在者的生命活动)在把自己变成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中,展现出了一个直接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层面(43)相反,唯有在异化劳动下,劳动活动作为“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才会导致人的类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分裂,使前者彻底沦为后者的手段。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5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活动不仅是技术实践的,它同时也是纯粹实践的,并且适于充当实践哲学的对象。
马克思的自由观。康德把自由看作独立于自然法则的因果性(44)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第69页(4:446)。康德指出:“意志是有生命的存在者就其理性而言的一种因果性,而自由则是这种因果性能够不依赖于外来的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的那种属性。”,并因此把自由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马克思当然不承认这种先验的自由,但他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康德是一致的,即把自由看作实践活动的属性——尽管不是道德实践的、而是劳动实践的——并且认为这是人类活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劳动实践以自然为对象,“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8页。。然而,倘若据此认为,马克思只是在讨论实践的自由,或者(像有的学者所主张的)自然法则统治之下的选择自由,甚至把选择的自由看作“人类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46)李卫红《马克思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实践论解读》,《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58页。,这即便不是彻底的误解,至少也是片面的理解。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言,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活动并不仅仅是自身以外的其他目的的手段,它同时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从而直接地表达了人类存在者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与自然也根本不是一种绝对对立的关系,劳动实践直接地把人与自然联结成一个统一体。康德认为,人类理性在劳动中的应用依赖于自然材料的先行给予,并且因此是有条件的。但是,马克思认为,自然固然是劳动的可能性条件,但劳动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外化”(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也就是说,劳动活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把自身固定在劳动产品中(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7页。,并且以此“再生产整个自然界”(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2页。。马克思把自然界说成是“人的无机的身体”(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因此,自然与自由之间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制约关系,而是以劳动实践为中介的相互制约、彼此统一的关系。
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前文的分析表明,马克思把劳动实践看作人的本质。但是这个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同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的定义似乎存在冲突。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然而,这种冲突只是表面上的。有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提纲》定义中的“现实性”,其实是对“抽象谈论‘人的本质’问题的做法的拒斥”,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总和(ensemble)”原本是指“戏剧团和歌剧团全体成员及其合演、合唱意义上的总和”(52)汪信砚、程通《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经典表述的考辨》,《哲学研究》2019年第6期,第34、37页。,马克思使用这个术语是要表明,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通过劳动实践,在自己个人的社会生活舞台上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人的本质必须被看作“由人的活动创造出来的与将人看作一种社会的、历史的存在物”(53)汪信砚、柳丹飞《马克思的类概念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9期,第46页。。因此,我们至多只能说,《手稿》的分析偏重于(但绝不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纲》的定义则偏重于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的最大阻碍来自于雇佣关系所导致的异化,即“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发展到了极致。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能乞灵于上帝,而是必须通过消灭劳动异化的社会性根源来实现。
总的来说,相比亚里士多德-康德式的实践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有这样几项重要的变革:(1)从以“道德”为中心到以“劳动”为中心的变革;(2)揭示出劳动实践中“以自身为目的”的层面,实现了纯粹实践与技术实践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对立统一;(3)以第(2)点为基础,经由实践与自由的同一,在自由观上实现了自由与自然直接的、而非间接的对立统一;(4)历史性地探索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的实践路径,彻底扬弃对上帝的需要。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看到那个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实践-自由-本质”的“三位一体”框架,这个框架使得种种看似互不相容的学说表现出了基本的同一性。当然,本文的任务只是初步揭示出这一框架,并且在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显得十分粗糙。囿于篇幅限制,无论是对更多类型的实践哲学的考察,还是对特定学说的详细分析,都只能放到其他论文中再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