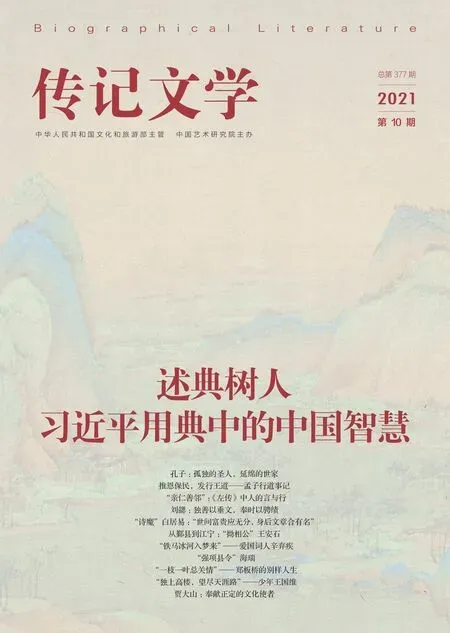从鄞县到江宁:『拗相公』王安石
徐文翔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了王安石在担任浙江鄞县三年知县期间取得“治绩大举,民称其德”的伟绩。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因政绩显著,于熙宁二年(1069)升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后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罢相。一年后被再次起用,旋即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纵观王安石的整个从政经历,我们或许可以从庆历年间的鄞县之任到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再到退居江宁的晚年岁月,来体味其作为“拗相公”的人生悲喜与理想脉络。

王安石画像
鄞县知县岁月之后的王安石,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他面对政治的挫折和人事倾轧不禁心灰意懒,在给友人的信中发出“触处多感,但日有东归之思尔”的感慨。熙宁九年(1076)六月,年仅33岁的长子王雱因病身故。王雱自幼聪颖过人,进士及第后与父俱侍经筵,深得王安石的喜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对于年近耳顺的王安石来说,不啻精神上的重重一击。其伤痛之深,从“空房萧瑟施繐帷,青灯半夜哭声稀”(《一日归行》)“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题雱祠堂》)等哭子诗句中便可见一斑。此前,王安石已经数次请辞宰相职务,只是因神宗的诚挚挽留而未果。王雱去世后,王安石更坚定了辞相的决心。十月,朝廷终于降诏,罢王安石宰相之职,迁为镇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但是,他随后就把这些职衔辞去,只领一份相应的俸禄以供养家人,从此彻底退出官场。
王安石出生于江西临川,但自幼随父亲王益迁居各处,并未在临川生活多久。相反,他却对父亲最后任职之地、也是埋骨之地的江宁特别钟情。早在熙宁元年(1068),他游览汴京附近的西太一宫时,就触景生情,写下:“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其一)在经历30多年的宦海沉浮后,头发花白的王安石终于实现了隐居江南的愿望,其人生也揭开了晚年的新篇章。
政坛上的“拗相公”
“拗相公”之名,既源于王安石性情的执拗固执和不近人情,也与他执政时期的锐意进取、不拘俗规有关。王安石政治生涯最高光、也是最为后人所熟知的,自然是那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但如果把目光放远到他整个从政经历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庆历年间的鄞县之任,来窥见其施政理想的原则和脉络。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放弃京城优裕的馆职,调任到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任知县。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他不求地位的优厚,而只想为天下百姓做一点实际的事情,这原是他的志向所在”。王安石在鄞县只任职三年多,但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却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生,他此时的施政理想,不仅显现出日后锐意改革的政治家风范,也对他后来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安石到鄞县上任伊始,便敏锐地发现了当时对百姓极为不利的弊政。鄞县沿海多岛屿,许多百姓便在岛屿上违反禁令营造私盐。官府为了禁止私盐,便通过悬赏的方式鼓励民间互相举报,但是赏金的支出却摊派到老百姓头上。王安石认为: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然势却不可止;而且重诱百姓相互捕告,又造成陷刑者多,导致民风败坏。所以,他认为这项弊政绝不可行,便上书反对禁私盐,认为此举虽然对政府有利,但对百姓却极为不利;官吏本是人民所养,穷民而富官,这是最下等的治术。在一首名为《收盐》的诗里,王安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诗中不难看到初涉政坛的王安石,心中即有为民的情怀。
在任期间,王安石还做了几件利民的事情:其一,动员百姓兴修水利。在《上两浙转运使杜学士开河书》中,他分析了鄞县的地理水文,认为本地旱灾频发“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他亲自进行实地调查,指导百姓浚治河渠,一月之内,足迹所至“凡东西十有四乡”。他怀着“肉食自嗟何所报,古今忧国愿年丰”的信念,夜以继日,不惧辛劳;其二,实行借贷。在春天青黄不接、百姓生活艰难时,他主持把官仓里的储备粮借贷给贫民,并规定秋收之后加息偿还。如此让百姓能够渡过难关,而官粮也得以不断换新,实为一举两得;其三,重视兴学。庆历年间,地方州县官学大多废毁,有的甚至改成了庙宇,鄞县也不例外。王安石到任第二年就恢复孔庙为县学,聘请有名望的大儒杜醇主持教育本县子弟。如此一来,鄞县学风大盛,士林面貌也焕然一新。此外,诸如整顿保甲、规范胥吏等,也是王安石在任期间施政的主要着力点。
皇佑二年(1050),王安石秩满离任。他在诗中抒发了对鄞县的不舍之情:“忆昨初为海上行,日斜来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铁幢浦》)老百姓也对一心为民的王安石感激不已,为其建立了生祠,四时拜祭。据学者陈九川考证,直到明代,鄞县的王安石祠仍香火不断,拜谒者众多。
在王安石后来的政治生涯中,特别是“熙宁变法”中的很多措施,其实都可以在他任鄞县知县的施政中看到影子。日本汉学家三浦国雄认为:“鄞县的这些政策,王安石日后在他成为宰相时也希望在全国推广,换句话说,王安石的新法在他的鄞县施政中就已有了萌芽。”同时,王安石的施政理想和风格,从中也能得以管窥:首先是一心为民,不计其他。王安石从不以个人得失考虑问题,只要是对百姓有利的事,哪怕得罪上级、同僚,也坚决去做;其次是大胆革新,不拘俗规。诸如私盐、水利、胥吏、学校等问题,鄞县的前任官员并非一无察觉,只是或为政策所束,或为利益所碍,只愿维持“无事便好”的状态而不作为。王安石甫入政坛,便打破了许多官场的常规套路或曰“潜规则”,这一方面是他锐意进取、不近人情的性格使然,同时也无形中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从而为自己树下政敌,遭到一些恶意中伤。这种“毁誉相生”的情形,可以说贯穿了王安石执政生涯的始终,至“熙宁变法”而达到顶峰。
在诸多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里,王安石都被称作“拗相公”,这确实是有原因的:一方面,王安石一贯“不近人情”,对个人卫生不讲究,不但厌恶洗澡,也懒于更衣,在一众衣冠楚楚的同僚中显得尤为特异;另一方面,王安石的性情中确实也有“拗”的一面。比如,宋代士人的风流韵事特多,而王安石却偏偏不喜女色。有一次,好友刘攽宴请王安石,按照惯例招来了不少妓女侍宴,他因此拒不入席,直到主人遣散众妓才平息怒火。另外,王安石遇事喜发异论,每每与俗见相左。在《读孟尝君传》这篇短文中,他就驳斥了“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因为刚直固执、言辞激烈,王安石便给人留下了“好辩”的印象,以至于晚年隐居江宁时,还因为在谢安(东晋名士,字安石)故居旁边营造宅第而被人戏谑道“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
然而,“拗相公”的形象内涵中毕竟蕴含着深厚的贬义,尤其是在北宋《邵氏见闻录》等笔记中,王安石屡屡被塑造为“奸相”,甚至其衣着邋遢、食不兼味等生活习性,也被别有用心地解读为故作姿态。比如《辩奸论》中的这段话: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贱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
此文据说为苏洵所撰,在当时极为有名,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见便知说的是王安石。神宗年间,新党、旧党因政见不同、利益相悖而势如水火,作为新党的主要人物,王安石又有着如此“不近人情”的性格,势力庞大的旧党成员提起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一些有识之士如司马光、苏轼等,还能坚守“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反对王安石之政治主张的同时,肯定其道德、文章;等而下之者,却往往不择手段攻讦其人品,以至于无中生有地敷演出许多“丑闻”。
王安石在生活上确实漫不经心,比如吃饭,哪个菜离他最近,他就专吃哪个。这其实只是一种“痴拙”的表现而已,但凡心志专纯之士,常在生活中闹出这样的笑话,比如陈望道蘸食墨水、陈景润穿错袜子。然而大拙若巧,王安石却因此被某些人解读为“奸诈”。南宋大儒朱熹在政见上虽然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但对其性格却有着“同情之了解”:“荆公气习,自是一个要遗形骸、离世俗底模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对于王安石所遭受的刻意丑化,近代梁启超更是不无激愤地说道:“吾于诋新法者,仅怜其无识耳,犹自可恕;至诋及公之人格者,吾每一读未尝不发为上指也!”如果我们不被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看待王安石的材料所遮蔽,而是全面了解其人其事的话,便会发现,“拗相公”不但一心为民、不求荣利,还有着可亲、可敬而“近人情”的另一面。
比如,世俗的眼光认为王安石矜持、自负,其实这种印象不过是来源于王安石身上那种厌恶凡俗的“洁癖”而已。三浦国雄认为:
王安石之孤独就源自与上述汲汲于名利的同辈青年的格格不入。他总是心怀莫可名状的疏离感,自觉不见容于时代、社会以及周围的人们,就像一只因离群而寂寞的野兽。这不是矜持或自负,而是一种深刻的寂寥。王安石非常渴望有能理解和接纳自己的友人,与他们切磋琢磨。
事实上,当王安石遇到这种能“理解和接纳自己的友人”时,他所表现出的热烈和真诚,能令千百年后的今人也为之感动。王安石34岁时,因偶然的机遇结识了比自己小11岁的书生王令(字逢原)。王令虽然身材瘦削、衣衫破旧,但气势昂然,双目有神,其才学、品德令王安石为之钦佩,将其比之为当世颜回。在一封信里,他称赞王令:“文学智识与性行诚是豪杰之士……某此深察其所为,大抵只是守节安贫耳。”王令传世的诗文不多,但有一首《暑旱苦热》却堪称名作,从中也能看出这位布衣之士的情怀与志向:“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遇到王令这位知己,王安石感到十分欣慰,他不但逢人便称赞王令,更主动包揽了王令的婚事;在王令死后,又主持了其女儿的出嫁。王令的去世,让王安石悲伤不已,他一连写下了《王逢原墓志铭》《王逢原挽辞》《哭逢原》《思王逢原》等悼亡诗文。在给友人崔伯易的信中,王安石悲伤地写道:“人之爱逢原者多矣,亦岂如吾两人者知之之尽乎?可痛,可痛!”
在王安石一生中,可以称得上知己的,除了王令,还有孙侔、王回等人,或许晚年的苏轼也算一个。他们和王安石的共同点,就是都不慕荣利、不同流俗、学识出众、品德高尚。王安石与友人的交往,印证了那句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清人何瓦琴的联句)由此反观其“拗相公”的形象,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贤者多谤。正如史家所说:“王安石的‘恶’绝大部分是旧法党和道学派在党争、学争取胜后,操作舆论塑造出的。在建构的过程中,司马光成为毫无瑕疵的高洁的宰相,他的政敌王安石则是所有罪恶的始作俑者。”
梦想平生在一丘
江宁可以说是王安石的第二故乡。当年少的王安石陪伴父亲在此居住时,六朝古都的人文积淀、秀丽风景,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终老于此的种子。因此,当熙宁九年(1076)十月终于辞去宰相职务的时候,他由衷地感到欣喜,在诗中抒发了这样的情怀:“城中灯火照青春,远引吾方避纠纷。游衍水边追野马,啸歌林下应山君。愁寻径草无求仲,喜对檐花有广文。邂逅一樽聊酩酊,声名身后岂须闻。”(《次韵酬宋妃六首》其一)在这一刻,曾经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官场上的人事纠纷,似乎都如浮云一般远去了;爱子王雱不幸早亡的悲伤,也似乎被隐居林下的恬静暂时冲淡。
或许早在熙宁元年(1068)写下“白头想见江南”时,王安石就渴望能在江宁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园子,有朝一日能悠游林下。因此,罢相伊始,他就将此事提上了日程。在几首诗中,王安石都用到了“一丘”这个词,比如《送张拱微出都》:“子今涉冬江,船必泊蔡州。寄声冶城人,为我问一丘。”因此,当半山园营建完成后,他感到空前的满足。之所以名“半山”,除了因为此宅离城七里、离蒋山也刚好七里外,更蕴含着“取乎其中”的人生境界。此时的王安石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建造一所精致的宅院,但半山园却异常粗陋,如李壁所描述的:“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续建康志》)对物质条件一贯随意的王安石,身处这粗陋的半山园里,精神世界却非常丰富。离此不远,往南有定林寺,是王安石常去读书、谈禅的地方;往北则是谢安的故宅旧址,他常去游憩;再远一些,还有孙权墓、宝公塔等古迹。古代的士人,常徘徊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中,尤其是政治上遇到挫折时,山水的慰藉就显得十分宝贵。圣贤如孔子,在周游列国狼狈归来后,尚发出“吾与点也”的感喟;此时、此境的王安石,能有半山园这片休憩之地,又复何求呢?当长女写信诉说生活上的苦恼时,王安石甚至这样来安慰她:“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寄吴氏女子》)

南京半山园王安石故居
江宁的隐居生活中,王安石常做的事就是随意闲游,没有目的地,更没有排场,完全随兴之所至。王鞏《清虚杂著》记载道:
王荆公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予尝谒之,见其乘驴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
没有阮籍穷途之哭的矫情,也没有刘伶衣不蔽体的颓废,有的只是快意自足的逍遥和舒缓。这段时间,也是王安石山水诗创作的高峰期,试观其此时的诗词,不少都与一个“闲”字有关,如:“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又如:“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云间。临溪放杖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定林所居》)闲游的王安石常一副村夫子的打扮,即便和人相遇,别人也绝难想象这位老叟就是当年名动天下的大人物。梁启超在其《王荆公》中形容王安石“罢政后日徜徉此间,借山水之胜以自娱,翛然如一野人。读其诗词,几不复知为曾造作掀天动地大事业开拓千古者也”。
除了随意闲游,王安石最常去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定林寺。定林寺位于宝公塔西北,寺内松柏参天,寺外流水潺潺。王安石十分喜爱这里的幽静,专门在此安置了一间僧房,作为读书之处。他甚至还邀请友人一同来游,其《和耿天骘同游定林》诗曰:“道人深闭门,二客来不速。摄衣负朝暄,一笑皆捧腹。逍遥烟中策,放浪尘外躅。晤言或世闻,谁谓非绝俗。”王安石一生不随流俗,但绝大多数时候又都身处流俗之中,至此方外之地,即便偶与友人言及“世闻”,其心境也是“绝俗”的。王安石一向仰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所感慨的“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想必他也曾多有体会。如今卸下了外在的包袱,心便不再为形所役使,正所谓“放浪尘外躅”。
由定林寺再往北行,地势渐高,便来到了著名的钟山,这是王安石另一处钟爱之地。钟山位于江宁城的东北方,故又称北山,南朝孔稚珪的讽刺名篇《北山移文》,说的就是这里。与文中的假隐士周颙不同,王安石游玩钟山,是怀着彻底归隐的心态,因此其和钟山有关的诗词里,也体现出物我两忘的意境。试看这首《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诗的末句本引王籍的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而反其意用之,令人感到“此时无声胜有声”。而另一首七律《登宝公塔》中的结句“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更是大有苏轼《前赤壁赋》的意味,两位颇具慧心的诗人尽管政见有所不同,但对宇宙的体认却在此刻达到了空前的契合。
钟山之盟空许约
既然说到了苏轼,那就不得不说他与王安石这两位旷世奇才的晚年相契了。按政见划分,苏轼自然是属于旧党的,但与那些顽固的守旧派不同,苏轼在变革现实政治的出发点上,与王安石实则是一致的。只不过他不同意王安石新政中的激进之处,认为应先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再徐图变革。另外,同为胸怀坦荡的君子,苏轼对王安石的批评也只局限在政治上,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他向来是钦佩的。这种态度令他在旧党重掌权势后仍然处境尴尬,但也为二人的晚年相契伏下了机缘。

王安石《过从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丰七年(1084)初夏,苏轼授汝州团练副使,经过江宁时主动拜访王安石。王安石热情接待了他,与之交游月余,唱和甚多。这段短暂的相处,既成就了两位君子间的一段佳话,也为北宋诗歌添上了绚丽的一笔。
此时的苏轼,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后,对政治也产生了深深的疲惫和疏离感,正是这种心态,让他抛开了以往政见的不同,与王安石只游山玩水,谈诗说佛,互相寻求精神的慰藉。苏轼游蒋山后,有诗曰:“竹杪飞华屋,松根泫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略杓横秋水,浮图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同王胜之游蒋山》)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句,王安石颇为赞赏,并欣然和诗一首。离开江宁后,苏轼还念念不忘这段与王安石相处的愉快时光,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
这次江宁相会,二人还有一个约定。王安石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说苏轼远离宦海风波,希望他“买田金陵”,二人常相过从,共度残年。《宋人轶事汇编》中记载:
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会坡近作,因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东坡卜居秦淮。故坡公和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径宅,从公十年已觉迟。”
“从公十年已觉迟”,这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在这一刻,往昔的政见相左、意气相争,早已化作了浓厚的友情。然而这一约定最终也没能实现,苏轼身不由己,未能践约,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遗憾地说道:“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读罢来信,王安石陷入了深深的惆怅中,复信曰:“知尚盘桓江北,俯仰逾月,岂胜感怅!”岂料造化弄人,苏轼就连“扁舟往来”的小小愿望也没能实现,在常州居住不久,就被调往登州任职。而两年之后,王安石因病去世,二人再也没能相见。
历史没有假设,但面对这样的缺憾,我们却又忍不住去假设:假如苏轼未受羁绊而履行了“老于钟山之下”的约定,两位大文学家的交际又会为文学的天空增添怎样的光亮?
世间唯有妙莲花
谈及王安石最后的隐居时光,还有一点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他的学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王安石对佛法几乎达到了崇信的程度,这在历史上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里是少有的。他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元丰七年(1084),也就是苏轼来访之前不久,已是64岁高龄的王安石大病一场,虽然侥幸康复,但他还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他做了一个决定:将自己钟爱的半山园进献国家,并将之改为寺庙。舍宅为寺的做法,在北宋的佛教信徒里并不罕见,但王安石此举还是引发了世人的热议。一种说法是为了给神宗祈寿,因为神宗对王安石有着非比寻常的知遇之恩;还有一种说法则是为了超度已故的爱子王雱。但不管怎样,都说明王安石对佛教的信奉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最终,半山园如王安石之愿被改为了佛寺,并由神宗赐名“报宁禅寺”,高僧真净克文禅师为首任住持。
实际上,王安石在归隐江宁之前,便与佛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儒生不同,王安石年轻时读书涉猎极广,除了儒家经典,他对佛典也颇感兴趣。任职扬州期间,他与高僧慧礼十分亲近,并写下了《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在文中,他从“材”与“道”的关系立论,认为佛教兴盛的原因是“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难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儒、佛之间始终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那便是“经世济民”与“四大皆空”的矛盾。王安石作为一名儒家学者,能对佛教毫无成见,大方地承认其合理处,体现了他思想的包容,也为晚年专力学佛埋下了种子。
在此后的岁月里,王安石辗转多处任职,但不管到了哪里,他都与当地的高僧或佛教信徒相过从,其佛学素养也逐渐加深。比如在应瑞新禅师之托所作的《涟水军淳华院经藏记》一文中,他称赞佛法能令人“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而“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又与儒家思想进行了关联。对王安石学佛产生影响的,还有大觉怀琏禅师、蒋山赞元禅师、道臻禅师以及老友孙觉等。
尽管如此,长期以来王安石对佛法的关注更多地还是出于兴趣。胸怀“经世济民”之志的王安石,尽管给予佛教以较高的评价,其立场归根结底还是政治家的。微妙的变化出现在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慈母的离世引发了王安石对于终极关怀的哲学思考,与佛教相比,儒家在心、生死等领域的理论话语是有所缺失的。因此,王安石开始跳出“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维范式,展现出对“心”与“生死”的关怀。宋代僧人惠洪所撰的《禅林僧宝传》中记载了一段王安石向蒋山赞元禅师请教的公案:
元曰:“公受气刚大,世缘深。以刚大气,遭深世缘,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则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经世之志,何时能一念万年哉!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名利如脱发,甘澹泊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在王安石所结交的众多高僧中,蒋山赞元禅师大约是对其影响最大的。熙宁九年(1076)隐居江宁后,王安石拜访这位禅师更加便利,但有意思的是,见面后二人却并不怎么说话,多数时候只是相对默坐而已。因为学佛悟道的关系,王安石笔下的诗词也多了几分禅意,兹举几例:“云从无心来,还向无心去。无心无处寻,莫觅无心处。”(《即事二首》其一)“寒时暖处坐,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佛即是众生。”(《题半山寺壁二首》其一)“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再次前韵》)
以王安石之聪慧与勤奋,他一旦开始信奉佛法,必然要精研内典,穷其究竟。江宁隐居期间,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注释佛典,我们知道的就有《首楞严经注》《维摩经注》《金刚经注》《华严经注》四种。这其中最体现功力、也是最受佛门推崇的,当属《首楞严经注》。惠洪在《林间录》中称赞这一注本道:“其文简而肆,略诸师之详,而详诸师之略,非识妙者莫能窥也。”
即便王安石投入了大量精力来学佛,他也始终没能达到那种“四大皆空”的理想境界。事实上,对山水丽景的眷恋本身就已经堕入了“色”“空”的矛盾中,更何况王安石的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一丝微弱的火苗。元丰八年(1085),神宗皇帝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由极端厌恶新法的宣仁太后摄政。在“祖宗之法”的大义名分下,推行了15年的新法被一朝根绝。得此消息后不久,王安石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衣着古朴的伟丈夫出现在面前,自称是“桀”,与王安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双方唇枪舌剑,王安石却始终无法将其驳倒。惊醒后,王安石自嘲似的赋诗一首:“杖藜随水转东冈,兴罢还来赴一床。尧桀是非时入梦,固知馀习未全忘。”(《杖藜》)心理学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反映,所谓“馀习未忘”,说明王安石对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还有所期待。也许在那一刻,鄞县施政、熙宁变法等过往的一幕幕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也正在那一刻,王安石才完全认清了自己。
一年之后,66岁的王安石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留下了一首名为《新花》的绝笔诗,最后一句是:“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从此,世间再无王安石。
注释:
[1]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2][4][5][日]三浦国雄著,李若愚、张博译:《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第44页,第161页。
[3][清]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62页。
[6][宋]王素、王鞏撰,张其凡、张睿点校:《王文正公遗事 清虚杂著三编》,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5页。
[7]周勋初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3页。
[8][宋]惠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