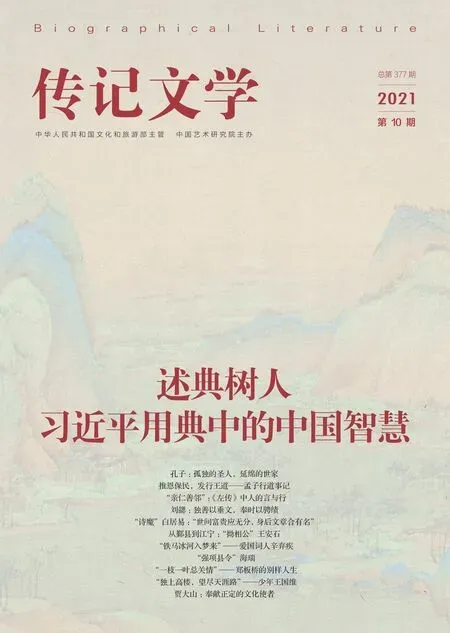作家自述的“编”、“注”及“闲笔”
——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为中心
操乐鹏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目下学界对作家自述/自传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几类路径与趋向:或立足于自述之本体,对其语言、风格以至结构、形态的诸多面向,均作微观剖解;或以“史料学”视野切入,尝试辨析自述/自传之名实、考镜源流,以确立作家自述在现代文学史料体系或学科中的位置及归属;或聚焦于自述的生产语境,以略带系谱学的姿态考察有关作家自述的问世或自述热潮中的出版操纵与学术风向。此外,以自述为媒通向作家、作品研究,自是应有之义。
是类研究而外,假如不纠缠于空对空的范畴论争(如日记是否可算作自传等),而更注目于实打实的作家自述之文本生成;假如不仅仅关注自述的出版发行等“外部”因素,也倾心于作家自述的编、注、评等技术要素:那么,尚存一类作家自述仍有重新发覆勘察之必要。这其中,黄裳辑存自家日记,王安忆整理评说茹志鹃日记,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尤为独特。三者对自述文本的编纂、注疏乃至其中的“闲笔”,相较于自述部分而言,即便不能说是喧宾夺主,至少也是秋色二分。三种自述无不呈现出作家的自述文本与编注者的阐释介入相交织的样态构型,作家自述之编纂修辞学的况味呼之欲出。本文即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在自述文本上的编注实践与诗学阐释为中心,揭橥此三家自述所昭显出的修辞义蕴与文体型态,兼而探析其与时下研究方法、学术体制之分殊离合。
修辞与体例:作家自述的“编”与“注”
若依循史学研究范式“叙事”转向的逻辑理路,则可以说,本文的聚焦点也或多或少由自述本身移向编注者对“自述”的处理与思考。以作家自述的编纂来看,既有着“汇群言而骈列之,异同自出”的客观面貌,编注者的主体取舍与主观取向往往也藏蕴其中。黄裳抄录自家日记,“全部照录,只于各别文字少加修饰,事实并无变动”。而黄裳多次指摘的,正是金圣叹式注《水浒传》“其所删易,辄曰,‘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老舍自述》由编者“将老舍的自传材料做了适当的调度,合并、删节、组合”,其准则是“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这也与陈垣所说的“引书法”与“组织法”可堪比照。《老舍自述》的剪裁、配置,颇具匠心。如第九章“茫茫末世人”,仅有两个字与一个标点:“再见!”此为老舍最后对小孙女说的两个字。
《茹志鹃日记》收录茹志鹃日记十段,外加王安忆的一则序和七篇解读文章。序言《走向盛年》中的部分内容与“校记”相类,王安忆缕述抄录整理日记的经过,且交代日记的部分段落有删节,“因这几段日记以采访为主,所删部分多是访谈对象的述说”,此外便是数字、错别字和笔误的更动。在1954年日记的个别段落,茹志鹃展现了较多的个人心绪,尤其透露出与王啸平间的感情低潮。在序言中,王安忆坦言:“这也是我最后才决定收入本书的一段日记。”身为儿女,“难免会将父母间的龃龉看得过分严重”,然而茹志鹃夫妇“方从传奇式的战争生活走出,进入平常日子,养儿育女,所有安居的琐细全都扑面而来”,故王安忆又说:“倘若持客观态度,也就觉得很自然。”王安忆看待作家父母遗存史料的通情、通达,自然与个别作家亲属的作为/伪,判然不同。
抄录日记材料时,王安忆注意到不同时期纸张、字迹的各异。如1947年日记只是一些残页,“大六十四开的尺寸,纸张黄,而且粗糙,没有行线,但居然不洇水”。王安忆敏感地将笔迹与心迹相勾连,努力获取日记背后的个体思绪与情感。1947年的日记,“字是用极细的钢笔尖写下的,字很小,却相当清晰,端正,而且认真”,每有错字,便会划掉重来。而到了1958年的日记,“日记的笔迹相当潦草,与母亲向来的习惯不符,是不是焦虑所致?”在《茹志鹃日记》中,自述的主体部分为茹氏日记十段,王安忆同时增补进相关史料。1949年进上海的日记,只留存了三四日的断片,王安忆在《进上海记》中抄录了茹志鹃的一份草稿,补述相关境况。在梅陇日记和南汇日记后的《谷雨前后,点瓜种豆》中,王安忆补进茹志鹃一直保存着的1960年安诺写给母亲的明信片。如此一来,家事与国史遂交互缠绕,安诺的儿童视角既透露出时代气息(如“群英会”“献礼”“先锋小队”等专有名词),却也遮蔽了残酷的饥馑与斗争。两个小女孩的上海与茹志鹃的乡下,也构成了无形的对照。
黄裳日记与茹志鹃日记,毕竟与所记时代构成共时性的真实联系(自然,前提是后世整理刊布者没有对日记进行“溢美”或“溢恶”的“处置”);作家自述,往往带有极大的虚构性与后设性。“尤其老人,总易于受一种潜在欲望的支配:在此时的认识、心境下重新度过彼时的生活”,自述便成为作家在中晚年“对自己青壮年往事的重新阐释甚至是塑造”。因此,作家自述/自传的“非虚构性”是大可怀疑的。比如,《老舍自述》“父亲”一节,其中一段自述选自《神拳·后记》,而这篇后记写于1960年。注者不忘在此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努力更新自己的老舍,处处讲“新”的评价与个人家族经验糅合,打上了20世纪60年代的印迹。
这里编注者借以点出自述的后设重塑性质的形式正是注释。注疏本《老舍自述》的相关书评与研究无不注意到它对传统方法的使用,如舒济所说:注释的“词汇名目繁多,涉及大量历史、地理、习俗和人名,有些注释的资料是很难搜集到的”。从内容来说,不难看出注疏所关涉的内容何其丰富,且在时间上跨越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重语境。各评家的态度,或称扬其注疏内容之宏阔,或欣然于传统方法之现代运用,但却对“注疏”究竟何以熔接“作家自述”语焉不详。
自渊源论之,《老舍自述》的“注疏”与传统的“经注”“史注”“说部注”既相像,又非完全对等,笼统地称其为“传统方法”似有不妥。如徐德明自陈“虽名‘注疏’,但切不可拿经学标准衡量我们注释、疏证现代作家”,其所心仪的,“便如唐德刚注老师胡适,张爱玲注译《海上花》”。换言之,现代文学、学术的注释与疏解,方为注疏本《老舍自述》的渊薮。自形式而论,《老舍自述》采取的是现代学术文体中常见的尾注方式,既非《洛阳伽蓝记》式的“子注”,也不是明清说部评点本的“夹批”或“眉批”。应当说,其实质仍不脱现代学术规范的牵引与塑形。自效应来看,在传统“注疏”中,如刘孝标之注《世说》,陈垣认为“增加材料,可独立成书,与《世说》文本价值相等,与《三国志》裴注之情形同”,而老舍的自述与徐氏的注疏无法如是简单地拆散开来。“注疏”将老舍的自述连置于编注者的文化批评逻辑与文学阐释脉络中,自述的言说系统一方面保持着意义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同编注者的话语体系构成弹性结构。用巴赫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表述与另一种表述之间的积极关系。质言之,徐德明将注经注史的“注疏”转接入现代文心与学术流脉,以“注疏”重构注释与正文的关系,从而引动了作家自述/自传的文体型变,且极大唤醒了“注疏”的修辞潜能。“注释”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附骥,它引发了编注者的阐说与作家的自述之间暗辩、干扰、佐证、修葺等多向的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裳略带“子注”况味的“案语”,以及王安忆对茹氏日记的解读评说,虽无“注释”之形,其体式与效应,正与注疏本《老舍自述》同。黄裳为《凤城一月记》作“小引”及“后记”,交代日记的缘起、时间及相关线索;于日记中插入数条“案语”,随时提点所关涉的人事。在“其应加说明处,别加案语,以便观览”,遂“将文献的滋味与纹理带入自己的叙述中去”,同样显示出“佩涅罗珀”式的修辞与体例。
注疏与阐释:自述中的作家心史与编注者的诗学读解
茹志鹃日记生动鲜活地镌刻下一代知识/革命女性的生命史与精神史。在辑录的同时,王安忆也试图为之作出注解,并将日记与家事等相关人事相佐证。在解说1947年日记的《成长》一篇中,王安忆体认出茹志鹃身上携带着身世飘零、多愁善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分,并且具备天性严格、生来不容忍低级趣味的禀性。可也正是因此,“我妈妈的这种对感情格调的高度要求,在革命中得到了满足”。1950年1月5日,黄裳离津去京。当日的日记并没有细写初抵新都时的感受,黄裳在“案语”中不得不承认“五十多年后想再追忆当日的心情,是不可能的”,毫未拔高当年的思想意识。与之相类,编注者也在注释中论说老舍的思想轨迹与进路。这些注解常常溢出其所属章节的时限范围,从而带有贯通的视域。如“英国”一节的注释,论及老舍平等观的形成,进而述及老舍50年代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动力。“新加坡”一节在论说老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同时,也直指其大男人的气息尚存。
王安忆敏锐捕捉到茹志鹃日记话语方式的转变。土改日记中,茹氏拿简单的阶级观念观看着沧桑的中国腹地,凭革命信念不断应付着狡黠的世事人情……可是,“转党问题”就让她心焦急迫,一谈到私人感情,茹志鹃文字与情感的“学生腔”也暴露无遗。在层层分解中,茹志鹃的心史展露无遗。对于1958年的日记,尽管茹志鹃所记不可谓不忠实,王安忆仍毫不讳言地说:“但因整体性的真相被掩饰和歪曲,细节便也经不起推敲了。”且就此剖析了时代氛围下知识人的天真。在王安忆看来,茹志鹃这类共和国的文学写作者,在气质上总是被生活中的诗意所吸引,“甚至会有意无意地规避阴暗面,攫取光明的因素”。茹志鹃此时段的日记,也令王安忆联想到了周作人与日本新村。大约正可看作“那中国式乌托邦梦寐的破碎细节”。
占据整本《老舍自述》四分之一篇幅的注疏部分,在史料采掘与使用上确乎详尽、可靠。于是,这也引得有论者认为该书呼应着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学术实践。表面看来,注疏本《老舍自述》所携带的文献视野与史料方法,似乎与目下学界的“史料转向”位于同一延长线上。然而细究其实,二者存有路径上的分野。在唯“史料”是瞻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热潮下,相当一批研究者埋首于史料的挖掘、整理,其在史料建设上的贡献自不待言,其流弊也无须讳言:或以“学术”的名义,将正当的版权问题、当事人的意愿与心声等因素置之不顾;或缺乏问题意识,仅仅追求史料上的竭泽而渔;或抢占先机,自矜于独得之“秘”,流露出微妙的窥探欲与占有欲……《老舍自述》的注疏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警惕。且看第四章中有关赵清阁的注释:
我们的文化历来不缺乏打探私人生活的兴趣与勇气,哪些是真实过程,哪些是推论加想象,哪些是八卦,都是吸引人的事情。这本书的读者也许会关心赵清阁为何终身未曾有过婚姻,编者万分抱歉,奈因这是“自传”,老舍不写,我们就提供不了任何发挥想象的材料。有研究老舍的圈内传闻,赵清阁晚年烧了一些可能有文献价值的纸质品,诚为可惜。赵清阁自有她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
注疏者以不符“自传”体例为由,解释缘何没有较多谈及赵清阁。事实上,在不少注释里,注疏者都曾述及老舍与他人的交游往来,此处独独对赵清阁不语,更是一种学术姿态的表达:赵清阁自有她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同样,王安忆在追索茹志鹃日记的历史背景与相关人事时,亦昭显着其谨严与温情并存的诸面向。为了排查某段日记的具体时间,王安忆向上海作协资料室的冯沛龄求助。冯确认该段日记所记时间为1964年10月至1965年2月,又从日记中的蛛丝马迹推测出此时茹志鹃应当是在精业机械厂。冯沛龄随后找到了日记中提及的两位工人和干部的下落。为了理清“四清运动”的相关史实,王安忆其实下了很大的力气,如查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等文件。而当历史当事人近在咫尺时,王安忆却抑止住了历史考据的欲望,“时过境迁,生活已经变成另一个样子,很多事情未必是愿意记起的”,“其中一名是当时的运动对象,往事对他一定不会是愉快的,我决定不去打扰他”。不难见出,在史述的整理与考辨上,王安忆依旧抱持着其“鸽子视点”下对众生的慈悲与温情。
老舍、茹志鹃均为小说家,编注者亦同时阐述自述与创作之关联,以见出“天才的横剖面”。可也正是这一点,才显示出与当下某些小说批评模式更大的分殊。老舍提及初写小说时的境况:“我初写小说,只为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注疏者于注中有言:这篇老舍最早的作品《小玲儿》“小说背景即是老舍担任过劝学员,并对其整顿的京城北郊”。在“父亲”这节中,注疏者有注曰:“父亲故世前后的年头,正是老舍《茶馆》《断魂枪》《神拳》等作品中人事与生活的语境。这些人事的叙述过程中,幽幽飘荡着老舍父亲的一丝气息。”在“英国”一节中,“康拉德”这条注释在介绍完康拉德本人后,述及老舍对康拉德的推崇,且有“《骆驼祥子》烈日暴雨下拉车,有康拉德海上风暴的修辞效果”的论说。应当说,注疏本中的此类注解已然涉及作家生平经历与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注疏者并未完全将老舍的生平与其小说内容做一一相应的映射式解读,更不汲汲于找寻小说的材料来源。
王安忆亦如此。她以茹式日记为核心,不断牵引出茹志鹃的创作历程与人生轨迹。在解读1952年马鞍山日记的《翻身的日子》一文中,王安忆又补充进茹志鹃笔记本上的一个“详细的构思”,并将这个构思与马鞍山日记的记叙、与当时已发表的话剧《不带枪的战士》及未发表的小说草稿《矿山上的回声》相对照,以分析茹志鹃对材料的“贪婪”、“饥渴”,以及所酝酿的种种设想。茹志鹃在1963年的南汇日记中曾提到《风车》的提纲。王安忆将《风车》与改易后最终发表的《回头卒》相比照,勘探茹志鹃的创作运思。在梅陇日记与南汇日记中,王安忆自然很容易地辨识出《阿舒》《第二步》等小说中的形象与日记所载人物之渊源关系。对于茹志鹃苦心经营的“海媛”这一形象,王安忆也看出海媛“也有些像《百合花》里的新媳妇,还有《三走严庄》的收黎子”。当然,王安忆并未忽视集体创作这一“十七年”文学生产方式的典型症候,称《不带枪的战士》“写得可不容易,几易其稿,每一稿都组织集体讨论,提意见建议,群策群力,广采博纳,终于上演”。
综合来看,对茹志鹃、老舍自述性文本的注解,体现着王安忆、徐德明对小说家自述材料与小说创作之关联“度”的精到把握。二人从未将文学创作的审美活动等同于“索隐”,不同程度地与“材源考”式的小说批评拉开距离。正因未坐“实”自述材料与小说文本的一一对应,才给了小说家的审美创作以充裕的空间,方带来阐释上实实在在的妥帖。如钱锺书所言:“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旨归。”王安忆的解读,自有一股小说家的慧心充盈其中。徐德明对张爱玲译注《海上花》心有所仪,看中的正是张氏与韩邦庆的互为生发与遥相冥契。因此,表面看来,《茹志鹃日记》《老舍自述》在编纂上是“史”的风范;骨子里,编注者的解读分明是“诗”的。无论文学家的自述、传记,甚或其他史料文献,“如果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学领悟,那个轨道可能永远到达不了文学家的艺术境界与心灵深处”。这也是黄裳对某些研究倾向的警惕所在:“有渐近于清人考据遗风,且为末流饾饤之学,而遗其大者。”
“闲笔”非闲
茹志鹃日记常常不标年份,故而首先需要确考每段日记的时间。一方面,可以从日记中所记载的时代讯息加以判断,如冯沛龄根据日记中提及的“二十三条”断定其时间为1965年;另一方面,王安忆也借助他人帮助(其中包括历史当事人),如曾收到当年与茹志鹃同行的金宗武的来信,那么“日记的纪年便从湮灭的时间里跃出来”。此种考据功夫,类乎文献学中“本校”与“他校”的校勘之法;王安忆的数篇解读文章却并非单纯的“校记”。实际上,王安忆是把自己对茹志鹃日记及相关史料进行整理、考辨、辑存的全过程全盘展现出来。不能把王安忆的解读文章仅仅看作是对茹志鹃日记的文献保障;与茹志鹃日记等史实、家事相贯串交织的,正是王安忆本人的所思所感所惑以及她横亘于现实与往昔间的心路历程。
1965年出访日本,茹志鹃向老舍借来外汇,给女儿买下了圆珠笔作为礼物。即如那时的茹志鹃未必理解当时的老舍;1983年母女爱荷华之行中,王安忆也并不全然理解自己的母亲:“可我当时并不以为然,觉得我妈妈顽固不化。”17岁的王安忆黯淡中离家远行。茹志鹃求助于欧阳文彬,在欧阳的书橱中挑出一本《勇敢》(以代替茹想买却买不到的高尔基《在人间》)送给女儿,并在扉页写下给女儿的几行字。王安忆在《成长》中照录之。“文革”时期苏联文学的出版、流布及知识分子藏书的流散,于此可见一斑。茹志鹃喜欢《勇敢》中的少女托尼亚,却也一眼看出作者没有笔力去发展这个人物,这也侧面透露着茹式的审美眼光与小说观所在。
编注者在对作家自述注解的同时,时或夹杂着自家的生平遭际或心绪精神。凡此,可以视为作家自述中的“闲笔”。经由此种“闲笔”,个人被遮蔽于大时代的背面得以呈示。可再稍举几例。在为《骆驼祥子》注解时,自然会涉及作品的版本与修改之议题,编注者也特意一提70年代末辗转找来《骆驼祥子》复印本全本的阅读经历。又如王安忆、王安诺生活在上海,少不知事,无忧无虑,“大人们总是尽力满足我们,不让我们受委屈”,并不感到时日的艰难,也不懂得饥饿是怎么回事。王安忆一贯的工笔细致地描写了茹志鹃下乡前怎样将糖果和饼干分配给姐妹俩,姐妹二人又如何以两颗糖招待母亲老战友的儿子,以及这位大哥哥急骤嚼糖的动作与听到“饼干”时的震愕与垂涎。回望过往,王安忆才真正理解妈妈茹志鹃如何扛起命运的重闸,“看孩子们在闸下游戏”。而较少提及自己父亲的王安忆,在《茹志鹃日记》中难得地提供了较多的生活细节。黄裳在日记案语中,多借当年访书阅书之直接便捷,批评如今门禁森严的各类图书馆,“非但见书难于登天,所见也只能是微缩影本,又倡‘创收’之新例,复印也计叶论钱,有如书肆”。值得一提的是,黄裳1956年的一册日记曾于1969年被查收,遭致“欣赏、研究、分析、归纳”。黄裳在重录这册滇游日记时,“有些地方也添加上一点新材料”,即保存当年“某些人”的批注。此种“闲笔”,便可为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立此存照”。
结语
无论“注释”抑或“注疏”,其实都受制于现代学术共同体中的学术体制、文体规范、技术实践、职业道德等。当学术规制日益整齐划一,走向固化乃至僵化,势必窒息学术文体的多样探索。当洪子诚先生尝试“材料与注释”这种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时,并非没有对学术刊物是否能够接受此类文体叙述样式的担忧。如王风所言:“学术文体的千门万户,是基于不同的学术思考方式,而具体化为文本的各种样貌,格式的僵化,正意味着学术多样性的消失,和学者的身入彀中。”如果将黄裳日记、茹志鹃日记、“老舍自述”(注疏本)看作“注疏”性质的学术著述或“作家自述”的文体新创,那么,其各自的“编”、“注”及“闲笔”,所呈现的技术环节与体式创变,确乎能够为时下的学术与文体提供有益的示范。正缘乎此:“一点注疏拿得出手,没惭愧!”
注释:
[1]黄裳所辑录的自家日记,未专门结集。本文主要聚焦黄裳的《凤城一月记》与《滇游日记——从昆明到大理》(均收入黄裳著:《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尽管篇幅容量不大,但黄裳在日记中“别加案语”,确是一种“新创的写法”(《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8页)。
[2]即茹志鹃:《茹志鹃日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王安忆所整理的茹氏各段日记,在结集前曾刊于《上海文学》《十月》《万象》《江南》等。
[3]据谢昭新:《运用传统方法创作与研究老舍传记》(《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院版)》2021年第1期):“徐德明著述老舍传记,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此之前已有多部老舍传记问世,可他编著的《老舍自传》一登场,即以崭新的面貌,打破了老舍自身未写过完整的自传以及学术界也未曾有过的《老舍自传》的格局。《老舍自传》于1995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更名为《老舍自述》;201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自传》未标明徐德明编著。”可以稍作补充的是,徐德明著述的老舍传记,还有其他版本或版次,如:江苏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的《我这一辈子》(2011年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世界名人传”《老舍自传》(2018年版),贵州民族出版社的《老舍自述》(2019年版)。以上各书实为徐德明编写的《老舍自述》。尽管贵州民族出版社在书末列出“出版者”的“编辑后记”,三家出版社除江苏文艺出版社外,未标明徐德明编注。由此前《老舍自述》《图本老舍传》到注疏本《老舍自述》(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在保持内在学理关联的同时又包含方法与文体上的新变。
[4]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页。
[5][22][25][48]黄裳:《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第3页,第7页,第14页。
[6]黄裳:《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8页。黄裳引述的陈寅恪所批评的学风,至今仍未断绝。
[7][14][16][19][28][31][32][33][51]老舍著,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注疏本)》,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393页,第392页,第15页,第389页,第185—186页,第58、69页,第14页,第72—73页,第389页。
[8]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9][10][12][13][24][26][29][34][35][36][42][43][46]茹志鹃:《茹志鹃日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第2页,第25页,第109页,第26页,第109—111页,第180页,第66页,第163页,第67页,第178页,第26页,第160页。
[11]当该作家亲属同样从事学术研究或位列学术圈高位时,更甚之。
[15]钱理群就此有过评说。钱氏认为,茅盾的晚年回忆过度强化了他与鲁迅的亲密关系,淡化了与周作人之往来,与历史实情不符。张大春也曾以黄春明为例,谈及作家序言后记等文本的“虚构”本质及小说家的“大说谎家”之本色。故而,对于那些依托新时期小说家的序言后记进行的年谱或作家论,似乎需要更加审慎地辨析。
[17]舒济:《序言》,老舍著,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注疏本)》,现代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18]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0]同处于此一脉络上的自觉凸显“注疏”性质的学术著译,民国时期便有:王古鲁译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潘光旦译霭理士:《性心理学》等;当下学界则有洪子诚:《材料与注释》、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等。
[21]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页。
[23][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著,张弢、王春华译:《脚注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8页。
[27]艾翔:《传记、选集和研究的集成——读〈老舍自述(注疏本)〉》,《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30]“鸽子视点”引自徐德明对王安忆小说创作世界的提炼。在《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中,徐德明拈出“鸽子视点”以示王安忆的全知型智慧叙事,且与“鹰的视点”形成对照。翟业军指出:“众生话语”是王安忆的,也是徐德明的(参见《主持人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与此相类,“鸽子视点”同样可视为对王、徐二人史料方法与姿态的概括。此等主体精神与襟怀,正是方今为史料而史料的研究中所缺乏的。后者的取向,也正与风高月黑中枭啸唬人、以攫取为能的“鹰的视点”相符。
[37]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1页。
[38]另如徐德明:《考掘知识与托辞增义》(《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4期),“材源考”之外,也更在意小说家主“拿来”之义的托辞增义。
[39]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
[40]徐德明著,舒济供图:《图本老舍传》,长春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41]黄裳在《零感》中论及这类“考证”文章与研究“真的下不于,甚至超越了乾嘉诸老,是一篇典型的‘繁琐考证’。尤为奇怪的是,文章并无明确的结论,也无论辩的对象,好像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似的,疑莫能明,过后细想,其实又并非如此”。(黄裳:《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9页)黄裳此论,对时下的学术走向,仍有纠偏之助。
[44][苏]薇拉·凯特玲斯卡雅著,关予素译:《勇敢》(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
[45]“闲笔”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习见语汇。韩少功曾用“闲笔”点评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
[47]王安忆关于父亲的文字不多。参见徐德明、易华:《“寻找”中的主体:重探王安忆〈海上繁华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49]黄裳:《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7页。如“十一月十日”日记有言:“更添了一位女服务员,穿了一套灰咔叽制服,胖得像只小猪”。这句话后,黄裳有如是插入:“(朱笔批:污蔑劳动人民服务人员)。”(黄裳:《来燕榭文存》,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8页)这种“案语”在滇游日记中仍有不少,既照录相关批注内容,也对批注的笔迹形式加以标注(如“大量的红杠子”等)。
[50]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