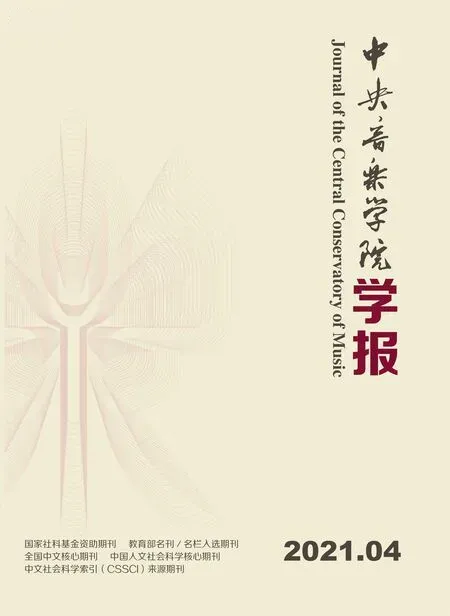书写历史
——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与范畴之中国经验
齐 琨
书写历史,是人类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的独特视角,也为民族音乐学家在面对历史研究时所运用。由于中国音乐研究的自身特点,传统音乐成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本土化后的主要研究对象。然而,我们不得不看到“传统”与“历史”实为一对近义词,它们都是表意过去、以往、传承、变迁、习惯、风俗等,它们可以具化到时间、地点、人物、行为、事件,也可以泛化到价值体系、观念系统、话语权力、交流模式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历史逐渐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史学也越来越成为民族音乐学需要涉足的学科。
然而,作为民族音乐学者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眼光关注历史?中国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踏出哪些路径?进入历史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学者所持历史观是什么?这些都是介入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话题。受篇幅所限,本文将聚焦研究范式梳理,从而厘清作为研究领域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不同以往的学术意识,这些学术意识带来了哪些研究范畴的更新,而对这些问题的梳理需要首先基于笔者对“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回答。本文写作基于阅读中国学者相关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的200多篇文献所获的体会。本文的叙述模式不定位于述评,因此不追寻面面俱到,仅期望总结核心文献,从范式的角度梳理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发展脉络,以此作为对历史民族音乐学之中国经验的归纳。
一、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
在对标题中的设问回答之前,笔者期望先聚焦什么是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研究?抑或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是民族音乐学者介入历时性研究需要首先自问的问题,笔者选择的回答起点为“什么不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首先,以历史资料作为文本的叙述背景,这肯定不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这样的回答是表明那些因民族志写作惯例而在绪论中呈现历史文化背景的内容不属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显然,历史不是民族音乐学用来装点门面的资料,面对历史,民族音乐学学者需要带来有深度阐释与理解的内容。
研究核心仍是延续传统音乐史学以考证与考据的方法对待历史资料,这当然也不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历史民族音乐学可以有哪些独特的历史研究视角、观点与方法?这是民族音乐学者面对历史资料时需要自问的另一个问题。历史民族音乐学不是“新瓶装旧酒”。我们要寻找那份在方法与观念上散发创新气息的“新酒”,装入“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这一在20世纪80年代首现于英文文献的“新瓶”中。
将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套用到历史的探索中,也不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特点即表现为多学科交融与跨学科结合。这一特点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能在持续的自我反思中推动学科拓展。因此,面对历史,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民族音乐学的常用研究方法与文本表述模式将遭遇的新挑战和我们可以拿出的解决办法。
在上述三个否定回答后,我们可以理解到,历史民族音乐学是不同学科(1)可以是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理论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但目前看来主要是民族音乐学学者以及有着史学学科背景的民族音乐学学者。作为一个领域,历史民族音乐学呼唤不同学科的学者加入,以此构成这一领域的跨界思考与多元交融。的学者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以往传统音乐史学研究的、融合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等多学科思维的理论认识。因此,一方面,历史民族音乐学可以成为阐释历史的一种策略,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呈现多元化,对历史资料的解读给予多视角。另一方面,民族音乐学在对历史的认识与解读过程中会产生新问题,由此可拓展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什么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笔者认为,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学术视角、一类学术方法、一个学术领域,因此,它可以被音乐史学家与民族音乐学家共同采纳、介入与运用。笔者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给出定义:将观念——音乐人物、行为——音乐表演、声音——音乐产品放置在时间的过程中解读,把这个过程作为文化给予阐释,从而发现与理解各地域音乐人的观念、各类音乐表演行为、以各种声音为表现的音乐产品所展现的历史感和历史观。简言之,历史民族音乐学是阐释音乐文化的历史深描。历史民族音乐学不仅是对共时与历时的兼顾,还是对空间(文化)和时间(历史)的兼顾。
作为领域的历史民族音乐学,它可以吸引各学科学者,在时间过程中对音乐人物、音乐表演、音乐产品解读出多元内容,从而界定自己眼中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是什么?可以给自己的学科带来哪些反思与拓展?而在民族音乐学者的面前,历史似乎可以成为一个放大镜,我们拿着它重新审视民族音乐学视为根基的研究方法——实地考察与记谱分析的历史观与历史感;文本呈现方式——音乐民族志写作的历史叙事;传统的研究模式——音乐形态分析的追源溯流;新兴的研究范畴——表演理论、声音景观、音乐制度的历史表述。简言之,民族音乐学者在历史之镜的观照下,可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丰富其研究对象。
二、传统音乐理论家与音乐史学家的贡献:“曲调考证”与“逆向考察”
笔者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关注现在与过去、历时与共时关系的观点追溯到中国音乐史学家与传统音乐理论家的创见。“史论不分家”是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自开创之初即有的模式,杨荫浏先生即为最著名的代表。
黄翔鹏先生与冯文慈先生是中国传统音乐史学与理论研究领域里的两座高山。对他们的仰望中,我看到了在20世纪80年代初,音乐史学家们以历时的眼光观照到“音乐实践中存留至今的、活的历史资料”(2)黄翔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人民音乐》,1980年,第7期,第9页。,提出“曲调考证”之研究方法(3)“曲调考证”是黄翔鹏先生在“1983年第二届‘华夏之声’活动中提出”的学术概念。引自黄翔鹏《逝者如斯夫——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问題》,《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5页。和“逆向研究”之研究范式(4)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音乐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页。,共同思考了我们当下所见所闻的音乐与古代时空中的音乐表演存在何种关联。“曲调考证”是基于“古乐藏于今乐”的思考,是音乐研究中的硬功夫。黄先生阐释今乐对于理解古乐之重要时,例举了杨荫浏先生“曾经通过研究西安鼓乐解决了南宋词人姜白石歌曲的译谱问题”(5)黄翔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人民音乐》,1980年,第7期,第9页;黄翔鹏:《杨荫浏先生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年,第3期,第4页。,可见这一研究思路的起始点,可以向前再推。冯文慈先生受丁伟志《论历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译文的启发,提出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可以做“从结果推断原因”的“逆向考察”。(6)同注④,第1页。此后也有音乐史学家论及史学中的共时研究,以及音乐史学对民族音乐学的借鉴,但从类型看,均不能超出冯先生归纳的“纵向联系研究”与“横向联系研究”这两类,以及“逆向研究”这一特殊视角,本文不复赘述。
比较两位先生的观点可见,黄翔鹏先生从史料的角度提出“曲调考证”的研究方法,冯文慈先生从史观的层面提出“逆向研究”的追源视角,二者的共识在于看到了考察今乐对于研究古乐的意义,以及共时研究对于历时研究的作用。(7)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人类学家张小军曾指出历史人类学最先被历史学家抢注,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高勒根为更好地显现新史学理论之史料多元化与更关心整体历史的特点首创提出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概念。张小军:《史学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被历史学家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8页。虽然,黄先生、冯先生并未提出“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概念,但作为史学家(8)黄先生曾言:“我没有写过史,只下了综合研究的功夫。……我做过音乐考古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系统研究、中国音乐形态学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古谱学研究和曲调考证研究。这些都是为音乐史铺路的。但是,我始终不承认我是考古学家或乐律学家。我的目的在音乐史,只是目前还没有能力写成。我是个可怜人,什么‘家’都不是!”黄翔鹏、崔宪、杨韵惠:《我的治学思想与学术目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第5页。读此段文字,不由得心生对黄先生不求名利、矢志不渝、奉献学术的崇敬!他们是最先撰文提议关注古乐与今乐的关系,并特别指出以今观古、以今探古之角度的重要性。更为不谋而合的观点是同时驾驭历时与共时研究的难点,在于需要多学科知识结构。
两位先生对于关注古乐与今乐关系的提议,在当时的音乐学界颇具影响。在民族音乐学初入中国的第一个十年中,投身于这一新兴学科的学者,已将目光投向历史学的研究领域。1990年,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一文对当时“文化史性质的研究”有具体描述,认为其目标与历史学研究基本一样,其对象为活的音乐传承,以此区别于以文献为对象的历史学,因此,相关研究路线、手段和方式与传统历史学也不尽相同。(9)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载《中国音乐年鉴》(199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第347页。文中归纳的相关文献总体来说,都是对当前传承的传统音乐之历史渊源的探寻,研究对象“侧重在有明显历史深度的乐种、乐曲、乐器和乐谱方面”。(10)同注⑨,第348页。这些研究都可以视为在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这一概念提出前的研究序幕。
三、两种研究模式:“叙事”与“接通”
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数位具有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双重学科背景的学者,他们的双重学科知识结构对于民族音乐学相关历史研究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推动作用。本文选择两位学者洛秦和项阳给予详细叙述,一方面他们对于学术的历史观层面具有深度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各自的学术取向代表了具有双重学科背景学者显现的音乐人类学倾向和音乐史学侧重。
虽然,20世纪末已有民族音乐学学者提出共同关注共时与历时研究(11)例如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第三章第二节时空观中既有相关叙述。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61—63页。,但对历史是什么以及何为历史研究等问题进行反思的论文当首推洛秦《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1999),文中认同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观点,并将历史研究定位为理解与阐释。
叙事与阐释是洛秦持续贯穿于学术实践的两个关键词。2009年他提出“音乐文化诗学”的研究模式(12)洛秦:《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音乐研究》,2009年,第6期,第21—22页。,随后以唐代长安音乐社会生活(13)洛秦:《“新史学”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唐代长安音乐社会生活研究的刍议》,“汉唐音乐史国际研讨会”,西安,2009年。、上海俄侨“音乐飞地”(14)洛秦:《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第52—71页。、国立音乐院(15)洛秦:《音乐1927年叙事——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诞生中的中国历史、社会及其人》,《音乐艺术》,2013年,第1期,第6—29页。和宋代音乐(16)同注,第5—11页。为研究对象,在这一系列成果中都延续了对叙事与阐释的关怀。发表于2014年的《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是一篇总结性的论文。洛秦不仅梳理了自己相关新史学的认识,还提出重写音乐史的必要与可能。他通过认识音乐历史的“被发现”“被书写”和“被阐释”特性,反思了以往史学研究“重实证、重史实、重作家及其作品的特点”,而叙事与阐述正是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之核心。对于叙事与阐释的关系,洛秦有精准的理解:“同样的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叙事,这就是‘阐释’。”(17)洛秦:《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音乐艺术》,2014年,第1期,第6—25页。
项阳提倡融合历时与共时研究方法的观点较早显现于《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论域的交叉》(2003)一文。在此篇论文发表前后展开的山西乐户—轮值轮训—乐籍制度等系列研究中,项阳具体实践了融合历时与共时的研究倡议。此后,在与人类学家的学术接触以及对历史人类学的了解中,将融合历时与共时的音乐研究具体定位于理查德·威德斯(Richard Widdess)文中的“历史的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概念(18)对于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是否应该翻译为“历史的民族音乐学”,以及对“历史民族音乐学”讨论是否可以基于理查德·威德斯的那篇论文,笔者执不同意见,详细论文请见齐琨:《历史民族音乐学在英文文献中的建构》,《中国音乐学》,2020年,第3期,第22页。。在此后提出一系列“接通”的理念中,与历时—共时研究相关的有“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19)项阳:《接通的意义——传统、田野、历史》,《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第13页。“接通”理念对于民族音乐学的贡献在于提倡一种超越学科边界、融合历时共时、链接文献记载与表演实践的研究,其重点在于建立关联。
相较两位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洛秦是在对历史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给出自己的历史观定位,即历史是一种叙事,在此基础上着重探寻了历史音乐民族志阐释的深度与广度,观念认知与叙事性写作是其为历史民族音乐学做出贡献的两个重要方面。项阳是“从实地考察出发,发现问题”,借鉴了华南历史人类学学派提出的“回到历史现场”之研究理念,在他提倡“接通”的系列概念中推崇“致力于田野的活态与文献接通式的研究”。(20)同注,第9—20页。可以看出,田野实践与接通式理念是其奉献于中国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重要内容。此外,在洛秦的叙述中,笔者会联想到人类学诗学的叙事取向以及阐释人类学所言的阐释存在多样性及其追寻深描式的阐释;在项阳文中能明确地看到到他对人类学功能主义的偏爱。(21)项阳:《功能性、制度、礼俗、两条脉——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认知》,《中国音乐》,2007年,第2期,第25—34页。
从研究范式来说,笔者用经度—纬度比喻历时—共时,则洛秦展现的是历史民族音乐学“纬度式研究”,亦即定位历史上的某一个时间段或时间点,对当时的音乐人物与事象做民族音乐学式的共时性文化研究。项阳建构的“接通式研究”,亦即抓住当下与过去两个端点的音乐事象做了“经度式研究”,从而论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整体一致性”(22)同注,第15—16页。。以“经度式研究”看“接通”模式,似乎与冯先生所言“逆向研究”异曲同工,不同之处在于接通式研究强调“历时性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23)项阳:《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中国音乐学实践》,《人民音乐》,2019年,第2期,第74页。,是双向经度,古今互证。
四、研究对象的拓展:音乐民族志中的历史研究
进入21世纪,相关历史的音乐民族志书写,因其对象的拓展而色彩纷呈。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民族音乐学如何切入历史人物、古籍文献、口述资料、音响档案、声音文本、音乐文物、学术/科史的研究,以此观察在“经度式研究”与“纬度式研究”这两个范式基础上,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具体涉足了哪些历史研究范畴,并在结语中给予具体归纳叙述。
(一)历史人物与古籍文献
郑长铃硕士论文《陈旸生平及其〈乐书〉著述背景研究——以民族音乐学视角》(2002)和博士论文《陈旸及其〈乐书〉研究》(2004)都以民族音乐学为研究方法并给出自己的解读,对宋人陈旸的生平和他撰写的《乐书》之本体、著述动因、学术特点进行了重构与分析。在其研究中,除了史学常用的史料鉴别与考据的方法外,还将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的方法运用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文献的研究中,提出“在田野中走近陈旸”(24)郑长铃:《在田野中走近陈旸——关于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的民族音乐学方法选择与思考》,《中国音乐学》,2005年,第4期,第51页。,对陈旸故里福建闽清县际上村进行实地考察,寻访故居遗迹、家族祠堂、墓葬等,这与历史人类学提出的“历史现场”的方法颇为接近。虽然郑长铃未将其硕博论文定位于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成果,但在论文中对历史民族音乐学的观念与方法给予梳理,提出“笔者的研究或许可视为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中国化’方面的一种探索”(25)郑长铃:《陈旸及其〈乐书〉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7页。。笔者将这一成果归纳于“纬度式研究”,是将历史人物或历史文献作为文化事象,做民族音乐学擅长的整体式研究。
臧艺兵对《清稗类钞》给予了民族音乐学式的解析。从文献研究方法论的角度,他指出“要注重历史事实与文化阐释的关系”,将文献研究的田野关系定位为“当代人(局外人)与历史人物(局内人)的关系”,并认同“任何记录历史的人,都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阐释自己所理解的历史”这一学术立场。(26)臧艺兵:《〈清稗类钞〉中的音乐史料——兼论民族音乐学观念与音乐历史文献解读》,《音乐艺术》,2011年,第4期,第61页。从臧艺兵的研究中,我们能感受到民族音乐学者在面对历史文献时对民间话语的观照、对整体研究的重视、对文化阐释的强调,这属于前文所言的纬度式研究。
笔者在对四条记述了琵琶源起的文献进行解析时提出了“文献表述模式分析”(27)齐琨:《文献表述模式分析——以相关琵琶源起的四条文献为例》,《音乐研究》,2019年,第3期,第67—79页。与“文献叠写分析”(28)齐琨:《文献叠写分析——以相关琵琶源起的四条文献为例》,《中国音乐学》,2019年,第2期,第84—107页。两种研究方法。这两项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历史文本所包含的历史感是什么?古籍文献的撰写者在何种历史观下转录、引用、制作了历史文本?与前文所述“用民族音乐学方法或视角研究音乐史”的成果不同在于,本研究更多强调不同时期的文献所表述的历史感,以及不同时期撰写文献者的历史观。前者是将音乐史视为一种文化给予阐释,其研究目的为理解,是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历史(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后者侧重发掘不同历史时期音乐表演者、记录者、转述者的历史观与文献表述的历史观,如此研究还可以拓展至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音乐表演的历史感与历史观的探寻乃至比较,其研究目的为发现,是关于历史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of history)之研究。
笔者以“文献表述模式分析”探索了“纬度式研究”,亦即对记载琵琶起源文献资料的《风俗通》和《释名》中的词汇与句式进行分析,详述了因古代社会—文化情境所限定的历史感,而使得古人在书写中的呈现内容和表述方式具有必然性。
笔者以“文献叠写分析”尝试了“经度式研究”。“叠写”关注的是文献表述过程,本研究设计的是在自南北朝至清代、自上而下的历时过程中,相关琵琶源起的四条文献是如何在历代史书、政书、类书中被引用、转载、解释、再造、新创,“文献叠写分析”的目的是发现导致上述众多叠写方式使用的原由是文献撰写秉持了“隐胡显汉”“化异为同”“以过去理解当下”的历史观,以此成就了琵琶从西域胡乐转向中国器乐的历史变迁过程。
(二)口述资料
民族音乐学擅长运用在田野考察中获得的口述资料,但如何用口述资料讲一个历史故事,是近年来面对的新课题。张君仁在个体生命史方面进行了探索,他的博士论文《花儿王朱仲禄——对一个民间歌手的音乐人类学实验研究》(2002)以近一个月录音访谈的方式获得的600多分钟音频资料为基础,重构了朱仲禄学花儿、唱花儿、传花儿、研究花儿的个体生命音乐史,以此探讨了民族音乐学历时叙事的一种方式——人物传记,而如此叙述的学术定位为“对一种文化和‘人’的‘意义’的认知,而不是单纯的对‘规律’的探求”(29)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对一个民间歌手的音乐人类学实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0页。。
在这样的传记叙事中,我们首先体会到的是传记和历史密不可分,然而,关注个人生命史的意义在于对以往专注于音乐文化典型性与规律性研究的反思,正如奈特尔所看到的极端不注重“个人的、特殊的或不同凡响的”作品,实际是纵容了“文化平均值”(cultural-average accounts)的描述(30)Bruno Nettl,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wenty-nine Issues and Concept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p.9.。正如李海伦(Helen Rees)主编《在中国的音乐人生》(LivesinChineseMusic)也曾以西方学者的眼光,展现了在传统音乐创作与传承过程中个体表演者所扮演的角色。(31)Helen Rees ed.,Lives in Chinese Music,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9.
运用口述史研究方法的音乐类成果可分为两类。其一,对所得口述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有选择地运用于对某一音乐文化事象的论证与阐释中。其二,文本呈现的方式是以口述者的讲述为主体,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口述访谈的问题设计、访谈交流以及口述资料的整理与撰写中,口述者与研究者共同参与了口述文本的制作。(32)单建鑫认为音乐口述史“按其文本性质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口述史材料的直接文本呈现’;另一类是‘以口述资料为依据的研究文本’。”单建鑫:《论音乐口述史的概念、性质与方法》,《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第96页。
第一类成果以臧艺兵博士论文《武当山民间歌师研究:民间歌者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2004)(33)后以专著出版,臧艺兵:《民歌与安魂:武当山民间歌师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与齐琨博士论文《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2005)(34)后以专著出版,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为音乐学研究的先行,两篇论文在不同程度上都以口述资料作为论述的基础,分别对湖北武当山民间歌师与上海南汇丝竹班社的历史变迁与互动展开了叙事与阐释。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更多突出了个体记忆,重构了吕家河歌师姚启华的个人生命史;后者则以不同年龄段成员的集体记忆,再塑了南汇丝竹清音班百年传承的过程,然而,根本上展现的是乐人生命史。需要强调的是,集体记忆不是个体记忆的平均值,而是由不同个体记忆共建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括集体认同的内容,也包含个体体验的记忆差异,并期望在研究中阐释差异存在的原因。虽上述两篇成果的叙事方式各有差异,但总体来看都属于“纬度式研究”,将个体生命历程或乐社传承过程作为历史中的一个片段,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展开整体叙事,并结合古籍文献、地方文本、实地考察等资料给予分析与阐释。
第二类口述史成果中以杨晓《蜀中琴人口述史》(2013)与乔建中《望——一位老农在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2014)为代表。当我们读这两本书的“跋”与“后记”时,能体会到研究者在口述史资料采集与文本撰写过程中的高度参与感。
在杨晓归纳的口述史工作的八个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环节研究者的参与内容。(35)杨晓主编:《蜀中琴人口述史》,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420页。作为研究者,她的思考是:“口述者为什么会在逻辑上给出这样的答案?是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促使他有这样的思考?我想,这要比直接给出答案更加引人入胜。”(36)同注,第427页。
在《望》这部口述史的叙事中,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到乔建中老师的参与方式。这不仅能从“双窗口叙事法”展现的一位民间文化守护者与一位传统音乐研究者间那神奇的对话中感受到,更能从以3天访谈完成口述资料汇集的奇迹中感受到。(37)乔建中编著:《望——一位老农在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70页。这一切的根源是乔老师与老林在28年间建立的深情厚谊。
综上所述,无论是研究型的口述史还是叙事型的口述史,都无一例外受到研究者的学术定位、视角、选择的影响。即便是看似“以口述史资料直接呈现文本”的叙事型口述史,学者的观念仍然在口述史从执行到完成整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口述史可以成为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的总结对象。
历史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不同的是,民族音乐学家不仅像历史学家那样去研究历史,更是要去观察生活在当下的音乐文化持有者如何对待他们的历史?如何评判自己的历史?持有的立场与态度如何?民族音乐学者不会用音乐史学家对历史的评判来取代表演者或音乐的创作者对他们自己历史的评判。
(三)音像档案与声音文本
面对历史音响/像档案,我们会生发出“在不同的年代,人们是怎么使用设备和技术的?他们录音的过程是怎样的?被录音者与录音者的关系如何?录音结果又如何被使用?录音本身被存放和使用的传记又能为我们讲述何样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它包含何样的文化变迁与他者故事?如此等等”(38)萧梅:《梦回故里——问询历史老录音》,《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第156页。问题。相关上述问题的成果多属于“纬度式”研究,亦即针对某些历史音响/像档案,做音乐文化整体分析。
在最先接触奥地利国家科学院音像档案馆藏芬兰语言学家兰司铁(G.J.Ramstedt)于1909年采录的蒙古族录音时,萧梅首先关注到了其中的笔录资料,并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录音登记表”作为参照,得出的思考是“记录‘节目’的取向和记录‘历史’的取向必然影响档案管理的规范”,档案中一些相关历史记录的缺失,直接影响到音响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不出所藏田野录音的历史和其中蕴涵的学科发展倾向。”(39)萧梅:《音响的记忆——田野录音与民间音乐档案》,载《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4—96页。
萧梅指导邹婧的硕士论文《历史的回声:1909年蒙古族历史录音研究》(40)邹婧:《历史的回声:1909年蒙古族历史录音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2010)延续对兰司铁音响档案的研究,体现了“‘历史录音在过去’与‘历史录音在当代’的双重维度。而通向这两个维度的路径,亦即‘回到现场’。”(41)萧梅:《近现代历史音/像的音乐人类学解读》,《民族艺术研究》,2015年,第6期,第9页。该研究一方面在兰司铁的录制缘起、动机与过程中探讨当时民族音乐学的学术特点与学科方法,另一方面以实地考察的方法,到田野中去认识与理解这些民歌的分类、表演与风格。
相关于历史音响/像档案研究的意义,正如萧梅所言:“音或像所记录的是历史,音或像自身亦为历史的一部分,而研究也在丰富这些音像档案生命史的同时,参与历史的建构。但要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则需要档案管理者、学术研究人员和相关音视频技术人员的共同参与。这也是当代音乐学研究的另一个学术生长点。”(42)同注,第11页。诚然,在呼唤不同领域学者参与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期盼看到复合人才的成长。当前学术与应用结合的生长点在于将掌握不同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复合人才放置于前沿的新兴领域中培养。
什么是历史音响/像档案的服务目的?“反哺归家”(repatriation)是学者们寻找到的最佳路径,“它带给我们的是对学者所收集的研究资料与文化持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是对如何‘让资料回家’的音乐人类学学科行动的期盼。”(43)萧梅:《梦回故里——问询历史老录音》,《民族艺术》,2016年,第1期,第157页。这一缘起于应用民族音乐学到视角,在学术与实践的双重角度下关注历史音像资料对于过去与当下的意义,因而带有“经度式”观照特点。
从感受的角度研究声音历史感的成果并不多见,主要以徐欣博士论文《内蒙古地区“潮尔”的声音民族志》(2011)为代表。该文从现场聆听的角度论述了“声音中的历史”,通过对局内人与局外人声音感受的描述,揭示历史文化内涵。(44)徐欣:《内蒙古地区“潮尔”的声音民族志》,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4页。在音乐的声音中寻找其中蕴涵的历史信息,是一个着实具有强大挑战性的研究论题,其中蕴涵的研究空间巨大,如何平衡与链接感性描写与理性分析是这一论题面对的主要难点,与声音景观研究的结合,是解决这一研究难点的路径。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研究论题的新、难、少之特点,使得相关这一论题的研究方法具有极大拓展空间。
(四)音乐文物
相关音乐文物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非常稀少,这也许是因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曾经分别代表了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两个端点,对于具有如此差距的两个学科的融合,具有思想与方法上的难度。
音乐考古文物资料如何进入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视角?方建军博士论文《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2005)(45)后以专著出版。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二章中着重探讨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可以存在交融。在研究方法的论证中,方建军解析了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对象上的重合内容,以及民族音乐学的局内、局外观对音乐考古学的意义在于,在研究古代音乐事物时,既不能“以今类古”,即“不以今人(局外)的眼光看待、衡量、评价古人”,而是将考古资料置于当时、当地去考量;也不能以今断古,即“不以今人(局外)的观点研究古代的音乐事物”,而要运用现代的手段与方法,以及现代历史研究的宏观视野。(46)方建军:《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35页。在对以今类古的反思中,我们能看到他提出了类似“历史现场”的方法,亦即“纬度式”的历时中之共时整体研究;在对以今断古的反思中,以现代之研究手段、方法、视野探古,与“经度式”研究异曲同工。
(五)学术史与学科史
相关专著与论文众多且叙述模式较为统一,或是对学术或学科的整体过程做不同程度的回溯与总结,或是对学术中的某一理论、方法、学科要点、学科结构等做历时分析与归纳(47)笔者将学科史的研究范畴列为学术史下的二级分类,亦即学术史包含学科史。。如何以民族音乐学的眼光切入这一论题?萧梅博士论文《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2004)(48)后以专著出版。萧梅:《中国大陆1900—1966: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编年与个案》,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中例举了人类学家观点,“在人们记忆中的学科发展的‘过去’,正是以‘现实’为基础,是在不断地解释的过程中被不断地重构的”(49)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1950—1997),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页。,并认为“作为解读者,则在这种参与重构的过程中,成为历史的介入者,历史的‘参与观察者’”,(50)同注,第9页。随后对如何理解王光祈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如何解读1950—1966年政治工作的压力等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一以参与观察者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理解与解读的叙事风格贯穿全文,从而成就了一部带有反思意义的学术史成果。
对于何为历史民族音乐学范畴的学科史与学术史研究,笔者同意纽曼在总结民族音乐学历史研究的三个范式中的叙述:音乐史的历史是反思的音乐史,旨在论述音乐学发展过程中争论的历史,研究对象是在历史过程中音乐学学者的思想与行为,研究者是这些学者的后辈。(51)〔美〕丹尼尔.M.纽曼:《跋:范式与故事》,载《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因此在历史民族音乐学相关学科史与学术史的研究中,参与观察者是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学者的思想与行为是研究对象,理解与阐释是研究的路径,而反思是写作的核心目标。
2021年《民族艺术研究》推出由杨民康主持的“田联韬先生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术专题的系列论文,“对于田联韬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和深刻影响做了全景式的鸟瞰;并且着眼于其核心层面——学术体系,从六个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52)“编者按”《田联韬先生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之一),《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1期,第30页。杨民康称其为微观学术史专题,并总结了“从族群—地域—定点”向“民族—区域—多点”的转型过程。(53)杨民康:《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民族艺术研究》,2021年,第3期,第49页。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多数的历史时空内,学术的话语权是掌握在核心学术精英手中。因此,这种以特定学术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学术史,实则透视出某一时间段学术研究整体观念的建构与转型。
历史民族音乐学对于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关注,不仅以民族音乐学为对象。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洛秦在《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意义》(2018)一文中总结了音乐史学史研究书写范式的三个特征:非实证、重过程、批判性,言明在其研究中“尝试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核心就是‘叙事’和‘阐释’”,认为“就音乐学界而言,这种尝试对既有的研究范式仍具有一定的挑战性。”(54)洛秦:《中国音乐史学史研究的意义——研究属性、观念、范畴和范式的思考》,《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第16、17页。
结论: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范式与范畴
1962年,当“范式”这一词汇出现在托马斯·库恩的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1970;1996;2012)中时,尚属生僻之词,经其点石成金地论述之后,人们对范式概念的推崇、使用、拓展到了近乎失控的地步,以至于库恩在晚年放弃了这个让他一举成名的概念。(55)伊安·哈金:《导读》,载《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1页。何为范式?有学者发现库恩在著作中对“范式”一词有21种用法,一词多义是接触这一词语的读者常抱怨的内容。(56)同注,第11页。笔者则更为认同“范式是共有的范例”(57)同注,第157页。这一界定,在笔者眼中,范式显现的是共有范例表述的共识学术研究思维模式。
在阅读诸多音乐学学科关于历史研究的成果后,笔者将中国的历史民族音乐学之研究范式总结为三类:经度式、纬度式、比较式。
经度式是以音乐史学的历时视角重新审视民族音乐学以往的研究对象,而其核心研究思路为链接历史(古籍、口述史、民间文本等)与当下(音乐观念、表演行为、声音感受等),进而达到或以今探古、或以古解今、或古今互证的研究目的。总之,这一研究范式是以过程为目的,我们可以称其为音乐史式的民族音乐学研究。
纬度式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共时方法研究音乐历史,以社会—文化多元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研究为核心思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58)或为短时段的一年、数年或数十年,或为长时段的某朝某代,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都可以泛意地将其称为“某一时期”。的人物、器物或事件给予整体性阐释。总之,这一研究范式是以阐释为目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民族音乐学式的音乐史研究。
比较式是在呈现各地域各族群历史与历史观/感是什么后,展开的跨文化、跨地域、跨族群比较研究,从而在历时的过程中揭示音乐文化的交流互动、传播样态、源流关系等内容。总之,这一范式是以发现为目的,让比较走进历史研究的视野。
笔者认为,历史民族音乐学所涉足的历史研究范畴有文化史、心态史、制度史、生命史、声音史、学术史,列表说明如下。

表1.中国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畴与范式

续表
笔者做这一归纳的目的在于,提供哪些是历史民族音乐学这一领域的研究之思考。诚然,随着学者们探索空间的增大,历史民族音乐学也会不断拓展其研究范畴,上述归纳还存在极大的补充空间。
一百年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以近乎上帝的视角,看到了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他俯视了人类的无知,和在这一无知之下将这个完整的链条碎片化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史学等拥有各自系统的学科,并预言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对自身认识的提高,必将重新链接碎片,将知识还原为整体观照与全元视野。(59)转引自于沛:《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页。一百年后,他的预言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之初不是音乐史学加民族音乐学,而是民族音乐学者对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目前的历史民族音乐学更是一个领域,召唤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盟,共同思考关于历史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具体到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这两个学科,目前展现的是在知识结构与叙事模式上的互补,这也是目前历史民族音乐学存在的意义。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未来,是将成为音乐史学与民族音乐学的交叉学科,或者是民族音乐学的分支学科,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目前还很难判断,在我看来,是否成为学科并不重要,而探寻有深度的学术问题,形成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绽放的学术激情、获得的玄思之乐,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