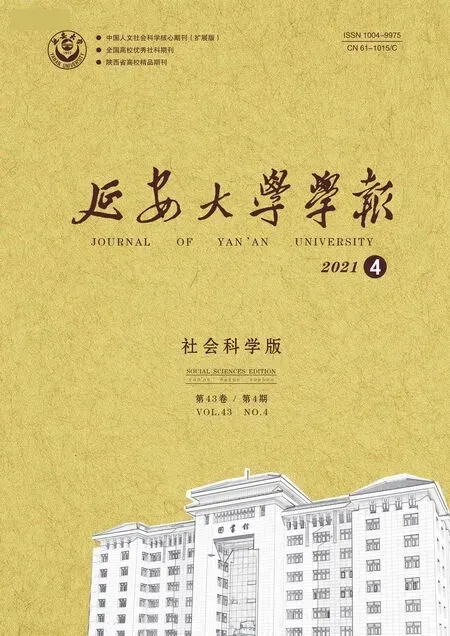永井荷风文学对儒学思想的批判与肯定
吕 娜
(1.延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2.日本东亚大学 综合学术研究科,山口 下关 751-8503)
1902年,永井荷风以自然主义倾向小说《地狱之花》登上日本文坛,受到了文学巨匠森鸥外的盛赞,后又发表《隅田川》《梅雨前后》《濹东绮谭》等具有江户情趣的小说和散文,奠定了其日本唯美主义文学鼻祖的地位。永井荷风的个人素养融合了日本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三方面因素。(1)参见野口富士男《荷風随筆集》(上),岩波书店1986年版,第298页。但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为国策,永井荷风对西洋思想文化的接受以及对儒学的批判更能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中国儒学思想对荷风的影响虽然有研究者提及,却没有得到重视和深入研究。(2)参见桑原武夫《桑原武夫集6:永井荷風》,岩波书店1960年版;赤濑雅子《永井荷風の批判精神:『断腸亭日乗』にみる韓国観を中心として》,《综合研究所纪要》1992年第18期;安井太郎《儒教を捨て切れなかった永井荷風の「生き方」》,《月刊テ-ミス》2009年第18期;奥野信太郎《荷風文学みちしるべ》,岩波书店2011年版。
永井荷风生于儒学世家,其父久一郎是有名的汉诗人,著有汉诗集《来青阁集》十卷,外祖父鹫津毅堂是幕末有名的儒学家,曾任明治新政府议事官。此外,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儒学家、汉学家大多与其家族成员有师徒关系,或是文墨之交。在明治时期汉文占绝对地位的教育背景下,永井荷风除在学校接受汉学教育以外,还在私塾接受了儒学的强化教育。其随笔中对于《大学》《中庸》《三体诗》等的学习和诵读多有记述,尤其是教汉诗的岩溪裳川先生家的孔子像,给永井荷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年后的永井荷风不仅有赴中国上海旅行的亲身体验,还有近两年的汉语学习经历。永井荷风以上海之旅为素材创作的《上海纪行》,是其目前可考的处女作。从这部作品中唐宋名家诗作的引用可以看出青年永井荷风对汉文汉诗涉猎广袤,不仅熟读强记,而且理解透彻,引用起来贴切自然。(3)参见钱晓波《青年永井荷风汉文素养小考——以〈上海纪行〉为中心》,《日语教育与日本学》2015年第1期。永井荷风的汉学素养,远远高于同时期日本作家的一般水平,他能够准确理解汉籍的含义,对于他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儒学典籍自然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领悟。那么永井荷风对于儒学的态度究竟如何?本文从儒学思想的角度出发,以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为理论依据,从批判与肯定两个方面来分析永井荷风文学作品中儒学思想的体现,探讨其对于儒学的态度,以期为新时期中国人民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带来启发。
一、永井荷风文学对儒学思想的批判
永井荷风对于儒学思想中“专制父权”的批判是显而易见的。在《狐》(1909)中,永井荷风表达了对冷酷无情、暴君一般的父亲的畏惧和憎恨,以及对温柔顺从的母亲的同情。因此,《狐》被视为永井荷风反对儒学思想的证据。实际上在较早出版的《一月一日》(1908)中,永井荷风就已经借主人公金田之口,声讨了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父权。金田是日本银行驻美办事员,与永井荷风曾在驻美日本银行供职的经历不谋而合。金田父亲接受的是明治维新前的教育,言不离孔子之道和武士道,精通汉学汉诗,爱好古董、字画、盆栽,这些正是永井荷风父亲的写照。金田的叙述以及他对日本食物的厌恶,折射出了永井荷风对于“专制父权”的批判。
金田父亲经常和友人在家里高谈阔论到深夜,而金田母亲不得不在一旁侍候。“你猜,给他们端菜热酒的人是谁?就是我妈一个人。当然,我们家也有两个打杂和做饭的女佣,但父亲沾染了茶人的习气,吃东西十分挑剔,所以烧菜煮饭的事情最终还是不能彻底放手交给佣人。母亲经常自己给父亲做菜热酒,有时连煮饭都不得不亲自动手。就算是这样,父亲也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每次都会对食物抱怨不已。早上喝酱汤时,他会说三州的味噌酱香味如何如何,盐放得不合适,又说日本酱菜这种切法简直让人看不下去,盐腌乌贼盛在这种盘子里简直太愚蠢了。上次买的清水陶瓷盘怎么样了,是不是又给你打碎了?你这样不小心,真让人生气……母亲的工作除了当永远得不到赞美的厨师以外,还要伺候那些一触即坏的古董字画,收集盆栽珍品。对此事,父亲从来没有说过感谢的话,反而找到一点儿错处,就要大肆发作,所以我出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从父亲干瘪的嘴里吐出的各种牢骚,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从未脱下束袖绑带、拼命干活的母亲的身影。没有比父亲更加可怕的人了,也没有人比母亲更加可怜的了。”[1]133-134
这段话形象地刻画了一个颐指气使、苛刻、经常借故大发脾气、暴君一般的父亲,最后一句话充分表明了永井荷风对于“专制父权”的强烈批判和控诉。金田不喜欢与美国的日本同胞往来,从不参与日本料理的宴会,是因为他一闻到日本酒,看到米饭、大酱汤之类的日本料理,马上就会想起已逝母亲悲惨的一生,浑身颤抖不已。他对于母亲的同情和对于父亲的畏惧、憎恨,已经迁移到了日本食物上,形成一种生理反应。可见作者永井荷风对于“专制父权”的深刻抵触。他对身为丈夫高高在上、苛刻挑剔、冷酷无情的做法深恶痛绝,进而认为父亲言不离口的孔子之道和武士道是“人生幸福的大敌”,但又表示,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抗思想”。一方面,这是因为永井荷风认为自己对儒学的认识不够清楚和深刻,“至死只不过是吴下的旧阿蒙罢了”;[2]160另一方面也因为儒学本身的复杂性。儒学博大精深,是一个极为全面的思想体系,涉及道德、伦理、哲学、政治、社会、自然等多个方面,并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宋明时期的儒学家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对儒学进行了新的注解和阐释,使儒学出现了与原始儒家思想相背离的专制思想。在地域上,儒学传入日本以后,日本人亦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和阐释,相继出现了古学派、阳明学派、折中学派、国学派等。其中古学派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为代表,主张排斥先秦之后儒者的注疏,直接以古代典籍为依据,探寻孔孟真意,复归原始儒家思想。武士道精神也吸收了大量儒家道德思想,但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仁”,提倡仁者爱人以及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方式,并不一味强调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服从,而武士道精神首推“忠勇礼义”,与原始儒学的侧重点完全反。
儒学较早提出的夫妻伦理是“夫义妇顺”,丈夫公正有义是妻子顺从的先决条件,从根本上来说,妻子顺从的不是丈夫,而是公正道义。在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夫义妇顺”渐渐演变成为“夫为妻纲”“既嫁从夫”,作为丈夫应公正有义的义务被弱化了,只片面强调作为妻子要顺从。在实际家庭生活中,男性虽然接受了儒学教育,但大多数人言行早已偏离了孔子之道,只强调“夫为妻纲”“妇顺”等利己的一面,并未真正做到“仁者爱人”“夫义”,不仅不体谅、爱护和同情妻子,而且对妻子的付出没有一点感恩之心。永井荷风虽然身为男性,却能够克制利己的私欲,反对男尊女卑,真正站在女性的角度上,同情、理解、体谅女性。“有日本人对美国家庭和女人的短处大肆批判,我却认为就算只是表面的伪善也好,丈夫在餐桌上为妻子切肉、取碗碟,妻子就会反过来为丈夫端茶、送点心……有时从歌剧院或话剧院回家,看到深夜餐厅里喝着香槟,看也不看丈夫或男伴一眼、只顾着自己在那里攀谈的妻子们,就算看到这样很极端的例子,我也感到由衷地高兴。”[1]135由此可见,永井荷风希望看到夫妻双方互敬互爱,希望女性能活出自我、快乐幸福,而不是在专制父权的压迫之下过完悲惨痛苦的一生。
永井荷风自小受到的儒学教育,源于以古代典籍为依据探寻孔孟真意的“古学派”。“专制父权”是儒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消极侧面,是对原始儒学思想的背离。在《狐》《一月一日》中,永井荷风虽然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父权”,但也隐约意识到不能完全否定儒学思想,他对“专制父权”的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孔孟思想核心“仁”的渴求,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克己复礼”“仁者爱人”。
二、永井荷风文学对儒学思想的肯定
永井荷风曾在随笔中进行了深入的自我剖析:“我于龆龀之时,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很早就学完了《大学》。成人后,以诵读儒家文章和诗词为乐。不少日常的道德于不知不觉间受到儒教的指导。”[2]160经过汉籍素读(一种以日语直读古汉语文章的方法)训练,能够培养出几乎相同的文章感觉和思维方式。(4)参见前田爱《近代読者の成立》,岩波书店1993年版。永井荷风在反复诵读《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和汉诗文的过程中,相应地形成了儒学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从他的散文和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他对儒学核心思想“仁”的肯定。
(一)儒学思想“仁”的直接肯定
散文又称“随笔”,内容涉及对人、事、自然、历史、社会的评论、思考等多方面,是作者品性、资质、才能的综合表现。永井荷风一生中写下了大量追怀江户时期人物、风俗的随笔,而江户时期的日本以儒学为官学,儒家道德思想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因此,儒学思想中必定有永井荷风认可的内容,以下从永井荷风的随笔《妾宅》(1912)、《砾川徜徉记》(1924)、《草红叶》(1946)、《雪日》(1949)等作品来分析他对儒学思想的肯定。
《妾宅》中的阿妾能够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根据四季变化,选择食材、做出美味而富有诗趣的饭菜,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给丈夫带来极大的满足与幸福,但却万事谦逊,从不居功、炫耀。永井荷风不仅对阿妾“克己”的品德赞美有加,还借珍珍先生之口说:“人不分男女之别,即使正当自然的事情,自己不以为正当而抢先出马,处处小心谨慎,老老实实,不是更能显出深沉而优雅吗?”[2]119此番论述毫无疑问是在提倡“克己复礼”的行为规范。看到年轻人毫无公德心,肆意破坏公共空间的摆设和环境,永井荷风痛感社会秩序的崩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那些提倡新艺术新文学的近世年轻人……对于堪称自己思想伴侣的桌面上的文房四宝毫无兴趣,也不爱好。他们有着卑俗商人推销商品的非美术意趣,又无意于进一步经营此道。他们单是把自己的居室弄得又脏又乱倒不要紧,他们一旦进入公众设施如饭馆的客厅,就将满是油污的外套扔到挂有绘画和放置雕刻品的壁龛,将吸剩的烟头扔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里,把榻榻米烤焦,向火盆的灰烬里吐痰,从一举一动上对于居室、家具、餐具和庭园等美术,毫无尊敬之意和爱惜之念。”[2]119永井荷风批评近世年轻人对于物品“毫无尊敬之意和爱惜之念”,一方面,是批评他们在公共场所没有保持“克己复礼”;另一方面,是批判他们对作为创造者的“人”及其“劳动成果”缺乏尊重和爱惜。物品和干净舒适的公众场所都凝结着人的劳动和心血。特别是艺术品的创造者要付出无数的光阴、精力和财物,经过无数次反复练习,才能练就高超的技艺,创造出有价值、能被摆放在公共场所的作品。打扫干净的院子、房间里铺设的榻榻米、为了客人特意准备的火盆,都凝结着人的劳动,如有污损,就得花费人力再去清理、修补。永井荷风对近世年轻人行为的批判再次证明,他所肯定的行为规范,正是儒学思想“克己复礼”。
在《砾川徜徉记》中,永井荷风追忆了曾在自己家服侍多年的名叫新的女佣人。永井荷风母亲曾对于新一家人给予了种种照顾,还帮她料理了婆婆的后事。新十分感激,在永井荷风父亲辞官之后仍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一家,年老请辞时仍表示年终大扫除时要来帮忙。永井荷风与新两家并没有因为社会地位的高低和主仆身份的尊卑形成对立,反而存在着一种超越了身份地位的温情和相互尊重。身处上位者看到贫弱的家仆遇到困难,能够心怀悲悯尽可能地提供帮助;身份卑微的女佣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知恩图报,即便是永井荷风家“失势”以后,仍然尽心服侍一如从前。永井荷风还特意去寺院里祭拜新,并感慨说:“新去世后,我家好多年没有找到像她那样善良的女佣。新生于武州南葛饰郡新宿的农家,本来不识字,但她恪守妇道,循规蹈矩。良人辞世后,她一直守寡,赡养婆婆,抚育儿子,以诚实之心回报别人的恩义。我纵观大正当今之世新型妇女之所为,幡然回顾我家老婢新的一生,不禁泛起敬畏之情,岂是偶然?”[2]84永井荷风怀念的不仅仅是新,更是新所代表的美好品德。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新都保持“克己”。同情女性的永井荷风回顾新的一生,“不禁泛起敬畏之情”,并不是在主张“恪守妇道”,而是在日本全盘西化、你争我抢的社会背景下,表达对儒学思想“仁”所倡导的“克己复礼”的敬畏。
从《草红叶》中也能看出永井荷风对人的重视、对温暖人情的怀念。在1945年美国发起的东京大空袭中,永井荷风的精神据点偏奇馆和藏书都被烧毁了。永井荷风居住的偏奇馆以及其中数以万计的藏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对此永井荷风抱着达观的态度,“十分悠然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藏书被烧毁,直到天亮”。[2]195在听说浅草那边烧死了人之后,却担心起生活在那边的与自己有过泛泛之交的荣子等人。由此可见,永井荷风“重人轻物”,受到了儒学思想“仁者爱人”的影响。永井荷风还十分珍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和流动,念念不忘多年前荣子母女在三社祭时赠送“红豆糯米饭”一事,在文中不厌其烦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动和惊喜:“这位母亲的厚意使我觉得无可名状的喜悦……似乎考虑到生长在下町的我的口味,这就更使我感到高兴……我能在学习爵士舞的舞女之家,品尝到三社祭的红豆糯米饭,在那之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2]196他深受触动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并不是说红豆糯米饭多么美味或有价值,而是通过荣子母亲赠予的红豆糯米饭,永井荷风感受到了别人对自己的重视,感觉自己被人记挂在心上,感受到了下町三社祭的繁荣与喜悦。其二,荣子母亲对于他人的一点点恩情,都记在心上,并想办法报答。在永井荷风看来,这种知恩图报、遵守道义的行为,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全面西化已不多见,十分可贵。永井荷风对于重视人情义理的荣子母女二人的怀念,是他肯定儒学思想“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的表现。
年近七十的永井荷风在《雪日》中回忆了四十多年前与好友受到的热情招待。傍晚,永井荷风和好友在向岛散步,忽然下起雪来,二人一时兴起来到一个酒肆饮酒赏雪,吟诗作对。为了免去老板娘的麻烦,他们一次性点了一整瓶酒,而不是一杯一杯地下单。从原文所使用的“掛茶屋”一词以及时代背景可以推断出,酒肆应该一部分是露天的,一部分是直接搭建在泥土地上的茅草棚或帐篷之类,老板娘并没有因为下雪天冷急于收摊而有一丝不耐烦,而是连忙招呼二人就座,周到地铺上坐垫,亲切地嘘寒问暖,并捧来了地炉。对此永井荷风感慨道:“这种待客的态度在当时也许并非少见,但今天回想起来,连同那市街的光景,那番心情,那番风俗,再也难得一见了。”[2]146作为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永井荷风念念不忘的竟然是这种细微之处的温暖人情,是克制一己私欲而站到对方立场上去考虑的同情心,可以说是他对儒学思想“仁”最直接的肯定。
(二)儒学思想“仁”的间接投射
小说不同于散文能够直抒胸臆,不能直接体现永井荷风对于儒学思想“仁”的肯定,但永井荷风成名作《地狱之花》(1902)中的园子以及晚年代表作《濹东绮谭》(1936)中的阿雪,这两个女神一般的女性形象都闪耀着儒学思想“仁”的光芒,是永井荷风肯定儒学思想“仁”的投射。
《地狱之花》的小说题目意指:“盛开在地狱中的白色百合花”,是女教师园子的象征。面对黑渊长义的请求,“园子注视着长义的举止和表情,被他为儿女们忧虑的真情所打动,同时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也更加体会到只有通过努力地教育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才能慰藉老人的内心。不管社会上为了什么排挤这一家人,自己既然来此做了家庭教师,进入这个家庭,就应当为此付出自己全身心的诚恳和热情。这时,长义又客气地向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园子能够住在自己家中,这样就可以随时为秀男提供教育和指导。对于主人的这一要求,园子表示非常高兴,也愿意接受”。[3]11长义年轻时与英国传教士侍妾私通,并通过侍妾将传教士的财产据为己有,因而遭到了社会的排斥。觉察到长义的悔恨,园子能够以“宽恕”之心,像对待一个普通人那样尊重他,真诚、热心地对待他。明知如果和这种不道德的人过从甚密,自己也很可能被人说三道四。但是园子还是抑制了利己的想法,选择宽容长义,理解同情他作为父亲对孩子的爱,力排世俗的观点和压力,在责任感的驱使下接受了长义的请求。园子之所以被永井荷风喻为“地狱之花”,是因为她有一颗纯洁、高贵的心灵,能够克制利己的私欲,同情、尊重、爱护他人,是“爱人”的“仁者”。在小说的尾声,园子向富子剖白内心:“人只有完全处在如同动物般自由自在的境地,并且还能够遵守令人尊崇的道德,才有资格戴起那不朽的赞美之冠,这样的道德才是有价值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恐怕连人的资格都不应享有。”[3]82目睹了社会的阴暗、遭受了暴行的园子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最终内心升起的信念却是儒学思想“仁”所倡导的“克己复礼”。园子的这番告白,正是永井荷风肯定儒学思想“仁”的投射。
《濹东绮谭》是永井荷风58岁时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是最能体现永井荷风本质的集大成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作者永井荷风化身为同样是58岁的作家大江匡,玉之井的阿雪于“我”而言是缪斯一般的存在,“她使我那倦怠、荒凉的心灵中清晰地浮现出往昔那令人怀恋的幻影”。[4]163阿雪总是梳着岛田髻和圆髻,和服腰带在前面打个大结,很像明治年间的艺伎。当然,“我”之所以被阿雪所吸引,不仅是因为她古风的装扮,还因为她与江户时代的人有同样的美德,能为他人考虑,富有同情心、恻隐之心和侠义之心。初相遇时,虽然阿雪为了不让狂风暴雨破坏刚做好的岛田髻,不客气地撑走了“我”的伞,一路上却也在“每次拐弯时,她都回过头来看我,怕我迷了路……在一排房屋中的一间挂着遮日草帘子的房前停下……她收起雨伞,不顾自己身上的雨水,先用手拂去我身上的雨珠”。[4]117由此可见,阿雪是一个能够为他人着想、“克己”守礼的人。在后来的交往中,阿雪对“我”真正卸下防备,却是源于对“我”身份的误判。“阿雪和客人一起上二楼时曾斜眼瞅见我正在楼下的房间里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于是,她似乎认定我是一个搞地下出版业的人……至此,我的职业被不由分说地定了下来,而且我的‘不义之财’出自何方似乎也自然明了了。于是,这女人对我更加推心置腹,全然不把我当作客人对待。”[4]132对待一般客人时阿雪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是在断定“我”是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的人之后,却对我敞开心扉,把我当成“自己人”。后文中,永井荷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点:“阿雪的话和她的态度都表现出她已推定我的职业是为社会所不允的,于是,她抛弃了狎昵之态,简直有点放肆之嫌了。”[4]138阿雪对“我”产生亲近之情,不是因为金钱和地位,而是源于对社会边缘人群的悲悯心和同情心。“我”们谈话中提到携款潜逃的罪犯时,阿雪“一副不管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情”,看到从窗口塞进来的偷盗犯搜捕令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扔在火盆旁。据此可以推测,即使发现了逃犯,阿雪也不会报警。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阿雪对这些社会边缘和底层的人心怀宽容和怜悯,是儒学思想“仁”的体现。永井荷风赋予了他心目中的女神儒学思想“仁”,是他肯定儒学思想“仁”的心理投射。
儒学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面。它的专制父权、男尊女卑等消极因素使无数人陷入痛苦的深渊,被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不断地痛斥、诟病,因此甚至掩盖了其具有普遍价值的核心思想“仁”。儒学思想“仁”倡导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等处世原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是值得每一个东方人都为之自豪的传统文化。青年时期的永井荷风曾狂热地倾心于法国文学和思想文化,但随着思想的日臻成熟,永井荷风逐渐意识到东方传统文化的价值,创作了大量富于江户情趣的唯美主义作品。和、汉、洋多元文化的滋养与丰富的人生阅历造就了永井荷风冷静、客观、敏锐的头脑,他深刻领悟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仁”,对于江户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儒学思想能够一分为二地去审视。从二十四岁时的成名作《地狱之花》到年近七十时的随笔《雪日》,他一生都在文学作品中对“仁”进行着反复的肯定和颂扬。在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重拾传统文化自信的今天,永井荷风对儒学思想“仁”的肯定以及他对于东方文化的客观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儒学创新发展的趋势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