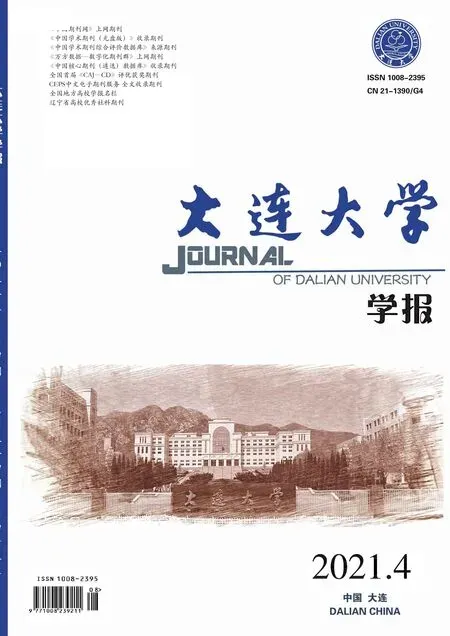论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艺术
李 贤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是散文家、诗人和学者。他既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又有文学批评理论著作,目前关于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歌与诗论研究,如孙玉石的《朱自清现代解诗学思想的理论资源—四谈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思想》;二是散文研究,如孙绍振的《背影的美学问题》;三是学术思想和史料研究,如王晓东的《朱自清学术思想研究》、朱金顺的《朱自清研究资料》。相比较而言,对他文论整体风格的研究较少,本文把他的文学批评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探讨他的文学批评艺术。他的文论既强调文学作品对现实、人生的关照,又重视纯正的文学趣味;既注重人的主观意志的表达又注重时代精神的充分表现。他的这一文学批评观念更多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影响,体现了中国哲学重伦理的特征,也体现了现代文学批评对古典文化的继承。概括来看,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艺术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刹那趣味”的文学审美观
在朱自清的文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是“趣味”,既有对“一刹那”的捕捉,又有对达到“圆满刹那” 的追求,这一特征暗含了作家的文学审美观。前者是就创作主体而言,突出灵感在创作中的意义,认为灵感的瞬间以文字艺术的方式永恒;后者着重于文学价值的实现,在“圆满刹那”中实现“文学里的美也是一种力”[1]237。这种力既是源于文学的美,又是通过对现实人生的反映引起读者共鸣的“力之美”。这一特征在朱自清散文中表现的最为明显,他作品中经典的“一刹那”有“背影”“荷塘”“秦淮河”“春”“匆匆”等。他对自己散文的评价是“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个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2]。他的诗歌大多追求一种“圆满的刹那”,如《雪朝》中一些清新明快的小诗。“刹那趣味”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在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作家的评论中,他具有中国传统文论风格的文字既见古典文学文论的蕴藉又见随时代而增的学术眼界,对茅盾著作的评论不同于阿英等侧重社会历史的批评,他着眼于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语言美、篇章布局的和谐等也是他评价作品时的标准。朱光潜以“情趣”论诗歌,他的“趣味”中包括“情趣”的美学意义也包括人间烟火,这就是对“味”的把握。“只从一般的所谓时代思潮的顺流的趋势或文艺思想的表面的发展顺序,去解释文艺发展的趋势。”[3]238这一特征的形成与他的审美观分不开,他的“趣味”是一个整体同时又代表了文学的审美与实用两个方面,与阿英在《文学百题》中提出“文学的趣味”意义不同,阿英的“趣味”与梁启超的“趣味”一致,朱自清是综合这两人的智慧并加以艺术的审美。哲学专业的他热爱中国古典文学,趣味是古典文论中常用的词语,源自道家的智慧,但不包括其中超然独立的人生趣味。他的“刹那趣味”是哲学与古典文论的凝练,体现了他对新文学发展的思考,把传统的诗文评纳入现代文学批评体系中。如《论诵读》《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等强调音节在文学发展与创作中的意义,与闻一多的“音乐美”相似,他对闻一多作品的评论借鉴并概括了自有《诗经》以来的诗歌理论发展脉络,是他“趣味”的实践和整体表现。他自己也曾说过“不擅长做小说”,小说中“刹那”因素远不如诗歌、散文来的自然,当他以这一审美观来评价小说时就显示出局限来。在《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中提出“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一时代还给一时代”的观点,一如他散文的温柔敦厚与平淡从容,这一美学风格也是他文学批评的总体风格。他是以创作和批评两个方面致力于现代文学诗歌和散文这两种文体艺术的探索,“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地位与趣味。”[1]26朱自清明确指出文学批评要有“趣味”,在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持这一观点的并不多,而这恰好是他的文论风格并在文本内部矛盾的呈现,这一特点贯串于他的批评体系中。
他一面强调“刹那”的体验在创作中的作用,一面要求以这“刹那”的感觉载道,并以美国诗人麦克里希为例论证了“诗以载道”在创作中的普遍性,“这个道是社会的使命。”[4]49朱自清的“道”是儒家的思想,他的创作与批评之路是寻求艺术与思想融合的过程,在强调文学“美”的“五四”时期,他有“道”;在强调文学“责任”的三十年代,他有“趣味”。曾撰文论述“逼真与如画”作为传统批评常用语的矛盾感,深感“真与好”兼得不易。从本质上看,他的审美观也是矛盾的一体,“刹那趣味”的获得要求较高的艺术敏感,从虚境到实境上偏于虚境的营造,从艺术到人生上偏于艺术对人生的价值,他注重趣味而不是意境,但又强调文学趣味还在于对人生的反映,是传统的“逼真与如画”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变体。如果按照王富仁对现代文学批评分类来看,朱自清的文学批评既是“学院派”又属于“为人生派”。与同时代的批评家相比,他更着重于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评论作家作品,不因“为人生”而轻视文学的趣味,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标语和口号”,将文学批评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去做,这严肃中有“趣味”。强调批评主体的情感介入,他的“刹那”离不开想象的参与,“诗也许比别的文艺形式更依靠想象,所谓远,所谓深,所谓近,所谓妙,都是就想象的范围和程度而言。想象的素材是感觉,怎样玲珑缥缈的空中楼阁都建筑在感觉上。”[5]36其实就正指的是作者在写评论文章时要有真切的感受,这种真切的感受是自我的经验,是“有我之境”,这种批评适合篇幅不长的作品,比如诗歌和散文,这也可能就是他写的小说评论有某种意犹未尽之感的原因。“趣味”是他的审美观,也是他批评文学作品时的一个标准,他的“趣味”不是无功利的纯审美,是文学反映时代与人生的艺术呈现,这两方面一个是主观感性的,一个是客观理性的,这种以感性表现理性、以理性渗透感性的方式与徽州朴学中的“情感哲学”一致。强调直觉感悟也看重内在逻辑的一致;强调批评者情感的主动性也注意创作的时代背景与写作目的;强调中国传统文论批评在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延续性也注重西方文艺理论的介入与影响,这三个方面成为朱自清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
二、“尊情崇志”的文学价值观
从现代文学思潮变化的角度综观朱自清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他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演绎始终不脱离文学艺术这一范围,以“刹那”的灵感寻求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的契合。从文学价值观的类型来看,朱自清属于“尊情崇志”类,“是以人的主观意志的充分表达和情感的宣泄为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把人的意志力量、情感意向及时代精神、人民情绪的表现作为具体的文学价值目标。”[6]165尊情崇志是理解朱自清创作和批评的关键,他的创作和批评注重主体情感的融入与再建构,在时代文学之中但又不在主流之内;反映社会现实但又是别样的视角;以文学的轻柔之美反观人生中那些不能承受之重。他以兼容并包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批评方法与现象,他的诗歌和散文评论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对艺术与美的探讨大多集中在这一类作品中。尊情崇志的文学价值观在创作中有利于充分展现文学自身的属性,在文学批评中有其自身的局限,有时会限制观察的视野,比如不能很好地概括现代文学中宏大的时代主题,不能准确地解释外部环境在文学发展规律中的作用。这一特点在朱自清文论中有明显的体现,他对闻一多、茅盾等作家作品的评论细致入微,更多是从文学艺术表现的层面论述“趣味”。他很少从社会时代思潮的角度解读文学,或者说他是透过这些文学表象直接正视文学发展中属于本质性的因素,即文学以怎样的方式表达现实生活中的“情、志”,文学批评应该如何发现这其中的“情、志”与“美”。“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文学是人生的语言”“文学最重要的是思想,是默喻的经验,那是文学的材料”[1]161。与紧密关注时代环境变化的文学批评不同,这里“文字的艺术”“人生的语言”无疑是在强调“美与志”及由此而来“情”,朱自清更偏向于志、情,“志”是有内涵的客观存在,不是小品文中的“志”,与他的“道”契合。“情”是他的审美,他能将沉重的现实生活在作品中化为淡然、淡泊的心境,蕴蓄成诗意的空灵。而“默喻的经验”源于既成的文学价值观和既有的认知体系,与杜威的“艺术经验”相通,“经验本身具有令人满意的情感性质,因为它拥有内在的、通过有规则和有组织的运动而思想的完整性和完满性。”[7]40朱自清的文学经验一是源自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二是新文学发生后中西文化对比下产生的自我判断,内在的情感性质和审美经验还是受数千年延续而来的儒家伦理的影响。在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及文化比较重视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在新诗发展道路上,他以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养在新诗与古典诗词之间建立桥梁。尊情崇志的文学价值观在中国文学发展不同时期都有存在,融“诗言志”的儒家内涵与“诗缘情”的审美追求于一体,朱自清的创作和批评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
作为一个经受过“五四”时代思想冲击的中国传统学者,他在三十年代的反思与审视似乎更为直观,早期作品中的迷茫(《毁灭》)焦灼逐渐化为平和从容(《荷塘月色》)。文学净化心灵的作用是文学性的体现,文学表达人生现实的层面是社会性的诉求,朱自清以“尊情崇志”实现了文本的内在和谐与个人的内心冲突。“五四”新文学阶段的“西方”作为“现代”的象征,与他既有的传统文化理念不断碰撞,在他创作中体现了“概念”的抽象意义,与其说他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不如说他是在时代思潮中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力之美”。“1921年到1925年的江南时期和1925年到1937年的北京时期。他在这两个阶段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特征:充满矛盾的,缓慢发展的,稳健向前的。”[3]89这两个时期的三个特征是他文学探索与文学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一是在中西、新旧对比中对思考文学的本质属性;一是在外部环境的变化中探讨文学的社会性,对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推崇,对“情与美”的偏爱,对作家时代责任感的认识,构成了他矛盾纠结的心境。“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标准”[1]26,重新认识传统里的价值是作家们反思“五四”文学时的群体特征,胡适于1923年提出的“整理国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坛表现为集体心理。相比较而言,朱自清的“矛盾”有内在的清醒和坚持,面对“新”不自觉地忆“旧”,思考并直面如何赋予“旧”以“新”的品质,最终在的“尊情崇志”中调和,并贯串于他之后的创作。他的作品大多是从自然中寻找意象,在情与志的统一中呈现温柔敦厚之美,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重伦理并寻求伦理和谐的关系,而非西方哲学思想。他的“尊情崇志”不是逸世高蹈,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不排斥西方文艺思想,是在对比中寻求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共通之处,比如,他认为“文以载道”并非中国独有,从本质上看“尊情”是遵循文学审美的一面,“崇志”是“载道”,他的“道”是“社会使命”,也就是作家的责任。这可归因于作家内心的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它迫使一个人不仅仅以骨子里的他自身一代的感受来写作……这种历史感可以使作家变得传统,同时也会使得他精确地意识到在自己时代所处的位置。”[8]49朱自清两个阶段的变化以及创作时的矛盾心态就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他的文学批评也呈现这样一个阶段性特征,早期的“为人生”批评是自我知识体系的碰撞整合,之后专注于“文学的美也是一种力”的批评。
三、“融情入理”的文学批评观
朱自清文学批评自成系统始于三十年代,“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批评是他尝试阶段,是以诗歌相关的理论探讨为主。尽管执着于“趣味”的实践,但不能否认社会思潮的变化是促成他文学批评观形成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三十年代是一个文学批评很盛的时期,这里所谓的盛是指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理论家、作家甚至是文学圈外的都在操文学批评之业”[9]149。这种盛况之下的文学批评一方面激发了文学的多样性,一方面削弱了文学的独立性,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理论迅速成长的时期。在强调文学参与时代变革的社会责任阶段,文学的政治批评、社会批评、价值批评等文学的外部批评成为主流,朱自清提出“文学的美也是一种力”是从文本内部批评出发,不同于康德哲学中“力学的壮美”[10]232,他文学的“美之力”首先源于“趣味”,这一“趣味”不是纯艺术无功利的,是源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儒家思想以及和谐美。这是他的美学观念,自身的性格因素以及中国哲学对他的影响促使他形成“温柔敦厚”的“实用”思想。因此,他的文学批评不是反功利的,是既要求文学的“情”又要求文学的“理”,这里的“情”是指文学反映表达社会人生时所蕴含的作者情感与文本内部情感,这里的“理”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道理、事理”,也就是朱自清的“道”,依然不脱儒家伦理的影响,他很少从哲学的角度或者用哲学术语评价文学作品,衡量的标准是“表情和达意”,也很少化用西方的文艺思想。“朱自清仅仅一般地承认异域学殖对于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助力……但是宽阔的眼光驱使朱自清专攻传统的文学批评。”[11]213发现并建立传统文论与现代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客观地看待异域学殖在本土学科发展中的作用,这一学术视野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在比较中看到了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以及审美心理的本土化在文学批评中的潜在制约。审美心理有时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心理,早在《论语》中就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论述,表达的道理就是如何“在情与理的融合中实现语言的力量”。朱自清“文学的美也是一种力”要求批评者具有“融情入理”的能力。
在各类文体中,朱自清的“诗论”卓著,然而他并不是单一的论诗,他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这一学科的发展有系统性论述。史料中有关于他在大学任教时讲授“中国文学批评”这门课的记录,其中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进行溯源式的研究,对现代文学批评既有个案的分析,也有宏观整体的概述。“在文学批评里,理论也罢,裁判也罢,似乎都在一面求真,同时求好。”[1]29这里的“真和好”与“逼真和如画”是一个意思,也是他在不同篇章中经常提及的话题,并且在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陷入自我矛盾的漩涡,最终又在“道”与“趣味”的和谐中圆满,即艺术的真与生活的真以及文学表现“真”时所取得的审美效果和实现的社会价值是衡量作品的标准。这些理论观点即是他文学价值观的反映又是他文学批评观的直接运用,适合于各种文体,与“尊情崇志”相对应,“融情入理”既是文学批评观又是他文论的风格之一。他不是社会历史批评者,但他注重文学如何表现“社会的使命”;也不是带有印象主义的审美批评,强调作品中的情感的体验,“文学作品之吸引人最大因却在情感的浓厚”[3]117,但有别于王国维、朱光潜的“审美非功利性”。比如 “文字的艺术,材料便是人生”“文字里的思想是文学的实质,文学之所以佳胜,正在他们所含的思想”[1]237-238。类似的论断还有不少,表达的是文学的无功利性与功利性两个方面,也是他作文学批评时的依据。《标准和尺度》一书是他文学批评观的系统体现,提出了“标准是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的”“尺度是自觉的修正了传统的”。他参照的对象是“传统”,是受文化心理习惯影响的无意识,尺度是随时代思潮而变化并且不断扩展自身的内涵。“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变得快的时代最容易觉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学术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也如此”[4]16。朱自清从纷繁的文学批评流派中看到关键性因素,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哪一种方法,文学批评的区别在于“标准和尺度”的不同。如果从这一角度考察文学批评方法的差异,可以发现几乎是一个真理性的判断。如果说深厚的英文功底是他博览外国文学书籍时的工具,哲学专业对他的影响则是认识到“文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的不同。无论是作品还是文论,都不是晦涩的文风,也不求深奥的境界,他在《什么是文学》中把胡适的文学三性“懂得性、逼人性、美”概括为 “达意和表情” 两重性。但不能因此否认哲学在他文学批评中的作用,他的审美观、文学价值观、批评观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也就是说他以哲学的“矛盾”概观文学意义上的“矛盾”,并以此解决文学创作、批评中的自我矛盾。哲学的矛盾观与考据的学术方法是他“融情入理”的途径,在“文学的考证和批评”中认为“绝对的超然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和批评联系起来”[3]35。他看出绝对超然的客观与超然的美学在现代文学批评中都是不可能永存的,考证是实事求是,文学批评是否如实反映了“道”。考据法在晚清以前是有影响力的学术方法,是清代徽州朴学这一学派的治学之道,西方学者对中国明清社会历史的研究中,称徽州朴学为 “江南学术共同体”,对学者们的辩证思维给予很高的评价。就这一学派的著作来看,他们在对古典文论的考据考证中有不少关于“诗文”的经典论段,是对“诗文评”地再判断。朱自清的文论以及他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思考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方法、古典文学、儒家伦理占有重要地位,欧洲游学经历坚定了从“国故”中建设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想法,与“拿来主义”相比,他是谨慎的比较、借鉴。
四、结语
把考证和具体的文学批评相联系,以学术考证的方法考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建设,对引进的西方批评术语进行追根究底的探讨,并结合具体特征思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或独特之处。作家的朱自清和学者的他有着不同的风格,前者是寓浓郁于淡然的情感表现、寓深沉于清浅的语言表达;后者是不厌其烦的考证、举例论证,是清晰、简洁的理性分析。在朱自清的作品、文论中,“情”以多种形式存在,但都要求“情”中有时代的生活,他认为只表现个人情感、情绪的作品不是好作品,诗文评中强调“独抒性灵”的论述是不全面的。这是他缘情而文,隐理而深的成就之一。其二,善于运用哲学方法,这种哲学方法调和了他文学批评体系中的自我矛盾,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相反相成,矛盾的发展”[4]27,而他个人的批评理论也呈现这样的特征。他的审美观、文学价值观、文学批评观都是矛盾的整体,他讲“趣味”但反对“无意义的幽默”,他的很多论述都在表明“文学是情感的,文学也是历史的”这一观点。如果单看他的这一“标准”很容易想到社会历史批评,然而他的这一主张并不是独立存在,他的另一个 “尺度”是“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净化的,安慰人的。”[1]246他的“标准和尺度”总是同时规范着批评的方向,文学净化心灵是以“动之以情”,文学研究参考“别的学科做根据”是为了“晓之以理”。缘情而文似乎是他所有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的最初动机,隐理而深则既关学术视野又关语言的艺术,这个“理”是他的“道”,是他学者的理性思维,有时会借鉴英文的语法书写中国的语言,用简明的句子表达繁复的内涵,直白中经得起品味。批评家的审美自觉与学者的严谨构成他文论的整体风格。
朱自清的文论在现代文学批评中自成一家,经历了从尝试的探索到稳健的纠结两个阶段,同时代学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关注于中国文学批评对他的影响,很少关注传统学术方法对他的影响,他的哲学专业知识很少被提及。而这两点在他批评中都至关重要,前者形成了视野,后者形成学术特征。“刹那的趣味”在“社会的使命”中寻找;情之所钟,道之所存;在传统文论与学术方法中飘逸始终未能超脱。他以实事求是做学问的方法建设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提出的“标准和尺度”是哲学的矛盾统一,他文论中的“缘情就理”是内在情感哲学的调和,他的文论是现代文学批评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