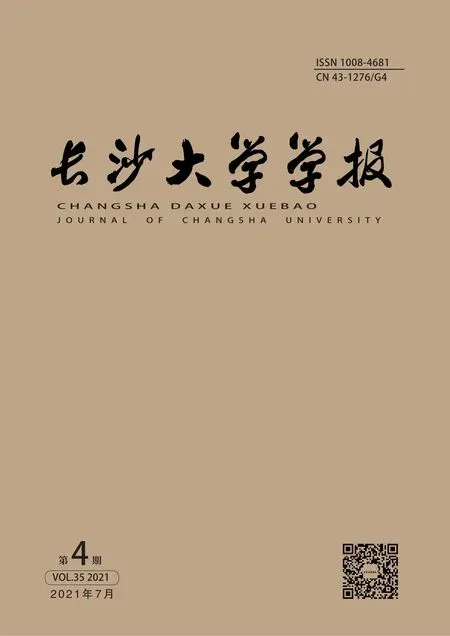韩愈散文骈散融合探析
成松柳,吴思聪
(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410076)
中国古代学者对文学本质问题多有探讨,对于内容与形式孰轻孰重亦争论不休。从“文质彬彬”到“文笔之争”,从古文衰微到骈文兴盛,古文的变革如“古文运动”等多与骈文对立。但文学的本质是相通的,任何文体都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且一种文体的发展离不开其他文体的影响,“古文运动”中不只有文体的对立,也有许多吸收和融合,韩愈散文亦受到骈文与古文的共同影响。
韩愈散文在唐代独树一帜,对后世亦影响深远。唐以后提及古文,皆离不开韩愈,他既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也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但韩愈的散文并不完全如他所说,只从三代两汉之书中的古文发展而来,更是从偏向审美特性的南北朝骈文而来。一方面,韩愈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他的文道观念使其往往以骈文为对立面,大力发展古文的创作;另一方面,骈文文体源远流长,且便于逞才使气,在唐代使用广泛且无可替代,韩愈散文创作受之影响,多注重文辞。在唐代骈散互相影响之背景和韩愈文道观念的影响下,韩愈散文呈现骈散融合的特色,本文将从韩愈散文的语言特色、句型结构和文章布局进行探析。
一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背景
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在唐代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两者也不可避免地有了互融。骈文中的浮靡之风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观,古文也不断发展起来,韩愈散文就产生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在韩愈之前的诸多骈文与古文的斗争,为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奠定了基础,也为韩愈散文的骈散融合提供了经验。
(一)唐代骈文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之时,人们对于文学作品形式美的研究不断深入,骈文顺应文学自觉发展规律且走向繁荣。至韩愈所处的唐代,骈文发展有了新的转向,骈文作品也有了新的风格,相比古文仍占主流。唐初的骈文,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代文风的影响,绮丽婉约,适合宫廷应和,其创作多藻饰而少内容,后在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笔下文风才有了转变。自此,唐代骈文的气势与意境开始博大,思想和内容也不断充实。盛唐时,整个社会氛围都较昂扬激越,骈文内容丰富、感情基调上扬、气势雄浑,已有骈散融合的端倪。“燕许大手笔”虽多庙堂台阁之作,但作品大都典雅庄重、博大恢宏,书序和碑文等作也多有拓展。当时有名的骈文作家也大多是大诗人,颇具盛唐气象。中唐时期,骈文几经改革后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庙堂之类的应用文与抒情叙事文的骈体也都有了不同的变化。而晚唐骈文在国势衰微、社会混乱之下逐渐走向华丽浮泛。
骈文在唐代长期占据文坛的主要原因,一是骈文具有符合文人审美要求的特性,在表现汉字之美方面比古文有优势,也可展现文人的才气,受到诸多读书人的偏好。骈文便于逞才使气,在形式上多有雕琢,将用典、对偶、声律等的形式之美发挥到极致,使作者显得博学渊雅。虽在内容的表达上有缺陷,但在审美性上仍有价值。二是科举制和官场公文的需要。进士科中所考的律赋使得想要入仕的读书人都须做好骈文,而上传下达的公文也须采用骈体,骈文运用广泛且无法被替代。三是优秀的骈文作家对其改革创新,使它得到长足的发展。唐代在韩愈之前,已有初唐四杰致力于骈文文风的转变,后陈子昂力倡革新,宋之问、李峤倡导疏宕有致;“燕许”、王维、李白、杜甫、李华、元结的骈文气象高昂,陆贽的骈文流畅。这些对韩柳在散文上的创作以及“古文运动”都有着重要影响。
(二)唐代骈文与古文的融合
每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衰微与兴盛之时,骈文在唐代虽占主流,但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其弊端。骈文在六朝发展至顶峰后,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走向极端,只注重四六的格式和声律,将华丽的辞藻和生僻的典故用至其中,最终落入俗套,失去内容和真情的表达,这正是唐代“古文运动”要反对骈文的原因。古文的精练生动、简明实用更符合韩愈等人的需要,在他们的努力下,古文开始不断崛起。后有学韩愈者一味追求古奥怪涩,完全反对骈文和文辞藻绘,复古模拟之风过甚,又使得古文走向另一种桎梏,晚唐骈文因此又兴起。
唐代骈文较散文更为繁盛,但骈文也从唐代开始受古文影响产生了新的蜕变。骈体文与散体文长期共存,古文运动的成功与骈散之间的相互批驳和借鉴是密不可分的。骈散在功用上各有长短,但二者也是相辅相成的,骈体与散体只是体制,稍加变化就可以改骈成散,韩愈许多文章中的句子就是如此。其实从张说、苏颋、常衮等人创作骈文开始,骈文就有了骈散融合的趋势,有了逐渐散体化、素淡化的趋势。文章好坏与骈散无必然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才至关重要,而韩愈散文正是形神兼备才成就深远。
二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特点
韩愈散文受骈文和古文的共同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体现。清代刘熙载评价其散文道:“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1]20-21韩愈散文内容之丰厚,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体察和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形式之多彩,来源于对前代诸多文体的融会贯通,包括古文与骈文的诸多技法。观其文章布局,文典结合、铺陈渲染、化骈为散;观其语词特色,新词生动、口语自然、虚词调和;观其句法结构,用韵灵活、奇偶并行、长短句相间。总之,从谋篇到用词造句,皆可看出韩愈散文出神入化之特点。
(一)谋篇
骈文在谋篇上自有长处。刘师培曾言:“有韵及四六之文,中间有劲气,文章前后即活。反之,一篇自首至尾奄奄无生气,文虽四平八稳,而辞采晦,音节沉,毫无活跃之气,即所谓死也。”[2]170韩愈散文的谋篇布局与骈文风格紧密相关,虽然韩愈行文无定法,以内容的表达为宗旨,自成高格,但其谋篇取了骈文之长:以典入文,自然晓畅;时有铺陈,含蓄深远;化骈为散,推陈出新。
骈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用典,可以展现作者的积累,这使得骈文自六朝以来就受到诸多文人的推崇,这在韩愈散文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全文可由典故布局,整篇皆围绕一个典故来阐述观点,如在《杂说》中,韩愈用伯乐与千里马之事表达对人才难被发现的叹息;《送董邵南序》开头提及荆轲高渐离之事,暗示今非昔比;《答陈商书》以齐王好竽之事来鼓励陈商不随波逐流。此外,在《原道》《原性》《原毁》等论说文中,韩愈所用典故出自不同的经书、子书、史书甚至佛家典籍,可以看出韩愈学识之渊博,用典广泛且密而不繁,这也是韩愈文章布局谋篇中的重要一笔。用典恰当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可以增加渊雅之气与含蓄之妙,韩愈所用皆契合文章主旨大意,与纯粹堆砌典故的骈文相比,显得更明白流畅。
骈文以四六句式为主,在对句中呈现出典丽精工的特色。韩愈散文继承了骈文句式的一些特点,又大胆出新。袁枚曾说过:“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 肾,为奥博无涯涘,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拗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8]1549四六句式往往一个偶对结束就已句意完整,但韩愈经常采用散而长或错综排比的句子。韩愈的散文中时有对句,亦多大气磅礴、沉郁顿挫的长句,以及简练精悍、意味深长的短句,这些更能增强表达的力量。《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在下论“士穷乃见节义”[3]572后,即用长句层层深入地论述了人情冷暖、世风日下之现象,与柳宗元的高洁义气做对比,更显悲愤。《蓝田县丞厅壁记》中也用一个长句描述县丞行事,使其神态毕现,完整的句子由“文书行”“卷其前”“目吏”“则退”[4]100等短句组成,尖锐地讽刺了官场弊病,更显对郁郁不得志的人才的惋惜。韩愈在论述和描绘上使用长句使得语气文情更为饱满。不过方东树也曾评价韩愈“笔力强,造语奇,取境阔,蓄势远,用法变化而深严,横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间有长语漫势,伤多成习气”[5]219,可见长句的使用也需妥当处理,以避免造成阅读障碍。
六朝骈文十分重视辞藻,尤其是形式上的美感。韩愈则提出“惟古于词必己出”[3]604“惟陈言之务去”[4]190,重视词语的创新。韩愈散文中有“耳濡目染”“跋前踬后”“下塞上聋”“粉白黛绿”“形单影只”“任重道远”“神施鬼设”等词,这些词一三、二四字相对,是韩愈从诸多经典中提炼而成,言简意赅、对称工整。此外还有许多叠词,如“油油翼翼”“矫矫亢亢”“伦伦睨睨”“戚戚嗟嗟”等,形式精致,彰显个人风格。韩愈的许多散文读起来艰涩难懂、佶屈聱牙,与他所选用的词语是分不开的,如《曹成王碑》中“嘬锋蔡山,踣之,剜蕲之黄梅,大鞣长平, 广济,掀蕲春,撇蕲水,掇黄冈, 汉阳,行跐汊川,还大膊蕲水界中,披安三县,拔其州,斩伪刺史”[4]478,所用动词都极生僻。韩愈为了反骈而复古,但有时过于追求奇特,反而不利于内容的表达。不过他那些融合了骈文技巧的文章,倒显得文从字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的优异成绩足以向世界证明我国已经实现体育大国的目标,后奥运周期,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新的认知,群众体育由此重新登上体育发展的大舞台。自2008年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态势迅猛,群众体育领域研究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通过知识图谱的分析也发现我国群众体育研究存在跨单位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缺乏中心作者群等问题。因此,后续相关研究应当注重不同机构与作者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从而为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夯实理论基础。
韩愈在骈文的基础上对传统文体进行了诸多改革。六朝时骈文盛行,在韩愈和古文运动之前,祭文多是骈体,以四言为主,讲究韵律,句式整齐,风格庄重典雅,便于当众朗诵,韩愈本人亦有诸多四字祭文流传于世,如《祭柳子厚文》《祭河南张员外文》《祭穆员外文》等。但在《欧阳生哀辞》中,韩愈先用散体描写了欧阳詹的生平,蕴含深切的惋惜与悲痛,最后用“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4]339这类四字与五字语句,进行了总结,加深了感慨。最能打动人的《祭十二郎文》是散体,全文倾诉真情,不同凡俗,影响深远。六朝后碑志基本使用骈文,虽能做到情文并茂,但限制了写人叙事功能,而韩愈使碑志从记载资料的应用文变为充满文学性的文体,既可抒情言志,又充满传记色彩。在《柳州罗池庙碑》中,韩愈采用玄幻手法表达对柳宗元的赞叹;而在《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又用诙谐的语言描述了一位不与世俗同流的奇男子王适。韩愈对骈文的改革体现在许多应用文中,这些文体长期流于僵化的程式,而韩愈使其焕然一新。
(二)遣词
韩愈散文在用词上具有突出成就。首先,他能从骈文固定套语中吸取经验,从前人之作中提炼词语,创作出所作文章需要的新词,推陈出新;其次,韩愈对俚言俗语的运用得心应手,对骈文的渊博雅致之气与古文的艰涩之风都处理得当,使得文章平易畅达,突显骈文与古文融合的特色;最后,韩愈在虚词的运用上也有所发展,使得骈文与古文的融合与转换更为灵活。
唐代声律发展已较为完善,尤其体现在诗歌上,文章自然也不例外。韩愈散文在声律上用韵自然,散语之中夹有声调和节奏。与许多古文完全无韵相异,与诸多辞赋骈文要求严格也有些许不同,韩愈采用散句来押韵。《后汉三贤赞》中“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为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4]66,语句虽散,用韵却齐。《子产不毁乡校颂》开头说“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4]75,四字与五字相间,却依然押韵。韩愈用韵有时较为松散自然,如《柳州罗池庙碑》中的最后一段字数与骚体不合,用韵也多有改换;《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最后一句,本可以每个短句都押韵,一韵到底,却出现了“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兮”[4]274这句短语将其打断。用虚词和语气词押韵来源已久,屈原的《离骚》中就有大量的“兮”,韩愈对此也颇为精通。《送孟东野序》中许多句末为“之”“者”“也”“耶”等字,《送董邵南序》中多“哉”“矣”等字,《送李愿归盘谷序》和《欧阳生哀辞》中有大量的“兮”字,《祭十二郎文》中则有“呜呼”“乎”等字,这些字多无具体意义,在句尾重复出现,叠加起来却合乎韵律。
韩愈常年做官,文集中有数篇上书和表状,这些都需要文辞委婉,虽不及汉赋的“劝百讽一”,但仍需极尽铺陈方能达到目的。如在《谏佛骨表》中先直接下结论——“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3]684,后用上古的轩辕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为例来说明无佛之前的统治者如何长寿,又举殷汤、汤第四代孙太戊、汤第十代孙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穆王等例来佐证帝王的长寿与佛无关。韩愈知道自己此举定然激怒皇帝,所以进行了大量铺陈。《燕喜亭记》中,韩愈为亭屋周边的每一处盛景都取了含义丰富的名字,包括山丘、石谷、土谷、山洞、池塘、山泉以及厅屋,看起来有些眼花缭乱,但这些取名皆与对友人的关怀相关,读者从中既能感受到山间美景,又能收获劝诫,意义深远。
骈文在唐代虽占主流但有弊端,如过于注重雕琢词句、铺陈泛滥,影响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中唐时期要求革新的古文家势力较弱,韩愈既以执道者自居,就得大力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和浮靡文风。他在《答吕毉山人书》中讲道:“方今天下入仕,惟以进士、明经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习熟时俗,工于语言,识形势,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坏,恐不复振起。”[4]243骈文在科举和公文中占据重要地位,导致入仕之人更注重形式的雕琢,真正的思想则难以表达,韩愈对于这种现象很是不满。因此,他在文体复古中常取古书“单行直下”的散文句法,并习得了尧典、舜典之“浑浑无涯的气格”[4]245。
例如,在给学生讲解《妈妈的爱》这篇诗歌的时候,教师可以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读出妈妈对孩子无私的关爱以及孩子对妈妈的感恩之情。然后,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学生理解诗歌的具体内容,感受修辞手法的运用,激发学生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进行写作练习,自己创作简单朴实的诗歌来表达对母亲的爱,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达到促进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双向提高的目的。
韩愈散文在句法上对骈文既有继承又有突破。在声律上,韩愈发扬了骈赋押韵的特性,用韵灵活,散句亦可押韵;在句型上,不拘定格,多有奇偶并行、骈散夹杂之语。韩愈散文中长句雄健有力,短句精简灵便,二者在韩愈笔下超脱了骈四俪六的格式,在叙事和抒情上加强了表达效果,使文章读起来抑扬顿挫、感人至深。
虽然翻转课堂起始于课前视频知识传授,但本文作者认为,课前知识传投并非只能通过视频实现。鉴于微课的制作人力、技术、时间成本太大,任课教师可以上传课件或者提供与教材配套的网络学习平台资源实现课前知识传授。目前,由于多媒体技术的推广,任课教师都对英语精读的教材进行了PPT课件制作,出版社也提供了参考课件和网络平台学习资源。如果摒弃现有的这些资源,教师都把时间花在重新制作微课上,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甚至会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因此,实施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师;可以灵活应用现有课件和网络平台资源,根据学生水平选取相关内容,进行资源的整合和优化,然后将课前学习内容给学生上传到指定网络平台上。
(三)造句
韩愈对虚词的运用也有创新。先秦两汉之文发展至唐代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虚词在文章的节奏、音律和格式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虚词,既可增强文章的抑扬顿挫,也可丰富对句的形式,韩愈散文中可见大量的虚词衔接其中。一方面,文章中的虚词有助于抒发感情,增强或舒缓语气;另一方面,韩愈运用虚词使得文章更显自然灵活。方东树道:“而于不经意语助虚字,尤宜措意:必使坚重稳老,不同便文随意带使。此惟杜、韩二家最不苟。”[5]222《祭十二郎文》作为韩愈感情流露至深之文,其中的虚词对于感情的表达作用是巨大的。如“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4]380,于句首连用三个转折连词“而”,感情强烈,层层深入。陈子昂在《堂弟孜墓志铭》中连用四个“欤”:“呜呼,其无命欤!遭命欤!天不忱欤!道固谬欤!”[6]28李华在其成就最高的骈文《吊古战场文》中也说道:“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6]65韩愈在《祭十二郎文》中也有着相似的句子:“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4]380此处连用三个“邪”字,加重了语气和情感的表达,加深了节奏和韵律,读之感人肺腑。至于使文章更自然灵活,则可见《答李翊书》中有关气与言关系的论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4]191用“也”“而”“之”“则”等虚词使气与言的定义和关系清楚地展现出来。
阅读推广既是一种活动的服务形式,则可能会在多个地点、多个不同空间、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其多样性特征相对于图书馆传统的固定地点、单一形式的服务而言,其辨识度更低。因而,它更需要代表其特质的标识来标明服务的前后一致性及增加读者的辨识度,而品牌化则可以将具有多样性特点的阅读推广统一在一个框架或主旨下来实现。
韩愈虽提倡古文,但他也在散文中大量运用了骈偶的修辞手法和对句,并对对仗的句子加词改造,这比骈文又多了几分松散自然。但语句仍具有形式上的对仗,既能彰显文采,又有利于朗诵和流传,在精美整齐的句式中意义得以凸显。许多对偶句在现代仍有警示意味,如《师说》中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4]49,《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4]50等,形式对仗,内容精辟,自然且不露痕迹。钱基博曾评论《进学解》说:“虽抒愤慨,亦道功力;圆亮出以俪体,骨力仍是散文;浓郁而不伤缛雕,沈浸而能为流转;参汉赋之句法,而运以当日之唐格。”[7]155意思是它既吸收了骈偶句法,又自有骨气。
通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对水库水质进行富营养化评价,汾河二库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处于30~50,属于中营养水体。
三 韩愈散文骈散融合的成因
在骈文为主流、古文衰微的大背景下,韩愈的文道观念和他古文的创作实践也有一些矛盾之处。一方面,韩愈的思想与儒家密切相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自是排斥佛老,而且他也认为自己继承了儒家的真正道统,因此渴望复兴儒学、重振古文,这使得他的文章重视现实性和功利性,为此他系统性地提出“文以明道”理论。另一方面,韩愈此举又使得文与道有了分离,也使得散文的文学性和审美性在文章中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虽然韩愈大力倡导古文,想要完全革除浮靡文风,但他对于骈文辞藻与形式之美有着深刻的认识,重视文辞的表达,也注重吸取和借鉴骈文的技法,因此其散文创作呈现出骈散融合之特色。
(一)“文以明道”与对古文的推崇
韩愈散文中有大量通俗化与大众化的口语词汇,这些口语化词汇能使文章更自然简明,在骈文与古文融合的散文中也更能见其价值。而在一些需要直接抒发感情的作品中,口语化的词更能体现感情的自然真挚,如《祭柳子厚文》的最后一段无一生僻词,即使字数固定,也很好地表达了韩愈的哀痛与对友人的赞美。而在刻画人物和叙事时,口语化的语言更为鲜明生动。《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对李翰所著《张巡传》的补充,韩愈在文中对多个人物的事迹都有刻画,尤其是对南霁云的描写无任何套话虚语,也无僻字怪句,口语化的语言皆体现了他对人物透彻的观察。
在车牌定位模型中改进了Yolov2模型,重组了特征图,融合多级细粒度特征,以适应车牌在输入图片中的结构化特征。为验证其有效性,以上述自制数据集作为实验数据,比较Yolov2模型、Yolov2模型与不同特征图重组、及FAST RCNN所训练的检测器效果如图5所示,训练时为避免过拟合及提升速度,选用动量常数为0.9,学习率为动态衰减,初始值为0.001,衰减步长为10000,衰减率为0.1,批大小为10,共迭代10次,批迭代次数为5000,框架为Darknet。
在《与冯宿论文书》中韩愈道:“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4]220韩愈认为那些随大众的时文即骈文是令他下笔都感到惭愧的,其中难有真正的思想和感情,这对于他的传道也是有碍的。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又提到“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4]186,愈发突出自己的审美意味。在《题哀辞后》中韩愈说自己“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4]340,可见他改革文风就是为了习得古道,并发扬自己坚持的道。韩愈在当时能不与时俗合流,践行自己的为文之法,在古文创作上多有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心中的坚持。在“文以明道”思想的指导下,韩愈推崇古文,并在骈文的主流中开拓出新的道路,使得骈文与古文不断融合与蜕变。
(二)“文道并重”及对骈文的借鉴
韩愈虽重道,但也并未就此轻文。他提出“文以明道”,但这样反而使“道”与“文”得以分开,使“文”在文学性上可以单独地、更好地发展。因此,韩愈的感情可以在文章中不受束缚地表达,他随意“舒忧娱悲”,甚至“以文为戏”,这也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极大的自由,并取得丰硕的创作成果。韩愈志向高远,注重文学对现实的社会作用,但并非闭门著书,他的古文也并不是单纯的弘道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常被同时代的人不理解,也受到后世儒家学者的批判。但韩愈对骈文有着包容的心态,且有不拘骈散的创作实绩,开拓了文章的创作之路。即使面对诸多不理解,韩愈依然坚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值得后世学习借鉴。
韩愈创作的《送穷文》《毛颖传》等文就曾引发诸多争议。他在《答张籍书》中自我辩解道:“吾子又讥吾与人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裎也。”[4]148可见他承认文学在娱乐上的重要作用。后世亦有许多人批评韩愈“以文为戏”,对韩愈所论之道有诸多不满,这也从侧面证明韩愈并没有完全把文学当成一个纯粹的传道工具。而且,韩愈并不只是研习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也都有涉猎。在《进学解》中韩愈就说自己“上规姚、姒”“下逮《庄》《骚》”[4]51,对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也能从中学到知识,从而充实自己的文章。韩愈的观念并不狭隘,因此其散文既能传承厚重的思想,又能吸收骈文的形式。
法拉利812 Superfast上下车的便利程度不亚于一辆普通的大众高尔夫,并且驾驶席侧车窗可在120公里/小时的车速下保持开启而不会产生刺耳的噪音。不仅如此,当前车速和挡位等信息还可以实时呈现在副驾驶的眼前,这无疑为驾驶员和副驾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韩愈散文成就非凡,最重要源于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韩愈认识到文学的独特价值,认为许多流传千古的文章与道德和政事并无关系,成就高低主要取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特点。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中说“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4]102,这说明他对于骈文的美和功用是有体会的。在《答陈生书》中韩愈也提到“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4]197,他虽然重视传道,但也注重文辞,而这正是他超越前人之处。“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4]163,韩愈对于“文”的作用有着明确的认识。
将文学视为传道的工具,这对古文来说也是一种束缚。虽然古文在论述时的生动大都超过骈文,但骈文的文采亦不能完全抛弃。无论骈文还是古文,它们终究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和历史渊源,且它们的终极指向即明道也有相通之处,但它们的创作终究受到创作者自身才华和经历的限制。而韩愈能在骈文和散文中找到平衡,文道并重,创作出骈散融合、内容与文采兼具的优秀作品,领导古文运动,并影响后世,可见其才华和能力。袁枚曾道:“韩、柳琢句,时有六朝余习,皆宋人之所不屑为也。惟其不屑为,亦复不能为,而古文之道终焉。”[8]1549后世学韩愈者多矣,但都难以冲破文体之限反而受其束缚。韩愈将骈文与散文之优势融会贯通,不持偏见,文章自有高格、终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