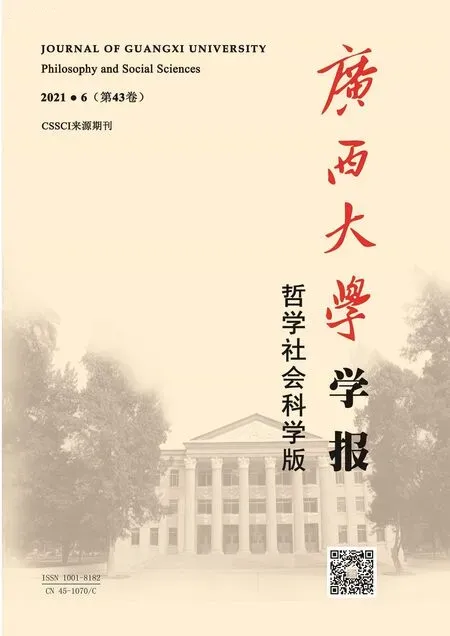日落条款启动背景下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
魏艳茹
印尼是东盟最大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消费市场,也是历史上华人“下南洋”、如今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作为印尼顶层战略规划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成功对接、基于“利益和合”的全球投资治理网络重组的时代背景下,中印投资交往更为密切。从2014 年起,印尼渐次终止了26 个双边投资协议(简称BIT),1994 年中国—印尼BIT 也在其列。在已终止BIT 日落条款(sunset clause)普遍启动的新变局中及时开新局,为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做好法律谋划非常重要。学界对该问题关注不多,是以笔者略述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印尼BIT 日落条款的启动背景
早在亚非拉国家竞相掀起外资国有化浪潮的20 世纪60 年代,印尼便开始积极缔结BIT①整个20世纪60—70年代,印尼缔结了8个BIT,其缔约伙伴均为欧洲发达国家:荷兰、丹麦、德国、挪威、比利时、法国、瑞士和英国。,以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1]。自1968 年与丹麦缔结第一个现代BIT 起,至决定渐次终止BIT 的2014 年止,共缔结了71 个BIT。这些BIT 核心条款普遍用语模糊、笼统,具有片面保护投资者私权、对东道国主权保护不够、全面接受投资仲裁庭管辖权等特点[2]。
截至2014 年,涉印尼的投资仲裁案件共8起,仲裁庭的裁决并未明显出格。但由于体现全球话语的BIT 规则未能与体现地方话语的印尼国内治理规则良性互动,恰恰是这些BIT 中片面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规则本身及BIT 框架下非常独特的私人(投资者)挑战东道国的投资仲裁机制,导致这些案件尤其是最后3 起矿业争端案件给印尼政府带来了极大的监管和舆情压力[3]。
在上述背景下,2014 年3 月,印尼通知荷兰,1994 年 印 尼—荷 兰BIT 将 于2015 年7 月1 日 有效期届满后正式终止[4]。迄今渐次终止了26 个BIT。因投资通常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为确保投资法律环境的稳定,依循国际投资协议缔约实践,印尼BIT 终止条款都内嵌了日落条款,以期为终止前对已投入的既有投资提供延伸保护。比如,1994 年中国—印尼BIT 日落条款(第13 条第2 款)规定:“第1—12 条的规定对本协议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10 年。”②印尼BIT日落条款所规定的延伸保护期以10年为主。极少数印尼BIT未指明延伸适用的具体期限。除1992年印尼—澳大利亚BIT、1995 年印尼—阿根廷BIT 外,其余24 个已终止印尼BIT 的日落条款均已启动。
各国根据国内外情况定期或不定期更新BIT范本本是常规工作,但通常借助新旧BIT 更替转变缔约立场,而不是在新范本以及基于新范本的新BIT 尚未签订并生效之前,大面积终止已生效的BIT。这是因为,后者不但将导致国际投资保护网络出现真空,而且还加剧其动荡性,不利于为外资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判印尼大量终止BIT 进而“日落条款”陆续启动后,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现状、问题、对策非常必要。
二、日落条款启动后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现状
在本文的语境中,“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包括两类:一是中资企业以印尼为首个投资目的地进行的投资,这类投资通常被视为“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受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国际投资协议之保护;二是中资企业以印尼为最终投资目的地而非首个投资目的地进行的投资,这类投资通常被视为“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①出于善用境外资源、市场、技术等关键要素的考虑,跨国公司通常倾向于搭建复杂的全球投资架构。中资企业亦然。“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经常以避税港或低税地为最顶层/顶层投资地,以税制规范透明、避免重复征税协定多、税收条件优惠的国家或地区为中间层投资地,以实际业务运作的国家或地区为底层投资地,通过复杂的融资结构投资。对于这种股权安排,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2018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已予以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意义上的肯定,将受承认的国际税收间接抵免层级由三级升至五级。,受第三国与印尼之间的国际投资协议之保护。上述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之国际保护框架包括BIT 框架、其他协议框架。
(一)BIT 框架下的投资保护现状
印尼始终采用传统的欧洲式BIT 范本。将现行有效的印尼BIT 与业已终止、借由日落条款延伸适用的印尼BIT 相比较可知,除非缔约对方另有不同坚持,整体上这两类BIT 均极为偏重投资者利益。主要表现有:一是投资定义条款多采用以资产为中心的缔约模式,将包含间接投资、买卖合同在内的各类资产都认定为投资,故印尼有义务用BIT 保护投机资本和国际贸易活动。二是绝对待遇标准条款未附加必要的限缩性解释,故投资仲裁庭有机会用该“口袋条款”扩大保护投资者利益。三是征收补偿条款的规定非常笼统,未界定间接征收,从而为仲裁庭扩大解释间接征收预留了空间。四是资本转移条款允许投资的本金与利润自由转移到境外,未设置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必要限制条件,故投资者可自由撤资②在东道国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时,外资大量出逃不但可能导致东道国在国际上无力购买基本物资和服务,而且可能助推金融危机的发生,而1997—1998年印尼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恰是外资大量出逃。。五是投资者和国家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全面接受了投资仲裁管辖权,允许投资者就其与东道国之间的任何投资争端提起投资仲裁。
(二)其他协议框架下的投资保护现状
除了早在1981 年缔结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议》采用当时风行的传统欧洲式BIT 范本,印尼缔结或参加的、现行有效的所有“东盟+”类协议和双边自由贸易类协议均采用了美国式BIT 范本。这些协议均订立于2007 年以后,具有美国式BIT 之注重预留东道国正当规制空间、投资保护水平相对略低的特点:一是缩小投资定义的外延,或采取以企业为中心的定义模式③如2019年《印尼—澳大利亚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第14.1条(定义)。,或将不具有投资属性(如投入资本、期待获得收益、承担风险等)的资产排除在受保护的投资范畴之外④如2009年《东盟全面投资协议》脚注2。。二是对绝对待遇标准条款予以限缩性解释,澄清公平公正待遇、全面保护和安全的含义,以及这两者与习惯国际法的关系。三是在征收补偿条款中明确了间接征收的判断标准,以及征收与税收措施之间的关系。四是对转移条款设定了除外条件,规定东道国有权为了遵守国内强行法、遵守《国际货币基金协议条款》、解决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问题及外部财政困难等原因,限制投资者转移其本金与利润。五是限制投资者对投资仲裁条款的滥用,限定可提起投资仲裁的争端范围,细化投资争端解决程序,增设防止滥诉的机制,如要求滥诉的投资者支付东道国的应诉费用和律师费。
根据印尼缔结的两类协议的通常规定,当不同投资协议的调整范围重合时,投资者有权选用更优惠的规则。具体如下:一是多数印尼BIT 明确规定,调整同一事项的两类协议可并存,投资者可适用对其更优惠的协议或规定①例如,1994年中国—印尼BIT第11条(其他义务)规定:“如果……缔约双方签订的国际协议为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提供了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的待遇,应从优适用。”。二是其他类协议也均允许并存。有的协议简单承认,缔约方有权签署待遇更优惠的平行协议②例如,1981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议》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方可签订协议,提供比本协议规定的待遇更优惠的待遇。;有的协议进一步规定,应适用对投资者更优惠的规定③如2009年《东盟—韩国投资协议》便是如此。;还有的协议在承认并存的同时责令或指引缔约方努力解决条约冲突④如2007年《印尼—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便是如此。。
三、日落条款启动后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障碍
(一)保护网络的可预测性差
对24 个已终止BIT 项下的既有投资来说,因日落条款的缘故,已终止BIT 继续为之提供若干年限的延伸保护,其国际保护框架暂时稳定。但是,由25 个现行有效的印尼BIT 所构建的国际保护网络的可预测性却较差。
首先,印尼的BIT 终止立场尚不稳定。一是以共时性视角观之,投资保护水平本身并不是影响印尼BIT 终止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现行有效BIT 与已终止BIT 的投资保护水平整体看来并无明显差异,但个体差异可能巨大。例如,因中国在投资仲裁条款方面的格外坚持,1994 年中国—印尼BIT 的投资保护水平严重偏低,投资者仅有权就征收补偿款额争端提起投资仲裁。在终止过分褫夺东道国正当规制权的老一代BIT 的过程中,印尼顺便单方终止了极为尊重东道国规制权的低标准BIT。二是以历时性视角观之,随着时间迁延而产生的BIT 代际区分也不是影响印尼BIT 终止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印尼BIT 缔结立场有明显的代际特征,但是,印尼所终止的BIT 遍布各个代际。同时,经济考量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例如,印尼何以在是否保留BIT 上对两个首屈一指的外资来源国——中国、新加坡态度不一?
其次,部分印尼BIT 包含了赋予缔约方随时单方终止权的终止条款。印尼BIT 单方终止规则可大体分为两类:默认展期终止、固定期限终止。在前一种情况下,BIT 在缔约双方商定的初始有效期(如10 年)内生效;除非缔约一方利用该初始有效期结束前的窗口期(如至少1 年前)发出终止通知,否则默认续展一个额外的有效期。据此,印尼每隔一定年限才可获得一次单方终止BIT的机会。在后一种情况下,BIT 在缔约双方商定的初始有效期内生效;该有效期届满后,无限期自动续展,但缔约一方可随时向另一方发出终止BIT的通知。对方收到该通知起经过特定时间(通常为1 年)后BIT 终止。考虑到自2014 年以来,印尼在BIT 终止与否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的立场或做法,故固定期限终止条款加剧了印尼BIT 背景下国际保护框架的不稳定性。
(二)保护真空不断扩大
同全球的国际投资保护网络一样,印尼的国际投资保护网络既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也存在保护真空。印尼渐次终止BIT 继而启动日落条款后,其缔结或参加的其他具有BIT 功能的协议并不能无缝补位,导致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真空不断扩大。
首先,新投资及延伸保护期届满的既有投资进入保护真空。未进入保护真空的此类投资只有两种:一是获得印尼BIT 衔接性保护的极少数投资。印尼BIT 中使用弹性用语界定投资国籍的仅为已终止的1992 年印尼—澳大利亚BIT(单独采用“拥有或控制标准”)、现行有效的1992 年印尼—瑞典BIT(单独采用“住所地标准”)。鉴于前一个BIT 日落条款已为两国共同终止,故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新投资和既有投资里,只有住所地设在瑞典的中资企业的那部分可获得衔接性保护。二是获得印尼其他投资协议衔接性保护的部分投资。申言之,依“组建或成立地标准”获得保护的新投资和既有投资,条件是在协议中非印尼缔约方领土内依其法律成立企业、以此类国家企业身份赴印尼投资;依“拥有或控制地标准”获得保护的新投资和既有投资,条件是被其他缔约方投资者所拥有或控制。
其次,日落条款本身被终止情况下的既有投资进入保护真空。通过共同终止的方式,印尼一并终止了与阿根廷、澳大利亚之间的BIT 及其日落条款。根据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4 条(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国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并考察诸国际法院判例及相关仲裁案例可知,该条款确实得因缔约方的一致同意而终止[5]。考虑到共同终止BIT 及其日落条款甚至无需等到BIT 有效期届满,在印尼尚未形成一致的BIT 终止立场或做法的背景下,存在发生更多既有投资直接步入国际保护真空的可能。
(三)保护水平不敷其用
印尼1999 年地方分权法将地方自治确定为国家制度,且规定“中央政府应把除了外交、国防、法院、金融与宗教之外的权力移交给地方政府,并在政治层面进行权力的转移”[6]。由于地方政府的投资治理能力和资源各异、央地之间投资治理权限划分不明确、沟通协调不畅,央地之间及地方政府内部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具体决定经常交叉重叠并发生矛盾。复杂的投资法律环境导致投资者面临的投资法律风险剧增,而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者尤甚[7]。2014 年以前发生的8 个涉印尼投资仲裁案件中,涉地方分权后投资治理困局者占半数之多。例如,Churchill案、Planet 案凸显了地方分权落地实施后地方政府在许可证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①Churchill Mining and Planet Mining Pty Ltd v.Republic of Indonesia,ICSID Case No.ARB/12/40 and 12/14,Award dated 6 December 2016,paras.22–37.;Cemex 案凸显了地方分权落地实施后中央与地方权力移交过程中的监管失控②Cemex Asia Holdings Ltd v.Indonesia,ICSID Case No.ARB/04/3,Award embodying the parties' settlement agreement dated 23 February 2007,pursuant to Arbitration Rule 43(2).;East Kalimantan 案凸显了地方分权后央地之间的投资治理权之争③Government of the Province of East Kalimantan v.PT Kaltim Prima Coal and others,ICSID Case No.ARB/07/3,Award on Jurisdiction dated 28 December 2009.。印尼中央政府其后虽试图通过分级治理的“再集权”方式协调各级政府之间的法律法规,但效果有限,因地方分权后治理不善的投资仲裁案件仍在不断发生④Indian Metals &Ferro Alloys Ltd v.Republic of Indonesia,PCA Case No.2015-40,Award dated 29 March 2019.。
诚然,渐次终止26 个BIT 是印尼改革BIT 体制的前奏,并非抛弃该机制的号角,印尼将在新范本基础上继续缔结BIT及其他投资协议。但是,根据印尼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披露的信息,印尼将在新BIT 范本中严格限制投资仲裁的进攻性[12]。既有BIT 的大量终止及后续缔结的BIT 之投资保护水平大幅降低,导致其无法充分满足地方分权后产生的高企的国际保护需求。
四、日落条款启动后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对策
日落条款启动后,为稳定中资企业在印尼投资的国际保护法律环境,尽可能缩小保护真空,提高投资保护水平,本文认为,应在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采取法律对策。
(一)国家层面的对策
1994 年 中 国—印 尼BIT 于2015 年3 月31 日被单方终止后,两国共同缔结或参加的具有代偿功能或此方面潜力的国际协议目前有二: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2010 年1 月1 日生效);2020 年11 月15 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尚未生效)。中国—印尼之间的国际投资保护机制尚未达到差强人意的水平,唯一现行有效的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不仅保护范围狭窄,而且保护水平很低,比如,甚至未真正赋予投资者以投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鉴此,中国应与印尼乃至包括印尼在内的东盟10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其他成员国展开谈判,完善或新签相关投资保护协议,至少为中资企业以印尼为首个投资目的地的投资提供适当水平的投资保护。
首先,尽快推动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第二次升级。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曾于2015 年进行了第一次升级,但只完善了投资促进和投资便利化条款,未涉及投资保护条款。为稳定中资企业以印尼为首个投资目的地的投资之国际保护机制,提高其保护水平,中国应及时推动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再次升级。对标同样作为“东盟+”协议的2014 年《东盟—印度投资协议》,侧重完善如下两点:第一,扩大协议保护的投资范围,将“拥有或控制标准”纳入“投资”定义,具体措辞可以考虑:“缔约一方投资者根据缔约另一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后者境内拥有或控制的各种资产。”第二,扩大协议所约束的东道国行为范围,将东道国的具体决定、措施囊括其中,具体措辞可考虑:“措施一词是指所采取的,影响投资者和/或投资的,任何法律、法规、规则、程序、行政决定或行政行为。”
其次,及时推动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项下的投资仲裁谈判。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之投资篇章(第10 章)虽属于BIT 类型,但却未包含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根据该协议第10.18 条(工作方案),在尊重缔约各方立场的前提下,缔约各方有义务在该协议生效两年内就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展开谈判,并在开始谈判后的三年内结束谈判。本文认为,为确保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之国际保护机制的稳定性,中国应密切关注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生效后的第10.18 条谈判问题,努力推动投资仲裁条款的最终纳入。考虑到自2014 年以来,印尼继续缔结包含高水平投资保护内容的自由贸易类协议,如2019 年《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且2020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缔约方之间现行有效的BIT 及其他协议大都包含投资仲裁机制,故亦有可能说服印尼及其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成员继续接受投资仲裁机制。
最后,尽早推动双边自由贸易类协议或BIT的商签。2018 年,印尼与新加坡新签了BIT,亦与卡塔尔共同推动了2000 年BIT 之正式生效;2020 年,印尼通过了旨在使2018 年印尼—新加坡BIT 生效的2020 年第97 号总统令,亦与澳大利亚共同推动了2019 年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之正式生效。上述双边性质的自由贸易类协议投资篇章及BIT 均包含投资仲裁机制。可见,对于已与之建立了包含投资仲裁在内的次多边国际保护机制的伙伴国家而言,印尼在继续签订包含投资仲裁机制的双边自由贸易类协议或BIT问题上确有转圜空间。作为排名仅次于新加坡、日本的印尼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国,中国尚未为本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建立起堪与新加坡、日本相媲美的国际保护机制。无论是与新加坡投资者能享受到的2009 年《东盟全面投资协议》项下之保护相比,还是与日本投资者能享受到的2007年《印尼—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议》项下之保护相比,中国投资者根据1994年中国—印尼BIT(已终止)和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所享受到的投资保护水平都明显偏低。为更有效保护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中国应充分考虑和借鉴印尼新近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之间的缔约实践,从双边协议入手,尽早推动双边自由贸易类协议或BIT 的商签,争取此类双边协议能为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提供超出2009 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水平的国际保护。
(二)企业层面的对策
为有效保护其在印尼的投资,中资企业应注意增强国际投资法意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动出击,像税务筹划那样,提前进行国际投资保护方面的筹划。除应购买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外,还应格外注意采取以下国际保护对策。
首先,善用国籍规划。一是采用叠加协议的方式确保投资保护的稳定性、可得性和高水平。能促进投资保护网络的稳定性、可得性的优先选择是自由贸易类协议、次多边协议。不过,此类协议的投资保护水平往往远不及BIT,所以,叠加选择高水平的BIT 效果更佳。二是采用叠加协议的方式重点防范特定投资风险。例如,印尼国内法不能为地方分权后的投资提供充分保护,投资者迫切需要国际投资协议“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保护。因此,未雨绸缪地选择以伊朗、约旦、摩洛哥、卡塔尔、沙特、苏丹、叙利亚、突尼斯等国投资者身份赴印尼投资,不但可享受到1981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议》的稳定保护,还可享受到这些国家与印尼之间的BIT 之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的高水平保护。另外,1981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投资协议》第11 条极为支持成员国间的资本和利润自由转移。因此,采用本文所言的叠加策略亦可有助于投资者应对汇兑限制风险。
其次,必要时申请母国外交保护。对于中资企业已在印尼的投资而言,倘在剩余的延伸保护期届满前未能受到叠加的国际投资协议之保护,即便保护期届满之时或其后立即进行适当的国籍规划,也会导致一些重要的投资争端不能通过投资仲裁机制解决。原因在于,BIT 保护期届满时尚未提交解决的投资争端将失去依据该协议解决的资格;国籍规划前业已产生的投资争端无法通过相关BIT 或具有类似功能的国际投资协议得到解决①See e.g.,Venezuela Holdings BV and others (formerly Mobil Corporation and others) v.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ICSID Case No ARB/07/27,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dated 10 June 2010,paras.193-205.。尽管对于何为“已发生的争端”,不同仲裁庭的观点各异,但是,“试图利用国籍规划解决既有争端的做法乃是滥用程序”[9],已成为投资仲裁庭的主流观点。鉴此,在印尼投资的中资企业在进行国籍规划的同时,需仔细排查与东道国印尼之间的投资争端,对于那些无法借助国籍规划予以解决的已发生争端,应设法通过友好协商、国内诉讼、一般国际商事仲裁等方式予以妥善解决。确实无法解决的重大投资争端,在已经“用尽当地救济”的情况下,必要时可考虑申请母国予以外交保护。
最后,妥善管理争端。一是严格履行投资者的“守法义务”。充分尊重和遵守印尼国内的法律法规,不但是投资者确保其经营顺利、防止产生投资争端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印尼国际投资协议中始终坚持的投资者“守法义务”的必然要求。印尼缔结的类似协议明晰指出,违反东道国法律的投资不受国际保护。2019 年《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第14.21 条(不得提出的索赔请求)第1 款即是如此。二是主动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印尼有关气候①关于气候治理与投资治理之间的冲突,可参见:魏艳茹.国际投资协议视野中的气候治理[J].江西社会科学,2021(9):193–200.、健康、劳工等事宜的法律法规之保护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尚有明显距离,而其国际投资协议大多未提及公司社会责任,或仅设定了软性约束义务②印尼最新缔结的一些投资保护类协议已经开始注意提及投资者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例如,2019年《印尼—澳大利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第14.17条(公司社会责任)便是如此。这类规定仅为缔约国设定义务,且缔约国的义务只限于“鼓励”投资者“自愿”遵守“该缔约方认可或支持的、国际公认的”公司社会责任标准、准则和原则。。但是,投资仲裁实践中最近出现一种默认存在投资者的公司社会责任之趋势[10]。对于违反公司社会责任的投资者,仲裁庭或拒绝行使管辖权,或在受理后裁定投资者败诉。鉴此,中资企业应积极主动践行公司社会责任,此举可使自身成为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进而不容易遭受未经充分补偿的征收、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也不容易与东道国之间产生其他不可调和的投资争端。
结语
在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经济下行、外资流量锐减的低迷形势下,中国对印尼的投资额逆势激增。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矿产等领域。此类投资具有资本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内在不确定性多、社会影响广泛等特点,容易因东道国政府更迭、体制机制改革、排外情绪等种种原因而遭受政治风险,其行稳致远不能仅靠东道国国内法,还需借势适当的国际投资协议,提前披上国际法铠甲,以策万全。在日落条款启动背景下有针对性地从国家、企业层面加强对在印中资企业投资的国际保护,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