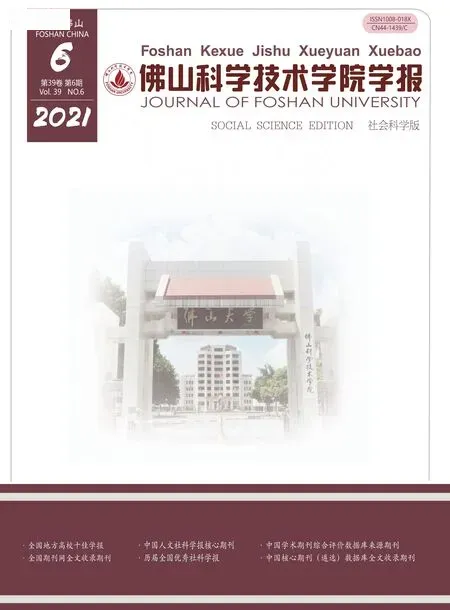弥合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预期技术伦理探索
徐敏睿,胡景谱
(1.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2.东北大学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辽宁 沈阳 110169;3.长沙理工大学 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4)
近年来,荷兰技术哲学界掀起了一股预判性伦理思潮,致力于在新兴技术嵌入社会度较低的时期,以负责任的方式,前瞻性地识别技术风险、伦理问题。预期性伦理探析(ATE)是荷兰学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A.E.Brey)基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理论框架,提出来的实践伦理方法。布瑞主张在技术研发、应用等层级,整合多种预测手段,使预期全方位、立体化,从而发现具有研究价值的伦理问题。预期式技术伦理作为一种前控式实践伦理方法,在新兴技术的设计研发阶段获取经验性描述,对潜在伦理问题、技术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在技术治理阶段,处理评估结果;在技术设计环节,进行反馈和预期责任分配,从而达到以预测结果为导向的防控处理目的[1]。
当前,由于数字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依循了“先应用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使用和适用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需求表达受市场利益影响而被忽视,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信息弱势群体。为此,基于预期技术伦理探析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成因、老年群体数字技术诉求,构建老年群体数字技术的关怀体系,不仅可以回应老年群体需求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数字技术需求,更是可以以科学的理念引领、以科技创新支撑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统筹政府、社会、家庭、市场等主体的合作,构建全责任制的人文关怀体系,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保障老年群体“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2]。
一、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成因分析
当前,数字技术以实时化、泛在化和微型化等特征嵌入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不得不按照数字技术的规则而生活。由于老年群体客观上被数字技术边缘化,“数字鸿沟”问题在这个群体中日益突出。数字信息碎片化、数字传播倾向化、数字受众圈层化等现象,都使得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的交互过程中情感失衡,从“不会用”的行为现象中逐渐衍生出“不想用”的否定情感和“不敢用”的恐惧心理。为此,基于预期性伦理的概念,本文从数字技术的技术层级、使用主体层级与监管层级三个层级进行分析,研判老年群体“数字鸿沟”的成因[3]。
在技术层级上,“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数字技术在研发阶段对老年群体的忽视,是引发数字鸿沟的一个原因。当前,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受流量经济的驱使,将主要目标受众定位为年轻群体[4]。数字技术研发设计阶段未能将老年群体的生理特征、行为习惯及设备使用模式数据纳入设计系统,缺乏针对老年群体特征的建构性评估[5]。当下,适合老年群体的个性化产品较少,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的需求。老年群体选择以信息检索和新闻搜索为主、棋牌娱乐为辅的应用模式表明,数字普惠性福利在老年群体中未能实现有深度的普及[6]。其次,数字技术作为社会—技术的系统成分,创新主体未能对数字技术进行伦理编码和实现价值负载,是产生鸿沟的另一个原因。长久以来,数字技术在设计初期并未被按照用户分类进行预期性建构,因而也没有预测对具体用户的益处与局限,这导致数字技术在监控发现与评估调整的治理阶段呈被动的特征。例如,在数字技术赋能新冠疫情防控时期,“健康码”“行程码”等数字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部分老年群体却因不会使用相应功能而“寸步难行”。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黑箱化发展背后暴露出对特定用户的忽视,这必将损害此群体的现实利益。
在使用主体层级上,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相对偏低,是数字鸿沟形成的原因之一。数字化的现代生活要求技术使用主体养成与之相匹配的素养,其中数字素养主要指“主体合理使用数字技术用以实践的态度和能力”[7]。与青少年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对新兴事物的学习能力相对不足,导致数字素养较低。具体表现在:第一,受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老年群体易对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所延伸的各项功能产生陌生感。第二,老年群体在使用数字技术产品时认知不足,对伴随其产生的风险评估不够。第三,老年群体在对数字信息进行筛选、归纳、分析和利用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认知主体的信息焦虑,通常表现在信息中断、信息超载、信息消化不良等方面[8]。第四,“现阶段,数字技术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所形成的“个性化服务”“沉浸式体验”加剧了老年群体认知偏差的风险[9]。碎片化阅读”“选择性阅读”使认知活动缺乏全面性、多维度的审思,陷入单一性、简单化认知,导致认知主体批判性思维的丧失。第五,数字技术所产生的信息焦虑、认知偏差风险无疑影响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感知易用性。
最后,在监管层级上,数字技术改造升级所对应的监管模式滞后,这是老年群体数字鸿沟形成的又一原因。由于数字技术是异质性聚合体的智能生态系统,包含了多种技术单元,各技术单元的监管系统、数据标准和统计口径各异,这就导致数据管理和社会管理等监管部门协同效应存在短板,处置标准因而也出现交叉、冲突。数字产业主体不明、法律监管滞后、数字产业模式混乱、市场监管乏力、消费者维权困难等一系列难题,是工商管理等传统监管部门与新业态产业的信息化管理尚未形成监管合力的具体表现[10]。与此同时,单兵式、粗放式、分段式监管的传统监管模式尚未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滞后于数字技术新业态的创新需求。监管部门对传统业态在数字化升级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伦理和技术风险,缺乏前瞻性识别、测度和防控,数字环境缺乏具有包容性的预警机制。以“数字金融”“直播带货”等形式为代表的新兴业态的兴起,也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技术风险和复合性的社会伦理争议等伦理问题。由于监管部门对数字创新的监管缺乏技术预期与伦理预期的相互参照,数字环境适老化仍然不足,很难对老年群体形成有效的关怀保障。正是因为监管模式缺乏前控式的价值与伦理原则的预判、没有全面地审查技术风险并及时发现技术对老年群体的伤害,老年群体使用技术时盲目或被动地依赖技术,缺乏对技术批判性审视,容易对技术产生错误的情感认同;在数字技术人机交互领域中,由于传统监管模式尚未更新业态升级所对应的监管经验、监管部门未能准确地对技术伦理问题进行属性识别、相应解决手段失效或力度不足等原因,数字技术对老年群体的隐私权、财产权、知情同意权等权益损益兼而有之。
二、基于预期技术伦理探析老年群体数字技术诉求
预期技术伦理是以技术为中心,将预期与伦理相结合的实践范畴。技术创新主体对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主体诉求上的预期审视,是其对现代技术创新前置性规约的必要前提[11]。多数情况下,老年群体是被动接触数字技术的,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他们的需求、心理特征和实践行为等,都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预期技术伦理在探析老年群体数字技术诉求中的基本要求,是对老年群体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伦理定位和技术心理预判,并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认知能力和社会心理等层面的技术期望,对数字技术的建构提出适应老年群体特征、满足老年群体用户的建议,从而促成数字产品功能的实现。
首先,自主诉求是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意识形态层面的主体性要求。在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老年群体的数字自主诉求可以理解为:在满足其需求的前提下,彰显主体特性。老年群体的数字自主诉求涉及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选择、自由应用及尊严需求等[12]。当前,以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目标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应用和扩张,往往使得老年群体不得不使用数字技术。诚如马克思认为自主性活动是相对异化实践而言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主性发展的手段[13]。老年群体数字自主性的提升,是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自主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基于预期技术伦理的数字技术研发,需探析老年群体的数字自主诉求。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数字自主诉求是对外部数字技术环境提出的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数字技术环境是规约老年群体数字实践的外部因素,同时也为其生存和发展制造了条件。这就决定了老年人数字自主性的彰显,需建立在更具温度与活力的数字环境中。另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数字自主诉求,是老年群体精神需求的呼吁及人文价值的渴望。数字环境更应该满足老年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其次,能力诉求是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实践行为层面的基本要求。老年群体的数字能力诉求包括数字素养的养成与技术能力的建设。一方面,数字素养是认知能力、运用能力与传播能力等能力的综合。数字素养提升的核心在于,帮助老年群体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自主判断的实践精神。通过对数字信息的全面性整理、批判性甄别及利用,老年群体利用数字技术检索、理解、评价信息的能力可以得到提升,从而在数字社会生存、学习及发展。另外,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建设还需根植于文化观念的土壤。文化观念的动态建设有助于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形成,进而帮助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功能定义、语言规则同现实实践经验进行切实地联系。另一方面,老年群体在相关数字技术使用中萌生了诸多技术能力诉求,如信息获取技能、数字交流技能、数字消费技能等能力诉求。老年群体数字技术能力的建设,离不开所处环境的影响。这就需要社区、家庭、以及相关场所形成合力,打造具有数字学习功能与易于实践的外部情景,帮助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更新、充实技能知识,在实践的过程中提高、改善技术能力。
最后,归宿诉求是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理想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愿景。由于老年群体未能在数字产品研发的事前阶段充分参与其中,因此,难以对复杂的数字技术产生信任感与认同感。当前,数字应用市场中针对老年化的数字应对手段未能发挥出情感协同演化的数字技术适老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感官适老”方面,由于数字技术未充分理解老年群体生物特征的触觉变化、听觉变化、视觉变化以及环境信息对老年身体机能的影响,因而难以根据老年群体的信息提供进一步的智能化决策方案和主动式、科学性的情景感知数字服务。二是在“情感适老”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主体缺乏对老年群体情感问题的回应,数字技术缺少“衰老经验”,数字技术在面向用户时,陷入了单一的、简单的应用逻辑,未能根据数据终端分析,总结个体对象特点、结合具体情景分析,未能提出人性化的指导意见、方法路径并提供具体、多样、全面的操作。为此,老年群体因个体差异、文化水平差异、经济收入差异等因素影响而失去良好的数字体验。
三、基于预期技术伦理建构老年群体数字技术的关怀体系
基于预期技术伦理构建老年群体数字技术的关怀体系,要求在技术、社会、家庭等维度回应数字鸿沟的形成,关怀体系的构建要求设计主体与老年群体协商性沟通、映射性对话,嵌入人文关怀创新数字技术,以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实际诉求。
(一)在老年群体数字技术应用的技术层面设置预期关怀
在老年群体数字技术应用的技术层面设置预期关怀,技术创新主体需要在技术设计层级上通过“数字技术预期伦理清单”设置相关标准和要素,将自由、尊严、隐私、知情同意等多方位的伦理价值和原则前置为数字算法原则,用以对技术的开发、维护、控制等主体行为进行哲学指导[14]。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需突破阶段性技术局限,在技术设计层次上建设质量高、真实性强的数字应用,以获得老年群体的情感期望认同。作为技术使用相对保守的老年群体数字用户,在面对“不确定”“不完美”的数字技术时,他们往往表现出拒绝的态度。因此,打破阶段性技术壁垒,便要求数字技术设计团队形成跨学科人才团队,提升对前沿科技产品信息的敏感性,能动整合交叉领域的学科知识,从而促使数字技术产品与不同领域的前沿科技协同发展。在技术应用层面,在内容端上构建以老年群体的需求为导向的数字服务。这就要求数字技术团队开展田野调查,通过深入社区观察和参与的方式,以老年群体在数字应用中“真正需要什么”为特定视角进行研究和建模分析。一方面,网页端口应提供老年群体“感知有趣性”的各类信息,涵盖老年群体的饮食住行、医疗服务、休闲娱乐等方面,提供更高效、更全面的内容服务。另一方面,在操作端,数字系统应围绕老年群体机体特征为考虑目标,增设数字技术的移情关怀机制。技术创新主体应重视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以降低接入障碍的阈值,并设计更具操作便捷性的应用软件、更适浏览的简洁页面以及更适合老年群体视力、生理大小的图文、字体、颜色等[15]。在老年群体数字技术应用的技术层面设置预期关怀,是老年群体与数字环境之间互动而实现自主建构的途径,是增强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掌握,从而在人机交互的实践中显现其主体性地位,进而使数字技术成为老年群体自主能力的一部分。
(二)在社会层面构建具有人本主义考量的监管模式
监管主体应该在社会层面的监管中加入人本主义考量。在数字技术应用模式“适老化”标准体系的设立过程中,监管主体需要通过监管模式规范技术创新过程,使创新主体重视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应用中的获得感、满足感、实用感。具有人本主义考量的监管模式,要求数字技术的创新主体坚持传统社会服务与数字技术创新并行,在产业升级的智能化道路上,兼顾以老年人为代表数字弱势群体的需求。首先,监管模式应落实创新主体责任制,坚持数字创新主体以内容为导向,树立底线思维,以符合公序良俗的内容制作原则,营造友好、文明的数字宜老环境。梳理数字内容各方面的教育元素与思想功能,将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知识普及融入其中,这就要求数字创新主体按照老年群体不同机体特征、文化水平等标准制定相应的“主题”。为此,创新主体应配套创作更具趣味性和生动性的叙事文化作品,利用数字技术丰富且广阔的渠道优势,为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的知识传播注入新动力;在数字软件使用须知、操作说明等多种内容窗口,数字创新主体应明确多类型、多业态的风险差异,设计更具有直观性的数字图文,将风险防控与人性化、个性化的宜老元素相结合,引导老年群体科学识别、有效防控数字技术潜在风险的侵害。其次,监管模式需在社会层面设置数字技术适老体系,建立兼具预警和监管的健康发展机制。监管主体需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统筹安全与发展的角度,将数字技术纳入社会体制机制监管,有力推进数字技术对新兴业态发展,维护绿色健康的市场环境,保证老年群体使用数字技术时的“强环境诉求”。监管主体应该从国家科技战略发展层面上设置预警监管机制,重点对潜在风险进行预防与规避,在数字技术事前管理阶段,监管主体需要开展前瞻性识别与负责任式排查;针对风险信息的获取与预警,在数字技术实时应用阶段,监管主体应注重建构性评估与审思性反馈;针对风险发生的控制与处理,在数字技术事后管理阶段,监管模式应当倡导科学性矫正与柔性重构[16]。
(三)在家庭层面打造具有后喻反哺功能的关怀场域
在新型文化传播承模式中,家庭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应当被打造成具有后喻、反哺功能的人文关怀场域,以营造良好反哺环境和后喻文化氛围。家庭层面的数字文化反哺,可以促使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中深远持久地学习、实践,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在社会活动中的数字困境,从而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17]。数字文化反哺,是年轻群体对老年群体的社会行为潜移默化地动态塑造的过程,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能力的养成[18]。为此,既要建设良好的互动场所、营造良好互动氛围的关怀场域,又要构建知识传播、情感传递、意念传承等功能的反哺文化。首先,反哺行为应当通过亲子间的日常分享、社交感悟,为老年群体提供切实的事例,让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多维度拓展数字技术应用面。其次,老年群体的价值观、行为模式等可以通过反哺文化得到改造、升级。年轻群体在家庭反哺实践中,可以作为老年群体的经验“蓄水池”和“拓展内存”,这有助于消除老年群体在数字技术使用过程中的陌生感与不安全感,引导老年群体感知数字技术有用、易用等技术情感,从而使老年群体形成对数字技术的价值认同。最后,数字文化反哺需拓宽以组织、机构、社区为代表的更广泛、多功能的外家庭化的反哺场域,可以将老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数字技术培训与社区园区建设相结合。外家庭化的反哺场域可以设立互联网知识墙,定期更新计算机应用知识及文明上网、安全防控为主题的板报园地。社区聚集群可以被布置成具有数字技术功能的老年活动中心,满足老年群体的数字技术需求,形成有效协助数字反哺的代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