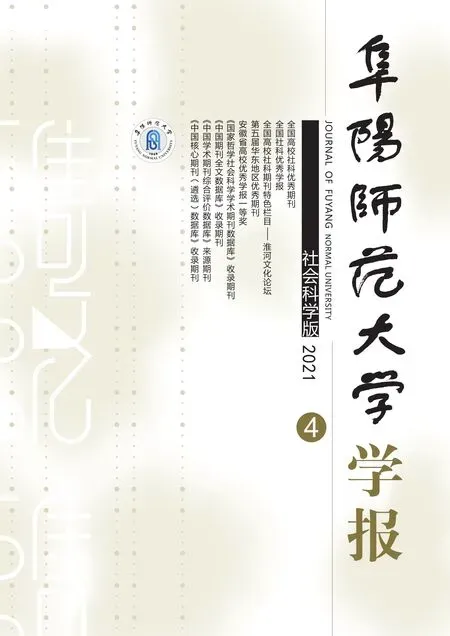《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良宝
《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张良宝
(淮南师范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淮南子》是西汉皇族刘安召集宾客集体撰写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全书共二十一篇,涉及天地万物、治国理政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关于音乐表演思想的论述系统而全面。《淮南子》在强调音乐表演技术训练必要性的同时,尤其强调表演者内在认知与意识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中有本主,以定清浊”“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另外,《淮南子》深刻阐述了“服习积惯”之于音乐表演技巧获得的重要性。这些见解闪烁着深刻的艺术哲思,对于当今的音乐表演理论建设以及音乐实践训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与借鉴意义。
《淮南子》;音乐表演;本主论; 得道论;至情论;技巧论
《淮南子》是一部集汉初黄老思想之大成的学术著作,由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招天下数千方术之士集体撰写而成,全书共二十一篇,广涉天地万物、治国理政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宋代高似孙称刘安为“天下奇才”,赞美《淮南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1]1;胡适称《淮南子》为“绝代奇书”“集道家之大成”;梁启超称“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中著述第一流也”[1]2。在《淮南子》博奥深宏的论说中,涉及音乐表演的文字散布于各个章节,其中篇幅最多的是强调音乐表演要“中有本主,以定清浊”,要“得其君形”,要“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音乐表演内、外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音乐表演的核心要义,本文先集中对《淮南子》关于音乐表演理论进行梳理分析,然后结合现代音乐表演的实际需求,阐释《淮南子》中音乐表演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淮南子》中的音乐表演理论
《淮南子》从本主、得道、情感、技艺等四个方面来阐述音乐表演理论,通过梳理,将其概括为“本主”论、“得道”论、至情论和技艺论,下面分而述之。
(一)“本主”论
在古汉语中,“本”是指示字,从木,“一”标明树根的位置,意指基础和根本;主,即事物的本质与核心。本主,即要把握事物的根本与核心。《淮南子·汜论训》云:
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2]735
“中有本主,以定清浊”,就是表演者在表演的整个过程中,内心始终要有明确的物象和意旨。“清”是形声字,本义为水清,而在用来描述声音时,用作形容词,意思是响亮、清越;“浊”,用来描述声音时,为形容词,意为声音低沉。《淮南子》对“清浊”设定的前提是“中有本主”,即“本主”是声音“清浊”之核心。意思是说,演唱者如果不熟稔音律,不参透音乐的内在机理,那么,他就无法触及音乐的本质,就不能真正领略音乐的精妙。如果歌者歌唱低沉的声音时沉郁而缺乏光泽,唱清越的高音时则生涩而尖利、刺耳而缺乏歌唱性,至多是完成了形式上的歌唱,而不能称之为艺术性歌唱。韩国的韩娥、秦国的秦青和薛谈、上古时期的侯同、曼声等歌者的歌唱之所以发声与音律相谐共振,能够与听者直接产生共鸣,就是因为他们不仅熟谙音律,体悟到了音乐的根本,而且能够根据表现的需要来确定音的高低变化与轻重缓急,自由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善歌者必须通晓音律,深悟音乐肌理,畅达事物根本,只有做到“中有本主”,方能做到演唱游刃有余。
不仅声乐演唱要“中有本主,以定清浊”,对于器乐表演,《淮南子》也同样提出了“音有本,主于中”的要求。《淮南子·汜论训》云:
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彠之所周者也。[2]720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著名琴师,演奏技艺精湛。当他在演奏瑟时,将手施加于瑟柱之上,在上下推送移动的过程中,演奏没有一个音不符合音律。《淮南子》认为,音乐表演中的声音溢出蔓延实乃内心的“本主”使然。由此可见,在音乐表演中,通达礼乐之道,做到“音有本,主于中”,这同演唱中“中有本主,以定清浊”的要求并无二致。
(二)“得道”论
《淮南子》集先秦及汉初道家思想之大成,继承并发展了老庄的道家思想。在音乐表演方面,《淮南子》重视音乐表演中“内”与“外”的接通关系,要求音乐表演要“得道”。《淮南子》关于音乐表演的“得道论”有三种表述方式,即“得其道”“知音”和“得君形”。
第一,“得其道”。
《淮南子》在肯定技巧对于音乐表演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强调技术的目标指向。《淮南子·诠言训》云:
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2]800
《淮南子》强调,艺术表现的价值体现在表演者能够洞察掌握事物本质,体悟声音之道,技术仅为达成艺术表现之道的手段,技巧应服务并服从于艺术表现。《淮南子·缪称训》云:
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于其美者也。金石丝竹,助而奏之,犹未足以至于极也。[2]548
《淮南子》认为,如果歌唱者在演唱中仅仅着力声音本身的修饰,而没有对音乐本体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体悟,那么这种声音不可能给人以真正的美感。即便是加上金钟、石磬、丝竹、弦管等乐器伴奏而加以润饰,也不可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只有真正体悟音乐之道,才能实现“足以至于极也”的真实美感。可见,音乐表演“得道”,尤为重要。
第二,“知音”。《淮南子·脩务训》云:
夫以徵为羽,非絃之罪。
邯郸师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后知其非也,而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2]1155
演奏中把徵音当作羽音,无论如何都不应当是琴弦自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演奏者根本不懂音乐之道。邯郸的乐师创作了一首新的音乐作品,但假托为著名作曲家李奇所作,于是众人争相研习之。而当后来得知这首作品不是李奇所作时,大家便都将乐谱丢弃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状况,是因为这些人并不真正懂得音乐创作的基本道理,对作曲家李奇的音乐创作风格也缺乏基本的认知。《淮南子》在此强调研习音乐本体,静心悟道,掌握作曲家的艺术创作特征对于“知音”的重要性。
第三,“得君形”。《淮南子·览冥训》云:
昔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已而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为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精神形于内,而外諭哀于人心,此不传之道。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为人笑。[2]307
“君”者,主宰也;“君形者”,即至精主宰形体,意思是把握作品的内在本质。对于雍门子“陈辞通意”“抚心发声”,孟尝君泪流满面而不能自制,很显然,是因为雍门子的歌声与言辞中所表达出来的哀怨之情触动了他,精诚形成于雍门子的内心,歌声和言辞只是其表达哀怨情感的载体,这绝非是通过口耳相传就能得到的,此论与下文的至情论也密切相关。《淮南子·说林训》云:
使但吹竽,使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2]988
《淮南子》认为,如果让一个并不会吹竽的人吹竽,而让一个会吹竽的人为之按孔,尽管节奏整齐划一,但若要获得美的音乐效果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使但吹竽,使工厌窍”的演奏“无其君形者也”,其演奏纯属形式表达而已,根本无法表达作品的真情实感,也找寻不到精神的主宰。
(三)至情论
“情”属于心理学范畴,它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表演领域中的重要内容,是人们在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中对人或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价值判断。《淮南子》主张情因感生、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主张在音乐表演中要追求文情理通。
《淮南子》首先强调音乐表演效果来源于内在的情感,《脩务训》云:
夫歌者,乐之徴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2]1129
《淮南子》认为,耳目与物接而心志知忧乐,情感表现是人与外物接通后所引起主体内心真实的自然外露,是人的“感于物而后动”,情感与物接才有可能通达庄子所说的“道”。
其次,《淮南子》主张音乐表演要“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齐俗训》云:
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熟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2]581-582
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歌唱源于快乐,哭泣源于哀伤,二者都是内心感情激荡的结果。《淮南子》将“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作为情感流露的自然法则,强调情感的表达路径是由内向外,不管是“乐”的情绪抒发,还是“悲”情感的表达,都必然存在着内与外的互通关系,《淮南子》意在强调内心真实的感受对于形式上自然恰切表达的指向性意义。
再次,《淮南子》主张音乐表演要有“根心”,并要“文情理通”。《淮南子》倡导生命的主体意识和文艺作品应该表现自然而真实的性情,并强调,歌舞表演,都须建立在“根心”的基础上真实自然的艺术表现。《诠言训》云: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可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2]827
《淮南子》认为,不管是从事歌唱艺术还是从事舞蹈表演,都不能简单追求外在的形式,而应该具有建立在牢固生活沉淀和情感积累的“根心”,如果是为唱而唱,歌声不可能感动别人;为舞而舞者,其舞姿不可能曼妙。因此,任何从事艺术表演的人在任何时候,其内心都不能缺失艺术表现的根由和内心的本然情感。这些论述与前文的“本主论”“得道论”都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淮南子》深刻地揭示了音乐表演中的“声”与“情”的关系,要求歌唱者在表演中要追求音乐情感的自然流露,要使人通过艺术欣赏得到美的享受。另外,《主术训》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缪称训》有“情系于中,行形于外”的论述,阐明音乐表演要从内心发出,情感表现要“文情理通”:
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壅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所能为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2]552
《淮南子》的“至情论”是建立在对音乐内容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而展开的,强调音乐表演者对于音乐“道”“根”“情”的认知与体悟,强调音乐表演中的“内”与“外”的接通,音乐表演者应该听从内心,在表演时要达到“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的艺术效果。《淮南子》关于音乐表演的“得道论”与“本主论”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得道”也就是“中有本主”,因此也就可以推出“得其道”方可“定清浊”。
(四)技艺论:“服习积贯”“淹浸渍渐靡”
任何表演都须具备相应的技术系统,技巧越高,表演的质量越高。如果说,“中有本主”是决定音乐表演质量与效果的关键,那么,表演技巧就是“以定清浊”的前提与手段。《淮南子》认为技巧是音乐表演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并强调技术训练要“服习积贯”。“服习”,即熟习,“积贯”,即积久而形成习惯,“服习积贯”即经过长期练习而熟能生巧,从而形成建立在“本主”基础上的行为习惯。《脩务训》云:
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黑白,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摽拂,手若薎蒙,不失一弦。使未尝鼓琴者,虽有离朱之明,攫掇之捷,犹不能屈伸其指,何则?服习积贯之所致。[2]1143-1144
盲者无法分辨白天与黑夜,也无法分辨黑色与白色,但弹琴抚弦,运用参弹复徽等手法,指法娴熟,伸缩自如,不错一弦。对于未曾习琴者,即便拥有离朱那样明亮的双眼,攫掇那样敏捷的手指,演奏中也做不到伸缩自由,这是因为没有经过长期积累而养成习惯。《淮南子》强调,音乐表演需要技巧,技巧的掌握不仅得益于丰富的知识积累,更来自于在长期的科学训练,强调技术学习要自立自强、刻苦勤奋,最终达到“服习积贯”,同时阐明“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的习艺道理。不仅如此,《淮南子》还对技艺训练理论推而论之,认为舞蹈、杂技等舞台表演艺术都必须要以精湛的技艺作为基础与保证,精湛的技艺都必须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脩务训》云:
今鼓舞者,绕身若环,曾挠摩地,扶旋猗那,动容转曲,便媚拟神,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驰骋若鹜。木熙者,举梧檟,据句枉,猿自纵,好茂叶,龙夭矫,燕枝拘,援丰条,舞扶疏,龙从鸟集,搏援攫肆,薎蒙踊跃,且夫观者莫不为之损心酸足。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夫鼓舞者非柔纵,而木熙者非眇劲,淹浸渍渐靡使然也。[2]1162
杂技表演者并非生来就敏捷强健,舞蹈表演者并非天生就柔弱委纵,他们精妙的技艺来源于渐进式教化与持久的磨练。同样,音乐表演具有不断发展的技术体系,《淮南子》阐明了表演技术训练要经过“淹浸渍渐靡”、不断积累的基本道理。
二、《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的当代价值
琵琶演奏家、教育家刘德海先生在其《凿河篇》中指出:“每位音乐家在奏乐前,皆须从三个方面进行构思:用什么样的情感去宣扬什么样理念;用什么样音响去抒发什么样情感;用什么样技法制造什么样音响。”并说:“‘技差’,而无‘情理’,为劣之劣者;‘技佳’而无‘情理’,为匠之劣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而技术又是以副之,为‘优’之优者。”[3]19刘德海先生关于音乐表演中情感、理念、技法的思想主张,概括了音乐表演体系的整体构建过程,可谓鞭辟入里,这一表述对于任何音乐表演学科都具有绝对性的指导意义。但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赋予中原大地独特遗传密码和民族基因的著作《淮南子》,就已经对音乐表演理论作出精辟阐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刘德海先生关于音乐表演的主张应该是《淮南子》关于音乐表演理论的现代表达。
(一)“服习积贯”“淹浸渍渐靡”,理应成为掌握音乐表演技术的基本途径
音乐表演中的技巧是演绎音乐作品的技术总和,是作品价值实现的载体,也是音乐表演者传达自己精神意志的重要手段。《淮南子》通过描述“盲者”高超的演奏技艺,来说明“服习积贯”对于技艺形成的重要作用;通过对“鼓舞者”的“身若秋药被风,发若结旌,驰骋若鹜”,观者莫不为“木熙者”损心酸足的描述,阐明舞蹈技术的获得是“淹浸渍渐靡使然也”。《淮南子》强调音乐技巧对于音乐表演的重要性,这对于当下的音乐表演艺术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刘德海在《凿河篇》中提出“学求深、艺求绝”的主张,要求表演者要努力做到“技术全面、身怀绝技”[3]17;声乐教育家栾峰认为:“要‘养成’一位优秀的男高音,特别是美声唱法的男高音,除了近10年的技术训练之外,还要辅以作品的熏陶、语言的完善等条件,要‘细火慢炖’。”[4]A4声乐技术训练如同树木的生长,“莫见其益,有时而修”,也如石磨的损减,“莫见其损,有时而薄”[2]1162。
乐器演奏技术的训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劳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演奏器官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自动化”[5]220。如今,有很多具有较高音乐天赋的音乐表演者,经常在运用综合性或高难度技巧的时候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或力不从心。原因在于表演者缺乏规范、扎实而系统的技巧训练,也缺乏对技术与艺术关系的深入理解。约瑟夫·霍夫曼认为:“艺术上的自由需要有充分运用技巧的能力,钢琴家随时可以支付的艺术存款就是技巧。金钱对于一个上流人物只不过是一种相当有用的身外之物,技巧却是钢琴家必须的装备。”[6]293由此可见,表演技巧对于音乐表演过程的实现的重要性。为山九仞,非一日之功。“服习积贯”“淹浸渍渐靡”,正是实现演奏器官自动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说,《淮南子》对于音乐表演技术训练的主张,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丰富了中国音乐表演美学理论,尤其对当今的音乐表演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
(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理应成为音乐表演艺术的根本标准
古往今来的文艺作品都十分重视情感的抒发,因此,“至情”,应该是文艺创作与舞台呈现的根本要求。“情就是指真实、本质的东西。”[7]17这一观点来源于庄子对于“情”与“道”关系的认识。庄子认为,“情”与“道”具有相通的属性,是一种可得而不可见、可传而不可授的内在性存在。“音乐艺术就其特性来说,是一种善于表情的艺术,音乐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作为第二度创造的音乐表演,它的最重要的艺术使命之一,就是深刻揭示和完美再现音乐作品中的情感内涵。”[8]96-97两千多年前的《淮南子》就已经对音乐表演中的情感表现问题有全面而深刻的阐述。《淮南子》强调音乐表演者在实践中对“情”“道”“根”“质”要有透彻领悟,表演要“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要“内”“外”接通,《淮南子》的这些主张对于当今的音乐表演实践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戏曲理论家李渔在其所著《闲情偶寄》中说:“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节也。解明情节,知其意之所在,则唱出口时,俨然此种神情。问者是问,答者是答,悲者黯然消魂而不致反有喜色,欢者怡然自得而不见稍有瘁容,且其声音齿颊之间,各种俱有分别,此所谓曲情是也。”[9]345李渔指出“唱曲宜有曲情”,并阐述了戏曲唱腔如何“投情”。实际上,持“情感论”者均重视音乐表演对情感的领悟与传达的准确性。声情并茂是中国传统唱论基本的美学法则与评价标准,认为:“情为声之本,声为情之形,声是情的外在的物象、条件和手段;而情以驭声,声以抒情。”理解作品内涵、把握作品风格、富有情感表现,依然是当代音乐表演评价的重要标准。可以这样说,后人对于音乐表演中“投情”的理论,都是对《淮南子》“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的诠释与延伸。
当前,很多器乐演奏者具备娴熟的演奏技术,但缺乏对音乐机理的深刻探察,演奏缺少打动人心的力量。近年来,尽管我国屡有学子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在技术功底上,我们毫不逊色,但对于作品风格的把握,对作品中内蕴的掌控却明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音乐的真正表现。约瑟夫·霍夫曼说过:“我们衡量一个艺术家的价值不是凭他的技巧,而是要看他如何运用技巧。”[6]293在第5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中,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音乐学院的中国学生谭雅冰获得了“帕格尼尼小提琴随想曲最佳诠释奖”,她的指导老师美岛丽在技术上要求严格,在音乐上要求更高,她说:“真正成功的炫技作品,是要让听众忘却或者感受不到技巧,让他们感受到的应该是它给人所带来的情感,包括激动、兴奋、悲伤以及更多能触碰到听众和演奏者最内心深处的情感。”[10]B3享誉国际乐坛的当代钢琴作品演绎大家、俄罗斯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鲍里斯·贝尔曼说过:“很多人在学钢琴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先学技巧,而后在慢慢练习钢琴的投入。我认为这个练习顺序是错误的。对于音乐作品的理解,特别是对于作品中情感部分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我们在弹琴时对于技巧的应用。比如在抒情部分的段落,需要轻巧的、温柔的弹奏,如果没有对于作品情感方面的正确理解,就会影响到弹奏者在触键、和声和音色等方面的控制。同样对于比较清冽的感情投入,感情方面的投入仅仅通过机械的技巧是远远达不到的。”[11]贝尔曼强调音乐表演中“投情”的观点同《淮南子》一样,音乐表演技巧指向必须与艺术情感指向完全一致。
真正的音乐表演就是把技术训练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动作意识与感情心理及时整合、加工与完善,让手中之弦、嗓中之音与情感体悟紧密协调,达成融合,达到情动音发、音中孕情、音情相依,恰如身体与精神之不可分离的理想境界。“音乐表演中的投情,应该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做到呼之即出,挥之即去,以达到挥洒自如、变化有序的境界。”[8]96-97从而实现《淮南子》所提出的“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的表演要求。
(三)“中有本主,以定清浊”,理应成为音乐表演的恒远追求
《淮南子》不仅重视音乐表演中“道”的核心地位,同时重视“伎”对于音乐表演的支撑作用。在当下的音乐表演领域,存在重“道”轻“技”或重“神”轻“形”的不良倾向,因此,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态与浮躁的心理,抗拒追求功利的诱惑,秉持“工匠精神”,扎实苦练基本功,研究表演技术规范与技术要求,培养专注与坚持的精神,坚持科学渐进的训练方法,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是器乐表演技能学习的正确法则;音乐表演者不仅要具备精湛的技巧、敏锐的音乐判断力,还要懂得音律法则,通达礼乐之道。《淮南子》“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的思想,一语道破了音乐表演中技巧与音乐之间的辩证关系。音乐表演者能够自由驾驭技巧,游刃有余地表达自我,正是《淮南子》所期许的艺术境界,正所谓:“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倘用现代音乐表演理论来解释,“本主”不仅是作曲家运用诸如音符、休止符、力度、速度等纯粹的物质手段,在其作品中蕴藏了其整个幻想的世界,也是表演者在音乐的自为自在中所领悟到的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理内容。表演者的责任就在于:“从这些物质的材料中提取精神的实质,并把它传达给听众……要把个人成熟的概念传达给自己的听众,需要高度的技术技巧,而这些技巧,又必须在意志的绝对控制之下。”[12]34-35同时,对于外在的干扰和影响有坚定的抵抗力和约束力,从而形成自己的歌唱风格而自成一家。正如杨易禾所言:“音乐表演者是先于他的听众听见作品的人。”[13]30音乐表演者的首要任务是在内心听觉中建构具有自律性标准的声响,实现这种自律性标准音响的过程应该就是《淮南子》所说的“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
在进行声乐表演的过程中,能运用正确的声音处理方法,充分发挥表现主体的精神自觉性,并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2005年,帕瓦罗蒂在上海大舞台举办告别巡演时被问及演出唱不唱“高音C”时,他反问道:“很多人总把我的名字和高音C联系在一起。这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它只是一名男高音的技巧之一,却不是终极目标。”[14]帕瓦罗蒂一语道破了演唱技巧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关系。在诠释音乐中:“出色的表演技巧与完美的艺术表现在音乐表演中是相辅相成、互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没有表演技巧根本谈不上艺术表现,脱离了艺术表现,表演技巧也将失去它自身的存在价值。”[15]15“音乐表演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表演艺术家生命体验的外化过程。”“不论是音乐艺术范式的存在和生成,音乐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征服,还是音乐演奏技巧的种种操作,都蕴含着音乐表演艺术家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丰富的心理内容。”[16]69
在现实器乐教学中,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技术与音乐分割开来,“常常把技术作为硬指标,而把音乐看做软指标;缺乏音乐可以容忍,而对技术上的错误却十分敏感;技术训练是主动的,有条有理的,而音乐上的要求则是自发的,被动的,有时音乐充其量不过是被当做味精了花椒面罢了”[6]296。在音乐会上人们常常惊叹于孩子们“高超”的演奏技巧,但很难为他们的音乐所感动,原因在于,人们感受不到他们对音乐的真实理解与表现。音乐表演的技术固然重要,但需注意的是:“对于音乐表演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具有把学到的基本技术灵活地运用于艺术表现的能力,或者说是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基本技术的能力,这才是音乐表演技巧的真义所在。”[15]194前苏联钢琴家涅高兹指出:“目的(内容、音乐、表演的尽善尽美)愈是清楚,它就愈能确切地指明达到它的手段。”[17]2卓越的演奏技巧只有和深刻的艺术表现完美结合才能实现音乐作品精神内涵的全面展示。肖邦“练习曲”和“谐谑曲”是肖邦人为添加的标题,我们在分析与演奏时不应该照字面来理解,因为这两种体裁的作品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因此,在练习曲的阐释里,高难度和复杂的技术手法不应该成为目的本身。”[18]18练习曲技术训练自有其特定的目标指向性。随着现代音乐教育的正规化与系统化,具有高超表演技巧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真正能够恰当且创造性地运用技巧,最终成为表演艺术家的却寥寥无几。很多表演者以炫耀技巧为目的,这样的演奏因为缺乏深刻的艺术表现而最终成为一名音乐匠人。正如海菲兹所言:“那些把好的提琴家和伟大的提琴家区别开来的东西一定是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19]
音乐始于人类情感宣泄的本能,同时储存于求真的童心里。从事艺术教育的人,应该以科学求真的态度,注重开发学生的艺术直觉,培育学生的艺术自觉,发挥学生的艺术潜能,引导学生用真心感受体验音乐,呵护孩子们的本能和童心,培养真正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鲁宾斯坦说:“在你的手指触键之前,你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开始演奏这首乐曲,就是说,你必须在脑子里确定速度、触键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在你真正开始弹奏之前想好头几个音符的演奏法。再说,这首乐曲的特征是什么?是戏剧性的、悲剧性的、抒情的、浪漫的、幽默的,英雄般的、崇高的、神秘的?”[12]9技巧是音乐表演的组成部分,是艺术的行为载体和实际体现,但技术一定要有目的性与指向性。关键在于,人们在运用技巧实施艺术表现中,内心有无“主”、有无“道”、有无“根心”、有无对作曲家创作中所产生的内心期待。因此,在音乐文化繁荣发展的当下,深入研究《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加强音乐表演学科建设,都具有非常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结语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人们对音乐表演艺术的体认与研究更加科学,理念更加先进,方法更加多元。表面看来,《淮南子》的音乐表演理念已经成为远古的历史,与当代丰富的音乐表演理论相比,《淮南子》中的音乐表演思想可能看起来较为肤浅,但是,《淮南子》中关于音乐表演的“中有本主,以定清浊”“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音乐表演技巧训练要“服习积贯”“淹浸渍渐靡”以及“不得其道,伎艺虽多,未有益也”的音乐表演思想揭示了音乐表演的本质与核心要义,永远闪耀着智慧的光辉,并将源源不断地为当今的音乐表演者提供智慧的滋养,指导着当代音乐表演实践。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20]108中国古代音乐表演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的内容之一,凝聚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而成的智慧、神采和气韵,为当代音乐文化发展提供了汲取丰厚营养的巨大宝库。
历史表明,《淮南子》中丰富的音乐表演理论和思想,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和思想文化遗产,对建设当代中国音乐表演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艺术智慧,我们甚或可以说,《淮南子》中的音乐表演理论是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表演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如今,我们无论是在表演的实践中或者是进行音乐表演理论研究,既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继承《淮南子》音乐表演理论的智慧,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态度发展《淮南子》的音乐表演思想。“本主论”“得道论”“至情论”和“技巧论”,这些完全产生于艺术实践而带有丰富而朴素的音乐表演意识,是中国音乐表演理论的集中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好包括《淮南子》在内的中国古代音乐表演故事,挖掘、研究、阐发其中的音乐表演机制原理,唤起对中华音乐文化的认同和热忱,应当引起音乐表演与教育从业人员的高度重视,也理应成为从事音乐表演与研究事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音乐表演理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陈广忠.淮南子斠诠:上册[M].合肥:黄山书社,2008.
[2]淮南子[M].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3]刘德海.凿河篇[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1).
[4]陈茴茴.男高音高音之后路还长[N].音乐周报,2015-03-18(4).
[5]根·莫·齐平.音乐演奏艺术——理论与实践[M].焦东建,董茉莉,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6]王朝刚.器乐表演技能教学新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
[7]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8]张前.音乐欣赏、表演与创作心理分析[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9]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所.中国古代乐论选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10]徐丽梅.帕格尼尼:“忘记技巧”.你就成功了[N].音乐周报,2015-04-29(3).
[11]紫薇.鲍里斯·贝尔曼:音符是死的,表演是活的[N].音乐周报,2014-09-17(4).
[12]约·霍夫曼.论钢琴演奏[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
[13]杨易禾.《意念》与音乐表演美学[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8(4).
[14]徐璐明.男主角能否驾驭9个高音C[N].文汇报,2017- 05-9(10).
[15]张前.音乐表演艺术论稿[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16]冯效刚.对音乐表演若干心理问题的研究[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4(4).
[17]Γ·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M].汪启璋,吴佩华,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18]雷吉娜·斯门江卡.如何演奏肖邦[M].梁全炳,姚曼华,译.于润洋,审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19]海菲兹是怎么样学小提琴的. https://tieba.baidu. com/p/842542979?red-tag=0706979820.
[2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Theory of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ZHANG Liang-bao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is an encyclopedic work written by Liu An,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book consists of 21 chapters, covering all aspects of the universe, state governance and human society. Among them, the discussion on musical performance thought is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musical performance training, and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of performers’ inner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many tricks without their own way, but they are not beneficial”, “there are original masters in the music, so as to calm down the turbidity”, “emotion comes from the middle, while sound should come from the outside”. In addition,profoundly elabo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abit of obedience and accumula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musical performance skills. These insights shine with profound artistic philosophy and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our current music performance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training.
; musical performance; affection theory; skills theory
J605
A
2096-9333(2021)04-0025-07
2021-06-10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基于跨界融通理念下的普通高校音乐专业科学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018jyxm1199);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精品线下课程“合唱与指挥”(2020kfkc490)。
张良宝(1969— ),男,淮南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史论、音乐美学。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1.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