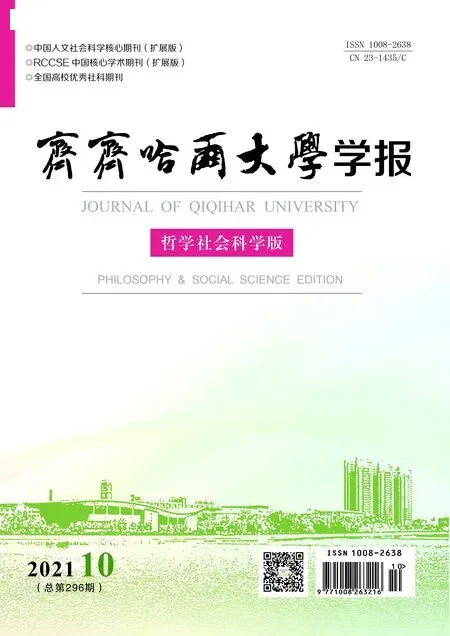论朝鲜朝末期文人金泽荣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杨会敏
(宿迁学院 中文系,江苏 宿迁 223800)
金泽荣(1850-1927)与姜玮(1820-1884)、李建昌(1852-1898)、黄玹(1855-1910)被誉为朝鲜朝末期文章四大家,其诗文创作及文学思想在中韩文坛都颇具影响力。而韩愈则为中唐时期开拓新诗风、倡导新文风的主将之一。金泽荣曾在《自志(庚申)》中明确道出自己的诗文创作渊源:“于文好太史公、韩昌黎、苏东坡,下至归震川,于诗好李白、杜甫、昌黎、东坡,下至王士正(笔者注:应为王士祯)”,[1]407韩愈是其中唯一的一位诗文皆受金泽荣推崇的唐代文人。本文拟从比较文学渊源学的角度对金泽荣诗文创作所受到的韩愈诗文的影响渊源进行实证性的考察与研究,以期从接受的历史文化语境、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全面梳理两者诗歌的内在关联,并进一步探究金泽荣汉诗宗尚韩愈在朝鲜古代汉诗文史上的诗学意义。
一、朝鲜古代文坛接受韩愈诗歌的背景和历史进程
虽然迄今为止中韩学界无法从现有文献资料确证韩愈诗文传入朝鲜的时间,但大都推断韩愈文集可能在以诗赋取士的光宗年间已被引入,且在高丽高宗(1214-1259)时期已被翰林学士们广泛阅读。最迟至高丽中期,韩愈诗文已被文人作为典范。至高丽中后期,被誉为朝鲜汉诗三大诗人的李奎报在《吴先生德全哀词(并序)》中曾言:“为诗文,得韩杜体,虽牛童走卒,无有不知名者”,[2]83这一评价极具代表性。虽然高丽中后期的朝鲜汉诗已由宗唐转为宗宋,全面开启了学习“苏黄”的时代,以李奎报、李齐贤及活跃于明宗朝(1171-1197)的朝鲜第一个汉诗流派“海左七贤”为卓越代表。但诗名最盛的李奎报在评价“海左七贤”之一的吴世才时,却再次强调“韩杜”诗文的典范地位,对于当时学苏、黄流于形式主义的弊端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而高丽中后期长达百余年武人执政的时代背景以及前代、当代重文轻质的文风共同促成了文人们接受韩愈诗文的这一思想导向。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年爆发的以郑仲夫为首的武臣之乱及随之而来的长达百余年的武臣执政,促进了海左七贤、李奎报、李齐贤、陈澕等新一代诗人的崛起,他们引领了这一时期诗风、文风流变的主要走向。面对遽变的国运和时势,面对自身由安逸闲适的政治上层被抛入到仕途坎坷、被边缘化的社会下层的悲剧命运,他们不仅开始反思和批判前代诗风,特别是占据诗坛长达200年的浮靡雕琢的宫廷诗风,也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愈演愈烈的注重雕章琢句、苦练形式技巧的科诗之风,那么,主张文道合一、经世致用的韩愈备受推崇自然合乎情理。
相对于韩愈文章在朝鲜朝典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韩愈诗歌在朝鲜朝的地位有所下降,由高丽时期至朝鲜前期韩诗与李杜并称,降到朝鲜中期勉强与杜诗并提,再降至朝鲜后期不及李杜,具有代表性的评介如下:“近世学诗者,或以韩诗为基,杜诗为范……不妨与杜诗并看”(李植《学诗准的》),[3]517“宋人尚韩诗,多以为胜于李杜,故其弊至此”(金万重《西浦漫笔》),[4]2259“韩退之一生慕效李杜,然比诸李风神不足,比诸杜气骨不足”(李瀷《星湖僿说》)。[5]3831即使如此,在朝鲜朝前期以宗宋为主、中后期唐宋兼宗的汉诗坛,韩愈诗歌仍被作为仅次于李杜诗的重要艺术渊源。
二、朝鲜历史文化语境中金泽荣对韩愈诗歌的接受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韩愈在继盛唐李杜后另辟蹊径,着力古诗,风格以雄奇高古、奇险怪异著称,与其友人孟郊等人的“韩孟诗派”影响深远,堪称中唐诗歌开拓新变的领军人物。其诗歌擅长写愤世嫉俗之心态,在行文体制上“以文为诗”,以议论见长,与杜甫一起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由唐入宋的两位先驱人物,由此可见韩愈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朝英祖、正祖以后,随着性理学统治的松动、党争的缓和,以及以实学派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兴起发展,宗尚宋诗的道学派主导诗坛之局面被打破,由此才出现唐宋兼宗的多元化诗风,而处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金泽荣对引领变唐入宋的韩愈诗歌的接受在朝鲜汉诗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一)追摹韩愈雄健奇崛之风
韩愈以雄健奇崛的主体诗风兀立于唐代诗坛,而这种豪迈刚劲、雄奇险怪的诗学追求在诗句中多有体现,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醉赠张秘书》)[6]29等。且这一诗学倾向不仅仅指语言的奇崛劲健,还应包括意境架构、用词造句、韵律格调、气势情感等多位一体的内涵,正如韩愈本人所强调“才豪气猛易语言”(《赠崔立之评事》)。[6]61此外,韩愈也努力践行自己的这一诗歌主张,他以文入诗,力去陈言,押险韵,用拗体,善铺陈,用生僻字,其诗歌雄浑壮大,意境幽邃,奇崛险怪,如《南山诗》《石鼓歌》《山石》诸作。
朝鲜古代诗评家尤为称赏韩愈雄健奇崛的诗风,“昌黎之雄肆,杜牧之粗豪,长吉之诡……然唐之诗体,至是大变矣”(李睟光《芝峰类说》),[7]1086他们还进一步以比较的眼光分析韩愈主体诗风的成因:
文章以气韵为主。……韩退之诗世谓“押韵之文”耳,然自有一种气韵。(佚名《诗文清话》)[8]2077
又如韩退之,笔力往往有冗卑下乘之语,然细详之,非退之之不及,乃故为此延绵气脉,以待激昂奋发。比如山势逶迤,峻必有低,过峡则陡巘,天秀自露。不然只剑脊鳝走,不与化工相肖也。如是看,方得退之圈套。(李瀷《星湖僿说·诗文门》)[5]3803
《洪范》:“唯孟子得其气而善养者,塞于天地之间,则是百世而一人也。孟子后,唯韩退之“何以验高明,柔中有刚大”者近之。而至如孟东野“壮志性刚决,火中见石裂”,则是直性燥暴者也,非所谓刚也。(南羲采《龟礀诗话》)[9]7368
宋张戒云:柳州诗精矣,“不若退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不能强也。”此言却是。(李睟光《芝峰类说》)[7]1047
以上将韩愈与孟子、陶渊明、李杜、柳宗元、李贺诗文进行比较的看法都围绕“气势”展开。既有肯定张戒的韩愈“才气”胜于宗元说,还有追踪溯源认为韩愈的刚正之气源于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清代道光年间的宗宋诗派及稍后的同光体诗人对此早有论述。但从“以文为诗”的角度认为韩愈诗歌的高古之气源于渊明以及从结构的抑扬顿挫解读韩愈诗歌如“山势逶迤”让人耳目一新。当然,也有诗评家认为韩愈诗奇在“押险韵”(李睟光《芝峰类说》)。[7]1059
同不少中朝前辈及同时代诗评家一样,金泽荣非常看重韩愈雄浑壮大、奇崛不平的气势美,他曾直言不讳地称许“韩文公之推许李杜诗至甚者,以其神化之空灵也。若气力,则韩岂后李杜哉”(《杂言三》)。[1]324又言“凡文字平易中有奇变,是为真奇变。质朴中有光辉,是为真光辉”(《杂言三》),[1]318金泽荣意识到作诗不仅要追求奇怪,还须“平易”,正如韩愈强调“妥帖”。作为朝鲜朝后期重要的诗评家,金泽荣在评论朝鲜诗家的创作时,将类于韩愈诗的气势雄健作为首要评价标准,因此,李奎报、李穑、李齐贤、车五山、李芝峰、黄玹等皆在称颂之列。而作为朝鲜末期至近代的代表诗人,金泽荣诗歌的“劲健”、“新奇”则受到不少朝鲜诗评家的称颂,如:“近世金泽荣沧江、黄玹梅泉二家作,而一则雄健,一则古雅,破诗坛之寂寞”(金锡翼《槿域诗话》),[10]10504“李修堂南珪文章劲健,为一时之冠,其诗辞之高亦与沧江、梅泉相上下”(河谦镇《东诗话》)[11]9672“沧江尝有诗云:‘一种青天无主管,月轮祗在禁街行’,人皆以为新奇”(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12]10773
在以杜诗为正宗的朝鲜朝中后期的主流风尚下,金泽荣选择避开主流且极力推崇韩愈的雄健奇崛之风有什么样的诗学史意义呢?从金泽荣论朝鲜自高丽至朝鲜朝末期诗风演变可窥见一斑:“吾邦之诗,以高丽李益斋为宗。而本朝宣仁之间,继而作者最盛,有白玉峰、车五山、许夫人、权石洲、金清阴、郑东溟诸家。大抵皆主丰雄高华之趣。自英庙以下,则风气一变,如李惠寰、锦带父子,李炯庵、柳泠斋、朴楚亭、李姜山诸家,或主奇诡,或主尖新。其一代升降之迹,方之古则犹盛晚唐焉”(《申紫霞詩集序》),[1]251可见,较之于前代因袭已久的诗学李杜的盛唐风气,金泽荣认为朝鲜朝末期诗人学韩愈的“奇诡”、“尖新”之风可谓另辟蹊径。就正如韩愈本人对李杜的反叛和突破一样,又由于韩愈本人又承继了李白的豪迈和杜甫的奇险,又下启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风,选择韩愈作为诗学对象,既能上接盛唐,又能消弭自朝鲜朝初期以来的唐宋之争,并由此开启类似“盛晚唐”的兼容并包的多元化诗风,何乐而不为呢!
金泽荣学韩的纪行诗、酬唱诗大都学习韩愈的奇诡恣肆、以文为诗的风格,也有极少部分咏物诗歌如《落叶四首》,借鉴韩愈暗寓微旨的咏物诗的写法以寄托个人的羁旅之思和家国之思。究其原因,“凡文字,心窍材力俱宏大,然后方能包涵众体。诗之李杜、文之韩苏是也”(《杂言三》),[1]318极有可能金泽荣认为李杜诗为正宗,而被视为变调且基于不满社会现实和个人不幸遭际而发的“不平”之鸣的韩愈之诗悖离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而深受朱子性理学影响的金泽荣更倾向于由韩归杜,借鉴杜甫“以诗为史”,特别是在日本吞并朝鲜后,他痛心于朝鲜的亡国和时局的动乱给民众带来的乱离别苦,大量书写时事、一己之遭遇和家国之思的具有“诗史”价值的诗歌。结合金泽荣亡命中国的经历和以文章报国、以史救国、以新民救国的思想,他把对内忧外患的朝鲜时局的满腔愤懑都投注到以文章报国的宏大事业中。综上,金泽荣学韩仅停留在气势、句式等形式风格上,而其诗歌的主体精神意蕴更接近杜甫。
(二)对韩愈“以文为诗”的全面借鉴
如上所述,在韩愈的诗歌理论中,如果说抽象的较难言说的“雄健奇崛”风格具有多重的内涵,是另辟蹊径的韩愈诗风的代名词,那么,作为具体诗法的“以文为诗”这一概念也同样具有包容性,且更为具体和被感知。顾名思义,韩愈的“以文为诗”即以散文的章法入诗,即可从表情达意的直接明了、注重结构布局的起承转合、以议论入诗、以文字入诗,押险韵、窄韵等诸方面进行阐析,对于此点,古今中国学者多有论述,此不赘述。仔细推究,“雄健奇崛”和“以文为诗”应互为表里,共同构建了韩愈独特的诗风。
包括金泽荣在内的多位诗评家对韩愈的“以文为诗”的优劣争执不下,持否定者大都因袭中国古代诗论观点,认为“以文为诗”非“本色”,为“变体”,“古人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睟光《芝峰类说》),[7]1081“沈曰:‘退之之诗乃押韵之文,格不近诗’”(徐居正《东人诗话》)。[13]224而肯定者则从诗文互渗的角度加以称赞。
还有诗家从铺陈白描的角度称赞韩愈《猛虎行》“一篇铺叙,笔力千钧”(南羲采《龟礀诗话》),[9]7110或从语言助词的角度赞赏“退之《南山》诗中露尽平生傲物性,五十个“或”字中,人之情状备矣”(李瀷《星湖僿说·诗文门》)。[5]3752另有学者较为理智地通过追溯铺陈手法的发展源流来看待韩愈的铺陈,力图破除“世之人皆以为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固胜于宋,宋固逊于唐,此以唐诗多影描、宋诗多铺陈故也”(申景浚《诗则》)[14]108的成见,他认为唐宋诗优劣之争不在于铺叙、影描孰多孰少之区别,而在于主题意蕴的不同选择决定了格调的高下,这一论见颇具新意,也对朝鲜诗坛接受韩愈具有启发意义。总之,朝鲜诗家全方位地解读韩愈的“以文为诗”,为金泽荣接受韩愈的这一诗法提供了较好的舆论环境。
金泽荣虽然没有像其他朝鲜诗家那样直接评析韩愈的“以文为诗”,但他评析“太史公之文,便是诗”(《杂言四》)[1]320已间接表明他熟稔并认可这一理论,那么,他阐述司马迁文中所使用的“焉哉乎也之而故则”(《杂言四》)[1]320等语助词的妙用也适用于诗歌。韩愈的《南山诗》《山石》《调张籍》《此日足可惜》等五七古以散文章法入诗,其中,《南山诗》的章法布局尤为人称道,终南山四季壮丽奇诡的景色通过铺排一览无余。金泽荣的《龙头矶(其二)》《搜胜台》两首五古的结构明显师法《南山诗》,如“前瞻齐鲁出,斜眺荆吴没”、“朝潮月凄澹,夕汐风蓬勃”、“土人看寻常,野客言拙吶”(《龙头矶(其二)》),[1]163“前望飞鸟失,后顾白云起”(《搜胜台》)[1]165等诗句,诗人只不过将四季更替的铺叙转化为“前瞻”、“后顾”、“斜眺”、“仰视”等不同的空间视角、清晨与傍晚不同的时间以及“土人”、“野客”不同的审视对象等进行立体化地铺写。细读《龙头矶(其二)》《搜胜台》,其开头、结尾与《南山诗》也如同一辙,《龙头矶(其二)》的开篇“我昔探丛石,垂足濡溟渤。三面天苍茫,六棱状诡谲”[1]163与《南山诗》的起笔“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东西两际海,巨细难悉究”[6]15何其相似。而《搜胜台》的结尾“踞石且放歌,一撼乖龙耳”[1]165和《龙头矶(其二)》的结尾“共生天地初,神功敢独伐”[1]163与《南山诗》的结尾“斐然作歌诗,惟用赞报酭”[6]18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形似,后者神似,后者不约而同地赞美造化神功。《南山诗》连用51个“或”字句进行铺陈描写,金泽荣对此特别青睐,“盘陀或横陈,巃嵸或高揭,或举如鸟翔,或奔如兽狘,文绣或华衣,雕镌或隆碣”(《龙头矶(其二)》)[1]163“或相雷同或诡异”(《次韵谢朴天游霁鸿(文逵)先生赠诗》)[1]155“或为蓂生庭,或为鼎沉水”(《遥题文寿峰章之(永朴)新筑广居堂》)[1]215等多处使用。
金泽荣也喜好模拟韩愈打破五七古惯用的五、七字数,随着诗歌气势流走增减字数,最典型的如《退翁送扇与金泥,要写近作诗,余既拙于书,又苦扇之难书,作此乞李晓芙代写以归之》一诗,诗中云:“何不念我书尤恶,又何不念扇书有如着屐行瓦屋”[1]203“请君勿深诘,且就北窗一枕招凉时。……妍吾足自奇,俟君他时抖擞老气。挥扇办国贼,诸葛白羽谢公绿葵,与之相仲伯。我虽无力尚能踊跃,铭彼燕然石”,[1]203五七言诗句中间以八字句、十三字句,错落有致,别有韵味。而如同韩愈一样打乱五言上二下三、七言上四下三的常规句式的诗句在金泽荣诗歌中也较为普遍,“焉哉乎也之而故则”等虚词的使用更是俯拾即是。可见,金泽荣全面地实践了韩愈“以文为诗”这一制胜法宝,极大地提升了诗歌的阳刚雄奇之气。
综上所述,最迟至高丽中期,韩愈诗文的典范地位已确立,其后,高丽末叶至整个朝鲜朝,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相较之下,韩愈诗歌在朝鲜朝的地位有所下降,即便如此,在朝鲜朝前期以宗宋为主、中后期唐宋兼宗的汉诗坛,韩愈诗歌仍被作为仅次于李杜诗的重要艺术渊源。朝鲜朝英祖、正祖以后,随着性理学统治的松动、党争的缓和,以及以实学派为主的新的思想理念的兴起发展,宗尚宋诗的道学派主导诗坛的局面被打破,出现唐宋兼宗的多元化诗风,而处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金泽荣对引领变唐入宋的韩愈诗歌的接受在朝鲜汉诗史上显得尤为重要。
金泽荣避开韩愈的诗歌之源——不平之鸣而不取,唯取其雄健奇崛的气势和以文为诗的技法,根源于他认为韩愈的悲愤之鸣悖离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儒家诗教,而深受朱子性理学濡染的金泽荣更倾向于由韩归杜,抒写朝鲜亡国和个人亡命中国的“诗史”,这更契合他文章报国、以史救国的伟大理想和朝鲜朝后期诗宗杜甫的主流审美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