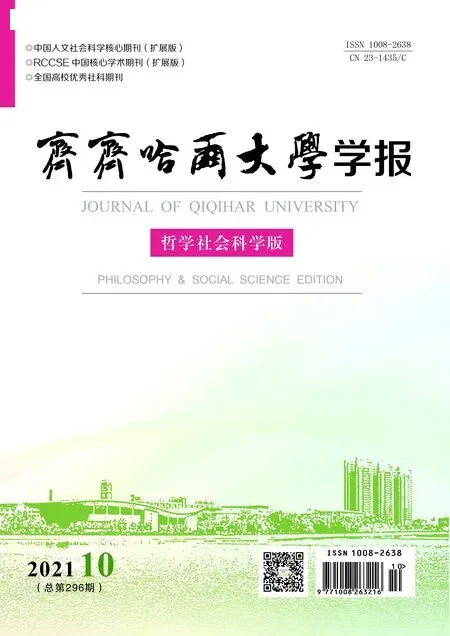论宋代“小话”的文体特点
李山岭
(亳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亳州 236800)
唐宋时期有敷演唱说故事的伎艺,称为“说话”。“故事之腾于口说者,谓之‘话’。取此流传之故事而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其中,又有“小话”,孙楷第先生指出“宋人言‘小话’,亦与故事同义。事之资谈剧、无关宏旨者,谓之‘小话’。”孙先生《说话考》一文,把“小话”和“说话”放在一起考述,梳理“说话”发展源流,[1]27-30但没有细致区分“小话”和“说话”的不同。若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宋代的“小话”是和“说话”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通俗文学样式。宋代“小话”具有篇幅短小、内容多样、语言俚俗、即兴讲说、融入自我的文体特点,以故事的独立性和非连续性、演说的随机性区别于“说话”,以自娱自嘲、谐中寓庄区别于“笑话”,从而自具面目,自成一体。
一、“说话”的特点
“说话”一词不始于宋,隋唐时期已见使用,为当时流行的习语。它的特点,约略如下:
其一,从演说的故事内容看,到两宋,已形成规模,有了内容细分,趋于成熟。据《都城纪胜》载:“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2]11可见,当时“说话”表演已经很兴盛,有了很细致的职业分工。
其次,从“说话”的长度看,其中小说、讲史等,多为连续性的故事,故事丰富、篇幅较长。“宋代所谓‘小说’,一次或在一日之间可以讲说完毕者,《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古今小说》……之类均属之。”、“宋代所谓‘讲史’,其讲述的时间很长,绝非三五日所能说得尽的。”[3]5从演说故事的时间之长,足以见出故事内容的丰富。
第三,“说话”是商业演出行为,聚众演出的场所称为“瓦舍”,“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时。”也许最初并无固定场所,艺人只要在所到之处,圈起场子,聚起听众就行了。听众听“话”是文化消费行为,据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4]7可知,听众“听说古话”是要付费的。
第四,“说话”同后来的“说书”一样,宜有简单的伴奏。孙先生说:“曰‘说话’,曰‘说书’,古今名称不同,其事一也。然‘说书’之义甚明,‘说话’今不通行。”[1]27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三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5]517这盲翁在山村作场说话,正是用鼓伴奏的。
第五,“说话”有底本,即话本,其中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等故事话本,多出于虚构。“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或“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2]11
二、“小话”的文体特点
“说话”由于和古典小说的发展关系密切,很多文学史对它都作了介绍,已为大家所熟知。与“说话”相比较而言,对宋代“小话”的讨论还不多。“小话”有自身的特点。
首先,从故事文本的篇幅看,“小话”篇幅短小,是非连续性的、独立的微型故事。如下面两则:(A)“东坡先生出帅定武,黄门以书荐士,往谒之。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昔有人发冢,极费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语盗曰‘公岂不闻此山号首阳?我乃伯夷,焉有物邪?’盗慊然而去。又往它山,镢治方半,忽见前日裸衣男子从后拊其背曰‘勿开勿开,此乃舍弟墓也’。”(《挥麈录·余话》卷二)[6]3825故事本身仅有百余字。(B)“世传小话: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若干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往来于怀,不觉欢适起舞,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狂计者,谓之瓮算。”[7]640故事也只有七十余字,都极其简短。因其简短,也就没有像“说话”那样有入话、散场诗等相对复杂的结构要素。
第二,“小话”的讲述受特定情境的激发,具有即兴言说、自娱自嘲的特点,含蕴着言说者鲜明的情感、情绪,通常有话外之话,言外之意。 如(A)载东坡所讲小话,就是缘境而发,并非事先预备,其意也在委婉地表达自己和弟弟苏辙处境的窘困,对拜谒自己的士子无能为力。讲说者自己的态度、观点蕴藏在故事之中,借故事来表达,“话”中有话,听话者也不难理解其中的潜台词。
又如,《乌台诗案》中记载有苏舜举给苏轼说的一个“小话”,“熙宁六年,因往诸县提点,到临安县,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本县界外太平寺相接。轼与本人为同年,自来相知。本人见轼后言:舜举数日前入州,却被训狐押出。轼问其故,舜举言:我擘划得《人户供通家业役钞规例》一本,甚简,前日将去呈本州,诸官皆不以为然。呈转运副使王庭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来。轼取其规例看详,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舜举言:(C)自来闻人说一小话云,‘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于凤凰,凤凰是百鸟之王。至路次,逢一禽。谓燕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云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却是训狐权摄。’舜举意以此讥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隔得一两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来临安,与轼同游径山,苏舜举亦来山中相见。周邠作诗一首与轼,即无讥讽。轼次韵和答兼赠舜举,云‘餔糟醉方熟,洒面唤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其意以讥讽王庭老等如训狐不分别是非也。”[8]13苏舜举借小话中的“训狐”(按,训狐是鸮的别名,俗称猫头鹰。)暗中讥笑王庭老等不知是非,即是“话”中有话。
据《东皋杂录》载,东坡还曾经说“小话”戏弄他人。那是在他经历下御史狱,谪居黄州之后。元祐初年,苏轼被起用知登州。不久,即以礼部员外郎召赴朝。于路途中遇见了当时的狱官,狱官面有愧色。(D)东坡戏之曰:“有蛇螫杀人,为冥官所追,议法当死。蛇前诉曰:诚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赎。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黄可治病,所活已数人矣。吏收验可,不诬,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狱吏曰:此牛触杀人,亦当死。牛曰:我亦有黄可治病,亦数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狱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杀人,幸免死,今当还命。其人仓黄妄言:亦有黄。冥官大怒,诘之曰:蛇黄、牛黄皆入药,天下所共知。汝为人,何黄之有?左右交讯,其人窘甚,曰:某别无黄,但有些惭惶。”(《说郛》卷二)[9]37苏轼好谐谑,但这则“小话”不免有失尖刻。
又,南宋王仲荀讲述的小话,讽刺一些士大夫贪恋在朝为官,不愿出任州县官。(E)“秦桧为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显美,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人怀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求外迁,重内轻外之弊,颇见于时。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坐于秦府宾次,朝士云集,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众官久俟,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出谒未归,有客投刺于门,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门状,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乃称不在。我与某官厚,故来相见,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竢其来,面白以治汝罪。’阍拱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例告以如此,若以为不可,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额曰:‘我官人宁死,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座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门,预褺客,老归建康以死。谈辞多风,可雋味,秦虽煽语祸,独优容之,盖亦一吻流也。”(《桯史》卷七)[10]84-85
再如,《桯史》卷九有一则“鳖渡桥”的小话:(F)“虞雍公允文以西掖赞督议,既却金主于采石。还至金陵,谒叶枢密义问于玉帐,留钥张忠定焘及幕属冯校书方、洪检详迈在焉,相与劳问江上战拒之详。天风欲雪,因留卯饮,酒方行,流星警报沓至,盖亮已惩前衂,将改图瓜洲。坐上皆恐,谓其必致怨于我也。时刘武忠锜屯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议遣幕府合谋支敌。众以雍公新立功,咸属目,叶四顾久之,酌巵醪以前曰:‘冯、洪二君虽参帷幄,实未履行阵。舍人威名方新,士卒想望,勉为国家卒此勳业,义问与有赖焉。’雍公受巵起立曰:‘某去则不妨,然记得一小话,敢为都督诵之。昔有人得一鳖,欲烹而食之,不忍当杀生之名,乃炽火使釡水百沸,横筱为桥,与鳖约曰:能渡此,则活汝。鳖知主人以计取之,勉力爬沙,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桥甚善,更为我渡一遭,我欲观之。仆之此行,无乃类是乎!’席上皆笑。已而雍公竟如镇江,亮不克渡而弑,自此简上知,驯致魁柄。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10]101《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二记虞允文所说“小话”与此同,惟涉及的人物有异。在此话中,虞允文以处于沸水之上的鳖自比,表达处境的凶险与被战局驱使的无奈,而又起到以谐化庄、寓庄于谐的效果。
概而言之,“小话”的讲述不是商业性行为,不是在瓦舍的演出,是在特定的情境激发下的即兴表达,对故事的选用有明确的指向性,融入了讲述者独特的情绪、心理体验。
第三,“小话”内容多样,如(C)、(D)、(F)是有寓言性质的动物故事,或借动物影射讥笑他人,或借动物类比自己;(A)是历史人物故事,借伯夷、叔齐虚构一段故事,道出自己现实处境的困窘;(B)讽刺世俗间不切实际的妄想,画出人心痴念想往富贵的镜像;(E)是当时的官场现形记。
第四,从传播看,“小话”的传播,依靠的是口耳相传,或即兴创作,可能没有现成的底本。其中(A)“东坡一见云:某记得一小话子。”(B)“世传小话”,(C)“自来闻人说一小话”,(F)“记得一小话”,都表明“小话”是口耳相传的,岳珂又说“鳖渡,本谚语,以为蟹,其义则同。”则可知这个“小话”本是“谚语”,流行已久,在被不同讲述者讲说时,有适当改动,可改“鳖”为“蟹”,并不影响故事的意义。而(E)王仲荀说“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他所讲的故事,可能是现场创作,也可能是听闻得来,但其讽刺现实的意味非常浓厚。在语言上,以俚言“说小话”,通俗、简洁而语含风趣,在亦庄亦谐中,或自嘲或讽世,并非单纯的诙谐笑谑。
第五,从文本结构看,“小话”讲述时都有“某记得一小话子”、“世传小话”、“自来闻人说一小话”、“记得一小话”、“某有一小话”等近似的发端语,表明“小话”的讲述有大体相同的结构模式。同时,“记得一小话”这样的发端语,是讲述中的提示语,把对讲述者的现实处境等背景性叙述与小话的故事本身区分开来;它也把二者联系起来,因为讲述者往往在故事主角的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影子,他仿佛正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旁听者分明感受到的是讲述者的境遇、心情,才会心领神会,粲然一笑。
综上所述,宋代“小话”的文体特点是:篇幅短小、内容多样、语言俚俗、即兴讲说、融入自我。以故事的独立性、片段性、非连续性,演说的随机性,区别于“说话”。讲述者以小故事自娱自嘲、谐中寓庄,区别于单纯谐谑的“笑话”。
当然,若论“小话”的源头,孙先生曾节引过《太平广记》卷二百四十八“诙谐四”隋代侯白说的一个故事。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毎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晩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为玄感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11]1920侯白所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小话”,从讲述的背景看,也显然是临场发挥,即时创编的故事。故事中的“大虫”,对橡斗(即橡栗)所说的话:“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非常切合当时的场景,把杨素、杨玄感、自己都涵容在了故事里,巧妙而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