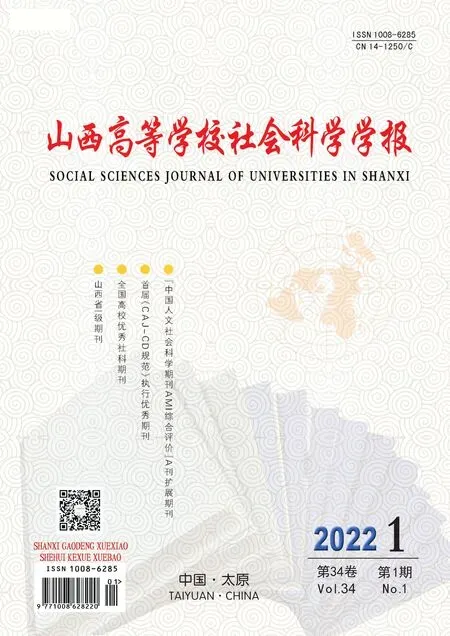立位、行道与为己
——《中庸》“素位而行”思想析义
张文旭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在儒家思想中,“人”之为“人”不是生来即是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一个人必须要经过学习和修养的过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以一种生成性、过程性的观点看待“人”,“成人”便成了儒家人道思想的主题,而“成为何人”与“如何成为”便是“成人”思想必须要阐明的两个问题。对此,儒家以“君子”作答,倡导人要学习君子、成为君子。“成为何人”指向目标与境界,“如何成为”指向工夫与实践,这二者在“君子”身上都得以呈现。可以说,“君子”既是人格境界的典范,也是个人行为的榜样。因此,要理解儒家关于“人”的思想,懂得一个“人”应当如何立身处世,就要从君子之“行”中找寻答案。
《中庸》中有许多关于君子之行的表述,“素位而行”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处。从“素位而行”的内涵入手,可以很好地把握君子之所立、所行和所为。“素位而行”语出《中庸》第十四章(1)关于《中庸》的分章,郑玄与朱熹不同,朱熹从“君子素其位而行”起至“反求诸身”为第十四章,并认为此章是子思之言。本文依从朱熹之分章。,其语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对于“素位而行”,人们常易产生两种看法:一者,将其理解为安于现状,加之“不愿乎其外”的说法,从而更加引申出一种不思进取的消极意味;二者,将其理解为政位或职位上的安分守己,联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表述,从而将其简单视为儒家“不越位”的思想、态度。这两种看法,第一种不察其义,流于浅薄,第二种从政治伦理入手,对其内涵有一定把握,但不免失于狭隘。基于此,需要回到《中庸》文本,并结合整个儒家思想,对“素位而行”的准确内涵作一疏解。
一、位:君子之所立
《中庸》第十四章开篇即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这是对“素位而行”的总论述。所谓“素”,孔颖达解释曰:“素,乡也。”[1]1673“乡”,所也,也就是处所的意思,这里可看作动词,理解为处在。朱熹的解释则稍有不同:“素,犹见在也。”[2]24释“素”为“现在”之意。对比来看,朱熹强调了所处之位是“现在”所处的,突出了一种当下的境地,但从《中庸》原文看,是更为一般性的描述,未有强调当下之意。“素其位而行”,可依据孔疏理解为:“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1]1673基于此,可以看到君子“素位而行”的关键在于对“位”的把握,君子要能够依据自己所处之“位”而行“位”内所当行之事,因此“位”在“素位而行”中是一个首要概念。那么什么是“位”呢?
(一)“位”从外在确定人的存在
《说文》曰:“列中廷之左右谓之位。”[3]“位”的本义是官吏于朝廷上所站之处(2)陈立胜曾概括先秦思想重“位”的五种涵义:狭义上的“位”,即“朝列之位”;爵位,即“阶位”“职位”;泛化的天伦、人伦之“位”;“居其所”之“位”“地位”;“正位”。(详见陈立胜:《谁之“思” 何种“位”——儒学“思不出其位”之中的“政治”与“心性”向度》,《宗教与哲学》2016年第5辑,第182页。)由此五义可知,“位”的意涵从朝列之位置不断泛化延伸,但其含义都以“位置”为基点。。由此可见,“位”本身就与人所掌握的权力、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概括地讲,“位”就是位置。而将“位”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则会有不同的意义:在自然之中,就是方位、处所等空间位置;在社会之中,就是职位、地位,涵盖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定的身份、职务、家庭以及社会境遇等。一个事物处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就必然会占有一定的位置。换言之,每一事物、每个人都受限于一定的“位”,“位”规定着一事物、一个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存在。
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对于“位”是极为强调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周易·系辞上》)宇宙原先本为混沌,清气上浮、浊气下降而有天地。天地的位置确定了,才有整个世界。所以在传统的观念中,“位”的确定是“天道”使然,“位”代表了一种秩序,而秩序正是与混沌未分时相对立的,有了“位”这个世界才呈现出天高地卑、四时推移、万物并生的形态。由天道而明人事,人类社会也同样需要确定“位”,从而确立人类社会应有的秩序。基于这样的思路,儒家“位”的思想可以从两个层面把握。首先是天道层面,表现为“天—人—万物”之间的位置关系。这一层次解决的是人之为人而与万物区别的问题,是人立于宇宙间的问题。其次是人道层面,表现为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确定,总体上不外乎政治、伦理两大方面。这一层次解决的是人之为社会中之一人的问题,是人立于人世间的问题。综合这两个层面的意义,可以看出“位”从外在方面确立了人在自然与社会间的存在。
(二)“位”的内在根据在于“德”
“位”是人在自然中、社会中的位置,是外在的一种规定,但如果仅从这样的外在的自然位置、社会地位去理解,那么儒家强调“位”的社会秩序就会单纯变成形式上压制人的框架而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应该进一步探究“位”的内在性含义。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尚书·大禹谟》)此处所言之“位”是政位,而君子与小人是德性高低不同的人,小人得位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可见“位”与居位之人的“德”不能分离。《管子》中也指出:“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管子·立政》)《中庸》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表述,这些都明确表达了“德位一致”的思想。对德位相配的强调,凸显出外在品阶之“位”与内在品性之“德”的对应关系。对“德必称位”的强调,表明外在的“位”的价值最终落实到了内在的“德”之修养上,因此君子首先应该追求“德”的达成而不是“位”的实现。《论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君子所担忧的不是外在之“位”的有无,而是得以立于“位”的根基的有无。能够立于“位”的根源正是自身的德性,外之“位”的根据在内之“德”。所以,在德位、内外之间,“位”的思想被进一步内化和深化了。从“位”到“德”的进路,把人在自然与社会间的定位与人之人格的完善联系起来,把人格的实现当作人自身的价值追求。于是,内在之“德”的确立,变成了一个人实现自我的根基,人于社会中的多种身份及位置最终都取决于己身之德,故而守其德,才能立于位,成就己身才能成就万物。
(三)“位”是有所作为之地
中庸之“中”,有中和、中正、时中、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诸多含义,然而不论何种含义,其与“位”的关联都是明了的。从自然角度看,方位之中央、两端之中间都是一种空间位置;从社会角度看,许多学者考证“中”最初是旗帜或圭表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权力、权位的象征(3)王学伟对“中”之地位、权位的含义作了详细论证。他在唐兰、萧良琼、李零等人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详细分析了“中”在时间意义、空间意义、政治意义上的权威之义。他指出:“‘中’从最初的圭表逐渐演变为权力、权位的象征。传‘中’,是尧、舜、禹以降的政治传统。周朝的武、成之际,把地理意义上的权威揉进象征时令权威的‘中’里,使‘中’的权威、权位色彩更加浓厚和牢固。”(详见王学伟:《中庸政治思想解读: 基于“位”“功”的视角》,《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15—116页。)。“中”与“位”原初内涵的相关性决定了“位”是理解“中庸”“中和”等思想的重要基点。《中庸》首章总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于此句,郑玄注曰:“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1]1662孔颖达疏曰:“言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得其养育焉。”[1]1663朱熹曰:“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2]18这些注解都很一致,表明中和之道的最终境界就是天地正其位置,万物得其养育。这是儒家天下大治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的核心就是天地万物都有其“位”,皆处其“位”,正其“位”。要实现世界的这种天人秩序,就需要人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先正己之“位”,这也就需要人修养自身,以中和、中庸之道行事。
基于上述理解,再看“素位而行”,其所谓的“安其所居之位”至少有以下四种内涵:一者,找到自己在自然、社会中的位置,对自己的位置有所认识;二者,人立于天地间的位置、人处于政治中的职位、人处在家庭中的位置、人与人之间的位置关系等方面共同构成了人之“位”;三者,多样的“位”是外在的,“位”需要内在“德”的支撑,所以“素位而行”也是守德修身;四者,“素位而行”是个人的安顿,是成己,其最终指向是“中和位育”下万物各得其位,即成物。从此四者含义看,“位”的丰富内涵决定了“素位而行”的丰富内涵,它是天人之际的人的挺立,也是社会人伦中人的长成,更是仁义之德的普遍实现。《周易》将“位”视为“大宝”,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周易·系辞下》)韩康伯注曰:“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4]350“位”之所以被称为“大宝”,是因为其有用,是因为于其上可以弘道。可见,“位”不是消极意义上的宿命似的规定,“素位而行”也不是安于现状的无所作为,“位”是“有用之地”[4]350,是人之根本的基点,“素位而行”正是让人立足这个基点,真正行君子所能行而有所作为。
二、道:君子之所行
《中庸》第十四章提出“素位而行”之后,又列举了四种人生情境来对其作更为具体的阐释,其曰:“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一)行“道”于其位
处富贵行富贵、处贫贱行贫贱、处夷狄行夷狄、处患难行患难,君子在不同的境况有对应不同境况的行为。但问题在于,不同境况下的行为究竟是怎样的?一般来讲,富贵之人财富充裕,而好有奢侈享乐之行;贫贱之人穷苦微贱,而常为衣食奔波,且为人所欺;夷狄乃偏远之地,未受礼仪教化,不行文明之事;患难中艰险困苦,人常常难以经受。难道君子于其四种境况下的行为也是如此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对于富贵贫贱的问题,《论语》记述:“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贫而卑屈、富而骄矜是常人之弊病,所以孔子认为子贡所言“无谄”“无骄”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做到无谄、无骄说明一个人能够不被贫富的境况所影响。但孔子进一步明言,这依旧是不够的,只有贫而乐、富而好礼才是完备的。做到贫而乐、富而好礼才说明真正忘却了贫富之境遇。
黄式三对此段有一解说,其曰:“君子之于贫富,有忘有不忘。乐之至,则不知己之贫;礼之恭,则不知己之富,此忘之之时也。贫毋逸乐,富则不劳,富必备礼,贫则从简,素位而行,随分自尽,此不忘之也。”[5]黄氏所言“忘”正是在“乐”与“礼”中对外在贫富环境的“不知”,而其所谓“不忘”则是随贫富之分而行,贫则不要希求安逸享乐而从其简朴,富则自不必劳累但礼仪常备。黄氏所言“不忘”大概可对应“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所言“忘”即是“贫而乐,富而好礼”。所以,“忘”实要高出“不忘”,不过二者也都是君子之行。黄氏之解不可谓不贴切,但其将“素位而行”理解为“随分自尽”而归之于“不忘”则似有不妥。“素位而行”正是要在富贵之差别境遇中而行君子恒常之行,它要说明的正是对外在贫富境遇的超越。在“不忘”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忘”才是做到了“素位而行”。“素位而行”所行、所乐的正是超越贫富之上的“道”。正如胡瑗所云:“所谓富贵,圣人固无心于此,假之以行道耳。博施济众,举贤援能,是富贵之中道也。不为苟进,不求苟得,此贫贱之中道也。”[6]136“无心”于富贵、贫贱的外在环境,“行道”才是君子的追求。
对于居夷狄的问题,《论语》记述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未开化的夷狄之地相较于文明开化的华夏中原肯定是不好的,而在孔子看来,君子居夷狄之地则没有什么鄙陋。因为君子有至德,处夷狄之地,并不会被夷狄影响而丧其德性,反而能“君子所过者化”(《孟子·尽心上》),教化夷狄而使其文明开化。这表明君子之行不因为夷狄之环境而改变,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
对于处患难的问题,孔子一生的患难经历就很多。《论语》记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厄于陈蔡,乃君子固然有穷途之时,但不与小人一样胡作非为,即便在艰难的境地君子也依旧有所坚守。“穷”即患难之时,正是体现君子德性之时,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对“天之未丧斯文”的如此自信,是在“畏于匡”的境地下升起的,表现出对于人生困厄的泰然和对于自身价值的坚定自信。如果没有对困厄、患难的超越是不足以有如此信念的,而这一超越的关键正在于心中有“道”。胡瑗指出:“患难有二:或一身之患难,或天下之患难。处天下之患难,生重于义,则舍义而取生;义重于生,则舍生而取义。一身之患难,但自守其道,不变其志,此行患难之道也。”[6]136不论处天下之患难还是一身之患难,君子都应当以自己坚持的“道”为准则,守道而行,不变其道。
论述至此,即可明了“行乎富贵”等句的真正意涵在于:不被人生外在的境况所左右,时刻守“道”而行。富贵、贫贱、夷狄、患难虽然有所不同,但对于君子来说,这些环境都是要被超越的。处富贵,则不纵情声色,能心态平常,富而好礼;处贫困,则不以贫困累其心,安贫乐道,箪瓢陋巷不改其乐;处蛮夷,则以礼乐施教化;处患难,则以平常心对待,有弦歌自乐的气象。游酢注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盖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无古今,则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损,故无得丧。”[7]陈柱也说:“此谓君子向其所处之位而行其道。……无在而不可以行其道,故无在而不自得。”[8]故而,“素位而行”要求君子行其所当行,而“当行”的标准实质上就是“道”。
(二)自得于其“道”
“位”的内在根据在于“德”,“位”的价值意义在于“道”,“位—德—道”因而紧密结合在一起。此三者恰与外在的名利、环境等相对,而独属于人之“内”。沈焕说:“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不是位,正是外也。《易》之‘正位居体’,孟子居‘天下之正位’,乃位也。”[6]137“位”虽然从外在确定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位置,但在“德”与“道”的关联中“位”早已不属于“外”,而成为与人之生命价值相关切的“内”。如此意义上,“素位而行”便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
由此,“不愿乎其外”,就不是简单地安于所处的位置,不是安于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的处境,而是要求君子不被这些外在的环境限制,不去考虑这些“外”,而时刻谨守于其“内”,谨守于君子之道,依道而行。这种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人生境地都安然处之、依道而行的境界,《中庸》称其为“自得”,即自有所得、自得其道。“自得”并不是于“外”有所收获,而正是于“内”自有所得。谭惟寅曰:“自得云者,所乐在内不在于外故也。彼在外者,一豪已上,君子皆以为无预于己,而未尝容心于其间,或归之天、归之人,皆非我也。……学者唯知所以立命,然后存心养性有用力之地。”[6]138人生之所以能够安处,正是因为心中得其“道”。而非安于外,所以“素位而行”不是消极的安分守己,其所安守的是君子立身的“道”、君子立位的“德”。正如《孟子》所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赵岐注曰:“欲使己得其本原,如性之自有也。”[9]“本原”正是“道”,得“道”于己,“道”如本性一般存于己身,便是“自得”所达到的境界。“素位而行”所要做到的正是“自得”:从道德践履上讲,要达到自有所得的至高精神境界;从为学修养上讲,是能够做到反身而诚,从己身而得而不是向外寻求,即程颢所言“学莫贵乎自得,非在人也”[10]。自得的境界和为学方法在宋明儒者那里被进一步推崇,被视为与孔颜乐处之精神主旨直接相关。而“自得”境界所强调的“内”与“我”也指出“素位而行”思想内涵的关键还在于“己”。
三、己:君子之所为
论述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四种境况后,《中庸》第十四章转而从上下之位的差异来论述。其文为:“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人生之“位”的变化无非在上或在下,“上”与“下”极具概括性。通过这种上下的差异,《中庸》指出“素位而行”是为己的。
(一)“正己”是目的也是方法
要做到“素位而行”,就要做到居上位不欺凌在下者,处下位不攀援其上者,端正自己而不去苛责别人,这样就不会有怨怼产生。《中庸》在这里论述了一条重要的处事安己之道,即正己而不求于外。正己,就是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端正自己的心态,首先去要求自己;不求于外,就是不把希望寄托于外者,不一昧向外寻求,不苛求于别人。基于此,“素位”就是正己,“不愿乎其外”就是不求于外,“素位而行”在此意义上就是强调要在“己”上做功夫。
儒家思想极为重视“己”,有“为己”“知己”“成己”“修己”“克己”“反求诸己”等说法。“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论语》这两处表述最能体现“己”的重要性。可以说,“己”和“人”的区分既是为学目的的不同,也是为学方式的差异,更是君子小人的分野。从为学目的或人生目标看,“为己”表明君子之行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的德性与价值,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通过“成己”其最终指向是兼济天下。这与如今所言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完全不同,其恰恰是对功利心态的一种超越。从为学方式或行动看,“为己”是以内圣为本,以外王为末,其实质就是“修身”,也就是《大学》之“明明德”、《中庸》之“率性”。所以“为己”就是在“己”上行,从“己”开始行。其方法就是“反求诸己”,如射箭一般,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而去反思自己的问题。恰如王夫之所言:“作圣之功,反求诸身心而已也。”[11]以射箭之事来比拟君子,原因就在于要强调“己”。心能专一,身有其正,方能箭矢平直,正中靶心。常人以为靶心是射箭之关键,其实“正己”才是核心。
(二)“俟命”是尽己之可能性
能够做到“正己”,则能不怨天不尤人。以这样的心态对待人生的一切,便是“居易俟命”。朱熹注此句曰:“居易,素位而行。俟命,不愿乎外也。”[2]24“素位而行”被理解为“居易俟命”,说明“素位而行”与儒家对于“命”的看法也有所关联。正是从这样一种关联性看,有人才把“素位而行”理解为一种对宿命的消极对待。实际上并非如此。
“居易俟命”,郑玄注曰:“易,犹平安也。俟命,听任天命也。”[1]1672孔颖达疏曰:“易,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处,恒居平安之中,以听待天命。”[1]1673也有注家注解“易”为“平地”。不论是“平安”“平易”还是“平地”都是以“平”释“易”。与这些解释不同,毓鋆认为以“平易”作解与前文不类,他以“变易”[12]解之。毓鋆的解释也有其道理,“居易俟命”在他看来就是处在变易的环境中自己不变而等待天命。郑注孔疏强调的是君子守道便常居平安,“居易”被视为守道、行道获得的状态或结果。毓解结合前文富贵、贫贱、夷狄、患难等境况,强调居于多变的环境要有其所守。这些解释皆有所取而侧重不同。事实上,“居易以俟命”与“行险以徼幸”相对,小人冒险而求,希求的是分外之物,而君子尽己行道,安待天命。与“险”相对的“易”,指的是君子有其所坚守的“常道”。换言之,君子所居之“易”不是平易平安之地,也不是简单的变动的外在处境,而应是作为“位”之根基的“德”和“道”。守常处道进而等待天命,和小人无所守而无常行正相区分。
守道、行道以待天命,正是以“素位而行”来安身立命。《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和影响的,人生一切遭遇无一不是命运使然,它是由天而来的对人的外在限制。虽然人没法对“天命”有所为,只能接受,但人自己的部分是可以自己主宰的,如孟子说的不立岩墙之下、行道等都是人自己能够决定的。所以儒家要求人人要学为君子,要通过各种修养功夫提升自己的德性,最终达到与天地并立的境界,最终凸显出人作为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所谓“正命”指的正是人志于道,据于德,尽己之所有可能性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生死寿夭都是“正”,因而所有遭遇都是君子立身立德的场所,而不再是限制,即“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所以,“居易俟命”指的是“正命”“立命”,而不是消极地听任命运安排,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只有从“尽己”而“立命”的积极意涵出发,才能理解“素位而行”不是不思进取。
四、结语
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把握 “素位而行”的准确内涵。“位”作为人在自然与社会中的立足点,从外在规定着人的存在,而其内在根据则在于“德”,所以“素位而行”就要立于其“位”而修其德性,从个人之“位”这个起点去修为,最终要达成的是天地万物的位育秩序,所以从“位”看“素位而行”,我们能发现它与《大学》修齐治平的路径是一致的。“道”虽然没有出现在“素位而行”一章中,但它是《中庸》的一个核心概念,“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不远人且广大精微,君子“素位而行”之所行就是恒常之“道”,不因外在境遇而有所改变,守道即是“素位”,“道”存于心而显于行,所以能有“自得”的境界。“己”是“素位而行”的最终指向,作为君子为学之方式、修身之功夫,“素位而行”就是“为己之学”,重视自身的价值与责任,不向外寻求,不向外苛责,这样的态度放到人生中,便形成“居易俟命”的观念。综合这三者,在“位—德—道—己”的进路中,“位”从外在不断深化到内里而与“道”“德”统一于“己”,“位”也从外在规限逐步转变为超越的基点和动力而使内在之“己”的价值得以实现。所以,“素位而行”不是消极固守或不思进取,而是关涉人生修养、人生作为、人生态度等多方面的积极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