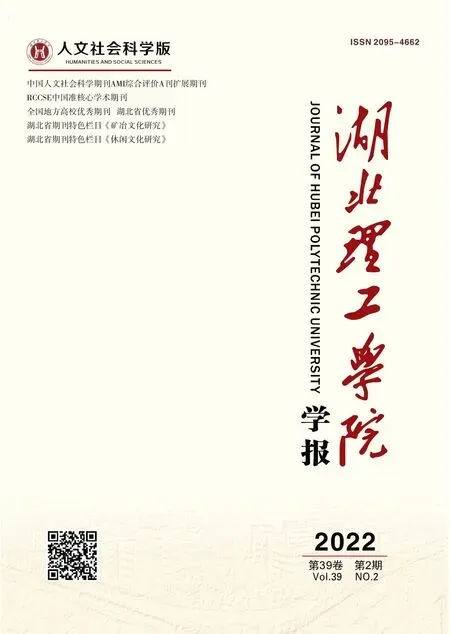战后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与清理*
李柏林
(湖北师范大学 汉冶萍研究中心,湖北 黄石 435002)
汉冶萍公司作为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煤联合企业,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①。研究者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公司债务、公司体制及其对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此相悖的是,学界对抗战胜利后公司的命运却甚少关注。实际上,汉冶萍公司作为一个商办股份制企业,在全面抗战时期被日军占领和控制后,战后是如何被接收的?公司与国民政府之间围绕资产处理问题进行了哪些交涉?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处置其资产的?公司最终为何被撤销?此一决定是临时之举还是早有预谋?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拟以湖北省档案馆、黄石市档案馆等所藏原始档案资料及相关汉冶萍公司资料为基础,对战后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与清理问题进行梳理,并进一步考察战后国民政府钢铁国营政策的实施与影响问题。
一、抗战胜利前汉冶萍公司基本概况
汉冶萍公司成立后,因资金来源匮乏,只能通过举借外债来维持经营和扩建,其中以向日本借款最多,导致公司逐渐被日本控制。为改变此种状况及实现钢铁产业的国有化,1927年初至1929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先后试图对公司实施接管,但均因日方的阻挠,无果而终。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汉冶萍公司的行动失败后,由于此前公司炼钢、炼铁均已停产,萍乡煤矿也于1928年被江西省政府接管,只剩下大冶铁矿继续生产。至此,汉冶萍公司基本沦为向日本提供铁矿石的原料基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满足汉阳兵工厂的用钢需要,1937年8月底,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借用”名义,电令汉阳钢铁厂交由兵工厂接收,并尽快复工,“兹定于本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时接收,……即希查照,迅造机器、工具、材料暨器具、房地产业等项清册送厂,俾凭点收为盼”[1]738。经过多次交涉后,是年底,汉阳钢铁厂将机器、工具、材料及相关产业等转交汉阳兵工厂。但汉阳钢铁厂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许多设备长期闲置,毁损严重,短期内复工复产显然难以实现。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意识到武汉可能难以守住,为避免汉阳钢铁厂落入敌手,1938年2月7日,蒋氏颁发手令,下令迁移汉阳钢铁厂,国民政府随即于3月1日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将汉阳钢铁厂、大冶钢厂、大冶铁矿等厂矿的设备拆卸并转运到重庆大渡口,另建新厂。“计自二十七年六月初开始迁运,至二十八年底告竣,共计迁运五万六千八百余吨。”[1]741不能迁走之大型设备,则实施爆破予以破坏。至武汉陷落时,汉阳钢铁厂由于搬迁、损毁和日军轰炸,几乎只剩下一片废墟,大冶铁厂和大冶铁矿的设备一部分被迁走,一部分被破坏。1938年11月,日本占领武汉、大冶后,大冶铁矿随即由军部占领并接管。“大冶陷落,蒋军退却,我军占领,以后冶矿概归军部管理,生产、运输、管理等,汉冶萍不能参加与闻。”[2]1083随后不久,军部委托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经营管理。“日铁”随即成立大冶矿业所,迅速恢复矿石采运活动。“属于日本制铁会社之大冶矿业所,事变后迅速进行恢复,结果,石灰窑至铁山间铁道完成;江岸安置了装载机两架,号称东洋第一。”[2]1094与此同时,日本为加大对铁矿石的掠夺,新置了许多设备。“日本人新置之设备及开采工作,均集中于狮子山一带,所有探矿、开掘矿井、采矿、选矿、动力及修理等设备颇为齐全。”[2]1100原大冶铁厂则成为“日铁”大冶矿业所本部,作为各种设备修理工场及职员宿舍和医院所在地。此外,整个抗战期间,日本在大冶地区共开采矿石500万吨,先后共运走440万吨,尚余80万吨堆积于江边②。抗战结束后,这些厂矿设备、矿石及房地产成为政府接收的主要对象。
汉阳钢铁厂经历拆迁和日军的轰炸之后,基本上只剩下一片废墟,公司在此地的资产也只剩下了一些房地产。除了汉阳、大冶、萍乡等地以外,公司在上海总部也保有一部分资产,包括房屋、码头、银行存款及公司抵押于上海正金银行的契据等。
二、战后国民政府的接收政策及对汉冶萍公司的初步接收
二战后期,随着盟军的节节胜利,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失败成为必然。在此情况下,如何对敌占区经济进行接收与清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就成为一个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1945年抗战胜利前,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即拟定了《沦陷区工矿事业整理计划》,拟具11条整理原则和《沦陷区工矿事业处理草案》,建议国民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对沦陷区工矿事业进行统筹整理,实行集中生产与管制,以树立国营事业之基础[3]480-481。1945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收复区处理敌产应行注意事项》,对接收敌产作出了5条原则性规定[4]373。10月,行政院设立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全面负责收复区敌伪产业的接收工作。11月,行政院颁布《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了相应的接收机构和处理敌伪产业的原则,不同物资、产业和机构,分别由不同部门进行接收、保管和运用。根据行政院的安排,收复区工矿事业由经济部负责接收[4]375。与此同时,随着抗战的胜利,经济部的接收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8月,经济部设立了收复区工矿事业整理委员会,拟定了《收复区敌伪工矿事业接收整理计划》,先后颁布了《收复区敌国资产处理办法》《收复区工矿事业接收整理办法》两项法规,初步规定了收复区敌国资产和收复区工矿事业的接收处理办法[4]389。9—10月,为进一步规范对收复区工矿企业的接收和处理,经济部又接连颁布了《经济部战时生产局各收复区特派员办公处登记及接收工矿事业实施办法》《收复区敌伪工商机构应行遵守事项》《收复区公司企业应行遵守事项》《收复区重要工矿事业处理办法》和《处理收复区工矿事业原则》等5项法规,把接收地区分为苏浙皖区、湘鄂赣区、粤桂闽区、冀察热绥区、鲁豫晋区、东北区、台湾区共计7个区,各接收区分别成立特派员办公处,负责本地区的接收事宜,并对收复区工矿事业的接收作出了更为具体详细的规定。1946年5月,行政院决定将资源委员会从经济部分离出来,升格为部会级机构,此后原经济部负责的工矿企业的接收和兴办工作便由资源委员会来办理。行政院和经济部等部门在抗战胜利前后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及资源委员会的升格,为战后初期接收汉冶萍公司奠定了基础。
抗战期间,由于汉冶萍公司资产散处多地,被国民政府和日伪分别控制和经营,历经八年的抗战,公司早已名存实亡。因此,战后对公司资产的接收由不同机构负责和实施。
公司在湘鄂赣等地区的资产,主要由经济部湘鄂赣区特派员办公处负责接收。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设立湘鄂赣区特派员办公处,负责接收汉阳铁厂和“日铁”大冶矿业所等事宜。
汉阳铁厂的接收较为简单。由于在武汉沦陷前,其部分冶炼设备被国民政府拆卸运至重庆大渡口另建新厂,其余的大型设备和厂房被炸毁,因此,当经济部湘鄂赣特派员办公处派人前往接收时,只剩下一些房产和土地。
1945年10月31日,原日铁大冶矿业所所长松村雄次向负责接收的特派员李景潞递交了《日铁大冶矿业所引继书》(以下简称《引继书》),《引继书》粗略地列出了大冶矿业所的财产目录和借贷情况③。根据该《引继书》,至此,国民政府初步完成了对日铁大冶矿业所的接收,但相关设备和资产的清点和移交工作,因人手过少进展缓慢。在完成初步接收工作后,经济部分别设立了“汉阳铁厂保管处”和“日铁保管处”,负责对这两处资产进行保管。
为加快对大冶厂矿相关设备和资产的清点移交工作,1945年12月,资源委员会派钢铁组长严恩棫、郑翰西前往大冶厂矿视察,事后严、郑二人详细报告了大冶铁矿和大冶铁厂实际状况,并建议在原厂基础上筹建新的钢铁厂[1]756。此后,资源委员会于1946年1月派刘刚前往大冶“接管大冶厂矿”。2月1日“日铁保管处”改为“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大冶厂矿保管处”。从2月1日起,日铁保管处代表与大冶厂矿保管处负责人员逐步点验交接日铁在大冶各项财产和设备,于7月初基本交接完毕④。
萍乡煤矿在战前实际上就已脱离公司。早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即被当时成立的汉冶萍公司整理委员会接管[1]152。宁汉合流后,江西省政府接管萍乡煤矿,后由资源委员会与江西省政府合组整理处,运营开采直至抗战爆发。抗战期间,为免被日军夺占,江西省政府派人将“窿内原有工程”破坏殆尽[1]759。抗战胜利后,该矿首先被经济部湘鄂赣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后由资源委员会接管,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赣西煤矿局。
公司在上海总部的资产,因涉及不同产业,分别被国民政府不同部门予以接收。公司抵押于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契据,先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正金银行办事处接收,后移交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保管⑤。公司在上海浦东的码头基地,由中央信托局上海特派员办公处接收。
三、清理委员会的设立及其与汉冶萍公司的交涉
为发展长江中游地区的钢铁工业,抗战胜利前夕,资源委员会就已拟定初步方案,计划战后在大冶设立钢铁局,统辖大冶各铁矿、鄂城铁矿、大冶钢厂、汉阳钢铁厂及湘潭锰矿,由资源委员会独资经营,恢复生产[3]374。战后,接收汉冶萍公司资产工作甫一启动,资源委员会就邀请美国专业从事钢铁厂设计的麦基公司派专家前往勘查,最终决定在大冶石灰窑筹设新厂。1946年7月10日,资源委员会在石灰窑成立“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有限公司筹备处”,决定将大冶厂矿保管处和汉阳铁厂保管处一同划归其接管。资源委员会计划以汉冶萍公司残留之厂房和设备为基础,“拟利用旧有厂基,积极筹划建厂”。但汉冶萍公司的资产在战后由多部门接收和保管,资产分布及现有状况迷雾重重,若不厘清其资产状况,则根本无法转移交接,遑论加以利用。为加快新厂的筹建,资源委员会呈请行政院同意,决定与经济部共同组织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将汉冶萍公司资产交由清理委员会统一接管与清理⑥。
经过资源委员会与经济部的多次接洽和协商,1947年4月22日,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根据清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其主要职责为调查清算汉冶萍公司全部资产,并拟定处理办法[1]758。当天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推选孙越崎⑦为主任委员,李鸣龢、程义法为常务委员。本次会议确定了清理汉冶萍公司的两项原则:一是公司一切资产包括契据账册档卷等交由清理委员会接管和清理;二是自抗战至清理委员会接管之日,公司在此期间对其资产的任何处分和转移,应逐项说明情况,并附相关证件移交委员会并案清理[1]757。同一天,清理委员会即以“汉清字第3号文”将以上清理原则呈报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并请其转呈行政院。在行政院于5月2日批示同意后,清理委员会随即以训令的形式将上述两项清理原则告知汉冶萍公司,要求其严格“遵照办理”,并派委员宋作楠(6月14日后改为卜昂华)、顾问孙治方前往上海公司总部进行接洽⑧。
宋、孙二人到上海后,即于5月13日面见公司总经理盛恩颐,递交清理委员会训令,要求公司遵令办理移交。由于行政院将训令送至汉口,未能送达盛恩颐,因而盛恩颐声称未收到行政院训令,须等收到行政院训令后召开董事会,再予以答复。几经周折后,二人于19日再次前往公司,面晤盛恩颐。盛氏答应于27日召开董事会讨论此事后,分别呈复行政院、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通过与汉冶萍公司负责人的初步谈话,宋、孙二人对公司的资本、债务、帐册档卷等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从初次接洽情形看,对于国民政府的接管清理行动,公司方面虽然明知钢铁工业国有化是政府既定之国策,汉冶萍公司被政府接管之势已无法改变,但盛恩颐显然对此心有不甘,甚至幻想呈请政府发还所接收之公司资产。因此,对清理委员会派去的接洽人员,盛氏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藉词拖延⑨。
面对盛恩颐的一再拖延,在与盛氏继续交涉的同时,清理委员会于7月7日召开第二次会议,专门讨论汉冶萍公司的接收方式及清理办法。关于接收方式,清理委员会决定呈请行政院饬令盛恩颐于收到公文15日内将资产契据、借款合同、账目清册、股东名册、档卷清册等送交南京清理委员会点收清理。否则清理委员会将直接接管其上海办公处及其各地有关产业,并在京沪汉三地登报公告,直接通知公司股东携带公司股票及有关证件,一个月内前来南京清理委员会申请登记及审核。此次会议还重点讨论了清理办法,最终确定了三项清理办法:一是公司所借日债之债权,一律收归国有,所有抵押品经行政院批注后全部由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接管;二是关于资产与负债原有价值的清算,按照1937年上半年物价标准折合计算;三是承认公司解散后所有未附逆股东合法权益。在清算后公司资产有剩余时,剩余部分将摊还未附逆股东⑩。
在清理委员会开会讨论接收方式和清理办法的同时,7月10日,盛恩颐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呈文行政院,同意将公司汉冶厂矿资产交由清理委员会接管,但要求将萍矿资产划归民营,仍旧保留汉冶萍公司之名义。不仅如此,盛氏还要求政府“将前所征用汉冶厂矿之机器材料及此次准备接管之资产按市价酌予贴补”。在政府满足上述要求后,公司再召开股东临时大会通过,并遵令移交汉冶厂矿资产及契据档案[1]757。显然,盛氏的如意算盘是在不能保留公司全部资产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保住萍矿,获得政府补偿,最终保住自己在公司的资产和地位。
在获知盛恩颐以公司董事会的名义呈复行政院的呈文内容后,清理委员会随即于7月16日向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呈文,一方面呈报关于汉冶萍公司的接收方式和清理办法,请两部会转呈行政院审核批示;另一方面则汇报了与盛氏接洽情形,并历数了盛氏父子擅借日债、依赖日本阻挠政府整理及勾结敌人充任伪职等“违法丧权种种罪行”。在此基础上,清理委员会对于盛氏所提出的要求,一一进行了驳斥。对于是否需要召开公司董监事会及股东临时大会,清理委员会认为,汉冶萍公司原有之董监事为战前股东会选出,不具有合法地位。盛恩颐曾任职伪华中矿业公司,依照呈院成案,不能再担任公司总经理,其地位已不存在。因此,清理委员会的接管行动无需经过原公司董监事会讨论通过,亦无需等盛恩颐召开所谓临时股东大会。对于汉冶萍公司的债权和厂矿资产,清理委员会提出应全部收归国有。“该公司所有厂矿资产已全数抵押于日本,胜利后此项债权依照敌伪产业处理办法,应归政府所有。”为避免盛恩颐“再事拖延,拒不移交”,清理委员会限令盛恩颐于文到15日内将所有资产契据等档案资料该会点收清理[1]760。盛恩颐先是试图继续拖延,但在了解到行政院及资源委员会接管公司的态度坚决后,明白接收之事势在必行,其态度随即发生反转,反而建议清理委员会发布措辞更为严厉之训令,令公司限期移交,否则迳行接管。
在接下来的8—9月,由于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副委员长孙越崎率领资委会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前往东北视察接收的工矿企业,汉冶萍公司的清理工作无形中停顿下来,清理委员会的呈请直到9月底才获得行政院的批复。在批复中,行政院作出了两点指示:“一、关于接收方面,可由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径向该公司洽接清理,如该公司延不点交册据,可即由清理委员会径行接管;二、关于清理方面,萍乡煤矿部分准一并接管清理,已由院饬知该公司未附逆股东部分公司承认其合法权益。”○11从指示内容看,行政院基本同意了清理委员会的接收方案,但对于如何处置公司资产、资产估价之标准及股东合法利益的维护等问题,行政院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在接到行政院的批复后,清理委员会随即着手准备接收汉冶萍公司。11月初,清理委员会委托资源委员会钢铁事业管理委员会上海营运处,暂时代其接管汉冶萍公司在上海浦东24保之码头基地。12月初该会派接收专员卜昂华赴沪会同钢管会上海营运处副处长刘美荫将浦东码头正式予以接收○12。但由于行政院对于清理委员会所拟清理办法迟迟未能答复,因此,对汉冶萍公司的接收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四、国民政府对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清理与处置
1948年1月14日,行政院指令资源委员会,明确同意了清理委员会的接管方案和清理办法,清理委员会的接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1月下旬,清理委员会派卜昂华再赴上海,专门负责汉冶萍公司的接收清理工作,并分别去函上海市政府、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请求上述各部门对接收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及相关资产的工作予以协助○13。与此同时,清理委员会训令汉冶萍公司负责人“克日将1、资产契据2、借款合同3、各种帐表4、股东名册5、档案等造具清册点交本会人员接管,以凭清理”○14。28日和30日,卜昂华先后两次面见盛恩颐,要求其遵照训令将各项册据等造具清册点交清理委员会接收清理。此外,为防止汉冶萍公司继续拖延,作好迳行接管的准备,卜昂华还先后拜访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及警察局副局长,以便必要时请求协助○15。
从清理委员会的举动来看,显然,为接管汉冶萍公司,此次清理委员会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即便如此,盛恩颐依然没有立即移交,从1月26日接到清理委员会训令后半个月之久,未见任何回音。在此情况下,清理委员会决定按照行政院指令,直接派人前去接管。2月11日,清理委员会再次训令汉冶萍公司,“遵令将该公司全部资产契据账册档卷克日点交本会接管人员,以资清理”○16。12日,清理委员会分别在《申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武汉日报》等报纸上刊登公告,宣布于2月16日接管汉冶萍公司并进行清理。与此同时,清理委员会再次去函上海市政府等部门,告知即将对汉冶萍公司进行接管事宜,请求给予协助○17。17日,清理委员会呈文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报告了其接管汉冶萍公司的相关情形。从2月16日起,清理委员会派接收专员卜昂华等人在汉冶萍公司上海总事务所与公司人员办理接收清理事宜。交接清点工作系由双方人员分3组办理,第1组负责档卷钤章合同等,第2组负责资产契据账册表报公债股票等,第3组负责器具图书等。但由于公司现有人手太少,实际上各种清点及编造清册工作均由清理委员会人员负责,至4月13日,清点造册工作才告一段落,除抵押在正金银行后被中国银行接收的契据未接收清点外,“所有各种资产账册文卷等均经点收完竣并造具移交清册11种”○18。
抵押于上海正金银行的契据战后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收,后转送中央信托局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这些抵押契据分别放置于3个保险箱内,其钥匙由汉冶萍公司和正金银行分别掌管。2月16日清理委员会接管汉冶萍公司上海总事务所时,3只保险箱连同各种档卷帐册一并移交。但在战后接收时正金银行并未将其所掌管的钥匙交出,因此要清点这些保险箱里面的契据,必须毁锁开箱。为慎重起见,清理委员会先后去函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苏浙皖区敌伪产业清理处及财政部清理敌伪金融机构督导委员会等机构,洽谈会同开箱事宜。几经公文往返,最终确定由清理委员会派员会同公司原经理人,并邀请经济部上海工商辅导处及资源委员会上海办事处作为监交人,一起毁锁开箱。6月2日,接收专员卜昂华会同盛恩颐、经济部及资源委员会上海营运处所派监交人员毁锁开启保险箱。3只保险箱保存的契据均为汉冶萍公司的地契,其中第3号箱和第5号箱内分别为大冶铁厂部分地契和萍乡煤矿部分地契,第4号箱为汉阳铁厂及大冶铁矿部分地契,但由于该箱受潮过久,“所存地契全部霉烂,已无法逐件点收”○19。至此,汉冶萍公司在上海所保存之各项契据、档卷帐册的接收工作基本完成。
经过清理,公司的档卷基本整理完成。董事档卷自民国元年起至民国三十四年止,均分类整理就绪。经理处档卷,自民国六年起至民国二十六年止。抗战以后的档案未曾整理归档,均列于未归档卷内。接收该公司账册自民国八年改用新式簿记,至接管之日止。此前之档卷账册等均移存浦东码头栈房内,于民国三十年日军拆除该码头栈房时全部散失。此外,公司汉阳铁厂及大冶厂矿之文卷账册图表等,于抗战开始后全部运至汉口,设立保管处。除图表一箱借与日本制铁所运回大冶外,所有此项档卷账册于民国三十四年1月该保管处被炸时全部损毁○20。
在接管各种帐册契据的同时,清理委员会亦开始着手对包括股票在内的公司资产进行调查和清理。
早在1932年,公司曾办理过一次股东登记,共有1 183户登记,计211 185股。1947年6月,在清理委员会接收前,公司又举行过一次登记,但仅登记了5万股。1948年5月5日,根据清委会第3次会议的决定,清理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广州、武汉、北平等地报刊上刊登公告,要求各股东在6月底以前,“携带股票连同有关凭证及原存印鉴,或具函检附上开证件,向上海四川中路33号807室本会上海办事处,在限期内声请登记”○21。到7月初,前往登记的股东有505户,共计136 050股。但公司先后发出的股票有37万余股,此次登记的股票数仅占全部股份1/3左右[1]764。不难看出,应该还有许多股东在限期内未能前来登记。
在进行股票登记的同时,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委托法律顾问孙治方就如何处理汉冶萍公司股权及债务草拟处理意见,孙治方随即拟定《汉冶萍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处理公司股权债务意见书》,提出了处理公司股权债务的几条原则性意见。汉冶萍公司股权,如政府决定收归国有,则应给予各股东一定补偿。如果决定依照公司法进行清算,则应先按照公司法和民法之相关规定,确定公司资产余额,再按照各股东所缴股款之数额比例分派;对于已登记之股权应即确认,未登记者,“一概将其股权暂为保留,在分派资产余额时,仍一并加入计算”,其“应派得之金额提存国库并另催告限期具领,逾期即收为国有”○22。将股东股权全部收归国有,显然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清理委员会经过讨论,最终确定对于未附逆股东之合法权益,在公司资产清理完毕后作价收回或改发新公司股票○23。
在期限截止后,还有一部分股东因未能及时登记,要求继续办理登记,接收专员卜昂华建议,“由各该股东叙明逾期理由,准予补办登记,抑即再行公告展期登记一个月”。同时由李鸣龢等5人组织股权审查小组,负责审核各股东之股权。但孙越崎担心延期登记将使得清理工作推迟,并有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因此,该建议并未获得其同意○24。
在与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接洽的同时,清理委员会亦分别去电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赣西煤矿局及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等处,调查和搜集公司资产设备及战时损失情况。
从1947年4月到1948年8月,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工作,清理委员会在克服了各种不利条件和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最终完成了对汉冶萍公司的资产的接收和清理工作。根据清理委员会的报告,汉冶萍公司资产状况如下:
股票方面,截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公司发出股票374 263股,每股国币50元,共计股本国币18 713 150元,清理委员会举办股权登记后,除该公司原有工商部官股29 504股,合计股本1 475 200元。此外,前来登记股东共计505户,一共136 050股,合计股本6 802 500元。
债务方面,抗战前公司欠日本正金银行等债款共达3 800余万日元,另包括上海规元银250万两,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已付利息2 400余万日元及上海规元银160余万两。
固定资产方面,抗战初期兵工署为应军事需要曾征用公司汉阳铁厂之设备材料并拆迁一部分至后方使用,但这部分资产因时间过久,加上牵涉面广,交涉起来十分不便,因此这部分资产未能统计与清理。公司在大冶、汉阳两地之资产由华中钢铁公司筹备处接收与利用。萍乡煤矿在战后仅存基地,其他资产荡然无存。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由经济部、工商部设定国营矿业权,交由华中钢铁公司及赣西煤矿局分别经营。
帐册档案方面,公司各厂矿之帐册档卷等据原经理人称均于抗战时期移存汉口后被完全炸毁,无法查明。上海公司总部所移交之帐册档卷,多残缺不全,全厂矿财产目录均付阙如。
在报告汉冶萍公司资产状况的同时,清理委员会就如何处理相关资产提出了三项办法,呈报资源委员会:一是公司所欠日债债权一律收归国有,公司全部厂矿资产拨交资源委员会处置,撤销汉冶萍公司名义;二是为维护未附逆股东合法权益,拟在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公司股份中划出部分股权,作为公司合法股东核换股份。对于不愿加入新公司的股东,可以由资源委员会作价收回;三是汉冶萍公司所欠正金银行250万两上海规元银借款,其债权一起收归国有。此项欠款及由正金银行上海分行代为保管的地契等抵押品,交由资源委员会一并接收○25。
工商部、资源委员会随即于9月17日把清理委员会的呈文转呈行政院, 9月29日,行政院对此进行了批复,最终确定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处理办法:一是该公司全部资产业已抵押与日本银行,该项债权已收归国有,所有抵押品由政府接收后,拨交华中钢铁公司使用,撤销汉冶萍公司名称。二是承认未附逆股东合法权益。已办理登记的股东,以原有股份加入华中钢铁公司;如不愿参加,可由资源委员会规定价格,收回股票。从批复内容来看,行政院基本同意了清理委员会的处理办法[1]766。
在接到行政院的批复后,清理委员会随即与华中钢铁公司联系,着手移交汉冶萍公司相关帐册契据及清理委员会尚未处理完毕之事务。华中钢铁公司随即派会计处长李家麟前往上海负责接收汉冶萍公司帐册契据及商洽继续办理清理委员会未了之清理工作○26。10月初,因接收清点人数不敷,工作进展缓慢,华中钢铁公司再派郭锡雍等3人赴沪协同点收帐册单据。11月6日,清理委员会召开结束会议,正式宣布结束清理工作,遵令撤销并登报公告。所有“档卷器具租赁房屋等及接收汉冶萍公司上海总事务所内之档卷、帐册、地契、股票、钤章、合同、图表、器具、租赁房屋等,连同上海浦东24堡码头基地一方一并移交资源委员会华中钢铁公司接收”。股票补办登记及换股或作价、日债及接受资产折算转账及各地房屋地亩清查等未了事宜由华中钢铁公司赓续办理○27。
至此,汉冶萍公司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其全部资产由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接收继承,公司的名称亦就此撤销。
五、余论
南京国民政府对汉冶萍公司,早就存有国有化之意图。抗战以前,汉冶萍公司凭借日本政府的支持,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公司的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在抗战期间,汉冶萍公司的资产散处各地,其中大部分被日伪所控制和利用,此种状况为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公司资产提供了重要理由和依据。实际上,早在抗战中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计划,准备在战争胜利后,全面接管汉冶萍公司的资产,实行国有化经营。因此,战争一结束,国民政府便迅速接收了汉冶萍公司在收复区的各地资产,先后设立了大冶日铁保管处(后改为大冶铁厂矿保管处)、汉阳铁厂保管处,邀请美国麦基公司专家前往勘查,最终决定在大冶石灰窑筹设新厂。为促进新厂的筹建,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汉冶萍公司资产清理委员会,将由不同部门接收的汉冶萍公司资产统一接管和清理。从1947年4月至1948年11月,清理委员会先后与各方多次交涉,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对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和清理工作。在清理工作完成之后,国民政府正式决定撤销汉冶萍公司,并将其全部资产交由新成立的华中钢铁有限公司接收和利用。
纵观南京国民政府对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清理及撤销公司名义转归国营等一系列运作过程,不难看出,汉冶萍公司在战后的命运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便已注定。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是孙中山先生国家资本思想的核心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结合孙中山先生的国家资本思想,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其国有经济政策。作为“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的钢铁业和铁矿,南京国民政府明确规定,“悉由国家建设经营之”[5]。钢铁国营政策的确立直接决定了汉冶萍公司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最终命运。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南京国民政府根据时局的变化,先后采取了全面接管、战时征用及战后接收与清理,最终取而代之等措施与策略,把汉冶萍公司这一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商办钢铁煤联合企业,改造成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国营钢铁企业。
至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汉冶萍公司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命运之坎坷,亦令人唏嘘。但另一方面,华中钢铁公司对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和继承,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汉冶萍公司的重生。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不仅奠定了华中地区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和总体布局,影响深远。
注 释
① 2007年以前具体研究成果参见李江《百年汉冶萍公司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2007年以后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李玉勤,《晚清汉冶萍公司体制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方一兵,《汉冶萍公司与中国近代钢铁技术移植》,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后铨,《招商局与汉冶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田燕,《文化线路下的汉冶萍工业遗产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左世元,《汉冶萍公司与政府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参见《张松龄致南京钢铁委员会电》,黄石市档案馆:L2-4。
③ 参见《日铁大冶矿业所引继书》,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LS56-10-132。
④ 参见《刘刚呈文(1946年2月1日)》,黄石市档案馆:L2-90。
⑤ 参见《财政部1947年4月27代电》,黄石市档案馆:L2-84。
⑥ 参见《资源委员会训令》,黄石市档案馆:L2-92。
⑦ 孙越崎,时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汉冶萍公司清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⑧ 参见《呈请转呈行政院转知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应行遵办事项祈鉴核示遵由》,黄石市档案馆:L2-84。
⑨ 参见《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清理委员会报告》,黄石市档案馆:L2-84。
⑩ 参见《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清理委员会呈文》,黄石市档案馆:L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