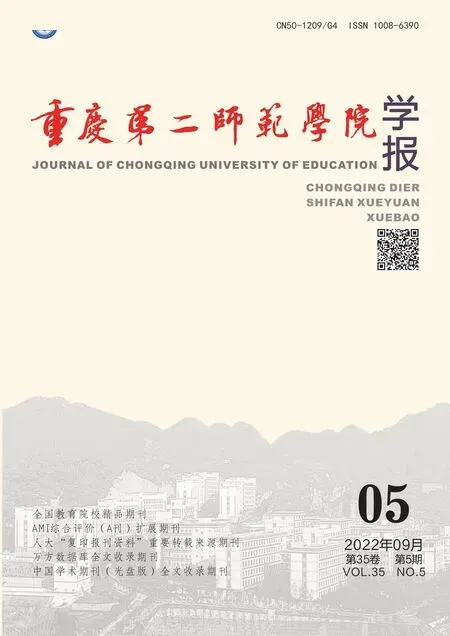李白诗歌的审美认知
——以济慈“消极能力说”为研究视角
陶 青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 400067)
英国诗人济慈在1817年12月28日致乔治和托马斯的信中说:“一些事情开始在我的思想中相吻合,立刻使我想到是什么品质造就了一个有成就的人,特别是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如此多地拥有这种品质——我指的是消极感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即是说,一个人能够经受不安、迷惑、疑虑,而不是烦躁地务求事实和原因。例如,科尔(勒)律治会暴露从秘密的最深处捕捉到的貌似真实的事物,因为不能再满足于一知半解。”[1]32济慈所谓“消极感受力”,亦即“消极能力说”,强调审美认知中主体精神状态的“神秘、含糊、不清”,主张审美主体认知延缓,审美客体自然呈现,探讨了文学创作主体的审美认知方式、认知目的及实现审美认知的途径,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中主客体的关系和文艺创作的本质。无独有偶,早在中国唐代,李白就曾主张诗歌创作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强调诗歌语言本真率直,文学作品清新脱俗、自然天成、浑然一体,同样涉及文学创作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关系。“出”强调审美客体的自我开放和自我展示,无须审美主体的干预和打扰。李白和济慈作为中西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诗歌均呈现出风格雄浑大气、想象绮丽深远的特点。本文拟从三个层面以济慈的“消极能力说”观照李白的诗歌创作,分析其审美认知,以求在中西文学互鉴中发掘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经验,从而拓展李白作品研究的视野。
一、主体认知的延缓
李白诗歌反复歌咏的主题之一是大写的自我,而这种执着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要求表现力度的跌宕起伏、激越豪迈、高亢惊险,达到浪漫的极致。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诗歌虽不及雪莱、华兹华斯的汹涌澎湃,但朴茂隽永,穿透力极强。在诗歌美学的震撼力上,两者殊途同归。济慈的文艺观“消极能力说”,强调主体认知的延缓和“诗人无自我”,这与李白书写的大我难道不矛盾吗?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弄清楚了李白书写大我的极致浪漫,也能更好理解“消极能力说”这一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文艺观。
“消极能力说”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理性束缚消失,审美认知延缓,创作主体进入神秘、含混、麻木的状态,想象冲出樊篱,游弋于大千世界,达到物我两忘。诗人无自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先验经验,进入审美客观对象。审美客观对象则自然、自由、自如地舒展。审美主体不急于摄入审美客体,而是以一种迟缓静候的状态经历审美认知,达到自我的丧失。“但是,正是这种自我的丧失,使我们从对象的回光返照中认清了自己的真实面目。”[2]也就是说,审美主体暂时屏蔽自我的先验感知和客观世界的理性干扰,没有知识性探求和主观说教, 而是任由思绪自由飘荡,任由审美客体自在呈现。审美主体通过这种客体感受调动读者的心智, 不直接告诉读者他要陈述什么,而是让读者感受他所描写的客体,让读者在客体中完成自我的创作和审视。其“客体”眼中之世界亦是“主体”眼中之世界 , 所以这种自然流露反而更加真实可信 ,更加符合其物我交融的创作境界[3]。审美主体通过这一认知的延缓实现在客体中的凝神与关注,实现“诗人无自我”①,实现对客体的审美把握,实现在客体中的遗忘、麻木、困顿。这样才有益于进入平和、从容的创作心境,才有益于创作灵感像“枝头生芽”一样自然降临,以“物”之心去感悟这个世界,以物去传达世界的博大之美。济慈强调审美客体的自然呈现,无须审美主体干预和评判,让读者在客体中完成自己的创作,这正应和了李白的“清水出芙蓉”的著名诗论。
李白诗中通常有一个极致浪漫的大我,这个大我脱离了实实在在的本我,是用另一个“我”去填充浪漫的想象。这一大我化山川于无形,有昂扬亢奋的狂狷之气和朦胧不安的越逸之美。在诗歌创作中,这种雄浑高昂的自我所追求的是大千世界的博大无形。李白诗中的大我无形于山水,是精神主体的游离,是虚拟与抽象化的艺术升华,直抵审美境界。那么,李白诗中的大我与济慈提出的“诗人无自我”有相似之处吗?济慈在“消极能力说”中强调“诗人无自我”,他在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伍德豪斯的信中说过,他说过的任何一个字都不能理所当然地被看成从他这个人的本我中流露出来的。济慈在这里区别了作者“我”与“我这个人的本我”,也是“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试图区分真实的作者与隐含的作者”[4]56。这一区分有助于理解济慈的“诗人无个性”“诗人无诗意”等观点。济慈强调主体认知的延缓,认为审美认知主体只有进入平和、从容的认知状态,才具备这种“消极能力”。情感与认知休眠,诗人失去固执偏执的自我,第二自我离开诗人的肉身去填充其他实体。这里的第二自我是虚拟化、抽象化的艺术自我,寄情于宇宙万物。从主体认知延缓这一层面分析,李白诗歌中洋溢于大千世界的大我,是脱离了“个性”与“诗意”的大我。这一大我与济慈的“诗人无自我”文艺观不仅不矛盾,反而还有某种程度的契合。
李白诗歌中审美主体认知延缓,审美主体不急于摄入,不急于评判,而是处于休眠的状态。以李白《峨眉山月歌》中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为例,其审美对象是峨眉山、秋月、月影、平羌江。秋月挂在蛾眉山头,且是半轮;月影投射到平羌江,随流而下,一泻千里。此时的审美主体是在静看客体后,不掺和主观情感,屏蔽先验认知,任由客体对象在视野中涌现。静谧爽朗的审美对象极易唤起读者的审美情趣,直接进入诗歌的审美体验。诗的后两句“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点明回望的地点是清溪,而且是“夜发”;“向三峡”,向巴山蜀水的尽头,离乡越来越远了。诗歌前两句白描写景,不掺入审美主体的评判和见解,呈现的是一幅静谧画卷,开阔辽远,引人入思。诗人在前两句中没有主观的摄入和评判,只是一种静观后的待物呈现。后两句酣畅淋漓,看似平静,却把离乡的伤感通过空间距离的跨越和时间距离的回望不露痕迹地呈现。再看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众鸟高飞,闲云飘荡,这些都没有主体的干涉和掺和,唯有客体的动态表现“飞尽”“独闲”,天空此时没有色彩,干净爽朗,高远无穷。而诗人的孤独之情和对逝去事物的无奈,对永恒宇宙的感悲却隐匿于景物之中,不急于表露和抒发,在景物的呈现中自然唤起读者参与诗人情感的体验。这正是济慈所倡导的“消极能力”:“济慈有针对性地提出他认为的作为一个伟大诗人所必备的素质——消极能力,即抑制主体智力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力和干扰 ,在不判断、不说教的基础上让客体自然地涌入心中 ,吐纳之间投身于物 ,以物之心来感悟世界。”[3]不难看出,李白在诗歌创作中具有这种审美认知,即消极能力。正是这一审美认知的延缓,摒弃我见,摒弃一个偏执的“我”,李白诗歌才能厚积薄发,书写一个丰沛的大我,一个消融于宇宙中的无形大我。
二、美与真的认知目的
李白诗歌创作中审美主体呈现出的认知延缓状态,其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综观李白的诗歌,无论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还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都有一种俊逸开阔的奇美和充实真诚的大美。不难看出,美与真是李白诗歌艺术孜孜以求的目标。李白的“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强调诗歌创作的“无为而治”“贵清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追求审美认知的真与美。济慈的“消极能力说”强调创作中审美主体“无目的”“无自我”,无论是主体实在感受的美,还是想象中的客体美,都是在力求一种“客观的主观化”,也即主体所感受的客体的真与美。而把这种对客体事物真实的感受或体验准确地表达出来, 就是诗人主体创作的目的。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提出“美即是真,真即是美”[5]18,可视为对“消极能力说”的进一步表述。所以,李白诗歌追求的率真奇美与“消极能力说”所倡导的美与真的认知目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白诗歌洋溢着对生命激情的书写和赞美,既有浪漫的理想光辉又有对生命本真质朴的捕捉,“奔越的英气与舒展的逸气”[6]4交织的是个体生命璀璨执着的体现。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整首诗给人真切的闺怨,白色晶莹的意象(玉阶、白露、罗袜、水晶帘、秋月)叠加构织,朦胧和清冷透出的因怨而生发的真切和美丽。女子思念远方的未归人,长久伫立在玉阶,直到白露浸湿了罗袜,无奈却下水晶帘,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因为感情的真挚和对生命本真的把握,无论是现实中的伫立,还是想象中的望月,李白都把她呈现得晶莹美丽、优雅从容。诗人要把对客体事物美的真实感受或体验准确地表达出来,离不开真实的感情支撑。在“美”与“真”的关系上,李白强调诗歌创作“贵清真”无疑与济慈所主张的“美”与“真”类似。
诚然,在美与真的认知目的上,李白与济慈略有差异。济慈认为“想象力把它作为美来捕捉到的一定是真”[1]27,强调的是由美及真,这里的真不完全是实实在在的客体,也可以是主体对客体的想象和情感,“经过美之审判, 区分出真与非真, 从而达到对真的把握”[7]。所以,济慈的文艺观“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是把美放在第一的,美是评判审美对象是否为真的标准,这一认知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历程。由美及真既是艺术审美的必由之路又是艺术审美的目的。济慈强调的“美是恒久快乐的源泉”,美是前提,是统摄。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能把冰冷古瓮的亘古之美捕捉到,少女、笛声、吹笛少年、诸神、田园、树木、风笛、鼓谣犹如画卷在眼前,甚至乐声“听得到的很美,听不到的更甜美”,美能抵达现实和想象的客体,从而认识客体的真,也即是美。李白诗歌则追求生命力度的厚重和生命本真的奇美。李白诗歌书写的“大美”后面支撑的是其“贵清真”的文艺主张。李白率性的真挚情感,在诗歌创作中力求真与美的审美认知目的,如其《子夜吴歌·秋歌》所吟唱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无尽的秋风从远古吹向未来,风送砧声,传递的是同一个愿望“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整首诗意象单纯明亮,语言简朴流畅,犹如天籁震撼人心、触动情怀。李白诗歌的力度之美可见一斑。正是情感上的真淳厚朴,艺术主张上的清真无为,才能在创作上追求一种洋洋洒洒的大美。较之济慈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二者虽然在真与美的着重点上不尽一致,但美与真都是二者追求的审美目的。
三、想象是创造力的认知途径
李白诗歌想象奇异,意象丰富。想象是通往美与真的翅膀,大胆的想象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开始展开奇异的想象,进入梦境。李白梦见自己在湖光月色下,一夜飞过镜湖,又飞到剡溪。他脚穿谢灵运特制的木屐,登上天姥山与青云相连的石阶。站在高山之巅,观东海红日从半山腰涌出,听天鸡在空中啼叫。从飞渡镜湖到登上天姥山顶,景物不断变幻,梦幻的色彩逐渐加浓,一直引向幻想的高潮。但奇伟壮观的梦境后面是潜在的摆脱不去的幻灭感。通过想象,诗人可以到达高而清的山水之景,创造出理想中的王国,暂时规避现实的黑暗,追求生命理想的灿烂之光。
在对想象的重视上,伟大的诗人是相通的。济慈把想象力看作一座庙宇,他则是里面的和尚。换言之,离开想象他不能成为诗人。济慈凭感觉展开想象,对理性认知是排斥的。他曾表示自己宁愿过一种感觉的生活。诗歌创作中的想象是诗人、读者、批评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济慈把诗歌创作中的想象和创造力的关系阐释得很清楚。他在致贝莱的信中指出:“长诗是一种创造力的检验,我认为这种创造力是诗歌的北斗,正如幻想力是船帆,而想象力则是船舵一样。”[1]23他理解的创造力就是依靠想象来营造宏伟世界并传递这种感觉的能力。伟大的诗人能感受世界的深邃庄严并把这种力量和感染力通过想象传递出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诗歌创作中的想象不是凌空蹈虚,而是要以实实在在的感觉为砖瓦梁柱,去建构其心目中美轮美奂的世界。”[4]66这些实实在在的感觉来源于传统和自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获得传统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济慈在书信中多次谈及他如何从荷马、莎士比亚、弥尔顿那里汲取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的创作想象源于传统并深植于传统。自然也是想象力的源泉。在自然面前,想象力相形见绌,大自然的博大之美是超越想象的,使人显得渺小,他要从自然学诗,要给博大之美添上一笔。
纵观李白诗论,可以看出他对传统和自然也相当重视。有学者指出:“李白的复古观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以《诗经》这一正,统御后世之万变,他要恢复的‘正声’‘宪章’就是正风正雅。”[8]李白认为,《诗经》是风雅的真正源头。他对《楚辞》精髓的承继,以及对汉魏风骨的肯定,都表明他对传统的重视,对创作严谨和慎重的态度。《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说的就是校书叔云文章老成,远追两汉蓬莱东观,得建安风骨。小谢指谢朓,李白自比,其诗文清新秀发。由“中间”在自汉以来的历史长河中展开,并引出下文“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今人古人逸兴同怀,壮思远飞,共上青天揽明月。在历史的纵深感中,前文的“酣高楼”生发的酒性已经在上青天揽明月的想象中达到了浪漫的极致,这是一幅令人神往和羡慕的图景。此外,在《蜀道难》中,李白将传奇与现实、大自然的山川奇观融为一体,除了有古老的蚕丛、鱼凫传说,五丁开山的神话,还有令人魂悸魄动的自然奇观。“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依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描写连绵的山峰,顶天而立,枯老的苍松倒挂在悬崖绝壁之间,飞泻的瀑流争相吼叫,砯崖击石发出震撼千山万壑的声响。奇特的自然景观起伏有致,整首诗在高扬、低回复又高扬、低回的节奏中,完成对蜀道艰难奇险的一咏三叹,既有音韵上的波澜起伏,又有楚辞意象的华美浪漫。诗人的想象超越时空限制,想象驾驭他激情跌宕的情怀和挥洒大度的胸襟,从而引领读者驶向美的诗歌艺术境地。李白诗歌艺术的想象不是凌空乱舞,而是紧致有序。正如济慈所倡导的诗歌创作的想象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感觉为基础,这种感觉、这种能力就是伟大诗人所具有的“消极能力”。诗人具有感受世界博大之美的能力,通过想象把这种美创造出来,并以一种真的方式存在。这里的真属于认知范畴,而美属于艺术范畴,而将美与真连接起来的正是想象力。如前所述,济慈认为“想象力把它作为美来捕捉到的一定是真”[1]27。所以,从诗歌创作中的想象角度认识李白,李白能让神话传说素材融入诗歌,运用想象去“填充”对世界的感悟和体验,并把这种体验传递出来,也就和济慈一样具备莎士比亚所拥有的品质,即文学创作的“消极能力”。
四、结语
柏拉图曾说:“凡是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 。”[9]27李白的“清水出芙蓉”和济慈的“消极能力说”,与柏拉图所强调的神灵禀赋的“灵感说”和迷狂状态下进行创作的“迷狂说”是一脉相承的。在审美认知延缓层面上,中西浪漫主义诗人都强调审美主体对于认知经验的暂屏。济慈强调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在李白那里就是“贵清真”,追求天马行空的大美和澄净明亮的赤诚,强调真情、真境、真性情。济慈认为“诗人无自我”,类似李白诗歌中的“大我”,不为外物所困。李白与济慈对生命本真的执着追求,都源于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心。正如王佐良所指出的,济慈和拜伦、雪莱“他们作品的感染力最终来自一种结合,即抒情式的理想与人世苦难的结合”[10]154。李白的诗歌同样也有这种结合。此外,济慈认为想象是通往美与真的途径,其诗歌中的想象艺术更是美与真的统摄。李白诗歌想象丰富瑰丽,冲破藩篱的束缚,追求理想主义,力求表现自然客体的真,达到美的艺术目的,而想象正是达到这一审美认知目的的途径。
注释:
①参见傅修延《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傅著认为,“诗人无自我”中的“自我”仅仅指的是“我这个人的本我”,这个没有冲动的“自我”只能“止于静观”,而“我”(诗人的“第二个自我”)却承担着“填充其他的实体”的出击任务。将“我”与“我这个人的本我”区分开来,是济慈对浪漫主义诗论乃至西方文论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