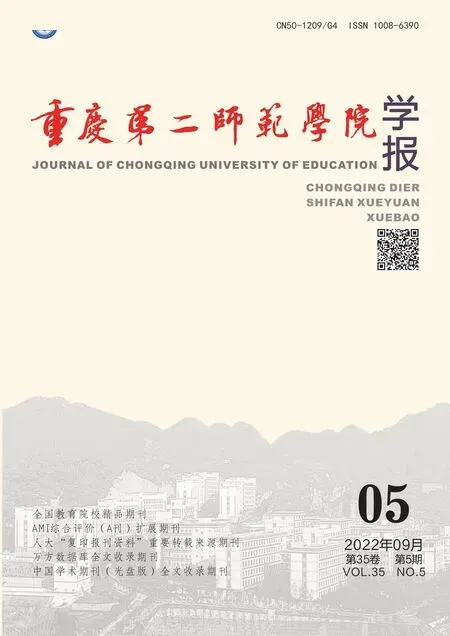李奎报《白云小说》诗学观述论
金 华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重庆 400067)
李奎报(1168—1241),初名仁氐,字春卿,号白云居士,朝鲜高丽时期诗人,著有《白云小说》《东国李相国集》《东国李相国后集》等。《白云小说》[1]是李奎报所撰诗话集,它虽然用了小说的名称,但其内容更像是诗歌品评或诗歌随笔。当然,作为古代小说前身的稗官文学的一种,它也是探究“小说”语源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资料。李奎报《白云小说》的诗学观可从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三方面予以阐释。
一、创作论
(一)诗之意气与辞采
诗话云:夫诗,以意为主,设意最难,缀辞次之。意亦以气为主,由气之优劣,乃有深浅耳。然气本乎天,不可学得。故气之劣者,以雕文为工,未尝以意为先也,盖雕镂其文,丹青其句,信丽矣。然其中无含蓄深厚之意,则初若可玩,至再嚼则味已穷矣。虽然,自先押韵,似若妨意,则改之可也。唯于和人之诗也,若有险韵,则先思韵之所安,然后措意也。句有难于对者,沉吟良久,不能易得,即割弃不惜,宜也。方其构思,思若深僻则陷,陷则著,著则迷,迷则有所执而不通也。唯其出入往来,变化自在,而达于圆熟也。或有以后句救前句之弊,以一字助一句之安,此不可不思也。
这则诗话涉及诗歌创作论。李奎报在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主张“诗以意为主”“意以气为主”“缀辞次之”。诗歌创作立意、意趣最难。而“意”又源于“气”,气有高下优劣之分,即每个人有自己的先天之气。“气本乎天”,气源于主观个性、有先天个人差异,故不可学。低劣的文气论者,以雕文为工,过于注重辞采修饰,不能做到“以意为先”。这样的诗文,只能让人“至再嚼则味已穷矣”。
在这则诗话中,李奎报还探讨了艺术构思心理问题,亦是重要的创作心理诗论。他主要围绕押韵、措意、对句难等,提出诗人创作没有灵感时应果断放弃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艺术构思要注意避免偏于深僻,否则沦入“陷”“迷”等窠臼,造成艺术构思不能通达、通透。其中所言“出入往来,变化自在,而达于圆熟”则涉及艺术构思的出与入,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亦有“入乎其内,出乎其中”的观点。艺术构思出与入的关系是辩证的,既要认真钻研、精心构思,同时也要能摆脱单纯的构思状态,跳出苦思,做到出入自如。
(二)文章华国
诗话云:至崔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名动海内。有诗一联曰:“昆仑东走五山碧,星宿北流一水黄。”同年顾云曰:“此句即一舆地志也。”盖中国之五岳皆祖于昆仑山,黄河发源于星宿海,故云。其题润州慈和寺一句云:“画角声中朝暮浪,青山影里古今人。”学士朴仁范题泾州龙朔寺诗云:“灯撼荧光明鸟道,梯回虹影落岩扃。”参政朴寅亮题泗州龟山寺诗云:“门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闲。”我东之以诗鸣于中国,自三子始,文章之华国有如是夫!
李奎报在诗文功能和地位上,主张“文章华国”。这则诗话提出三韩自夏时始通中国,而古高丽文献却少有记载。直至崔致远、朴仁范、朴寅亮三人作诗方使得高丽文人诗显名于大唐。李奎报之所以感慨“文章之华国有如是夫”,是因为他认为诗文具有重要的政治作用,可以显耀、彰显一国之气势、威名。“文章华国”的观念实际上涉及文学的政治价值和舆论宣传功能。当今世界,各国纷纷强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重要性,李奎报诗话隐含了这样的思想,颇有政治前瞻性。
(三)寓兴触物
诗话云:余于中秋泛舟龙浦,过洛东江,泊犬滩。时夜深月明,迅湍激石,青山蘸波,水极清澈,跳鱼走蟹俯可数也。倚舡长啸,肌发清快,洒然有蓬瀛之想。江上有龙源寺,僧出迎相对略话……遇兴率吟,亦未知中于格律也。
李奎报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主张遇兴率吟、寓兴触物,写“造物心”,推崇诗文与作者人格形象的高度统一。他追求“率然自作”,尝记其创作体会:“尝过主史浦,明月出岭,晃映沙渚,意思殊潇洒,放辔不驱,前望沧海,沉吟良久,驭者怪之。得诗一首云:‘一春三过此江头,王事何曾怨未休。万里壮潘奔白马,千年老木卧苍纠。海风吹落蛮村笛,沙月来迎浦谷舟。拥去骢童应怪我,每逢佳景立迟留。’余初不思为诗,不觉率然自作也。” 类似的诗话条目还有“夜泊元兴寺前赋诗”“过主史浦赋诗”等。
(四)病诗与诗病
诗话云:余本嗜诗,虽宿负也,至于病中尤酷好,倍于平日,亦不知所以。每寓兴触物,无日不吟,欲罢不得,因谓曰:“此亦病也。”曾著《诗癖篇》以见志,盖自伤也。又每食不过数匙,唯饮酒而已,常以此为患。及见《白乐天后集》之老境所著,则多是病中所作,饮酒亦然。其一诗略云:“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不然何故狂吟咏,病后多于未病时。”《酬梦得》诗云:“昏昏布衾底,病醉睡相和。”诗云:“药消日晏三匙食。”其余亦仿此。余然后颇自宽之曰:“非独余也,古人亦尔。此皆宿负所致,无可奈何矣。”白公病暇满一百日解绶,余于某日将乞退,计病暇一百有十日,其不期相类如此,但所欠者,樊素、小蛮耳。然二妾亦于公年六十八皆见放,则何与于此时哉!噫!才名德望虽不及白公远矣,其于老境病中之事,往往多有类余者。
从这则诗话可以看出,李奎报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深受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影响。李奎报自称:“老境忘怀履坦夷,乐天可作我之师。虽然未及才超世,偶尔相侔病嗜诗。较得当年身退日,类余今岁乞骸时。”李奎报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涉病诗”类型与“诗病”说诗论,即诗人在生病的状态下,反而诗歌创作更多,“至于病中尤酷好,倍于平日”。诗人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反而会呈现出一种病理性的诗歌创作的高产亢奋状态。唐代涉病诗中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医学、疾病和身体资料,虽有夸张色彩,但多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2]。诗人作为医疗活动与文学创作的体验者与参与者,其对疾病、医药和治疗等概念的认知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可反映整个时代的医学观念。他们借病抒情、以诗言志,将审视自身病痛的目光延伸至整个社会,以此影射国家命运。唐代涉病诗可分为叙述自身病痛、亲友互相慰问、咏外物而自喻和悲悯他人之痛四种,且不同时段、不同阶层、不同地域诗人的疾病表达都不尽相同、各具特色。每首涉病诗都有其创作的特定情境,每种疾病也都有其滋生的特定背景。杜甫是唐代涉病诗诗人群体的代表,白居易涉病诗也颇多。
诗话云:人有言诗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则从之,否则在吾意耳,何必恶闻如人君拒谏,终不知其过耶? 凡诗成,反复视之,略不以己之所著观之,如见他人及平生深嫉者之诗,好觅其疵失,犹不知之,方可行之也。
李奎报提出“诗病”论,强调对诗歌批评持开放辩证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强调对诗歌的修改,以提高诗歌的艺术质量。李奎报的“诗病”论带有宋代诗话的痕迹。宋代诗人论诗亦常阐释诗病。苏辙著有《诗病五事》[3],主要涉及诗经《大雅·绵》,汉代刘邦《大风歌》,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郊,宋代王安石等作家作品,以《诗经》为标准扬杜甫,贬李白、白居易、孟郊等。《诗病五事》的诗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义理”诗歌本质论,认为诗是人格精神的体现,高标“义理”;诗歌功能论,认为诗歌要有道德功能,诗歌的更高标准是“闻道”;章法结构论,提倡“语断意连”,重视叙述脉络的安排。《诗病五事》充分论述了“气”在文学中的表现,即“文势”“脉理”“波澜”构成诗歌的节奏和艺术风貌。
(五)知诗
诗话云:余昔读梅圣俞诗,私心窃薄之,未识古人所以号“诗翁”者。及今阅之,外若茧弱,内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知梅诗然后可为知诗者也。但古人以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为警策,余未识佳处。徐凝《瀑布》诗“一条界破青山色”则余拟其佳句,然东坡以为恶诗。由此观之,余辈之知诗,其不及古人远矣。
这则诗话记录李奎报往昔轻漫梅尧臣诗歌,多年后再读方觉其好,“外若茧弱,内含骨鲠,真诗中之精隽也”。李奎报认为梅尧臣的诗歌看似茧弱、实则内在蕴含风骨、韵致,提出只有真正理解梅尧臣诗才能称得上“知诗”。李奎报又说不懂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之好,不解徐凝《瀑布》诗“一条界破青山色”之恶,感叹自己“知诗,其不及古人远矣”;又学陶渊明之诗,终不得其神韵。李奎报认为写诗学诗要知诗,要真正懂诗,要向前代圣贤学习,抓住诗人经典的真正精髓,只有知诗后方能学诗、写诗。
二、作品论
(一)警语
诗话云:俗传学士郑知常尝肄业山寺。一日夜月明,独坐梵阁,忽闻咏诗声曰:“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以为鬼物所告。后入试院,考官以《夏云多奇峰》为题而押“峰”韵。知常忽忆此句,乃续成书呈,其诗曰:“白日当天中,浮云自作峰。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电影樵童斧,雷声隐寺钟。谁云山不动,飞去夕阳风。”考官至颔联,极称警语,遂置之嵬级云。
李奎报结合高丽时期诗人郑知常的汉诗,提出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警语问题。中国古代诗话称警语又为警策、警句。宋代诗话尤其喜欢探讨警策,即诗要有惊人句。李奎报《白云小说》记载郑知常的警句创作逸事,强调“僧看疑有刹,鹤见恨无松”这样的警句创作难得,假托“以为鬼物所告”。当然,这也涉及诗歌创作的灵感现象。
(二)诗言物之体与用
诗话云:《诗话》载李山甫览汉史诗曰“王莽弄来曾半没,曹公将去便平沈。”余意谓此可句也。有高英秀者讥之曰:“是‘破舡诗’也”。余意凡诗言物之体,有不言其体而直言其用者。山甫之寓意,殆必以汉为之舡而直言其用曰“半没”“平沈”。若其时山甫在而言曰:“汝以吾诗为‘破舡诗’, 然也。余以汉拟之舡而言之也,而善乎子之能知也。”则为英秀者何辞以答之也?《诗话》亦以英秀为恶喙薄徒,则未必用其言也。
李奎报在这则诗话中提出“诗言物有不言其体而直言其用者”,认为诗歌用事写物可以不言其体直言其用、大量使用借代词。使用借代词的习气中国古代文人早已有之,但在宋人那里变化更多,且更有理论上的自觉。这在苏轼、黄庭坚等的诗话中常见。宋代诗人,尤其是苏、黄和江西诗派,注重对禅宗典籍的参究,直接把禅的阐释方式转化为诗的表达技巧。惠洪总结作诗经验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惠洪总结的诗法在宋人中很有市场。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表述过相近的意思:“‘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不说作赋,而说雕虫;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疾病,而云沉绵。‘ 颂椒添讽咏,禁火卜欢娱’,不说节岁,但云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这种“言其用而不言其名”的诗法,在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诗中可找出很多例子。
宋人这种作诗习气与当时禅门宗风如出一辙。苏轼就曾指出:“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水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尽管僧人是出于对佛教戒律的忌讳,但其语言技巧却是标准的“言其用不言其名”,与诗人的借代词并无二致。司马光曾有感于当时的状况:“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怅怅然,益入于迷妄。”[4]这种情况在江西诗派中同样存在。陈师道云“险韵瘦词费讨论”,任渊注“《晋语》曰:‘有秦客度辞于朝。’注云:‘度,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可见,宋诗中隐语的“踵事加厉”,是与同时代禅门隐语玄言的流行分不开的[5]。
(三)诗有九不宜体
诗话云:诗有九不宜体,是余之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内多用古人之名,是“载鬼盈车体”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盗犹不可,盗亦不善,是“拙盗易擒体”也。押强韵无根据,是“挽弩不胜体”也。不揆其才,押韵过差,是“饮酒过量体”也。好用险字,使人易惑,是“设坑导盲体”也。语未顺而勉引用之,是“强人从己体”也。多用常语,是“村父会谈体”也。好犯丘、轲,是“凌犯尊贵体”也。词荒不删,是“良莠满田体”也。能免此不宜体格,而后可与言诗矣。
这则诗话是李奎报重要的诗歌创作论。他提出“诗有九不宜体”,即“载鬼盈车体”“拙盗易擒体”“挽弩不胜体”“饮酒过量体”“设坑导盲体”“强人从己体”“村父会谈体”“凌犯尊贵体”“良莠满田体”等九种诗文之陋习。“诗有九不宜体”涉及诗歌创作的人名使用、攘取古人之意、押强韵、押韵过差、好用险字、语未顺、多用常语、好犯丘轲、词荒不删等多种诗歌创作技巧手法的不当和错误。“诗有九不宜体”与李奎报的诗病说是一脉相承的。
(四)诗备众体与自成一家
诗话云:纯用清苦为体,山人之格也。全以妍丽装篇,宫掖之格也。唯能杂用清警、雄豪、妍丽、平淡,然后体格备,而人不以一体名之也。
这则诗话在诗体意识上,主张兼采众体、不拘一格而自成一家,提出诗歌风格要多元统一,不能仅用一种文体、受限于一种风格。单用清苦、妍丽等风格不好,只有综合使用清警、雄豪、妍丽、平淡各体,杂取诸家之长,才可以“体格备”。这样的诗论已经涉及后世诗的理想创作方法。正如席勒提出要将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相结合一样,文学创作只有追求多种创作方法和多样风格的融合,才能自成一家。
三、接受论
(一)崇尚古意,反对雕琢
诗话云:我东方自殷太师东征,文献始起,而中间作者世远不可闻。《尧山堂外纪》记乙支文德事,且载其有《遗隋将于仲文》五言四句,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髙,知足愿云止。” 句法奇古,无绮丽雕饰之习,岂后世萎靡者所可企及哉?按乙支文德,高句丽大臣也。
这则诗话记载了《遗隋将于仲文》五言四句,评价其句法奇古,无绮丽雕饰之习。李奎报论诗喜欢崇尚古意、类似唐代韩愈的诗风,反对一味雕琢绮丽的诗风,批评空无内容的绮靡之文。
(二)新罗真德女主《太平诗》高古雄浑
诗话云:新罗真德女主《太平诗》,载于《唐诗类纪》,其诗高古雄浑,比始唐诸作不相上下。是时东方文风未盛,乙支文德一绝外无闻焉,而女主乃尔,亦奇矣。诗曰:“大唐开鸿业,嵬嵬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时康。幡旗既赫赫,钲鼓何煌煌。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和风凝宇宙,遐迩竞呈祥。四时调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用忠良。五三成一德,昭载皇家唐。”
所谓高古指高雅古朴。《宋史·种放传》:“尝因观书赋诗,上曰:‘放体格高古。’”中国古代论诗,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高古的风格。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杜甫诗歌高古风格在于别具匠心地运用俗语、民谣等,这种语言很好地契合了诗人充沛的思想感情与气韵[6]。所谓雄浑是一种文学风格、审美风格。雄浑风格指思想情感境界上具有一种开阔大气、包容一切的特质,具体内涵则有儒家的雄浑与道家的雄浑之别。《新唐书·文艺传序》:“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这里的雄浑指雄健浑厚,即孟子所谓“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或者“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等义。这则诗话提出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具有高古雄浑的审美风格,可以与中国盛唐诗歌相媲美。李奎报引用中国传统诗话审美范畴评价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并结合帝王御制诗的内容特点,认为新罗真德女主的《太平诗》风格上更偏于儒家意义上的高古雄浑之美。
(三)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
诗话云: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其所著《琵琶行》一首载于《唐音·遗响》,而录以无名氏。后之疑信未定,或以“洞庭月落孤云归”之句,证为致远之作,然亦未可以此为断案。如《黄巢檄》一篇虽不载于史籍,巢读至“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不觉下床而屈。如非泣鬼惊风之手何能至此!然其诗不甚高,岂其入中国,在于晚唐后故欤?
《唐音》是元代杨士宏编纂的唐代诗歌总集。始自元统三年(1335),成于至正四年(1344),“积十年之力而成,去取颇为不苟”(《四库全书总目》)。全书15卷,分为“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共收唐诗1341首。因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所以不收李、杜、韩三家诗。在《全唐诗》卷七百八十五,可以看到无名氏的这首《琵琶行》:“粉胸绣臆谁家女,香拨星星共春语。七盘岭上走鸾铃,十二峰头弄云雨。千悲万恨四五弦,弦中甲马声骈阗。山僧扑破琉璃钵,壮士击折珊瑚鞭。珊瑚鞭折声交戛,玉盘倾泻珍珠滑。海神驱趁夜涛回,江娥蹙踏春冰裂。满座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曲终调绝忽飞去,洞庭月落孤云归。”这是一篇描写琵琶弹奏艺术的杰作,有论者认为,崔致远《琵琶行》受了白居易的同题诗《琵琶行》的影响,二者关系匪浅[7]。
这则诗话记载高丽诗人崔致远《琵琶行》一诗收录于《唐音》一事,佐证了高丽诗人在唐代与中国交往的事实,具有重要意义。但诗话指出单凭“洞庭月落孤云归”之句判断《琵琶行》为崔志远所作,难以定论,因为佚文校勘需要多方求证。这则诗话见出李奎报对诗文校勘的严谨态度。宋代诗话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唐诗学,包括对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文的批评,李奎报的诗话《白云小说》与宋代唐诗学关系颇为紧密。
诗话云:按《唐书·艺文志》载崔致远《四六》一卷,又刊《桂苑笔耕》十卷。余未尝不嘉其中国之广荡无外,不以外国人为之轻重,而既载于史,又令文集行于世。然于《文艺列传》不为致远特立其传,余未知其意也。若以为其事迹不足以立传,则致远十二渡海入唐游学,一举中甲科及第,遂为高骈从事,檄黄巢,黄巢气沮,后官至道统巡官侍御史。及将还本国也,同年顾云赠《儒仙歌》,其一句曰“十二乘舡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奈何于《文艺》,独不为致远立其传耶?余以私意揣之,古之人于文章不得不嫌忌,况致远以外国孤踪入中朝,躏踏当时名辈,若立传,直其笔,恐涉其嫌,故略之欤?是余所未知者也。
这则诗话,李奎报对崔致远不能在《文艺列传》立传颇为不平,认为其事迹载于史、文集行于世,没有任何理由不能立传。估计因为崔致远作为高丽人来唐以后名声过盛,使得当时文人面子大跌,立传之人为了避嫌,故意忽略了崔致远。从有唐文学史看,崔致远的文学地位虽有名声,但也未能“躏踏当时名辈”。李奎报为宣传高丽诗人,难免有推崇过誉之嫌。
(四)高丽诗人吴德全诗风“遒迈劲俊”
诗话云:濮阳吴世才德全,为诗遒迈劲俊,其诗之脍炙人口者不为不多,而未见其能押强韵。及登北山欲题戟岩,使人呼韵,其人故以险韵呼之。……先辈有以文名世者七人,自以为一时豪俊,遂相与为七贤,盖慕晋之七贤也。每相会饮酒赋诗,旁若无人,世多讥之。时余年方十九,吴世才德全许为忘年友,每携诣其会。其后德全游东都,余复诣其会,李清卿目余曰:“子之德全,东游不返,子可补耶?”余立应曰:“七贤岂朝廷官爵而补其缺耶?未闻嵇、阮之后有承乏者。”阖坐皆大笑。又使之赋诗,占“春”“人”二字,余立成口号曰:“荣参竹下会,快倒瓮中春。未识七贤内,谁为钻核人?”一座颇有愠色,即傲然大醉而出。余少狂如此,世人皆目以为狂客也。
这则诗话评价高丽诗人吴世才德全,认为其诗风遒迈劲俊,擅长押强韵。同时批评高丽诗人无耻自我夸耀,“相与为七贤,盖慕晋之七贤也”。李奎报批评这些文人沽名钓誉,展现了自身俊洁独立的人格。
(五)高丽诗歌传入中国获赞赏
诗话云:余昔登第之年,尝与同年游通济寺。余及四五人佯落后徐行,聊鞍唱和,以首唱者韵,各赋四韵诗。此既路上口唱,非有所笔,而亦直以为诗人常语,便不复记之也。其后再闻有人传云,此诗流入中国,大为士大夫所赏。其人唯诵一句云:“蹇驴影里碧山暮,断雁声中红树秋。”此句尤其所爱者。余闻之,亦未之信也。后复有人能记一句云:“独鹤何归天杳杳,行人不尽路悠悠。”其首、落句则皆所不知也。余虽未聪明,亦不甚椎钝者也。岂其时率尔而作,略不置意而偶忘之耶?昨者欧阳伯虎访余,有座客言及此诗,因问之曰:“相国此诗传播大国,信乎?”欧遽对曰:“不唯传播,皆作画簇看之。”客稍疑之。欧曰:“若尔,余明年还国,可斋其书及此诗全本来以示也。”噫!果若此言,则此实非分之言,非所敢当也。次前所作绝句赠欧曰:“惭愧区区一首诗,一观犹足又图为?虽知中国曾无外,无乃明公或有欺。”
这则诗话记载李奎报与朋友游通济寺,随意和韵作诗,因是游戏之作,没有正式文字记录。后来听闻所作诗句竟然传入中国,只言片语为当时士大夫欣赏。诗话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的自得与骄傲。这也显现出《白云小说》作为高丽时期韩国诗话,极力为高丽诗人进行宣传褒扬的诗歌批评特点,展现出《白云小说》作为诗话的民族性特征。
总之,李奎报的《白云小说》作为诗话,记录了其诗歌评论和创作的情形,在只言片语间体现出他的诗学观。总体上,李奎报的《白云小说》诗话理论性不强、特色不太明显,更多是高丽文人事迹的辑录,具有幽默风趣的叙事特点,这也导致这部以“小说”命名的“诗话”在后世更多地被视为古代高丽稗官文学——小说的源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