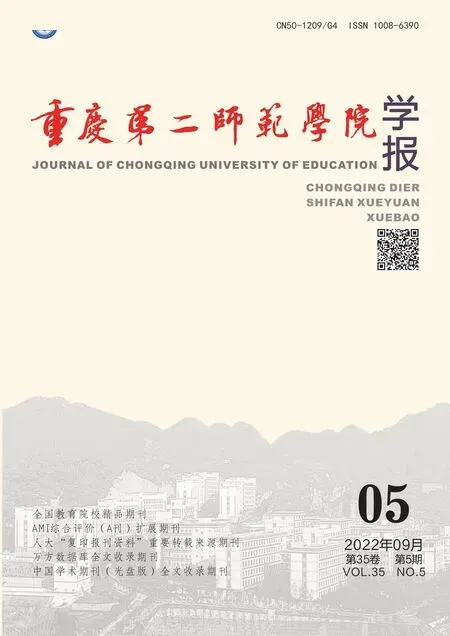论美国婴儿潮一代对斯蒂芬·金作品的影响
杨 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重庆 400067)
作为当今美国著名的作家和剧作家,斯蒂芬·金在他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主人公,有《克里斯汀》(Christine)中离经叛道的高中生,有《撒冷镇》(Salem′sLot)里单纯善良的牧师,有《黑暗塔》(DarkTower)中勇敢独行的枪侠,有《宠物墓园》(PetSematary)中热爱生命珍爱家人的医生,有《闪灵》(TheShining)中职业生涯屡屡受挫的父亲,有《绿里奇迹》(GreenMile)中坚持正义的警察,等等。这些身赋异能的人物在试图纠正各种错误和克服他们所面临的许多困难时,表现出一种倾向,即摧毁那些需要保护或拯救的人或物,许多学者认为这些人物的命运与斯蒂芬·金本人及其同时代的美国婴儿潮一代的人生经历十分相似。
一、美国婴儿潮一代
斯蒂芬·金出生在1946年,他亲眼见证并经历了对美国意义重大的“婴儿潮时代”,该时代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来年,即从1946年到1964年。美国从欧洲、太平洋及美国本土军事基地转业的复员军人数量达1600万,随后而来的是结婚潮,从1946开始出生人口达340万,第二年达380万,在1957年达到顶峰430万[1]。据统计,美国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约76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30%左右,被称为婴儿潮一代。他们一出生就享受着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福利和战胜国的荣光,是战后美国经济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就是这一群“对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或战时配给制一无所知,一出生便被繁荣的经济、充裕的食物所环绕,视自在消费为理所当然”的婴儿潮一代[2],他们发起并参与的学生运动和嬉皮士运动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
仔细分析斯蒂芬·金的作品,学者们发现他总是把作品的主人公置于令人瞩目甚至严苛的环境中,这样的处境要求他们必须取得非凡的成就,但几乎不能保证胜利会真正实现,这与婴儿潮一代所经历的失败与打击如出一辙。“斯蒂芬·金为自己和他这一代人的痛苦提供了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美国婴儿潮,这群人被定位为会彻底改变他们社会面貌的人,然而他们没能使用好现有的所有资源,因此没能达成他们的目标,而不得不忍受关于这代人‘集体垮掉’的质疑声音。”[3]Vehar也认为斯蒂芬·金的作品真实地记录了美国婴儿潮一代的真实历史,是一本具体的“默契指南”——“他的作品确定无疑受到同龄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影响,是他生长的社会环境下各种思潮、反思和批评的集合”[4]8。本文综合整理了斯蒂芬·金的主要作品,从主人公的行为动机、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三部分详细阐释婴儿潮一代如何影响斯蒂芬·金的作品。
二、斯蒂芬·金作品中的婴儿潮一代
(一)主人公的行为动机:理想主义和盲目自信
斯蒂芬·金在作品中常引导读者认为,主人公的行为动机源于自以为充分的准备和对成功的幻想,并让主人公无视即将到来的危机。理想主义和盲目自信成为斯蒂芬·金作品中主人公行动的关键动机。这与婴儿潮一代出奇地一致,他们生活在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生活优越,受教育程度很高,天然地就认为自己被赋予了守护世界和平、追求人类理想的权力,他们踌躇满志地投入嬉皮士、五月风暴、新浪潮、新左派以及马丁·路德·金运动中,甚至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总统约翰·肯尼迪也成为他们的偶像,“世界(美国)是他们的,或将是他们的,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和观点有绝对的把握”[4]14。但Vehar指出,他们尝试改变社会景观非但不是一种富有同情心的责任表现,而恰恰是妄想偏执的疯狂行为,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表现。
斯蒂芬·金作品的主人公就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怀揣梦想,追逐成功,相信天赋神力,幻想拯救世界,如《撒冷镇》中“身穿黑色的祭衣,手持可以驱赶黑夜恶魔的十字架”的神父唐纳德·卡拉汉在面对僵尸王时,“坚信自己的身体就是可以避邪消灾的法器,是一个能将神力从十字架中传导并激发出来的通灵人”,他自信地挡在被保护者男孩马克前面。《宠物墓园》中的路易斯·克里德也是一个婴儿潮一代的典型,他在一个大学任校医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一个神秘的印第安墓园可以使死人复生,他欣喜若狂,冥冥之中感受到了“命运的召唤”,觉得这是一个难得一显身手的好机会。恰巧数日后小儿子被失控的卡车撞死,他没有同妻子一样痛哭绝望,而是立即将儿子送到这个墓园,虽然重生的儿子举止怪诞、面如恶鬼,路易斯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就是重塑世界的“天选之子”的偏执信念。《黑暗塔》则更是描绘了理想主义和盲目自信支配下的个人主义悲剧,主人公枪侠罗兰是蓟犁王国的王子,他十四岁就成为枪侠。蓟犁由于内乱遭到灭顶之灾,罗兰成了唯一幸存的枪侠,高贵的出身、古老的预言、族人的期望、天赋以及血液中渴望主宰一切的冲动让他自然地就被赋予了拯救世界、找到所有平行世界的中心——黑暗塔的任务。
这些手握天赋“神力”并极欲操控一切的主人公丝毫不考虑即将到来的失败。《撒冷镇》中当僵尸王轻易地打掉了卡拉汉神父的十字架,狂笑着嘲弄“你的信仰到哪里去了”时,卡拉汉突然意识到这个十字架不过是他妈妈在都柏林旅游商店购买的一块石膏质纪念品,“手臂的肌肉虽然还记得那无以伦比的震颤感,但那个向他手臂输送力量击碎墙壁和石头的神力消失了”。当《宠物墓园》中路易斯的小儿子盖吉以活死人的模样从“米克马克族”墓园爬出,并残忍地杀死邻居贾德和母亲瑞秋后,路易斯似乎没有失望,反而抱起了妻子瑞秋再次跑向墓园,企图再次重复制造恶魔的实验。学者Tony Magistrale评价:“他(路易斯·克里德)有意识地选择解放‘米克马克族’墓园的邪恶能量,因为他希望拥有可以操控时间、改写天命的能力。”[5]时代和命运赋予《黑暗塔》中枪侠罗兰绝对的权力,却并没有给他带来恢复帝国、拯救苍生的荣光,反而让他失去至亲(他亲手杀死了母亲),牺牲了朋友杰克。为了个人私利他甚至还屠杀了一个村庄的人,但当他找到血腥之王盘踞的黑暗塔时,却无法到达塔顶而陷入了某种轮回,终点又变成起点,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每天重复着推巨石到山顶一样,罗兰重新启程找寻黑暗塔。
(二)主人公的行为模式:消极面对与推卸责任
“当斯蒂芬·金小说的主人公被要求行使自主权力时,他们的行为模式涉及四个主要步骤:行动响应,为完成一个特定的目标获取手段,对潜在失败的考虑,以及对参与动机的合理化解释。”[3]传统英雄故事的主人公当面临异常恶劣的环境,面临死亡、虐待、甚至整个世界的毁灭时,他们必须做出果断反应,采取坚决的行动。然而在斯蒂芬·金作品中大部分主人公面对威胁到生命的邪恶力量时,即使肩负重任、手握神器,他们的反应往往也是迟疑和慌张,这导致他们在关键时刻延误时机,做出错误判断,事后他们也会找出种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错误选择。这些主人公都具有这样的行为特征,除了前面提到的《撒冷镇》中的卡拉汉神父、《黑暗塔》中的枪侠罗兰、《宠物墓园》中的路易斯·克里德,还包括《黑暗的另一半》中的作家撒德·博蒙特、《死亡地带》中的警察约翰·斯密斯、《克里斯汀》中的少年阿尼·坎尼安、《狼人周期》中的牧师罗威等。他们都在作为与不作为、坚持与沉沦、精神与肉欲、善与恶中挣扎和徘徊,最后找出种种借口并选择了逃避。
这种行为模式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表现颇为相似,当面对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被刺、阿波罗号登月、越南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时,婴儿潮一代感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激荡,他们当中许多人即使对战争中无辜死者的同情和对霸权主义的厌恶情绪日益加深,但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却对是否亲身参与造反运动心存顾虑。Patrick认为彷徨犹豫、患得患失是他们的真实状态——“当被迫在至少两条路径之间做出选择且每一条路径都可能导致失败时,如何才能使一个选择比另一个选择更加合理?”[3],这也成为斯蒂芬·金的自传体小说《亚特兰蒂斯之心》(HeartsinAtlantis)的素材来源。
《亚特兰蒂斯之心》故事发生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作家本人的早期经历,小说详细地描绘了在那个动荡年代婴儿潮一代的生活。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和军方发起了征兵令,18~25岁的适龄男子都必须响应号召入伍。这个征兵令如同催命符,让主人公皮特·莱立和他缅因大学的同学心烦意乱,尤其是广播中传来美国飞机为袭击越共集结区而造成平民死伤的消息更让他们坐立不安。大部分学生虽然反战,但由于害怕参加反越战“抵抗委员会”(Committee of Resistance)会被学校处分而影响未来就业,即使如此大学生还是利用各种机会表达了对越战的不满和不愿意参军的态度。因为有规定在校大学生有权利不用立刻服兵役,大家都集中精力专注学业,避免由于学业差被学校开除而被迫服兵役。小说中多次提到差生克里斯和弗兰克为自己即将退学而忧心忡忡,担心一旦离开校园就会接到征兵通知,这几个大学生试图穿着印着反战标语的夹克来表达对越战的质疑和抗议。小说花了大量篇幅描写男孩们在“亚特兰蒂斯之心”打牌和打牌时的闲聊,尤其是通过对话刻画了在越战的背景下一群“胆小鬼”对离校的焦躁和对前途的焦虑,对参加反战示威运动人员的羡慕和崇拜,以及对获得机会参与书写反战标语的兴奋。校方发现了斯托克利·琼斯夹克上的反战标语“ND”(Nuclear Disarmament)后,因查不到真正书写标语的学生,只得开除琼斯。面对自己的怯懦和对无辜的琼斯的落井下石,这群男孩虽然有些歉疚,但还是找到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我们是星尘”“我们尝试过了”,并心安理得地完成了学业各赴前程。
Landon Y. Jones对婴儿潮一代做出了如下评价:“婴儿潮一代的愿望和机会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理想主义的愿望,而他们的能力却使自己作茧自缚,无法自救。更糟糕的是,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以及对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愿望的逐渐消沉的意志,产生了阻碍他们进一步尝试的意愿。这一代人最终患上了一种典型的焦虑综合症——高抱负、低动力。他们仍然是梦想家,但不能够承受实现梦想所需的风险。”[6]255
(三)主人公的行为结果:放纵狂欢或孤独苟活
“(20世纪60年代)反战运动中所汇集的公众舆论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政治成果……对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总体战略方向和称霸世界的目标基本没有产生本质性的影响。”[7]婴儿潮时代的年轻人理想开始破灭,他们怀疑政府,怀疑所依赖的社会制度,这时期出现了标志着反战的嬉皮士运动,年轻人厌倦了压制个性、迫害个人自由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宣扬逃离社会,摆脱与现实社会和文化模式的种种联系,它的高峰是“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一群颓废而迷茫的青年人在整个演出期间,以赤裸身体、吸食大麻、彻夜嘶吼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他们对社会的厌恶;也出现了代表“垮掉一代”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倡导极端的生活方式,比如放纵的性爱和吸毒,其代表人物艾伦·金斯波格的作品《嚎叫》(Howl)就描写到:“我看到我这一代的精英被疯狂毁灭,饥肠辘辘、赤身露体、歇斯底里,拖着疲惫的身子,黎明时分晃过黑人区,寻找痛苦地注射一针。”因为对现实世界的彻底失望,“他们(婴儿潮一代)对生命中的奉献与牺牲、承诺与责任嗤之以鼻”,“认为任何可能改变世界的希望都会变成沮丧和焦虑的世代萎靡”[6]330。
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和60年代反战运动的亲历者,斯蒂芬·金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消极避世观的影响,如《闪灵》中饱受事业打击、生活落魄的杰克·托兰斯在酒精的引诱下参加了瞭望酒店的酒会,这场被恶灵控制的酒会场景描写无疑就是受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启发,所有的与会者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伴奏下吞云吐雾,交换酒精和迷幻剂,杰克·托兰斯深陷其中,精神逐渐失控。《克里斯汀》中的高中生受恶灵蛊惑开着一辆二手普利茅斯Fury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车上电台震耳欲聋的诸如DeadMan′sCurve的摇滚乐重重地冲击着主人公的耳膜,激励着他加速地奔向死亡,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一群瘾君子一边开车一边吸毒,跟着摇滚乐嘶吼,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除了放纵狂欢,苟活也是作家大多数作品的主人公暂时安抚伤痛的唯一出路,如《撒冷镇》里的卡拉汉神父,他因为失败而抛弃了信仰,最后狼狈地逃离了撒冷镇,将全教区的居民出卖给了恶灵;《宠物墓园》中的路易斯·克里德一心想通过墓园的神秘力量复活死人,结果却失去了好友和至亲,最后只剩自己疯癫而孤独地苟活。这些主人公失败的社会人生体验让他们放弃了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各种努力,认识到“胜利的前景”如同婴儿潮一代对改变世界的憧憬一样只是其角色认知的幻象,“苟活才是人生的真实目标”[8]。
斯蒂芬·金的长篇超现实主义小说《绿里奇迹》采用梦幻和寓言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曾经热情善良的人背叛信仰后,无法直面内心、无法得到精神救赎而孤单苟活的故事,引发了读者共鸣,连续六周蝉联《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是作家遁世、避世思想的代表作品。这个故事发生在冷山监狱,保罗·埃吉科姆是一个关押死刑犯的E区高级警卫,因为E区的走廊被铺上了绿色的油毡,而被称作“绿里”。黑人囚犯约翰·科菲因为被控谋杀了两个小女孩而被捕,这个罪犯在监狱期间表现得像上帝派来拯救人类的天使,他虽然智力低下,却心地善良、个性纯真,还拥有治疗疾病的超自然能力,他治好了保罗等多人甚至老鼠的疾病,种种迹象和线索都表明约翰不是凶手。保罗暗中调查后已经锁定了真凶,但由于错综复杂的法律取证程序、种族歧视、民众“要求立即声张正义”的激烈情绪等诸多因素,法庭始终拒绝重新审理这个案件,最后约翰被送上了死亡电椅。这让保罗的个人价值观和信仰与当时的社会规范产生了极大冲突——“我们扼杀了上帝的礼物……”面对要求处决约翰的义愤填膺的“正义群众”,保罗退缩并屈服了,但他也知道他无法直视心中的罪恶,无法坦诚地面对上帝。小说的结尾处保罗由于曾经接受过约翰的医治获得了生命的奇妙延长,但这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欢愉,老年的保罗常常念叨“上帝啊,绿里太长了”,长寿让他觉得是一个诅咒:约翰从这个丑恶肮脏的生活中解脱,所有的亲人朋友也都早逝于他,自己孤单地苟活到100多岁,这是对他执行了种族歧视背景下的白人法律而没有做出正确行为的惩罚。
三、结语
庄礼伟认为作为婴儿潮一代发起的社会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个中产阶级学生运动,所以他们将造反运动的目标锁定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而下等阶层的人迫切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因而不存在所谓抗议者和被代表者之间的友谊或者利益共同体的神话”[9]。并且,“这代人(婴儿潮一代)总是把个人利益和人生目标放在社群需要之上,随后就会沮丧地发现所依赖的社群分崩离析、家庭破裂、学校预算缩水、城市内部衰退、预算赤字增加”[10]。战后二十年的大变革给美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婴儿潮一代激情澎湃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去,然而社会的形态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马丁·路德·金也被暗杀,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日益加剧,他们眼中的世界变得可怕而狰狞,正如斯蒂芬·金在小说《爱上汤姆·戈登的女孩》(GirlWhoLovedTomGordon)中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的失望——“这个世界是一个长着獠牙的怪物,任何时候它都可能张嘴咬人”。作为通俗文学的大师,斯蒂芬·金一直在用寓言的形式讲述着这些真实世界的恐惧和悲伤、希望与迷茫、梦想与抗争、梦醒与幻灭,对婴儿潮一代的叹息、怜悯和对那个影响美国二十年的大时代的追忆都记录在作家对“时代英雄”自由意志和冒险行为的反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