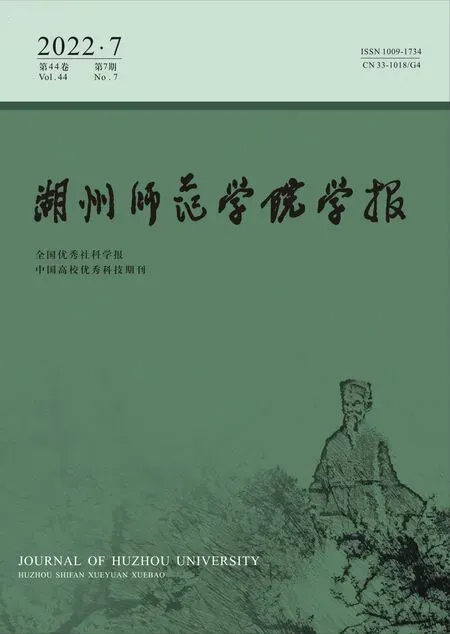走近夏文化*
李学功
(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发展研究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谈到夏史与夏文化,著名先秦史家詹师子庆先生(1)按,詹师子庆先生曾著《走近夏代文明》,先生以近24万言娓娓说“夏”,从夏史研究回顾、夏史研究中文献资料的运用、夏文化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中原文明领先地位的确立、鲧的传说和夏族的起源、夏史纪事本末、夏朝的国家形态、夏代地理蠡测、夏代邦盟探析、夏代物质生产和文化、夏代文明对后世社会的影响等11个方面,穷究夏史研究原生、次生、再生之文献与考古资料,博采诸说,汇纂于著。詹师并著有《古史拾零》,力倡建立中国礼学研究学科。本文即是学习先生著作的随感,并以此纪念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走近夏代》见真义,春风育李莫能忘,如门弟子心香祭。曾感言:“夏史好像是一座神秘莫测的山峰,从不同角度遥视它,会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受。为了解破这段历史谜团,前辈学者和当代夏文化探索者们付出了极大的艰辛。”[1]318
学术意义上重建夏史的工作,至少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开始,其标志即《史记·夏本纪》。走近夏文化,则绍自西周、春秋和战国,《豳公盨》的发现,以及孔子“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的感慨即其证。就夏史和夏文化研究而言,其实有两个层面或意义上的夏史和夏文化:一个是史籍文献学层面和意义上的夏史与夏文化,一个是考古学层面和意义上的夏史与夏文化。设若夏史和夏文化研究的两个层面随着新材料的涌现,在认识上能够逐渐达成共识,特别是考古发掘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则夏史将不再是“初曙”(2)按,徐中舒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曾发表《夏史初曙》一文,对夏史、夏文化研究寄予厚望。详见:徐中舒:《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第 12-15页。,当然,或许这仍将是一个漫长无期的等待过程。鉴此,就夏史与夏文化问题,谈些不成熟的认识。
一、夏社会经济
论及夏代社会经济,除却一些基本的文献资料外,不能不提及20世纪50年代末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1959年开始的在河南偃师进行的二里头文化发掘工作。这一发现以及考古工作者其后在山西东下冯等地进行的二里头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使长期疑而未决的夏史的可靠性问题,自此有了落实的可能。尽管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工作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但有一点人们则是大致认同的:历史上应有一个夏代,它起码与二里头文化的某个部分有比较直接的联系,考古发掘所及,夏文化已在其中。据此,借助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当可一窥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一般面貌。
(一)夏的生产工具与农耕技术
考古资料显示,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以农耕为主。夏代农业生产继续向前迈进。生产工具似仍以木石类居多。其中有以石器为主的铲、刀、镰、斧、凿、杵等,亦有蚌质为主的铲、刀、镰以及骨质的铲、镞、锥、鱼叉等。木质工具由于易朽腐,很难保存,故迄今考古发掘中尚无大量发现,但因为它来源方便,加工容易,确是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之一。《韩非子·五蠹》即有“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记载。耒为古代常用工具,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中均发现有用耒痕迹。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时限:龙山文化晚期—夏代)发现有数十件木质器物,其中就有为兵器、生产工具安装的木质柄杆。准此,夏代用耒应是可信的。
至于铜制工具,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有刀、锥、镞、凿、戈、锛等青铜器具,同时还发现有铸铜遗址。只是截至目前,尚未发现青铜制造的农业生产工具。考诸史籍,文献亦仅言:夏禹时“以铜为兵” “铸九鼎”(《越绝书·记宝剑》《左传·宣公三年》),其间并无青铜以铸农具的史影。
农耕技术上,史载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表明夏处于耜耕农业阶段。史籍并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并说佐禹治水的农官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孟子·滕文公上》),禹则“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此皆反映出夏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并懂得了水利灌溉对农业的重要性。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标志着夏时人类改造自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禹平水土,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时,除了开沟洫灌溉、排涝之外,还可能利用了地下水源。传说“伯益作井”(《世本·作篇》),在考古发掘中也确有古井的发现,除供人畜饮水外,用于井灌也不无可能。夏时已有了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夏时”,按12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每月的星象、气象以及应从事的农事和政事。凡此,皆说明夏时的农业生产技术的确有了长足进步。孔子即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对夏文明颇多称许。
(二)夏的田制与剥削形态
首先,“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所透露的夏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结构形态。在前工业社会,“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2]482-483,考察夏生产关系的变化,自应以此为钥匙。
在夏代的考古发掘中,尽管迄今尚无文字材料直接坐实,存疑、假说、待定之处亦多,但在当代考古学中,对夏史可靠性的支持还是大量的,可凭据的。如前所述及的夏文化代表性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皆从时间(年代时限)、空间(地域范围)上提供了夏存在的可信证据。至于在中国文化典籍的朝代传承系统中,夏的存在更是明确无疑的。鉴于目前以考古发掘资料证夏史尚有诸多困难、局限,故对夏代土地制度的研究,仍需依赖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在传世的文献资料中,较早讲到夏代田制的当推《左传》。
《左传》哀公元年谓,昔夏少康避难有虞时,虞思对少康曾“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夏少康在纶邑拥有田一成、众一旅,励精图治,由此奠定了中兴的基础。晋杜预就“成”“旅”作解曰:“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考工记·匠人》云:“九夫为井”,井方一里,“方十里为成”,一成即是百井。东汉郑康成在注《周礼·小司徒》时指出:“一旅之众而田一成,则井牧之法,先古然矣。”明白无误地点明了少康时已行井田的事实。此外,《夏小正》亦有“初服于公田”的说法。足见,夏代(特别是它的中后期)已有“公田”“私田”的划分,已有所谓“井田”制度的存在。
夏少康之世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表现为井田制,与社会结构表现为村社制是密切相关的。其时,夏之立国发展去原始社会未远,在原始社会内部已是积久成俗、十分牢固的聚落共同体形式不可能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一下子销声匿迹。不唯不能,而且这种共同体还相当牢固,个人尚在共同体的强有力的钳制之中。正如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公社的耕地还是共同耕种的”,“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3]541夏之情势,与恩格斯所论说的雅利安民族、俄罗斯人社会,其实并无质的不同。夏在迈入阶级社会门槛之后,在尚自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作用下,不仅没有消除原始的集体共耕现象、脱离村社共同体,相反,还将其保留下来,并凭依着这种原本固有的、十分便当且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系统(村社),使之成为立国施政的基础。翻检《左传》,不难看出,夏少康正是凭借其所拥有的村社经济单元,如纶邑,作为基本力量“复禹之绩”的。
其次,“夏后氏五十而贡”昭示的是夏代的剥削方式。由于资料的缺乏,有关夏代剥削形态的具体情况十分模糊。战国时代孟子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孟子·滕文公上》),引起后世学者纷纭不一的种种说解,至今余波犹在。“贡”字虽晚出,但作为一种剥削方式,贡纳制在历史早期,如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实行,实无疑问。夏代去原始社会未远,其前期亦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故夏代行贡,亦属正常,只是限于材料,贡的具体内涵已无法确知了。

过去,一些学者常目“夏后氏五十而贡”之贡为田税,实际这是以战国之贡为夏贡,“非夏后氏之贡法”(4)胡渭:《禹贡锥指》,详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说到底这都是不从发展上看问题的结果。孟子所言“五十”“七十”等数目字,很可能只是孟子的虚拟、推想,是孟子的用数习惯或口头禅,一如孟子习用之“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五十镒而受”“七十镒而受”“子男五十里”“伯七十里”之类。对此,杨伯峻亦言:五十、七十、百亩之数,“这只是孟子假托古史以阐述自己的理想,古史自然不如此”(5)详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第121页脚注。。此外,贡法征收之率如何,因史无足凭,不便妄测。但贡的性质应当可以看得出来,那便是,贡(包括其后的助、彻)根本不是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是封建性质的东西。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论:“贡、助、彻是表现封建生产关系的地租名称。……夏朝的贡法,可以说是封建生产关系的最原始形态。”[6]52
二、夏社会阶级结构
夏社会阶级结构的特征是族社首领、官吏和剥削者的三位一体,族社成员、臣民和被剥削者的三位一体。那时,尚无后世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体剥削者,也不存在独立的、个体被剥削者。
首先,村社首领、国家官吏和剥削者的三位一体。夏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政治单元是族社。族社既是一种地缘组织形态,又是血缘组织形态,与希腊颇不相同。在希腊,甫进入国家时期,血缘的纽带就基本断裂了,农村公社成为一种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体。而中国则不是这样。在中国,家族公社与农村公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是一种以血缘家族组织为外在形式,以“公”“私”二重性的族社为基本内容的复合型社会组织结构形态。在这里,族社所饰演的角色不是“过渡”,它并没有随着国家时期的到来而退场、消失,相反,却成了早期阶级社会赖以存在的坚实基础。这种族社,既是生产编制,又是行政编制,颇有些“政社合一”的味道。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族社的“变”,事实上,变还是有的,进入国家时期的族社已与原始社会末期的族社大不相同——国家的威权色彩、阶级社会的影响、对剩余产品的掠夺等,都已经沿着不同的途径渗入族社内部。从政治上说,这时的族社,已由原来自立、自治的单位变为早期国家政权的基层行政单位,原为族社服务的族社首领已蜕变为君主的臣僚、下级官吏,成为统治集团、剥削者集团的一分子。并由此构成了族社首领、国家官吏和剥削者三位一体的统治关系格局。文献记载的有虞氏、有穷氏、有仍氏、有鬲氏、斟灌氏、斟寻氏、陶唐氏、伯明氏等活跃在夏的大的姓族部落,其本身就是一个个集血缘团体与地域行政编制于一体的复合型社会组织。这种较为牢固的共同体的存在,表明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个体尚不足以应对严峻的生存挑战。当时,个体小家庭虽已出现,但其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参与,仍是通过族、村社,并以族、村社的面目进行的,它仍包容在共同体之中,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生产、生活单位。各姓族部落之下,包含着许多个家族公社,即村社,家族公社(族社)则由若干个体家庭组成。这样,便形成了部落、家族公社(族社)、个体家庭三级而以家族公社(族社)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体系。夏少康复国前曾在有虞氏的庇护下,领有纶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此时夏少康的身份正是集族社首领、官吏、剥削者于一身,肩负着组织生产、管理居民、征收贡赋等项事务。夏少康在纶的族社首领、官吏、剥削者合一的身份,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夏统治阶级的基本构成形态。有夏一代,剥削、统治集团中的剥削者(财产拥有者)、统治者(权力拥有者)、家族长等不同社会角色还没有分离开来,这是由夏尚不存在土地私有、个体的人尚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以家族公社形式出现的族社尚是国家社会的最基本的经济、政治单元的状况决定的。
其次,族社成员、国家臣民和被剥削者的三位一体。夏被统治者的社会角色定位,表现为族社成员、国家臣民和被剥削者的三位一体。这是因为,处于早期国家时期的夏,既不会像原始社会那样,仍以氏族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而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制约,亦不会像战国以后那样形成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那时,基本的生产单元和生产组合形式是“井”,即家族公社、村社,个体家庭尚未完全从家族公社、村社,亦即“井”中独立出来。因此,夏代国家对剩余产品的剥削也是通过族社、面对族社的,而非面对具体的个人或个体家庭。国家对族社的剥削,在初尚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还只限于在“贡”的名义下向村社责取一定的贡纳,大概到了中后期,才渐趋规范化,才有了较为明确地圈定出专供上面剥削的公田之举,于是助法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夏代前期是行用“贡”法的,中后期则用“助”法,《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贡”(《滕文公上》),《夏小正》言“初服于公田”皆有所本。夏被剥削者——族社成员的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身份,当然不是什么奴隶,他们所受的剥削,当然亦不是什么奴隶制的剥削,这样的社会也自然不是什么奴隶社会。长期以来,人们靠“第一个阶级社会必然是奴隶社会”的所谓“普遍规律”来推定夏代之为奴隶社会,即使在没有任何史料支持的情况下也深信不疑,安之若素,这是一种十分要不得的学风。当然,也有学者觉得单靠泛泛之论,终难服人,于是,亦间或有举证奴隶史料的论著出现,但所举证之史料皆难以支持其说。如百卷本《中国全史·中国远古暨三代政治史》的作者在言及夏为奴隶制国家时,即曾列举“奴隶”史料三则以证:一为据后人《楚辞天问》注,言启灭有扈氏,曾将其部罚作“牧竖”;二为少康在有虞氏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三为启伐有扈氏时作《甘誓》,其中有言“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7]78第一条,即通常所谓的“种族奴隶”“集体奴隶”根本不成立,因为不过是征服后令其贡献牛羊而已。此处之“牧竖”,一如后世之“亡国奴”,只是在政治含义上使用的,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第二条,只是讲有虞氏给少康一块地盘,连同人众,如此而已,同奴隶完全无涉。第三条,虽可释作没为“奴”,但这在长期阶级社会中历来有之,并不足以据此证明夏是奴隶社会;况且,对“帑僇女”(此据《史记·夏本纪》引,《尚书·甘誓》作“孥戮汝”),学者间尚有不同解释,如有学者即解释为:不但诛杀本人,且连及子孙[8]451。
由上,从两个方面讨论夏社会阶级结构的问题,试图说明,在夏社会结构中族社居于主流、主导地位。正是由于族社的顽强存在,才排拒了统治者对土地的私有和对个体劳动者的奴役,一切都在“国家”“公有”的名义下无声地进行。由于资料的缺乏,颇难说清夏社会阶级结构的具体内容,但从整体角度分析,说夏阶级关系体现为一种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对三位一体的被统治集团的关系,应是大致不差的。
三、夏国家行政机构
从国家行政机构的建构形态看,夏国家行政机构无论与商周,还是与以后的秦汉相比,都具有一种“原生性”特质。据现存吉光片羽的有关夏的文献资料,夏国家行政机构尽管原生的成分、色彩十分浓重,但大体上还是具备了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组织形态的雏形,夏代社会的国家属性还是清晰可辨的。
(一)中央国家机构
《礼记·明堂位》记述虞夏商周官制时曾言“夏后氏官百”,表明夏国家官僚机构的框架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从现已了解到的有关夏代一些职官的名称与职守看,夏中央行政机构的官员大致可分为高级政务官和具体事务官两大类。
夏的中央高级政务官,见之于史籍的有:“五丞”“六卿”“三正”等。“五丞”,据载是禹时设。从《战国策·齐策四》“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的文意看,“五丞”当是夏后(王)的辅政大臣,地位甚高。“六卿”之名见于《尚书·甘誓》。启伐有扈氏时,曾召“六卿”议事。“六卿”对夏后(王)的决策拥有建议、咨询、议决之权。《尚书·甘誓》中还提到“三正”。启讨伐有扈,将“怠弃三正”列为有扈氏一大罪名。说明“三正”地位在夏代颇高,或许是六卿中权位更高的三人。从“五丞”“六卿”“三正”的职守情况看,他们极有可能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核心机构的初始形态。
高级政务官之下,还设有一些具体的事务官,细析之,也可分为两类:一类属政务性事务官,一类属宗教性事务官。政务性事务官,见诸史籍的略有:
稷。主管农事之官员。见《史记·周本记》。周之始祖弃,即曾出任虞、夏之稷官,世称“后稷”。以后周之祖“不窋”亦曾出任此职。
车正。主管车辆之事。《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杜注云:“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
牧正。主管畜牧业之官员。事见《左传·哀公元年》。据少康曾为有仍牧正推断,夏王朝中央亦当有此职。
庖正。主管膳食之事。《左传·哀公元年》谓少康曾为有虞庖正,中央亦当有此职。
水官。主管水利工程。《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谓殷之先祖冥曾为夏之水官,且死于职任之上。
六事。统兵武官。《尚书·甘誓》载有“六事之人”,《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各有军事,故曰六事。”
夏宗教性事务官,见于史籍者略有:
官占。负责卜筮。《左传·哀公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杜注云:“官占,卜筮之官。”
太史令。负责“图法”。《吕氏春秋·先识》:“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
天地四时之官。负责天文、历法。《史记·夏本纪》载:“帝中(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集解引孔安国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时之官。”《史记·五帝本纪》谓早在尧时,就“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集解引孔安国曰“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说明羲、和二氏乃世代为天文历法职守之官。
以上,仅是据史籍所能稽考者勾勒出的粗线条的夏代中央国家机构的基本架构,其实际内涵,当更丰富些。
(二)地方行政机构
《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表明夏可能已行分封制。禹还曾“别九州”(《尚书·禹贡》)。《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禹划九州说,彝铭亦有反映,如春秋时器《叔夷钟》载:“成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既然春秋时人多承认禹划九州,《尚书·禹贡》(6)按,关于《尚书·禹贡》的成书年代,学界多有争议。金景芳先生等认为成书于春秋初,其内容当或更早。可从。详见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第297页。关于禹别九州的记述多少会含有一定的史影。这说明,夏禹之时确已开始进入国家时期,为治理方便,从大的方面依各姓族部落、方国所在区位,对夏之“国土”作出一定的区划,应是可能的。当然,这种九州之别,当是十分粗略的,与后世严格意义上的郡县制远非一回事。此亦反映出夏代国家的早期性和不成熟性。
夏的地方行政机构,当由受夏所封的同姓或异姓部族、方国构成。如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有仍氏、有虞氏、昆吾、葛伯等。这些大的姓族部落、方国组成了夏代国家的第二级政府形式——地方政权组织。据现所掌握的零星资料,夏王朝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确乎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其首领或在中央任职,或职司地方,接受夏后(王)领导。他们平时需向夏后(王)贡纳一定的财物,即服“贡职”(《说苑·权谋》);参加夏之盟会,如启之“钧台之享”、桀之“仍之会”等;并通过“来宾”“来御”(7)“来宾”,《尔雅·释诂一》:“宾,服也。”“来御”,《尔雅·释诂二》:“御,进也。”等形式,申明、巩固与夏的臣属关系,如《古本竹书纪年》即载有“于夷来宾”“方夷来宾”“九夷来御”等。虽然进一步的情形不得而知,但夏国家既能“以国为姓”“别九州”,则表明夏通过同姓及臣服于它的各大姓族部落、方国,已能对“天下”“九州”实行直接或间接、有力或松散的控制。
(三)基层社会组织
过去,有学者论及三代基层社会组织时曾将之目为奴隶劳动集中营。遗憾的是,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考古发掘材料均难以对此类说法提供有力的支持。有的虽承认中国早期阶级社会中族社存在的事实,却囿于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3]449的论断,立论持说往往是首鼠两端,使人不知所云。由于传世文献中关于夏代的史料本就不多,涉及行政机构特别是基层行政机构的资料更是支离破碎,因此,有的论著竟干脆将夏略去不书。但夏既载于简帛,且作为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第一个王朝,对其社会结构和基层组织面貌只字不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应一切准之以事实,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夏国家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无疑是族社一体的村社。众所周知,农村公社见诸人类历史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东西方间村社内部公、私二重性因素消长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古代东方社会中,村社不但没有迅速、完全消除原始的公有制传统,反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牢固地保存了它,其突出表现便是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实际上仍然归整个村社所有。这样一种状况,就使得村社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不仅没有解体,反而长期留存下来,成为古代东方早期阶级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作为古代东方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中国,在夏商周三代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村社在三代既是一种血缘组织,又是一种生产组织和行政组织,可谓血缘与地缘的合一,政社的合一。这与马克思对农村公社所作的“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的论断显然是不同的。在中国,村社的血缘色彩十分浓重,村社往往就是以家族公社的面目出现的,一个家族公社(村社)由若干个个体家庭组成。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组成家族的家庭数及家庭人口数的不一,村社规模亦大小不等,不会如古书所描绘的“井田”那么整齐划一。民主改革前,少数民族地区残存的如鄂温克人的“乌力楞”、独龙族的“克恩”等社会组织,即是这类性质的家族公社(村社)。
夏国家依靠各大姓族部落、方国,建立起对地方的统治体系;而各大姓族部落、方国又仰赖于传统的基层组织——族社,将这种国家统治落到实处。族社既承担着生产的组织者、家族的管理者角色,又负有上交贡赋、提供兵役、劳役等诸多事务的责任,是一个微小的社会组织机构。史籍称夏少康复国的基地——纶邑,“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左传·哀公元年》),杜预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便是一个包括有众多族社的区域性政治集合体。
四、夏意识形态
过去,说起思想史上的夏代,史家往往因资料过简、无征而略去不提或一笔带过。这是不对的。既然我们把夏目为中国进入国家期后的第一个王朝,那么,对夏的思想文化就不能采取规避的态度。实际上,有关夏的思想材料虽少,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它不仅存在于后人赓续不断、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及断编残简中,也存在尘封于地下的遗存中。如传留的《夏箴》《夏小正》《尚书·虞夏书》及“大禹治水”“禹征三苗”“涂山之会”“禹铸九鼎”“甘之战”“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书传、传说,都不会是任意编造的,而是有所凭借的。再加上考古学在夏文化探索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都无疑为人们认识包括夏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夏社会面貌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夏自不例外。因此,研究夏意识形态,也主要是把握它的由统治者编织、锻造的主流意识形态。据现有资料,夏已形成了与原始社会迥然不同的具有鲜明国家色彩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家天下”之国家观
国家观中的“家天下”意识和观念,是夏统治者对统治族其他成员及广大被统治族行使统治权的理论辩护。因为初起的国家要在人们心目中得到认可,除暴力一途外,还需要相应的官方意识形态提供理论的说明、支撑,以争取更多的人对以夏王为代表的夏统治集团实施的国家、社会整合、统治的认可。另外,在古代中国,“家天下”观念的出现,也是当时血缘关系强固、“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9]32这一特定社会构成在国家架构上的反映,表现出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形态上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鲜明特征。“家天下”的理念根源于家族、村社所培育的族、社合一思想,又是在族、社基础上对权力、领地范围的一种放大。“家天下”局面的实现,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绵延数千年的王朝体系。尽管在初“传子”“世袭”制的确立经过一些反复,国家统治机构亦相对粗糙,王权的贯彻还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它一开始所奠立的这种根本不同于希腊城邦政体的,以追求大一统和至高王权为依归的体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走向。夏立国伊始,就以建立一家一姓王朝的统治为基本目标,并为此构建起为一姓政权辩护、并使之具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家天下”观念。历史证明,夏统治者为赢得以家为国、以国为家合法性所进行的这种努力,取得了成功。禹、启父子两代凭借家族积蓄起来的势力和个人才能开创了传子制、家天下的格局,也播下了家天下的观念种子。史称禹死,“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一来是“启贤”,再则,也是诸侯们都以“吾君帝禹之子也”为由,纷纷“去益而朝启”(《史记·夏本纪》),不由益不“让”出王座来。后虽有有扈氏的不服,有太康的失国,但传子制、家天下的观念并未因此而动摇,少康的“中兴”,正是得益于族的势力和身为禹后的人心力量。这种“家天下”的思想植根于血亲宗法,使人们很容易达成家国一体、君父一体的理念认同。因为人们虽可超越、无视、甚至拒绝来自行政的、外在的制约或命令,却无法摆脱、割断与之血脉相连、生死相依的族的血亲、共产联系。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管是谁王“天下”,都只能凭借族的势力、以家族代表的身份王“天下”。因此,在当时,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家天下”和观念形态上的“家天下”都是难以避免的。夏王朝一家一姓王朝体制的创建成功,使夏本身成为一种统治范式,这种范式被后人连同商、周一起誉之为“三代模式”——一个典型的家国一体的家天下政权模式。正像《汉书·盖宽饶传》引《韩氏易传》所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二)“九州”之“天下”观
随着夏人建立起自己的家天下国家,夏人对“天下”的认识也变得日渐具体起来,于是便有“九州”说法的提出。《尚书·禹贡》《序》云:“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亦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春秋《叔夷钟》铭亦谓:“成唐(汤)……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
《禹贡》虽晚出,但夏时已有“九州”却是可信的。此时的“九州”虽远没有后世那样辽远,也不是正式一级行政建制,但已显露出一定的按地区来划分国民的国家特性,且这种划分的终极目的——剩余劳动的榨取即所谓“任土作贡”,也已十分清楚。所谓“九州”“天下”,是当时人们对所能知见世界的一种粗略表述,其隐含的政治诉求乃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者对统治区无限扩大的强烈企盼。此说一出,便很对中国古代统治者追求政治大一统的胃口,很快成为夏乃至历代封建王朝追求、宣扬“大一统”思想的精神锚地,并深刻影响其后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便是迄今仍挥之不去、萦绕人们心头的“九州情结”。
(三)“祀夏配天”之宗教观
夏立政之初,粗糙处颇多。当时的所谓王朝体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色彩。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自禹、启至于少康,夏王朝经历了一段并不轻松的过渡、动荡期。其间既有族人有扈氏的不服,也有夷人有穷氏后羿代夏的巨大变局。至少康中兴,夏的国家职能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缘,国家面貌才大体有个样子。出于维护夏一姓家天下统治地位的考虑,夏少康时,统治者强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宗教的渗透与改造,从而使原始的宗教一变而为打上族姓国家烙印、为巩固王权服务的新意义上的宗教。史称少康“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杨伯峻认为:“依古礼,祀天以先祖配之,此则祀夏祖而同时祀天帝也。”[10]1606将夏王室的“祖先”与“天帝”平列一起祭祀,表明夏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立特别的宗教仪式来加强夏朝的国家意识形态”。[11]377《国语·鲁语上》载,夏人已按国家大典的规格祭祖,“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鮌而宗禹。……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褅 、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这是借助隆重的宗教仪式,对夏之先祖进行礼赞、神化,在世人面前捧出一尊祖、君、神三位一体的偶像来,以神权辩护族权、政权。考古发掘亦显示,二里头遗址墓葬区发现有多处与祭祀有关的坛、墠类建筑基址,清楚地表明是祭祀鬼神的场所。[12]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