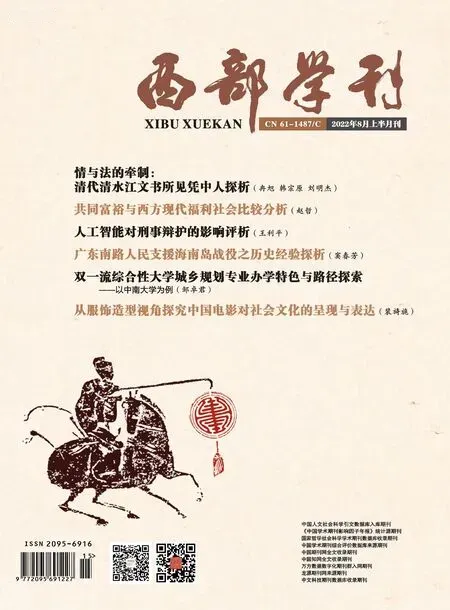儒家政治伦理与地缘政治战略
——先秦至宋的“德”与“险”关系思辨
徐自恒
葛汉文在《心脏地带、帝国威望与意识形态——中国地缘战略传统及其效应》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有“反地缘政治”的传统,即遵循儒家政治伦理,反对使用武力进行征服、扩张甚至于保卫政权的地缘战略,实际上这个思想传统在先秦至宋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对“德”与“险”关系的思辨。
“德”与“险”的关系问题在先秦就已经被讨论,“德”是指儒家话语体系中的以仁义道德、礼乐教化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险”一开始指地理空间中的因地形而形成的险阻,后世其内涵扩展到使用军事手段保卫政权的地缘战略,在儒家的政治伦理中,两者呈现对立的态势。随着先秦至宋国家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也不断变化。
一、“在德不在险”思想的形成
“德”与“险”问题的讨论始于先秦,《周易》首先肯定了“险”的价值,《左传》提出了“德”“险”之辨的问题,孟子以“地利不如人和”首先回答了“德”“险”轻重的问题,至西汉《史记》中吴起对魏文侯的“在德不在险”成为一种经典表述。先秦至汉代关于“德”与“险”关系的表述,成为后世反复引述和讨论的对象。最早对“险”的论述出自《周易》“习坎”卦的彖辞:
坎卦第二十九: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周易》经传并行,“彖”作为“传”的一部分是对于“经”的注解,学界对其经传各自的创作年代争讼不一,主流的看法是“经”作于周初,“传”作于春秋战国。“习坎”卦象为两“坎”相交叠,大致是指一种困境,上述“彖”对“习坎”卦逐句解析,而最后一句“天险不可升也……大矣哉”是一个总结和评论,程颐对这句话的理解是:
高不可升者,天之险也。山川丘陵,地之险也。王公,君人者,观《坎》之象,知险之不可陵也,故设为城郭沟池之险,以守其国,保其民人。是有用险之时,其用甚大,故赞其“大矣哉”。
在程颐的理解中,这句彖辞是说“习坎”卦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天险”不知为何,“地险”指地形地势,“设险”指人为建造的防御工事,“天险”“地险”“王公设险”是并列的关系,但“设险”的意思是在“天险”“地险”之外“造”人为的“险”,还是在“天险”“地险”上“设险”,还有探讨的空间,但“设险守国”无疑指向了一种军事手段,春秋战国诸侯争霸使得当时对地理事物的认识突出其军事属性,《周易》的这则彖辞即反映了这个时代特点。
《左传》首先提出了“德”“险”之辨的问题,在昭公四年的“传”中有司马侯谏晋平公的一段话:
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州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
《左传》中与“德”相对的是“险与马”,“险”常在而守险之国却有兴亡,所以“险”不足恃,“马”代表的是古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强的骑兵,骑兵的多少决定了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所以与“险”同指军事实力,“险”在当时的含义是确定的,就是指地势险阻。《左传》的作者等相关问题在学界尚存争议,但从这段话至少可以得知在春秋战国时已经出现了“德”这一理想的政治秩序高于军事手段的观点。
孟子也有类似的更细致的论述,虽然没有提及“德”与“险”,但也是将军事手段与儒家理念放在政治范畴中进行比较,分辨两者孰轻孰重、谁高谁低,实际上是相同的问题: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在先秦“地利”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军事上的,如《六韬》对地利内涵的表述为:“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二是指经济上的,如《管子》中的:“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此处的“地利”从“城”“池”“兵革”“米粟”来看指向了城池的攻守,以一城之守为例推而广之,是“封疆之界”“山谿之险”“兵革之利”,即用武力划分疆域、统治国家的手段,结合孟子“王霸之辨”的政治理念,指向了“以力假仁”的“霸道”,与此相对的“人和”或“道”虽然没有解释其中的内涵,当是指“以德行仁”的“王道”。孟子对于“地利”的认识是其政治理念在地理问题上的投射,“王道”的理想化的统治理念高于对现实地理优势的利用,这为之后汉代对“德”与“险”的认识定了调。
在汉代,大一统的秩序确立,儒家的政治理念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思想界掀起了对战国权谋批判的热潮,如刘向在《战国策》序中所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不可以临教化。”在这个背景下,如果说战国时孟子的“王霸之辨”是对诸国以“力”相争现实的反叛,那么两汉对“德”的重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汉代对“德”“险”关系的认识,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德不在险”,这个表述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
这则史料已难以溯源,但就吴起的政治军事实践而言,他表达的这个观点似乎与自己的行为不符。王应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解释是:“起兵家者流,然尝学于曾子,故能为此言,非能践其言也。”吴起的这则言论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后世的演绎,留下了一些遐想的空间。回到这则史料中,其所要表达的就是君主若无德,则虽有险亦不能保有政权,与孟子“地利人和”论异曲同工,在这里“地利”被“险”这个明确指向地势险阻的概念取代,对于“德”的内涵虽然没有明确的表述,但列举了几个暴君作为“德”的反面例子,这样的表述自然地把“险”与暴君无道的统治手段联系了起来。
这样的认识在这之前已有先声:
《吕氏春秋》: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
《淮南子》:武王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迴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
上述引文虽然出处和表述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都认为“险”是暴君才需要的手段,要统治者彻底放弃守“险”,以便朝贡明君或者讨伐暴君,君主的“德”即是“险”本身,与孟子的“暴君放伐”论类似,只是在这里与地理问题相关联。这样就把“德”“险”关系引向了“德政”与“暴政”的对立中,刘向的《说苑》中就将吴起对武侯这则史料放在了“贵德”一章,可见在当时的知识界,这似乎是儒家政治伦理范畴中的问题。
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举《盐铁论》为例,作为会议记录,尤能看出当时上层知识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险固”这一专题讨论中,共收录六人的言论,其中四位贤良文学所述即“在德不在险”的观点,两位大夫所述的是边防和战国的地缘战略。观点的差异或许是因为身份不同,政府官员更关注现实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在德不在险”是被当时知识界所广泛认可的。
可以看到,“险”作为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事物和儒家政治理念相交汇,产生了特殊的意义。从孟子认为“人和”高于“地利”,到“在德不在险”将“险”与“德”政相对立,开始象征一种不义的、暴力的统治手段,使得对“德”“险”关系的认识逐渐陷入儒家政治伦理的思辨中,失去了地理学范畴中的意义而成为一种衬托“德”的象征符号。虽然“险”在政治实践中十分重要并且一直被统治者实际关注着(如历代皆有编绘地图、地志之制),但在儒家的政治文化中是不提倡的。
二、汉至宋对“德”与“险”关系认识的变化
汉代形成的“在德不在险”的认识至宋以前没有太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已经被统治者所认可,在苻秦永兴二年(公元358年)薛赞对刚刚讨平军阀张平进据关中的苻坚建言:“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竄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苻坚的反应是“大悦”。又如《魏书》所载群臣请北魏太祖加固京城,他就以“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为由拒绝。可见,“在德不在险”即使是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也已经被广泛认可,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
知识界总体上延续了汉代的观点,但也出现了不将“德”“险”视为对立矛盾的观点,同时注意到了“德”“险”之辨的学术谱系,如三国两晋时人陆机在其《辨亡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人有言曰:天时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言守险之由人也。”这段论述提到了《周易》的“设险守国”、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与“在德不在险”三个代表性的观点,总体上是以孟子的观点为纲,下面他的论述表现得十分明显: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达经国之长规,审存亡之至数,谦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是以其安也,则黎元与之同庆,及其危也,则兆庶与之共患。安与众同庆则其危不可得也,危与下共患则其难不足恤也。
其与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类似,而其中并没有表达“险”不如“德”,而是认为“德”的缺失导致“险”也无法发挥作用,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已经有并重的趋向。
“德”“险”并重被明确提出是在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中,有一专门论题为“议守险德与险兼用”,在这里他首先自设了两个问题:
问《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记》曰在德不在险,然则用之则乖在德之训,弃之则违守国之诫,二义相反,其旨何从?
何则苗恃洞庭,负险而亡,汉都天府,用险而昌,又何故也?
上述第一个问题最为重要,直指儒家政治伦理范畴中的“德”“险”关系本身的矛盾,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要“设险”,但后来的儒者又说“在德不在险”,到底应该遵从谁的?白居易给出的答案是“兼用”,其中有两重含义,一是是否用“险”要根据时势:“天地闭否,守之则为利;天地交泰,用之则为害。盖天地有常险,而圣人无常用也。”二是区别“德”与“险”发生作用的领域:“以道德为藩,以仁义为屏,以忠信为甲胄,以礼法为干橹者,教之险,政之守也;以城池为固,以金革为备,以江河为襟带,以丘陵为咽喉者,地之险,人之守也。王者之兴也,必兼而用之。”在他的观点里,“德”负责形而上的部分,“险”负责形而下的部分,自然也就没有矛盾之处了。因为“德”“险”要兼用,所以第二个为什么同是据险却成败不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白居易的“兼用”论是为两宋“德险并重”论的先声,但这种观点在宋以前只是“在德不在险”主流中的昙花一现,我们可以做一推测:有透露出“并重”意识的陆机生于孙吴灭亡之际,白居易生于安史之乱后,社会的剧烈变动或许使他们在看待“险”的问题上更加实际。
三、南宋“德险并重”观念的形成
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战争不断,无论在北宋或是南宋,边防和军事都是极为紧迫的问题,这样的局势使知识界的目光不得不投向现实,出现了一批从历史角度研究地缘战略的著作,同时对于“德”与“险”关系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里的知识界指的是两宋时期的上层知识分子,虽然在他们中间很明显地出现了讨论的热潮,但都是在地理学范畴外讨论“险”,是宏观层面的而非具体地理问题的讨论,同时由于这些论述多见于私人著述,有很强的主观性,就现有的资料很难梳理出一个详细的两宋各个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图景,所以在此仅以观点的区别为线索,突出知识界对“德”“险”之辨的关注和认识上发生的变化。
第一种认识是“在德不在险”的观点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仍然是主流。《职官分纪》所记皇祐中侍御史徐宗况奏真州长芦江口因修建佛寺而拆毁古城壁之事,仁宗的回复是“朕方恃德不恃险设”。在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秘阁试论中,《形势不如德论》即其中的一道考试题目,在这次考试中苏轼以此题目所作的文章中,认为以“人”和“地”为“形势”,也就是分封和守险,并不足以捍卫政权。不论政治实践如何,对崇尚儒家思想的中央政权来说,必然要表现出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同时从苏轼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对保障政权安全手段的认识不仅限于地险,也涵盖了与地理空间相关的政治制度。
而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论述“德”“险”关系的“语境”,区别其目的是强调地理范畴中“险”的重要性,还是在儒家政治思想范畴中借“德”“险”之辨来说明一些别的问题。如:
《范太史集》谕城濠:臣伏闻开修京城濠,日役三四千人……然财出于民一也,岂可不计校爱惜而枉费用之……太祖因之建都于此百三十年,无山川之险可恃,可恃者在修德,在用人,在得民心……
《春秋说》夏城中丘:用民力于夏,非时也,不务德而益城,非政也……
《春秋通说》夏城中丘:……不修德政以为结人心之本,而区区以城郭沟池为固,轻用民力者,皆非也……
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指向了反对役使民力修建城垣壕沟等防御工事,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在这个问题上,城垣加固工程是过分消耗民力的行为,违背了儒家政治伦理,所以“德”“险”之辨在这里实际上是为他们的论述提供理论依据,重点不是地理空间中的“险”,而是“险”在儒家政治思想范畴中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
又如洪咨夔有诗曰:“天险以德强,地险以势阻。王公设人险,颇牧与羊杜。”“险”在其认识中分天地人,对此他有进一步的表述:“臣闻江流汤汤,万古一天险也,而飞渡者有之……天险在势,人险在德与政。君无阙德,天人交助,夫谁敢犯之。”他所谓的“天险”“地险”实际上指的都是地形地势,而“人险”就是贤明的君主,代表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理念,“险”在这里既是一种符号,也是在借“地险”强调“德”的重要性。
第二种认识中的“险”就是纯粹的地理范畴中的概念了,认为“德”与“险”应该并重,以下试举几例。这种认识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因素的影响,陈师道认为开封无险可守,只能重兵戍卫,导致“军卫多西戍,山东城郭一空,卒有盗贼乘间而作”,这就是违背“古者守国本末并用,建德而阻险”的恶果;身经靖康之变的徐梦莘更是痛感于此,批评北宋都城“无山川之险,四面受敌”,认为“恃德而不恃险者,危国也,惟险与德俱恃,国乃尊强”;南宋时人刘宰更加激进,面对岌岌可危的防线,彻底否定了“在德不在险”:“淮南一日未能按堵,则江南亦未容一日安处,江面风寒不止一处,海道四达无复蔽遮,则不容守在德之虚言。”
另外还有从历史的角度论证“德”“险”并重。胡宿认为上古圣王也定都于险要,他们“岂乏德哉?”因为他们遵循了《周易》“设险守国”的观点,由此进而驳斥“在德不在险”:“岂《易》之书故,不及春秋战国一时之辩乎?”吕祖谦认为周的衰败“非德薄,形势弱也”,这个观点出自《史记》,而吕祖谦明确地把“形势弱”的原因指向周丧失了关中的地利,通过周秦成败的对比得出了“德”“险”并重的结论:“秦得周之形势,以无道行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辅之以形势,其孰能御之耶?”
由此可以看到上述论述已经有将“德”“险”关系问题从儒家政治伦理思辨中分离的趋向,不再将其视为矛盾的两面,郑獬对这一点表达得最清晰,他将两者关系表述为“德者行于己,险者外御之”,并将重“德”轻“险”比作“蓄百金之箧,置之通衢,曰吾有德以守之”,区别了两者发挥作用的领域,自然也就没有矛盾的关系了。
第三种认识是受到理学的影响,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观点。这些观点都针对《周易》坎卦中的“天险”,将其内涵明确指向了等级名分,继承了理学宗师程颐的观点:
《五峰集》:故圣王明于天险,尊卑之分,贵贱之等,定天下之制而奸邪莫能越;明于地险,山川丘陵以为阻,城郭沟池以为固,而暴客莫能干。险设如是,然后能守其国。
《泰轩易传》:名分等制以象天险,金汤关塞以象地险,合天地之险而用之,则当用险之时。
《鹤山全集》:愚谓盈宇宙间截然有等级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险也。昔之人以大师为垣,以得道为助,以在德为险,以礼义廉耻为城,皆是物也……不明乎是而专以城郭兵粟为山川丘陵之守,则宁怪夫离合去来之无常也。
程颐在《伊川易传》中认为等级名分等理学思想与“设险”异曲同工:“山河城池设险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贵贱之分,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但程颐对“天险”的解释只是“高不可升者”,并没有与等级名分相联系,而上述观点则更进一步,直接赋予了“天险”以等级名分的意义,强调其至高无上,这是宋代理学对儒学更新的反映。
综上,汉代以后“在德不在险”成为主流观点并作为王朝官方的主流话语,但也有“德险并重”的观点出现,在宋代对“德”“险”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大的变化,“在德不在险”虽然仍是官方主流话语,但知识界的认识已经出现“德”“险”并重,剥离“险”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重新审视其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反映了儒家政治理念与现实时代问题之间的矛盾,面对游牧民族的铁蹄和国土的沦丧,代表着地缘战略手段的“险”的地位自然得到了提升。
四、结语
在先秦提出“德”“险”关系问题后,两汉时期对此有集中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在德不在险”的“德”重观念,长期影响着对“险”的认知;直到两宋时又有一个讨论的高潮,形成了“德”与“险”并重的观点。在“德”“险”关系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的支配力在时代变革和王朝秩序崩溃的冲击下一步步削弱,“险”即政治实践中的地缘战略逐渐从儒家政治伦理的思辨和争论中脱离出来,作为一种保卫政权安全的手段而回归现实。
①“险”的表述有时已经被“形势”所代替,与地理相关的“形势”最早在《六韬》中出现:“凡深入敌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势,务求便利,依山林、险阻、水泉、林木而为之固。”指地形地势,《史记》中也将“阨塞地利”称作“形势强”,但历代不同著述中含义也有所不同,在此不多赘述,至少在这一时期“形势”已经代指地形上的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