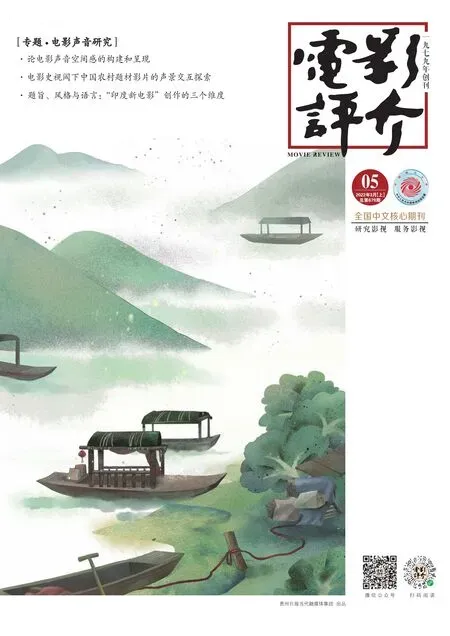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乡土叙事的艺术修辞
赵亚峰 赵亿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在党的十九大确立的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同样在这次大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用光影再现时代故事,以情怀抒写时代华章”为己任的中国电影创作者扎根乡土,聚焦田野,把电影“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创作出一大批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思想和实践的优秀电影作品,成为新时代电影创作的热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笼统而言,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是在指涉乡土的“言说”,即通过对乡土空间或乡土社会的影像再现方式完成乡土叙事。它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影像化的乡土“现实”世界,也是一种经过创作者比较、选择、修饰和加工的乡土艺术世界,即“修辞化”后的乡土世界,“就使‘常态现实’转换成一种‘修辞化的现实’,而成为一种必须重新‘感知’和‘再解释’的‘新现实’景观”。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乡土叙事的艺术修辞是内嵌于乡土叙事中的影像修辞,修辞的目的在于消解乡土的一般意义,强调和突出在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乡土特质,以及乡土世界的内在意蕴,以实现创作者希冀达到的效果。此类电影指涉乡土的艺术修辞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极其丰富的。本文主要从乡土物象修辞、乡土民俗修辞、乡土政治修辞这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这三种“材料”在乡土艺术世界建构中所呈现的修辞性特点,对于现在进行时的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创作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探索主旋律电影创作的艺术出路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乡土物象修辞
乡土物象是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中除演员以外的,又远比演员更加丰富的所有与乡土世界有联系的“物象”,其中“物”指的是乡土世界中的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如高山大川、土地房屋、生活器具、牲畜家禽等;“象”则是电影文本中“物”的影像表现形式,是指代“物”的符号,从“物”到“象”是经过修辞化的选择行为。
(一)乡土物质空间的再现:叙事的基础
乡土物质空间是由乡土物象建构起来的“可视的”“具象化的”乡土空间。建立在乡土叙事的情节架构之上,乡土物质空间的真实性是由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乡土物象共同组合而成的,镜像中的乡土物质空间为乡村振兴的叙事提供了最重要的环境基础。乡土物质空间的核心修辞首先是呈现了这一特定空间的乡土特征和地域色彩,如《十八洞村》,影片一开头就是云雾飘渺的群山、鳞次栉比的土家族民居,还有在阳光的直射下熠熠生辉的层层梯田等,这些画面迅速把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湘西乡土气息的村寨中。而《千顷澄碧的时代》呈现的则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和壮阔的平原等,让人感知到的是厚重的中原乡土特色。这些不同的地域胜景顺理成章地为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展开了铺排的空间。其次,乡土物质空间修辞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我和我的家乡·最后一课》讲述了生活在现代的人们通过“造假”让范老师回到了1992年的望溪村,而对创作者来说,这意味着要在同一个地点营造出两个时代的乡土空间:过去的村庄是土墙断壁、青砖小瓦、羊肠小路、木板小桥和乌篷小船,现在的村庄则是过河长廊、别墅院落、平整的水泥路、智能蜂箱等等,针对不同历史空间所框选的物象渲染出特定时代下浓厚的乡土氛围,也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
(二)乡土物象的意象性修辞:天地中的人心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叙事中的乡土物质空间首先是一个客观的空间。这一空间在叙事上最基础的要求是必须忠实于相关历史时空的原貌,其“逼真性”越强越容易被人们忽略,但它诗意的生发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通过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乡土物象,可以赋予电影文本更加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即通过“意象性修辞”来建构“意象世界”,透射出具有审美和象征意义的象外之象。乡土物象修辞有微观和宏观建构之分。所谓微观是对指代物的高度聚焦和具体化,比如《十八洞村》中多次出现的公鸡形象,因叙事内容的不同公鸡每次出现的寓意也有较大的差别。影片开始出现的公鸡打鸣场景暗喻男主角杨英俊的起早贪黑、勤奋劳作。在绝交酒仪式上的公鸡是以被束缚的祭品形象示人的,与同样被捆绑的杨懒互相映衬,此时大公鸡的符号显然意指懒汉杨懒。乡土物象修辞的宏观建构则是抽象笼统的,比如《出山记》中关于“家园”背后的意象,为彻底地摆脱贫困,大漆村村民有的享受扶贫搬迁政策离开了祖屋,进入城市的新家;有的为了打通进山的道路要拆毁自己辛劳多年才建起来的房子,重新再造一个新家园。这时不断出现的家园符号起码有了两种意义:一是大量破败的乡土物象,如雾气笼罩中灰暗的村庄、低矮潮湿的房屋,还有被挖掘机推倒的院墙,杂乱的瓦砾等,营造出一幅惨淡、压抑的乡村图景;二是许多富有生机的乡土物象又显示出了家的温暖、温馨,比如烟雨蒙蒙的高山下申学王家冒出的袅袅炊烟、屋里火红的灶膛等;还有申学科儿子儿媳回到家时,家里的母牛刚刚产下一头小牛,母牛正温情地“舔犊”等等,这些大量出现的乡土空间物象隐含着创作者的诗意想象和情感寄托。
(三)乡土特殊物象修辞:直抒胸臆的表达
特殊的乡土物象修辞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电影新技术创造的全新物象,一种是通过对立建立的一种“拧巴”的物象修辞,这些都是创作者心中所想之意最直接的表达和阐发。比起一般的乡土物象,新技术手段的运用使电影呈现的物质空间更加有想象力和超现实感,如《十八洞村》用特技制作了一只七彩的凤凰,当杨英俊在水田里劳作的间隙抬头望向天空时,这只凤凰正迎着太阳展翅飞翔,而凤凰所象征的吉祥如意、富贵幸福等意义是每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的渴盼,而这也正是创作者想表达的。特殊的乡土物象修辞还包括与乡土有关联的对比修辞手法的运用。所谓对比修辞是把两种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说明,乡土特殊物象修辞更强调通过影像比较后的对立结果。比如“城”与“乡”物象的对比修辞,《出山记》中的城市镜头只占全片的十分之一,借助搬迁户申周一家的视角所展示的城市是新城、新楼、新房的集合,与大漆村的陈旧衰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比修辞是导演主观意识的隐性表达。还有“土”与“雅”的对比修辞,主要指乡土的田园诗意与原始粗蛮的对比,如《平原上的夏洛克》中美丽的金鱼被养在塑料布中并吊在房梁上,乡村美景经常被恶心的小广告破坏,表现了乡村景象的复杂多样。特殊的乡土物象修辞是一种经过“实体—影像—创造”的再抽象,是电影创作者直抒胸臆的表达。这些亦真亦幻的场景既有某种隐喻的指向,也因奇特的空间营造而引人遐思。
二、乡土民俗修辞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乡土民俗与乡土物象的空间、物质不同,它往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以及精神世界产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一种写意的载体,也是乡土世界建构中的重要修辞手段。
(一)日常中的非常:乡土民俗形式的意指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传统乡土民俗是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存在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在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叙事中,存在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乡土民俗不仅仅是一种乡土日常生活的自然再现,也包含着创作者构建乡土日常生活的修辞意向。除了春种秋收、饮食起居之外,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和礼仪信仰等平常生活中的非常事项也成为电影突出表达的内容,在“仪式化”的场景中既有浓厚的历史感和乡土特色,也有强烈的修辞审美价值。如电影《一点就到家》在开场不久就有一组全村人载歌载舞、村长攀爬竹梯祭茶神的画面,在创作者的修辞意图中,种茶制茶是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的农事,祭拜茶神的民俗活动是他们对赖以生存的根基的一种祈福,而未来要让村民们砍掉茶树改种咖啡树将是十分艰难的。民俗活动潜隐的话语是:砍去茶树如同斩断这一代人的根,断掉他们与祖先的联系。再如《出山记》中申学科的儿子结婚,展现了中国乡村热闹传统的婚俗形式:浩浩荡荡的婚礼车队、震天的锣鼓和鞭炮声、拜天地仪式等——婚俗背后的寓意用这些直观形象的画面表达了出来,那就是泉里的路修通了,老百姓有盼头了,深山引来了金凤凰。
(二)陋俗和新规:乡土文化观念的隐喻
乡土文化观念与乡土民俗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它是指长期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拥有同一个文化环境的人们,逐步形成的对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基本的、比较一致的观点与信念。在乡土叙事的艺术修辞中,乡土民俗内含的文化因子会使其在修辞意向上与乡土世界的文化观念加以连接,构成乡土文化观念的某种隐喻。当创作者用现代理性的视角去审视乡土传统民俗时会发现,其蕴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观念,一种是落后、愚昧的被称为乡土陋俗,比如《十八洞村》中残障人士杨英连的女儿薇薇结婚了却不敢回家,因为她的丈夫施又成是一个不能嫁的人——施又成的先祖与全村人喝过绝交酒,按照民俗,所有十八洞村人将世代不与施姓人来往,更别说通婚了。还比如《出山记》中的申学科是一个孝子,专门为身患绝症的父亲请来了傩戏班子,这也是仡佬族人祈福纳祥、祛病消灾的一种民俗。但“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的颂词下却是一张张麻木无奈的脸,让观众感受到创作者清晰的价值选择和修辞意图。另一种与陋俗相对应的,是新的、先进的可以叫做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民俗。在乡土叙事中,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施成为了改变陋俗的一个契机,它通过叙事人物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最终“战胜”了旧的、落后的习俗,并建立起新的符合现代社会和主流价值所倡导的新民俗。比如《十八洞村》中的杨家人在驻村干部王申的帮助下,终于冲破旧规接受了施又成,作为一名新村民,施跟着残障的岳父学习起了“十八洞村的规矩”,而其中包含着的“尊重生灵,平等待人”等新条目预示着乡土文化观念发生的巨大变迁,这也构成了新民俗中乡土文化观念的另一重隐喻。陋俗和新规在乡土叙事中互为矛盾、互相映照,最终构成复杂、多元的乡村文化图景。
(三)借用和凸显:乡土奋斗精神的象征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乡土叙事中的民俗,不管是对陈规陋习的剖析批判,还是对新风俗的赞美讴歌,其本质是以一种解放的、理性的心态对乡土文化的反思。乡土民俗是千百年来的乡村居民基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点”,其闪光的一面历久弥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创作者根据乡村振兴主流话语的需要有意识地对民俗的相关内容进行借用或凸显,揭示出乡土社会及其民众中所蕴含的重信守诺意识、艰苦奋斗精神等内容。如《十八洞村》中为了修路要占用杨懒家的土地,但杨懒死活都不同意,无奈中村民们想到了“喝血酒”的民俗,喝了血酒意味着一条道走到黑从此与村民绝交,不喝血酒代表着默认公路可以从自家的土地上经过,借助这个民俗映射的其实是村民们的朴实,以及村民们讲究诚信、信守诺言的思想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中华民族向来以特别能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讲究节俭著称于世。艰苦奋斗精神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中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和民俗的方方面面,如《我和我的家乡·回乡之路》中的乔树林买两碗羊杂汤都吓出了冷汗,却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荒漠治理并和大家一起种植沙地苹果;再如《千顷碧澄的时代》中贫困户韩文魁拒绝接受扶贫基金,自力更生做起了馒头生意;原来四处打临工的姚大鲁则因地制宜地办起了琴弦厂;年轻的扶贫干部芦靖生带领乡亲们苦干力拼等。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挖掘和凸显了人们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摆脱贫穷的奋斗精神。
三、乡土政治修辞
影像政治修辞“是指把政治作用力或权力融化在影像形式中的过程,或者是指在影像形式感染中渗透政治意图的过程。”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是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统一,所以政治修辞是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中乡土叙事艺术修辞无法回避的背景和底色。
(一)乡土政治叙事的类型化
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最基本的政治叙事模式延续了主旋律电影“辉煌的胜利”等书写传统,即按照党发出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伟大号召,展示乡村的贫困现状。比如村民们尚有很多思想误区等情况,总之形势严峻复杂,经过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行动人,常常是影片的主要角色)千辛万苦的工作甚至要经历对抗和各种艰难险阻,结局必定是少数贫困户彻底觉醒,乡村面貌得到巨大的改观,脱贫攻坚取得圆满或阶段性的成功这一叙事逻辑来展开。由此可见,政治修辞首先要有一个政治话语的代表即政治人,他们通常是基层党员干部或先进农民的身份,一般都被赋予了坚定的革命意志,不懈拼搏的精神品格。政治人占据着叙事的中心。比如《出山记》中的村支书申修军、《秀美人生》中的黄文秀等,虽然间或也会表现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脆弱的一面,但总体上是作为一个“英雄和平民的结合体”来叙事的。其次,要建立一个促进政治任务完成的“系统”,如始终地依托于优秀党组织的培育及信任,众多无名干部群众的协作,广大群众的支持与配合等等。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才会取得胜利。乡土政治叙事的类型化成为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显要特征,在这样一个较为封闭的文本中既有利于承载政治的宣教内容,但也因“千篇一律”而被观众诟病。
(二)主流政治话语的“软”修辞
近几年乡村振兴题材电影的叙事和修辞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一点就到家》,影片从形式上看是一部讲述三个年轻人创业的荒诞喜剧,没有铿锵有力的官方语言,但却把宏大严肃的意图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乡村是大有可为的,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这种把乡村振兴的主流政治话语通过个人化或非国家化等方式隐性或柔性地加以表达,造成国家的理性要求被融化为感性或富有感染力的效果。受王一川论述电影中国家形象与修辞的关系时提出的“国家硬形象的软化术”和“国家软形象的硬化术”概念的启发,我们把这种修辞方式称为“软植入”。与“软植入”相反的是“硬切入”,即显性地或刚性地表达主流意识形态规定的话语的修辞方式,当前还有大量的电影采取这种传统方式,比如《筑路之梦》《农民院士》《扶贫主任》《后池新愚公》等影片,因为其背后都有一个被高高树立起来的“人物原型”存在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所影响,创作者往往难以取得突破。无论是票房收益还是政治认同目标的达成效果,“软植入”都应成为创作者的首选。
(三)不同农民的政治参与修辞
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推动农业农村农民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壮举,它首要的任务是汇聚亿万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力量参与新农村的建设,对于农民来说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在乡村振兴题材的电影中,以对乡村振兴政治认同的程度为标准将农民划分为进步农民和落后农民两个群体。进步农民是承载意识形态的有效符码,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战胜贫困的坚定信心和不畏艰难的实干作风。虽然创作者为更好地将其人格化、增加亲切感也常常会为他们植入一些缺点,但进步农民总体上呈现的是一群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党保持高度一致的先进分子,如《十八洞村》中的杨英俊等。落后农民是乡土叙事电影批判的对象,他们思想麻木,对乡村振兴或脱贫攻坚政策不认同,经常感情用事甚至会站到脱贫攻坚的对立面上,是制造激烈冲突矛盾的一方,是阻碍乡村发展的绊脚石。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落后农民的思想也会逐步发生改变。进步农民和落后农民的政治参与修辞不仅是对现实的映射,更是对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的政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感召力所抱有的信心。
结语
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乡土叙事的艺术修辞是内嵌于乡土叙事中的影像修辞。修辞的中心始终围绕着“乡土”展开,通过特定的乡土影像符码以及乡土表意方法、手段进行新时代乡土世界的艺术建构:乡土物象是乡土叙事的环境基础,通过对“物”的修辞化“框定”,物质世界也成为承载人类情感和想象的“意象世界”;乡土民俗修辞借助千百年来积累的民族生活文化成果,发现潜藏在乡土文化观念之中的重信守诺、艰苦奋斗等精神内涵,并大力弘扬其当代价值;乡土政治修辞以类型化、闭合式的文本,主流政治话语的“软植入”,农民的政治化分类等修辞手段的应用,达到与观众的有效对话、沟通,潜移默化地实现弘扬主旋律的政治修辞效果。作为乡村振兴的“艺术文本”,乡村振兴题材电影指涉乡土的艺术修辞是极其丰富的,远远不止上述的三个层面。乡土叙事的艺术修辞作为重要的“制造效果的策略”,创作者在实践中要坚持艺术性创作原则,以再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乡村变革的本质为艺术目标,在修辞艺术和技巧方面进行更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不断发现和挖掘艺术表达的新内容和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