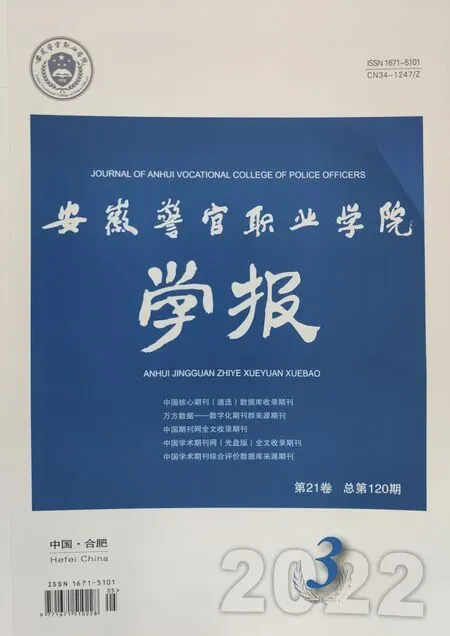话语共同体视域下胡寅道学思想探析
包佳道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胡寅,字明仲,一字仲刚,又字仲虎,号致堂。宋福建崇安人。生于北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年五十九,谥文忠。胡安国之子,胡宏之兄。他因其家学渊源,有着深厚的张载、二程道学熏陶。胡寅承继着胡安国、杨时等对张载和二程道学的阐扬和扞护,使得伊洛道学话语共同体不断得以扩大和凸显,他作为其中一员所作的学术贡献不可忽视。有著作《崇正辩》《读史管见》《论语详说》及文集《斐然集》存世。
胡寅《崇正辨》一书,系统阐述了他对于佛教思想的批判性认识。胡寅除了从夷夏之别,佛教徒不事生产、徒费民生等传统立场出发批判佛教外,还从其自身关于宇宙本体、道德良知等根本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出发,系统辨析了佛教与儒学在这些问题上似同而异的观点,其论述具有很高的思辨性。他的这些努力,在批判佛教的同时,更有力地遏制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将儒佛混而为一的思想倾向,实际上通过“反佛”这一特殊角度,明晰了道学家视域中的孔孟儒学传统,推动了宋明道学的发展。有鉴于此,《宋元学案》评价他:“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皭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1]朱熹更称赞他道“致堂多有说得好处,或有文定、五峰说不到处。”[2]当然,胡寅的反佛思想,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们要讨论的不是立场之是非,而应挖掘其“反佛”背后自身的道学思想。
除了通过反佛理论而在道学有所贡献外,胡寅在政治、礼法等问题上,也很有建树。朱熹就曾指出:“致堂《管见》方是议论”,陈寅恪亦曾指出:“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此外,作为朝廷重臣,胡寅的多封奏疏,如《上皇帝万言书》《论遣使札子》《请行三年丧札子》等文章,也表现了他的政治、礼法思想。
一、本体话语:气之运与天理、性命
胡寅道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一点,是在本体论上坚持“实有”的观点主要以“气之运”和理、命、性等话语展开阐发。
(一)气之运
胡寅以“气之运”这一话语来具体阐释,以此来反对佛教的“空”观。他说:
“阴阳之气,分为天地,凝为日月,转为四时,散为万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气之运,未有能外之而独立者也。聚则成,散则坏,盈虚相荡,一息不流,未尝止也,安得言住?不成则坏,不坏则成,皆可耳闻目见而心知也,安得言空?是故中国传圣人之道者正之,曰:有成坏,无住空。佛以世界终归于空,故其道以空为至。然实不能空也,佛强空之耳。”[3]佛之学不明乎气,以气为幻,故学之者其弊如此。”[4]
胡寅这一反对佛教以空为至的本体论观点是以“气之运”这一本体话语为理论依据的。胡寅继承前人观点,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气”。从以“气”为天地万化之本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胡寅进一步指出,天地间的一切自然变化与人事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也是可以认识的。他以此批评佛教,认为佛教以天地为幻化,以世事为无常,以生命为苦难,以持斋戒、奉养僧众为解脱之道的观点,根本是虚妄的。他说:
“日月星辰运行无止,而名之曰时,此中国之常言,何待佛然后明之?今夫瞬息之速,顷刻之暂,岁月之积,古今之异,成坏相因,治乱相续,载籍以来,皆可致矣。何时为住时邪?何时为空时邪?诬蔑按据而造说茫昧,幻观天地而实证八荒,多见其妄矣。”[4]8
(二)天理与性命
胡寅一方面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运动性和载体性的“气”,一方面又坚持规律性、规范性和主宰性的“理”是与气并列的最高范畴,是人至善本性的根源。胡寅继承张载《正蒙》中的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性”、“命”等概念的本质做了系统思考和阐述,建立起自己的心性论主张,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了佛教缘起性空、三世因果的观点。他首先阐明道学关于“性”“命”之所谓,并批评佛教“业报”的概念,他说:
“性者,万物之一源,而气禀则有清浊,是以圣哲贤愚资质有异。命者,万物之所同受,而阴阳变运,参差万殊,是以五福、六极值遇不一。以此理观之,千古犹指诸掌也。浅狭之人,记功于岁月,责报于促近,而不知天地之气,消息、盈亏、迟速、显晦,终不可违,非如人私意小智之所测量也。既不明天理,于是为三世之说所自诳,是未尝知性命。不知性命,其言殆难当乎!命与业异。业者,人也。命者,天也。不可同语也,有志之士,考《正蒙》之论气,则于典仪所辩,如数黑白,无足疑者。”[3]25
这里,胡寅认为,人性以天理为根据,本无不同,皆生而至善,只是由于个人气禀之差异,才在行为中有“性善”或“性恶”等不同的表现。而人的命运则由于不同人所处时空不同、际遇不同,自然福祸不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真正的君子也不会为个人的际遇而改变自己的本性。佛教则以为通过因果报应,可以改变命运,却根本不知道天地间万事万物自有其运动规律,不依人力而有所改变,是以佛教“业报”之论,根本是荒诞之说。
这“理”,也称为“道”或“神”。“理之所在,先圣、后圣,其心一也。”[4]50又说:“道一而已,更万古而无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后百世而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4]66这一作为价值本体的“理”或“道”,作为终极的道德源泉,是永恒而亘古不变的,不依人事的变迁而有所转移。正因为坚持这一观点,所以虽然同为反佛,但胡寅并不赞同南北朝时期范缜《神灭论》的观点,他认为范缜没有认识到“神者,阴阳不测,妙万物而言,未尝斯须亡也”的高度,他说“形有质而神无方,正尤刀之利也。形虽亡,神固自存;刀虽坏,利固自在。利非锋芒之谓,神岂智识之拘邪?”[5]胡寅认为“神”不是个人的精神、智力之谓,而是终极的价值根源、不变的“天理”。胡寅这一理、气并行思想,继承并综合了二程、张载,对朱熹有积极的影响。胡寅反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天理”这一概念,他认为佛教尚空,以山河大地为幻化自然是虚妄的,但更比这更严重的是佛教亦不承认这一最高的“天理”。在道学体系中,天理是人的心性之源,不承认天理,便无法理解人性本善的道理,也会使心性沦为空寂。而坚持穷理而尽心,则是胡寅在心性论范畴反对佛教的重要观点。
二、功夫话语:穷理精义与推仁心、别亲疏
胡寅在功夫话语上,一方面将格物、穷理和正心结合强调穷究人伦则精察事务职分,一方面以仁心、推、别亲等阐发了道学的爱有差等,批判了佛教和墨家的爱无差等。
(一)穷理而精义
胡寅主张格物就是穷尽物理,并指出通过格物诚意来正心修身。他极为强调穷究人伦理则精察事务职分对正心的价值,指出儒学与佛教虽然同样主张以本心功夫为本,但二者之间关于“心”的理解则有不同。相应地,二者的下学功夫也不同。他指出:
“圣学以心为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圣人教人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穷理而精义,则心之体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为法,起灭天地而梦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扬眉,以为作用,于理不穷,于义不精,几于具体而实则无用,乃心之害也。”[4]48
“心”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中,表征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尤其是人的伦理德性能力。胡寅也持这一观点,并认为“心”这一官能是人能够沟通世界,理解儒学道理的根本所在,所以,圣学以心为本,而佛教也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双方虽都以“明心见性”为治学之关键,都主张从“心”上下工夫,但儒学认为“理”“义”这是人心本具的基本内容,是“心所同然者”,而这些心所本有的理、义由于为气禀所遮蔽,故而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挖掘,所以儒学教人深究于理义,以明心体之全。而佛教则不认为人心本有关于“理”“义”的基本内容,恰恰要消除心上对世间一切的执着,所谓“以心为法”认识到心法“起灭天地”、“梦幻人间”,这样才会得解脱。胡寅专门举出历史上唐代道氤法师向唐玄宗讲解《金刚般若经》典故以说明这一点,“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术耳。明皇方疑而未决,一闻其言,致思入念,如道家存想,随所欲而萌焉,龙华之会,灵山之集,妙喜之国,兜率之天,种种现前,皆可自诳。虽高才颖质,攻苦学道之士,于此犹不脱,又况明皇志满气骄,乐佚游,乐宴乐,其心昏然者哉!”[4]48当时唐玄宗对佛教因果轮回理论表示怀疑,道氤则告知玄宗皇帝,要他“更沈注想,自发现行”。玄宗因其法而行,果然沉迷于自诳想象之中。胡寅以此批评佛教,认为其所谓“以心为本”,其实就是让人沉迷于自诳、冥想之中,完全是虚假而带有欺骗性的。言下之意,儒家是心不离对现实世界人伦的穷究和事务职分的精察。
(二)推仁心与别亲疏
在功夫论上,胡寅还以推仁心、别亲疏等道学话语批判了佛教和墨家的无差等之爱。
北宋以来,佛教僧侣为弥合儒佛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动吸收儒家伦理思想,突出佛教教义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的良性关系,如契嵩法师就认为,佛教不杀、不盗、不淫、不饮酒、不妄语五戒,其实正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二者名称不一,实质相同,儒学从正面昭示道德精神,佛教从反面限定行为禁区。这种思想在当时很有影响,而胡寅批评了这一似是而非的观点,他说:
“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此圣人戒杀之训也。由是推之,博施济众,使民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鸟兽鱼鳖咸顺其性,本于此心而行之,有法度焉,久而无弊。非如佛氏之不杀,无别无义也。举此一端,则仁义礼智信皆然,岂五戒之浅浅可比方哉?其途自异,其归不同,其虑自百,其致不一,不当引圣人之道以文其说也。”[3]10
这里,胡寅承认好生而恶杀是君子的美德,并指出这一好生之心正是儒者道德良知的出发点,由此心推而广之,便可以博施济众,成就一番事业。但他同时强调,这种推而广之一定是有法度的,如此才能避免各种弊端,才能使民生得到保障,社会得到安定,这里面的微言大义,不是佛教五戒所可以比拟的。而胡寅所谓的“法度”,正是儒者所强调的“爱有差别”之义。如胡寅说:
“仁之实,事父母也。义之实,从兄长也。礼之实,为仁义之节文也。乐之实,由仁义而和乐也。不知释氏所谓仁义礼乐者,与此同乎异乎?同则不当弃父母、绝伦类,异则不当言仁义、谈礼乐。”[4]11
“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然天下之人物众矣,自父母推之,秩其亲疏,至于飞雉,不知其相去几等也。智舜不忍飞雉之见获,而忍于父母之见弃,何哉?佛氏不明天理,以我与人,以人与物,以父母与禽兽,无有差别。故其行事迷谬,无一中理者。”[4]88
佛教徒持五戒,自有其理论依据与宗教情感的支持,胡寅对其的批评并非尽是。但无论如何,胡寅明确指出了儒家伦理道德与佛教伦理最重要的差别之一,即在于儒家伦理以孝悌之情为起点,由此扩充,“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所谓“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也应当依照这一亲疏有别的法度而行。因为在儒家看来,孝悌之情是人最根本的天性,由此扩充的仁心,才是真正自主自发的,不孝敬父母而泛爱庶物的人,不足以称之为仁人,其爱物之心,归根结底,都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胡寅认为,墨家“兼爱”说就犯了这一错误,佛教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
“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之弊也。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释氏之弊,岂不甚于此乎?弃父母出家而不顾,见蝼蚁蚊蚋则哀矜之,谓之别亲疏,可乎?不别亲疏,故不辨贤否。今有圣贤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则释子必不誉也。小人亡国败家,建寺宇,崇塔庙,厚给其田,广度其众,则释氏必以为宿植家根,亲受佛记者也。试用此观之,其情见矣。”[4]11
儒家讲“仁爱”,自父母及于庶物,亲疏自有别;佛教则背弃人伦于不顾。儒家认为,孝悌人伦是进行一切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佛教否认这一点,便无法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故其衡量人物是非的标准,其伦理主张,根本是出于党同伐异而已。
三、伦理政治话语:无所为而为善与不顾私亲
在伦理政治话语上,胡寅以无所为而为善批判佛教和法家功利性诱人为善;以孝悌忠义来阐发君王当明父子之恩、君臣之义,凸显道学的外王功业。
(一)无所为而为善
在辨析儒、佛伦理思想本质区别的基础上,胡寅进一步指出佛教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道德观,同时强调儒家伦理的非功利性。他引用《正法念经》中“若有终生扫如来塔,命终,生意乐天”的说法,批评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
“佛设如此等教,其发心也,不知欲诱人为善乎?抑将自保其塔乎?如诱人为善,莫先于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乐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为利路以张之,必有一中,中则其说可入,此佛之术也。言生意乐天,则凡心意有所好乐而不得者,必为之扫塔矣。言生白身天,则凡丑黑,为女子所恶,欲淫色而不得者,必为之扫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转轮王,则凡瘖哑聋聩、贫穷下贱者,必为之扫塔矣。其设教之心如此,果可谓之正道乎?今欲诘之,则必曰:‘此皆无碍方便也。人之根器万端,不如是,不能摄之入善。’呜呼!使人随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则得女,好贵则得王,天下大乱之道也。曾谓如是而为善乎!”[3]17
胡寅坚持并发挥儒家传统观点,认为道德行为应当是纯粹的非功利性行为。在真正的道德实践中,行为人只应考虑行为本身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不应考虑自己所能得到的结果或者回报的问题,这正是孟子所谓“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的本意。与之相应,劝人向善,正确的方法是激发人先天本有的好善恶恶的道德良心,而不能靠可欲之事来引诱人从善,这样只能诱发人无尽的欲望,终与善道无缘。佛教这一建立在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基础上的伦理体系,正是其功力主义本质的体现。其目的,则在于自壮声势,吸引信徒。
相比于以“善报”诱人,胡寅更为痛恨的是佛教以“地狱”怖人。这样不仅逼人从己,而且其关于地狱中痛苦的种种描述,为世间酷吏提供模仿对象,帮助他们造严刑峻法以害人,唐代来俊臣等酷吏就是典型代表。这点虽不是佛教所直接造成的,亦由其流弊所致。胡寅说:
“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严酷。汉世稍宽,而无复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以佛图澄之多术,不能止石虎之好杀。然多杀而已,尤未有巧杀也。及梁武为懺,丛集佛书地狱苦虐之状。至唐世,人君奉佛者众,而酷吏始以巧杀。苛毒惨虐,真如地狱变相,又有甚焉,所不忍闻者、呜呼,悲夫!彼佛之说本欲恐动,使之向己,不虞其流祸至此之极也!”[4]11
无论善报、恶报,净土、地狱,都是佛教徒编造出来的。胡寅认为,佛教所宣扬的这种功利主义的因果轮回思想,危害极大,使得天下人好利恶义、世态炎凉、人心不古。他说:
“富贵逸乐,人之所贪也;瘖聋瞽跛,人之所恶也。以人之所贪者诱人,使人相劝而出家;以人之所恶者怖人,是人相信而勿离。此所谓以利道病良民之心,而不可救药也。凡有所为而为善者,皆人欲之私,是利道也,异端邪说是也。无所为而为善者,天理之公,是本心也,孔孟之教是也。其道正尤水火之不相如,而或者欲比而同之,盖惑溺而未之思耳。”[4]28
“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顺受其正,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不闻有轮回之说,岂非简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经营,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国,说天堂可慕,地狱可怖,轮回可脱,于是人皆以死为一大事,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为常事,必至于贪生失理,惧死怛化,而不顺受其正也。自两汉而上,战国、春秋之时,圣人所谓道丧之世也。当其时,义心激切,视死如归者,班班可考,其心初无慕怖,安于义而已。后世学佛者,自以为其道可以了达死生,而其行事视三代之风尚未能及,况圣贤之际乎!”[4]57
实际上,佛教“三世因果”这一轮回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开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心对德福一致的向往与历史上善者难得善终、恶者反有福报这一冰冷现实间的落差而致。面对这一善恶与福祸的不相应现象,胡寅对其原因也有清楚的认识,他说:
“夏至之日,一阴初生,而其时则至阳用事也;阴虽微,其极必有折胶堕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阳初生,而其时则至阴用事也;阳虽微,其极必有铄石流金之暑。在人,积善积恶所感,亦如此而已。颜回、伯夷之生也,得气之清,而不厚,故贤而不免乎夭贫;盗跖、庄蹻之生也,得气之戾,而不薄,故恶而犹得其年寿;此皆气之偏也。若四凶当舜之时,则有流放窜殛之刑;元凯当尧之世,则有奋庸亮釆之美;此则气之正也。何必曲为先业、后世因果之说乎?若行善有祸而怨,行恶值福而恣,此乃市井浅陋之人计功效于旦暮间者,何乃称于君子之前乎!盗跖脍人肝,虽得饱其身,而人恶之至今;颜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若颜子之心,穷亦乐,通亦乐,箪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钟鼎庙堂何足以淫之!威刑死生何足以动之!而鄙夫之见,乃以贫贱夭折为颜子宿报,呜呼陋哉!”[3]22
这里,胡寅坚持气本论的观点,认为人一生的夭寿、福祸在于气禀之不同,与德行无关。强行将道德行为与生平福寿相联系,其实质是功利主义观点,与市场上讨价还价无异。虽然行善不一定有善报,但美名可流传千古,儒者穷亦乐、通亦乐,正彰显了其伟岸的独立人格。
胡寅认为,世人之所以沉溺于佛教,正是因为有三弊,即惑、惧、贪:惑于不识世界本来实有,轮回本为虚妄;惧于因果报应、地狱鬼怪;而贪于来世之福华。而他之所以著《崇正辩》,也正是为了通过反佛来倡明儒家义理,根治世道人心。平心而论,佛教理论自有其价值,片面反对佛教当然有偏颇之处,但胡寅通过反佛这一特殊角度,辨析了道学中的种种问题,其思想贡献的确有不可磨灭之处。
(二)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义
除了在道学上的贡献外,其最主要的观点,就是重视“孝悌”思想,认为孝悌是为政之本,这首先表现在其政治主张上。
建炎三年,胡寅至临安,有感国事艰难,作《上皇帝万言书》,立言抗金大计。文中,胡寅提出应当从七个方面着手改进当下的局面,包括:孝悌、求贤、纳谏、任将、治军、爱民、为天子。而其中最有突出意义的,是他从“孝悌”观点出发,对高宗皇帝在徽、钦二帝被俘的情况下急于登基而消极抵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据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省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愉安岁月。敌兵深入陕右,远破京西,漫不治军,略无捍御……凡此节次十余条,皆所谓失人心之大者也。”[4]336胡寅认为,高宗在没有得到先皇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继位,本已不合礼制,尚若再消极抵抗,则有负孝悌。他说“东南之州郡几何,翠华之省方无矣。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悌之衍,常有父兄之责。人心已去,天命难恃。”[4]337他甚至强烈要求高宗下“罪己诏”。胡寅的这一观点从儒家义理出发,为生民之利益、国家之社稷着想,不愚忠君主个人,为后人所称赞。张栻、朱熹都认为这是胡寅生平一大功绩。
此外,胡寅重视孝悌还表现在他对于“三年之丧”的看法上。绍兴七年,徽宗皇帝在金国逝世的消息传到南宋,高宗皇帝打算依照宋朝惯例以日易月,服丧27天。胡寅此时上疏,要求皇帝应依古礼,服三年之丧。首先,三年之丧是最基本的礼制,胡寅说“臣闻三年之丧,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古之圣帝明王躬率天下,著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义,由尧、舜逮汉初,其道不变。”[4]235而以日易月则有违礼制,“以日易月,臣窃以为非是。自常礼言之,犹须大行有遗诏,然后行之。今大行遗诏不闻,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4]236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胡寅指出,徽宗皇帝被敌国俘虏,高宗本已有负身为人子之职,若再不服三年之丧,则薄情寡义,有悖人伦。他说“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饮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药,必无供億;崩殂之后,衣服敛藏,岂得周备?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为谁?伏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难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仇之切,切于圣情。情动于中,必行于外。苴麻之服,岂可二十七日而释之乎?”[4]236同时,胡寅还认为,在当时国土沦丧的特殊时刻,高宗皇帝服三年之丧,有助于凝聚人心,提升军队士气,正所谓“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动于人”[4]238。胡寅这一主张,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评价,朱熹认为“设使不继位,只以大元帅讨贼。徽庙升遐,六军缟素,是甚么模样气势!”[6]
胡寅的孝悌理论最为特殊的一点,则在于他关于作为养子,应当如何对待亲生父母与养父母的态度上。胡寅本人即为养子,对此有直接的体会。胡寅因不知情而没有为生母服丧,被他人非议,他曾就此事向时任丞相秦桧写信解释,提出过房入继与遗弃收养不同的观点,认为“过房入继,礼之正也,则当为本生行心丧解官。收养遗弃,本生之恩已绝,而所养之恩特厚,虽不为本生服,可也。”[4]336这一问题虽然是胡寅个人问题,但涉及礼法,关系极大。在《读史管见》中,胡寅就多次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他曾就历史上作为宗室藩王而继承皇位的汉哀帝封生母定陶太后为皇太后,及以侄子身份继承皇位的后晋出帝封生父为宋王两件事,批评到“若夫定陶立后,敬儒封王,纷纷为是无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为欺,以至此耳。”[5]82即他说“为人后者,不顾私亲,安而行之,尤天性也。”[5]82在重视宗法传承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为人收养者如何调节生父与继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十分严肃同时充满争议的问题。在胡寅之后四百年,明朝嘉靖皇帝还因这一问题与群臣展开了激烈的“大礼议”之争。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展现了儒家伦理内部情感和理性之间两个维度之间的张力:从情感出发,人无不与亲生父母更为亲切,孝悌之情,也是儒家伦理的起点;从理性出发,则孝悌不能仅限于个人情感,身为继子,将亲生父母置于养父母之上,既是有负养父母之恩,又会造成严重的家庭伦理问题,威胁家庭稳定,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不稳定就是社会不稳定,其潜在威胁极大。因此,坚持理性原则的儒者,在这一重要的礼法问题上,往往坚持养子首先应当为养父尽孝,尽所谓“为人后者”之职。
四、结语
胡寅一生历经两宋交替,目睹山河破碎、国家罹难,在内忧外患的儒佛道竞合,道学与荆公新学、蜀学论争的形势下,承继着胡安国、杨时等对张载和二程道学的阐扬和扞护,对内坚守道学基本价值立场,批判佛道法家墨家等的学说,使得伊洛道学话语共同体不断得以扩大和凸显,他作为其中一员所作的学术贡献不可忽视。胡寅的话语阐释虽有显著的道学道统捍卫色彩,但确实又凸显着道学家所秉持的积极面对现实人伦政治的儒家精神旨趣。胡寅晚年返回南岳故居后,曾与朱熹有过会面。朱熹评价他说“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