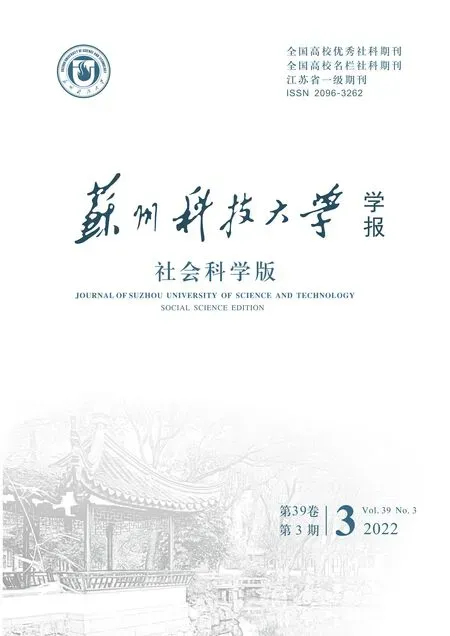道德理想与感情传达*
——列夫·托尔斯泰艺术伦理观重释
郭玉生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向来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近年来研究者从民族因素、艺术形式、宗教思想等角度分析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1)参见邱运华《“神圣使命”与诗性启示——19世纪俄国思想文化语境与托尔斯泰小说诗学的一个特色》,《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132~138页;王树福《东西审美伦理之间:托尔斯泰艺术形式观生成考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78~85页;王树福《道德诉求的审美表达:托尔斯泰论艺术形式与文学伦理》,《华中学术》2018年第3期第230~237页;郑绍楠《托尔斯泰论艺术》,《江汉论坛》2012年第4期第77~81页;等等。,向纵深层次推进了托尔斯泰艺术伦理观研究,同时又存在着从综合角度进行深化研究的空间。基于此,笔者尝试在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道德理想”和“感情传达”为线索,重新阐释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
19世纪的俄国处于封建农奴制、宗法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新旧交界点,俄国的社会变革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未来走向成为托尔斯泰关注的中心问题。托尔斯泰深受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激烈地批判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文明,认为有史以来的文明全部以私欲与专制为基础建立起来,需要通过人心的革命取代社会革命,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实现社会改造。他的艺术伦理观即以此为基础提出的。
一、“美”从属“善”:艺术的伦理本质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理解了‘美’的本质,因而也理解了艺术的本质。”[1]22由此他检讨了从18世纪美学奠基者鲍姆嘉通(Baumgarten)到19世纪末期欧洲美学家对于“美”的本质的种种理解,归纳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是以客观存在的因素(如绝对完满的东西)为基础提出关于“美”的定义,第二种则是以主观存在的因素(如快乐)为基础提出关于“美”的定义。托尔斯泰深入分析了这两种观点:“我们之所以认识外界存在的绝对完满的东西,并认为它是完满的,只是因为我们从这种绝对完满的东西的显现中得到了某种快乐,因此,客观的定义只不过是按另一种方式表达的主观的定义。实际上,这两种对‘美’的理解都归结于我们所获得的某种快乐。”[1]39在托尔斯泰看来,前述两种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解殊途同归,都是指向了快乐。倘若艺术把创造“美”作为自身存在的目的,那么艺术就只是人追求快乐的手段。因而他坚决否定“艺术的目的就在创造美”的诸如此类流行的艺术观念,强调衡量艺术的尺度不是“美”而是“善”。
托尔斯泰认为,把“善”“美”“真”放在同样的高度看待是错误的。他坚决反对“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观点,而强调“美”与“真”应当从属于“善”。“善”作为人类生活中永恒的最高目的,它是“不能用理性判断的概念”,“‘善’是任何人所不能判断的,但是‘善’能判断其他一切”[1]63。在托尔斯泰这里,“美”只是让人感觉快乐的东西,“美”与“善”不仅内涵不同,而且针锋相对,“美”构成一切癖好的基础,“善”却与癖好的克制密切联系,人们愈倾心于“美”,就离“善”愈远。对于“真”,托尔斯泰认为,它很难说具有自己的独立存在,“‘真’是事物的表达跟它的实质的符合,因此它是达到‘善’的手段之一,但是‘真’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美’,甚至跟‘善’与‘美’不相符合”[1]64。托尔斯泰强调,“善”“美”“真”这三个有着明显差异的概念被看作统一实体,就为错误的艺术观念提供了依据。按照这种错误的艺术观念,“表达善良的感情的好艺术和表达恶毒的感情的坏艺术之间的差别就被一笔勾销,而艺术的最低级的表现之一,即单为享乐的艺术……开始被认为是最高级的艺术。这样,艺术就并不象(像)预定的那样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而成了懒散的人们毫无意义的娱乐”[1]64。艺术的目的一旦被理解为享乐,就离“善”越来越远。
在托尔斯泰看来,艺术所提供的享乐,实质上表现的是欧洲社会上层阶级的狭隘癖好与趣味。美学家按照上层阶级偏好的艺术作品提出有关“美”的本质的理解,并将其视为衡量所有艺术作品的标准:“艺术中无论有怎样的痴愚,只要这种痴愚一旦被我们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所接受,就立刻会有人编出一套理论来,把这种痴愚加以解释,并使它变成合法。”[1]41由此可见,托尔斯泰考察有关“美”本质的各种观点,主旨在于否定上层阶级追求享乐的癖好与趣味,满足上层阶级享乐需求的艺术越美,它就越缺乏善的价值。托尔斯泰主张,每个人都同时具有兽性和人性,人只有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才能克服兽性,消除社会罪恶。所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从自传三部曲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以“善”为创作目的,宣扬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
二、“宗教意识”:艺术的伦理尺度
托尔斯泰认为,“生活中的善与恶是由所谓宗教决定的”[1]50-51,上层阶级的癖好与趣味的堕落,就是他们丧失“宗教意识”导致的。人活着就必须拥有信仰,而信仰也就是托尔斯泰所说的“宗教”或“宗教意识”。在他看来,“宗教代表着某一时代和某一社会中的优秀和先进的人们对生活的最深的理解”[1]51。托尔斯泰理解的“信仰”并不是教会的基督教,而是内心的上帝;“宗教意识”不是教会宣扬的教义,而是人的道德良心。没有信仰就不可能生活,也就意味着没有上帝就不可能生活。因此,尽管托尔斯泰指出,人类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宗教,但他认为“基督的学说”超越时空,适合世上一切人。“基督的学说”的基础是“勿以暴力抗恶”,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博爱精神”实现全人类的团结,从而走向平等友爱的大同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彼尔、娜塔莎等都体现了这种“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立足于“宗教意识”分析艺术问题,不仅把宗教作为衡量艺术的尺度,还把艺术的发展看作宗教和艺术之间关系演变的过程。原始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与博爱的教义承载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生活价值的认识。此时,艺术和宗教具有一致性,这种艺术称得上“真正的”“全民的”艺术。但是,后来出现的官方教会彻底违背了原始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与博爱的教义。在欧洲中世纪社会,上层阶级一些有教养的人虽然怀疑官方教会违背原始基督教信仰,却没有勇气公开揭露官方教会,缘由在于原始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与博爱的教义是对上层阶级优越社会地位的否定。因此,上层阶级虽然知晓官方教会完全违背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真相,但是终究不能恢复原始基督教信仰,于是丧失了“宗教意识”,身不由己地接受了异教观念,即生活的意义在于享乐。享乐进而成为衡量艺术的尺度。上层阶级把享乐观念灌入艺术中,于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产生了以“个人的享乐”观念为基础的艺术。
托尔斯泰强调,按照上层阶级的癖好与趣味,以享乐为目的进行艺术创造,不但导致欧洲社会道德败坏,而且使艺术不断走向衰退。艺术走向衰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是作品逐步丧失原本具有的丰富而深刻的宗教意蕴,思想匮乏,内容空洞。它所显示的只是上层阶级骄横自大的情感、放荡纵欲的色情与颓废消沉的情绪三种卑琐的感情。在托尔斯泰那里,文艺复兴时期颂扬天主教皇、教会主教与国王贵族的作品属于显示上层阶级高傲骄矜的情感的艺术;欧洲的小说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19世纪勒内·德·古尔蒙的《狄奥米德的马》等,属于描写各种形态的性爱或者肮脏的性行为从而表现上层阶级放荡淫乱的色情艺术;拜伦、海涅等人的作品属于表达上层阶级颓废消沉情绪的艺术。艺术走向衰退产生的第二个结果是作品在形式方面违背自然,缺乏清晰的道德态度与价值立场。在此,托尔斯泰批判的矛头指向了19世纪法国以波德莱尔和弗雷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倾向。他以否定的态度评价了波德莱尔及其创作:“波特莱尔的人生观是:把粗野的利己主义抬高而使之成为一种理论,并用象(像)云一般不明确的美(必然是矫揉造作的美)的概念代替道德。波特莱尔比较喜欢女人的涂脂抹粉的脸,而不喜欢自然的脸,比较喜欢金属制的树木和假造的矿物质的水,而不喜欢天然的树木和天然的水。”[1]89-90在托尔斯泰看来,矫揉造作是背离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含糊暧昧进而缺乏清晰的道德态度与价值立场则是19世纪法国以波德莱尔和弗雷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倾向的主要特征,即“再也没有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1]78,“在诗里必须经常含有‘谜’”[1]78。托尔斯泰反对含糊暧昧、谜一般的文学创作倾向,强调作家应该“对生活中的善恶有一个明确而固定的看法”[2]82。艺术走向衰退产生的第三个结果是艺术赝品盛行。为了逢迎上层阶级的癖好与趣味,艺术家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方法大肆炮制艺术赝品。上层阶级则给予艺术家非常丰厚的酬报,艺术家由此逐渐走向了职业化。而艺术一旦成为一种职业,艺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特征——纯朴性就严重减弱乃至部分消失。于是,色情的、荒诞无稽的东西不断地被炮制出来,致使“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艺术已经变成一个荡妇。这个比喻在最小的细节上也都非常妥切。我们的艺术也象(像)荡妇一样不受时间的限制,也是永远涂脂抹粉的,也是随时可以出卖的,也是引诱人心而对人有害的”[1]183-184。
托尔斯泰进而提出,艺术不是为上层阶级提供享乐的工具,而是承担着严肃的社会使命,应该成为人类进行社会交往、走向道德的自我完善的途径。由此托尔斯泰阐述了与柏拉图一脉相承的观点:“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失去所有现在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包括虚假的艺术和其中一切好艺术)好呢,还是继续鼓励或容忍现在存在的那种艺术好?那末(么)我想,每一个有理性和德性的人都会象(像)柏拉图为他的共和国解决问题那样或者象(像)教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类导师那样地解决这一问题。换言之,这个有理性和德性的人会说:‘与其让目下存在的淫荡腐化的艺术或艺术模仿物继续存在下去,那还是任何艺术都没有的好。’”[1]180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观念的发展趋势是从艺术功利论到非功利论、从艺术道德化到艺术非道德化。托尔斯泰认为,艺术非功利论和艺术非道德化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导致的追求物欲、崇拜金钱与背叛基督教义的结果,因而他批判以娱乐和快感为目的的艺术观念,强调艺术应该以“善”作为价值尺度。这种艺术观念来自基督教价值观与俄罗斯文化观的影响。基督教价值观强调,一切世俗价值追求例如金钱、权力、物欲等都是低贱的,而一切契合神意的精神才是高贵的。俄罗斯文化受到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认为艺术象征着人类对世俗价值追求的超越,对契合神意的高贵精神的向往。在托尔斯泰的时代,艺术观问题还关乎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认识。托尔斯泰强调艺术应当追求道德洁净,目的在于否定欧洲盛行的艺术观念,表达俄罗斯的民族性诉求,彰显俄罗斯文化拯救世界的使命。
三、感情传达:艺术的伦理功能
从“宗教意识”的伦理尺度出发,托尔斯泰为艺术下了这样的定义:“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的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1]47-48按照这个定义,艺术是人与人之间传达感情的手段,一部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必须能够激发读者感情的共鸣,也就是艺术家能够把体验过的感情借助于艺术作品传达给读者。托尔斯泰强调,只要表现了艺术家体验过的感情并能够激发读者感情共鸣的就可以称为“艺术”,但未必是好的艺术。因为享乐的欲望受到自然界的限制,涉及的只是个体的利害得失,由此产生的感情是有限的甚至陈腐无聊的,而源于“宗教意识”的感情既有个体的独特体验,又能体现人类普遍的愿望;所以这种感情是无限多样、不断更新的。因此,好的艺术作品或者说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表现与“宗教意识”相契合的感情。只有这样的艺术作品才能使“善良的,为求取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感情代替了低级的、较不善良的、对求取人类幸福较不需要的感情”[1]152。
托尔斯泰所说的“宗教意识”的核心是人类普遍之爱的感情。这种感情能够摆脱个体情感的狭隘性、阶级阶层的局限性与民族之间的隔阂性的束缚,由此具有普世性、永恒性的特质。所以唯有“宗教意识”能够使艺术传达人类的最高尚的感情,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教育人类和团结人类。以此为基础,托尔斯泰进一步强调“宗教意识”对于艺术传达感情极为重要,是衡量感情优与劣的标准:“只有在宗教意识(它表现着某一时期的人们对生活的最高深的理解)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1]71,“只有传达出人们没有体验过的新的感情的艺术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1]71。托尔斯泰强调的“感情的独特性”,也就是指超越个体情感的狭隘性、阶级阶层的局限性与不同民族的隔阂性,对于整个人类而言最高尚、最深沉、最普遍的感情。托尔斯泰把通过“宗教意识”传达的感情看作最高层次的独特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社会学维度的、受到具体阶级阶层限制和时代束缚的感情。艺术家如果意识到这种对于人类具有至高无上意义的感情,并把这种感情看作最高的道德理想而渗入创作中,赋予这种感情以美的形式,就能够满足艺术产生强大感染力的三个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3)艺术家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那种感情的力量如何。”[1]150艺术的感染性是托尔斯泰评判艺术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传达人类普遍之爱的感情是艺术作品获得强大感染力的源泉,这样的艺术作品可以使原本彼此仇恨的人相互宽恕、同情与爱。
基于同样的艺术观念,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中提出衡量艺术作品的三条标准:“一,作者对事物的正确的即道德的态度;二,叙述的明晰,或者说,形式的美,这是一个东西;三,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真诚的爱憎感情。”[2]67托尔斯泰认为,莫泊桑的作品只符合后两条标准,而不符合第一条标准。莫泊桑的作品具有形式的美,能够鲜明、精炼、优美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莫泊桑对于所描写的事物具有真诚的感情,绝不虚情假意。然而,莫泊桑的作品恰恰不符合第一条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准,“即缺乏对他所描绘的事物的正确的道德的态度,缺乏辨别善恶的知识,所以他就喜爱而且描绘了那不应该喜爱、不应该描绘的东西,而唯独不爱也不去描绘那应该爱、应该描绘的事物”[2]68。托尔斯泰批评莫泊桑的一些作品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地描写了女人怎样勾引男人和男人又怎样诱惑女人,甚至在《保罗的太太》中描写让人无法理解的秽行;莫泊桑冷漠且轻蔑地描写农村劳动民众,好像描写牲畜那样。托尔斯泰特别强调莫泊桑的《一次郊游》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莫泊桑以最吸引人的笑谈形式,详细地描写了两个裸着背膀划船的先生怎样同时地一个玷污了年老的母亲,一个玷污了年轻的姑娘,即那位年老母亲的女儿。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莫泊桑对这两个流氓持同情的态度,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而莫泊桑这种完全无视受害者的痛苦与不幸,把注意力放到了故事的最无意义的一面,即描绘这两个流氓所得到的满足,充分体现了他缺乏正确的道德态度。
托尔斯泰又以同样的道德标准对莫泊桑的一些作品表示赞赏。托尔斯泰肯定莫泊桑的《一生》是法国继雨果《悲惨世界》之后的优秀作品,完全符合真正艺术作品的三个标准。《一生》着力展示一个原本准备献身于一切美好事物而被摧残凌辱的天真可爱女性的一生,莫泊桑对她投入了全部的同情,表现了他正确的道德态度。在艺术形式方面,托尔斯泰认为《一生》是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形式美作品。在情感态度上,莫泊桑表现了对于所描写的善良家庭的真诚的爱,憎恨破坏这个善良家庭的幸福安宁并摧残凌辱了这个天真可爱的女性的恶人。
从托尔斯泰对莫泊桑作品的肯定和否定可见,托尔斯泰最为重视作家的道德态度,也就是他所说的基于“宗教意识”的善恶评价和爱憎感情。我们从托尔斯泰批评莫泊桑的一段话中,就能够具体地体会到他的道德标准的实质:“(莫泊桑)显然是屈服于那不仅统治着他那个在巴黎的圈子,而且统治着各地的艺术家们的一种理论,认为对于艺术作品不仅不需要任何明确的善恶观念,相反地,艺术家应当完全无视任何道德问题,艺术家的某些功劳甚至就正是在这里。根据这个理论,艺术家可以或者应当描写真实的,存在着的,或者美的、因而也是他所喜爱的,或者甚至描写那可能是有用的东西,如像材料之于‘科学’。但对于道德与非道德、善与恶的关怀,却不是艺术家的事情。”[2]79
在托尔斯泰看来,以“宗教意识”为基础的道德准则应该成为艺术家的根本立场与情感态度,道德纯洁性应该成为感情的最高目标,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获得成功的关键。托尔斯泰进而强调:“基督教的意识为人类的一切感情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因而完全改变了艺术的内容和意义。”[1]157以托尔斯泰所说的“基督教的意识”作为基础,艺术呈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表现与“基督教的意识”相一致的感情,即“从人与上帝之间的父子般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这样的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感情”[1]160;第二种表现的是“最朴质的感情”,即“日常生活中的大家(没有一个人例外)都体会得到的感情,例如欢乐之感、恻隐之心、朝气蓬勃的心情、宁静的感觉等”[1]160。这两种类型的艺术都属于“基督教艺术”或“现代的艺术”。“基督教艺术”表现的思想感情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因此它属于“普遍的”“世界性的”艺术。具体地说,“基督教艺术”能够使所有的人超越民族、阶级、职业甚至宗教信仰的限制,体验到它所传达的感情。“基督教艺术”借助于感情的传达产生“人类的友爱的团结”的社会效果。所以,未来的、真正的艺术“应当不单是某一群人的艺术,不单是某一阶层的艺术,不单是某一民族的艺术,不单是某一种宗教崇拜的艺术,……它所传达的是所有的人都能体会的感情”[1]159-160。在此,托尔斯泰试图采用全人类最高的也是最具有普遍性的道德标准评判并融合艺术活动的一切因素。衡量艺术的尺度并非人们一般遵循的道德准则,而是突破个体情感的狭隘性、阶级阶层的局限性与民族之间的隔阂性的限制,因而具有普世性与永恒性的人类道德,是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文学都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由此,托尔斯泰强调未来的、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能够贯彻博爱精神,从而实现人类大同的人道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个时代,艺术的使命是把‘人类的幸福在于互相团结’这一真理从理性的范畴转移到感性的范畴,并且把目前的暴力统治代之以上帝的统治,换言之,代之以爱的统治,而这对所有我们这些人来说是人类生活的最崇高的目的。”[1]202
四、评价与启示
不可否认,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托尔斯泰所认为的传达感情进而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界限的作用。艺术家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具有更为诚挚的感情,更为敏锐的感受,更为深刻的观察,更为丰富的想象,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吸引人们欣赏。艺术可以培养同情心,扩大想象力,增长新知识,而这恰恰是一切真正的道德能够维系的基础。艺术如果只是凭借完全脱离道德价值的形式,就很难成为伟大的艺术。因而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包含着真知灼见,对于片面强调艺术独立于道德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现代艺术观念具有纠偏补弊的作用。不过,托尔斯泰以基于“宗教意识”的道德准则衡量艺术,把艺术表达的感情视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反应,忽视艺术的形式要素以及审美经验区别于道德判断的特征,错误地否定了文艺复兴以来许多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一些评价就集中体现了其艺术观念的局限性。比如,托尔斯泰认为,如果说莫泊桑犯了“奸淫罪”,莎士比亚犯的就是“腐化罪”;如果说奸淫只是托尔斯泰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概括的道德方面的五戒之一,那么腐化却是五恶俱全的罪魁。莎士比亚所犯的“腐化罪”主要体现为其作品描写的都是王室宫廷的上层阶级的生活,因为托尔斯泰认为下层民众的生活切合道德准则,简单纯朴而精神充实;上层阶级的生活则违背道德准则,奢侈腐化而空虚无聊。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艺术模仿品”[1]147,其艺术感染力远不如原始民族的狩猎戏。这表明托尔斯泰的“宗教意识”蕴含着狭隘民粹主义,单纯强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和独特价值,由此导致了其艺术观念的偏颇。因而,托尔斯泰运用他所说的通过“宗教意识”实现“人类的友爱的团结”这个道德准则来衡量人类艺术史上的作品时发现,可以看作好的基督教艺术作品少之又少。同样,托尔斯泰以“基督教艺术”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早年创作,绝大部分作品都丧失了价值,勉强符合标准的只有两个小故事——《天网恢恢》和《高加索俘虏》。英国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指出:“托尔斯泰的理论甚至也未能使他稳妥地摆脱自己著作中的困难。因为,在他所举的一些合乎道德需要因而是好的艺术的例子上,他不得不承认,它们大部分是在质量低劣的作品中找到的。于是,这等于马上默认,只有另外的标准,而不是道德的标准,才是可适用的。”[3]实际上,托尔斯泰塑造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魅力,就体现为她对于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追求以及由此所表现的勇敢反抗精神,这一切恰恰违背了托尔斯泰所强调的“宗教意识”。因此,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与其艺术创作之间产生了矛盾,其根源在于“宗教意识”与世俗生命、道德诉求与艺术审美之间的矛盾。
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把欲望与理性、感官快乐与道德规范对立起来,这在人的各种欲望需求不断得到肯定与满足的现代社会,似乎显得僵化陈腐。不过,黑格尔就曾经明确指出:“艺术拿来感动心灵的东西就可好可坏,既可以强化心灵,把人引到最高尚的方向,也可以弱化心灵,把人引到最淫荡最自私的情欲。”[4]艺术对于人的心灵产生的效果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所以尽管托尔斯泰对于自身的道德立场、思维方式与批评视角缺乏自觉的反思,所提出的文学与道德关系的观点忽视了道德观念存在的社会历史情境,片面强调文学批评的道德标准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但他从“宗教意识”的角度论述了艺术快感完全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昭示人们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艺术快感向坏的方面发展。即使在现代社会,人的内在欲求依然需要多方面调解,人的外在世界依然需要总体性秩序,因而托尔斯泰的艺术伦理观仍然是我们应该珍视的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