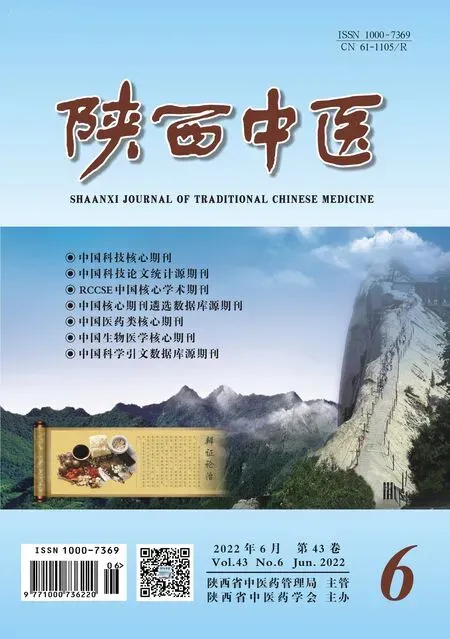张氏肝病流派从“补肝体强肝用”辨治臌胀
唐颖慧,李粉萍,薛敬东,杨跃青,何瑾瑜,叶苗青
(陕西省中医医院,陕西 西安 710003)
臌胀指肝病日久,肝脾肾功能失调,气滞、血瘀、水停于腹中所导致的腹部胀大如鼓的一类病症,临床以腹大胀满、绷急如鼓、皮色苍黄、脉络显著为特征[1-2]。臌胀名首见于《内经》,《灵枢·水胀》指出:“臌胀如何?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灵枢·水胀》篇:“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较详细地描述了臌胀的临床特征[3-4]。《金匮要略》奠定了臌胀的病机基础,其基本病理变化总属肝、脾、肾受损,气滞、血瘀、水停腹中,病位主要在肝脾,久则及肾[5]。肝主疏泄,司藏血,毒邪侵犯肝脏,肝病则疏泄不行,气机失畅,以致气化推动乏力,气滞血瘀,进而横逆乘脾,脾主运化,脾病则运化失健,水湿内聚,进而土壅木郁,以致肝脾俱病。病延日久,累及于肾,肾主水液气化,肾开阖气化不利,水湿不化,则胀满愈甚[6]。古代典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如《诸病源候论·水蛊候》提出臌胀的病机是“经络痞涩,水气停聚,在于腹内”[7]。臌胀病机总属本虚标实,初起肝脾先伤,肝失疏泄,脾失健运,两者相互为因,乃致气滞湿阻,清浊相混,此时以实为主[8-9];进而湿浊内蕴中焦,阻滞气机,既可郁而化热,致水热蕴结,亦可因湿从寒化,出现水湿困脾之候;久则气血凝滞,隧道壅塞,瘀结水留更甚。肝脾日虚,病延及肾,肾火虚衰,不但无力温助脾阳,蒸化水湿,且开阖失司,气化不利,而致阳虚水盛;若阳伤及阴,或湿热内盛,湿聚热郁,热耗阴津,则肝肾之阴亏虚,肾阴既损,阳无以化,则水津失布,阴虚水停,故后期以虚为主。至此,因肝、脾、肾三脏俱虚,运行蒸化水湿功能更差,气滞、水停、血瘀三者错杂为患,壅结更甚,其胀日重,由于邪愈盛而正愈虚,故本虚标实,错综复杂,病势日益严重[10-12]。总而言之,本病病因复杂,多与酒食不节,情志刺激,虫毒感染,病后续发有关,其病机主要在于肝、脾、肾受损,气滞血瘀,水停腹中,病位主要为肝、脾、肾三脏,病理性质属本虚标实,病情易反复,预后一般较差,故属中医风、痨、臌、膈四大难症之一。
中医臌胀主要对应现代医学的腹水,而肝硬化失代偿期的腹水尤为多见。由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制定的《肝硬化腹水及相关并发症的诊疗指南》[13]及《肝硬化诊治指南》[14],均将腹水的治疗分为三级:1级腹水和轻度2级腹水可门诊治疗,重度2级腹水或3级腹水需住院治疗。一线治疗包括限制盐的摄入(4~6 g/d),合理应用螺内酯、呋塞米等利尿剂;二线治疗包括合理应用缩血管活性药物和其他利尿剂,如特利加压素、盐酸米多君及托伐普坦,腹腔穿刺抽取腹水,补充人血白蛋白及行经静脉肝内门-体静脉支架分流术(TIPS术);三线治疗包括肝移植、腹水浓缩回输、肾脏替代治疗等。然而上述治疗手段及方式常引发多种并发症,加重病情。应用利尿剂可能会发生如肾功能衰竭、肝性脑病、电解质紊乱、男性乳腺发育、肌肉痉挛等多种并发症[15-16]。常规限钠和利尿治疗无效的患者,腹腔穿刺放腹水可有效缓解肝硬化腹水患者症状,但可引起严重的急性血容量下降、肝性脑病、肾功能衰竭、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并发症[17]。托伐普坦为血管升压素2型受体拮抗剂,需警惕长期用药出现的高钠血症及低血容量进而造成肾功能衰竭,故不建议使用超过30 d[18]。TIPS是大多数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有效治疗措施,其不足之处是较高的肝性脑病发病率,且远期存在支架狭窄和闭塞、再出血等问题。所有肝硬化腹水患者均可考虑肝移植治疗,尤其出现难治性腹水、肝肾综合征的患者应优先考虑肝移植,但由于其风险高,费用昂贵及肝脏供体来源有限,故肝移植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19-20]。总体来说西医对肝硬化失代偿期腹水,尤其是顽固性腹水的治疗,主要以消除病因、对症、营养支持为主,无特效方案,治疗效果不理想,病情重,且易反复,相关并发症不容忽视,预后差。因此,通过研究中医辨证论治肝硬化腹水的临床诊治理论对治疗本病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在创始人张瑞霞教授的带领下,长期从事各类肝病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研究,具有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知识指导,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诊治内科系统的疑难病症,特别是肝、胆、脾、胃等消化系统疾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理论建树,疗效较好。基于以上基础、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脏腑学说理论,结合“肝体阴用阳”的生理特点及“肝肾同源,精血同源”理论,形成特有的“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肝体阴用阳是肝之生理特性、病理变化的高度概括,明晓肝体阴用阳的特性,有助于临证疗效,肝之为病,多因肝用不足引起,肝用不足的治疗不仅需重视滋肝阴,养肝血,还需重视补肝气,温肝阳,肝病患者正邪交争的过程中,正气逐渐被消耗而相对不足,“损者益之”,及时补养,可使肝病患者正气充沛,阴阳调和,病自愈也,“医者善于调肝,乃善治百病”[21-22]。故以健脾益气、温阳利水等治法贯穿臌胀的临床诊治过程,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拓展了臌胀的诊疗思路,为丰富肝病中医诊疗理论提供新突破。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依托西北区域肝病诊疗中心优势条件,通过流派工作站建设,流派示范门诊的开设,对流派“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在辨治臌胀中的应用经验、临证经验进行深层次的整理和挖掘,对臌胀诊疗形成区域内优势诊疗方案,以便进一步应用于临床。
1 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
1.1 基于肝体阴用阳的生理特性 中医学阴阳学说认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阴阳者,万物之纲纪”,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相互对立的阴阳两方面,二者相互依存。肝之阴阳互根互用,若无肝之阳,则无肝之阴。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源于中医学的藏象学说、阴阳学说,以肝体阴而用阳生的中医基础理论为土壤,形成了“补肝体强肝用”的学术思想。“肝体阴用阳”最早见于《临证指南医案·肝风》:“故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主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此文明确指出肝体阴用阳的生理特性[23]。体,指的是肝的本体;用,指是肝的功能特性。肝为刚脏,以血为体,以气为用。肝为藏血之脏,血属阴,故肝体为阴;正如王冰注解《素问·五藏生成》言:“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表明肝为刚脏,非柔润而不调和,必赖阴血之滋养方能发挥其正常的生理作用。肝主疏泄,性喜条达,内寄相火,主升主动,故肝用为阳。《素问·灵兰秘典论》释义曰:“肝性刚强,主升发条达,藏血而舍魄,既能防御外辱,又能产生智谋,犹如将军,运筹帷幄,智勇兼备,为将军之官”。
1.2 基于肝肾同源、精血同源理论 肝藏血,肾藏精;肝主疏泄,肾主闭藏;肝与肾关系密切,有“肝肾同源”之说。肝与肾主要表现在精血阴液相互滋生和相互转化。肝主疏泄和藏血,体阴用阳。肾阴涵养肝阴,使肝阳不致上亢,肝阴又可资助肾阴的再生,肾阴充足,方可维持肝阴与肝阳的动态平衡。在五行学说方面,肝属木、肾属水,水为母,木为子,水木为母子相生关系,即为水能涵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相互滋生。正常生理状态下,肝血依赖肾精的滋养,肾精赖于肝血的充养,肝血与肾精,相互滋生,相互转化。精与血均化生于脾胃消化吸收的水谷精微,故称“精血同源”。因此,在病理上,肝阴亏虚,肝血不足等子病及母,则需补肾以强肝,即“补肝体强肝用”。
2 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在臌胀治疗中的体现
2.1 阴虚水停证 臌胀阴虚水停证临床表现多为腹大胀满,青筋显露,形体消瘦,面色晦暗,唇紫暗,口干,烦躁易怒,失眠多梦,亦或见鼻衄,牙龈出血,小便短少,舌质红绛,少苔或光剥苔,脉弦细数。
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认为“阳气易复,阴液难求”,临床重视滋养肝阴,同时兼以健脾益气;治疗以滋养肝肾,育阴利水为法。张教授认为,肝气血阴阳充盛,则肝用得以强健。阴血不能自行,气为阴血之帅,阴血得气助才能行之,故在补肝阴肝血时,张教授常用一贯煎或四君子汤加减,佐以黄芪以补肝气,使肝用发挥,后期病情较重者,重视以补肾阴,滋肝阴,方药用滋水清肝饮加金樱子、女贞子,临床多用滋补阴血药如熟地黄、山药、山萸肉、茯苓、杭芍、泽泻、丹皮、柴胡、栀子、酸枣仁、沙参、麦冬、当归、川楝子、夜交藤、何首乌、枸杞子、金樱子、女贞子、鳖甲、生地黄、白芍、鸡血藤、合欢皮、白茅根、石斛、酸枣仁等。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治疗臌胀在疏肝养肝基础上始终注重滋肝肾之阴,体现其“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
2.2 脾肾阳虚水湿内停证 本证临床多表现为腹大胀满,或见青筋显露,面色晦暗,口唇青紫,平素怕冷,神倦疲乏,少气懒言,或见纳呆,口干不欲饮,小便短少,大便稀溏不调,舌质淡绛,苔薄白,脉沉弦细。
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重视肝、肺、脾、肾,认为肝之气血阴阳,仰赖于肾精、肾阴的充实、滋养,血液之濡养,中宫脾土之气的培育,肾阳、脾阳的温煦,才得以保持其柔和条达畅茂之性,而脾胃为五脏之枢纽,故在温补脾肾基础上,兼顾肺、脾、肾三脏通调水道的作用。治疗初以温补脾肾,化气行水为主,后期乏力明显的患者,则注重益气行水,方药多以真武汤、四君子汤合五苓散加减,同时予桑白皮、大腹皮、冬瓜皮以利水。临床常用药物有制附片、党参、生黄芪、淫羊藿、白术、干姜、茯苓、猪苓、泽泻、车前子(包煎)、砂仁、桂枝、大腹皮、莱菔子等。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认为后期腹水消退,须重视肝脏体阴用阳的生理特性,合理运用温阳药物,以免伤肝阴,故常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龟板、鳖甲、牡蛎、阿胶等,体现其“补肝体强肝用”的学术思想。
3 典型病案
刘某,男,30岁。2018年2月23日初诊。以“反复腹胀大、尿少5年余,加重1个月”为主诉。患者16年前因“急性黄疸型乙型肝炎”入院,经治疗痊愈后未复查。5年来反复腹胀、尿少,西医诊断为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口服利尿剂后腹水消退。此后病情反复发作,每年3~4次,口服利尿剂后腹胀减轻。近1个月因劳累腹胀明显加重,伴纳呆,心烦失眠,为求中医治疗特就诊于我院门诊。刻下症:腹胀大,面色晦暗,腰膝酸困,五心烦热,口干但不欲饮,齿鼻衄血,午后发热,夜寐不安,二便正常,舌质红少津无苔,脉弦细。体格检查:体温36.4 ℃,脉搏80次/min,呼吸20次/min,血压180/110 mmHg。肝病面容,颜面毛细血管扩张,有肝掌、蜘蛛痣,腹水征(+)。上腹部B超:肝硬化并腹水、脾大。肝功能:总胆红素19.4 μmol/L,谷草转氨酶99 U/L,谷丙转氨酶127 U/L,白蛋白31.4 g/L,球蛋白35.2 g/L。中医诊断臌胀,辨证属肝肾阴虚水湿内停证。治疗以滋养肝肾、育阴利水为法。处方:猪苓汤加味。具体方药如下:猪苓、莱菔子各30 g,茯苓20 g,玄参、麦芽、仙鹤草各15 g,滑石、阿胶(烊化)、泽泻、生地黄各10 g,麦冬12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早晚温服。
2018年3月1日二诊:服上方后,患者腹胀、口干症状减轻,舌质红少津,薄白苔,脉弦细。继守前法,处方:猪苓、茯苓、生地黄各20 g,滑石、阿胶(烊化)、泽泻、麦冬、麦芽各10 g,莱菔子15 g,鳖甲(先煎)6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早晚温服。2018年3月8日三诊:服上方后,患者腹胀、口干基本消失,舌质红,苔薄白,脉弦细。继守前法,处方:猪苓、茯苓、生地黄各20 g,滑石、阿胶(烊化)、泽泻、麦冬、麦芽、玄参各10 g,莱菔子15 g,鳖甲(先煎)6 g。7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早晚温服。2018年3月16日四诊:服上方后,患者腹水消失。复查肝功能:总胆红素20.1 μmol/L,谷草转氨酶51 U/L,白蛋白38.4 g/L,球蛋白33.7 g/L。予六味地黄丸口服调理。
按:患者腹部胀大、脉络怒张,故辨病属中医“臌胀”范畴。《伤寒论》记载:猪苓汤可治疗伤寒之邪传入阳明或少阴,化而为热,与水相搏,水热互结,邪热伤阴而致的小便不利,及肝硬化腹水阴液已伤证、水湿内停证,尤适用于合并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出现的舌红症状,疗效较好。肝肾阴虚证多见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肝癌患者,一般均为病程较长、病情危重的患者,肝病见肝肾阴虚者预后多不良,“阳气易复,阴液难求”是也。患者腹胀大,尿少,故属中医“臌胀”范畴。结合牙鼻衄血,午后潮热,夜间烦躁不安,手足心热,小便黄少,舌红少苔,脉弦细数,证属肝肾阴虚、水湿内停。病久,肝肾阴虚,津液不能输布,水液停聚中焦,血瘀不行,故腹胀大,小便黄少。阴虚内热,热伤血络则牙鼻衄血。阴虚火旺,则午后潮热,夜间烦躁不安,不易入睡;舌质红少津无苔,脉弦细为肝肾阴虚、水饮证。
4 小 结
臌胀病情复杂,难以治疗,易反复,且预后差,西医治疗效果不理想。长安医学张氏肝病流派以整体观念、脏腑阴阳学说理论为指导,认为五脏皆有阴阳,肝体阴用阳,肝阴肝阳亦互根互用。肝阳是肝主升发、疏泄、温煦、藏魂、藏血的动力,《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肝为刚脏,内寄相火,寓一阳生生之气。肝主疏泄,又赖阳气之温煦。医者多见肝火而清之,见肝郁而用行气破气之品,均可伤及肝阳,遏其升发、疏泄、温煦、藏血之性,而致肝阳虚,故提出“补肝体,强肝用”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