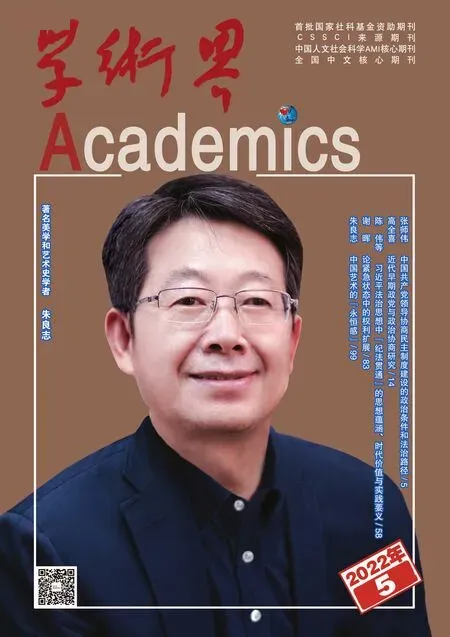“无道”的时代与道家的追求〔*〕
——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哲学解读
石丽娟
(安徽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政治伦理是老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正如政治议题在老子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一样。其伦理思想的这一鲜明特征,汉初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就以“务为治”〔1〕作出了阐释。历史地看,老子政治伦理的产生是因应时代发展而导致的“天下无道”,并在总体上涉及如下内容:其一,探索政治治理之“道”,这是老子政治伦理的基本立足点;其二,探讨治者应有的德性,这是老子政治伦理的核心;其三,阐发政治的根本价值目标,这是老子政治伦理的最终落脚点。
一、时代因素:“天下无道”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2〕社会动荡、战乱频繁,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革正不断冲击着社会的发展。自周代以降,以儒家“礼乐”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受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强烈冲击,从而逐渐瓦解乃至形成“礼崩乐坏”的混乱政治局面,并经由“政治治理之乱”和“社会生存之困”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政治治理之乱
自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制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主流与主导。维系这套政治伦理体系的核心是“礼乐”制度,由此,整个社会自上而下都严格遵循着社会宗法体系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并在各自等级中,遵守相应“礼”“乐”,这是古代社会长期发展的政治基础。但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礼乐”价值所维系的社会伦理体系和政治治理结构也逐渐被破坏。对此,先秦时代哲人的描述就是“天下大乱”“道术将为天下裂”。〔3〕当时社会大乱的主要表现其实就是社会政治治理之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的打破中得到体现。
一是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伦理价值。周代以降,以“礼乐”为价值所构成的政治价值体系便成为古代社会发展与运行的核心价值观,对此,我们可将之称为“礼乐”的政治伦理价值。可是,由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到了春秋中后期,诸侯、贵族等社会上层的财富剧增,从而引发他们借助于经济实力各行其是,甚而“犯上作乱”,原有的政治秩序被打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和谐局面被诸侯、贵族的僭越“礼乐”的乱象所取代。特别是到了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传统的“礼乐”政治伦理更是常常被整个社会抛在一边,甚至沦为了摆设,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物欲横流、道德败坏,人们经常以“仁义”作为外在的装饰,实则行不仁不义的勾当,昔日主导的“礼乐”政治伦理价值,遭到社会的抛弃,人们不再拥有纯朴自然的德性。同时,这一社会乱象反过来对百姓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二是打破了固有的社会治理秩序与结构。自春秋以来所形成的分封制,是实现阶级统治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和系统,它是“礼乐”政治伦理价值体系在阶级统治和治理结构上的反映。这一制度发生作用的基本逻辑是,经由分封制,使得全社会构成等级森严的政治治理结构,从而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平稳有序地发展。然而,当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起来以后,上层统治阶级及贵族势力日渐强大,为了争夺财富,相互之间的侵略战争与土地兼并经常发生,最终导致建立在“礼乐”政治伦理之上的分封制度分崩离析。
(二)社会生存之困
社会政治治理之乱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伦理价值与原有的社会治理结构,造成了“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更是为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生存困惑。这种生存之困主要反映在“天下无道”所产生的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及其给百姓所造成的生存困苦。
对于“天下无道”所产生的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老子指出: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老子·七十二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
这里,老子用相同的句式,突出批判统治者的强权及其给百姓带来的生存压力。其中,一个“威”字、一个“死”字,就足以看出百姓生存环境之恶劣。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深刻地体会到人们遭受到的生存环境的恶劣程度。然而,我们又通过“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两句明显地感受到百姓强烈的反抗之心。显然,在老子的心目中,生活于“天下无道”乱象里的百姓,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带给了他们刻骨铭心的感受。除了生存环境无比恶劣之外,“天下无道”的人们又强烈地感受到生存上的困苦,而这种困苦同样来自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也,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
老子用短短的几句话批判了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百姓陷于饥荒,食不果腹,因此铤而走险,冒死反抗。显然,这里揭示出百姓生存之困、之苦。其中“民之饥”与“民之轻死”是老子对于这一困苦的痛心揭露。
由此可见,置身于“天下无道”与“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生命之艰、生存之困是最为直接的真实感受。因而,正是由于“政治治理之乱”与“社会生存之困”,促使老子把批判的目光聚焦到社会政治伦理方面,进一步去探究如何让社会政治治理回归“大道”,并引发出对于诸如“治者的德性”以及“如何处理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等方面政治伦理的深入思考。
二、政治治理之道:“无为之治”
在老子政治伦理思想中,面对“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他首先追问的是,如何让社会的政治治理回归“大道”。前文已述,针对当时主流的“礼乐”制度过于“有为”的政治原则,老子主张“道常无为”(《老子·三十七章》)。由此他率先提出了“无为之治”这一极富批判性与颠覆性的政治治理之“道”。
(一)何为“无为之治”
老子“无为”思想历来遭受误读,人们常常认为,老子的“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做的“不为主义”,尤其是当老子把“无为”与“无不为”放在一起的时候,即“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则招到更多误读,有人甚而冠之为“阴谋论”的鼻祖,特别是当《老子》中出现诸如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老子·四十五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老子·三十六章》)等论说,就进一步坐实老子是一个“阴谋家”解读的文本学依据。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字面的意思去孤立地理解老子的“无为”,上述的误读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解读老子的哲学思想如果只是在字句的表面做文章,肯定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只是从字面上孤立地去解读,只能产生歧解、误解,甚至是无解,这也是有人冠以老子“阴谋家”的思想根源所在。那么,如何对老子的“无为”作出合理的诠释。我们认为,要想真正理解、把握老子的“无为”思想,必须内在于其哲学文本作整体性把握,并且需要与其“道法自然”的根本主张结合起来。下面将结合《老子》文本作进一步分析: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老子·二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
在《老子》中,老子首次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而且从其表达的“处无为之事”句式中,已经明示了如何理解“无为”的涵义,即“无为”是作为“处事”的修饰语来阐明要如何去“处事”。因此,我们可以把“处无为之事”译为“统治者以‘无为’的方式去‘处事’”。显然,“无为”就不能诠释为“无所事事”或“无所作为”,如果直译则是“以‘无为’的方式”。而要理解“以‘无为’的方式”的涵义,我们要结合老子“道法自然”的根本主张来理解,可以知道,“无为”的真实涵义应该是指“不要违反‘自然’原则的所作所为”。换句话说,“无为”之为是指不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遵循“道法自然”原则的一种“为”。故而,陈鼓应老先生认为“无为”的意思是“顺其自然,不妄为”。〔4〕基于上述诠释思路,第三十七章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根本就不是“阴谋论”的观点,而是指如果所作所“为”能够遵循“道法自然”,就没有什么事不能“为”,没有什么事“为”不成。“无为”是“无不为”的方式与前提;“无不为”是“无为”的结果与效果。
因此,“无为”所体现出的根本涵义应是“不肆意妄为”“不强行所为”“不执意而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无不为”“无不败”的结果。而之所以如此诠释,关键是老子的“无为”主张完全是基于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老子·五十七章》)这样的“有为”而起。另外,在《老子》中,“无为”一词更是形成了与之意义相同的否定式的“概念簇”,这些相同意义的“概念簇”从总体上是对种种“有为”行为的否定与批判。例如: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老子·三十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上述引文中,包括第三十章中的“不以兵强天下”“不敢以取强”,以及“勿矜”“勿伐”“勿骄”“勿强”;第五十七章的“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等,均是老子“无为”政治主张的具体展开。而且,这类否定性与批判性兼具的表达,贯穿于《老子》全书始终。在老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他之所以凸显“无为”这一“概念簇”,对此,刘笑敢先生给出了中肯的看法。他说:“只有‘无为’的最宽泛的意义可以代表老子对世俗传统以及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全面反思和批评。”〔5〕实际上,老子不仅仅在批评、批判,他更是以哲人的大智慧,精心建构如何才能实现“无为之治”的新思想。
(二)如何“无为之治”
作为政治治理之“道”,如何实现与达成“无为之治”是老子政治伦理进一步探讨的重点。通观《老子》一书,老子对之着墨并不多,但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守道”与“清静”,换句话说,老子是通过“守道”与“清静”来实现其“无为之治”的政治治理主张。
接下来,我们结合对《老子》的解读作进一步的论说。首先分析老子关于“守道”的论述: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老子·三十二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一正。(《老子·三十九章》)
所引两章是老子对于统治者“守道”的集中论说。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在老子看来,守护好“无为之道”则是实现“无为之治”的根本。因此,老子的政治之“道”就是“无为之道”,其涵义即是上述所言“不要违反自然原则的所作所为”或者说“无为之为”应是不违背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遵循“道法自然”原则的一种“为”。显然,“守道”就是守护好“无为之道”,也就是“不肆意妄为”“不强行所为”“不执意而为”。所引证的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九章就是这一涵义的体现。
在第三十二章中,老子首先论述了“道”的特性与地位,即“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接着分析了“道”的功用,他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坚守“道”,实行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施政方略,那么就会让人民像江河融入大海一般归顺国家,从而实现天地和谐、国泰民安般的“无为之治”。在第三十九章中,老子以“一”指称“道”,同样首先论证了“道”之功用,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守道”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从“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与“万物得一以生”以及“侯王得一以为天一正”“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正反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
因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守道”是实现“无为之治”的根本。关于这一点,陈鼓应对之的解读是:“老子用‘朴’来形容‘道’的原始‘无名’的状态,侯王若能持守无名之朴的‘道’,亦即是持守它那自然无为的特性,人民当能安然自适,各遂其生。”〔6〕如果说“守道”是统治者实现“无为之治”的根本原则,那么“清静”则是统治阶级达成“无为之治”的具体方法。我们还是经由对《老子》的分析来说明。老子指出: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二十六章》)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五章》)
在第十六章中,老子通过观察万物生长周期的循环往复,论说了遵循自然的“清静”规律的重要性,从而主张人们要保持虚静的生活态度,回归事物存在的本来。在老子看来,“道”是虚无宁静的,统治者如果能够“致虚极,守静笃”,就能达到清静无为、“归根复命”的结果。第二十六章中,老子同样论述了“清静”的重要性,即“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清静”是领导统御的主帅,并以此警醒统治者不能轻率浮躁,脱离“清静”这个根本,否则将会造成“轻则失根,躁则失君”的严重后果。而在第四十五章中,“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则通过对比的言说方式明确地揭示了天下政治的内涵就体现为“清静”。对于统治者如何才能做到“清静”,老子同样有着深刻的论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
所引两章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即“知足知止”,这在老子看来是统治者做到“清静”的法宝。首先,老子主张“知足者富”。这个“富”并非财富上的“富”,而是指精神上能够持守“大道”的富有。其次,通过对比,老子揭示了为什么要“知足知止”。因为,老子认为,统治者最大的祸患是不知足,无休止地追求财货名利,其结果必然招致精神上对于“道”的偏离,只有“知足知止”,才能“不辱”“不殆”,才能“可以长久”,否则“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便是他们的下场。最后,老子再次从反面论证了“祸”和“咎”都是因为“不知足”与“欲得”。正如著名道家学者陈鼓应先生在解读老子上述观点时,指出:“常人多轻身而徇名利,贪得而不顾危亡。老子乃唤醒世人要贵重生命,不可为名利而奋不顾身。”〔7〕
总之,通过以上系统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对“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老子率先提出了“无为之治”这一极富批判性与颠覆性的政治治理之“道”。并经由何为“无为之治”及如何“无为之治”两个方面的剖析,向人们展示了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初步主张。当然,老子不会仅仅满足于这一主张,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进一步看到,为了达成完美的政治治理,统治者的德性便成为老子政治伦理关注的核心课题。
三、治者的德性:“上德”“玄德”
在老子政治伦理中,统治者(下文简称“治者”)的德性是其核心内容。之所以是核心内容,一方面,治者德性是政治治理之“道”的具体体现,关乎统治者以何种方略实施政治治理;另一方面,治者德性更是事关老子政治伦理最终价值指向的根本性问题,关系到治者以何种方式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
(一)上德无为
在老子哲学思想中,“德”的重要性与地位仅次于“道”。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德”作为“道”落实到社会政治治理方面的具体体现,其涵义主要指治者的德性。显然,在老子视域中,治者的德性一定是遵循“道法自然”的根本原则,一定是体现“无为之治”的治理之“道”。
显然,老子道家之“德”与儒家之“德”有很大的不同。在稍后的引证中,我们将可以看到,老子“自然”“无为”之“德”是对于儒家“仁义”之“德”的反思与批判,并在批判中确立治者应该具备的德性。关于治者德性,在《老子》第三十八章中,老子首先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
这一章是老子集中对“德”的论说,既包括道家之“德”的内涵、功用,也包含对儒家“仁义”之“德”的批判,在《老子》“德”论中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概括而言,本章虽然没有提起“自然”,但却是老子“道法自然”原则的一贯体现。诚如刘笑敢所言:“‘道法自然’的论题明确标示自然作为最高原则和最高价值的地位,因而其精神便渗透到《老子》思想的各个方面,而不必处处提到‘自然’二字。”〔8〕而且,正是通过本章论说,老子明确提出了治者德性的第一个主张“上德无为”。对于本章可以从四个层面分析:
其一,将“德”分作“上、下”。老子把“德”分作“上德”与“下德”,并借助于两者间的对比,表明“上德”符合“道”之“自然”“无为”的特性,因为,“上德”从来都认为自己“不德”,也就是说,不张扬自己“有德”。这是“道”在社会上体现出的最高层次,也是老子极力倡导的“无为之治”的表现。而“下德”是不符合“道”之要求,因为“下德”之人时时欲表现出自己有“德”,处处张扬“德”的存在。在老子看来,这不是“道”的体现,也是老子反对与批判的“有为”行为。
其二,揭示“上德”作为治者德性的涵义,即“无为”。这里,老子是通过与“下德”对比作出的揭示。老子认为,“上德”之人行为处事都能够遵循“大道”,遵循“大道”即是“道法自然”。“上德”不仅“无为”,而且“无以为”。这里的“无以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去把握,一是“上德”之人所作所为既能顺应天地万物之自然与规律,又不是故意的、勉强的、做作式的作为;二是“上德”之人遵循“无为”,就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然而,“下德”之人“有为”,“有为”意味着不能够行“大道”“法自然”,他们“虽始终不离德名,但是有意而求,有目的指向,有伪装和欺骗性”,〔9〕所以是一种“有为”。可见,老子赋予“上德无为”的涵义,实是与“道法自然”一脉相承的理论思路,是其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映。
其三,批判传统的“仁义”之德。老子在主张“上德无为”的同时,对当时社会上主流的政治伦理价值,包括“上仁”“上义”“上礼”等作出批判。在老子看来,“上仁”“上义”“上礼”都属于“下德”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之”。在政治治理领域,这种“为之”就是用“礼乐”制度,用“仁义礼智”去规范社会、范导百姓。但是,这种规范或范导有可能走向反面,因为“统治者用仁义来规范天下,天下人都奔命于仁义,抛弃自己的本性,用仁义伪装自己。所以,老子所‘绝弃’的‘仁’‘义’也可以说正是他所‘绝弃’的‘伪’‘诈’”。〔10〕
需要明确的是,老子这里批判的并非“仁义”本身,而是“仁义”盛行可能导致的对于人性的戕害。总之,针对“有为”的政治治理现实及其给社会与百姓造成的负面影响,老子主张治者应有的德性是“上德无为”。显然,“上德无为”是老子关于治者德性的原则性规定,其进一步展开必然是在具体操作层面的德性思想,这就是老子关于治者德性的第二个主张“玄德不有”。
(二)玄德不有
玄德“不有”并不是老子本身的论说,而是本文根据对《老子》“玄德”涵义及其特征的解读分析,所作出的一个概括性的方便说法。具体来讲,在《老子》中,作为治者德性,“玄德”真正出现次数只有三次,但是,“玄德”所表达的涵义及其作用,则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代表性,这就可以看作是老子关于治者德性的第二个主张“玄德不有”。
在老子政治伦理思想中,作为治者德性的具体体现之一,“玄德不有”首先表现为“道”对于万事万物之“不占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表现为治者的“不有”的德性。对此,老子认为: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
在本章,老子对作为治者德性的“玄德”作了系统论说。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玄德”就是指最深厚、最广大的“上德”,它是“上德无为”在现实层面治者德性的具体反映。我们通过两个方面的理解来阐发老子的“玄德”。
一是“道”与“德”的关系。“道生之,德畜之”告诉我们“道”产生万物,是万物存在的根源,但不是产生“德”的根据,而是“德”是“道”落实于现实的具体表现。关于二者的如上关系,刘笑敢先生也有着类似的看法,他在解读本章时曾指出:“德是道之功能的具体体现和保证,所以说‘道生之,德畜之’。”〔11〕
当然,也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在理解“道”和“德”的关系时,把二者看作是总体与个体,或总与分之间的关系。如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就认为:“德是一物所得于道者。德是分,道是全。一物所得于道以成其体者为德。德实即是一物之本性。”〔12〕在笔者看来,把二者关系视作是“全”与“分”的关系,这种理解其实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暗含着“道”产生了“德”。不是“道”产生了“德”,而是“德”是“道”落实于人世和人事的具体体现。
二是“玄德”的内涵。首先,这里涉及到“德”的功用。因为“德”是“道”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与保证,所以,当“道”产生万物之后,“德”的功用就呈现为蓄养万物,促进万物生长。其次,表明“道”生养万物的根本作用。尽管万物的成长需要“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的过程,但起根本作用的仍然是“道”。最后,揭示出“玄德”的涵义。即“道”之所以能够成就万物,其根本的因素在于“道”拥有“玄德”,这是因为“这既是最高之道本身的品德的体现,又是体现道之品德的圣人之德”。〔13〕刘笑敢先生对于“玄德”作用的高度评价,又为我们进一步澄清了“道”与“德”的关系。
因而,老子“玄德”的涵义是指“道”虽然生养、成就了万物,但却不是“占有”“恃有”与“宰有”。换句话说,“道”的创生性不带有任何自身的目的性。这也是本文把老子关于治者德性的第二个主张称之为“玄德不有”的关键证据。
综上所述,基于政治治理的“无为之治”,老子阐发了与之相契合的治者德性,并通过“上德无为”与“玄德不有”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主张。那么,基于“上德无为”与“玄德不有”的治者德性,老子政治伦理将会有怎样的价值追求?这也是老子政治伦理欲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
四、价值目标:“以百姓心为心”
价值目标是老子政治伦理的最后落脚点,这是在探索了政治治理之“道”、治者德性的基础上,理论逻辑上的自然结果。老子政治伦理价值目标回答的是政治伦理的最终理论归宿是什么。通观《老子》全书,老子对此的回答是“以百姓心为心”。
(一)“以百姓心为心”:民本实质
作为老子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以百姓心为心”也是整个老子哲学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基本含义是指,在政治治理过程中,统治者不应有自己个人或团体的私心与利益,处理政务凡事要以老百姓的意愿、要求与利益为标准和原则,为政要做到体恤民情、顺应民意,利而不害,善待百姓。可以说,“以百姓心为心”也就是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古代的道家版本。请看老子对此的论说: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
《老子》第四十九章的主题是阐发老子心目中政治理想:老子希望统治者应该是依“道”行政的圣人,希望政治环境应该到处充满着“善”与“信”,希望整个社会能够回归纯朴发展的状态。然而,上述这些希望又都是基于“以百姓心为心”价值目标作为根本出发点的,这从本章首句“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能够明显反映出来。
实际上,在《老子》一书中,体现百姓的“民”字一共出现次数达33次,这样高频的出现,显然明确地表明了老子政治伦理重民、为民、亲民、爱民、利民、善民的民本思想实质。可以说,上述民本思想就像一根思想红线贯穿于全书。比如,老子认为: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老子·十章》)
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
其中,第十章“爱民治国”强调的是治理国家要以“爱民”为核心;第十九章“民利百倍”与“民复孝慈”强调统治者施行统治要以“有利于人民”,能够让百姓回归“孝慈”的社会伦理环境为重;第五十七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是从反面论说,如果社会治理中政治禁令过多过频,必然会限制百姓的聪明才智与积极性,并导致人民的贫困。可见,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思想是其民本思想实质的具体反映。
对于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民本实质与特征,许多道家学者也是予以高度认同。比如,陈鼓应指出:“老子虽不能说是劳动人民的思想家,但他对劳动人民的不幸予以深深的同情,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民’、‘百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4〕徐梵澄先生在释读此章时,以孟子思想类比老子民本思想时,也认为:“‘以百姓心为心’者也,则大公而无私心者也。则百姓而治百姓者也。则百姓之自治也。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进贤去不肖,皆征之于国人,此孟子之说齐宣王也。此本意之大同者也。”〔15〕显然,上述陈鼓应和徐梵澄两位大家对于“以百姓心为心”的解读,可谓深得老子政治伦理思想的个中三昧。
在理解老子民主思想实质的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老子的民本思想与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在重视民意方面是一致的、相通的,但二者又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老子道家民本思想以“道法自然”为根本前提,强调政治的“无为之治”,注重百姓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儒家民本思想以“仁义”为伦理本位,强调政治的“礼乐”宗法属性与传统,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特别是政治利益。对此,我们也可以参考刘笑敢先生的一些观点来理解。他认为:“儒家传统和道家传统都重视民意,这是二者在基础层面上的一致,是山脉蜿蜒相连的一面,是儒道相通的一面。但是,从较高层面上看,儒道显然是不同的,二者所设最高价值不同,最高的理想目标不同。”〔16〕
同时,我们也应强调,不管是老子的民本思想,还是儒家的民本思想,皆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前者的本质是中国传统政治治理与政治思想中对于民意的尊重与重视;而后者的本质则是建立在一定政治制度基础之上“让民做主”的一种制度性体现。
(二)“以百姓心为心”:“无为”之道
作为老子政治伦理的价值目标,“以百姓心为心”民本实质无疑是老子一贯倡导的“无为之治”政治治理理念的体现,也是治者“上德无为”和“玄德不有”德性的反映,而这在根本上则是对“道法自然”根本原则的遵循,是“无为”之道。
对于如何实现“以百姓心为心”的无为之“道”,老子则着重从要求统治者减少私心权欲,限制权力乱作为等方面作出阐述。请看老子对此的论说: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故无失。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所引三章的主旨是老子政治伦理“无为”之道的体现,共同表现出了老子对于限制统治者权力的主张。以下我们分别作出分析。
在第二十九章中,老子首先论证统治者的“有为”政治治理,是无法达成目的的;在此基础上,老子强调唯有尊重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因势利导,顺其自然,施行“无为之治”。而文中的“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则是对本章主旨的揭示,表明老子“以百姓心为心”的“无为”之道,就是要求统治者通过“去甚、去奢、去泰”来减少私心权欲,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去甚”强调去除政治治理中的极端做法,“去奢”强调的是去除治者的奢侈与贪欲,而“去泰”则强调权力中过分的一面。总之,三者都反映了统治者要减少私心权欲,限制自身权力胡乱作为的政治伦理诉求。故“去甚、去奢、去泰”可以看作是老子对于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总要求。
第五十七章是老子在限制统治者权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如何处理治者与百姓的关系,也就是传统的君民关系作出的阐发。其原则性要求就是第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能够“无为治者”,百姓就能够自我化育、自然以成。而“好静”“无事”“无欲”分别从三个方面体现了“无为”的具体做法,其结果就是“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文中“民自化”“民自正”与“民自富”“民自朴”四词叠用,意在突出统治者治国理政要体现“无为之治”,要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
第八十一章是《老子》最后一章,老子分别从两个方面,再次强调了限制治者权力,造福百姓的重要性。一方面,在“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论述中,老子认为统治者越是约束对于财货的欲望,就越能让百姓获得更多。另一方面,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中,老子通过对“天道”与“人道”之别的论述,强调了统治者要像“天道”一样“利而不害”“为而不争”,从而成为百姓和天地万物的成就者,而不是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与民争利。
综上所述,在老子政治伦理思想中,基于政治治理“无为”之道的理论根基与治者“上德无为”和“玄德不有”的德性基础,“以百姓心为心”价值目标是这一理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体现,这也充分表明,在老子政治伦理思想中,“民”不应成为政治的工具与手段,而应是政治治理本身的目的与追求。
注释:
〔1〕汉初著名史学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其中的“道德”便是指老子所著《老子》的思想。
〔2〕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的社会特征,老子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而道家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庄子有着类似的阐述,他认为“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庄子·人间世》)同样,在《论语·季氏》中,孔子也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论说。
〔3〕对于当时“天下大乱”的现象,道家思想家庄子有着详细的描述。他在《庄子·天下》篇指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4〕〔6〕〔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9、196、240页。
〔5〕〔11〕〔13〕〔16〕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37、534、535、493页。
〔8〕刘笑敢:《试论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
〔9〕陈霞:《论道家道德哲学的几个特点》,《宗教学研究》2010年增刊。
〔10〕陈霞:《道家哲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
〔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4页。
〔14〕陈鼓应、白溪:《老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15〕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