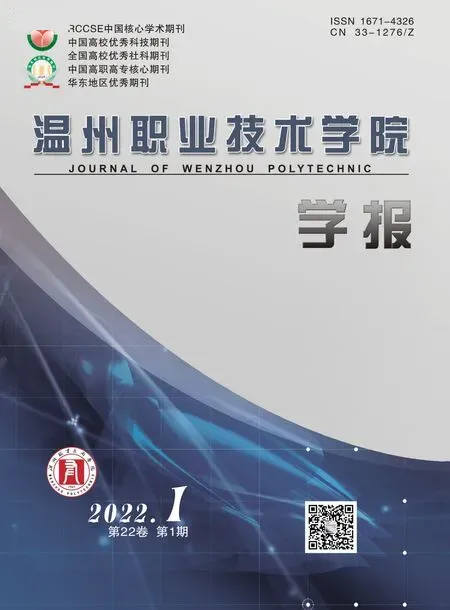温州竹枝词中的温州高腔
饶力钧
(温州大学,浙江 温州 325035)
竹枝词起源于楚地民歌①竹枝词的起源地问题曾引起历代学者的论争,竹枝词究竟起源于“巴渝”或是“荆楚”,迄今尚无定论。孙杰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楚地说”给出了较为可靠的论证,可供参考。见孙杰:《竹枝词发展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7-19页。,是一种以七言四句为主要形式(而非七言绝句)、以吟咏风土为特色的特殊诗体。温州不仅是南戏之乡,还盛行高腔、昆剧、京剧、乱弹等各类戏曲,观看戏曲演出已成为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文化的熏陶下,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戏曲元素融入竹枝词创作;加之竹枝词本身具备“咏风土”“讽世俗”的功能②王士祯云:“《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见(清)郎廷槐编:《师友诗传录》,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四八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00页。,部分温州竹枝词里存在戏曲活动的记载,我们也可以借此管窥当时观剧、演剧的情况。
温州竹枝词,顾名思义是以温州地区的人或事物作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笔者搜集到的温州竹枝词共56 种,总计1 790 首。其中,宋代作品有3种,元代作品有1种,明代的有3种,清代和民国的作品总计49 种、1 759 首,占了总数的98%。历代温州竹枝词作者共计45人。从历代作者的籍贯来看,除去籍贯不详的作者,温籍作者占了半数以上。除了本地文人,其他作者或是旅经温州,或是在温做官。
一、温州高腔起源考
温州高腔,亦称瑞安高腔,是温州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一般认为其产生于明末,迄今已四百余年[1]。但它并非萌生于瑞安,很可能缘于瑞安区域内流行的高腔班社多、从艺人员多且持续时间长,域外人呼贯以“瑞安”二字,更远者贯以“温州”二字而约定俗成[2]3-4。
瑞安高腔的音乐体系属曲牌体,然就其曲调旋律及剧目来看,则与“台州乱弹”中的高腔唱调及与新昌调腔相近或相同,或以为是新昌调腔的分支。又,瑞安高腔中有部分用管弦托唱者,则与松阳高腔类同[2]4。两种演唱方式构成两类唱腔:前者俗称“八平高腔”,不用丝竹乐器伴奏,一人启齿、众人帮和,锣鼓助节为其特点,部分曲牌多用转调移位或调式互转等手法[2]6;后者俗称“四平高腔”①李子敏云:“这里的‘四平’既不指京剧的‘四平调’,也不同于明中叶比‘海盐腔’稍后出现的‘四平腔’,而是增加了笛子、板胡伴奏的‘声各小变’的高腔。”,其特点是用管弦乐器托唱,歌唱性强,单曲使用时,间有类似“滚”的夹白、夹唱[2]6。总体来说,不托管弦、一唱众和、锣鼓助节仍是瑞安高腔的主要演唱形式,高亢激越、粗犷奔放仍是瑞安高腔的主要音乐特点;但由于“四平高腔”的融入,又给瑞安高腔带来了粗中有细、刚中带柔的一面②李子敏云:“从旋律线和‘定腔乐汇’(帮腔句)来说,变化还是不小的。增加了伴奏,显得新颖;在‘帮腔’句上,不再是句句帮,但保留了帮腔形式、制式,而以一种在‘滚唱’之后的‘段略句’尾,用发展、扩展、更易上口的‘大’的‘定腔乐汇’来统一唱段风格,别有一番情致。”[3]44。
瑞安高腔的起源已无明确文献记载可考,笔者认为其源头主要有四:
1.江西弋阳腔
弋阳腔是明代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剧种[4]。它流传到全国各地以后,与当地民间土腔结合形成了新的腔调;到了清代,文人们便把弋阳腔及其各种支派通称为“高腔”[5]。李调元《剧话》云:“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向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6]浙江毗邻江西,温州本地高腔也可能受到江西弋阳腔的影响。上文提到,瑞安高腔中的一类唱腔俗称“八平高腔”,而现在赣剧弋阳腔的俗名同为“八平高腔”[7]86。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云:“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8]温州高腔的帮腔形式与赣剧弋阳腔相同,都由乐队人员“齐帮”③沈沉云:“演员在台上演唱时,如果是一句七字,句尾一字或三字由后台或台上乐队帮唱,温州民间谓之‘夹燥挞’。”[9]49,帮腔时翻高八度,有锣鼓助节。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称自己“但爱看声色喧腾之出”[10],所谓“声色喧腾之出”,指的就是高腔、乱弹之类[11]8。再从剧目上来看,笔者将沈沉搜集的“老祥云”高腔班剧目表(这份剧目清单还包括了新祥云以及后来大玉麟等戏班的常演剧目)④据瑞安高腔老艺人瞿济柳称,瑞安各高腔班都把老祥云戏班的剧目奉为圭臬。[12]77,与赣剧弋阳腔“江湖十八本”相比较⑤江西赣剧高腔十八本剧目为:《青梅会》《古城会》《风波亭》《定天山》《金貂记》《龙凤剑》《珍珠记》《卖水记》《长城记》《八义记》《十义记》《鹦鹉记》《清风亭》《洛阳桥》《三元记》《白蛇记》《摇钱树》《乌盆记》。见李连生:《明代弋阳腔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第182页。,发现温州高腔班上演过《卖水记》《三元记》《十义记》等弋阳腔作品。这些都是温州高腔受到江西弋阳腔影响的直接证据。
2.四平腔(徽州腔)
根据流沙的考证,四平腔是徽州腔的别名[7]92-114。所谓“平”,就是指帮腔句的“韵头”,所以“八平高腔”实际上是八个韵头的高腔;浙江婺剧中的西安高腔俗名为“四平高腔”,则是四个韵头的高腔[7]86。温州高腔中的另一类唱腔也称为“四平高腔”,可见它亦与衢州的西安高腔有关。从四平腔的发展源流来看,有一条基本路线是:徽州腔—衢州四平高腔—绍兴和温州的四平腔[7]98。绍兴的四平腔集中体现在调腔的四平腔上,温州的四平腔则主要体现在温州高腔的四平高腔中。清代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四平腔〉序》云:“四平腔,浙之绍兴土风也。亦弋阳之类,但调少平,春赛无处无之。”[13]158与弋阳腔中的“八平高腔”相比,传入浙江的四平高腔在帮腔句上减少了韵头,故削弱了弋阳腔高亢激越的特色。除了韵头减少,四平腔“调少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声帮腔方面,大部分乐句已改为真嗓帮腔,只有少部分用假嗓[7]90。温州四平高腔在保持“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这一特征的同时,在唱腔上由假嗓改成真嗓,因而形成了“歌唱性强”“畸农士女皆能合”的特点。此外,在新昌调腔四平腔和昆腔的影响下,增加了管弦乐器伴奏⑥沈沉在《我所知道的瑞安高腔》云:“有的高腔剧种觉得这种演唱方式过于原始,就加入伴奏,同时废弃帮腔,称为‘高腔昆唱’,上世纪50年代温州胜利乱弹剧团演出的《循环报》就属于此类。”[9]313,唱腔间或“加滚”,时而散唱,遂成为独具特色的温州四平高腔。
3.徽池雅调
上文提到,温州高腔的唱腔曲调及剧目与新昌调腔接近,或以为是新昌调腔的分支[2]4,说明温州高腔受新昌调腔的影响极深。据流沙考证,现存的新昌调腔,是明代徽池雅调留在浙东的一支,也是徽池雅调的代表性剧种[7]153-183。既然温州高腔深受新昌调腔影响,那么那它必然与徽池雅调存在着源流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1)在唱腔方面,由于徽池雅调继承了青阳腔滚调,随着滚调的发展,徽池雅调的曲体也发生了变化——在音乐唱腔上打破了曲牌体结构,形成了类似于板腔体的音乐形式。[7]177王骥德把这种腔调特点概括为“不分调名,亦无板眼”①王骥德云:“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见(明)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释:《曲律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页。。如新昌调腔“古戏”中的“叠板”②石永彬主编《新昌调腔》云:“叠板为帮腔句独唱部分的扩展形式,其扩展部分常为旋律音型的反复。它可以是唱的,也可以是念的,或是二者的结合。……叠板仅见于古戏。”见石永彬主编;王秋华,水正槐,吕月明编著:《新昌调腔》,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 年版,第51页。,实际上就是青阳腔滚调[7]177-178。而在温州高腔中,虽然其“文体”(剧唱)以曲牌为基本结构单位,但其“乐体”(唱调)以腔句为基本单位③李子敏:“高腔中的腔句(唱),由‘一人启口’的传词与‘定腔乐汇’的‘接腔’两部分组成,即:一个腔句为一个结构单位。”[3]41,一个个独立的音乐“腔句”可以敷唱一句句曲文、曲牌甚至一“套”、一剧的剧唱,说明“腔句组”与文体并不完全重合[3]41,也证明了温州高腔的唱腔突破了曲牌体的限制。
(2)在角色体制方面,温州高腔的角色有老生、大花、小花、正生、老旦、正旦、青衣旦、文武小生等[11]8。根据吕济深《调腔初探》一文[14]165,调腔戏的行当有“三花、四白、五旦堂”之称④“三花”即大花脸、二花脸、小花脸,“四白”即老生、正生、副末、小生,“五旦堂”即老旦、正旦、当家旦、花旦、五旦(或称“拜堂旦”)。。由于新昌调腔传自明代的徽池雅调,在角色行当上继承了青阳腔的传统体制[7]295-296;温州高腔的角色配置与新昌调腔较为类似,进一步证明了徽池雅调是温州高腔的一个源头。
(3)在剧目方面,通过对比沈沉整理的温州高腔剧目表[12]77和吕济深统计的现存调腔“古戏”[14]143-146,可以发现两者中共同剧目有:《琵琶记》《荆钗记》《白兔记》《三元记》《金印记》《芦花记》《葵花记》等。“古戏”是调腔的早期剧目,大部分传自徽池雅调[7]168,这就证明了温州高腔中的剧目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徽池雅调。
4.早期温州高腔(温州腔)
温州是南戏的发源地,入明以后南戏在浙江形成余姚、海盐两腔,同时在温州地方留下的温州腔亦为宋元南戏在当地发展的结果[7]133。陆容的《菽园杂记》卷十云:“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15]祝允明在其《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谈到“温州戏文之调”:“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过在何处?噫嘻,陋哉!”[16]所谓温州戏文之调,就是温州腔,清初以后尚在演出的温州高腔与其必有承袭关系。根据温州昆曲老艺人钱百川的说法,清末以前瑞安县流传的高腔戏就是当地最古老的温州高腔[7]333-334。今人张潇潇亦通过旋律分析的技术手段,对今存瓯剧高腔曲牌进行整理、分类,考证出瓯剧高腔与其母体(温州民间歌曲)并未截然分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南戏音乐的早期特征[17]。既然是温州高腔,必然会以温州话进行演唱,在唱腔上吸收温州本地民歌小调的特点,在曲调上受到方言语音语调的影响,这些都是声腔传播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事实。
综上,笔者认为温州高腔上承弋阳腔和早期温州高腔,下接四平腔和徽池雅调,由多个声腔、剧种共同影响形成。
二、温州竹枝词视角下的高腔发展史
高腔是弋阳腔的俗名,清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弋阳腔〉序》曾云:“(弋阳腔)俗名高腔,视昆调甚高也。金鼓喧阗,一唱众和。”[13]157上文提到,明代弋阳腔传入全国各地后产生了各种支派,清初以后它们就被统称为“高腔”。据近人流沙考证,南方高腔是弋阳诸腔的发展[7]76-80。也就是说,明末清初的温州高腔是在弋阳腔的影响下形成的⑤李子敏云:“瑞安高腔之谓的‘形成’时间当不迟于明末清初。”。
乾隆时弋阳腔就已在温州地区流行。清人张綦毋《船屯渔唱》其九十四云:“儿童唇吻叶宫商,学得昆山与弋阳。不用当筵观鲍老,演来舞袖亦郎当。”[18]这首竹枝词描述的是乾隆年间出现在温州平阳一带的“小儿班”(乾隆平阳人杨士炳亦有《小儿班演剧》一诗[19]),这种“小儿班”专门学唱昆山腔和弋阳腔,受到时人称赞[20]。近人黄一萍也在《温州之戏剧》“高腔班”条云:“清初尚昆剧,后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21]398
弋阳腔(温州高腔)至迟在嘉庆时达到大盛。周衣德《永嘉杂诗》其四十四云:“《王魁》南曲擅无双,榜禁森严忆渡江。一自红羊遭浩劫,新声换作弋阳腔。”[22]185“红羊劫”语出唐殷尧藩《李节度平虏诗》:“太平从此销兵甲,记取红羊换劫年。”[23]宋人柴望《丙丁龟鉴》序言谓国家在丙午、丁未年多遭厄运[24]1-2,所以发生在丙午年(1126)的“靖康之耻”也被称为“红羊劫”①元人所续《丙丁龟鉴续录》云:“谨按历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24]40。周衣德的“一自红羊遭浩劫”在诗中具有双重作用与含义:第一,承接上文。说明在宋室南渡后,以《王魁》为代表的南戏在民间兴起,从温州流传到杭州后,甚至遭到了统治者的榜禁[25];第二,引出下文。据《周衣德集》前言,周衣德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22]1,其在世时只有乾隆丙午年(1786)发生了“红羊劫”②据《清史稿》和《清史编年》描述,乾隆五十一年(1786)全国各地多发生天灾人祸。见(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一卷),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8-472页。郭成康编:《清史编年》(第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0-541页。。结合下文“新声换作弋阳腔”,也就是说至迟在嘉庆时,周衣德见证了温州地区声腔的转变——即“弋阳腔”(此处指温州高腔)盛行。整首诗其实是作者对南戏历史的杂咏,从追溯早期南戏的风靡谈到高腔的兴起,中间以“红羊劫”作为线索将二者联系。
道光时温州高腔仍然盛行,不过此后即将由盛转衰。道光时梁章钜就养于温州,他在《浪迹续谈》卷六“文班武班”条谈到:“余金星不入命,于音律懵无所知,故每遇剧筵,但爱看声色喧腾之出……比年余侨居邗水,就养瓯江,时有演戏之局。大约专讲昆腔者,不过十之三,与余同嗜者,竟十之七矣。”[10]当时喜欢看高腔、乱弹戏的人尚有“十之七”,可见温州高腔在民间的受欢迎程度。温州民谚有“高昆乱弹,和调讨饭”之说,在四类地方剧种中高腔排行居首,证明高腔在温州传统戏曲之地位[9]50;本地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高腔班和别的戏班一起演出时,若高腔班未开锣,其他班不得抢先开锣,足见同行对高腔的尊重[11]8。
道光以后,温州高腔渐趋衰落;与之相反的是温州昆剧在同、光时期迎来了中兴。黄一萍《温州之戏剧》“昆腔班”条云:“以后有‘同福’、‘品玉’两班,继续而起,所演昆剧,均藉重排。……同、光年间,蔚然崛起,是时也,可谓中兴时期。”[21]399有学者对《张棡日记》中的戏曲史料进行分析,从光绪十四年(1888)到民国五年(1916),温州地区演出剧种以昆剧为主;民国六年(1917)起,京剧取代昆剧成为主要剧种[26]。这也意味着咸、同年间是温州高腔最后的余晖。
至光绪间,高腔单独成班者已寥寥无几,多数艺人加入“乱弹班”,部分艺人流入“超度”(亡灵)班演唱糊口[2]4。晚清以迄民国,温州高腔班可考者,仅剩来自福建的“老祥云”“新祥云”“大玉麟”等。民国十四年(1925)后,“老祥云”“新祥云”相继解体,班社中的瑞安籍艺人集资组建“大玉麟”班,终因大势已去,于民国十六年(1927)冬天悄然退隐[12]79。黄一萍定稿于1932 年的《温州之戏剧》描述道:“二十年前仅有‘祥云’一班,旋分为二,卒以社会不甚器重,卒并为一。(民国)十四年秋解散之后,久不见于内地。近虽遗硕果仅存之‘大玉麟’一班,但精华已失,佳剧沦亡,已成强弩之末矣。……温州戏剧之有艺术价值者,不能望其余矣。惜高腔已成广陵散,不需几时,恐成戏剧史上之蜕化物,诚可慨也。”[21]399-403所幸瓯剧中还保留了《雷公报》《循环报》《报恩亭》《紫阳观》等4本高腔大戏,以及《宜秋山》《北湖州》《访白袍》《磨坊串戏》等折子戏,使高腔的身影不至于完全埋没。此外,尚有一些唱乱弹腔的剧目插唱部分高腔,如《闹流沙》《太平春》《玉连环》等[2]5。
三、温州竹枝词中的高腔剧目
经笔者统计,温州竹枝词中涉及的高腔剧目有3种:
1. 《荆钗记》
此剧在温州民间影响很大,温州几种《竹枝词》均有涉及[27]10。如郭钟岳《东瓯百咏》其十七云:“乡人艳说梅溪事,不为章纶道姓名。”[28]方鼎锐《温州竹枝词》其二十云:“乡评难免口雌黄,演出荆钗话短长。”[28]这两首竹枝词中都提到了南戏《荆钗记》。
清戴文儁在《瓯江竹枝词》自序中云:“同治十有一年(1872)春,江都郭外峰司马作温州竹枝词。”[29]其中郭外峰司马即郭钟岳。据郭氏《东瓯百咏》自序,“余客此三年,略已能道,爰作竹枝词一百首”[28],则郭钟岳创作温州竹枝词的时间应在同治八年到十一年(1869—1872)。方鼎锐在同治年间曾任温处道道员,其《温州竹枝词》同样刊于同治十一年[30]91。说明两人观看《荆钗记》的时间均为同治年间。据徐宏图《浙江昆剧史》一书的划分,嘉庆至同治年间为温州昆剧的沉寂期[31];但随着同治年间“同福”“品玉”等昆班的崛起,昆剧至光绪时迎来中兴,这也意谓着高腔的时代在同治时缓缓落下帷幕。从高腔流行的年代来看,虽然同治时高腔的地位渐由昆剧所取代,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在民间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上面两首竹枝词中描述的观戏对象均为“乡人”),故郭钟岳、方鼎锐等人看到的《荆钗记》很有可能是用温州高腔演唱的;再从竹枝词内容来看,“乡人艳说梅溪事”的后半句为“不为章纶道姓名”,其中提到的“章纶”实指温州高腔剧目《拜天顺》①薛钟斗《戏言校记》云:“温高腔班所演之《拜天顺》,则乐清章恭毅事。”见薛钟斗:《寄瓯寄笔》,温州市图书馆藏民国七年(1918)油印本,卷一。,从逻辑上推断,前半句描述的“梅溪事”也应指高腔戏《荆钗记》。
2. 《拜天顺》
郭钟岳《东瓯百咏》其十七云:“夜泛扁舟到乐成,五更打桨待天明。乡人艳说梅溪事,不为章纶道姓名。”[28]这里提到了高腔戏《拜天顺》的主人公章纶。《拜天顺》是温州高腔班独有剧目,惜剧本已佚[27]5。章纶其人,《明史·章纶传》有载,现择要摘录如下:
章纶字大经,乐清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仪制郎中。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景泰)五年五月,钟同上奏请复储。越二日,纶亦抗疏陈修德弭灾十四事。……疏入,帝大怒。……立执纶及钟同下诏狱。榜掠惨酷,逼引主使及交通南宫状。濒死,无一语。会大风扬沙,昼晦,狱得稍缓,令锢之。明年杖廖庄阙下,因封杖就狱中杖纶、同各百。同竟死,纶长系如故。英宗复位,……帝乃立释纶。命内侍检前疏,不得。内侍从旁诵数语,帝嗟叹再三,擢礼部右侍郎[32]。
民间文人将章纶的这段经历稍加剪裁,并添些恩怨相报之类的关目,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大概是在清嘉、道年间[33]361。据瑞安高腔老艺人瞿济柳先生口述,《拜天顺》剧情大致为:
明时,外国进贡犀牛角杯与龙头绣帕两件宝物,皇帝将二宝交给兵部尚书王永保管。时值元宵梅山放灯,尚书夫人偕婢梅香携宝看灯,不慎弄丢宝物。乐清举人章纶主仆上京赶考,途径梅山时拾得二宝,便多方寻找宝物失主。红毛国主闻中国有此二宝,遣使送来战表,要帝亲自将宝物送往边关,否则领兵侵入中原。帝惧,命王永交宝。王永回府向夫人索宝,得知二宝被梅香失落。王永眼见要满门抄斩,盛怒之下踢死梅香,弃尸梅山。章纶途径梅山,救活梅香,方知失宝之事,即令梅香先行回府报信,主仆二人随后到王府送宝。王永闻讯大喜,大开中门迎接章纶主仆,并以金银为谢。章纶固辞不受,随即进京赶考。皇帝亲送宝物到边关,遭红毛国主掳至番邦囚禁。宰相于谦召集群臣计议,拟请皇叔暂借皇位。时章纶已中二甲进士,居官在朝,独持异议。皇叔登基后即诏章纶下狱,命三司勘问,并设计四种酷刑逼供。何文渊劝说章纶上表谢罪以全性命,反被章纶痛斥。王永为报章纶还宝之恩,不惜冒险重金贿赂武士,故章纶受刑之后未遭伤损,被打入天牢。温州农民王梦竹家世代祭祀五通神,因王梦竹进京贩卖杨梅干亏蚀严重,五通神施法在京师遍洒瘟疫,唯食杨梅干可解,王遂获厚利。闻章纶被囚天牢,乃买通狱卒进牢探望。章在狱中备受虐待,赖王梦竹上下打点并请医调治,病体逐渐复原。帝囚红毛国十五载,国主扬言“日出西山,始许放归”。帝日夜祈祷,感动上苍,日落后又蒸腾而上。红毛国主见天象示警,不敢再留,将其放还。帝还朝复位,改元天顺,赐死于谦,释出章纶,拜礼部侍郎。章上表谢恩,具言王梦竹相救,钦赐“九曲黄龙伞”,并建生祠配飨[33]361-362。
从高腔艺人口述的剧情来看,《拜天顺》的主要情节构建在“章纶下狱”的史实之上,并作了一定艺术处理——虚化时代背景,杜撰王永、梅香等人物,增改部分情节,等等。该剧的部分情节和人物设定确有历史依据,如章纶狱中所受酷刑与清人王复礼《明尚书章纶公传》中的描述较为接近[34];何文渊于宣德年间做过温州知府,为政清廉,治绩突出,为温州人民所熟知②光绪《永嘉县志》卷四“建置志二”条云:“何公祠在城隍庙东,祀明知府何文渊,今废。”见(清)张宝琳修,王棻等撰:《永嘉县志》(一),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413页。;最有趣的是王梦竹实有其人,而且与章纶确有过来往,温州敬乡楼抄本《章恭毅集》中录有章纶写给王梦竹的三首七绝①题为《寄王梦竹先生》《次王梦竹二韵》。见(明)章纶:《章恭毅集》,温州市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卷六。。从诗中来考,二人系多年好友;但章诗提到王梦竹会弹琴、写作且善饮,与一个卖杨梅干的农民似无多大联系[33]363。至于王梦竹为何会成为剧中人(甚至是章纶的救命恩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只能视为剧作家的艺术虚构。但“王梦竹卖杨梅干”这一情节的确富有戏剧性,而且“杨梅干”这一物产反映了温州地方特色,故《拜天顺》的俗名又称《王梦竹卖杨梅干》[27]6,必然与该剧情有关。郭钟岳《东瓯百咏》中谈到“乡人艳说梅溪事,不为章纶道姓名”,意谓着同治年间高腔戏《拜天顺》已经不甚流行,其受欢迎程度远在《荆钗记》之下。
3. 《雷公报》
杨青《丙寅冬闽军过温记事竹枝词》其七十七云:“多多少少害家私,多少存亡尚未知。不见雷公报一阕,害人总是周排奇。”[35]这里提到了高腔戏《雷公报》及其剧中人物周白其。叶大兵注云:“周排奇,误,应为周白琪(其)。温州乱弹《雷公报》剧中一反面人物,作恶多端,连害数命,故民间有‘做人勿学周白琪’之谚。”[30]423-424《雷公报》,又名《周白其》,为瓯剧(温州乱弹)四本高腔剧目之一[27]103。民国十四年(1925)后,新老祥云高腔班解体,仅存的大玉麟班不久亦衰落[12]79。所幸瓯剧中还保留了《雷公报》等部分高腔大戏,使我们尚可窥见高腔的一斑。该剧主要情节为:
苏州周白其在员外金贤达家管账,因赌博亏损甚巨,被金赶出门外。后周白其在城隍庙偶遇流落街头的扬州人于良和其妇丁氏,周见丁氏貌美,即约他们到自己家中。正巧金员外来周家要账,周白其指使丁氏素农打扮,以送茶为名,诱惑贤达,又假言表妹新寡,遂将丁氏改嫁金贤达为妻。白其也因此重入金家司帐。贤达自娶丁氏,和原配陆氏时常吵闹,周白其杀死丫鬟秋香,诬陷贤达之子金云,县官不察,系金云于狱。周白其复用药酒毒死金贤达,加罪陆氏,后又设计赶走于良,霸占丁氏为妻。于良愤而诉官,按院苏冰文因未获直接证据,无法审明此案,最后周白其被雷劈死[27]103。
此剧原为纯粹的高腔戏,台上由一人领唱,众人伴唱,以锣鼓助节,无丝竹伴奏。发音高亢激越,风格古朴[27]104。《张棡日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十七”条云:“午刻同小竹到芸苓表弟处吃年酒,并与诸人选本日陶尖殿戏文。下午同芸苓至陶尖殿看戏。是日正本演《雷公报》,颇可娱目。”[36]这是目前已知文献中关于《雷公报》的最早记载,说明《雷公报》至迟于光绪间就已在民间流行。张棡虽在日记中提到了该剧,却没有说明其为哪个戏班所演;光绪间温州专唱高腔的班社已所剩无几,多数艺人加入“乱弹班”[2]4,则该剧只可能由当时的高腔班或乱弹班中的高腔艺人所唱。《张棡日记》中提到的乱弹班有“新益奇”“新润玉”“竹马歌”等②见《杜隐园观剧记》戏班名称索引。,沈沉云这三个班社均演过《雷公报》[27]103-104。但张棡第一次见到“新益奇”乱弹班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廿五日③《张棡日记》云:“有寿戏,班名新益奇,日间在茶场庙做,是夜即在宅内扮演。”见温州市图书馆编;张钧孙点校:《张棡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67页。,“新润玉”建于1923 年[37],均晚于光绪二十八年,故《雷公报》并非由这两个戏班首演;来自福建的“老祥云”高腔班在道、咸时已经存在,但它半年留在浙南一带,半年在福建演出[27]350,再加上沈沉搜集的“老祥云”剧目表中并无“雷公报”这一剧目④沈沉云,老祥云高腔班的剧目清单中没有《雷公报》《循环报》《报恩亭》《紫阳观》四本戏,瑞安的“阿柳班”“阿庆班”也从未演过这四本戏,给温州高腔剧目的流传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故也可以将其排除。再来考察“竹马歌”班的演出地点,据《林骏日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十八日”载:“更初,同震轩在陶尖殿看三星竹马歌合班演《偷诗》《武松闹快活林》诸出。”[38]张震轩也在同年同日的日记中写道:“灯下二鼓后,同小竹到陶尖庙看戏。是晚系竹马歌、新三星二班合演,极可娱目,四更后方归。”[39]林骏号“小竹”,是张棡的内兄,两人时常一同看戏。上述两则材料证明“竹马歌”班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就已在“陶尖殿”演出过,则《张棡日记》里提到的《雷公报》最有可能先由“竹马歌”乱弹班中的高腔艺人表演。
四、结 论
经笔者考证,温州高腔上承弋阳腔和早期温州高腔,下接四平腔和徽池雅调,由多个声腔、剧种共同影响形成。通过研究温州竹枝词中的戏曲史料,可以发现温州高腔的发展脉络:温州高腔形成于明末,在清乾隆时就已在温州地区流行,至迟于嘉庆年间达到大盛;道光以后温州高腔走向衰落,至同治是高腔最后的余晖,光绪时高腔的地位彻底被温州昆剧取代,民国十四年(1925)后几乎绝迹。温州竹枝词中涉及的高腔剧目共有3种,分别为《荆钗记》《拜天顺》《雷公报》。同治年间,高腔戏《荆钗记》的流行程度超过了《拜天顺》;光绪时温州高腔班所剩无几,《张棡日记》里提到的《雷公报》应为“竹马歌”乱弹班中的高腔艺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