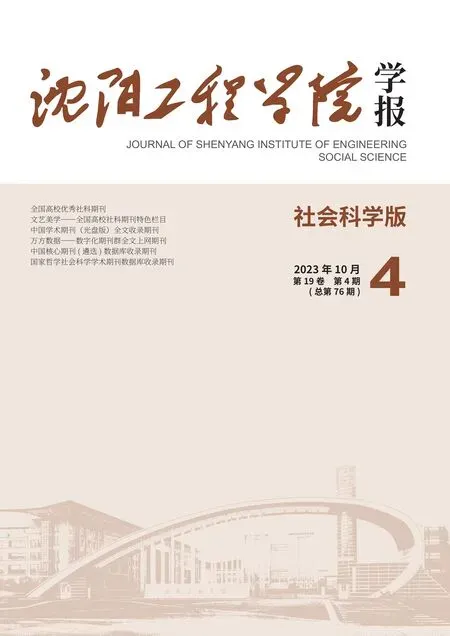庶民性·经验的均衡·当下意识的凸显
——吉剧对莎剧经典“在地化”改编重塑的几点反思
刘 爽,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a.教务处;b.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从国粹京剧,到昆剧、越剧、徽剧、川剧、婺剧、黄梅戏等,以中国地方戏曲演绎并“在地化”重塑莎剧经典俨然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景线。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方力量的介入,使得莎剧的中国地方戏曲改编重塑呈现出各显神通、多元并存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制的重要地方戏曲形态之一的吉剧也加入了莎剧经典改编的行列中来,先后将莎士比亚脍炙人口的两部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舞台,改编成了极具东北地方特色的轻喜剧,展现了新时代文化大发展中吉剧勇于自我突破、走国际化路线的新面貌和新倾向。
一、庶民性:吉剧与莎剧心灵呼应的隐秘通道
吉剧对莎剧经典改编与重塑的基础何在?可能的答案在于“庶民性”。所谓“庶民性”并非是一个先验的概念和范畴,它是作为改编主体的“我”经由人生经验和社会价值判断在情感和思想的体认中主观选择的结果。“庶民”通过“我”的选择而上升为价值主体,并在此基础上与莎剧经典建立联系,将莎剧经典从高雅的经典殿堂中请下来,还原为普通人的平等视角,进而展开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换言之,“庶民性”就是放弃莎剧精英化、学院化、体制化的原有立场,以平视经典的角度来重新对待、考量莎剧原著,从而找到独特的、属于自我的经典改编之路,探索出一种独特的思维与艺术呈现方式。在此意义上,“庶民性”构成吉剧与莎剧跨越时空、心灵呼应的隐秘通道,也是吉剧对莎剧经典进行改编与重塑的重要信心来源。
“庶民性”首先符合吉剧原初的内在创制特征。众所周知,二人转是吉剧的母体,作为地方剧种的吉剧是在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人转是典型的来自民间的劳动人民的艺术,它“唱的是庄稼调”“说的是庄稼话”[1],反映的是劳苦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及东北人的性格、思想情感、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在此基础上发展创制而来的吉剧与它的母体二人转一样具有“土生土长”性和“土色土香”的鲜明特征,弥漫着浓郁的民间气息,具体表现在插科打诨的艺术表现方式和对丑角的塑造机制、热烈奔放的艺术氛围和载歌载舞的狂欢化效果等诸多维度。这构成了吉剧最大的特色,也是其发展繁盛的基础,离开了这种民间性和地域风情,吉剧便成了“无根之树”和“无源之水”。
“庶民性”也是莎剧原初审美机制的重要语境。莎剧自诞生之初就来源于民间,带有强烈的民间戏剧的狂欢化色彩。在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看来,西方文学文化发展历程中来自民间的狂欢化情绪始终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潜藏的、间接的和难以捉摸的。但这种情形在莎剧诞生的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巨大的显性改变,“狂欢节式的世界感受”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深层基础”[2]28,它不仅“格外强烈”“甚至直接而清晰地表现在外在形式上”[2]317。可以说,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2]317。而受文艺复兴时期民间狂欢化整体语境氛围的制约,莎剧从人物到情节再到语言都显现出与严肃层面相对立的民间狂欢因素,物质的与肉体的基础形象、粗野的戏剧语言台词、民间饮宴的场面及丑角插科打诨式调侃的行为方式比比皆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极具更替与更新意义的“狂欢化激情”组成了“莎士比亚处世态度的基础”,这既能使他“看到发生在现实中的时代的伟大更替”,同时又能“理解这种更替的局限性”[2]319。
正是这种共同的“庶民性”来源构成了吉剧和莎剧跨越时空得以契合的重要基础。就戏剧的创制和演出来看,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更关注其艺术价值而忽视、甚至遗忘了其来源于民间的传统。而吉剧对莎剧的改编与艺术重塑恰恰在这方面处理得十分稳妥,通过“庶民性”这一心灵呼应的隐秘通道,吉剧恢复了莎剧的民间性,同时也解决了观众对于莎剧经典的接受问题,不仅成功地获得了市场,而且也保证了演出的艺术效果。在此层面,“庶民性”的立场将莎剧经典还原到了戏剧的原初,并恢复了其民间艺术本色,使吉剧和莎剧获得了平等对话的机会,同时也再次印证了“民间性”是当代经典戏剧改编的重要动力。
二、经验的均衡:从莎剧到吉剧的舞台改编实践反思
经典的改编是经验性的,而非观念性的,这就意味着经典改编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经典本身、改编主体和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彼此之间形成深刻的相互影响与塑造机制。没有经典本身,那么改编就无从谈起,这就意味着经典是改编保真性和可识别性的源泉;没有改编,历史悠远、跨越时空的经典就无法再现和复活,经典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跨地域、跨文化的艺术呈现;而没有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经典和改编便都失去了经验性意义。因此,成功的经典改编往往是经典本身所蕴含的普遍价值、改编主体的个人经验与观众接受的集体感受三者之间的碰撞、融合及相互转化,使之成为一个协调、交融的有机统一体,并最终实现这三者之间经验的均衡。
吉剧对莎剧经典的改编在处理经典原著的普遍价值方面采取了一条“中间道路”,既没有将莎剧经典“绝对化”和“客体化”,单纯再现经典原著的生命价值,也没有将莎剧经典“抽空化”和“个人化”,进而完全以个性化改编替代经典原著本身的价值经验,这种在“忠实原著”和“背离原著”之间徘徊的改编策略有得亦有失。
对于以中国地方戏剧演绎并重塑莎剧向来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尽管无法否认中国地方戏剧与莎剧存在不少重合和相通之处,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莎剧自身特定的语境、氛围、心态及情绪等因素,决定了二者之间的融合和借鉴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仅需要“一个一个的剧种和一部一部的莎剧反复进行实验,实事求是地评估得失,以极大的坚韧探索两者之间最大的匹配可能,寻求最强的亲和反应”[3],而且还要竭力避免产生形似而神不似的效果,即“取貌伤神”[4]。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优秀的经典改编首要的是要满足“原汁原味”,尽可能地回到经典原初的经验和立场中去,从原点出发,再打破对经典的陈陈相因的理解与阐释,进而实现对经典的再塑造,重现其本质上的核心内在活力。回到吉剧对莎剧的改编与重塑中来,可以看到从人物到故事主干情节,主要依据莎剧的样貌,表面看来是充分尊重经典的原貌,但仔细体味却发现两部改编剧对莎剧精髓的领略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待提升。莎剧《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原著主要围绕三条线索展开:一是没落骑士福斯塔夫被捉弄和冒险的经历,二是安·培琪的婚姻大事,三是由安·培琪的婚事引发的法国医生卡厄斯和威尔士牧师休·爱文斯之间的争执。莎士比亚通过以福斯塔夫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没落骑士阶级纵情声色、寡廉鲜耻的市井无赖行径,意在展现当时英国社会市民生活风俗,歌颂人文主义积极向上的乐观生活态度,其中的现实意义和身临其境的英国社会面貌成为了该剧最大的特色。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认为仅仅是该剧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与现实性”[5]。而吉剧在改编时,仅选取了该剧的第一条线索,即突出了福斯塔夫被戏弄的部分,在充分演绎了莎剧原著闹剧性质、突出原著滑稽效果的同时,却忽视了该剧的现实意蕴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层次内涵。而同样的问题似乎也出现在了改编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吉剧的改编在展现原著作为“年青人的剧本”[6]所呈现出来的富于青春活力的气息和男女主人公热烈而清纯的爱情方面相对细腻,对于男女主人公最终殉情场景的艺术传达与氛围烘托也显得壮烈震撼,但同样感受不到莎剧独有的人文主义气息和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思想主流的自由、平等观念及反抗斗争精神。换言之,吉剧轻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温莎的风流娘们儿》都缺少必要的莎剧原著的深层次精髓和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艺术再现。
吉剧对莎剧的这种多少带有“取貌伤神”式的改编和重塑也直接影响了其演出和观看效果。对于改编剧来说,观众是有着双重期待视野的,既希望欣赏到原著的艺术精华,又能感受到改编所带来的惊喜及艺术上的提升,而对于莎剧的改编更是如此。琳达·哈琴在谈及改编理论时曾以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认为人们或多或少可以接受将其改编为“一种受尊重的更高的艺术形式,比如歌剧或者芭蕾”,但不会接受将其改编为电影,如巴兹·鲁尔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现代激情篇》。[7]换言之,作为经典的莎剧在观众的心目中有着预定的接受和期待水准,这既受到改编媒介的影响,也受到改编水平的制约。唯有达到或高于观众的普遍期待视野,莎剧的改编才能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离,并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也才能与观众形成真正意义的互动与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吉剧对莎剧的改编似乎因为内在精髓的缺乏而导致接受效果出现了明显的错位现象,即熟悉吉剧的观众仅仅看到吉剧,而没有过多感受到这是由莎剧改编而来的;至于熟悉莎剧的观众更是觉得与以往经验中的莎剧大相径庭,甚至多少感觉有些偏离经典的意味。换言之,理想的吉剧对莎剧的改编应该不仅是吉剧,更要是莎剧,改编实践证明前者的艺术呈现驾轻就熟,而后者的艺术融合则显得略逊一筹、任重道远。
三、当下意识:吉剧与莎剧“在地化”融合的选择性凸显
如果说吉剧对莎剧的改编与重塑在经验的均衡方面有待提升和商榷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在当下意识的植入和时代精神的凸显方面则更为突出。改编和戏剧的演出都是当下的,这就决定了不能全部照搬原著,融入当下的意识和元素,挖掘作品与当下现实生活的交集以揭示生活的真理和时代的脉动,这样的改编及其剧本演出才具有时代的传承性和现实的多元性,也才能带给观众更多的理性思考,莎剧的改编更应如此,即“为了让莎士比亚戏剧在今天获得鲜活的生命,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人必须不拘泥于莎士比亚,将作品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然后再回到莎士比亚戏剧中去”[8]。
时代精神与意识形态主旋律的艺术呈现构成吉剧与莎剧当下意识融合的重要维度。莎剧被奉为“时代的灵魂”,犹如一面镜子映射着时代大潮中“人”与“人性”的变迁。在《温莎的风流娘们儿》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早期剧作诞生的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社会和谐安定,人的自觉意识提升,人文主义思想空前彰显。在此背景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之美”成为了早期莎剧的重要主题。吉剧自诞生之日起,便确立了“知守知创”的基本原则,强调不能过于守旧,必须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结合。因此,吉剧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对时代精神的展现,关注着时代变迁中人性的真善美。基于这一共同的认知理念和审美内在追求,吉剧对莎剧的改编充分继承了原著所展现的“和谐之美”思想,紧扣中国当下建设和谐社会的主旋律,通过“在地化”的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进行了完美的艺术诠释。改编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改原著福斯塔夫屡遭戏弄、自认倒霉的结局,而是强化了正面力量的胜利和福斯塔夫痛改前非的决心和行动,从而在欢快的音乐和互谅互让的美好气氛中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结局。而改编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为观众呈现出了独特的“双团圆”结局,一方面尊重原著,世代仇恨的两个家族在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力量下握手言和,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增加了莎剧原著没有的一个重要场景——幕间戏《教堂婚礼》,以此暗示男女主人公在现实中修成正果,“弥补了莎士比亚原著的一个小小的遗憾”[9],实现了中国观众心目中对纯美爱情的希冀,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符合莎剧本身“悲剧阶段——过渡阶段——喜剧阶段”的“圆形结构”[10]。
改编不是回溯而是更新,缩短原著与当代观众之间的距离是改编的重要意图之一,这决定了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大众时尚艺术的直接引入成为了吉剧与莎剧当下意识融合的另一重要方式。当下的戏剧观众呈现年轻化的趋向,而无论是作为地方戏剧形式的吉剧,还是作为西方经典的莎剧,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年轻观众的审美价值观存在一定的隔阂,如果墨守成规、一味地遵照原著必然导致年轻观众难以认同,在此情形下,吉剧改编融入当下时尚的新元素和内涵,如歌曲《小苹果》《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广场舞等艺术形式,不仅可以提升观众的带入感,而且可以凸显国家文化大背景下观众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意识。毕竟包括吉剧改编剧在内的戏剧演出不是单向的输出,表演不能触及观众的当下感受和经验,不能引起观众对当下生活现实的共鸣,再好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缺乏灵魂的。
四、结论
吉剧创制之初,老一辈工作者便提出吉剧在剧目题材上既要二人转和梅兰芳,也要关汉卿和莎士比亚[11]。新时代由吉林省艺术研究院提出的吉剧发展战略构想中又再次提出吉剧在题材选择上要有“横空出世般的重大突破”,要利用“全球的视角和现代思维”[12]。很明显,吉剧对莎剧经典的改编和重塑是契合吉剧原初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总方针和全球化新趋势下国际发展路径的。但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地方戏剧与莎剧经典的深度融合,既展现出中国地方戏曲的艺术魅力和中国当下的时代精神,又凸显出经典的永恒价值、超凡的再生能力和本质的“创作美学”[13]特质,而不是单纯地呈现视觉幻象是一个长久的、值得深入思考的大问题。莎剧经典的新创化,若能如吉剧改编重塑般充分借鉴“庶民性”思路,并处理好经典本身、改编主体和观众三者之间经验的均衡,辅以当下精神的凸显,不仅有助于莎剧经典重回当代舞台的现实世界和经验世界,重构经典与当下生活的紧密联系,而且有助于中国地方剧种突破固有思维模式和表现内容,展现更为深广的能动性,进而走出一条从传统向现代、从封闭向敞开的质的转变之路。
——重返“五四”之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