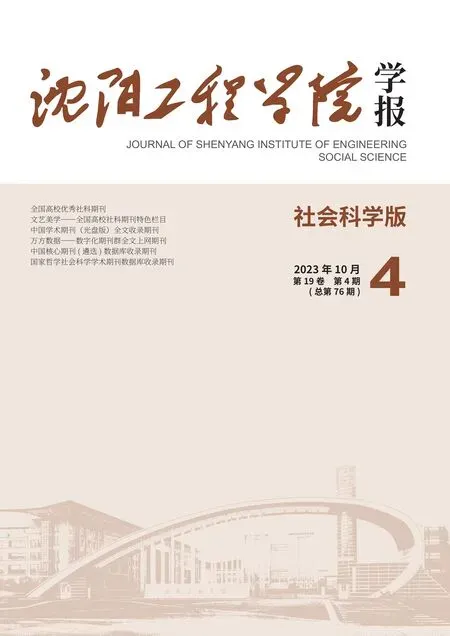朱光潜:艺术与自然关系之美学思想再探
王 晨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美之自然感是艺术创作的终极追寻,它代表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自然”与“艺术”,并不是完全异质的两个概念,艺术美不单是人造美、非自然的美,在其内部仍有自然性成分的存在。艺术的再创造性与自然性二者看似对立,实则有机统一,最终实现了和谐之美的关系,赋予审美对象生命力与张力的可能。
一、艺术形象的创造——主观之“意”与自然之“象”的结合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受到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Croce)的直接影响,他批判继承了克罗齐“美即直觉”“艺术即直觉”的观点,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对艺术形象的生成做了新的界定。
克罗齐称,艺术活动就是直觉的过程。内容即“质料”,内容即为未经审美直觉的作用而生成了不能为人所感知的情感印象,而形式则指心灵的活动或直觉的表现。克罗齐认为,情感在未经直觉之前,并没有特定的属性特征,而只有通过有机的心灵和直觉活动融汇情感印象后,情感才能转变为直觉。因此,他认为直觉是对“情感”的认识,而心灵活动则是所谓“情感”的质料,它并不是一种“自然”,而是先验的存在。在朱光潜看来,克罗齐之意图,是构建以“直觉”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心里直觉到一个对象,就是创造,就是表现。这形象本身就是艺术作品”[1]158。克罗齐直接将艺术活动与直觉的审美经验等同起来,不考虑心灵活动以外的任何东西。朱光潜认为,“自然”这一概念并不是克罗齐所想的粗陋而一无是处的简单材料,而是具有一定艺术的潜能材料,他立足于中国传统美学“感物”的传统,将克罗齐美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进行转化。
朱光潜表明,艺术创造要求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敏感而丰富的体验和审查,需要审美主体于客体关照中产生审美直觉,而“审美直觉”的概念,则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的美学范畴的思考。钟嵘《诗品》中对“气”有所概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2]这里的“气”,从创作主体的角度理解,可以阐释为人的气节,即主体的个性情感。诗歌艺术由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出发,对客观自然的景物产生想象,并生发感悟,从而将主观情感寄于自然万物之中,使其拥有了感动人心的力量。朱光潜将由气到物的神思关照过程与直觉说相结合,他认为,对于自然,凝神关照的“意象”就是艺术形象,它是主客观结合的结果,而生成意象的过程,也依赖于对自然物的“直觉”。在朱光潜的美学体系之中,“直觉”是一个在自然静观的基础上,始终伴随着主体情感的体验与自由伸张的过程,是主观之“意”投射于客观之“象”的过程,也就是朱光潜所说之“移情”。
“移情”是审美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创造的审美过程,而自然物正是这一过程的物质载体。审美者身处自然环境之中,通过初步的“感物”后,与自然物产生审美互动和强烈的共鸣,将自然物带入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助发了审美主体对于客观自然对象的美的体验与享受,进而使得审美主体“移情”于客观自然”从而审美主体将审美活动转向艺术创作,将审美快感转化为创作的欲望,对自然物进行再创造,进而将自然材料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使艺术家之“意”与客观自然之“象”相结合,构成“意象”,形成了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艺术家在完成创作的过程中,也就坐拥“得江山之助”的水到渠成之快感。
自然空间为审美关系的产生提供场域,“直觉”成为“意象”,少不了自然物象的参与。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形象的构成有其自然因素,艺术的自然性不言而喻。但艺术虽来源于自然,却已经“不复是生糙的自然”[3]95,这里“自然”的概念,脱离了粗糙机械性的物质实体,是融入了审美者主观情感内蕴的自觉。不同自然物的美的潜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经艺术家创构后,所实现后的美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同是苍松,由于艺术家移入的情感不同,给予其美的潜能不同,所创作出的诗的气质也会有所不同,“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是李白笔下挺拔、刚劲、笔直而高耸的刚性美;相对的,李商隐“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体现的则是纤细、柔情、孤单而独立的遗世美。自然的美感,通过艺术家的想象,运用形象思维和审美情感来提取艺术、塑造艺术美。实际上,艺术的创造不仅依赖于审美主体的情感投射,艺术形象也不仅指经过直觉的心理情感,更是立足于艺术家的感性实践,通过感物、移情后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结合,这其中少不了客观自然界的参与,这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情”与“景”统一相通。艺术之“景”来之于自然,是自然提供的,艺术之“美”来源于形象,是由寄予了艺术家情感的形象所引发的美感,情景统一,才能形成意象。
这意味着,艺术美所描绘的自然,实际上就是要求艺术中融入情感,具有栩栩如生“媚”态,这就包含着“美”的生命力亦或是“奇”的张力。在艺术审美过程中,经过“移情”,自然物质寄予人之情感,从而具有了艺术美感,最终呈现出不同于物质材料拓本的巧夺天工之美。
二、艺术情感的表达——自然生命意识的再现
艺术所展现的是个性的自然,要求张扬审美主体的情感,经由艺术家创造性的联想活动,而将其对物的直觉体验转化为审美主体与客体互动的知觉体验,进而把自然物美的潜能发挥出来。这是主观意志作用于客观审美对象上的表现,意在表现出鲜活生动的动态美感。
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在其著作《镜与灯》中明确指出:“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4]可见,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时,往往从自身生命活动出发,展现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感悟,对人的生命意义投去关切与探寻,以挖掘人性中自发自然的生命力和生命关怀。朱光潜提出“艺术人生化”的美学愿景,他认为:“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3]147能否由自身生活出发,面向自然生命观物移情,对生命本体意识进行关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审美价值,相较于一般审美者而言,作家、艺术家表现出更为强烈而深刻的生命意识,在感性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加让人震撼心灵的作品,能够振奋人们的生命活力。
审美艺术家有着更为活跃和敏锐的情感,这构成了异于常人的生命质素,推动了更为强烈的情感表达。审美主体必须要达到超然物外的境地,实现人的心灵与宇宙万物的同一,将自我生命融入天地万物,是追求在艺术境界中达到超乎于功利善恶的高度,以“神性”的审美关怀观照人生的节奏,探寻自我生命的意义、人性的本真和宇宙人间的常态。朱光潜认为,艺术欣赏和创作必须保持一定的“趣味”,而趣味正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艺术家只有在与自然之互动中不断丰富自己的审美情趣,保持高尚的艺术“趣味”,才可能在艺术创作中投入艺术家的真切情感,站在高于常人的视角去俯瞰人生,回味人生,探寻自我和剖析自我,才能使艺术作品有着感染人心的力量。
艺术情感要求“真”与“切”,需是自然自发的生命意识的展现。文学艺术作品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女性作家张爱玲善用意象,将人之情感投射于物象中,立足于女性视角,展现出女性渴望回归于生命本真的原欲和其自然的生命关怀,使文字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情感力量,由女性对于爱的信仰,导向人类对自我情感与生命的探寻和揭示,散发着狂舞生命动力的无限魅力;“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用富有地域特色的东北语言,“以一种追溯式的书写,寻找失望中的希望”[5],书写小人物于大浪潮中的悲戚命运,于不可逆转的命运中坚守着崇高信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艺术始终显现出灿烂的生命力,于不断地创作中保持着新鲜感。“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语境和文学结构的变化,文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艺术形式的突破,写作空间的开拓和创作群体的转型。”[6]艺术家能够站在人类的生存命运面前,以人性、人的精神建构去审视人的生存与生命,在壮美文字中悸动着生命的欢乐与苦痛,对人类的命运和生存不断提问和剖析,更显生命之道的广度与深度,塑造着生命的崇高感。
这是人的生命扎根、不断延伸的动力所在,也是艺术散发生命意识,展现自然活力,不断构建生命话语的独特之美。宇宙万物处在生生不息、流转不己的生命运动之中。艺术作为生命情趣的外化,也处于一种生命动态世界中,想观有无震慑心魄的魅力,还需看其有无自然生命活力的内蕴。
三、艺术境界的建构——“物我同一”之审美关系
在《说文解字》中有关于自然的定义:自,始也,是万物的本初;“然”则兼有“是”和“这样”的意思。由此可见“自然”即为“自是”,事物回归于本源,显现出自然而然的态势。自然而然是自由的最高象征,艺术需要达到自由、自在、自觉的状态。关于如何在创作中保持此种自由,朱光潜认为,“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乐天知足,将人本身置于自然之中,实现默契相安的和谐。”[7]人与自然处于共生的和谐关系之中,这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意境一脉相承,在艺术欣赏和创作时,主体的人将置于自在自为的自然环境之中,体悟自然之滋味,实现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物我同一的审美关系。
“物我同一”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美学中道家思想之精髓相呼应。朱光潜认为,审美者与其审美对象会进行一种情感交流,即“我”排除掉一切主观欲望与意念,对于“物”作纯粹的直观时,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感,而“我”又会将这种情感移至对象,同时又将对象的姿态吸收于我,于是“我”的生命便和物的生命在这种情感的往复交流中合二为一了。他所提出的“心与物的融合”,实际上是中国古典道家美学中“情景交融”和“天人合一”哲学的现代演绎。
“道”的学问贯穿于老庄哲学之中,庄子在老子论“道”的基础上提出,天地产生于“道”,天地间的万物自然也是“道”创化而成的。庄子主张精神的完全独立与绝对自由,强调个体与宇宙自然相契合,从而能超越人生,物我相忘。基于此,庄子意图建构自然万物和谐关系,“道”之所在使得世界存在着一种万物有其责的和谐秩序,要求人能够身处自然之境中,超脱形的束缚,无拘无束地体会生命的活力,超越物质的自然而进入生命自由的境界。若想参透世间法则,同天地并行,就要真正融于天地万物之间,顺应道之变化,通过“心斋”“坐忘”与“涤除玄鉴”,进入“道”之境界中,感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超然之境。
朱光潜深受庄子的影响,提出建构“物我同一”境界。这实际上就与老庄美学相承,是一种情景交融、心灵无限自由的审美境界,而此境界正是自然与人的相融,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在凝神关照时,我们心中除开所关照的对象,别无所有,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1]18朱光潜认为,移情的发生成为了物我同一的媒介,使“我”之感情投射到了“物”上,形成了物我两相忘的审美艺术境界。以观赏古松为例,朱光潜提出,我们观赏古松时,会把心中所敬仰的气概与风骨移注到古松上,古松就好像成为了一位智者高人。同时,“我”由于吸收了古松之情趣,就宛如成为了一棵峻拔之松。朱光潜把这种现象称为“物我同一”,移情使得“我”的情感投射到了物之上,而我与物产生了审美关系,“物”与“我”,自然天地与主体的人之“隔”被打破,真正实现了“同一”的和谐状态,使得审美主体有着寄于物而又超然于物外的审美感受,艺术的审美境界由此产生。
审美主客体建构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形成包孕万象的、自然而然的自然美感。也就是说,置于艺术境界建构之中,艺术之美能够拥有自然自为的超然特性。“生命现象作为大自然最伟大的创造,最能体现出大自然的审美匠心。”[8]陈望衡先生所言“匠心”,是一切存在物对生命的包孕和显现。艺术作为最高的美的显现,于“物我合一”的境界中生成,也就更应当有此“匠心”,包蕴着对物之生命特性的考察和定位,能够挖掘物自生成、物自显象的自然美。宛如山中行者,浸入自然而超越自然,进入“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超然境界,将人放置在天地万物之中,物物而不物于物,不受限于自然物本身,追求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于是更有了超脱象外、言已尽而意无穷的美感,这是艺术自然性之最高追求,体现着自然与创造、物与我之和谐的圆融之美。
四、结语
艺术美不仅是人化的自然美、单强调艺术异化于朴素自然的庄严感,艺术美更是要深刻认识到艺术美的产生依托于自然物象,来源于自然审美经验,植根于古典美学的传统,建构物我同一的审美关系,追求着自然美的最高理想。这要求审美者在审美活动中不可脱离自然性而单论艺术美,唯艺术而艺术,必须回归自然之物象,深刻感受物我同一之境界,吸收和保留自然物之特性。同时,发挥自然之艺术潜能,结合主观性审美创造力,保留和渲染艺术美中的自然感和纯粹美,最终得以以美的角度,再现自然与人、自然生活对生命力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