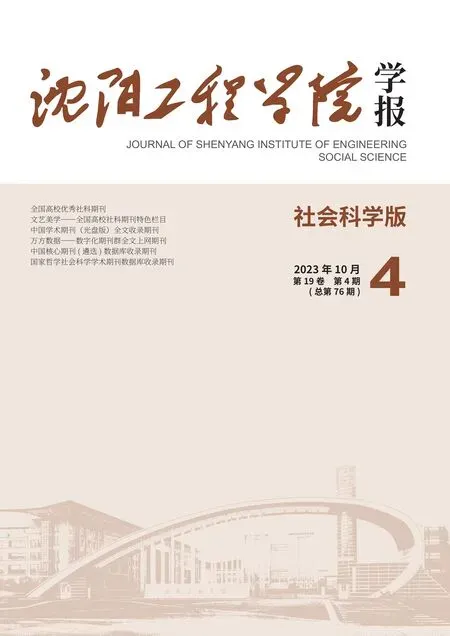镜像与拼贴:贾樟柯电影的异质空间表达
侯自然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人们有时以为能在时间中认识自己,然而人们认识的只是在安稳的存在所处的空间中的一系列定格,这个存在不愿意流逝,当他出发寻找逝去的时光时,他想要在这段过去中‘悬置’时间的飞逝。空间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1]这段话出自于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诚如其所言,空间不仅作为纳放物体的容器,亦是承载人类意识、情感、历史的地方。自20 世纪中后期起,后现代主义思潮迭兴,“空间转向”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福柯、戴维·哈维、亨利·列斐伏尔等学者从空间角度进行研究,其中福柯提出“异质空间”,旨在关注对常规现实产生颠覆作用的另类空间,其理论为艺术创作者的空间表达提供了新的视野。在电影叙事中,视觉化的空间形象直接影响影像意义的传递。贾樟柯以其独特的空间美学风格和创新的叙事手法成为“第六代”导演中的重要人物,其作品的别致之处在于:以影像空间中的个体境遇指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鉴于此,引入福柯所提的“异质空间”相关理论对贾樟柯的电影进行解读,可用以扩展我们对于电影空间的想象。
一、镜像空间:超现实元素的影像实践
异质空间也被译作“异托邦”和“差异地点”。“可能在每一文化、文明中,也存在着另一种真实空间——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形成社会的真实基础——它们是那些对立基地(counter-sites),是一种有效制定的虚构地点”,通过对立基地与真实基地相互间的再现、对立与颠倒,进而形成一些游离于所有场所外的空间类型,其在现实中的位置仍可被清晰指出。[2]21据福柯描述,异质空间有两个各为极端的重要特征:一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示真实空间更为虚幻,二是创造一个完美、拘谨、细致的真实空间,以彰显空间是如何混乱、污秽和病态。异质空间以新奇的、差异的、镜像的形象而存在,是对现实既定常规的颠覆与瓦解。换言之,较之于异质空间的显在,福柯更希望阐释的是外部空间中潜在的危机。
在双主角双线叙事的影片《三峡好人》中,韩三明伫立在天台凝视三峡景色,UFO 忽然划过天际,跟随着UFO 的飞行路线,女主角沈红入画继而开启影片的另一篇故事。再者,在沈红晒洗衣服的日常场景中,远处的纪念碑如火箭一般腾空升起。片末,韩三明望见烂尾楼上走钢索的人若有所思。在贾樟柯纪实感十足的影片氛围中,这些短暂的另类时刻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超现实元素在《三峡好人》中的运用,贾樟柯在采访中解释道:“一座原本完整的城市就变成随处可见的拆迁之后的废墟,非常超现实,很像遭遇外星人文明破坏之后的摧毁”,它等同于“现实里面存在的超现实氛围的有机组成部分”[3]。这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取材与书写方式,意味着人类考察现实世界角度的改变。
与《三峡好人》相通,影片《江湖儿女》中再度出现超现实元素——UFO。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女主角巧巧直言曾见过UFO,这一情节与《三峡好人》中沈红的遭遇串联相依。当巧巧与爱人感情破裂,不知该去往何处而深陷困境时,UFO 的出现映衬出巧巧心中的孤苦无依。在这种特定的“异质空间”中的象征性行为拥有某种情感的召唤结构和功能,可以唤起人们的神圣感、神秘感、庄严感、膜拜感等各种内在情感体验,并进一步对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4]。于片中人物而言,UFO 是神秘又亲切的存在,它佐证着人物对宇宙万物所拥有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如福柯所言:“这些差异地点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我再度地开始凝视我自己,并且在我所在之处重构自我。”[2]22这面镜子所对照的即是现代社会中发人深思的部分,“当认识主体面对一个由异质空间所构成的镜像时,他者的异质性就会映衬出主体所处的秩序的存在,并有可能推动文本对自身身处并习以为常的秩序进行置疑和颠覆。”[5]123它就像一面布满神圣光辉的镜子,让主角借由这一镜像空间链接现实、照见自身,在超然的秩序中完成对自我的确认。于观众而言,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元素内嵌于日常场景中,超现实与纪实性杂糅交织形成了一种视觉上的新感性。值得注意的是,与观众新奇的视觉体验相比较,片中人物似乎并未对超现实元素的骤然出现有所讶异。之所以如此,或是因为在创作者所建构的空间中,神意、魔幻与现实肌理相当,超现实符号只是对现实中异质性的复沓,因而它们都重新成为符合现实逻辑的自然存在。
概而言之,福柯的观点揭示出异质空间存在于真实空间中,超越主流而显现出边缘与差异性。当影像中现实与超现实的边界消弭,魔幻时刻的光晕即从其中浮现。在这些差异与断裂的缝隙之间,充满超现实想象的异质空间犹如一面镜子对真实空间进行补偿,更照映出现实中的无言与悲伤。贾樟柯平静地向观众展现出人物所处的时代洪流,以独特的空间手法探索人类与外部空间、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进而揭示社会的复杂与不确定性。
二、拼贴复现:多文本的异质性建构
《三峡好人》中,韩三明从山西寻妻至三峡待拆的居民楼,楼中小孩正忘我地唱着《老鼠爱大米》;在沈红寻找丈夫的轮渡上,小孩再度现身唱起《两只蝴蝶》;《江湖儿女》中,巧巧自山西独乘轮渡到三峡寻多年未见的斌斌,途径广场一角,巧遇街头艺人唱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歌词仿佛正预示或印证了主人公多舛的寻亲之途。如此刻意而为之的“偶然”,是导演对生活的揣摩与刻画。在其影片中,常可见卡拉OK、歌舞厅、街头表演等娱乐空间,也常觅得音乐随主人公的境遇变化而变奏叙事,于人物而言,直白的歌词无疑是对心中迷惘的直诉。
“偶然”不仅发生在人物与空间的联系上,《江湖儿女》巧巧寻斌斌与《三峡好人》沈红远赴异乡寻亲的场景也几乎如出一辙。《江湖儿女》在人物设计、拍摄场景、故事情节上可寻见贾樟柯过往作品的多处印记。人物设计上,演员班底中有导演以往作品的角色身影。更富巧思的是,《江湖儿女》延用《任逍遥》等作品中的角色名“巧巧”与“斌斌”,其人物造型也多有《任逍遥》《三峡好人》临摹重现。场景方面,《江湖儿女》集结了《任逍遥》《三峡好人》中山西和三峡等地理景观,斌斌在舞厅掉枪的情节也不禁让观众回想起《任逍遥》中的画面。“随着符码被故事主人公征用,成为文本时空的一部分”[6],时空之再联结也意味着角色与观众的个体经验被重构。
异质空间能够在其内外并置两种或多种相互矛盾的秩序和法则,并且打破其所处的系统的均质性和同一性[4]123。正是在福柯的定义之上,贾樟柯的作品集合可被视为一个饱含人类社会进程意义的重要隐喻,他将不同文本、人物、故事拼贴合成,在多个文本“偶然”的重复中打破单向叙事,进而在个人作品集中串联起多层叙事结构。从表达空间的方式看,后现代主义最常使用的是虚构、拼贴和复制的手段,呈现出的则是一个分裂、短暂和多元的世界[7]。观众置身于一个充满变化与不确定的世界中,而这种“不确定性”即是时代变化的表征所在。概而言之,在贾樟柯的影像世界中,多文本重现的瞬间所黏合的不仅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他将贯穿性的角色放置在时代之流并拼合起一幅变迁长图,是尝试引领观众以一种象征化的视角认识影像与现实。这是一种更为纵深的叙事逻辑,一种往复的、交迭的、去主体性的运作逻辑,即命运飘摇的巧巧与斌斌代表的是时代的缩影。
三、异时之地:时间的累积与压缩
对于空间的择取与塑造,贾樟柯曾描述:“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的空间和现在的空间往往是叠加的。”[8]111他对于异质空间的构思不仅是将历史的瞬间进行复现与拼贴,若围绕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场所说开去,会发现他在空间版图上早已有宏大规划与精妙设计。
拆迁与废墟常散见其中,无论是《三峡好人》中将被浸没的城市,还是《江湖儿女》中将被远迁的矿厂,在由扬起的飞尘与乱置的砖块构成的废旧图景中,承载着人类数年生活记忆的场所正在逐渐消逝。一面是被遗弃的空楼废墟,一面是布满想象的迁入地,由拆迁与重建所形成的新旧对立叠加在同一空间,它们分别指向过去与未来。差异地点与差异时间是在一个相对复杂的方式下被结构与分配的[2]25。差异地点通常与时间的片断性相关——这也就是说它们对所谓的(为对称之故)差异时间(heterochronies)开放[2]25。由时间与空间组合所得的,一类是“积累时间的异质空间”,如博物馆与图书馆;另一类是绝对瞬时的“狂欢的异质空间”,如游乐场与度假村。基于此,我们可将废墟视为对线性时间的破坏,在某种意义上它等同于对累积时间的永恒性破除,是追求现代化进程而弃置历史的标识。而当《江湖儿女》的巧巧来到三峡,昔日沈红在《三峡好人》中走过的废墟已被一道喧哗的观光线取代。在此,主角和观众好似回到历史位置,由复现所唤起的记忆为当前文本填充起更深长的意蕴。
在福柯看来:“差异地点可在一个单独地点中并列数个彼此矛盾的空间与基地。”[2]25他将剧院与电影院作为重要范例,在电影院中,人们凭借银幕可观看投射在二维平面上的三维空间,联系起多个彼此无关的地点。在贾樟柯的作品中,舞台、影院及电视的观看空间频繁出现。在《站台》中,舞台上演着《火车向着韶山跑》;《任逍遥》中,斌斌热衷于看《西游记》;《江湖儿女》中,斌斌和兄弟们齐齐观看《英雄好汉》。电影院等空间作为情感与欲望的释放地,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同时,观看空间蕴含着观看文本中被压缩的时间,令叙事时空得以无限延伸。而“压缩”也可能存在着另一种形式,在《世界》中,世界公园将国际景点胜地压缩齐集于此以供人观览,在这狂欢的景观背后,蕴含着空间被创造和复制的可能,成为偶然与连续、现实与虚幻的另一种构成方式。这一空间框架亦加剧了人物与环境间的割裂程度,促使人物与空间的关系更显疏离。
如果说废墟是对绵延时间的切割,那么影院和公园则是对时间的累积与挽留。在其中,空间不仅映现出对于时间不同的书写范式,亦观照人物内心与外部空间的关系。除却公园、影院、废墟,在其电影中常出现的矿厂、公交车、歌厅、桌球室、歌舞厅等空间也同样超越物质层面,涵盖着背后不断流变的人际关系与时代语境。
四、流向何处:“故乡”与“江湖”的影像刻画
自1995 年贾樟柯拍摄第一部作品《小山回家》,他便将镜头聚焦于自己的家乡山西,在其早期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及此后的导演生涯中,“故乡”一直是他创作的重要场域。如《世界》讲述了景区舞蹈员赵小桃与保安成太生的情感故事,描绘北京外来务工者的生存状况。《三峡好人》中,一边是寻亲的异乡人沈红和韩三明,一边是迁往外地的当地居民。城中倒塌的砖瓦、多处标记的水位线、时而响起的号召广播,“寻找”与“消逝”成为片中动态的母题。《江湖儿女》取景自大同、三峡、新疆,构建出“故乡”“江湖”“远方”,“巧妙展现流散者漂泊异质空间的边缘美学”[9]。
将贾樟柯近20 余年拍的影片相串联,可以看出他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变化和压缩的“江湖”,并将个体投放其中令其产生精神困惑。这种困惑在《江湖儿女》里得到集中表达,角色操持着山西话,穿着流行衣裳穿梭在棋牌室、歌舞厅、煤厂等空间,他们以“江湖”规则维持生态,直至忽觉时代已不复从前。主角斌斌原本是人人敬仰的“头子”,刑满释放后离乡寻求发展,后因重病返乡疗养,片末再度黯然离开。斌斌几番“出走”与“归来”皆折射出在现代化进程与变迁下,人与故土间的情感连结几近断裂离析,无法适应的人心中充斥着剧烈的疏离感。对于片末斌斌的离场,或许导演早已埋下伏笔。当巧巧在三峡找到斌斌并劝他一同回乡时,斌斌说道:“我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异乡,斌斌已找不到自己在“江湖”的定位。在贾樟柯的影片里,“江湖”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那条江流淌了几千年,那么多的人来人往,应该有很强的江湖感在里面。直到今天谁又不是生活在江湖里面,……你要遵守规则,你要打拼,你要在险恶的生活里生存下去。”[8]194在时代世事的洗练下,“江湖”境地在变,飘摇于“江湖”中的个体命运也在改变。
审美实践与文化实践对于变化着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特别敏感,正因为它们必须根据人类体验的流动来建构空间的表达方式和人工制品。它们始终是“存在”与“形式”之间的中间人[10]。在贾樟柯的创作中,“游荡”与“找寻”是其作品中常见的人物状态。无论是《三峡好人》里的韩三明和沈红,抑或是《江湖儿女》里的巧巧,游走状态的主人公彷佛一叶在时间长河漂泊的小舟,“是一个浮游的空间片段,是一个没有地点的地方,以其自身存在,自我封闭,同时又被赋予大海的无限性,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个航向到另一个航向。”[2]28其中主角同轮渡、火车、公共汽车共同联结着故乡与异乡,见证着流动的风景。在《小武》《任逍遥》等作品中,“游荡者”的个人意识与流动空间的相互碰撞同样折射出复杂的社会动态。他们寻找、观望、离开,眼里饱含着所到之处的变化与历史的变迁,这一段流动之旅是“一种对空间幻觉效应的体验”[11]110,亦是属于江湖英雄的救赎与实践。他们作为“一个蕴涵着丰富意义的现代性时空的观察者、体验者和抵抗现代性的英雄”,其形象不仅为过去的时代提供说明,也为有着相似历史经验和生产经验的时代建立起富有启发的参照系[11]119。
从《三峡好人》中的沈红到《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历经十余年的“找寻”光阴,昔日蓄水迁移的奉节已永没水中,“故乡”与“江湖”的定义亦不断被改写。“人类基地与生活空间的问题,不仅是了解这个世界是否有足够空间容纳的问题……也是在一个既定的情境中,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与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我们的世代相袭是空间带给我们的,是基地间的不同关系形成的世代相袭。”[2]19诚然,无论是观影者,还是影像中的巧巧与斌斌,人们时刻置于空间中并受其影响。贾樟柯所构建的异质空间意在刻画处于变迁中的时代图景,以及漂泊其中的社会个体,他通过多文本拼贴而成的影像宇宙亦可作为打开现实的一个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