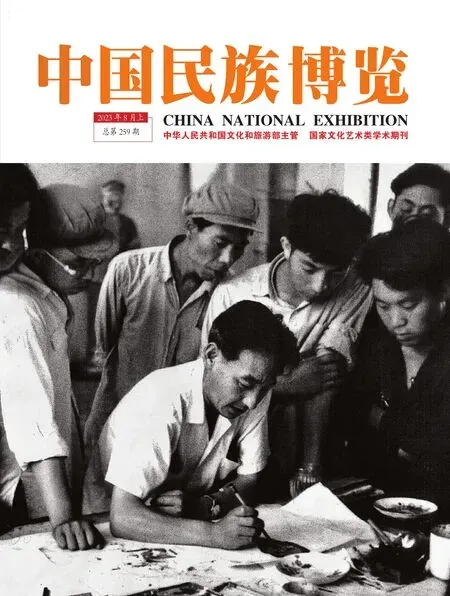傈僳族配饰变迁中的艺术与叙事
——基于维西县叶枝镇案例的分析
吴 龙
(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傈僳族作为一个历史上常年游牧和迁徙的民族,在定居滇西北前进行了大量的走动迁移,因此他们身上的配饰既是他们的标识,也是帮助他们狩猎耕种的工具。配饰的美承载着祖先的传说记忆,配饰的实用蕴含着傈僳族祖祖辈辈的勤劳与智慧。傈僳族配饰中的民族符号,饱含着傈僳族在过往千年中的民族记忆和民族情感,研究及阐释这些符号,对于学习民族艺术的后来人而言弥足珍贵。傈僳族早在公元8 世纪前后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民族群体,目前,其大部分人口聚居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滇西北山区。现今傈僳族服饰分布十分广泛,一直跟随傈僳族的迁徙而变化,其配饰与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息息相关。不同地区的傈僳族服装会呈现不一样的文化特征,例如德宏傈僳族的“五彩军功衣”就是与少数民族戍边文化有关。维西叶枝一带的傈僳族是云南省各地州傈僳族迁徙的祖先之一,相对而言,现保留在叶枝一带的傈僳族配饰较具本真性。叶枝镇的傈僳族配饰从头到脚可以分为:头饰、颈饰、腰饰。当地傈僳族节日庆典需要跳“阿尺木刮舞”(羊的舞蹈)的时候,会穿上自己民族的盛装。本文尝试通过配饰符号与傈僳族传说故事相结合,以一种非线性,散点叙事的方式来分析维西傈僳族配饰中蕴含的艺术特色与民族故事。
一、溯源:以配饰形成的族群记忆与区分
自然生态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少数民族艺术是属于生活的艺术,是人与世界的结合物。傈僳族配饰作为非文字的文本,他的艺术符号中寄存着傈僳族先长们为谋求美好的生活实践,以及祖先神话的精髓。最早的傈僳族艺术形象诞生在先祖与自然相习的山野生活之中。
(一)银月与艳阳:繁衍生息之基
在维西傈僳族女子的三角帽“呙亨”上,钉上三块银制圆片象征日月的“普扁”,帽檐会缀上一圈海贝“矣玛”和彩色小珠串“来俄马省”用以象征星星。傈僳族男子帽子“壳扒腊哄”(羊毡帽)上,有手巧的傈僳族妇女会根据自身审美在帽子前后左右四处缝上同样象征日月的“阿木数吕”(麦草编织)的装饰圆盘。金色麦编在黑色“壳扒腊哄”上如风和日暖,开朗外放,银色圆盘在蓝色“呙亨”上如月色静谧,柔和内敛,在男女头戴上相得益彰。当傈僳族先祖开始认真地观察太阳运行时,他们实际上是迈出了认识时空世界的第一步。傈僳族的传说中是这样解释这一天象的,“天上最早有九个太阳和七个月亮。白天,九个太阳挂在天上,把一切的水都晒干了,晚上,七个月亮都出来了,把大地照得冷冰冰的,人们晒的晒死,冻的冻死。于是为了生存请来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用一个大弓弩将八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射了下来,虽然解除了旱灾和寒灾,但是却吓到了剩下的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都不出来了,天地之间一片黑暗。人们只好又请智者出山,智者先让山林中的百鸟歌唱,太阳月亮还是不出。最后智者又让公鸡叫太阳和月亮出山,公鸡哦哦哦叫了三遍,太阳月亮才出来,后来天地间才有正常开始。”维西傈僳族对太阳月亮的看法是即崇拜又忌惮的,将太阳、月亮的形成视作符号,人类的生存繁衍需要太阳月亮。故日月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傈僳族男女的头戴上,以帽为天,悬挂日月,将其时时带在身上,记在心里,配饰成为人与世界关系考量的载体。

图1 维西叶枝镇男子服饰

图2 维西叶枝镇女子服饰
(二)羊:配饰之基
羊作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是远古人类生活、生产乃至生存必不可少的资源之一。在叶枝镇傈僳族的男性配饰系统中,羊并不是作为显眼的符号所出现的,但是在其所使用的材料中羊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是傈僳族男性配饰的地基。羊毡帽、羊皮褂和羊腰带,是装饰的底。傈僳族妇女在羊毛制成的帽子上缝上红色的丝带,绣上美丽的花纹,钉上象征日月的金色草编圆盘。傈僳族男子戴上羊毡帽,穿上防风防雨的羊毛褂和毛毡衣,厚重的毡衣在狩猎时可作为软甲,抵御兽袭和他族的冷箭,腰上艳红的羊毛带在必要时刻可以作为绳子,在野外受伤的时候作为止血带包扎伤口。
羊在傈僳族神话中亦是同等的重要,叶枝镇傈僳族与羊的故事开始了很久,在维西傈僳族的神话故事《阿弓玛的传说》中讲述了一位神通广大,专门为人间惩恶扬善、造福人类的女子,她能把山上的石头变成羊赶到江边,又让羊变成石头,为人类造桥。
(三)鸟:先祖及服饰之来由
在“阿尺木刮舞”中叶枝镇的傈僳族男子会戴上黑色“壳扒腊哄”(羊毡帽),帽前用雉鸡尾羽做装饰,帽子后缀一长串“阿木数吕”(麦草编织)的穗子,这种佩戴习惯只有维西县北部巴迪乡、叶枝镇、康普乡一带的傈僳族才有,维西县南部以及其他地区傈僳族均无这种佩戴习惯。叶枝镇的傈僳族时常佩戴的都是纯色或有一圈绣带的羊毡帽,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会戴上配有鸟类羽毛的帽子。傈僳族装饰鸟羽毛的习惯有很长一段历史了,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傈僳族长期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鸟作为较好狩猎的动物,逐渐从食物演变成为傈僳族鸟氏族的标识,在传说《鸟氏族》中讲到,相传:古时,有一对夫妻。一日,妻子生了小孩,丈夫无好食物让妻子吃,心中不忍,便上山打鸟。但一连三天未能打获一只鸟。为此他非常悲伤。这事感动了鸟王。从第三天起,每天,鸟王都赐鸟让他猎获。夫妻为此非常高兴。当他们的孩子满月的这一天,丈夫对妻子说:“我们的孩子是吃鸟肉长大的,以后他长大了就让他成为鸟氏族吧!”这样,这个孩子长大后就成了鸟氏族。维西傈僳族服饰上也充满了对“鸟”的形态模仿,维西县南部的傈僳族男子服饰叫做“喜鹊衣”,女性服饰叫做“画眉衣”,北部叶枝镇的傈僳族服饰叫做“锦鸡衣”,这些服装都呈现一种对“鸟”的模仿。在南部这种模仿呈现在整体服饰的结构和颜色上,在北部的叶枝镇呈现在男女的头戴上,女性的三角帽既有促进丈夫积极向上之意也有对鸟头部的模仿,男性则直接将象征鸟的羽毛缝钉在盛装的礼帽上。
配饰体现的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复写和创意,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叶枝镇傈僳族多用物的一部分来指代物本身,在傈僳族配饰的装饰上我们可以看见傈僳族用鸟的羽毛和三角形的帽子来指代鸟,用银质圆盘和麦秸圆盘指代太阳和月亮,这样的注重配饰象征意义的装饰方法使得傈僳族的配饰十分简朴清丽。作为族群精神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种穿在身上的符号是早期自我认知和自我识别的关键部分。作为族群保护桥梁的“羊”,作为被“日月”赐予生息的族群,作为鸟的孩子“我”只有认可了这些,才被认可为傈僳。傈僳族的信念并非独特,这种共同信念是由于民族所生活的土地而决定的,是山区民族的共性。
二、蜿蜒:叶枝镇傈僳族配饰记载的文化适应
配饰的形成过程像流淌在维西高山峡谷中的河流,顺应着地形的变化,改变着河流的走向。在多民族的共同记忆中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傈僳族逐渐从迁徙到稳定,生产方式也从游猎和游耕向后期的狩猎耕种一体式过渡,傈僳族配饰艺术特征也留有着本民族性格和高山峡谷环境烙印,适应着高山的生态环境和周边的多民族文化。
(一)弩弓与背带:山野中的力量与温存
弩弓一直贯穿在维西叶枝镇傈僳族的生活中,一直伴随着傈僳族人从曾经原始社会形态走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时代。弩弓作为叶枝镇傈僳族男性的重要配饰之一,是其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男子威武形象的重要饰品。在漫长的山野生活中,傈僳族人逐渐学会了如何处理猎物皮毛。在制作织物的过程中,傈僳族人制作出“友嘿贝缅玛”(羊毛弹弓),将兽毛拔下,弹散,蓬松,纺线,做毡。傈僳族猎人将其进一步改造,给弹弓装上弓弦,安装弓片,便有了射杀猎物的“华贝缅玛”(弓)。傈僳男子“善用弩”与“性枭雄”的文化形象,在男性猎人配饰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弓箭包和猎人头戴上的符号多是不同兽元素的堆砌拼接,獐子角、麂子角、野猪牙、熊爪等等,对于猎人而言,猎物的符号越多越证明这位猎手的狩猎能力出众。
古老的傈僳族在进行狩猎行为时,需要将弓弩、弓箭、刀等武器固定在身上,背带“腊裱”就此诞生了。“腊裱”的出现与傈僳族人民辛勤的劳动行为息息相关,具有很强的劳动属性。傈僳族在过往的生活中是男子狩猎,女子纺织,因此“腊裱”又作为傈僳族男女之间的定情信物。“腊裱”随着傈僳族的社会进程慢慢演化得更美更丰富,从“腊裱”变成“花腊裱”(花挎包),少女们在空白的麻布上绣出美丽多彩的图案,绣上表达自己爱意的花、草、树、鸟。因为在维西到处有杜鹃花,因此当地人的腊裱上也绣着一朵朵花,这是傈僳族人对于美好外界的复写。在织物上的创作和演绎,渐渐地形成了一种乡风,如“花腊裱”上一朵杜鹃代表着单身,两朵杜鹃代表已经定亲,枝干上带花苞的两朵杜鹃花就代表夫妻家中已有子女。叶枝镇同乐村傈僳族在花腊裱的制作上可谓是丰富多彩,如今“腊裱”从单纯的麻布口袋慢慢成为富有创意的手工艺品,为当地傈僳族人开拓了经济来源。
(二)贝币和麦编:贫瘠中的财富象征与向往
千百年来,傈僳族常常居无定所,依山而居,择林而住,迁徙农业也是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清代乾隆年间,余庆远《维西见闻纪》有记载:“(傈僳)喜居悬岩绝顶,耕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居住在叶枝镇的傈僳族将村落周围的山地分成一块块田地,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玉米、油菜等作物,经常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竹、麻和棉花,与此对应的是叶枝镇傈僳族男子常年穿着棉麻白衣,羊毡帽尾佩戴麦草编结而成的璎珞。《维西见闻录》也曾对古代维西傈僳族衣着服饰作过详细记载:“男挽鬓戴簪,编麦草为缨,络缀于发间。”据考察,现代傈僳族中尚保持着“编麦草为璎珞缀于发间”的传统,仅为维西县境内的叶枝一带的傈僳族特有。编织麦秸璎珞是叶枝镇傈僳族姑娘们小时候必学的技能。早年间,村寨中男性帽尾所缀饰的麦秸璎珞指代的是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璎珞上麦秸的数量代表着田地亩产的斤两,亩产愈多,璎珞愈长,但现今的麦秸璎珞已经失去了计量田产的意义,男性背后的麦秸编织越来越长,逐渐与村寨周边的田地脱离了关系,成为识别叶枝镇傈僳族人的符号。
“云南海贝文化的兴起,是受氐羌海贝文化的影响。”。作为氐羌族的分支,在维西县叶枝镇,傈僳族女性三角帽“呙亨”上镶嵌满了象征家族财富“矣玛”(海贝和鱼牙)。叶枝镇女性帽饰的装饰方法比较简单,以白为主,在白色的麻布上钉满排布整齐的海贝,现在则会更注重设计和色彩关系,只会在帽檐上缝上三五排海贝。这种装饰上的变化显示出配饰从实用功能向审美功能的转向。新中国成立后,材料的多样性启发了叶枝镇的妇女,不再将海贝铺满帽子,而是以蓝色三角帽、少量海贝、红丝带和银圆盘为基础,在此之上加上彩色珠帘等新的装饰品,逐渐形成现在的以蓝、白、红为基础色,辅以黄、绿和紫等色进行点缀的叶枝镇傈僳族女性头戴。
随着时代变化,傈僳族配饰折射出了该民族丰富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心理,傈僳族人的文化经验饱含着美学式的憧憬与渴望,正是这种向美之心促使他们在贫瘠的物质世界之中孕育出了属于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很多曾经物品的实用功能逐渐退化,但蕴含在配饰中的生活经验在时间的长河中却逐渐沉淀成为极具价值的艺术瑰宝。
三、绵延:叶枝镇傈僳族配饰现今的存续生态
傈僳族配饰作为傈僳族文化的艺术象征,既有稳定性,也有相对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一步千年”地进入生产力旺盛的现代社会后,其配饰在保持民族本真性的同时,也不断学习现代的制作材料和工艺技术,使其呈现出新时代的样貌。在历届维西县委、县部门以及州委、州部门举办的康巴艺术节、州庆等庆典活动中,配饰在歌舞中起到修饰、美化、画龙点睛的作用。随着傈僳族服饰的进一步开发,傈僳族配饰已从最初的自给自足变成了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
近些年来,叶枝镇在同乐村建立了非物质文化工坊,开启了企业与当地手工艺传承人的商业合作。县内共有5—6 家维西服装手工作坊,主要以传统傈僳族服饰设计和傈僳族配饰的文创产品设计。不同于外来设计师多关注非遗技艺的外在形式,叶枝镇的傈僳族人更在意也更能体会传统造物中的精神内涵,所以能够极大地保留文创产品中原有的文化内涵。曾经的傈僳族配饰是生存性的被动变迁,如今的傈僳族配饰是谋求发展的主动变迁。

图3 叶枝镇花腊裱创意设计图四叶枝镇弩弓摆件设计
社会各界参与傈僳族配饰的传承和保护,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多项技艺已申遗成功。但由于原材料的缺乏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傈僳族的配饰设计实践,还处于初步的设计转换中,将日常配饰转化为旅游快销品,规模化和产业化还存在许多困难。但从其对建党一百周年庆的花腊裱创作上,可以看见傈僳族对当下时代叙事与民族特性的反思。配饰的活性如同叙事的活性,当故事结构只能放在书中,那么由此诞生的艺术也只能放在博物馆或舞台上。傈僳族传承人们用自己的视角构思,融入当下的时代叙事,在创新上有所发展,在时代洪流中寻求一种属于傈僳族的平衡。配饰的命运如同民族叙事的命运一般,创造新的叙事亦是创造新的民族艺术。
四、结语
维西叶枝镇傈僳族的配饰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他寄托于一种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互动。配饰又具很强的野生感,整体艺术风格中充满着物与物的拼接,傈僳族配饰独特的组织材料、组成形式、以物而非通过抽象或具象的纹样形式象征精神,以羊皮、羊毛、羊角来指代羊这一精神象征,民族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种由极简、抽象发展到繁杂的过程。傈僳族配饰从最开始的民族自我标识的形成,中期的面对残酷无情的文化生态系统出现的生存性适应,到步入现代社会之后,渐渐成为文明的装饰符号。面对意义丧失的今天,傈僳族带着他一贯以来勇往直前的民族鲜明特点,面对新的环境加入新的叙事结构,创造新的艺术形态,使得傈僳族可以不断适应环境并对配饰进行改良,一直跟随时间前进,像一条蜿蜒曲折却绵延不绝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