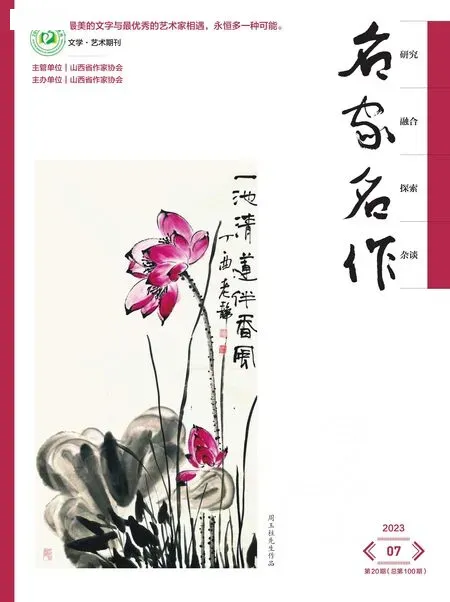维多利亚时代绘画中的溺亡女子形象探究
杨 傲
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是大英帝国的巅峰阶段,经济的繁荣催生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兴盛,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层出不穷。绘画领域,浪漫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拉斐尔前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派等艺术流派风格此起彼伏、交替并存,社会生活的图景也反映在其中。溺亡女子是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形象。
一、绘画中的溺亡女子
拉斐尔前派活跃在19 世纪的英国,强调专注研究自然的形态,从文学和历史中取材。围绕着西方艺术史上最经典的溺亡女性角色——《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拉斐尔前派画家描绘了一系列作品。这一角色的文化影响力也扩展到了其他国家,如法国画家保罗·阿尔伯特·斯特克、亚历山大·卡巴内尔都绘制过同名的溺水女子作品,H·保罗·德拉罗什的《年轻的殉道者》中也可见这一绘画传统的痕迹。
溺亡女子的形象也出现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象征主义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在1848—1850 年间创作了4 幅大型社会现实主义画作,其中的《被发现的溺死者》描绘了一具被河水冲到滑铁卢桥下的岸边的溺亡女尸。现实主义画家奥古斯塔斯·艾格的三联油画《过去和现在》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破裂,其中第三幅作品描绘了被逐出家门的女主人公寄身于泰晤士河上的滑铁卢桥桥洞下的情景。米莱斯《叹息桥》《索尔维的殉道者》等作品也暗含着女性与溺亡的关联。
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溺亡是常见的绘画母题,溺亡水中的女性生命与文艺传统、社会现实、道德观念都有密切的关系。
二、溺亡女子形象的解读
(一)水、自然和女性气质
古希腊时期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曾提出“万物从水中产生,又复归于水”。在各种自然元素中,水被视为生命的源泉,它与生命的密切联系与女性怀孕生育的能力相似,由此就产生了水与女性、母性、生育等概念之间象征性的联系。女性在水中的死亡既可以被解读为“水—自然—女性气质”三联象征的体现,也可以视为是人向自然的隐喻性回归。
深不见底的水体能给人神秘和恐怖之感,而刻板的女性气质常与疯狂、感伤和异变联系。眼泪、母乳、身体曲线,以及性别刻板印象下“捉摸不透”“阴晴不定”等特性,让女性与男性相比仿佛更加湿润、多变,就像水一样流动而不可预知。西方文化中,美人鱼、塞壬、宁芙等神话生物都生活在水域环境中。它们以女性形象示人,有着美丽的外表,其下则是致命的危险,人类一旦不慎受其诱惑注定凶多吉少。水体既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也成为与人类社会稳定性对立的威胁,二者的综合,傍水而生的幻想生物就成为这种威胁的具象化体现,映射着人类对未知而不可控之物的恐惧。
(二)被动的死亡
水与女性的关联早已有之,但维多利亚的溺亡女子主题绘画以“死亡”介入其中,重新建立了“女性”“水”和“死亡”意象的联系。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曾经指出:“自杀基本上是男性现象。”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因为“体质虚弱”而更容易有自杀倾向,但数据却并非总是如此。根据奥利弗·安德森所著《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自杀》一书,维多利亚时代虽然精神病院的女性患者人数远超男性,但女性的自杀行为发生率远低于男性。[1]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中频频出现女性溺亡自尽的情景,但有理由认为这并非对事件频次的简单反映,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更值得关注。
1852 年R·汤普森·乔普林《自杀统计》显示,男性自杀案例中采取刀刺、割喉、枪击等暴力方式的情况比女性要频繁得多。这些具有暴力和侵略性质的方式被认为是光荣的、英勇的或有“男子气概”的。相反,女性则多采取上吊、服毒或投水等相对温和、不激进的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作家和心理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将女性自杀的非暴力特点归因于她们“具有得体感和对制造混乱的强烈恐惧”[2],以及敏感和脆弱的心理特质。尽管埃利斯在女权、性教育和性少数群体平权等方面起到了突出的推动作用,他的观点仍不可避免地受到19 世纪刻板印象的局限。将女性自杀简单归结于偶然的个人特质,事实上却掩盖了存在于系统和制度中的社会矛盾的真实存在。
绘画作品中,溺亡女子形象大多呈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无力感,文学中也不乏典例。诗人托马斯·胡德《叹息桥》记录了一起女子投河事件。“那湿漉漉的双唇/请为她拭干”;“她散乱一头长发/未被梳篦整理/那金棕色的秀发/请你替她束起”。该时期的文艺作品倾向于将女性的溺亡描绘为安详、平静的简单屈从。当女性没入水中时,她不再是具有主动选择能力的个体,成为听任支配而毫无自主意识的对象,等待打理处置。
自杀尤其是女性自杀母题在西方艺术史上并非没有前例。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不同艺术门类已经充分呈现了卢克丽霞、狄多、朱丽叶等女性角色的自杀。她们有的以死证明清白,有的以死追随爱情,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证明了某种事物具有高于生命的价值。19 世纪早期,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更是将自我毁灭的行为视为自由自主的终极表现。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绘画中女子投水大多是出于自我厌恶和不堪重负,她们的死往往引发的不是观众的敬意,而是惋惜、同情或警醒。19 世纪,人们相信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的脆弱使她们容易患精神疾病,无力抵抗自杀和自残的冲动。在文学艺术中她们不似哈姆雷特那般需要质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而是如同奥菲利亚那样,作为一片非理性、非自主,甚至歇斯底里的空白被动地承受命运的安排,除却自我了断之外再无法做出其他回应。如果说文学艺术中的自杀可以是一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自我主张举动,那么维多利亚时代女子的投水自尽则大多出于自我厌恶的被动消亡,折射着父权社会对女性控制欲的强化。
维多利亚时代绘画中的溺亡女子也存在非完全被动的个例。乔治·克鲁克山系列版画《酗酒者的孩子》系列中的第八幅描绘了酗酒者的女儿失去父兄之后无依无靠、最终绝望跳桥自尽的情景。《警察新闻画报》于1872 年9 月21 日刊登了爱丽丝·布兰奇·奥斯瓦德的跳桥自杀案件并配以插图,这名刚刚20 岁的女性因在伦敦四处碰壁,无以为继,而被逼上绝路。这些木刻版画并没有将自尽的女性定格在水中,而是捕捉了她们绝望一跃的瞬间。这些妇女并非完全如前述那样麻木、被动、脆弱,她们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算作是一种自主主张。但这类图像远不及被动死亡的图像那样广泛存在,且究其实质,她们的行为其实是“主动的屈服”而非“主动的反抗”。
(三)社会道德规训
现实主义的作品蕴含着更加强烈的道德主题。米莱斯的蚀刻版画《叹息桥》中,一位表情绝望的年轻女子站在泰晤士河岸边思忖,在她宽大的黑色斗篷的褶皱里似乎藏着一个婴儿;艾格的三联画《过去与现在》中的第三幅中,一个被逐出家门的女子怀抱婴儿栖身于滑铁卢桥的桥洞下,呆滞地望着一轮盈凸月,身后墙壁上张贴的海报和面前近在咫尺的河水仿佛昭示了她的命运。
“家中的天使”这一称谓来源于考文垂·帕特莫尔的同名诗集,指向一种谦逊、纯洁、天真的,符合中上阶级道德标准的理想女性形象。她们无需外出工作,只需在家里画画、弹琴、唱歌、缝纫,并全心投入家庭,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关爱孩子。与“家中的天使”对立的“堕落的女性”的涵盖范围更广。这个标签不仅适用于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还可以加于被情人抛弃的女工、性侵犯罪的受害者、未婚先孕的母亲、有不忠行为的妻子,以及模特和女演员身上。总的来说,“家中的天使”和“堕落的女性”几乎能够涵盖一切女性,她们要么遵守社会期望,成为贞洁、顺从的天使,要么便被打入堕落女性的范畴而难以轻易摆脱。
基于此,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艺术构建起了一套关于“堕落女性”叙事话语,从有关作品中可以发现一条既定的叙事路径:女性受到并屈服于男性的诱惑,失去贞操或做出不忠的行为。她们因此背叛了当时的女性最要紧的责任所在——家庭,于是成为“堕落的女性”。这些“不洁”而“腐坏”的灵魂无法被家庭和社会接纳,只能面对被放逐和排挤的命运,最终不堪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负担,沦落到自杀的田地。水作为象征净化的元素,与“洗礼”的观念密切相关,因此溺亡的尸体图像同时承载了罪孽和救赎的双重意义:一个有罪的女人在水的坟墓中可以找到救赎。经过水的洗礼,她可以重新变得纯洁。[3]
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溺亡图像受到当时社会道德的影响,也反过来参与了社会道德的进一步构建。“家中的天使”与“堕落的女性”的话语体系能够为当时的女性产生一整套规范。符合“家中的天使”的女性受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而不符合的则沦为“堕落的女性”,接受社会的谴责和羞辱。如果她们无法忍受自己“不洁”的灵魂和身体,此时这个叙事传统又能贡献一个出路,即在泰晤士河里消解自身的社会存在。
维多利亚文学艺术以“家中的天使”和“堕落的女性”的对立为核心的一系列话语体系以父权的口吻为女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并对那些威胁秩序稳定的女性发出警告,从而维护中上阶层的父权社会道德和秩序。有批评家指出,文学艺术反复强化的“堕落的女性”及“堕落-溺亡”模式有可能在现实中进一步提高女性自杀率。
(四)被“凝视”的“他者”
他者即是主体之外的一切,他者的存在对自我的总体性和自发性构成了一种质疑,使自我感到某种威胁,从而产生收编和控制他者的冲动。凝视是一个不平等的物化他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我”沦为了对象“我”,被他人的意识所支配和控制。凝视与反凝视是一场为争夺支配权而产生的权力斗争。[4]“他者”和“凝视”的概念因为关注到了被边缘化、被压迫的群体状况,而被经常运用到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中。
上述的绘画作品大多出自男性艺术家之手,居于幸存者视角的男性创作者及观众与受害的女性产生了凝视和被凝视的关系。男性凝视是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男性站在观看者、审阅者、支配者、偷窥者的地位,女性则是被动的物品而不是有自主意识的主体。文学艺术中,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角色往往被物化,她们作为人物的价值被简单压缩为吸引男性观众和顺从传统刻板的男性观念。
溺亡女子经常处于被观看的位置。以《奥菲利亚》为例,画家米莱斯仔细安排了画面的空间构图,精心描绘了水流和自然植被,包括奥菲利亚在内的整个场景笼罩于一层玻璃般清透、精巧而易碎的氛围之中。奥菲利亚经历的言语和精神暴力发生于画面呈现的死亡之前,而濒死的她在画中仿佛由受害的“人”变成了受视觉支配的“物”。大量精细的细节描绘掩盖了她死亡的情感意义,画面中宁静而精巧的形状、光线、色彩十分引人注目,甚至让人几乎忘记了她在恋人、家人、命运之间的辗转拉扯和绝望挣扎。在这里,艺术家塑造出的“经过美化的尸体”和“经过美化的死亡”取代了对主角死亡本身的阐释,主宰画面的是艺术家技巧的展示,而不是主人公本身。
垂死或死去的女性也经常被色情化和美化。仍以米莱斯的《奥菲利亚》为例,画中奥菲利亚的衣裙尚未被水浸透,像云朵一样轻盈地漂浮在水面上,仿佛画面捕捉的是她刚刚落水的瞬间。然而奥菲利亚已是双眼失神,面容宁静,体态无力,几乎不再有挣扎的迹象,这样看来她又好像已经处于濒死的恍惚之中。她同时是完好的和无反抗能力的,然而这两种矛盾的状态显然不能同时存在,但河水仿佛是葬礼仪式上的一口透明棺材,精心地将濒死的奥菲利亚以最完美的形态展示出来。
在许多有关画作里,观看还来自另一个维度,即虚构的观众:溺水的女人不仅是画面外观众的凝视对象,也是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凝视对象。英国画家亚伯拉罕·所罗门所作蚀刻版画《溺亡》、威廉·詹姆斯·格兰特的油画《叹息桥》、威廉·克雷的插画《发现》、杰拉德·费茨杰拉德的蚀刻版画《叹息桥》,以及俄罗斯画家瓦西里·彼罗夫的油画《淹死的女人》中都有旁观者的形象。旁观者数量上有少有多,构成上以男性为主,他们的表情有的诧异、有的惋惜,但更多人脸上流露的是冷漠、好奇,甚至带着病态的兴奋和猎奇的窥视欲,或是急切地凑近观看,或将手电的光束直直地打在遇难者的脸上。画面中尸体是女性的,而目击、哀悼和讲述的幸存者则是男性。[5]经过艺术处理的死亡与女性并置而远离了男性自我,男性因此获得了与死亡的安全的心理距离,从中产生了心理上的优越感、支配感和永生感,男性从而能将遇难女性的尸体视作幻想和欲望的载体,或一种死亡的奇观。
三、结语
“溺亡女子”作为绘画中的形象,不仅体现了女性、水、死亡意象的古老联系,更以艺术的形式折射着维多利亚时代社会话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规训。溺亡女子形象反映了在一个以男性主导的社会和文化体系的社会中,女性身体和性别角色受到的强烈控制和束缚,被艺术加工和美化的溺亡的女性形象背后隐藏着对女性身份和权利的剥夺和忽视。
——电影《奥菲利娅》的跨时代改编
——《奥菲利亚》的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