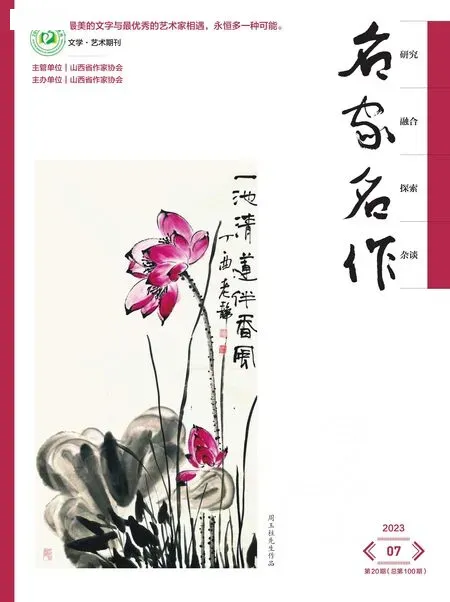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插图发展研究
何 婕
一、 延安木刻版画的发展背景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动荡的社会局面再一次使中国的艺术发展陷入了困境。在物资匮乏的战时环境下,延安等敌后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仍在党施行的开明文化政策下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根据地自由、开明的学术氛围更吸引了无数爱国青年和文人志士怀揣着爱国热情奔赴而来。来到延安的文艺家们在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都产出了很多的硕果,毛泽东同志在1942 年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就曾提及根据地的文艺盛况:“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很多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1]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文艺人才之多、文艺事业之繁荣。
而木刻版画也是根据地文艺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在此诞生了古元、彦涵、王琦、焦心河、罗工柳、张映雪等一大批著名木刻艺术家。这些木刻艺术家们在极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下,仍坚持着木刻版画的创作,跃身成为抗日救亡文艺阵线里的主力军,不仅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探索出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木刻版画风格,将中国的木刻版画艺术推向了高峰,还以简单、明快、富有战斗力的木刻版画作品鼓舞、唤醒了无数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念。
二、 木刻版画流派与插图应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文艺家们纷纷拿起自己的文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当中,“抗日救亡”“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等爱国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家们创作的主题旋律。这一时期的木刻版画家们以艺术家和革命战士的双重身份站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一方面以木刻刀作为艺术武器,为思想教育和抗战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是一种珍贵而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表现手法独树一帜,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人民生活、人民形象、人民精神面貌。
(一)新兴木刻版画风格
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赛珍珠在1945 年出版的《从木刻看中国》版画集收录了李桦、王琦、古元、沃渣、荒烟、刘铁华、汪刃锋等人在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作品。他们这些作品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甚至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反抗压迫的决心,作者赛珍珠在书中就以“木刻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战斗”来高度形容木刻版画在抗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木刻版画之所以能被视为一种有力的艺术武器,与其革命性、艺术性的特点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因为木刻版画在视觉上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能够以明暗对比渲染出壮阔的革命场景,与抗战时期爱国艺术家渴望宣传抗战、救国的诉求不谋而合,因而备受艺术家青睐,成为抗战时期各类宣传的常用艺术形式。
实际上,木刻版画在中国并不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鲁迅在《北平笺谱》的序言中曾提道:“缕象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法人伯希和氏从敦煌千佛洞所得佛像印本,论者谓当刊于五代之末,而宋初施以采色,其先于日尔曼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2]可见,我国在古代时就已有了木刻的艺术形式,甚至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仍是作为复制型版画来使用。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的传统木刻由于与现实生活隔绝,由于画、刻、印的分开,缺乏独立的创作意识,逐渐失去生命力[3]。20 世纪30 年代时,鲁迅洞察到了木刻版画蕴含的艺术潜能,便开始大力推进新兴木刻版画运动,把许多西方版画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使人们看到了木刻版画所蕴含着的新的可能性。在轰轰烈烈的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影响下,一八艺社、平津木刻研究会、MK 木刻研究会等木刻创作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鲁迅创立的木刻研习会更是为这一时期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新兴木刻家,如李桦、陈烟桥、郑野夫、黄兴波、朱宣咸等人,他们也成为推动当时中国木刻版画发展的主力。然而,新兴木刻版画更多的是受到当时西方版画的启发,因而在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与西方木刻比较贴近,画面比较讲究明暗光影、刀痕线条、写实效果、艺术张力,如郑野夫在1933 年创作《卖盐》木刻连环画中就借鉴了麦绥莱勒的创作技法,使画面黑白语言既简洁又富于变化,整幅构图考究,非常注重表现刀刻线条的艺术效果,阴阳线刻交错,使人能深刻地感受到黑暗社会给人的压迫。再如张明曹在1939 年创作的《仇》木刻连环画,也是新兴木刻风格的经典之作。张明曹作为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倡导人之一,善于利用巧妙的黑白对比、律动感的刀刻线条渲染出故事情景,从而引发读者内心极大的波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张明曹的《仇》一经出版便广受读者追捧,半年内出版多次,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胡一川在早期的木刻版画创作中也明显受到当时德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影响,在他1932 年创作的《到前线去》中也可以找到很多西方木刻语言的影子,这幅作品的构图、刀法、造型上都经过了仔细的考究,巧妙地利用了黑白对比、构图突出了造型夸张的主体人物,整个画面既粗犷又大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二)延安木刻版画风格
面对战时环境下物资困难的局面,木刻版画因创作工具简单、制图效果快等特点,成了根据地艺术家们常用的美术创作形式。延安的木刻,是在承继三十年代鲁迅先生苦心培育的新兴木刻的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一些活跃在上海的新兴木刻家,如马达、刘岘、力群等也相继来到了延安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这批新兴木刻家之中有许多人以鲁艺为活动阵地,一边将新兴木刻版画的创作经验传授给青年一代,一边又创作了许多表现根据地劳动人民面貌和抗战题材的木刻版画作品,如马达的《五月》、刘岘的《巩固、团结、抗战到底》、力群的《饮》、江丰的《码头工人》、陈九的《血战台儿庄》、沃渣的《查路条》、夏风的《小八路》等,这些作品内容都是从根据地生活中取材,非常具有生活气息,这些新兴木刻家们对根据地的木刻版画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置于争夺话语权以及救亡的语境之下,大众不仅成为文学所指向的目标,还成为革命依托的对象[5]。国家身处危难之际,艺术肩负着广泛唤醒民众抗战激情的重要任务。然而,中国传统绘画审美倾向于平面。取法西欧的阴刻法,用黑白对比组织画面、刻划形象的新兴木刻,不容易为人民群众接受[4]。在根据地,许多老百姓却并不理解新兴木刻版画中的素描语言,有些甚至将这些有着强烈黑白对比的木刻版画作品称为“阴阳脸”。由此可见,根据地的欣赏群体与创作者之间存在着审美差异,因而创作者笔下的作品难以激起欣赏群体内心更深层次的共鸣。1942 年5 月,著名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毛泽东同志在本次会议上正式把题材上表现工农兵、形式上做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趣味确定为解放区的文艺发展方向。在此号召下,延安的木刻家们纷纷将目光转向群众身上,开始自觉地探索“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形式。他们一边从群众的生活中取材,将自己的作品和群众结合起来;一边又对根据地群众所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进行研究和改造,期盼用群众熟悉的视觉语言来对抗战事业进行宣传。因此,版画的表现形式上,延安木刻家有选择地保留了曾对中国新兴木刻革命化有过影响的外来技法,并在适当地融合于阳刻线条造型的中国传统木刻技法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4]。随后,这种带有鲜明中国民族品格的木刻版画风格也被广泛地运用在根据地的各类书籍插图和宣传画中。
(三)延安木刻风格在插图中的应用
鲁迅曾言:“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6]鲁迅认为,插图能够补充文字内容,提升阅读体验,有着教育大众的作用,而连环画便是插图的一种。连环画对比单幅插图来说,其在表现故事主题和叙事上更具感染力,能以多幅连续图画来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因而深受民众喜爱,连环画也被延安艺术家看作是对大众展开文艺宣传的有力形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这种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木刻风格也被延安木刻家们带入连环画创作中,使木刻连环画在群众中取得了特别广泛的传播。如罗工柳和张映雪以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为蓝本绘制的木刻连环画,他们从“文艺大众化”的角度出发,在技法表现上兼顾了群众的审美习惯,使画面语言变得更为通俗易懂。在罗工柳绘制的《李有才板话》二十幅木刻连环画中,罗工柳为避免人物形象刻画“阴阳脸”的问题,不再大面积地使用明暗对比,而换以民众习惯的传统木刻线条来刻画,整个画面趋于平面化,显得更为明快、洁净。而张映雪为《小二黑结婚》绘制的木刻连环画虽使用了西方木刻版画的透视技法和明暗关系的表现刻法,但是也为了照顾群众的审美习惯,避免在人物脸部使用明暗刀法,因而画面既有素描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又符合民众的审美心理。彦涵创作的《狼牙山五壮士》木刻连环画则有着浓郁的中国气派,其木刻语言堪称经典,画面构图巧妙,人物形象生动,即使在用色单调的黑白木刻中,彦涵仍能把中国画的意境深融其中,营造出恢宏的画面感。力群在为《王贵和李香香》《小姑贤·刘保堂》绘制的木刻插图中,也不再追求写实效果、繁复的背景,变得极为朴素,换以简练的线条来塑造人物,整个画面极具装饰性。而莫朴、吕蒙、程亚君三人创作的《铁佛寺》则是在根据地艰苦环境下少见的大型连环画作品。《铁佛寺》的木刻连环画虽由三人分工合作,但整体风格非常统一,他们在《铁佛寺》的创作上借鉴了民间年画、剪纸的形式,改变了以往木刻版画偏重于以黑白塑造人物和背景体积的表现方式,变得更为质朴明快、通俗易懂,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除此之外,娄霜的《戎冠秀》、彦涵的《民兵的故事》、马达的《陶端予木刻集》、沃渣的《黑土子的故事》、安明阳的《女英雄刘胡兰》、古元的《新旧光景》、吕琳的《纪利子》等也是当时根据地广受欢迎的木刻连环画作品,这些连环画大多数都从真实事件和农民日常生活中取材,并且为了贴近根据地群众的审美习惯,减少了黑色在画面的占比,多以阳刻线条来塑造人物,变得更为简洁、洗练,以便于让作品更加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为弘扬抗战和新文化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真正让艺术作品起到了从“大众化”到“化大众”的作用,极具教育意义。
三、 结语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但延安木刻版画对于研究中国插画艺术发展方向和中国抗战文化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我国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7],并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7],号召新时代文艺创作者仍要“扎根人民”“扎根人民生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见,“大众化”“民族化”仍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所急需探索的重要命题。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代的文艺创作者浸润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之中,而商业文化和外来文化对插画创作者的影响颇深,一些插画创作者对于“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似乎已经有所遗忘,因而使自己深陷“泛西方化”“同质化”“商业化”等创作困境。而在抗战时期,延安木刻家通过践行“民族化”“大众化”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捧读和热爱,正说明了“民族化”“大众化”思想对于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所起到的有效作用。因此,不管时代语境如何变化,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民的生活中找到设计灵感,仍是新时代插画创作者打破自身创作困境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