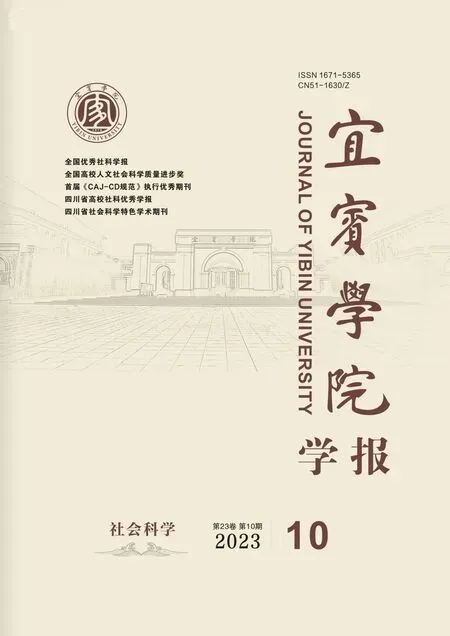礼制与今古
——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贝承熙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黄开国提到:“如果没有张之洞的拔识,廖平这块璞玉很可能被埋没在山乡,永无出头之日;而他师从王闿运,又决定了他一生之学的基本方向”[1]422-423。一般认为,张之洞与王闿运是影响廖平最大的两位学者,而在“今古文学”方面,与常州学派颇有渊源的王闿运似乎是令廖平重视“今古文学”之别的重要源头。但是,张之洞素来对廖平分判“今古文学”的做法并不赞同[2]12-13,而王闿运本人的著作中也看不出他对于“今古文学”之别的重视[3]141-144。更重要的是,吴仰湘即指出,王闿运对廖平经学的影响未必太大,他在尊经书院中更未以今文经学劝诱诸生[4]。
在这一认识下,大多数学者认为廖平之学是他自己默学深思的结果,如黄开国、崔海亮等学者即以为廖平揭发了前人从未揭示的汉代学术史史实,即使有一定问题,也作出了较大的史学贡献[2]115[5]263-265;李学勤、皮迷迷等学者则更是主张廖平自我建构了一套新的体系,其体系具有极强的原创性[6]247-255[7]。
然而,如果以清代的“今古文学”观研究作为基础,就可发现廖平之学并非无根之木,一变廖平与陈立的思想息息相关,廖平从一变向二变的转向与邵懿辰脱不开干系,三变廖平也仍保留较多来自陈立、邵懿辰的礼制认识。在本文中,笔者便将以陈立、邵懿辰的理论作为参照系,通过廖平与陈立、邵懿辰之间的理论比较,阐发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始末。
一、以陈为骨:《王制》《周礼》平分今古
(一)陈立以礼制分今古是廖平的立足点
光绪十二年,廖平作《今古学考》,自称详考今古学派。此书影响颇为深远,晚清以来言“今古文学”者大多皆本廖平之说。廖平分判今古的条目众多,而论其根基,无非是今古文经礼说之异,他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的《一变记》中自述道:
乃据《五经异义》所立之“今”、“古”二百余条,专载礼制,不载文字。“今学”博士之礼制出于《王制》,“古文”专用《周礼》。故定为“今学”主《王制》、孔子,古学主《周礼》、周公。然后二家所以异同之故,灿若列眉。千黔百壑,得所归宿。“今”、“古”两家所根据,又多同出于孔子,于是倡为“法古”、“改制”,初年、晚年之说。然后二派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判然两途,不能混合[8]547-548。
廖平区分今古异同的基本立足点便是礼制不同,而他认为这种礼制不同的根本在《王制》与《周礼》的礼制差异。一变时期的廖平认为,以《王制》与《周礼》所载礼制不同出发,推究二派不同的缘故,可以发现二者出于孔子早年“法古”所用周礼与晚年“改制”所参四代礼制的区别。
这一观点并非无根之木,陈立早在廖平之前,即提出了“今古学”之间存在礼制层面,尤其是殷、周礼制之间的区别。陈立受到老师凌曙的影响,以为采用三代旧制,尤其殷商之礼是《公羊传》的一项重要特征。如凌曙认为,《公羊传》兼用四代礼制,尤其多用殷礼,陈立认同此说。故于“君子不近刑人”章,陈立《义疏》即引凌曙之《公羊问答》曰:“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礼》墨者使守门,何也?曰:‘《祭统》云: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注谓夏殷时,然则《春秋》用四代之礼,不独用周礼,故不同”[9]2291。此外,凌曙认为,在四代礼制中,由于《春秋》与殷同属质家,《春秋》之制以变周从殷为主,陈立亦从此说,故于“练主用栗”章亦引凌曙《公羊礼说》曰:“《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公》《穀》所说皆殷礼”[9]1433。
但是,凌曙强调《公羊》多有改周从古之义,实本于何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春秋公羊传注疏·桓公卷五》)之论。这一论断基于《春秋》存三统之义,强调《春秋》依据以殷制为主的三代制度,定立新王之法,本为《公羊》学内部固有之科旨,故而凌曙仅关注《公羊》内部之条例,从未提及今古文学的差异问题。相比之下,陈立尤其强调今古文二派间的礼制差异,他相信今古文二派自身内部道一风同,彼此间水火不容。如陈立提到:“《公羊》与《三家诗》皆今文,故说相近”[9]1845。同属今文的经说大体相近,不同古文。他也提出:“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及降杀以两,皆《左氏》说,周制也”[9]1977。古文师说亦多相似,其旨均同周制,而迥异今文。
于是,参用三代还是专用周礼已不仅仅是《公羊》科旨的问题,更是今古学派之别。从《白虎通疏证》开始,陈立已注意到《公羊传》在是否从周问题上与古文经说有所差异,如对于《白虎通》中练主用木的问题,《五经异义》即提及《公羊》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与《周礼》说“虞主用桑,练主用栗,无夏后以松为主之事”两种说法,陈立遂评曰:“案《周礼》说专言问制,《公羊》说并明三代之礼,夏之练主以松,殷之主以柏,周之主以栗,与《礼》说本无异义也”[10]577。陈立指出,这一记述的不同源于《公羊》通贯三代之礼,而《周礼》则仅专言周制,今文《春秋》说与古文《周礼》说已在择取礼制的范围上有所差异。
《公羊义疏》中,陈立更为明确地表明了今古文学间礼制之异。其于开篇“元年春,王正月”之疏即以三统术费心推致《春秋》之历,论曰:“是《春秋》实用殷历”[9]9。实已与《春秋》用周正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而在全书之中,陈立皆有意彰显今文学多采殷制,古文学多采周制。
以对军制的说解为例,陈立认为:“按郑氏以万二千五百人为军,系古《周礼》说。依何氏,则隐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9]2163。这一论述将两种军制的差异归因于今《公羊》、古《周礼》所守殷周礼制之别。类似的,陈立对隐公五年中何休所言“师众者,满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疏证道:“其实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之说,自是周礼。其以师为军,是《春秋》今文家说,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礼也”[9]238。在陈立看来,夏、殷之制中军队分为“六师”,每一师为二千五百人,六师合为“一军”,采用夏、殷制度的今文《公羊》学即用此说;周制中军队分为“六军”,每一军二千五百人,六军合为一师,体现于古文《周礼》之中。
其实,何休等传统《公羊》家本来未必如此明确地划分今古礼制,陈立则有意强调今文、古文二派自成体系,认为前者所述兼通三代,偏重殷礼;后者师说多用周制。以何休“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一句的疏解为例,陈立曰:
以皮弁为武冠,盖今文家说。成二年《传》:“衣服与顷公相似。”何注:“礼,皮弁以征。”彼疏云:“即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义’是也。”引《韩诗传》,亦有是语。《御览》引《三礼图》:“皮弁,春八月习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诗》、《春秋》家皆然。惟《周礼·司服》云:‘兵事韦弁服。’即成十六年《左传》之“韎韦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韦,柔皮也。”皮韦同类,故同有皮弁之称。惟皮弁白色,韦弁韎色尔。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韦弁之别与[9]1655-1656?
何休本来并未强调以“皮弁”为武冠与今古文异制有何关联,此句只是单纯地对《公羊传》文的疏解。陈立则有意进行发挥,认为何休之说能体现今古文家的根本差别:《韩诗》《公羊》的今文师说均以皮弁为武冠,均采纳殷商古礼;而《周礼》《左传》的古文师说普遍以韦弁为武冠,体现的都是周代礼制。在这一叙事下,今古文间礼制层面的差异被刻意放大,从古、从周成为审视今古二学的核心视角。
由此而言,以礼制分别今古出于陈立之首创。廖平深受其泽,《今古学考》便提到:“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翬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8]89。其中,陈立所治经疏即指《公羊义疏》,显然廖平对其成书过程、注疏特点颇为熟悉。而廖氏在《今古学考》中又说:“以今古分别礼说,陈左海、陈卓人已立此宗旨矣”[8]76。此处虽说同时提到了陈寿祺、陈立二人,但陈寿祺的“今古文”仅指文字之别,唯有陈立认为“今古文学”的差别在于周公所制周礼与孔子依三代礼所制新礼,故而真正令廖平注意到可以“以今古分别礼说”的只有陈立。
因此,廖平一变体系中重点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实可回溯到陈立的“今古学”体系,只是与陈立不同的是,陈立以《公羊》《左传》的不同为今古学之别的核心,廖平又受俞樾影响,认为《王制》与《周礼》的对立才是今古学礼制之别的关键。当然,廖平从何种意义上继承了陈立,又从什么程度进行发展,仍待更深层次的反思。
(二)从“以今古解礼制”到“以礼制解今古”
在陈立对“今古学”的讨论中,已经俨然有将“今古学”问题视作先秦礼制问题的倾向,他往往追绎二派经典所载先秦制度之别,探讨两种文本中所蕴含的礼制差异。但陈立尚未将这一思想倾向放大,廖平《今古学考》却将“礼制”置于“官私”之上,从而彻底摆脱汉代史料的束缚,完成“以今古解礼制”到“以礼制解今古”的转变。
陈立的“今古学”观仍以宋翔凤式的理解作为基础,对陈立来说,“今古学”首先意味着以官学、私学相区分的两种经典,只是这两种经典对礼制的记载各有差异,才衍生出了礼制之别的问题,他说:“今文立于学官,当时所习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间,往在蝌蚪文,故无师传,因皆目为古文也”[9]292。廖平则以礼制作为区分今古的唯一标准,他自述道:“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8]70。在他的认识中,凡是与《王制》所载礼制相合者皆可算作“今学”,而不合《王制》者皆可归入“古学”。
具体而言,廖平发现《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所载礼制与《王制》多有不同,《左传》与《王制》反而偶有相合,他因而认为:“《公羊》今学,有改古从今之条;《左传》古学,有从今改古之条”[8]55。相比之下,由于“《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8]91,《穀梁传》便被廖平当作最得孔子大义的“今学”经典。其次,在礼类文献中,《仪礼》与《王制》所载多不相合,《礼记》大部分篇目则与《王制》说同,廖平便提出:“《仪礼经》为古学,《记》为今学,此一定者也”[8]69。当然,《礼记》之中,有部分篇目也与《王制》不合,廖平补充道:“《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8]69。此外,由于《诗经》《尚书》与《王制》《周礼》均难相合,廖平遂认为二者本无今古归属:“《诗》《书》有四代异制,以今、古学说之,皆非也”[8]81。而对于《孝经》《论语》,廖平也有评价,他基于对二书的礼制研究说:“《孝经》为古派,全书自成首尾。《论语》则采录博杂,有为今学所祖,有为古学所祖”[8]80。
除了对六经今古学归属的判定均以《王制》《周礼》为裁断,廖平对“今古学”二派异同的判断也都建立在对《王制》《周礼》二书内容的理解上。廖平认为,《王制》与《周礼》间存在燕赵齐鲁之别、殷周制度之别、新制古史之别,这些差异即构成了“今古学”在地域、制度、方法方面的两种不同特点。首先,他考察《周礼》的特点说:“《周礼》之书,疑是燕赵人在六国时因周礼不存,据己意,采简册摹仿为之者”[8]86。《周礼》多为燕赵学者所传,故而应该是燕赵后学所推想的周代制度,这一特点被他放大为“古学”整个学派的特征。相比之下,他评价《王制》的性质说:“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8]78。《王制》之义与周礼多有不合,则当为孔子所立新法,这一特点便被廖平划归为“今学”的总特点之一。由此,陈立的“以今古学解礼制流别”被廖平转化为了“以《王制》《周礼》礼制之别解今古学”,《王制》《周礼》的差异被廖氏视作平分今古的唯一标准。
当“今古学”由汉代师法差异衍生出的礼制问题变为典籍内部本身蕴含的观点对立,“今古学”便不再是汉代经学史的事件,而是完全成为先秦出现的事件。因此,陈立对“今古学”的基本看法仍依据汉代史料,廖平则不再认可汉代经师论及的“今古学”差异,仅将“今古学”问题置于先秦视阈之中。首先,廖平认为,汉儒的“今古学”师法大多并不以《周礼》《王制》之别作为根本,这样的师法流别已偏离今古学的本义:“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至于先师异解,汉人因其异师,亦以为有今古之别,实则非也”[8]79。由此,汉儒的“今古学”师法差异多出于后人附会,与先秦的“今古学”划分已有不同。
其次,许慎《五经异义》以典籍体系之别作为区分今学、古学的标准,廖平便同样认为这一做法不明“今古学”之真意,他说:
予言今、古,用《异义》说也。然既有许义而更别有异同者,则予以礼制为主,许以书人为据。许以后出古文为古,先出博士为今,不知《戴记》今古并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为今学,此大误也。其中篇帙,古说数倍于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8]102。
廖平认为,许慎不明先秦经籍内部的礼制之别,遂以为今古文为博士典籍与后出典籍之别,实为“大误”。
由此,廖平对陈立体系在礼制的主体性与先秦的重要性两个层面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周礼》《王制》二书的礼制之别取代官学、私学之别,成为区分“今古学”的唯一标准。殷周礼制问题取代汉代师法流别,成为“今古学”立论的时代依据。廖平的一变体系在这一意义上区别于陈立的《春秋》学,由“以今古解礼制”转化为“以礼制解今古”。
二、以邵为魂:完整的今学与伪造的古学
(一)邵懿辰与廖平划分今古的新标准
1888 年,廖平的“今古学”又有了新的转向,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中,廖平自述曰:
盖当时分教尊经,与同学二三百人,朝夕研究,折群言而定一尊。于是考究“古文家”渊源,则皆出许、郑以后之伪撰。所有“古文家”师说,则全出刘歆以后据《周礼》、《左氏》之推衍。又考西汉以前,言经学者,皆主孔子,并无周公;六艺皆为新经,并非旧史。于是以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8]549。
据廖平所言,他在二变时期的代表作即为《古学考》与《知圣篇》二文,其中《知圣篇》讨论孔子素王改制之说,《古学考》(后改名《辟刘篇》),对“今古学”的源流进行了新的阐发。从他的自述来看,他在这一时期划分今古的标准在于是否出于刘歆伪造——西汉以前的经典皆为孔子所传之“今学”,直到刘歆才依据《周礼》《左传》推衍出一套“古学”的体系。
廖平这一观点的核心在于刘歆作伪旧案,似乎与刘逢禄的伪经说脱不开干系。但是,廖平二变时期几乎从未征引刘逢禄的论点,反而颇为强调自身学问与邵懿辰《礼经通论》之间的关联:
余因邵说,乃持诸经皆全,亦备为孔修。盖授初学一经,首饬之曰:经皆全文,责无旁贷。先求经为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残佚俗说,然后专心致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专一之余,鬼神相告。故学者必持经全,札硬营,打死仗,心思一专,灵境忽辟,大义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书为前绝后,为东汉下暗室明灯[8]210-211。
考察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邵氏贯穿始终的总体观点便是六经均为孔子所修,而六经也均完整地流传于世。邵懿辰通过考察《礼运》等文献中所引相关礼制皆与《仪礼》十七篇相合,试图论证《仪礼》十七篇从无亡佚,之所以仅有十七篇,也是孔子有意为之[11]1a-8a;通过论证《乐》本无经,证明《乐经》不存不可归因秦火[11]8a-10b;又通过论证《逸书》《逸礼》之说为刘歆所伪,从而说明《尚书》《仪礼》本皆完备[11]14a-17a。
在确认六经全部完备流传至西汉后,邵懿辰自然而然便可得出结论,不在汉传经籍之列的晚出经籍只能出于后人所伪,于是他说:“然《毛诗》《左氏》当歆世固已流行,特以佐其《逸书》《逸礼》之为伪,自来无觉其诈”[11]15a。邵氏以为,《毛诗》《左传》早有其书,便多半为真;《逸书》《逸礼》不在汉代所传六经之列,便只能为伪。
依照廖平的自述,邵氏这一思想使他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说:“邵《礼经通论》以经本为全,石破天惊,理至平易,超前绝后,为二千年未有之奇书”[8]210。因此,在《古学考》中,廖平以邵氏之说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利用邵氏的观点改造自身的“今古学”理论。他首先改造邵懿辰的说法,认为孔子传授的“今学”经典本来完备无缺,“古学”皆为依傍今学而作:“刘歆援《周礼》以为主,其徒党最盛,推之于《诗》《书》以成古学,是古全由今生,非古在今前”[8]138。他也接受邵懿辰的观点,认为刘歆有意通过改窜《周礼》,建构了一套适用于王莽新朝的法度,以此与孔子之制立异:“刘歆作《周礼》,以为新室法”[8]136。
至此,邵懿辰对于二变廖平的影响已经了如明镜。当然,邵氏之说与廖平关注的今古学问题究竟存在距离,因而廖平为具体采纳邵懿辰的观点,对邵氏之说不无改造。
(二)从“六经完备说”到“今学完备说”
邵懿辰《礼经通论》的核心在于“六经完备说”,邵氏认为,孔子所修的六经完整传授于世,刘歆为了作伪部分古书,才制造了秦焚六经之说。但是,邵懿辰虽提及六经完备、刘歆作伪等观点,却从未将其与“今古学”问题相关联。廖平则将这一论点转化为“今学完备说”,在他看来,孔子所修六经均完备流传至汉代,完整构成了汉代的“今学”体系;刘歆为伪造新的经典,才提出“古学”这一名目。
判分“今古学”的标准发生改变,便也意味着“今古学”经典的划分需要更改。廖平细考汉代所传六经,发现《古文尚书》《毛诗》《左传》《国语》《费氏易》《仪礼》《孝经》均于西汉完整流传,在“今学完备说”之下,这些原本在一变时期被定为古学的经典就都需要“平反”。如《公羊》《左传》《国语》原本被廖平认为多用古学,此时便被重新划为今学典籍,他说:“《公羊》与《穀梁》异义,旧以为《公羊》用古学,今合勘之,乃得其详。《左》、《国》全本六艺佚礼,亦属经说。西汉以前,道一风同,更无歧路,则乡土未定之说皆可删之”[8]119。至于《古文尚书》《毛诗》,既为刘歆以前的经籍,自然亦当属于今学之列;“孔氏写定《尚书》,以今文数篇推其异者写成隶字耳,有经无说。《毛公诗》班云:‘自以为子夏所传’。此二家亦今学也”[8]117。甚至遭刘歆改窜前的《逸礼》以及后来的《费氏易》,都不能归为古学,他强调:“总之,刘歆以前不可立古名,建武后古学乃成,则不得以《逸礼》、《费易》为古学也”[8]119。
至于真正属于古学的经籍,则唯有刘歆所改的少数经典,廖平说:“刘歆改《逸礼》为《周礼》,弟子又从三家欧阳、夏侯本翻改《毛诗》《古书》”[8]146。则古学范围仅在于《周礼》中被廖平判定为刘歆所窜入的部分条目与《毛诗》《古文尚书》被刘歆后学篡改的部分而已。这些条目加起来其实并不多,他说:“歆改《周礼》,今为删出明条,不过千余字,又杂有原文,然则合其零星所改,不过千字耳”[8]137。唯有刘歆在《周礼》中数量极少的改窜部分才建构出一套新制度体系。
“今学完备说”撬动了廖平整个体系。由于完整传世的经典都可归为“今学”,唯独遭到刘歆篡改、牵连的经籍才能归为“古学”之列,廖平在一变时期提及的“今古学”经史之别、乡土之别便都需要用新的逻辑重新阐释。对此,廖平说:“今学有授,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无师说。歆好奇字,以识古擅长,于是翻用古字以求新奇”[8]138。这一观点正是廖平对自身一变体系的“扬弃”,“今古学”之间有无师说、文字用今用古的差别不再是《王制》《周礼》等典籍呈现出的不同特征,而是变为刘歆改经的副产品。
与此同时,廖平对自己在一变时期所提出的《王制》与古学诸经之别便也进行了“扬弃”,他依旧认为今学诸经的礼制应当相合,但这只意味着自身在一变时期对今古诸经差异的判断并不正确。首先,廖平重估《仪礼》礼制,认为它其实存在与《王制》相合的方面,他说:“《仪礼》为孔子所作,孺悲所传,《士丧礼》可证为《王制》司徒六礼之教,与《春秋》莫不合,此亦为今派,非果周之旧文为古派”[8]117。类似的是,《左传》《官礼》等书与《王制》虽多有差异,廖平亦加以弥缝,以为此诸书与《王制》的大意非但没有矛盾,反而参差互补:“孔子以后惟今说盛传,《左传》及《官礼》皆为今学。其与《王制》不同者,则仪节参差,一书不能全被,参差互见,润泽经说以补之,非异说也”[8]117。又如《孝经》与《王制》之间的抵牾,也被廖平以类似的方式化解,他认为《孝经》便同样属于今学,其异说反而是对《王制》可贵的补正材料,评价说;“今定《孝经》与六艺同为今学。至仪节异同,则统以补证《王制》。说经以异说为贵,可以备证,非礼制偶异,便为古学”[8]119。
当然,邵懿辰原本只是抨击刘歆伪造《逸书》《逸礼》,未尝言及“今古学”之别,廖平如要将邵懿辰的观点与“今古学”分派联系在一起,难免需要对邵氏的部分论点进行调整,使其更能迎合他所期望的“今古学”理论体系。如邵懿辰虽将矛头直指《逸礼》,对于《周礼》,则只认为它是后人附益修改之书,他说:“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固未必然。而汉武以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则未始不然也。末世渎乱,谓为后王所附益修改,又推之诸经,而礼制官名多不相符验耳”[11]36a。相比之下,廖平则坚持《周礼》为古学核心的观点,认为《逸礼》与《周礼》本是一书,而《逸礼》亦是今学,只有刘歆改窜《逸礼》而成的《周礼》才是真正的古学,提出:“《逸礼》即《周礼》之原文,礼经非古,则逸者可知”[8]119。
总体而言,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仍是廖平转向二变的根本依据。廖平正是在邵氏的影响之下,有意辨刘歆古学之诬,确立今学经典体系的完备性,从而证成“尊经”“辟刘”二说,申说孔子改制立法之大义微言。
(三)陈、邵余影:“小统”治国,“大统”治世
可能是受到19 世纪末国际格局变动的影响,廖平在三变时期对“今古学”的理解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三变记》中说:
及考明《周礼》土圭三万里与《大行人》之大九州,乃知皆为《周礼》师说。根本既立,枝叶繁生。皇帝之说,实较王伯尤为详备。一人之书,履变其说,盖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又安知不有鬼谋天诱,以恢复我孔子“大一统”之制作?故编为《小大学考》。于《周礼》取经,去其师说谬误。故改“今古”之名曰“小大”。盖《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深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今以《王制》治内,独立一尊,并无牵制;而海外全球,所谓三皇五帝之《三坟》、《五典》者,则全以属之《周礼》,一如虬髯公与太原公子,分道扬镳[8]551。
面对势如水火的晚清变局,“恢复我孔子‘大一统’之制作”便成为廖平最为关心的问题,他试图要用传统儒学对这一全新的世界格局进行回应,遂将“今古学”之别改造为制度的“小大统”之别,孔子学说的要点成为中国之制与全球之制之间的差异。三变廖平认为,“今古学”之别在于二者制度所涉及的疆域大小问题,其中《王制》治内、《周礼》治外,而“今古学”这一名义已不足概括两派区别,廖平便以“小大统”这一名词取而代之。这一时期,廖平似乎已完全跳出了陈、邵之说的束缚,完全建构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
然而,三变廖平看似不再依傍陈立、邵懿辰的框架,其思路仍有早期“今古学”观念的影子。廖平三变时并非如钱穆所说“不复为今古之辨”[12]846,他看似以“小大”体系替代了“今古”体系,仍对“今古学”问题保持关注:“小大”体系恰从“今古”体系发展而来,并仍旧继承了源自陈立、邵懿辰的“以礼考经”方法。
廖氏在三变后期所作的《知圣续篇》一文便充分体现了他如何以“小大统”衔接“今古学”,他指出:“初考《周礼》,以为与《王制》不同,证之《春秋》《尚书》《左》《国》皆有龃龉。因以为王刘有羼改,作《删刘》一卷。丁酉(一八九七年)以后,乃定为‘大统’之书,专为‘皇帝’制法”[8]229。可以发现,三变时期的廖平仍在关注《周礼》《王制》的礼制问题,只是对二书礼制有了新的阐释。廖平一转二变时期的观点,认为以《周礼》为主的古学之所以与《王制》不同,并非源于刘歆伪篡,而是因为《周礼》是为“皇帝”制法的“大统”之学,故而与为“王伯”制法的《王制》多有立异。
廖平一如一变、二变时期,仍将“今古学”或者说“小大学”视为一种礼制差别,只是“小大”之学关注的是《王制》与《周礼》礼制中涉及疆域大小的部分,他说:
又官有小大之分,《大行人》言大九州,则可知《小行人》为小九州。其以“小大”分者,即“小共大共”、“小球大球”、“小东大洞”之义。“小”为“王伯”,“大”为“皇帝”。一书兼陈二统,“小”同《王制》,“大”者由《王制》加三加八以至卅五倍,所谓“验小推大”是也[8]230。
廖平发现,《周礼》中《大行人》一篇所载幅员远大于《王制》,直接结论便是:《周礼》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治理海外藩国,因而是一种治理地球的“大统”之学,故而既有统管疆域辽阔的《大行人》篇,又有涉及疆域较小的《小行人》篇;相比之下,《王制》只考虑治理中国的制度,因而只是一种“小统”之学。由此,廖平认为,孔子之所以分别提出《王制》与《周礼》两套体系,便是为了应对大小两种疆域范围的治理问题,他说:“所谓《王制》‘今学’者,王霸小一统也;《周礼》‘古学’者,皇帝大一统也”[8]224。这一视礼制为经学核心问题的思维方式,即仍与陈立、邵懿辰一脉相承。
与此同时,廖平的新体系也并未抛弃原先对“今古学”礼制差异的认识,而是将其“扬弃”,认为“今古学”的疆域差异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已。例如廖平仍认同陈立的观点,以为“今古学”间存在殷周礼制之别,只是殷周之别指的不是时代不同的两种制度,而是作为中国的“周”与作为海外的“殷商”之间的差异,他说:“《诗》以文为中国,质为殷商。《荡》七‘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七章为七襄、七子,为以文化质、周监于殷。一文王为中,东七殷商为七州牧,以中国化海外,为以一服八”[8]225。廖平也仍然认同邵懿辰对于六经皆孔子所作的强调,只是认为不仅今学所传六经,古学所修经典也同样为孔子所修,他说:“是孔子不惟制作王伯,兼制作皇帝”[8]237。
因此,廖平在三变时期看似出现了断裂式的变化,其具体思想、立学方法仍与陈立、邵懿辰的礼学研究相关。以往的廖平研究鲜少考虑到廖平之学的这一清学来源,不能不令人感到可惜。
结语
廖平自始至终的诉求都在于探寻“今古学”的礼制之别,他期望效法孔子所定立的万世之法,以此匡救时弊,因而陈立、邵懿辰等清代礼学前辈自然成为了廖氏之学的主要来源。基于这一逻辑,廖平在第一、第二变时期分别以陈立、邵懿辰之学作为自身立学的主要参考,而他在三变时期看似出现了断裂式的变化,其具体思想、立学方法也仍与陈立、邵懿辰的礼学研究脱不开干系。
就此而言,廖平之学的学术史源头,及其几次转变的缘由始末,均已完全得以呈现。陈立与邵懿辰的礼学正是廖平一生学问的根本所在,它们铸就了廖平早年学问的核心骨架,也在之后成为始终回荡在廖平思想之中的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