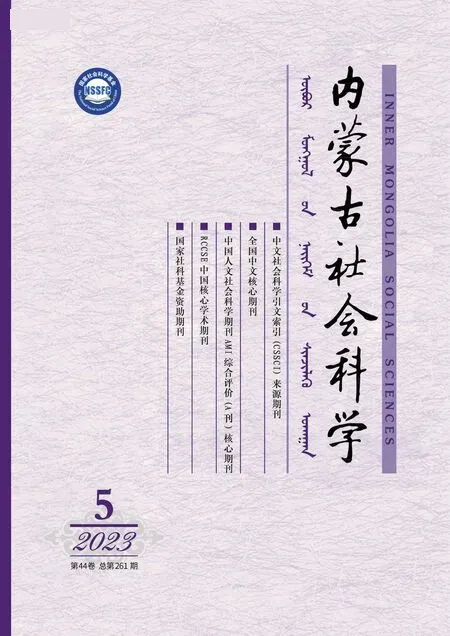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
——以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为例
胡玉春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东汉初年,南匈奴大规模南迁入塞,屯驻在北地、上、朔方、五原、云中、代等北方沿边八郡。同一时期,活动于大兴安岭、老哈河流域、阴山山麓、蒙古高原腹地的鲜卑、乌桓、丁零等族正逐渐摆脱匈奴的役属。北匈奴龙庭西迁之后,蒙古高原上的古族经历了大规模的迁移:漠北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各部向南、向西迁徙,一部分进入东汉障塞内,还有一部分进入西南方向的准格尔盆地以北地区;原活动于乌桓山的乌桓经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又进一步迁入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等十郡障塞内;乌桓南徙后,东部鲜卑顺势南下、西进,占据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拓跋鲜卑人也经过两次迁徙,从大鲜卑山经“大泽”迁到阴山北麓的“匈奴故地”(1)目前,学界关于“匈奴故地”的具体方位未达成共识,但多数学者主张拓跋鲜卑迁入的“匈奴故地”在五原郡塞外阴山北麓地区。如马长寿认为在漠南阴山之北的头曼城(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第241~244 页);宿白认为在匈奴始祖头曼、冒顿发迹之所,即今内蒙古河套东部一带(参见宿白《东北、内蒙古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载《文物》1977年第5期);佟柱臣认为在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之地(参见佟柱臣《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舒顺林认为在河套阴山地区(参见舒顺林《“匈奴故地”初探》,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曹永年认为匈奴故地的核心部分在河套顶端阴山以北草原(参见曹永年《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考古学研究的文献反证——重读宿白先生〈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等等。。这次人口迁移活动规模大、人群多,延续时间长,从东汉初期一直持续到北魏初期,波及范围广,从蒙古高原北部、大兴安岭北段直至整个黄河流域。此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中国北部地区形成了多民族交错杂居、共存共生的局面。
西晋时期,北方边郡的游牧民族人口比例明显增加。西晋初年郭钦上书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1](卷97P.2549)江统也曾描述当时北方边郡的人口情况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而“并州之胡”又“过于西戎”。[1](卷56PP.1533~1534)
在长期杂居共处过程中,北方各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交融。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是炎黄子孙的传说逐渐被北方游牧民族接受和认同,他们在追述自身族源时,往往将本族先祖归入到黄帝之后、大禹之裔的谱系之下。这种寻根溯源中的自我塑造和宣明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华夏认同”基础上对其政治身份的重申和确认,也是“华夷”走向一体的重要推动力。研究4~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理解各个时期“华夷”关系的特点,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古代民族互动交融的内在逻辑,对于进一步夯实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基于此,本文以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为例,探讨其在族源叙事中对“华夏”“中华”认同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而阐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在认同华夏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的客观史实。
一、铁弗匈奴与夏后氏之苗裔
铁弗匈奴是十六国时期大夏政权的建立者。关于铁弗匈奴的族源,《魏书·铁弗匈奴传》中称铁弗匈奴部帅刘虎是“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2](卷95P.2054)。从《魏书》提供的线索和信息来看,铁弗匈奴是匈奴人与鲜卑人融合后形成的新部族,南匈奴左贤王去卑(2)《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记作“右贤王”。参见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1页。一系在铁弗匈奴形成初期和发展过程中成为其核心家族。《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和《太平御览·偏霸部》引《十六国春秋·夏录》也都记载刘虎家族与去卑有直接关系(3)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1页;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夏赫连勃勃》,中华书局,1960年,第615页。。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根据文献中相关联的史事提出铁弗匈奴属于屠各或乌桓的说法(4)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铁弗匈奴的族源,在1600多年前大夏政权官员撰写的《统万城铭》中有一段重要文字记录。413年,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发岭北十万民众修筑都城,419年,都城竣工,取名“统万城”。随后大夏秘书监胡义周、胡方回父子奉命为新都定鼎刻石作铭,即《统万城铭》。该铭目前没有实物资料出土,但其文字内容保存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中。《统万城铭》是大夏政权留存至今的最完整的一份文献资料,其中留下了关于铁弗匈奴对其族源历史叙事的重要信息。
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网漏殷氏……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爰始逮今,二千余载,虽三统迭制于崤、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杀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薮,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1](卷130P.3210)
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等相关记载可知,上引《统万城铭》中所记录的“故能控弦之众百有余万……平阳挫汉祖之锐”这段史事,实际上指的是战国秦汉时期匈奴的历史。而《魏书》所载“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的相关信息,在《统万城铭》中并没有提及。可见,以赫连勃勃为代表的铁弗王族在追述族源时,采取了强化“匈奴”记忆的叙事模式。《统万城铭》中对于犬戎伐西周(5)犬戎为西戎的一支,其与匈奴的关系尚不明,或为匈奴统一草原后的一支部族。《史记》《汉书》认为北方草原上早期活动的荤粥、猃狁、山戎与匈奴有相承关系。参见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743页。铭文所用“偏师”一词说明胡义周或者大夏王族认为犬戎应该属于匈奴的一支。,匈奴对秦、赵、燕三国构成的军事压力以及匈奴在平城包围汉高祖刘邦等史实的铺叙,意在通过回顾匈奴历史展现匈奴往昔的辉煌业绩,对铁弗匈奴先世进行歌颂和赞誉,从而强化其为匈奴后代的族源叙事。在大夏建立之前,铁弗匈奴人经历了一百多年夹缝中求生的艰辛岁月,不断地遭受拓跋鲜卑的驱逐和追击,甚至面临灭族危险。大夏政权建立后,铁弗匈奴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利用共同的族源纽带来维护铁弗匈奴内部的凝聚力,重塑政治自信,巩固统治,成为大夏政权统治阶层的迫切需要,自认匈奴后代的族源叙事和对匈奴历史文化的宣扬,正呼应了大夏政权当时的社会现实需要。
在自认与匈奴一脉相承的基础上,铁弗匈奴还进一步认同司马迁提出的匈奴人是夏朝后裔的观点,并将其先祖直接追溯至大禹。《统万城铭》开篇即称“我皇祖大禹”,将铁弗匈奴人列入大禹的直系,接着对大禹的文治武功进行了高度评价,显示出对“大禹之后”的高度认同和自豪。同时铭文对匈奴北迁也给出了解释:夏朝灭亡后,殷商建立,匈奴先祖“长辔远驭”率众北迁,至大夏政权时期已有两千余年。根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先祖名淳维,是夏后氏之苗裔。而《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和《淮南子》中都提到夏都被商攻破之后,桀奔鸣条,汤与桀曾经在鸣条开战,夏桀败亡,夏人四散迁徙。《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乐产《括地谱》中进一步解释:“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粥(另作獯鬻),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6)参见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2880页。《括地谱》除将淳维的名字换成獯鬻之外,更明确指出匈奴是夏人北迁的一支。《统万城铭》中采用了这个说法,即夏被商灭亡后,夏桀之子淳维率领部众北迁,发展成为后来的匈奴。
以西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士族流行的“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观念来看,铁弗匈奴王族宣扬匈奴是夏朝嫡系后裔的举动有利于维护其政权的稳定。当时,大夏辖境内除了铁弗匈奴人外,其根基之地幽州地区主要活动着鲜卑、丁零、乌桓、氐、羌、汉等不同族属的人群,新占领的关中、岭北地区主要是氐、羌、汉等各族的活动区域。这些不同族属人口中,除部分鲜卑、杂胡因为较早接受了铁弗匈奴的统治,对大夏政权较为认可外,其他很大一部分人口或者是在战争中掠夺来的或者是在扩张统治区域过程中控制的新降户。这些人群多非自愿接受大夏统治,特别是关中和岭北地区经常发生叛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赫连勃勃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以“朕大禹之后”的身份,提出了“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1](卷130P.3205)的口号。这一举动既宣扬了“华夷同源”的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夷夏之辨”对巩固政权的不利影响。
此外,铁弗匈奴“大禹之后”的族源叙事模式也与北方地区各民族文化交融密切相关。铁弗匈奴活动的朔方地区是农牧交错地带。从南匈奴依附东汉开始,匈奴人已经习惯了在此与汉族人口共同生活,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这里经历了从碰撞、冲突到并存、交融的发展过程。赫连勃勃为代表的铁弗匈奴人在此过程中,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很深,对于“正统”“大一统”观念的认同逐渐增强。比如在政权建设方面,大夏吸收传统中原职官制度,设置三公、三省及御使台。赫连勃勃大量任用汉族文臣,史称“以王买德为谋臣,拔之羁旅,以皇甫徽为记室,玩其文辞”(7)参见缪荃孙《夏百官表》,本书编委会《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4077页。。大夏以汉字为官方用字,“大夏真兴”钱、“大夏龙雀”刀都是用汉文刻字,《统万城铭》《北凉盟书》均用汉文书写而成。赫连勃勃将铁弗王族姓氏改为“赫连”意在凸显“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征赫实与天连”[1](卷130P.3206),表明大夏统治的合法性。“大夏”国号的确定也强调了对夏朝正统的承袭,而国都取名“统万”,也体现了国主赫连勃勃“统一天下,君临万邦”[1](卷130P.3205)的大一统思想。可见,在当时的北方地区虽然多民族交错杂居,各种文化并存,但各族对汉文化的吸纳已然成为一种趋势。正是在文化交融基础上,才有了“大禹之后”的族源叙事模式。
《统万城铭》虽为胡义周、胡方回父子所写,却也是奉君命而为,具有官方性质。因此,《统万城铭》所透露出的族源信息反映了以赫连勃勃为代表的大夏政权统治阶层真实的情感和思想活动,即希望以大禹之裔、匈奴之后的身份来叙述铁弗匈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并通过选择、规范族源叙事兼顾族体利益和政权利益,实现两者密不可分的链接。大夏政权建立者赫连勃勃对“华夷同源”理念的提倡和“大一统”思想的积极践行,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君王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二、拓跋鲜卑与黄帝之裔
拓跋鲜卑是北魏王朝的建立者。《魏书·序记》开篇即追溯拓跋鲜卑的族源,以寥寥数语交代了鲜卑的族源以及“拓跋氏”从传说时代到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2](卷1P.1)
《魏书》书写时,史料来源多据北魏时期已完成的邓渊的《代记》、崔浩的《国书》以及高允、李彪、邢峦、崔鸿等编著的当朝起居录。其中《序记》的内容多出自邓渊的《代记》。而《代记》中的北魏早期历史当以《代歌》为本,对于这个问题,田余庆先生有过详细的论述[3]。《魏书》卷109《乐志》记载《代歌》为北魏宫廷音乐,其内容“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2](卷109P.2828),可见《代歌》中确有可能提及拓跋鲜卑早期历史。遗憾的是《代歌》歌词失传,其真实内容无法确知。而《代歌》在北魏时期也并非完本,邓渊是授命集辑《代歌》的主要人物,也就是说北魏时期经邓渊整理辑录的《代歌》也当有所本。按照《魏书·序记》的记载,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记述来源于“人相传授”。然而若非乌洛侯使者的报告,北魏皇族尚且不知在大兴安岭北段有鲜卑旧墟的存在,民间却能口传更久远的昌意、始均、女魃、田祖等人名和远祖史事,显然这段“拓跋氏”早期历史的文字记载并非来源于“人相传授”。
查昌意、始均、女魃来历,可以探寻《魏书·序记》开篇来源。昌意,最早见于先秦史籍。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昌降处若水。”[4](P.349)先秦古籍中这样的记载有很多,如《鬻子》说“黄帝正妃曰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颛顼,为高阳氏”[5](P.60)。《史记·五帝本纪》即采用了这一说法,《索隐》进一步注曰:若水在蜀地,昌意娶蜀山氏女昌仆为妻,生有一子颛顼。[6](卷1P.11)关于始均,先秦文献中仅《山海经·大荒西经》一处提到“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4](P.321),但并没有文献提到始均和受封蜀地的昌意存在关系。而《魏书·序记》中提到的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的事情,在《山海经》中则系于叔均之下。《大荒北经》云:“(女)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4](P.342)这里的魃是黄帝之女,其所到之处无雨。叔均把这个事情报告给黄帝后,女魃被驱逐到赤水之北,叔均被封为田祖。但同书中叔均又是后稷之弟台玺之子[4](P.320),按照传说中的世系,他是黄帝曾孙帝喾之孙,和黄帝之孙始均不应是同一时代的人物。以上《山海经》所记述的传说在时间上本身就比较混乱。《魏书·序记》将这些传说黏合在一起,对其中的部分内容做了节选和重新整理编排。因《山海经》所记始均为黄帝之孙,所以《魏书》将他记作昌意之裔,而始均无他事可载,故将叔均的故事录于始均之下。叔均之后的历史,《山海经》没有写,《魏书·序记》自然也无从书写,故记作“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
考虑到前文邓渊辑集《代歌》之事,则编写拓跋鲜卑族源及早期历史的工作,最有可能是由邓渊来完成的。而关于拓跋鲜卑族源和早期历史的内容得以保存下来,显然是得到了拓跋鲜卑皇室的认可。在上古时代众多的神话传说中,史家们选择将鲜卑的历史系于黄帝—昌意—始均一脉,这其中除了因为这一显赫的身世既可为政治、文化服务又契合了当事者追求正统的思想之外,还可能与《山海经》中所记“始均生北狄”所体现的北狄出于黄帝一脉这样的观念有关。
《魏书》有对“拓跋”一词的解释说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2](卷1P.1)《北史》沿袭了这一释义。尽管有学者对此释意提出了怀疑,但没有证据表明,北朝时期的拓跋鲜卑人对这一解释有过质疑。另外,按照《魏书》卷23《卫操传》的记载,拓跋猗去世时,卫操为其立碑颂德,其中就提到“魏,轩辕之苗裔。”[2](卷23P.599)可见早在代政权之时,已经有了拓跋鲜卑是黄帝之裔的说法,卫操作为西晋旧臣主动提及这一说法,说明至少在当时这一说法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至于刻文中出现“魏”的称呼,大概是因为史家在为卫操作传时,北魏已经建立,且猗已被北魏皇室追封为“桓帝”。除此之外,《白虎通·号》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7](卷2P.60),而《晋书》记载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1](卷108P.2803)。可见慕容鲜卑也认为他们是黄帝的后裔。显然,无论是慕容鲜卑还是拓跋鲜卑,在对族源进行追溯时,都表明鲜卑与黄帝存在某种关联。
事实上,关于鲜卑的族源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学界主流观点认为鲜卑源于东胡,此观点源出文献记载,同时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当无疑窦。就文献反映的信息来看,东胡在西周时期出现于人们的视野时,已经活动于燕北地区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不可否认,在此之前,东胡必然经历了若干年的发展历程,而这些具体的历史已不为人所知。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是从何而来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大致有屠何说、山戎说、土方说、通古斯说等。其中土方说和屠何说可合为一说。据金岳先生考证,屠何与夏商时期的土方有关,东胡可能源自土方,土方主要活动于两土河(老哈河、牤牛河)流域,而古东胡也世居两土河之间的紫蒙之野[8]。又《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记载黄帝曾孙高辛氏少子曾经在紫蒙之野活动,亦号曰东胡(8)参见李昉等《太平御览》卷121《偏霸部·前燕慕容廆》,中华书局,1985年,第583页。。此信息与“始均生北狄”等文字分别被载于不同时代的汉文史籍中,至少提供了一种信息:在鲜卑人强盛时期,他们在对族源的追溯中有过这样的联系,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当时的历史书写者所认可,因此鲜卑是黄帝后裔身份的叙事模式才得以记录并流传。
汉文史籍的记载虽受史官主观想法、政治塑造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经得起推敲的,也有好多事例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因此古籍之中多处提到的北方民族与黄帝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如同华夏族通过熟知的神话传说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裔一样,当时鲜卑人记忆中的传说时代也可能与黄帝有关。拓跋鲜卑在族源认定上倾向于“黄帝之裔”正与鲜卑的这种历史观有关。北魏建立后,称东晋为“僭晋”,将南朝视为岛夷,主张“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2](卷62P.1394)。孝文帝三次南征,有“南荡瓯吴,复礼万国”[2](卷7下P.185)的志向。北齐魏收编修国史,也以北魏为“诸夏”和“中国”之本。这种北魏即“中华”,北魏即“中国”的政治主张和举措都反映了拓跋鲜卑自认华夏、主动融入“中华”体系,并力争担当传承“中华”统绪之责的决心和政治目标。
三、柔然与“光复中华”的口号
3世纪末4世纪初柔然出现于阴山南北,5世纪初建立了横跨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6世纪中叶柔然政权被突厥灭亡。关于柔然的族源问题,仅南北朝时期的相关记载就各不相同。
《魏书》《北史》认为柔然是“东胡之苗裔”,同时两书还提到柔然自认为“先世源由,出于大魏”[2](卷103P.2299),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北魏朝廷的认可。可见,北魏和柔然政权官方均认为柔然与鲜卑同源。然而在《魏书·蠕蠕传》同卷中,魏收在阐述个人观点时又称“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寻”[2](卷103P.2323)。而记录南朝历史的相关文献又有不同说法,如《宋书》认为柔然是“匈奴别种”[9](卷95P.2357),《南史》《梁书》记载大同小异。《南齐书》卷59《芮芮虏传》记载柔然为“塞外杂胡也”,但在同卷中又提到“芮芮、河南,同出胡种”[10](卷59P.1023)。这里的“河南”指的是吐谷浑,吐谷浑与鲜卑同源有明确的记载。从上述可知,不仅不同文献之间的记载有出入,像《魏书》《南齐书》在同一史籍不同卷次的记载中也有前后不一致之处。这种分歧和混乱与柔然早期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各家史书记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有关,同时反映出与柔然政权同时并立的北魏和南齐,对柔然族属信息所知也是有限的。
柔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世纪后期。始祖木骨闾在拓跋力微末年时为拓跋鲜卑的奴隶,后免为骑卒。大概在建兴三年(315)以后,木骨闾因军事失期当斩,于是集合百余人逃亡到了纯突邻部。木骨闾此次军事上的“失期”,不会只是他个人的行为,和他一起逃亡的百余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们都是拓跋鲜卑中地位较低的奴隶或者士兵。至于这百余人的族属身份并无记载。从柔然早期的历史发展来看,他们曾经接受拓跋鲜卑的统治并且是从拓跋鲜卑中分离出去的,可见早期柔然人长期与鲜卑人共存共生,甚至自身可能为鲜卑人。因此《魏书》记载柔然为东胡后裔的说法当是以木骨闾和这百余人从拓跋鲜卑中出逃事件为依据的。
而《宋书》《南史》《梁书》记载柔然与匈奴有关,但并没有提出实质的证据。《宋书》中用了“匈奴别种”的表述,即柔然是从匈奴部族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发展的一个分支。柔然曾长期占据匈奴故地,即使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前,柔然所依附的各部落中也有很多匈奴人口,因此柔然部众中存在匈奴血统的人口当是没有问题的。柔然族源的另一种观点“塞外杂胡”与“同出胡种”同时见于《南齐书》中,“塞外杂胡”中的“胡”更倾向于匈奴,而“同出胡种”因与吐谷浑有关,则与东胡关系更大,可见《南齐书》所指“胡”并非明确的指代某一具体古族,而是指柔然之前北方草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南齐与柔然关系较为密切,双方互派使臣,有国书往来,且两个政权无实际利害关系,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南齐对柔然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南齐书》也只记录柔然为“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柔然族属的复杂性。
实际上,单从木骨闾从拓跋鲜卑中逃离出去这一事件是无法判定他本人的族属的,至于和他一起逃亡的其他百余人的族属成分更无从知晓。史书明确记载木骨闾儿子车鹿会时期始有部众,自号“柔然”,这些部众可能包含了先前和他父亲一起逃亡的百余人,但绝不仅限于此,还应包含了当时草原上分散的、力量相对较小的各种“胡”。至于《魏书》所记载的阿那瓌言“先世源由,出于大魏”,显然是针对柔然王族而言的,即其先祖木骨闾曾经是北魏人。而柔然部众早期的血缘世系和历史发展脉络是比较模糊的,如曹永年先生指出的那样,“柔然部根本就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部落组织的自然发展”[11]。《南齐书》将柔然记录为“杂胡”“胡种”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而即使是记录柔然“出于大魏”的《魏书》和《北史》,在史家的评述中也不得不指出,“魏晋之世,种族瓜分,去来沙漠之陲,窥扰鄣塞之际,犹皆东胡之余绪,冒顿之枝叶。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寻”[2](卷103P.2313)。
在柔然族源问题上,北朝时期出土的墓志中还有另一种叙事模式。北齐时期南迁的柔然人称他们的祖先“始则分源白帝,终乃光宅幽都”[12](P.421),“夏有淳维,君其苗裔”[13](卷11P.269)。这种族源叙事上的关联是北朝后期南迁柔然人的个人行为,还是柔然政权时期统治阶层存在这样的观念并对柔然族源进行过类似的叙述,目前无法确知。但是从柔然政权给南齐的一份国书中可以发现,尽管柔然的政治中心远在蒙古高原鹿浑海(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侧的乌吉淖尔)一带,但其与进入黄河流域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也受到了中原正统观的影响,并明确提出了对“中华”认同的思想(9)曹永年先生较早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参见曹永年《关于柔然自号“皇芮”并宣称“光复中华”——兼论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俱僭大号,各建正溯”的潮流》,载《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刘宋升明二年(478),刘宋派遣使者王洪轨出使柔然,约期共伐北魏。次年,柔然按照约定发兵30万南侵。其时恰逢南朝朝代更迭,萧道成迫使刘宋顺帝禅让,刘宋灭亡,因此柔然与刘宋这次“共伐魏虏”的约定未能实行。南齐建元二年(480)、三年(481)柔然两次遣使南齐,再次相约共伐北魏。柔然国相邢基祇罗回在此期间出使南齐,并递交柔然国书。这份国书的内容保留在《南齐书》中。
昔晋室将终,楚桓窃命,实赖宋武匡济之功,故能扶衰定倾……今皇天降祸于上,宋室猜乱于下。臣虽荒远,粗窥图书,数难以来,星文改度,房心受变,虚危纳祉,宋灭齐昌,此其验也……陛下承乾启之机,因乘龙之运。计应符革祚,久已践极,荒裔倾戴,莫不引领。
皇芮承绪,肇自二仪,拓土载民,地越沧海,百代一族,大业天固。虽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治兵缮甲,俟时大举。振霜戈于并、代,鸣和铃于秦、赵,扫殄凶丑,枭剪元恶。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永敦邻好,侔踪齐、鲁。使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岂不盛哉
在这份国书中,柔然首先承认南齐代宋是顺应天命、应运而生,在表达了对南齐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后,话风转向国内,自称“皇芮承绪”(南齐称呼柔然为“芮芮”)。这个称呼显然是与刘宋先前提出的“皇宋属当归历,受终晋氏”[9](卷95P.2338)相比肩的,意在表达柔然也继承了皇统。对于如何解决其中的冲突,柔然方面提出了“吴汉殊域,义同唇齿,方欲克期中原,龚行天罚”。这里柔然将天下分为吴、汉两地,南齐占据的区域为吴地,北魏占据的中原为汉地,柔然承认南齐是天命所归、合法的吴地统治者,而占据中原的北魏则是不合时运的“凶丑”“元恶”,所以柔然约南齐共同出兵驱逐扫平北魏,然后“皇舆迁幸,光复中华”。这份国书反映了柔然对其政权的定位是接续正统中原政权,并与南朝并列,认为由柔然统治中原、南齐统治吴地,双方永敦邻好,才是“四海有奉,苍生咸赖,荒余归仰”的统治秩序。这与北魏大臣主张的“惟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2](卷62P.1394)的观点如出一辙。国书内容体现了柔然贵族有较高的儒学文化修养,他们提出的“光复中华”的口号表明柔然受中原正统观思想的影响并不逊于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北方各族。除了这份文书上的申明之外,柔然政权在漠北地区实行年号制度和设置中原职官名号可看作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
综上,铁弗匈奴、拓跋鲜卑、柔然等族均将本族源流归入华夏谱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十六国北朝政权林立的政治环境中争取正统、巩固统治,但从中也可看出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心向华夏的思想倾向,构建统一的中华正统政权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魏晋以来,类似于这样的族源叙事模式较为普遍,比如独孤部后人认为他们是东汉光武帝之子沛献王的后代,其先祖因战败亡入匈奴,被单于封为谷蠡王,号独孤部[14](卷75下P.3437)。宇文部人在建立北周之后,追溯祖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15](卷1P.1)。这些族源叙事中的“华夏认同”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性、代表性,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对“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和对“中华”的政治认同,这种思想认同既是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驱动的结果,也是“华夷”走向一体的重要推动力,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