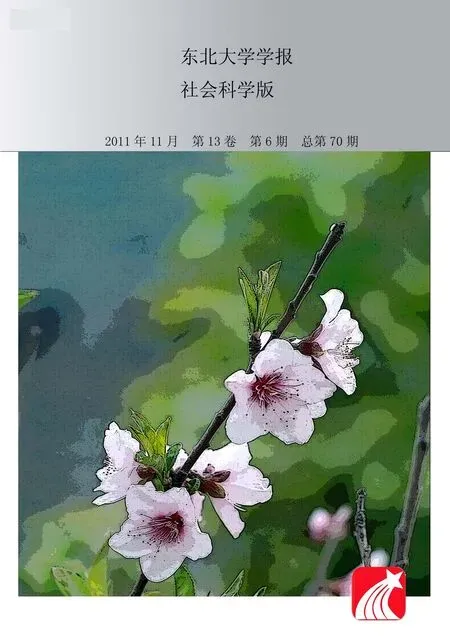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王欢明,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回潮现象,挫折和反复把公共服务改革置于风口浪尖之上,对市场化改革的怀疑和否定日益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显然,社会现实已向学术界提出严峻的挑战[1],从而需要有更多的力量研究公共服务治理问题。兴起于20世纪末的网络治理是当前国外公共服务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对其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研究和理解,可为我国当前公共服务管理面临的问题提供参考。
一、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研究
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中,伴随政府职能转型,公共服务治理的路径已从管制型和经营型向网络治理型发展,其理论基础也从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向公共价值管理演进。后一种理论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前一种理论缺点的改进,例如,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无效率作出的回应,公共价值管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狭隘的市场功利主义特征的反应。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缺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思考新的方式来推进公共服务改革,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网络治理及其相关理论引起了广泛关注。
1.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概念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出现是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变革为基础,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埃格斯[2]认为网络治理是第三方政府、协同政府、数字化革命和公民选择四种有影响力的发展趋势的集合。第三方政府意指利用私人公司和非营利机构从事政府工作;协同政府是从顾客—公民角度考虑,采用横向“协同”政府、纵向减少程序的做法;数字化革命是指技术上的突破大大减少伙伴间的合作成本;公民选择是指希望增加公共服务选择权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网络治理既包含高度的公私合作,又意味着政府强有力地对公私合作网络的管理,并在服务运行方案中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是跨界合作的最高境界。
在已有文献中,网络治理概念十分广泛,其他公共管理研究者也将其称为合作治理。Calanni[3]认为合作治理作为政府的一种战略,在公共服务传递过程中将政府机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这种解决途径是建立在审议协商的基础上,而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方式。公共服务合作的过程是各方组织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从而能够开发多种方案来解决单个组织无法处理的问题。合作治理的路径可能横跨一个或多个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包括政策的形成、执行、评价和反馈,在这种意义上,其超过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强调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Shui-Yan T.等[4]将合作治理定义为:针对公共政策问题,建立、掌舵、运营、监管跨组织的安排,这些问题是单个组织不易解决的,这种安排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和自愿参与形成的正式自治实体。从这一定义可看出,合作治理不同于纯市场中依靠经济交换和竞争实现的交易,也不同于仅仅是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而是充分将政府合作与市场委托代理相结合。
虽然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在概念方面尚未形成一致共识,但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即网络治理是相互依赖的结构,涉及到多元化主体组织,政府机构起着领导作用;存在某种程度上正式和非正式的结构稳定性;目的是为了通过各个组织合作的形式,相互依赖和信任,共同完成一致的集体目标。网络组织,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而不是偶然因素或机会主义组建的[5],其作为一种正式组织对于实现集体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网络成员自发组织或是授权建立的团体,均是通过最大努力来建立合作。其一关键特征是组织结构将其控制权力划分给各个相互依赖的权力中心[6],也就是网络组织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主体,从而使彼此之间相互制衡,这种多元权力中心能够汇集众多智慧进行决策;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引入了各主体独立的前馈—反馈交流和控制机制,网络治理可以根据其需要允许各种成分的组成,包括员工、顾客、供应者等,让其扮演组织如何发展和控制的角色,这也是达到网络组织自我治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2. 网络治理的指导理论:公共价值理论
虽然网络治理理论提出了许多公共服务的解决框架,却没有一个简洁有力的概念表达其核心诉求,以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新公共服务的“公平”以及新公共管理的“绩效”相区别。如果网络治理理论要继续巩固其优势地位,就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一需求之下,对公共价值的讨论越来越趋于热烈[7]。公共价值首先由马克·莫尔 (Mark H. Moore)[8]提出,他认为公共服务的最终目的是给社会创造公共价值,其已成为指导政府活动、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传递的一种新理念。
由于公共价值一词比较抽象,目前对此尚无一致的定义。Kelly & Mulgan[9]等认为公共价值由三大块组成:服务、结果和信任。服务,只是作为政府传递给公民公共价值的一种载体,使公民能够得到公平、平等的价值;结果,是指公共服务给公民带来的社会效益和影响;信任,作为网络治理的机制,在政府、企业和公民的关系中非常重要,是合作传递公共服务的关键。此外,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10]也给出了理解公共价值的四条建议:第一,与经济学家推崇的市场干预导致的市场失灵相比,政府干预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为了寻找公共价值;第二,在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中,有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被授权参与,实现共同的目标;第三,采用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进行公共服务采购,但需考虑公共服务伦理;第四,在网络治理中需要管理者采用适应性和学习性的态度来实现公共价值。从上述对公共价值理论的理解,可认为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理论更多的是反映公共价值的内涵,公共价值需要政府的介入,为公众提供集体偏好,反映的不仅仅是新公共管理强调的绩效,而且还包括传递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审议、信任、平等程序。
随着该理论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将其称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10-11],这就需要将其与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和新公共管理范式进行比较分析,更加突出其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管理范式的比较

续表1
从表1可看出,公共价值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相比:在目标层面,具有多重目标,不仅需要完成集体目标,还需组织成员创造、维持彼此间的信任,对公民的集体偏好进行回应等,而不单是组织的绩效;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集合利益相关者合作,进行审议和协商,注重政府的政治推动力,而不仅是市场激励和行政力量;在责任设置中,存在多重责任,成员间彼此依赖和监督。
二、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结构和机制
从结构功能主义和政府治理工具的视角看,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被看成是一种有意识的组织设计,形成了一种有异于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治理结构,Ostrom[12]曾认为公共服务的集体行动取决于信任、互相依赖、互惠等因素,这些都是网络治理结构和机制所须考虑的。
1. 治理结构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意味着需要创立治理结构,能允许网络参与者在解决集体行动时进行联合决策和合作,以及怎样决策和合作,即谁来作决策、哪些行动是允许和限制的、需要提供什么信息、成本和收益如何分担等等,这也是网络成员必须理解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学者K.G.Provan & P.Kenis[13]提出了三种基本的网络治理结构模式,分别是共享治理(shared governance)、领导组织(lead organization)、网络行政组织(network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NAO)。共享治理涉及到所有网络组织成员,通常采用小型、多公司联盟和伙伴关系,参与者自主处理内部管理事务和与外部组织的联系,只有通过所有成员平等地参与才能完成集体目标,当共享治理形成后,网络层面的决策权利是对称的,理论上没有哪个成员能代表共享治理的集体。但有很多情况下不存在这种扁平化情况,尤其是共享组织治理的无效率意味着需要更加集中的途径进行治理,这可称为领导组织。在该模式中,主要的网络水平活动和关键决策都是由单一参与者进行协调,其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高度集权化,拥有非对称的权力,存在独裁管制倾向。在这种环境下,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实体来治理网络,即网络行政组织,其在合作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同于领导型组织模式,是一种扁平而非集权化的组织。上述三种基本治理结构引起了关注,其他学者也分析了与其类似的治理结构,R.Birner等[14]在研究危地马拉森林治理的过程中,认为成立的组织Instituto Nacional de Bosque(简称INAB)是一种网络治理结构,INAB是政府委托授权由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组成的独立机构,这些成员分别代表财政部、市政委员会、教育研究机构、伐木工业组织、环境NGO,这些成员都是选举出来的,任期两年。他们不仅是监管的实体,而且还是管理机构,其委员会每月至少召开两次会议,农业部长作为该机构的主席,跟其他成员一样也只有一票。这样INAB就是一个由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组成的伙伴关系。INAB的两大制度特征就是授权和合作,政府通过授权给INAB,使得INAB在法律层面具有决策、执行和监管的自治权力,同时强调各成员间的合作,不是由政府单一决策,这样增加了执行结果的可接受性。从INAB的治理结构分析可看出,其与上文的NAO治理模式相类似。
综合上述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结构的研究可发现:首先,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包括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公民代表等,形成相互制衡的权力中心;其次,网络组织具有自治性,其决策、执行、监督等环节均是建立在成员审议、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实现该组织的共同目标;再次,网络成员间的互相依赖性,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囊括在决策层,目的是为了借鉴彼此的优势资源,实现单一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
2. 治理机制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运行机制,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行政机制,以及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市场价格机制,网络治理采用的是商议和信任机制,这两者是网络治理正常运转的基础,缺一不可。
(1) 商议机制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涉及到多元化主体,单靠政府机制或市场机制无法完成共同目标,需要通过商议机制的安排,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Denhardt Robert & Janet Vinzant[15]认为公民参与的商议机制是公共服务传递的核心。T.L.Cooper等[16]在研究以公民为中心的公共治理进程中,认为商议机制比选举、信息交换等更有效,此外,商议最能够实现公民信任,提高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曾经指出了协调的四种形式,即多头政治、科层、协商和市场。其中,多头政治指的是民主代表的形式,人们以此来制约政治领导人的行为;科层主要指的是官僚组织的中心协调;市场则依靠价格机制来促使人们的行为相互调适;协商则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商议形成互动来调整行动者的行为[17]。在本文研究中,商议就是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所指的协商过程,也是协调网络成员各方和整合利益的过程。一些学者认为商议协调机制不同于互补效应,互补效应是由于资源上的互相补充而造成的效应,而商议协调是通过相互的合作而导致的1+1>2的效应[17-18]。在公共服务网络治理中,各网络成员因为资源互补效应而相互合作,但是需要通过商议机制才能使合作取得成功。
(2) 信任机制
如果各成员间在合作之前就有敌对或冲突,那么在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时,信任就是最重要的过程,也是最难的培养过程。可以说信任是网络治理的必要条件,但在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文献中,缺少信任研究,更多的是研究监管机制,但随着网络治理的兴起,对信任机制的研究显得非常重要。J.Edelenbos & E-H.Klijin[19]认为在复杂的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有三个特征:第一,自愿性,当彼此相互信任时,就处于一个开放和自愿的地位,期望其他合作者能克制机会主义行为,相信能在相互交往中考虑彼此的利益;第二,风险性,在一个无法预测和存在风险的情境下,信任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缺少信任并且存在风险,大多数联合行动会被取消;第三,期望性,信任是对其他合作者有积极期望,能降低无法预测性、复杂性和模糊性。
在公共服务网络治理中,商议和信任机制使各成员间的合作更加流畅。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运行机制相比,商议和信任机制能够比监管机制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因为商议和信任能够加强对合作者的预测,减少机会主义行为。Ostrom等认为信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机制,其能够通过顺利地和有效地分配资源来降低交易成本[20]。在商议过程中,专有信息能够共享,并且信任程度越高,就会有更多的人希望共享和交换信息,从而越能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三、 国外公共服务改革理论与实践
对网络治理的理论研究,目的是引导公共服务改革,提高服务效果,实现公共价值。传统上政府是通过垂直权力或是横向合作来传递公共服务,这样能够提高效率、明确责任界限,但是面对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社会事务时,仅依靠垂直管理或是横向合作就显得不能胜任。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治理成为西方各国公共服务改革的首选,并基本通过政府、企业和公众参与等环节来实施。
澳大利亚政府在其改革蓝图中明确以人为本原则,改革措施包括:第一,加强政府与公众、私人部门横向联合。在公共服务传递过程中依据环境情况给予私人部门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充分发挥公民和社区的作用,政府的职责是安排简明的合同条款和监控。第二,加强包括州政府、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合作。这种合作能够整合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员工团队,以一种联合的姿态来传递公共服务,彼此间共享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及时向公众公开。第三,进行公民满意度调查,了解公众对公共服务传递过程中的态度和反馈信息,为服务的改善提供依据[21]。
英国是“整体政府”改革的首倡国家[22],其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组织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协同,主张政府管理从部分走向整体。同时也将公私合作、公民参与等方法结合起来,力图打造世界级(World Class)的公共服务水平[23],这在内涵上已经走向了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模式。
美国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盛行的国家,大量的学者以美国各州、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经典的理论著作,例如《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从对美国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发现,提供公共服务的网络关系包括联邦—州政府、州—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包括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私人部门间的契约、管制等多种形式,并且在公共服务的决策、执行过程中吸纳了多层次的公民参与。例如自2001年发生恐怖袭击后,美国就将反恐战争界定为:政府各层级的执法机构和私人保安公司、商业和工业、市民协会及其他许多组织间的协作[24],从而形成一种网络组织模式来提供国防安全服务。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在对各国“整体政府”与公私合作等改革理论与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形成了一种直观和形象的网络治理模式,如图1。

图1 网络治理模式的形成图
从图1可发现,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是两条路径的合成,即政府间横向合作的权力线和公私合作的纵向执行线的合成。自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治理模式先后经历了科层管理—政府外包—协同政府三阶段,但在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自的问题,而网络治理的运用,可以弥补科层管理缺乏灵活性、政府外包缺少公平考虑、协同政府忽视公民参与的缺陷。
四、 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通过上文回顾可知:虽然各国存在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但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时采用的策略和制定的政策具有共性,即采取网络治理模式来安排公共服务,目的是实现公共价值。但网络治理实现需要一定的基础,这是政府内部机构整体性运作以及政府与社会各类组织联手的需要,具体来讲分为三个:第一,政府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公众最需要的公共服务;第二,一些公共服务需要跨部门合作才能解决,而不是单一政府机构的功能所能处理的;第三,为了解决这些公共服务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各类组织共同合作[22]。因此对于人口基数大并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我国,在面临严峻的公共服务治理问题时,需要从国外治理研究和实践中获得借鉴,思考如何构建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网络治理模式,具体分析如下:
(1)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正逐步走向网络治理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的是为了提供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由于我国的行政体制不同于欧美国家,过去主要集中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现在通过改革,逐渐走向网络治理模式。一方面,政府积极推行大部制改革,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合协同;另一方面,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引进社会资本,并出台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推行政府与市场的合同制形式。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公民社会的逐步成熟,我国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模式将会逐渐完善。
(2) 网络治理,关键是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和体现治理机制
首先,多元主体包括服务接受者、安排者和提供者,三者的内在结构联系表现出三方面的责任关系:其一,在服务接受者与安排者的关系中,扩大服务接受者在政策制定中的发言权,需要有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手段来推动,改变单纯依赖政治精英、学术精英、财富精英的决策方法。其二,使服务接受者能够监督和规范提供者,维护自身的权益。在我国,公共服务也面临着打破垄断、增加竞争的问题,需要加强政府与市场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服务供公民选择。其三,加强对服务提供者的激励,使之服务于接受者,合理地安排契约形式。我国公共服务的网络治理需要加强各主体间的磋商与合作,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
其次,网络治理强调各主体间的商议和信任机制。在制定政策和出台措施时须本着互信的原则,积极吸纳各方意见,反映不同主体的利益,从而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只有这种商议和信任机制的实施,才能使得各方合作能够持久和连续。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合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 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实现是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过程
我国在网络治理中,可从问题的决策阶段—执行阶段—评价阶段三个环节来改革。在决策阶段,应该吸纳服务接受者,使公众从深度和广度上增加发言权,从而在决策时就能考虑公众的利益,避免公共价值被扭曲;在执行阶段,建立治理结构(治理实体)和合作治理机制,需容纳除政府机构之外的社会其他相关组织,同时对合作各方的收益和风险需要有全过程的反馈调整;在评价阶段,其理念应是提供社会满意的服务,由此可建立绩效评价公式为:
公共服务绩效=社会满意的服务=
(社会满意的服务/产出)×(产出/投入)×投入=
公众满意度×技术效率×投入
从中可看出,公共服务绩效可从政府投入、运营效率和公众满意度三方面衡量,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考虑投入和效率目标,但当前特别需要考虑公众对政府所安排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如何,或者更完整地讲,政府需要考虑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公众满意度结合的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总之,我国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核心问题是要供给社会满意的公共服务。因此一方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供给公共服务的理念和政策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我国形势,选择和改进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也是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周志忍. 认识市场化改革的新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09(3):11-16.
[2]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 威廉·埃格斯. 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Calanni J. Explaining Coordination Networks in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J]. 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2010(3):1-34.
[4] Tang Shui-Yan, Mazmanian 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ed Through Theory[EB/OL]. [2010-11-25]. http:∥ssrn.com/abstract=1516851.
[5]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18(4):543-571.
[6] Turnbull 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Network Governance of Public Assets[EB/OL]. [2010-11-25]. http:∥www.aprim.net/associates/turnbull.htm.
[7] 何艳玲. “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性范式[J]. 政治学研究, 2009(6):62-68.
[8] Moore M. Public Value as the Focus of Strategy[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4(3):296-303.
[9] Kelly G, Mulgan G, Muers S. Creating Public Valu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Service Reform[EB/OL]. [2010-11-25]. http:∥www.allamreform.hu/letoltheto/kozfeladatok/kulfoldi/public-value2.pdf.
[10] Stoker G. 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J].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1):41-57.
[11] O'Flynn J. From New Public Management to Public Value: Paradigmatic Change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7(3):353-366.
[12] Ostrom E. 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8(1):1-22.
[13] Provan K G, Kenis P. Modes of Network Governance: Structure,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ness[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18(2):229-252.
[14] Birner R, Wittmer H. Better Public Sector Governance Through Partnership with the Privator Sector and Civil Society[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06(4):459-472.
[15] Robert B D, Vinzant J.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Serving Rather Than Steering[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0(6):549-559.
[16] Cooper T L, Bryer T A, Meek J W. Citizen-centered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12):76-87.
[17] 鄞益奋.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J]. 公共管理学报, 2007,4(1):89-96.
[18] Klijin E-H. Network and Governance: A Perspective on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M]. Amsterdam:IOS Press, 2003.
[19] Edelenbos J, Klijin E-H. Trust in Complex Decision-making Network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7(1):25-49.
[20] Imperial M T. Using Collaboration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5(3):281-319.
[21] PM&C. Blueprint for the Reform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EB/OL]. [2010-11-25]. http:∥www.dpmc.gov.au/publications/aga-reform/aga-reform-blueprint/index.cfm.
[22] 竺乾威. 从新公共管理到整体性治理[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10):52-58.
[23] Cabinet Office. Excellence and Fairness: Achieving World Class Public Services[EB/OL]. [2010-11-25]. http:∥www.fitting-in.com/reports/world-class-public-services%20pdf.pdf.
[24] 罗伯特·阿格拉诺夫, 迈克尔·麦奎尔. 协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战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