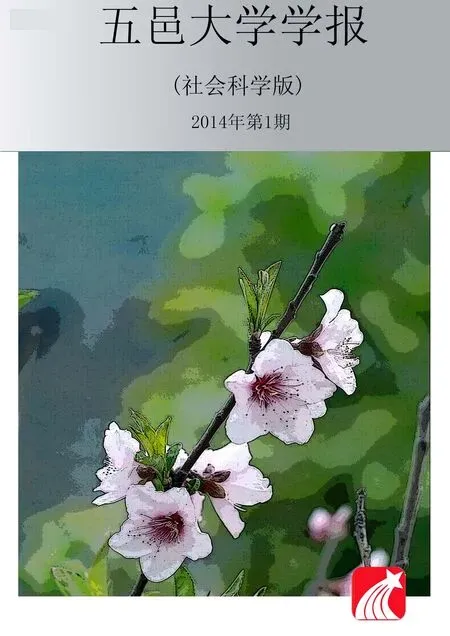岁时风俗知识的记录传统及多重记述形态
李翠叶,李 旭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钟敬文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中提出“记录的民俗学”,主张应重视各种民俗文献的记录方法。他说:“民俗是一种民众文化事象,对它的研究,不仅仅是理论考察,它的资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就关系到民俗志的问题。我把它叫做记录的民俗学。”[1]之后的学者,如王杰文的《反思民俗——关于钟敬文先生的“记录民俗学”》、高丙中的《中国民俗志的书写问题》、蔡磊的《民俗志的学术定位和书写》等,都撰文倡导和强调记述的意义。但是他们的研究,核心是创新民俗志的书写模式,以指导当代民俗学文献的写作,并没有将民俗作为一种知识,考察其记述的形式和文体特征。也有其他学者在专著中提及这一问题的,如徐杰舜主编的《汉族风俗史》、张紫晨的《中国民俗学史》、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日本学者直江广治的《中国民俗学》等,他们关心的是“记述”,而不是“记体”,并没有集中探讨岁时杂记类文献作为一种文体的体式特征,以及这种记述体例和岁时文化构建的关系。
所谓记录传统,不是指专门的记体文本,而是在岁时记体文本产生之前,附录于其他文献中对岁时风俗的记载。实质上,这种记录传统涉及到岁时民俗原来所附属的学术体系。汉魏时期,在政教风俗观、地理风俗观、民间风俗传说这三类体系下,形成了古代文献中关于岁时风俗知识记载的不同记录传统及其多重记述形态。
一、地理风俗观与地记类著作对岁时风俗的记载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记载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著作,为南北朝梁朝宗懔所撰。在这部笔记体文集中,作者所征引的文献有《风俗通》、《风土记》、《三秦记》、傅玄《拟天问》、《诗》、《广雅》共6种。其中的《风土记》、《三秦记》是汉魏新兴的地学著作。《荆楚岁时记》成书前,关于岁时风俗的记录,存在于子学文献、地记文献与志异类文献中,地理、风俗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知识性联系。
(一)地理风俗观与地方著作的产生
自汉朝开始有地方类著作,这是地理学著作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汉朝对地理的关注,最早始于对风俗的重视。汉人对风俗的理解与后世的岁时风俗不同。东汉应劭写有《地理风俗记》,同时也写有《风俗通》,他在《风俗通·自序》中言:“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2]8《汉书·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3]1640《汉书·五行志下》:“夫天子省风以作乐。”颜师古注:“应劭曰:风,土地风俗也”[3]1448。风与天气、地理、以及圣人教化有关,这本是承接《礼记》对风俗的认识:“凡居民财,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应劭亦言:“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因此对于汉人来说,他们对地理的关注,出发点实在于考论风俗。因此,称之为“地理风俗观”。
汉代专设有风俗使,“常以时分适四方,览观风俗。”[2]1《汉书·宣帝纪》:“(帝时)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3]258汉平帝派遣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3]357其对风俗的重视,盖因汉继秦之后,秦已经完成书同文、车同轨等经济、交通等基本的建设,继之于后的首要任务,即面对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多样的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统一,这种新的国家意志,促使汉代出现了大量与风俗有关的著作,如郡书、风俗传、风土记。
自汉代始,地方文献的产生,是从行政体系中逐渐演变而来,但是并不是严格的行政专属文献,因此对地理的思考,在超出政治之外,有更为细腻的观察角度。在文体上主要有郡书、风俗传、风俗记、风土记四种文体形式。这四种著作形式,展现了汉人新的地理观念。
(二)地记类文献与岁时风俗的记录体式
1.地方杂史类笔记。《三秦记》:“汉昭帝母钩弋夫人,手拳而国色,世人藏钩起于此。”《邺中记》:“俗人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甚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自作饮食祠庙,及五色缕、五色花相问遗,不为子推也。”《西京杂记》:“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到来年九月九日始熟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2.州郡地记。《临海记》:“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南岳记》:“其山西曲水坛,水从石上行,士女临河坛,三月三日所逍遥处。”《荆州记》:“父老传言,(屈)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
州郡地记与地方杂史类笔记对岁时风俗的记录体式存在区别。州郡地记主要在于存地理物象,并不对风俗行为作具体的介绍。魏晋时期,州郡地记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记述体式,即以地理物象为记述对象,总括所有关于这一地理物象的自然与人文事象,它的主体是地理。在州郡地记中,对于岁时风俗没有直接的记载,因此从记录传统的继承上看,其本身并没有对《荆楚岁时记》的成书形成一定的影响。而以地域为分类的地方杂史类笔记如《三秦记》、《邺中记》、《西京杂记》等,虽然在命名上和地记非常相似,但是它和纯粹描述地理的州郡地记不同,它以一地为记述对象,总括一地所有的事象。因此,岁时风俗在地方杂史类著作中,是作为认知一地文化的一种角度得以记载。而这种地域意识下对岁时风俗的记载,是以客观的身份形式进行介绍,有源头有辨析,并描述当时人的各种岁时行为。这又和《荆楚岁时记》中完全以行为物象为核心的记述方式不尽相同。
3.风土记。魏晋时的风土记,最早全面描写各种信仰风俗和岁时行为。晋周处《阳羡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多记载岁时风俗的书。可以将其与《荆楚岁时记》的记述体式作一个比较,如《阳羡风土记》:“蜀之风俗,岁晚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荆楚岁时记》:“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又如,《阳羡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阳羡风土记》:“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荆楚岁时记》:“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再如,《阳羡风土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弓区)。腊日之后,叟妪各随其侪为藏(弓区),分二曹以校胜负。”《荆楚岁时记》:“俗有藏钩戏,起钩弋夫人。俗云此戏令人生离,有物忌之家,废不修也”。

魏晋时,地记开始具备独立的文体形式和记述传统,对一地岁时风俗的记载并不在州郡地记中,而在风土记、地方史类杂记中。唐宋之后,地方志融合州郡地记与风土记的文体,才开始在地方志文献中出现对岁时风俗的记载。
二、政教风俗观与子部杂家类文献中岁时风俗的记录体式
自周朝建立以来,在行政体系中,就有观风以知政的“政教风俗观”,如《周礼》中的“天官冢宰”具有“礼俗以驭其民”的职守。这是中国政教理念的重要体现。汉朝政治颇重风教,地方官员具有整饬习俗的职责,简帛材料《日书》的发现,使今人对地方官员要具备的知识修养有一个新的认知。“秦汉时期官吏墓葬中《日书》与法律令(间或还有医药方)共存的这一普遍现象说明,秦汉官吏往往是精通《日书》与通晓法律两者集于一身。”[4]在官职上,设有三老、啬夫等具体职位,以风俗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
掌握、批判、纠正谬俗是汉代地方官吏的职能之一。子部杂家类文献受制于政教风俗观和地方官员“辨风正俗”的行政职能,对于岁时风俗的记录体式有记载、辨析、杂录三个特征。一是记载。《风俗通义》的成书,是地方官员的职能在文字表述上的一种展现。《后汉书》称应劭撰《风俗通义》:“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2]628,多以“世多言……”、“世俗……”等方式开端。刘咸炘:“昔之评者大都视为考证之书,推其博洽,此耳食目论也……况皇霸、声音、山泽诸篇,但有引据,罕下己意,六国一节及穷通一篇,全钞古事,但加总论,怪神一篇,记琐事而少质正,考证如此,亦何贵哉!”[2]649《风俗通义》一书,并不全在于考证,而有大量杂记汇录的成分,所谓识时俗嫌疑,首先应表现为对时俗的把握。二是辨析。岁时风俗的改变,最初引起子家的注意,形成的相关文献有应劭的《风俗通义》、王符的《潜夫论》、董勋的《问礼俗》等,在叙述体式上均是先以“世言……”记录民间俗传的内容,然后再作辨析。如《辨崇篇》:“世俗言祸崇,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迁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丝圭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2]1008这种记述方式,是受政教风俗观的影响。所谓的“正俗”,有使“俗”归于“礼”的内涵与功能。移风易俗是通过地方官吏为媒介而得以实现的。三是杂录。这些新兴的风俗,起初呈现为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生活行为,本质上只是民众在某一件事上的信仰,或是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种特殊的象征性行为,或是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因此进入到子家文献中多以条录的形式记载。
这种记录体式,是知识在新兴时零散样态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杂录描述式的语言,开创了关于岁时节俗记载的散文式语言表达方式。试比较《风俗通义》与《荆楚岁时记》。如,《风俗通义》:“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疾。”《荆楚岁时记》:“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名为天灸,以厌病也。”又如,《风俗通义》: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荆楚岁时记》:“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再如,《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不得曝床荐席。”《荆楚岁时记》:“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
将《荆楚岁时记》和《风俗通》相比较,可见这一类的语言表达在《荆楚岁时记》成书前已经在当时众多的子家文献中出现。月、日、节俗的叙述模式,在子家文献中也已经确立,这些并非宗懔首创。宗懔在写《荆楚岁时记》时,曾明引过《风俗通义》,甚至在有些条目上可以重合,那么在《风俗通义》中所采用的散文式的语体形式,要比宗懔在自序中所列出的汉魏诸赋对于《荆楚岁时记》成书的影响更大。
汉魏时期诸子渐有杂学的知识修养,杂学一脉对岁时风俗的记载体式被后来的文人笔记所承继。唐宋文人笔记对于岁时风俗的记载方式多不离这三种体式。因此学者在追溯笔记体的渊源流变时,即有将《风俗通义》作为笔记体的一种。《四库全书总目》将《风俗通义》和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宋代宋祁的《笔记》、苏轼的《东坡志林》列在一起,归为“杂家类”。
三、民间风俗传说与志异类著作对岁时风俗的记载
关于民间传说文本的定型,是经过魏晋时文人的搜集整理而成。《荆楚岁时记》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陈述,它隶属于当时新兴的民间知识。志异类文献中的岁时故事和岁时记中所记载的岁时行为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的言说和行为体系。以下录几则和岁时风俗有关的传说。《异苑》:“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续齐谐记》:“吴县张成夜起,见一妇人立宅东南角,招成曰:此地是君蚕室,我即地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我,必当令君蚕桑日百倍。言绝失所在。成如言,为作膏粥,年年大得蚕。今人正月作膏糜像此”(其他还有九日登高、上巳曲水、七夕牛女、明眼袋、五彩丝粽等)。
魏晋时期的民俗传说,和当时的《拾遗记》、《神异经》等文献相互补充,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当然,志异类文献影响的并不是《荆楚岁时记》本文的写作。确切地说,《续齐谐记》等志异类著作和杜公瞻的注是一致的。这一点说明,志异类文献和岁时风俗文献在记述侧重点上不同,一则强调岁时风俗的来源,一则强调岁时风俗行为,这形成不同的记载传统。后来唐代杜公瞻的注文正是合这两种记载传统为一体。
志异类著作中所记载的一些民间风俗行为,有一类不属于岁时风俗的范围,涉及面更为广泛,如:“轩辕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铁石……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氏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5]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它们往往记载事件的起因,并进行评论,有集注集说的功能。然而《荆楚岁时记》在写作上却表现出对“志异记”这种记录体式有意识的舍弃。
六朝时期的神异记、地记中也保存有大量的风俗传说。《玄中记》:“百岁之树,其汁赤如血;千岁之树,精为青羊;万岁之树,精为青牛。”[6]《嵩高山记》:“嵩岳有大松树,或百岁、千岁,其精变为青牛,或为伏龟。”[7]《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昭仪尼寺》载,佛堂前生桑树,京师道俗谓之神桑。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人伐杀之,“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8]这三类记体在撰写时,都根据自己的主题选择、整理各种民间知识,既有相通的地方,又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选材范围。
可以比较一下志异类文献和地记类文献、岁时文献这三种记录体式在同一岁时节日记载上的不同记述风格。地记,如《述征记》记载:“八月一日,作眼明囊,盛取百草头露洗眼,令眼明也。”
神异记,如《续齐谐记》:“弘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岁时记,如《荆楚岁时记》:“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小儿头额,名为天灸,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云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柏树露,为宜眼。后世以金薄为之,递相饷焉。”这三类记体,都是魏晋时对新兴知识范型的记载。六朝诸记之间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反映了当时知识的交错发展以及不同知识形态通过记体体式的分工而得以确立的现象。记体的繁盛,是和当时知识的进展、分化相联系的。
唐宋之后,延续六朝时的多重记录传统,对岁时风俗的记载主要存在于岁时记专著、文人笔记、地方志、杂记广记这四种文献中。第一,由《荆楚岁时记》单书形式存在的岁时记,被后人模仿,代表着新知识范型已经从原来的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形成一类以“记”命名的岁时风俗专著;第二,由六朝子部杂家类文献中的杂记形态,转变为唐宋新兴的文人笔记对岁时风俗的记载;第三,由六朝风土记中对岁时的记载,转变为唐宋后的风土记和官修地方志中的一项记述内容;第四,杂记广记类文献,是在岁时风俗广泛发展后,在唐宋后新兴的一种提炼和集合型的记体文献。这四种记体文献虽均为对岁时风俗的记录整理,但通过记述对象的更改、记载体式的变革等,发挥着不同的文体功能,建构着不同角度的岁时文化,共同形成关于岁时风俗记载的一个全方位的学术体系。
[][]
参考文献:
[1]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28.
[2]应劭.风俗通义校注[M].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8.
[3]班固.汉书[M]. 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历史研究编辑部.《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07.
[5]任昉.述异记[M].明汉魏丛书本.
[6]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八[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李昉.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三[M].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
[8]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周祖谟,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