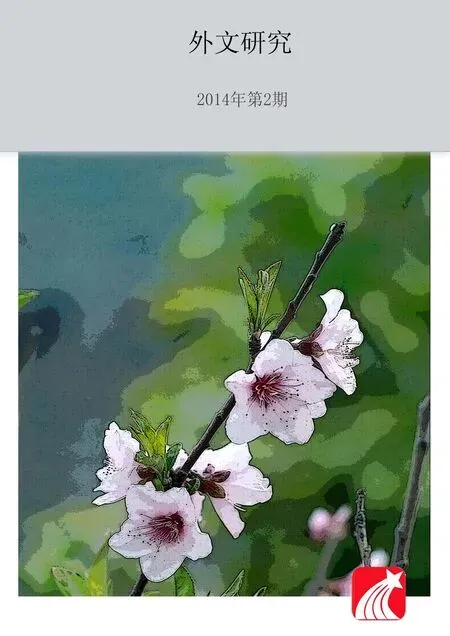层级性与汉语“双主句”、及物句的最简句法研究
——基于广义非宾格假设对“大象鼻子长”等句式的再分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马志刚
0. 引言
句子最为直观的形式特征就是其成分间的线性序列。就主语和谓语而言,“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的词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张斌 2007: 361)。基于这种线性顺序,汉语中的“大象鼻子长”和“张三喜欢自己”这两种句式可分别称为双主语句和单主语句。(杨成凯 1997: 251;徐杰 2004: 98)但这种称谓不能说明名词与谓词的句法语义关系,也不能解释为何前者的两个名词都居于谓词之前且具有领属关系,而后者的名词间则是同指关系且分别居于谓词前后。
生成语法以句法结构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比如,Chomsky(1957)就以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为例,力图说明句法结构的存在完全可以独立于其语义内容。而近期的最简句法也强调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层级性(而非线性顺序),而且谓词与论元、论元与论元之间的结构关系都制约着句子的意义解读。(Chomsky 2011)因此,基于最简句法的结构化理念对这两类句式重新加以分析,既可以从另一个视角辨析二者的句法语义属性,也有助于说明汉语句子的母语解读其实也同样受到层级性的制约。
1. 文献简析
1.1 陈述关系说
汉语语法研究通常从句法成分的功能视角来定义主语和谓语。比如,“主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谓语则对主语进行陈述和说明。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陈述和陈述的关系”(张斌 2007: 361)。但依据陈述-被陈述关系来界定主语很容易把(1a)“那些树木树身大”一类的句子和(1b)“他喜欢上海”这样的及物句混淆起来。比如,张斌就认为,“‘他喜欢上海’这句话,主语‘他’是被陈述的对象……;而谓语‘喜欢上海’则是对主语‘他’的陈述……”(张斌 2007: 361)。而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1a)类句子,因为完全可以说“‘那些树木’是被陈述的对象,而‘树身大’是对主语的陈述”。更有甚者,这种分析也同样可以推及类似于(1c)和(1d)在内的其他汉语句式。
(1)a. 那些树木树身大。 (Chafe 1976: 50)
b. 他喜欢上海。 (张斌 2007: 361)
c. 这条路人们从来都没有走过。
(张斌 2007: 361)
d. 电脑我是外行。 (徐杰 2004: 98)
1.2 话题说
Li & Thompson(1976: 480)把(2a)类句式视为汉语是话题突出性语言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区别于主语突出性语言(英语类)的主要特征。而陈平(2004: 495)则将(2a)类句式归为汉语的双项主语句,并把该类句式的信息结构分析为话题-陈述结构。
(2)a. 大象鼻子长。
b. 张三喜欢他自己。
c. 他会说三门外语。
d. 他啊,会说三门外语。
e. 大象啊,鼻子长。
f. 张三呢,喜欢他自己。
需要注意的是,言说者在构拟语句时除了估量听话者对陈述对象的了解程度外,更希望听话者能关注某个信息点。据此,仅仅把(2a)视为话题-陈述结构,而把(2b)视为陈述事实的简单句并不能充分说明两个句子的信息结构是如何组织的,因为“每一个正常的、用于交际的句子都至少有一个焦点成分”(徐杰 2004: 140)。尽管(2a)和(2b)表面上并无焦点标记可循,但二者的实际运用都肯定是为了传递某种新信息。也就是说,这两个句子除了句首名词对于听话者的熟悉度外(话题),还需要分析其用于话语交际的语用目的(焦点)。
此外,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主谓间的联系非常松散,因此在(2c)类简单及物句的主谓之间插入语气词后也可以形成合法句(2d) (张斌 2007: 361)。但这种分析使得(2a)类句式与(2b)类及物句在信息组织方面显得毫无差别,因为插入语气词后二者都可以形成话题句,如(2e)和(2f)所示。事实上,(2a)和(2b)这两类句式在论元选择、题元指派以及话语功能方面均有本质区别,而本文就力图阐明二者的差异所在。
1.3 谓素说
徐杰(2004)提出谓素分析法,认为汉语和英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差异在于INFL所具有的特征组合不同:汉语仅仅具有能把补语转化为谓语的谓素,而英语除了谓素外还具有时态和一致性特征,因此汉语的INFL可以把名词和句子都转化为谓语成分。谓素分析法可以把(2a)和(2b)类句式统一在主语的概念框架内,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但需要注意的是,自Koopman & Sportiche(1991)提出VP内主语假设(VPISH)以来,生成句法学就将其视为论元结构的公理性假设:无论是在SVO类语言还是VSO类语言中,句中所有论元均由谓词选择并在VP内执行题元指派。据此,(2a)中可被“谓素说”分析为主语的“大象”理应基础生成于谓词“长”的投射内,而非直接合并在spec-IP位置。可见,谓素分析法仅仅关注句子主语,却忽视了主语在论元结构内部理应具备的初始合并位置,更未论及其题元角色和话语功能。
上述有关汉语“双主语”句式的3种分析方案都只关注了其中主语的语法地位,而忽略了句法成分之间的句法依存关系。因此,本文将参照(2b)类简单及物句,进一步研究(2a)类句式的论元结构、题元指派及其话语功能。旨在说明,基于层级性的生成句法理念对汉语句式的分析有助于揭示出句子成分间的语义关联性及其句法实现方式,特别是(2a)和(2b)类句式在信息组织方面的差异。
2. 研究问题
2.1 领属关系
传统语法研究把(2a)类句式视为主谓结构做谓语句式中的一个次类。(王力 1985:49)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句式区别于其他句式的定义性特征就是其谓词前两个名词间具有的领属关系。比如,杨成凯(1997:251)在把(2a)类句式称为“主1主2谓”句时指出,如果“这棵树叶子大”为真,那么“这棵树的叶子大”也必定为真,因为其中的“主1和主2之间有领属关系,而且有可能把主1看成主2的定语”。仅就语义解读而言,(2a)和(2b)类句式中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为方便对比,如下将〈2a〉重复为〈3a〉;将〈2b〉重复为〈3c〉。):
A. (3a)类句式中谓词前两个名词间的领属关系在句法结构上是如何实现的?为什么汉语母语者不会把(3b)类句子中谓词前的两个名词也解读为领属关系?
B. (3c)类句式中谓词前后名词间的同指关系是否也受到某种结构关系的限制呢?汉语母语者为什么不会把(3d)类句子中谓词前后的两个名词也解读为同指关系呢?
(3)a. 大象鼻子长。
b. 今天我们讨论《离骚》。
c. 张三喜欢他自己。
d. 张三欺骗了李四。
2.2 话语功能
从句子使用的话语功能来看,一个句子可以没有话题,但不能没有焦点,因为任何句子的使用必定都是为了传递信息:要么提供未知信息,要么凸显某个已知信息。Rizzi(1997)提出,用于交际的正常句子必定具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焦点,而徐杰(2004: 140-143)认为,汉语句子中可以存在强式焦点和弱式焦点。据此,针对(3a)和(3c)类句式可以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C. (3a)和(3c)类句式在即时产出时所传递的信息在话语功能方面有何异同?具体而言,其中焦点成分的存在是为了提供新信息还是为了凸显对比性?
D. (3a)和(3c)类句式中,承载焦点的成分在句法结构中是如何实现其焦点化的?具体而言,这两类句式是如何获得其线性的表层语序的?其焦点化是否经由移位操作实现?
目前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未涉及上述4个研究问题,但从生成语法的视角看,这4个问题既考虑到谓词与论元之间的选择关系和题元指派,也讨论了信息结构在句法层面的实现方式,因而都是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问题。下面先简介生成句法的局域性原则和约束原则对语义解读的限制作用,然后提出本文的分析方案。
3. 成分统制的非对称性与语义解读
3.1 局域性原则、广义非宾格假设与领属语义的解读
生成句法学力图构建的语法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其基础性假定是任何语法操作都受制于一套内在于人类心智中的普遍语法原则,因而可以解释母语语法缘何得以在极短时间内以几近一致的方式完美习得。而局域性限制(Locality Constraint)就是诸多普遍语法原则之一。其主旨为:自然语言的语法操作和语义解读都应该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执行。目前最简句法中频繁讨论的移位、一致、格赋值等句法操作以及句法操作应尽早执行的“尽早原则”(Earlyness Principle)均在局域性限制下执行,(Chomsky 2013)而(4a)和(4b)则说明领属语义的解读实质上也是在尽早原则和局域性原则的限制下实现的。下面结合图示予以说明(其中的Pred指代谓词)。
(4)

基于最简句法的操作,谓词投射的中心语均有相应的轻谓词,(Larson 1988)因此(4a)和(4c)这两种句式的中心语X都有其相应的轻谓词x,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在于是否具有外论元。依据Burzio(1986)提出的Burzio定律:能够给补语指派宾格的动词必定具有施事论元,而Chomsky(2008: 145-147)近期也主张,具有施事(或经验者)外论元的轻动词可以给实义动词传递一致性论元特征,进而使后者能给其补语指派宾格。可见,(4a)和(4c)这两种句式是否具有施事外论元的区别实际上可以体现在谓词能否给其补语指派宾格。依据Perlmutter & Postal (1984)对英语类语言中动词的分类,不能给补语指派宾格的动词隶属非宾格动词,因此(4a)类句式可以称为非宾格句式,其中的中心语谓词X不能给其补语YP指派宾格,而(4c)类句式则可称为宾格句式,其中的ZP可以由中心语谓词X指派宾格。
与英语类语言不同,汉语的谓词包括动词和形容词(或者说汉语中还存在形容词谓语句),后者中有一类是表示状态、性质或者存现、变化义的。比如,“那些树木树身大”和“大象鼻子长”之类句式中的谓词就是这类形容词。这类可做谓词的形容词本质上也具有非宾格属性,因此可以基于汉语语料对非宾格假设的内涵和外延加以扩展。据此,我们提出“广义非宾格假设”(Generalize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与动词中存在非宾格类一样,形容词中也存在表性质或状态变化的非宾格类;而且当两个名词具有固定的语义关联时,其中一方被选择为补语的同时必然也会选择另一方作为其标示语。该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最简方案语段理论的支持:语段中心语负责选择形成语段的论元成分和谓词,而“大象鼻子长”这种句式仅仅具有一个CP语段,因此其语段中心语C在选择非宾格性谓词的同时也选择两个客体论元作为其标示语和补语。
基于如上论述,(4b)的生成过程如下:中心语谓词“长”作为非宾格类谓词选择“鼻子”做其补语并依据“尽早原则”为后者指派客体角色(THEME)和固有格(基于语义角色而非结构位置的格位);二者形成的中间投射必然选择与“鼻子”具有特定语义关系的“大象”作为其标示语并为其指派客体角色。依据局域性原则,“大象”和“鼻子”之间的语义关联之所以被解读为后者隶属于前者,是由二者在谓词投射内的结构关系限制使然,即受制于标示语—补语间的非对称性成分统制图示的局域性限制,汉语母语者将二者间的语义关联解读为领属关系。
3.2 约束原则、非对称成分统制与同指语义
生成句法学还提出了著名的“约束三原则”,其宗旨是为了给句子中名词短语的语义同指现象确定句法范围。(Chomsky 1981, 1986)其中的原则A就把(4d)中的复合语素反身代词“他自己”获得语义先行语的句法范围确定为其所在的完整句子(即Minimal IP,最小化IP*约束原则对管辖范围的确定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本文为避免汉语单语素反身代词所引发的歧义现象,仅选用复合语素反身代词,目的在于说明语义同指的句法限制条件是IP(或TP)中的非对称性成分统制。):复合反身代词必须在其所在的最小化IP内受到先行语的成分统制,否则二者就不能实现语义同指。依据句法操作应尽早执行原则和语义解读范围应尽可能小的最简理念(Chomsky 2008:155-157)和汉语不具有时态语素、一致性语素的语言事实,先行语与反身代词之间同指性语义解读的范围完全可以进一步局限在vP范围内。至关重要的是,先行语必须以非对称性的方式成分统制反身代词,而且先行语必为外论元。据此,(4d)的生成过程为:及物性的“喜欢”选择反身代词“他自己”作为补语并为其指派受事角色和宾格;及物性轻动词v的补语选择VP投射作为补语,然后引入外论元“张三”形成完整的宾格句式。此外,约束理论还为指称表达式的语义解读设定了C原则:非代词性的名词短语在任何范围内其指称均不受约束。据此,(3d)中的两个名词短语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各自独立的指称,既无需先行语来确定其语义内容,也不受结构关系的限制。研究问题B中的疑问因而得以解释。
4. “大象鼻子长”是焦点敏感式
事实上,任何句子的实际运用其实都是为了传递某种信息,因此句子可以没有话题,但不能没有焦点。众所周知,汉语句子中的大多数成分都可以通过添加标记词“是”得以实现焦点化,如(5a)和(5b)。但有些句子从线性排列方面看似乎并没有焦点,但这些句子可能只是没有陈述其成立的前提,因为使用这些句子的话语功能就是为了提供新信息,如(5c)中的“一辈子”。
(5)a. 张三是昨天回来的。
b. 李四昨天是回来了。
c. 王五在这个小镇上住了一辈子。
d. Everything the invaders have destroyed.
实际上,句法成分能否成为焦点并不取决于是否可以通过添加标记词来标明,关键在于言说者是否要强调该成分,该成分在语义概念上和语用意图上是否是言说者着意强调的。因此,除了使用特定词汇手段(如加“是”)外,有些句子中的焦点即使脱离语境也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其中的焦点成分经历了某种句法操作。如(5d)的句首成分显然是经历移位后成为句子焦点的,因此即便是没有标记词也同样得以凸显。下面我们试图说明传统语法中的“双主语句”就是一种表面上并无焦点标记词而实际上是经历句法移位后形成的焦点敏感句式。
4.1 “大象鼻子长”中的“鼻子”是焦点
和汉语一样,大多数语言中的焦点都具有显性标记,如下页(6a)中Kinande语语料所示(Schneider-Zioga 2007: 412)。事实上,鉴别焦点成分的手段其实也并不局限于使用焦点标记词。通常采用的语言学手段还包括:不允许添加标点符号(即不能有任何语音上的停顿),如含有语音停顿的(6b)就不合法;焦点成分可以是表任指(非定指)的不定代词(而话题则必须实指),如(6c);焦点成分不能经由复指代词重现,如(6d);焦点成分可以通过“甚至、的确、只是”等词加以修饰,如(6e)。
(6)a. Ekitabu kyo Kambale a-asoma.
book FOC Kambale agr-read.
“It was the book that Kambale read.”
b. *张三昨天(语音停顿),回来的。
c.Anythingpeople are willing to confess to under torture.
d. *Something I thinkitmust have upset him.
e. 李四的确也是如此。
采用上述测试手段对“大象鼻子长”中的“鼻子”加以检测可以发现其具有焦点成分的属性,如(7)所示:
(7)a. 大象是鼻子长。
b. *大象鼻子,长。
c. 大象某物长。
d. *大象鼻子它长。
e. 大象的确鼻子长。
4.2 “(NP1领有者+NP2隶属者)+谓词广义非宾格”属于焦点敏感式
前文提到,实际使用中的句子有时候并不会通过词汇手段或语法手段来显现其中的焦点成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焦点。事实上,通过某种特定的句法格式及其转换、代替和省略等方法完全可以把无标记的焦点成分识别出来,特别是那些为了实现对比或凸显的话语效果而实现焦点化的句法格式。比如,前文Kinande语中采用标记词的焦点句(6a)在英语中可以通过特定的强调句式来凸显其中焦点成分的话语地位。就汉语而言,徐杰(2004)提出,“焦点敏感式”跟汉语专用的焦点标记词“是”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焦点形式;其区别在于:焦点标记词“是”唯一的表达功能就是标明强式焦点,而且“是”没有独立……的语法意义(徐杰2004: 142)。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汉语中类似于“大象鼻子长”这种句首两个名词间具有领属关系的句式本质上也是一种焦点敏感式,而且其焦点成分“鼻子”是经历移位到达句首位置的。
(8)a. 大象啊,鼻子长。
b. 大象啊,它们的鼻子长。
c. 张三只喜欢他自己。
d. 大象只是鼻子长。
e. Fernando AlonsoTOPIC, 110 pointsFOCUShe has had.
(8a)和(8b)显示,这类焦点敏感式的句首名词具有话题属性:不仅可以添加话题标记词,而且可以采用复指代词使其在句子主体中得以复现。另外,我们之所以把(NP1领有者+NP2隶属者)+广义非宾格谓词”句式归入汉语的焦点敏感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其中的NP1和NP2均是移位生成的。这是因为仅仅提供新信息的焦点成分通常都滞留在其基础生成位置,而为实现凸显或对比这种话语功能的焦点通常都要经历移位操作生成。(8c)中的“他自己”就是基础生成的信息焦点(因而也可以采用“只”得以凸显),而(8d)中的“鼻子”则是对比焦点,意图在于实现对比和凸显的话语功效。相比而言,“(NP1领有者+NP2隶属者)+非宾格性谓词”这种句式中句首两个名词的句法地位和(8e)中句首两个名词的句法地位完全相同:话题+焦点;而且二者均属移位生成。
上述分析方案可以为文献中语义近似而话语功能迥异的句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沈家煊 2006):产出(9a)“王冕父亲死了”的意图在于凸显其中的“父亲”是对比焦点,如(8c)所示;而产出“王冕死了父亲”则为了提供新信息,其中的“父亲”是信息焦点,如(9d)所示。
(9)a. 王冕父亲死了。
b. 王冕死了父亲。
c. 王冕父亲死了,母亲还健在。
d. (地震中)王冕只死了父亲,其他家人都得以幸存。
5. 广义非宾格句式和典型宾格句式
5.1 基于最简句法的推导模式
上述分析表明,汉语中的(2a)类“大象鼻子长”实质上是一种焦点敏感句式,可以形式化地表述为:“(NP1领有者+NP2隶属者)+谓词广义非宾格”;该句式为焦点敏感式,当且仅当NP1为领有者而NP2为隶属者;且V为表达状态或性质的形容词性谓词,其中的NP1必为背景式话题而NP2必为对比式焦点。而(2b)类句式“张三喜欢他自己”中的语义同指关系则符合“约束原则A”对二者间成分统制的要求,属于典型的宾格句式。基于最简方案合并生成句法结构的理念,如(10a)和(10b)分别是对广义非宾格句式和典型宾格句式的推导生成图示(细节从略,其中有删除线的名词成分是移位前的原始母本,而未有删除线的是结构位置最高因而可以得到语音拼读的拷贝)。

(10a)显示,“大象鼻子长”一类的句式本质上就是一种无主句,这实际上和汉语中的非宾格句式大多都是无主句的语言事实(类型学特征)是一致的,比如“下雨了”、“来了一位客人”等都是无主句。而“张三喜欢他自己”则是具有主语的典型及物句式,其中的语义同指关系符合约束原则的要求,并在成分统制结构的限制下得以实现。据此,“大象鼻子长”和“张三喜欢他自己”这两种句式中的两个名词论元都基础生成于谓词投射内,因此符合所有论元都基础生成在VP内的普遍语法规则。(Speas 1986)至此,我们对前文的研究问题C和D均做出了回答:“大象鼻子长”隶属于焦点敏感式,其中的“鼻子”是借助于移位而前置于谓词,因而具有对比性焦点的话语功能,而“张三喜欢他自己”则可归于信息焦点句,其提供新信息的话语功能是凭借置于句末这种自然焦点方式实现的。
5.2 再论谓词的非宾格属性
与传统语法对形容词谓语句的研究不同,本文探讨“大象鼻子长”一类句式中形容词的属性特征,特别是做谓词的形容词是否具有非宾格性属性,并提出广义非宾格假设:汉语形容词与传统语法中的不及物动词一样,也可以区分为非宾格系列和非作格系列,而“大象鼻子长”一类句式中的性质形容词就隶属于非宾格系列。事实上,非宾格动词和非宾格形容词均可以进入“大象鼻子长”这一类焦点敏感句式。比如,杨成凯(1997)就认为,类似于(11)的“主1主2谓句”中,“最为常见的‘谓’是形容词性的成分,但……‘谓’也可以是动词性的成分”(杨成凯1997: 252)。
(11)a. 张三手破了、腿折了、头发白了一大片、心跳得咚咚的……
b. 这个旅馆客人都走光了、饭厅也关门了……
Perlmutter & Postal(1984: 98-99)在为非宾格假设寻找跨语言证据时认为,非作格类谓词可以区分为有意愿、言谈方式、动物叫声和不自主的生理过程4类;非宾格类谓词可区分为受影响者、起始行为、存在状态和不受主体控制的刺激行为(比如shine、clink、stink)等4类,而广义非宾格假设则进一步扩展了非宾格类谓词的范围,将描述事物性质的形容词也归入非宾格类谓词。此外,广义非宾格假设还提出,汉语的非宾格谓词在词汇序列中可以选择单论元,也可以选择双论元;在后一种情形下,所选择的两个论元必须具有特定的语义关系,从而有助于统一解释汉语乃至其他语言中的更多语料。
5.3 类型学特征与“大象鼻子长”
前文基于广义非宾格假设把“大象鼻子长”一类的句式视为汉语特有的一类焦点敏感式。该观点要具有跨语言的解释力,还必须回答英语为何不能形成类似于*Elephants noses long这样的句式。下面从汉英两种语言的类型学差异和格位理论的视角对此予以阐释。首先,汉英句法结构最为显著的类型学差异就是前者允准空主语而后者必备显性主语以满足EPP特征的需求,而(12a)的非法性可据此归因于其spec-TP位置缺乏主语。其次,局域非对称性成分统制约束下的标示语和补语成分分别基于中心语谓词的非宾格属性获得固有格的赋值,因此也不具有移位到spec-TP获得主格的动因。再次,英语实现焦点化这一话语功能的常规句法方式是通过特定的强调句式和假分裂句式(Cleft and Pseudo-cleft clauses),因此无需首选移位这一代价较高的句法操作来实施焦点化。因此,(12a)无法以最为经济的方式形成合法的焦点句式,而(12b)中的动词因具有及物性,可为其补语指派结构格,因此可以形成合法的及物句。
(12) a. *Elephants noses long b. John likes himself

6. 结语
现有文献对“大象鼻子长”一类句式所做的话题-陈述分析法(陈平 2004)和主语重叠分析法(徐杰 2004)均不符合所有论元均基础生成于VP投射内的要求,也未能把句法结构的层级性对语义解读的限制作用清晰地体现出来。而本文提出的“焦点敏感式”分析法旨在说明:当言说者在选用及物句、话题句、焦点句甚至话题-焦点句以及其他句法形式来传递信息时,既需要估量听话者对已知内容的了解程度,也需要凸显听话者需要关注的信息点。
据此,汉语的常规及物句和非宾格句都可从话语功能视角重新加以分析:“大象鼻子长”这种句式属于话题和焦点都很敏感的句式,因为其中的“大象”和“鼻子”都是从其基础位置移位而来的,其移位的动因就是话题投射和焦点投射的中心语所具有的边缘特征;相比而言,及物句“张三只喜欢他自己”则隶属于自然焦点句式,其句末成分便是言说者力图传达的信息点。英语采用特定的句式实现焦点化这一话语功能,而且英语无法形成同等的焦点敏感式与其必备显性主语的类型学特征相关联。
Burzio, L. 1986.ItalianSyntax:AGovernmentBindingApproach[M]. Reidel: Dordrecht.
Chafe, W. 1976. Give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topics, and point of view[A]. C. N. Li (ed.).SubjectandTopic[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7-55.
Chomsky, N. 1957.SyntacticStructures[M]. The Hague: Mouton.
Chomsky, N. 1965.AspectsoftheTheoryofSyntax[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omsky, N. 1981.LecturesonGovernmentandBinding[M]. Foris: Dordrecht.
Chomsky, N. 1986.KnowledgeofLanguage:ItsNature,OriginandUse[M]. New York: Praeger.
Chomsky, N. 1995.TheMinimalistProgram[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homsky, N. 1999. Derivation by phase[A]. M. Kenstowicz (ed.).KenHale:ALifeinLanguage[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52.
Chomsky, N. 2007. Approaching UG from below[A]. S. Uli & H. M. Gartner (eds.).Interfaces+Recursion=Language?[C].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29.
Chomsky, N. 2008. On phases[A]. M. Kenstowicz (ed.).KenHale:ALifeinLanguage[C].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33-166.
Chomsky, N. 2011. What is special about language?[J].LanguageandOtherCognitiveSystems2: 271-272.
Chomsky, N. 2013. The problems of projection[J].Lingua130: 33-49.`
Green, M. 2007.FocusinHausa[M]. Oxford: Blackwell.
Kang,Y. S. 1986.KoreanSyntaxandUniversalGrammar[D]. Ph. 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Kayne, R. 1994.TheAntisymmetryofSyntax[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Koopman, H. & D. Sportiche. 1991. The position of subjects[J].Lingua85: 211-258.
Larson, R.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J].LinguisticInquiry19: 335-391.
Li, C. N. & S.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A]. C. N. Li (ed.).SubjectandTopic[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480-489.
Perlmutter, D. M.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A]. J. Jaegeretal. (eds.).ProceedingsoftheFourthAnnualMeetingoftheBerkeleyLinguisticsSociety[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57-189.
Perlmutter, D. M. & P. M. Postal. 1984. The 1-advancement exclusiveness law[A]. D. M. Perlmutter & C. G. Rosen (eds.).StudiesinRelationalGrammar(2nded.)[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81-125.
Radford, A. 2009.AnalyzingEnglishSentence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zzi, L.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A]. L. Haegeman (ed.).ElementsofGrammar:HandbookofGenerativeSyntax[C].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81-337.
Ross, J. R. 1967.ConstraintsonVariablesinSyntax[D]. Ph. D. Dissertation. MIT.
Schneider-Zioga, P. 2007. Anti-agreement, anti-locality, and minimality: The syntax of dislocated subjects[J].NaturalLanguageandLinguisticTheory25: 403-446.
Speas, P. 1986.AdjunctionandProjectionsinSyntax[D]. Ph. D. Dissertation. MIT.
Trask, R. L. 1993.ADictionaryofGrammaticalTermsinLinguistics[Z].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Xu,L. J. & D. T. Langendoen. 1985. Topic structures in Chinese[J].Language61: 1-27.
陈 平. 2004. 汉语双项名词句与话题-陈述结构[J]. 中国语文(6): 493-507.
方 梅. 1995. 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J]. 中国语文(4): 279-288.
郭继懋. 1990. 领主属宾句[J]. 中国语文(1): 24-29.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J]. 中国语文(4): 291-300.
王 力. 1985. 中国语法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徐 杰. 2004. 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和功能[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杨成凯. 1997. “主主谓”句法范畴和话题概念的逻辑分析[J]. 中国语文(4): 251-259.
张 斌. 2007. 现代汉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论胡好对逻辑谓词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