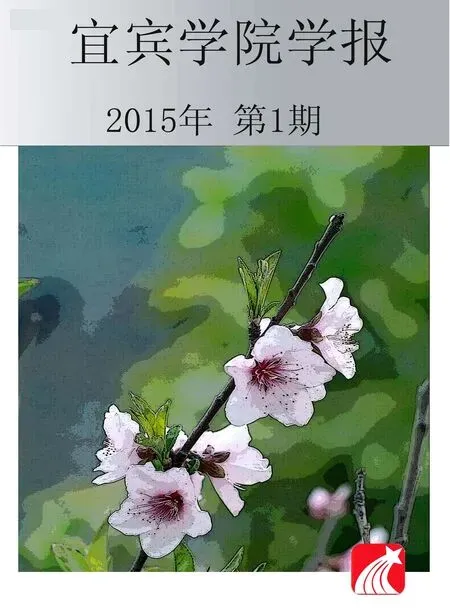“狂人手记”中的生命悲歌:沈从文的自我救赎
李玮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狂人手记”中的生命悲歌:沈从文的自我救赎
李玮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949年初,沈从文选择了自杀,得救脱险后他写下了不少类似“狂人呓语”般的书信和日记。这些书信和日记用内涵丰富的隐喻意象、意识流般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他精神上的困苦与挣扎,同时也体现出他在逆境中的坚守。最终,他将苦难转化为广博的“爱”与“责任”,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沈从文;书信;日记;救赎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后经家人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才得以脱险。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他在生命迷乱癫狂时,写下了不少日记和书信。这些日记、书信中大量意识流似的语言,内涵丰富的隐喻意象,本身具有文学上的审美价值。同时,这也是其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它们谱写了沈从文此时痛苦挣扎和自我救赎的生命悲歌。
一 宝玉顽石之辨
1949年4月6日,在精神病院疗养的沈从文信手写下了一组日记,记录了自己头脑中正常与混乱的错综思考。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事业结束了。“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2]联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沈从文断定“这一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2]。沈从文既无法改变这样的现实,又不能完全认同当前的文艺政策,思想与时代错位的结果是被边缘化。这让他悲从中来,“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2]。沈从文用“宝玉”自喻: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变成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2]
二十七年前从边地湘西闯入北京的“顽石”,在近乎绝望的生活中,忍受一切挫折和寂寞,终于蜕变成一块光彩夺目的“宝玉”,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但在新的评价体系下,“宝玉”被打回原形,“随时可以扔去”“随时可以粉碎”。这种失落和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见,沈从文对自己过往的文学成绩是珍视的,所以他宁愿搁笔也不愿改弦更张。“这时节最相宜的,不是头脑思索继续思索,应当是手足劳动,为一件带生产性工作而劳动。劳动收得成果,两顿简单窝窝头下咽后,如普通乡下人一样一睡到明。天明以后,再来劳动。在手足劳动中,如在一个牢狱工厂参加木器家具生产,或小玩具生产,一面还可以提出较新设计,我的生命也即得到了正常的用途”。[2]如果要继续在新的国家生存下去,沈从文也只有劳力不劳心,不再参与文学的思考和写作。
当“宝玉”变成“顽石”,沈从文难以自处。“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2]他在这时经常翻看过去的文章,并从中寻求安慰。“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看看十年前的《昆明冬景》,极离奇,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而一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弱点极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新的发展社会中的种种,我什么都想到说到过”。[2]
沈从文从不怀疑自己的文学成绩,虽然被批判被驱逐,但他仍然坚信自身创造的价值。所以多年间他“跛者不忘履”,多次想重新公开用笔写作,但文艺政策的阴晴不定和诸多限制,让他没能如愿。
二 蚁蝇之痛
1949年7月沈从文在致刘子衡的信中说:“‘破甑不顾’,古人说的或有道理,朋友可不必再为我过分担心,我近于夙命限制,已成一堆碎瓦”。[2]沈从文并不是自怨自艾,而是内心有刻骨之痛,亲人朋友无法理解。1949年11月22日,沈从文在日记中写道:
“可惋惜”亦只是相熟人而言,相熟不明过程的,即不会理解到,只是照人安排而已。学“忘我”的确是一件大事,忘我的学,亦可知相当困难。忘成就易,忘痛苦难。看看相片上万千人为国家社会而牺牲,我看出我自己渺小到不足道。然一蚁一蝇,其物固小,从错误中牺牲时,其为痛苦固与虎豹相同也。[2]
这里的“痛苦”有两层含义。首先,“忘成就易,忘痛苦难”中的“痛苦”是指沈从文在过往的痛苦生活中沉淀的独特沉痛的生命体验。“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辛酸。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3]。随军的生活让沈从文见惯了太多的杀戮,但他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环境中毁去,他说:“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3],它们是沈从文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也是他文学世界的基石。如果忘掉这些痛苦,如同否定了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追求。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忘记痛苦”,否定过去,是必须做出的牺牲。这导致了沈从文的精神迷乱,也就是他在书信和日记中经常提到的“丧我”之感。“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我在搜寻中丧失了我”“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2]随“旧我”远去的还有他的文学世界。“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2]沈从文呼喊的“翠翠”“三三”是其整个文学世界的象征符号,他不无伤感地说:“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2]因此,换句话说“忘痛苦难”是沈从文难以割舍过往的生命体验和已经成熟的文学生命的表述。
其次,在“然一蚁一蝇,其物固小,从错误中牺牲时,其为痛苦固与虎豹相同也”中的“痛苦”,是沈从文在“忘我”过程中的灵魂挣扎之痛。沈从文在给家人朋友的信中经常会提到与新国家相比,个人的渺小不足道。1950年4月在致布德的信中也提到“个人实渺小不足道,算不了什么的!”[2]这里当然有沈从文对新生国家赤子般真挚的热爱,但他个人的心结又能为多少人所真正理解。所以沈从文发出“人不易知人”的感慨。“学向大处看,大处想,个人已牺牲处也能忘掉,只看成个人不幸,无所谓。唯如何用生命从新学,从新作,为多数人有益,为新社会有益,实茫然不知从何作去;看看个人会到这个情况下,觉得人生离奇。因可看出人不易知人。我自己尚不知自己如何即可对新社会有益,也对自己有用,他人那会能作安排?”[2]因此,也只有沈从文自己才能彻底救赎自己。
一个人的生命教育有如此一个复杂过程,是任何人想不到的。宋儒言“明理”,由禅附儒,作成一种书生气的人生哲学,说来说去一篇胡涂账,比废名诗还不易理解,因为少一个条理明白的解说。惟属于自省,可能有些发展情绪经验是由一个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立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这过程是相当复杂辛苦的。到这种明澈为我所有时,我觉得我对一切,只有接受别无要求了。[2]
理解了沈从文生命“清算和挣扎”时的双重痛苦,也就理解了他生命回复过程中的“新生”到底意味着什么。明澈单一的“新生”为沈从文所有时,他能做的只有接受。那么这个“新生”只是肉体的新生,而不是灵魂的新生。“我失去了我,剩下的是一个无知而愚,愚而自持的破碎的生命。虽然有了新生,实十分软弱”。[2]“我”失去的是那个能用头脑继续思索的“我”,留下的只是残缺破碎的参加手足劳动的躯壳。“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2]正是因为沈从文放弃了灵魂的新生,才凡事无分。所以沈从文此时在日记、书信中表示的“入群”愿望,并不是真正的思想入群。“至于生活意识形态,实于社会进步无助无益。也可说正代表社会一种病的形态。从群的观点言,如仅看病的一面,我在任何方式下都可以毁灭”。[2]
沈从文在建国前离开北京大学,经郑振铎介绍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几乎停止写作。在之后十几年间,多次南下考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存空间的转换,沈从文的灵魂慢慢得以恢复,过往的生命体验慢慢渗透到新的生活,生出了新的枝丫,但质地却是没有改变的。这种历久弥坚的精神支柱让他能在之后更大的批判和斗争中顽强支撑下来。而此时此刻支撑沈从文的是他破碎静止的灵魂中的“爱”与“责任”。
三 十字架上的爱
沈从文始终信奉“爱”的哲学,他把对强权的否定和对现实恶的憎恨转化成对无辜受害的良善人民的爱,这是他独特的情感体验,也是其大部分湘西题材的小说所表现的主旨。他在1950年4月致朋友布德的一封信中详细阐述了这种独特的情感体验的转化:
唯一特别处,即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写城市,全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的抒情而已。正和写《月下小景》是观念抒情一样的。在新的尺度下衡量,可以说有害无益。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说奇怪,也奇怪,这个最重要影响,可能还是三十年前的。有一次在芷江县怀化镇,一个小小村子里,在一个桥头上,看到一队兵士押了两挑担子,有一担是个十二岁小孩子挑的,原来是他自己父母的头颅,被那些游兵团队押送到军营里去!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2]
沈从文在1950年8月8日的日记中,又借制器彩绘者的工作隐喻这种情感转化的过程:“架上一格那个豆彩碗,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型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依然是充满了制器绘彩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2]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美好、质朴的背后有着深深的忧愁,他将现实压抑的情感和痛苦转化而成的爱。这种“爱”的分量是沉重的。
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爱与受难纠结缠绕在一起。“上帝之子惨死十字架上,作为神圣的审判和爱的终极肯定,不仅是要促使个体深切理解社会的悲哀和世界的痛苦,也是在促使个体参与反抗社会的不义和邪恶的斗争”。[4]从文学对社会的作用的角度来讲,配合政治鼓动人心的文学势必会降为宣传一级,而将苦难转化为广博的“爱”的文学才是个人、社会得救之道,真正起到文学应有的伟大作用。就像沈从文自己说的:“我看过这种杀戮无数,在待成熟生命中,且居然慢慢当成习惯。一面尽管视成习惯,一面自然即种下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世界如不改造,实在没有人能审判谁。凡属审判,尽管用的是公理和正义作护符,事实上都只是强权一时得势,而用它摧残无辜。”[3]他深刻透析了现代政治的本质,这也是他对现代政治不信任的原因。基督教神学思想家尼布尔宣称“既不能把世俗政治形态神圣化,也不能完全放弃政治领域,因为,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爱的理想——既不能放弃,又无法完全实现,这正是人类的悲剧性现实”[4]。沈从文在40年代一度陷于抽象的沉思不能自拔,而“爱”是这时期他抽象思考的中心名词。在《长庚》《烛虚》等哲理化的散文诗中,他多次表达对“爱”的皈依。因为“人类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对美与爱完全丧失了感觉、人性已被扭曲的世界,而‘我’却是如此执著地要将这被亵渎、颠覆的生命法则昭示人,重新恢复生命应有的尊严”[5]。这里沈从文所表达的“爱”是抽象意义上的人类应有的本性和生存方式。
解放后,沈从文停止了“向远景凝眸”的形而上的思考。他此时的“爱”不是一种抽象的说明,而是一种生活行为本身,是针对自身境遇而言的,是他对这个时代及生活在此的民众的“爱”。1949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日记中写:“我怎么会这样?极离奇。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2]他不明白自己这种“爱”的行为为什么难容于世。1950年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学习,精神的紧张有了很大的缓解,他说“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对时代的爱。从个‘成全一切’而沉默,转为‘积极忘我’。或许人已老大,生命过于凝固,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就会不济事,终于结束了。或许还能够从挣扎中度过。对一切都依然是充满了爱,一种悲悯的爱”[2]。时移世易,“我们”代替了“我”,“群”取代了“个”,而游离于群之外的个体,被无情地抛弃。沈从文“爱”的行为成了单方面的付出,换回的是遍体鳞伤。沈从文在日记中写道:
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2]
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野草》中的《复仇(其二)》,这篇散文诗“消解了‘耶稣受难’的宗教意义而挖掘其人性内涵,把一种神性对苦难的超越转变成了人性对苦难的体味与反抗”[6]。鲁迅将“复仇”作为标题,通过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意欲向那些麻木的看客复仇,让他们无戏可看,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一种战斗精神。沈从文却不同,他见到的苦难或许并不比鲁迅少,但却没有走上“精神界战士”之路,他心中充满了“慈柔”,充满了“悲悯的爱”。这与“耶稣受难”的宗教意义接近。“上帝之爱是爱的本源和爱的终极对象,最大的不幸乃是上帝的不在场。上帝不在场,就不会有任何爱的对象,没有爱的对象,存在就是黑暗之狱,在黑暗中意味着人的心灵不再有挚爱,进而跌入深渊。然而,即便在这种时候,上帝之爱依然进入深渊——爱的十字架正是在深渊中竖起来的。”“上帝放弃自己、上帝让自己被处死,以使爱的创造得以完成。这也就是十字架上的爱的真之奥秘,被钉十字架而死的上帝的十字架,是新的人性的充满奥秘的新福音之象征。”“要爱必然受苦,因此,基督信仰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安慰,而是重负。”[4]沈从文自己说受到《旧约》的影响,他完全理解这种“受难以成全爱”的伟大之处。“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2]所以,沈从文是一个真正的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而这种人“往往是恭顺而随波逐流的,但这常常给了暴力趁隙而入的机会”[7]。沈从文解放后对加诸其身的不幸,反报之以爱,他在精神慢慢恢复之后,争分夺秒地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沈从文此时的“爱”是他精神修为的完整表现,这也是他“潜在写作”的一部分,正如刘志荣所言“即有形的写作背后潜隐着的人生的写作”[8]
[1]吴世勇.沈从文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1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68.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9-10.
[4]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1-251.
[5]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长沙:岳麓书社,2006:404.
[6]赵磊.拯救与复仇:“耶稣受难”故事在鲁迅《复仇(其二)》中的变异[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63.
[7]茨斯蒂芬·茨威格.异端的权利[M].张澜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4:143.
[8]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5.
〔责任编辑:王 露〕
The Tragic Dirge of A Madman’s Diary:Shen Congwen’s Self-salvation
LI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1949,Shen Congwen chose to commit suicide,and after being saved,he wrote many letters and diaries which are like“the ravings of a madman”.These letters and diaries,with metaphorical images,rich connotation and stream-of-consciousness language,recorded the hardships and struggles of his spirit,which also reflected his perseverance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Eventually,he converted his suffering into broad“love”and“responsibility”,thus completing his self redemption.
Shen Congwen;letters;diaries; salvation
I206.7
A
1671-5365(2015)01-0048-06
2014-11-14
2014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沈从文解放后的思想、生存与创作——以书信为核心”(CX2014B175)
李玮(1986-),女,山东枣庄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