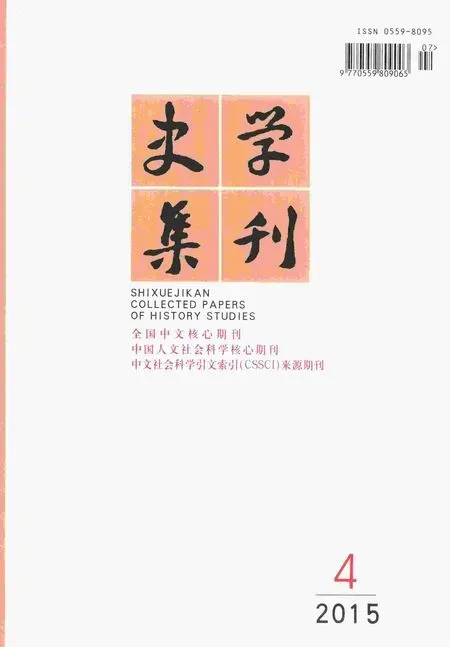纳粹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战后七十年联邦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思考
徐 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作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心国家,尤其是纳粹集权统治和“大屠杀”的制造国,德国学界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将再次成为焦点。对纳粹主义的反思历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隐含着“犹太人问题”以及德国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而对于普通德国人,它还同时指向战后德意志民族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具体来说就是对待民族分裂和统一的态度问题。在21世纪,它还涉及德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定位。
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历史的讨论往往是以辩论方式展开的,它完全开放,争论双方面向公众舆论,激烈交锋,进而使历史问题从学术争端演变成公共性历史事件。辩论的过程,按照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 (Joern Ruesen)的说法,实际上是“二次创伤化”的过程,“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回忆起恐怖的事件,历史思考获得了阻止恐怖事件再次发生的契机”。①[德]约恩·吕森 (Luesen,J.)著,綦甲福、来炯译:《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同时,它也是获得认同的过程,将这样一个悲痛的历史事件置于民族认同历史的中心。当然,战后七十年,纳粹史的叙事也存在模式转换的问题。历史叙事的方式只有在历史撰述的现实情境中才可以理解,而被现实政治所决定的历史叙事,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现实政治的发展。
一
战后初期,“民族神话叙事”②“nationale Meistererzaehlung”,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叙事模式,受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影响,植根于浪漫主义和日耳曼民族特性,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结。依然是纳粹史解释的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国家一分为二,接受盟军占领成为一个时期德国人的政治命运。德意志民族不仅经历了战场上的军事失败,更大的创伤还是源于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这远远超过了1918年的失败。战后的最初几年,能为德意志人带去精神安慰的只有劳动,“劳动民族”(Arbeitnation)代替了“文化民族”(Kulturnation),勤劳、敬业成为民族自尊的唯一支撑。①1945年10月,德国福音教会临时理事会曾发表《斯图加特认罪书》,提出教会和民众达成“认罪的团结”,但遭到普遍的反对。
不过,当整个民族还在集体悲痛中无力自拔时,历史学家的使命感促使他们迅速发出声音,要对纳粹德国的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以跨越认同裂缝,让民族精神在新的原则上达成一致。一反常态地,史学界对历史的批判情绪开始露头,“浩劫”、“悲剧”、“宿命”、“恶魔”等话语流行起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莫过于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的《德国的浩劫》②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Wiesbaden:Brockenhaus,1946.和盖哈德·里特尔 (Gerhard Ritter)的《欧洲和德国问题:德国国家思想的独特性》③Gerhard Ritter, Europe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ue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Muenchen:Muenchner,1948.。此外,还有汉斯·罗斯菲尔斯④Hans Rothfels,Die deutsche Opposition gegen Hilter,Krefeld:Scherpe,1949.(Hans Rothfels)、路德维希·德约 (Ludwig Dehio)等。前者著有《德国对希特勒的反抗》,后者著有《均势抑或霸权》⑤Ludwig 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Krefeld:Scherpe,1948.。
反思是痛苦的,作为历史主义的传承人,耄耋之年的迈内克不得不承认1871年后德意志的“普鲁士化”以及历史上“强权政治”(Machtpolitik)、“强权国家”(Machtstaat)观念的渗透和扩张为德国带来了致命问题,德国历史进程充满了悲剧性。但是,他和里特尔一样都相信德国古典文化的高贵性,坚持要把纳粹意识形态与德国文化传统区分开,即所谓的文化两分法或二元化。1949年,迈内克发表文章“我们的历史走错路了吗?”,试图再次肯定强权政治和军国主义的积极一面,理由是它们服务于创造伟大的德意志文化。而里特尔在“德国军国主义”一文中,也再次断言德国古典文化和普鲁士遗产的优越性。
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呢?在保守的历史学家那里,相信德国“误入歧途”成了广为接受的叙事模式。为此,他们把“强权政治”和纳粹主义产生的基础与法国大革命及卢梭的“公意”思想挂钩。里特尔认为希特勒的前驱“既不是弗里德里希大王和俾斯麦,也不是威廉二世,而是从丹东到列宁和墨索里尼的现代史上的煽动家和暴君”,⑥[美]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Iggers,G.G.)著,彭刚、顾杭译:《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是大革命的“大众民主”导致了强人政治和独裁统治。而迈内克则表达为是“民主化、布尔什维克化和纳粹化”带来了问题。温和的自由派史家特奥多·席德尔 (Theodor Schieder)也说,奥斯维辛的根源不在德国的“奴性”,而是作为技术化、官僚化时代的现象的非人化。⑦Theodor Schieder,Zm Problem der historischen Wurzeln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Politik und Geschichte,Nr,5(1963):19-27.总之,根源就在于人们对启蒙理想的幻灭和现代性本身的病态发展,是西方文明出了问题。在解释纳粹和大屠杀时,他们认为这是外来的,是不属于“我们的”历史的历史性事件,是“受那些陌生人的、那些从外面入侵的人的、根本是反历史的人的牵累”,⑧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76页。明确地说,重要的一部分责任就是犹太人“消极的和瓦解性的作用”⑨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S.29.,是他们打乱了德国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平衡状态。将纳粹“恶魔化”就是为了把他们理直气壮地逐出德国历史的属地,保持德国历史的纯洁性。
在澄清了权力恶魔的来源后,历史学家们呼吁要重塑德国的历史形象 (Geschichtbild)。迈内克建议用德意志古典文化和古老的基督教理念来疗伤,83岁的老人为德国人勾勒出一幅富有童话色彩的蓝图,要在每一个德国城市和较大的乡村建立起“歌德社团”,朗读诗歌、聆听音乐,让美妙的声音唤起新的“德意志精神”,让它成为德意志人集体归属感和行动能力的基础。
这个时期,在学界也有另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声音,但或被忽视或被批评。这些学者要么处于学术界边缘,要么定居在国外。联邦政府自1953年起资助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专门研究纳粹历史,但该所及其刊物《当代史季刊》却并未在德国历史中寻找纳粹的根源。显然,“民族神话叙事”依旧是历史分析的主要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没有将它撼动,纳粹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过度消耗也不能将之彻底摧毁,民族国家依然是维系情感的纽带,尤其在战后集体认同突然断裂的特殊阶段。因此,无论是将纳粹政权及其恶行外属化或将德意志文化二元化,都是为了所谓的“民族尊严”,是民族认同必要的心理策略。
这就是德国史学界的主流态度:内疚、不隐瞒,但保持冷峻气概,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推诿、排挤,并通过这种办法继续维护“民族神话叙事”下对德国19世纪以来历史的英雄般的、至少也是“还说得过去”的想象。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下,战后联邦德国采取了“克服过去”的“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对纳粹分子甚至战犯给予大赦,据说是为了通过融入,让他们在接受共和国政治秩序的同时,制约其极端右翼的倾向。
二
真正对“民族神话叙事”构成致命冲击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费舍尔大辩论”①关于“费舍尔大辩论”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广义的从1959-1985年,狭义的则为1962-1970年或1971年。本文倾向后一种说法。(Fischer-Kontroverse)和其后形成的“批判学派”。
1961年,弗里茨·费舍尔 (Fritz Fischer)抛出专著《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的战争目标策略》②Fritz Fischer,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Duesseldorf:Drost,1961.。尽管他研究的是德国在一战中的责任问题,但实际瞄准的却是纳粹政权以及二战。费舍尔指出: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战争目标具有连续性——争夺世界霸权。德意志帝国是纳粹政权的先驱,一战为二战打开了大门。也就是说,德国历史问题的症结在第二帝国时期已经埋下,俾斯麦帝国和希特勒帝国存在某种连续性,“强权政治”的终点是第三帝国及其发动的世界战争。一战与二战的联系由此滥觞,学界开始广泛接受“20世纪三十年战争”的说法。
费舍尔命题在1964年柏林召开的史学家大会上引发争论,并很快通过报刊杂志转化成对联邦德国政治和历史认同的大辩论,这一事件成为“联邦德国历史编纂学的决定性事件”③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scher Controvers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No.2(2013):251.。在冷战背景下,左派和右派阵营形成。里特尔此时已处于职业生涯的尾声,但作为右派代言人,还是“气得满脸通红”,批评费舍尔命题是“民族的不幸”,是对“德国历史意识的自我抹黑”,这与过度爱国主义一样都是灾难性的。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里特尔曾激烈反对希特勒,并因此于1944年入狱,而后来却被曝有同情纳粹的倾向。纳粹史专家安德烈斯·希尔格鲁伯 (Andreas Hillgruber)和克劳斯·希尔德布朗德 (Klaus Hildebrand)等也一直坚守自己传统的观点。而初出茅庐的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则出版了《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法兰西行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⑤Ernst Nolte,Der Faschismus in seiner Epoche,Die Action francaise,der italienische Faschismus,der Nationalsozialismus,Muenchen:Piper,1963.,几乎单枪匹马地要以法西斯主义理论取代极权主义理论。其意图在于强调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普遍性,并非德国所特有,实际上想继续维护迈内克的文化二分法。
不过,新兴的自由派脱颖而出,到七十年代逐渐成为史学正统,被称为“批判学派”或“结构派”、“功能派”。五十年代,一些生活在双重世界中的历史学家虽然依恋德国历史的传统,但已开始尝试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方法探讨民族国家的过去,他们的研究取向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如汉斯·蒙森 (Hans Mommsen)、沃尔夫冈·J.蒙森 (Wolfang J.Mommsen)、汉斯 -U.维勒 (Hans-U.Wehler)、伊曼纽尔·盖斯 (Imannuel Geiss)、马丁·布若斯查特 (Martin Broszart)等。这些年轻人广泛接触并熟悉英美历史学研究方法,研读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研读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运用社会科学的手段而非历史主义的流畅叙事重新解读德国历史。历史思考变成了历史批判,历史学的“批判”功能被广泛接受。布若斯查特就强调批判性对待德国历史的政治结果,称“批判性地对待古代和近代的历史是联邦德国公民赢得政治文明的最好元素之一……”①Hans-U.Wehler,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Ein polemischer Essay zum Historikerstreit,Muenchen:C.H.Beck,1988,S.103.。而批判的工具就是西方政治文化中的普世标准——政治民主化。自由派历史学家提出了所谓的“特殊道路”(Der deutscher Sonderweg)问题,用它来理解德国历史发展与西方的差异,突出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和“非常规性”。为此,他们构建了一个分析系统,在“历史社会科学”的旗帜下,着力分析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从结构框架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和传统的政治决策中寻找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产生的根源,②Hans-Ulrich Wehler,Das Kaiserreich 1871-1918,Goettingen:Suhrkamp,1973;强调“内政主导论”(Primat der Innenpolitik),以取代历史主义所看重的外交政策判断。作为第一位系统研究纳粹社会史的学者,布若斯查特的代表作《希特勒的国家:内部体制的基础和发展》③Martin Broszart,Der Staat Hilters,Grundlegung und Entwicklung seiner inneren Verfassung,Muenchen:dtv,1969.为我们描绘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宏大结构,将“形象高大”的希特勒纳入结构框架,“元首”的个人作用被相对化了。而“老派”历史学家如希尔德布朗德,他的代表著《第三帝国》④Klaus Hilderbrand,Das Dritte Reich,Muenchen:Oldenbourg Wissenschaftsverlag,1979.以及希尔格鲁伯的教授资格论文《希特勒的战略》⑤Andreas Hillgruber,Hilt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fuehung,1940-1941,1965.却成为维勒、蒙森等人的批评对象,指责它是老一套,带有浓厚的个人化和目的意志色彩。
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新学派开始把纳粹主义有意识地带入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他们对纳粹主义和大屠杀不再采取排挤和逃避态度,而是把它视为德国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消极的反面,通过彻底清算,与它划清界限,将自己和作恶者拉开距离。纳粹主义成为德国人自我理解的组成部分,“通过有意识的负面界定,纳粹主义成为自我认同的一个决定性元素”。⑥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79页。显然,这个派别是居高临下的,在右派看来,它掌握着“道德的惩戒棒”⑦马丁·瓦尔泽 (Martin Walser)在德国书业授予他和平奖时发表的批评言论。,包含着“政治正确”的意味。在这一派的冲击下,德国的传统价值被西方的普世价值所替代,而普世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本身又是超越历史经验的,于是,民族国家有个性的历史变得无足轻重了,德国的历史形象发生革命性颠覆,“民族神话叙事”的框架轰然倒塌。
当然,“批判学派”的胜利并非偶然,它有政治环境的支撑。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使欧洲政治急剧左转,对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批判成为风尚。而后,绿色运动崛起,成为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年轻人普遍拥抱后现代思想。一批新人—— “1968年一代”,从一战和二战中获取教训,满足于做欧洲小国,清除“帝国”旧梦,但同时也打消了德国再度统一的民族梦想,因为“谁试图促成统一的政治结果,或从旁推动,都将不可避免地将德国拖进第三阶段的强权政治中,并会再度由德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⑧Dirk Kurbjuweit,Der Wandel der Vergangenheit,Der Spiegel,Nr.7(2014):114.
与此同时,西德的民主化进程顺利推进,民主已成为联邦德国政治生活的常态。西德人慢慢开始认同于自己国家的“超民族性”,认同于被强制改造后的民主政治秩序。“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⑨“Verfassungspatriotismus”是政治学家多尔夫·斯特恩贝格 (Dolf Sterngberg)于1979年《基本法》颁布三十年之际召开的纪念大会上提出的概念。一词被制造出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爱国主义,至少在“半个民族”(西德)内被激活了,在有效运行着的宪法框架下,联邦德国培养起了民族自我理解的新方法。在历史批判意识主导下,民族认同从温和迅速转向了激进。
三
当政治被推到另一极端,历史学就会再次产生“修正”的愿望。沉寂多年后,保守派历史学家开始思考究竟能否、且在何种程度上能为联邦德国建立起清晰的民族认同,并赋予它合法性。新一轮辩论呼之欲出。
1986年6月6日,恩斯特·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不愿过去的过去”①Ernst Nolte,Vergangenheit,die nicht vergehen will,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6.April,1986.。作者抛出五个雄辩性问题:民族社会主义者和希特勒的“亚细亚勾当”②“asiatischen Tat”。在诺尔特的笔下,“亚细亚”一词象征着非同寻常的残暴,与斯大林和“红色高棉”的波尔波特等联系在一起。是自生的吗?奥斯维辛集中营难道不是源于“古拉格群岛”吗?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谋杀”在逻辑和事实层面不都要高于民族社会主义的“种族谋杀”吗?希特勒的灭绝手段难道不是出于对“鼠笼”③“Rattenkaefig”。据说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审讯政治犯时动用的酷刑,将犯人关进鼠笼,用火熏烤,使笼中之鼠仓皇逃窜,最后咬噬犯人。诺尔特强调该词是为希特勒的种族谋杀开脱。维勒为驳斥诺尔特,在1988年出版的书中专门撰有“鼠笼”一节,以证明诺尔特的观点是错的。参见Hans-U.Wehler,Entsorgung der deutschen Vergangenheit?Muenchen:C.H.Beck,1988第四章第8节。刑讯的恐惧吗?奥斯维辛或许有自己的历史起源,但就不应该忘却吗?其实,诺尔特的答案是清楚的,就像文章标题所写的那样:要让一切都过去。
汉斯-U.维勒在与哈贝马斯紧急磋商后,7月11日,由后者在《时代》杂志上刊发“一种损害回避:德国历史撰述中的保护倾向”④Juergen Habermas,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Die apologetischen Tendenz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Die Zeit,11.Juli,1986.一文,正式开启了著名的“历史学家论战”(Historikerstreit)。参与论战者无数,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后编辑成册。⑤Rudolf Augstein(hrgs.),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e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Muenchen:Piper,1987.论战的一边是自由主义左派,以维勒、哈贝马斯和《明镜周刊》主编鲁道夫·奥格斯泰因 (Rudolf Augstein)为代表;另一边是保守的右派 (新保守派),又称“新修正主义派”,其中包括米歇尔·施蒂默尔 (Michael Stuermer)、约阿希姆·菲斯特 (Joachim Fest)⑥菲斯特曾写过《希特勒传》(Joachim Fest,Hilter,Eine Biographie,Frankfurt/M,1973),该传记此后是希特勒生活的模本,后拍成纪录片,1977年首映,引发争议。该书对大屠杀涉及很少,是招致批评的原因之一。、希尔格鲁伯等。论战是激烈的,甚至出现了暴力行为,诺尔特的汽车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停车场被烧毁。
这场论争围绕两个概念展开:唯一性和因果性。左派强调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希特勒的暴行不能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相比较,奥斯维辛不是古拉格的翻版,而是源于德国人的种族仇恨。它是唯一的,没有因果解释。而诺尔特等则认为德国集中营灭绝人性的行动,早在当年的契卡和NKWD的集中营里就上演过。区别仅在于毒气施放过程中使用的技术手段。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学者。至于因果关系,诺尔特说,希特勒在谈到布尔什维主义时,常常会情绪失控,陷入高度紧张。“即使1917年革命不发生,德国也会出现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前左派”历史学家伊曼纽尔·盖斯为了从方法论上支持诺尔特,于1988年出版《哈贝马斯辩论:一场德意志人的辩论》⑦Imanuel Geiss,Die Habmas-Kontroverse,Ein deutscher Streit,Berlin:W.J.Siedler,1988.,重申“批判学派”强调的比较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因此被左派骂做随政治风向摇摆的“叛徒”。
在诺尔特的基础上,希尔格鲁伯借助《双重毁灭》进一步发问:对于德国国防军在东线的溃败以及东部德意志人被驱逐和逃离,历史学家究竟应该怎么看?①Andreas Hillgruber,Zweierlei Untergang:Die Zerschlag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d das Ende des europaeischen Judentums,Berlin:W.J.Siedler,1986,S.24.当然,他本人无疑是站在德方“受害者”立场上思考的。而施蒂默尔则抛出了“地理中间位置免除战争责任论”,认为德国的特殊道路是由它在“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所导致的。②Rudolf Augstein(hrgs.),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e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S.38.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哈根·舒尔茨 (Hagen Schultz)等人的认同。③H.Boockmann,H.Schulze,M.Stuermer(hrgs.)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Berlin:W.J.Siedler,1992.维勒批评它为“中间位置神学”。
必须承认,随着论战的白热化,学者间的辩论更像是一场政治争吵而非学术讨论,越来越失去了六十年代“费舍尔辩论”时的历史实证性。而诺尔特的某些观点也令人匪夷所思,比如他认为犹太人自己参与设计了“古拉格”,因为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就是犹太人,照此逻辑,犹太人也要为奥斯维辛承担责任。又比如,他说必须重新认识波兰和英国,因为是波兰政府在外交谈判中的僵化,不愿意将但泽归还德国,建立交通“走廊”,才导致希特勒入侵,否则德国原本是要与波兰结盟对付苏联的。
自由左派担心“民族神话叙事”会卷土重来,它的确有重新活跃的迹象。赫尔穆特·科尔此时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个具有民族历史意识的政治家,试图将由自由左翼掌控的文化政治转向保守。作为科尔的政治顾问,施蒂默尔在《无历史国度的历史》一书中再度提出“德国历史意识”的问题,他指出,战后以来的德国历史研究模糊了民族认同问题。阿登纳使西德融入了西方阵营,但却使德国的历史形象多样化了,出现了错误导向。因此,他呼吁回归传统文化,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谁塑造记忆、定义概念、解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④Rudolf Augstein(hrgs.),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eartigk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vernichtung,S.36.
不过,左派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维勒断言,“我们赢了”。⑤“Wir haben gewonnen”.在民族认同的问题上,该派坚持让西德的爱国者们继续信奉普世价值和宪法原则,拥抱西方而不是原始、质朴的民族感情。哈贝马斯说:“唯一不会让我们脱离西方的爱国主义,只能是宪法爱国主义。”⑥[德]扬-维尔纳·米勒 (Jan-Werner Mueller)著,马俊、谢青译:《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所以,德国历史越是具有特殊性,从历史的教训来看,民族统一也就越应该成为禁区。
四
1989年之前,历史学家们在争论纳粹历史与国家认同时,似乎早已把民族统一问题遗忘了。左派关心从“特殊道路”到“后民族认同”的叙事路径,而即使是反对历史连续性的保守派眼光也只盯着西德。然而,柏林墙突然倒塌,德国统一了。在冷战结束后新的政治现实面前,无论左与右,历史学家们都需要重新调整对历史的认同方式。“戈德哈根辩论”(Goldhagen-Debatte)就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发生了。
1996年,哈佛大学年轻学者丹尼尔·戈德哈根出版《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⑦Daniel J.Goldhagen,Hilt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Vintage Books,1996.,《时代》杂志专栏作家伏尔克·乌尔里希以一篇《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部书挑起一场新的历史学家论争》⑧Volker Ulrich,Hilter’s willige Mordgesellen,Ein Buch provoziert einen neuen Historikerstreit,Die Zeit,12.April,1996.的评论文章,点燃了这场世纪末的大辩论。与以往的争论不同,此次论争的最大参与者是公众,他们是戈德哈根著作的喝彩者,而专业历史学家们则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矛头对准了戈氏。
在书中,戈德哈根以101预备警察大队这样一个微小而普通的团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解剖他们在执行屠杀时的心理和行为,推导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极端反犹立场,认为酿成大屠杀悲剧的根源在于德意志的历史和文化。从学术角度看,戈德哈根的著述存在漏洞,被指资料不足,对资料文本的模糊性语言不能充分解读;缺乏历史性,推论过于简单,也无太多新意。①Hans Mommsen,Einleitung,In:Norman G.Finkelstein,Ruth Bettina Birn,Ein Nation auf dem Pruefstand,Die Goldhagen-These und die historische Wahrheit,Berlin:Classen,1998,S.9-22.但重要的是它否定了作为史学正统的“批判学派”的结构分析模式,重新强调个人意志的重要性。在德文版序言中,作者公开承认,“我将把种族灭绝的研究重点,从研究非人格的制度、抽象的构造转向研究犯罪者自己——犯罪的个人以及产生这些男女的社会方面去”。②Daniel Goldhagen,Hilters willige Vollstrecke.Ganz gewoe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Berlin:Goldmann,1996,S.4.但是,这样一本普遍不被史学界看好的书为什么能在非历史专业的人群中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应呢?这个矛盾揭示了一个长期存在但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德国人与大屠杀形成的认同关系中缺乏历史化”③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80页。。
“历史化”(Historisierung)的概念是由马丁·布若斯查特首次提出的。在“为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辩护词”中,他指出:现有的历史写作不应该将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当作一件特殊的、甚至是德国历史所独有的问题,而是应该将它们放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来考察。④Martin Broszat,Ploedoyer fuer eine Histor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Merkur 39,(1985):373-385.确实,长期以来,德国史学界将纳粹历史从一般的德国历史中抽离出来,对它进行道德审视,这在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普通德国人中形成了对父辈历史的隔膜感,好像他们与历史上的作恶者之间是“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不过,随着代际更替、纳粹统治时期的远去,德国人可以积极地正视自己历史的可能性在加大。在公开讨论的“欢庆”场面中,公众越来越多地将作恶者坦然称为“我们”,以此来弥合德国人与其祖辈、父辈间的精神裂缝。莱因哈特·科赛莱克 (Reinhart Koselleck)说:“作为德国人,我不可避免地站在作案人一边,……如果我想要植根于我的国家的话,那么我必须使自己渗入到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历史中。”⑤Reinhart Koselleck,Vier Minuten fuer die Ewigkeit,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9.Januar 1997.转引自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187页,注释第35。在纳粹历史的“历史化”进程中,高举着的道德惩戒棒落下了。戈德哈根直指人性的研究方法、寻找作恶者的努力触动了普通德国民众的心灵,对纳粹及其行为的研究不只是在“冷酷”的结构框架下,还应该在更为微观的历史细节中展开。实际上,布若斯查特本人在80年代就提倡考察第三帝国的日常生活,以代替空泛的道德谴责。
历史叙事模式再度发生改变。一连串的纪念馆和纪念碑拔地而起,如1991年重新修葺开放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92年柏林万湖别墅纪念馆、1995年“恐怖之地”战争纪念馆、以及1997年完工、1999年开放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更重要的是争论长达12年之久、最终建成和开放于2005年的柏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此外,各种类型的纳粹罪行展览,其中包括1995年的“武装部队罪行展览”;大规模的“绊脚石”运动⑥20世纪90年代德国民间发起的纪念运动,将篆刻了纪念文字的黄铜板铺在纳粹受害者的住地和工作场所的地面。截至今年年初,已铺设了5万多块,被称为世界最大规模的非集中式纪念碑。以及大量的电影、电视纪录片、报纸等公共媒体的渲染,在德国兴起了一股以纳粹主义和大屠杀为中心的“纪念/记忆潮”,大屠杀从专业历史学家的历史撰述变成了普通民众“活生生的历史记忆”。叙事模式多样化了,历史认识的主体、认知方式和传播媒介都发生了变化,实在性的历史被赋予了后现代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纳粹历史变成了作恶者、批判者和观众——所有普通德国人历史经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统一后新的民族认同形成了。著名史家海因里希·温克勒 (Heinrich A.Winkler)说:“世上存在一些棘手的国家,德国就是其中一个,而她正是我的祖国。”①参见2015年5月8日,海因里希·温克勒在联邦议会进行的主题演讲。无论爱与恨、对与错、是与非,历史民族的血脉是相融的、永恒的。
五
然而,当民族实现“正常化”、纳粹历史被“历史化”之后,不同版本的历史“修正派”也现身了。有些是八十年代论战主题的延续,有些则是新形势下的历史表达。列举如下:
首先,塑造自己受害者的形象。2002年,约格·弗里德里希 (Joerg Friedrich)出版《大火:1940-1945年炸弹战争中的德国》②Joerg Friedrich,Der Brand,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Muenchen:Propylaeen,2002.一书,引发争议。作者认为,盟军在1944年后对德国城市的狂轰滥炸是丧失人性的军事行动。这一场所谓的“炸弹战争”堪比奥斯维辛的火葬场和希特勒的焚书行动。汉斯-U.维勒提出反驳说,此书缺乏专业水准,是“令人乏味的重复”,作者明显是“感情用事”。③Lothar Kettensacker,Ein Volk von Opfern?Die neue Debatte um den Bombenkrieg,1940-1945,Berlin:Rowohlt,2003,S.140-144.
其次,关注犹太人之外的其他受害者群体。有学者提出广义的“大屠杀”概念,即除了犹太人,大屠杀受害者还应该包括欧洲的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障碍者、欧洲东线的苏联战俘、德国国内的异议人士以及战后被驱逐和逃离的东部地区德意志人。④参见 James Bacque,Crimes and Mercies:the Fate of German Civilians Under Allied Occupation 1944-1950,London:Warner Books,1998.
对不同受害者的关注是世纪末的潮流。它暗示着所有形式的集体受难从本质上说是相似的,甚至是毫无差异的,都可以被纳入德国重建自身认同的一部分。但它也因此产生了新的问题:受害者范围的扩大会不会客观上造成对犹太人大屠杀意义的减弱和相对化?
第三,对纳粹统治的新评价。新右翼学者如E.耶瑟 (E.Jesse)、R.齐特尔曼 (R.Zitelmann)、K.维斯曼 (K.Weissmann)等主张唤起民族自我意识,以“文化革命战略”推动大国政策。为此,主张历史学应克服过去,纳粹历史需要重新修正。齐特尔曼主编的论文集《过去的阴影:民族社会主义历史化的冲动》,提出纳粹主义不仅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希特勒政权在许多领域实施了以机会均等为目标的进步的社会政策。而维斯曼的《走向深渊: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1933-1945》⑤Karlheinz Weissmann,Der Weg in den Abgrund:Deutschland unter Hilter von 1933-1945,Berlin:Propylaeen,1995.干脆把纳粹政权称为制造了经济奇迹、解决了失业问题、提高了妇女地位的“社会国家”。
最后,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比较研究在当今德国史学界被普遍认可,它甚至是大学中讨论课的固定话题,这一现象发人深省。在诺尔特之后,1992年,盖斯的文章“世界历史中的大屠杀:人性的边界”⑥Imanuel Geiss,Massaker in der Weltgeschichte,Ein Versuch ueber Grenzen der Menschlichkeit,in:Eckhard Jesse,Uwe Backes,Ranier Zitelmann(hrgs.),Di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Impulse zur Historisierung des Nationalismus,Frankfurt/M:Propylaeen,1992.,就将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的大屠杀与斯大林的杀戮及第三世界的后殖民屠杀,笼统置于“集权主义的理论模式”下进行比较研究。2012年,洪堡大学东欧史家约格·巴伯罗夫斯基(Joerg Baberowski)出版新作《烧焦的土地:斯大林的暴力统治》⑦Joerg Baberowski,Verbrannte Erde,Stalins Herrschaft der Gewalt,Muenchen:C.H.Beck,2012.,利用俄文档案,揭秘斯大林及其“帮凶”的残忍,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一样,都采用了工业谋杀。巴氏断言:希特勒了解俄国内战和斯大林主义,自然不会不受其影响。此书获得了当年度莱比锡书展大奖,这一结果确实令人感到意外。
21世纪,德国的民族认同无疑将步入新阶段,它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德国在欧盟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不可否认,坚定地与欧盟站在一起,开拓欧洲认同的新视野,与欧洲以外的、非欧洲的或者说是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做严格的区分也将成为今后德国人欧洲认同的一部分。伊曼纽尔·盖斯在“欧洲认同”一文中便明确反对东正教的俄罗斯和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入盟。①Imanuel Geiss,Europas Identitaet,In:Universitts,59,(2004):1045-1052.
作为中年一代历史学家的代表,海德堡大学53岁的教授埃德加·沃尔夫隆②沃尔夫隆于2013年出版了专著《红绿执政》 (E.Wolfrum,Rot-Gruen an der Macht:Deutschland 1998-2005,Muenchen:C.H.Beck,2013.)该书借助档案资料,在20-21世纪的宏大历史背景下,研究1998-2005年间的德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Edgar Wolfrum)指出,“德国历史只是世界历史中很小的一部分,铁幕的落下、中国的开放、印度和巴西重要性的突显,以及其他历史领域的开放,诸如此类,大屠杀将不再是一切的中心。”③Dirk Kurbjuwei,t“Der Wandel der Vergangenheit”,Der Spiegel,Nr.7,(2014):117.而老一代学者如于尔根·科卡 (Juergen Kocka)则强调指出:1945年的德国历史已经归零,或者说已经终结。今后将不再会有德国和西方问题,而是如何处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问题。④2015年5月18日,于尔根·科卡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为“未来和历史学家”。两代学者达成了共识,右派左派形成一致:德国“特殊道路”的提法——无论是作为特殊成就还是悲剧性遗产——都已经过时了。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历史学是开放的,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出现,在承认纳粹罪行的基本前提下,纳粹史在未来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修正。